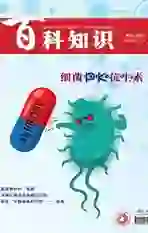“家常”又“讲究”的北京炸酱面
2020-06-01丹若
丹若
北方人喜好面食,但如果北京人说“今天吃面”,那说的就是—面条。面条有许多种,北京人首选的肯定是“炸酱面”。
作为北京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张名片,“炸酱面”常常被冠以“北京”二字。在北京街巷的面馆牌匾上,“北京炸酱面”前还会用个“老”字作前缀,外地人进门来,往往会被“小碗干炸”“七碟八碗儿”一类的“术语”弄得不明所以。虽是一碗炸酱面,但一家一店又不尽相同,让人觉得既很“家常”又颇“讲究”。
炸酱面的历史源头
关于炸酱面的由来至少有三个传说,都和皇家有关。
传说一:清朝奠基者努尔哈赤早年征战时,由于总是行军打仗,士兵盐分补充不足。为避免战斗力降低,努尔哈赤提出“以酱代菜”,每逢驻扎就在当地征购豆酱,然后晒成酱坯让士兵带在身上。野外用餐时,把酱坯用水泡开,采来野菜蘸着吃。清军入关后,这种饮食习惯被带入宫中,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也纷纷效仿自制酱料,各出奇招,逐渐演变出了炸酱和炸酱面。
传说二:光绪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至西安,走到城内南大街时,舟车劳顿令一行人疲惫不堪。此时,一阵香味扑鼻而来,总管李莲英抬头一看,是家炸酱面馆。众人进了面馆,每人来了一碗素酱面。没想到,慈禧太后意犹未尽:“味道真好,再来一碗!”后来,慈禧太后嘱咐李莲英把做炸酱面的人带回紫禁城,从此炸酱面就在北京落户了。
传说三:秦始皇东巡芝罘岛经过福山,听说福山的面好吃便要品尝。厨师切好肉和菜准备做卤,慌乱之中有人竟将肉和菜放在锅里一起炒了,还加了一大勺酱。没办法,厨师只得把用肉菜酱炒好的“卤”浇到煮好的面条上,忐忑不安地端了上去。秦始皇一见面条油亮、酱香扑鼻,立时胃口大开,连声称好,问厨师:“这是什么面?”厨师随口回道:“炸酱面。”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碗炸酱面的故事里浸润了封建制的起始和消亡。不过,炸酱面源于清朝似乎更可信,因为大豆酱的做法产生于汉代,东汉也已出现面条的雏形,北魏时用大豆发酵制酱的方法已很普及。秦始皇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虽也有酱,但那是用肉制成的酱,称为醢(hǎi)。这样看来,炸酱面和“大清”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
有学者考证,炸酱面从历史源头上说是京城满族文化的作品。清末,大多数八旗子弟家道中落,飲食上也难再讲究。但是为了维持排场,在吃面的时候要放上酱,酱还要用油炸一下,既好看又美味。然后拌入时令蔬菜,这样显得样式不单一,吃起来也别致爽口。这便是炸酱面的由来。
炸酱面的基础:面里有乾坤
炸酱面不仅是老北京的百姓当家饭,而且是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如果有人问地道的北京炸酱面怎么做?这还真不好说,因为,即便是普通百姓家中也有自己的“独门秘方”。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炸酱面无外乎三个步骤:制面、炸酱、备面码儿。
真正“讲究”的炸酱面的“面”是擀出来的。现如今北京人吃的“面”多是“买”回来的“切面”。手擀面对制作人的要求并不高,一要有力气,二要有耐心,但擀面却是一门精细的手艺。首先和面要注意比例。将水慢慢倒入面粉中,边倒边搅,将面粉中的2/3和成絮状粉团后就不能再轻易加水了,这时要用力将面粉撮合成团,把絮状的面粉用力揉成光滑的面团。
擀面同样需要力气和耐心。先在案板上铺上干面粉,边擀边延展,每次卷擀展开后要将面皮旋转45°或90°再次卷擀,这样才能保持面皮的厚薄均匀。一般擀到面皮厚度在 0.3厘米左右。将擀好的面叠成Z字型,边叠边放入干面粉或玉米粉以免粘连,然后均匀地将面切成3、4毫米的条。
接下来就是煮面了。这里有个很“讲究”的细节:煮面之前,要将生面条用凉水冲洗一下,目的是洗去面条表面的干粉,以免煮面时面汤过稠糊锅。煮面的水要多,行话叫“宽汤”,这样面入锅时才不易粘连。一碗好面煮熟了要透亮,口感柔韧,滑爽筋道,“糟面条子”是配不上炸酱面的。
过去大户人家吃炸酱面讲究抻面,但没个三两年功夫还真抻不出地道的面,所以后来手擀面受到了追捧,其技术含量一般人都能掌握,亦不需像面馆那样技艺精湛。不会擀面直接从超市买回切面,没问题,北京人也常这么做,毕竟省时省事。
炸酱面的灵魂:就是那碗酱
炸酱面好吃,关键在于酱。地道又讲究的老北京炸酱面的精髓都在酱上,用料和制作都不一般,可不是单纯的“炸黄酱”。

老北京人炸酱要准备黄酱和甜面酱两种酱,按比例混合后加水调和。将肥瘦兼有的五花肉切成1厘米见方的小丁。锅中放油,下肉丁,炒出油后倒入酱,小火慢熬,不停搅拌,当肉和酱水乳交融时,香喷喷的炸酱才算做好了。
北京人买酱认字号,炸酱必选六必居的干黄酱和天源酱园的甜面酱,因为这两种酱的黄豆质量好,且做酱时加的是白面而不是玉米面,这样的酱炸好后凉了也不会发坨。一般两者比例为3∶1,咸甜搭配起来的口感十分柔和。
从烹饪的角度说,“炸”酱其实应该称为“炒”酱。“炸”是油多食材少,“炒”是油少食材多。但为什么还叫“炸酱”呢?重点在“炸”字上,老北京人称炸酱为“小碗干炸”。所谓“小碗”,就是一次制作的量不能太多。发酵制品总带有特殊气味,非得高温才能除去,香味也才能浓厚醇美。酱太多,锅里的温度上不去,香味散不出来。量少,小火慢熬,中间还不能加水,即所谓“干炸”,慢慢地把酱炸透,让酱香与油香慢慢融合,并充分释放。这样制成的酱呈半凝固状,表面有较多油脂,黏稠泛光,肉丁亮中透红,香气扑鼻。“小碗干炸”还有个标准:炸好的酱放在碗里,用筷子从中间划开,缝隙不粘合,这才是一碗好酱。
北京人炸酱可以发挥无限想象,并不仅局限于黄酱、甜面酱和五花肉。比如,北京有家著名的炸酱面馆海碗居就是用三份六必居稀黄酱配六份六必居干黄酱。家庭制作中更富有创造性,有放高汤的,有炒好后放鸡蛋的,有以羊肉末代替五花肉的,有放海米、香菇丁、茄子丁、青笋丁、豆腐干丁的,既能中和口感,又能丰富营养。甚至还有人加进点威士忌,浓浓酱香中飘出淡淡酒香。
炸酱面的华彩:七碟八碗儿是面码儿
老北京人吃炸酱面,要根据季节佐以各种时鲜小菜,谓之“全面码儿”。这面码儿配料还有一个顺口溜—
“青豆嘴儿、香椿芽儿,焯韭菜切成段儿;
芹菜末儿、莴笋片儿,狗牙蒜掰两瓣儿;
豆芽菜去掉根儿,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要切细丝儿;
心里美,切几批儿,焯豇豆剁碎丁儿,小水萝卜带绿缨儿;
辣椒麻油淋一点儿,芥末泼到辣鼻眼儿;
炸酱面虽只一小碗,七碟八碗儿是面码儿。”
面码儿是一碗炸酱面的出彩之处,单这顺口溜的京腔京味就已醉人了。当然,这里的“七碟八碗儿”并不是说真有那么多碗碟,而是形容面码儿之多、种类之丰。北京人讲究“不时不食”,当季产什么青菜就用什么做面码儿,吃的就是个节气劲儿。比如,初春最宜选豆芽菜、萝卜缨,春末配香椿芽、青蒜最够味,夏天用得最多的是黄瓜丝,冬天则少不了水焯的大白菜。
此外,吃炸酱面时,蒜是不可少的,大蒜的刺激辛香与浓郁酱香相得益彰,北京人说“吃面不吃蒜,不如吃米饭”。还有人喜欢加些醋,既能调味增香,又能杀菌消毒。尤其是初春时节,家中还有剩余的腊八蒜,倒点腊八醋,放两瓣儿翠绿的腊八蒜,直吃得人心里美滋滋。

面条是一个绝好的食物载体,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有很好的相容性,无论是形体还是味道,都可以和别的食物相容相配,再加上独特的炸酱,一碗极其“家常”的面条就有了既可以尽情发挥又万变不离其宗的“讲究”。
若到正宗的老北京面馆吃炸酱面,看服务员上面也属“餐”的一部分。服务员会旋着手腕把8个小碟子一下“甩”进大圆托盘中,将各色面码儿放入其中,围绕着中间的大碗面条,三寸墩子碗儿的炸酱一人一碗。托盘端上桌,征得客人同意后,服务员便会娴熟麻利地把蔬菜和炸酱倒入面中,碟子“叮”地一磕碗沿儿,发出清脆的碰瓷声。这便是享受的炸酱面特有的“派头”。
或许有人说,北京人吃个面也这么讲究。其实,正是这种有“范儿”的摆谱成就了炸酱面的食趣,也让炸酱面成为北京的传统名食。
流淌在文字中的酱香滋味
虽然很多地方都有炸酱面,但为什么北京的炸酱面影响最大?除了北京人的“讲究”,还离不开文人的传播。文人墨客的笔下,从来不乏对“北京炸酱面”的描写。
著名作家梁实秋是一位尝遍山珍海味的老餮,但他最爱的一口还是炸酱面,因为“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他在《面条》中讲过一个神奇的故事:“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可救药,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病霍然而愈。”所以,梁实秋说炸酱面有起死回生之效!
民国时期,很多文化人在北京创办过文化沙龙,后离散到各地,对北京美食甚是怀念。比如珍妃的堂侄孙唐鲁孙自幼出入宫廷,对老北京传统、风俗等了如指掌。1946年到台湾后念念不忘炸酱面,不仅自己做,还创造出很多新的吃法,比如加入金钩海米和鸡蛋,用关东卤虾炸酱等。这些鲜美温淳的炸酱在唐鲁孙的笔下被描绘得出神入化,看的人忍不住吞咽口水。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最喜欢的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附带小米粥。炸酱面经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比如《茶馆》里:“老掌柜,您硬朗啊?”“嗯!要有炸酱面的话,我还能吃三大碗呢,可惜没有……”《四世同堂》里,常二爷一进门,祁老太爷就吩咐儿媳妇:“赶紧做四大碗炸酱面!”
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顶喜欢的三种北京吃食是炸灌肠、葱花饼、炸酱面。他在《北京城杂忆》中说:“比如我爱吃炸酱面,可怎么我也犯不着去纽约吃炸酱面,不管他们做得怎么地道—还能地道过家里的?”
著名作家刘心武也有一篇《炸酱面》:“在旧金山的唐人街,也曾巴巴地寻到一家卖炸酱面的中国餐馆,搓着手咂着舌要了—碗炸酱面。但端来以后,看不中看,吃不中吃,总觉得是赝品。的确,炸酱面这类家常便饭,必得由家里做、在家里吃,才口里口外都对味儿。所以炸酱面里实际上又凝聚着—种家庭之美,亲情之美。”
当众口难调不知吃啥才好时,炸酱面是最没有异议的。北京人对炸酱面的喜爱和惦记是埋在心底的。一碗炸酱面,实在家常,但煮熟了的面条盘在碗里透着白亮气派,看似软实则硬的韧劲儿像极了北京人“外圆内方”的性格:表面随意,心中有数,该讲究的时候,对人对事绝不含糊。一碗炸酱面,简简单单,又盛着满满的人间烟火,就像人生,从一碗白面条开始,不断加入调料,于是日渐丰富和精彩。
一碗炸醬面,味在面中,更在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