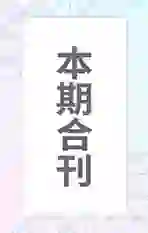陈之藩,尖端科学界的散文家
2020-05-27徐学

徐学

陈之藩
上世纪70年代,余光中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那时,港中大人才荟萃、风流云集,余光中与港中大7位教师过从甚密,一起度过近10年逍遥时光,他们被后人称为“沙田七友”。余光中晚年对港中大同事甚是怀念,每逢小聚,总会说起,我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那些友人的音容笑貌和出众才华。其中,陈之藩让我印象深刻。他居港中大7年,宿舍就在余家楼下,两家来往,只需走18级楼梯。陈之藩夫妇厨艺自成一格,余夫人常下楼去,跟陈夫人学烤烙饼、包饺子。
陈之藩在文学上专营散文,散文又是我最喜爱的文类,他早已成为我最喜爱的散文家之一。虽然未曾谋面,我却熟读过他的许多作品,也可算是神交。
感性的人都有好舌头
陈之藩本科学的是电子机械,硕士读的是电子系,曾任美国波士顿大学应用科学系教授,港中大和台湾成功大学理科教授,兼任英国电子机械学会院士。他一生发表百篇科学论文,写了十来种科学译著专著,研究领域从电子软件到人工智能,均属前沿尖端科学。虽是科学家,他却极力推崇性灵。在港中大演讲时,他对学生说:“比较一下科学描述的世界和我们感到的真实世界,就可以知道科学的可怜了。对于人的心灵,科学似乎并无所知。”这是他一以贯之的理念。
从少年时期,他就能跳出理工科思维,呼吸人文的空气,广交作家文人。大学时期,他给胡适写信,探讨辨析文化观念,一来一往,共写了13封。1948年,他被学校分配到台湾担任工程师,不久见到了胡适。1955年,他又受胡适资助到美国念理学硕士。在美期间,每逢暑假,他总去找胡适,感受学人风范,汲取人文方法。因为长时间耳濡目染,以至他遇到社会问题时,常常会自问:“不知适之先生对此会怎么想?”胡适去世后,他写了许多文章追念,痛惜中也有反思。他说:“我和胡先生是朋友吗?又不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改变了我的命运。”
“不是太谈得来”,主要是因为他和胡适有着不尽相同的文学创作观,胡适作文喜欢使用清楚明白的口语、考据式的论据和科学的说理。而陈之藩却向往感性奔放的文风和潇洒的修辞,不走清淡简洁一路。他更接近朱自清,引诗入文、字雕句酌,草木人事莫不有情。但胡适那爱国的操守与澄明的见解却化为陈之藩散文中的高贵和风骨,所谓“新道德中的旧伦理”。
陈之藩喜欢感性充沛、温柔细腻的散文,他常买来散文集分赠给朋友。感性的人都有好舌头,陈之藩也不例外,分享美文之余,也分享美味。在香港,他时常逶逶然从城里大包小盒地拎着糕点回校,余光中说他“总要隆而重之、夸而张之地再三推荐,唯恐朋友印象不深,且又以身作则,啖之咽咽,味之津津”。在台湾,他也广发邀请函请同仁共聚餐館,共享他发现的美味。
不甘失根每寻根
赴美期间,陈之藩应台湾《自由中国》杂志之请撰写专栏,其中1955年发表的《失根的兰花》流传最广。文中写古人画兰,有一兰花连根带叶都离土飘于空中,寓意“国土沦亡,根着何处”。他说:“国就是土,没有土的人,是没有根的草。”那我们的根在哪?陈之藩告诉我们,根是夏夜里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崇山峻岭中的竹篱茅舍,是祖宗的静肃墓庐,是可吟可咏的诗词……在反攻文学大行其道之时,他把乡愁写得古朴有意趣,让读者耳目一新。作家张晓风说,陈之藩不写肤浅的爱国文学,他每每从千古文化的角度来思索中国。他的散文善于活用古典,比如这样的句子:“魔鬼是什么?是以‘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慨叹,来掩饰自己的懒惰;是以‘天地逆旅,百代过客的诠释,来解嘲自己的苟安;是以淡泊明志作为学而优则仕的准备;是以滔滔皆是作为自甘沉沦的遁辞。”
1957年,陈之藩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以后源源不绝,皆风行一时,内地和港台各有多种版本,其中多篇散文被收入内地和台湾、香港的中学语文教材。台湾《国文天地》杂志在学生中做主题为“你最喜欢的课文”调查,陈之藩的《失根的兰花》名列前茅。一个作家在作品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象,几乎等于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陈之藩令人难忘的意象就是失根的兰花。
陈之藩自1977年起任港中大电子工程学系主任。港中大依山面海自成天地,没有一条路不随山势回环,没有一扇窗不开向澄碧。陈之藩大为动容,说:“要知道这么美,早就来了。我去过各国名校,论校舍,中大平平,论校园,中大却是一流的。”他曾借白居易诗赞美港中大校园——“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他在沙田住了7年,走时依依不舍,是因为海涛松姿,更因为是在这里找到了认同的文化。他在文章里说,香港是“保存中国传统最多的地方”,在年节和红白事上,也在方块文章里。香港让他最开心的是有许多会做律诗的朋友。

陈之藩写给胡适的信。

1978年,陈之藩(前排右一)在香港与文友杨世彭(后排右一)、余光中(后排右二)、刘国松(后排左二)等餐叙。
“像堂·吉诃德不甘心地提起矛,我也屡次荒唐可笑又可悯地提起笔。我想用自己的血肉与砂石相摩,蚌的梦想是一团圆润地回应八方的珠光。”
那时,港中大初创,同仁大都是在内地度过青春的漂泊者,他们如因风四散的蒲公英,落在海岛相濡以沫。他们方言不同、口音各异,却无一例外地喜好中国古诗古文,文言成为游子的共同爱好。多年后,陈之藩还记得同事的诗,“万变犹余此海隈,不然无地着吾哀”,他则以王国维的“客里欢娱和睡减,年来哀乐与词增。窗外薄阴飞日暮,池边吟思与花开”对答,两句古诗便一见如故,隔阂尽去,其乐融融。2002年,他又回到港中大,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十年。
陈之藩曾在香港自擬对联:“不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安心即是家。”是的,人要在外四处漂流,最后方能登堂入室;旅客遍叩陌生之门,最后才能寻得家门!
散步像是在做梦
陈之藩不是多产作家,他常常对朋友说起自己的各种见闻,那都是很好的散文,但他并不愿就写成文章发表,余光中曾戏言,陈之藩真是世界上最懒的散文家。
余光中曾这样勾勒陈之藩在港中大任教时的身影:“之藩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直是魏晋名士。山路之上经常见到一位穿浅咖啡色西服的中年教授,神思恍惚,步伐迟缓,踽踽然独行而来,独行而去。我在路上遇到他,十有六七他见不到我。”
散步是陈之藩唯一坚持多年的运动和休闲。他在自己文集的序言里说,“我觉得这本小书如一堆蓝色的影子,在月光下恍动……我自信这是些忠实的东西。在但有风雨至,不见故人来的黄昏,我的书可以是陪伴读者的谈天散步的伙伴。”

陈之藩散文集《散步》。
78岁那年,他出版了最后一本散文集,把它命名为《散步》,不但因为这是他晚年与妻子散步闲聊的记载,还因为其中有许多跳跃式的思考,轻盈洒脱。他说:“最痛快的是一边散步一边说诗,这样散步,不觉得是散步,倒像是在做梦,在梦中说诗。”我曾经把“闲闲着笔,缓缓为之,絮絮私语”的美学姿态命名为“散步的境界”。说到境界,人们常常将它与诗、与舞、与飞翔和美酒相联,很少人会想到散步也会有境界。散步,不就是那些大腹便便者带着计步器,在马路上东逛逛西瞧瞧地消磨时光吗?非也。美学家宗白华在《美学的散步》前言中说:“散步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文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哲学家庄子,他好象整天在山野里散步,观看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翻阅陈之藩散文时,我常会想起宗白华描述的庄子;想到定时散步的哲学家康德,想到乘兴出游的孔夫子,“逝者如斯夫”,应是夫子河边散步灵光一现的感悟。
陈之藩一生动荡不安,但总能带着对真的好奇,美的欣赏,善的向往闲庭信步般地优游于大千世界。他说:“像堂·吉诃德不甘心地提起矛,我也屡次荒唐可笑又可悯地提起笔。我想用自己的血肉与砂石相摩,蚌的梦想是一团圆润地回应八方的珠光。”他是一位散文思想家,文章有精微的辨析、敏锐透彻的见识和玲珑慧心的观照,科学的思辨化为敏锐的感受,让读者在如沐春风里获益。他说,“罗素上千页的数学原理,60年代的计算机五分钟就解决了,可他的散文至今清澈如水,在人类迷惑丛林的一角,幽光闪闪。”陈之藩的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
陈之藩(1925年—2012年)河北霸县人,北洋大学电子机械系毕业,剑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休斯敦大学、波士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著有《系统导论》《人工智慧语言》等科学论著,以及《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失根的兰花》等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