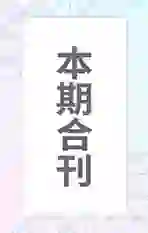流行病危机中的美国总统
2020-05-27田亮
田亮

乔治·华盛顿,1789年4月至1797年3月任美国首任总统。
2016年,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前不久,美国《科学》杂志发文称,新总统应准备上好6堂科学课。第一堂课就是“危险的进化——病原体的变化快于我们的防御”。文中写道:“病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会在人类、家畜、野生动物、树木和农作物中引起疾病,与它们的寄主进行攻防竞赛。不幸的是,它们总是处于上风,能够进化出回避或突破寄主防御的能力,潜在地成为致命的超级病菌。美国要为严峻的传染病甚至全球流行病问题做好准备。疾病无国界,因此要做好国际合作。”
可如今,特朗普口中的这场“大号流感”“新冠流感”,已经让美国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累计确诊量约占全球总数的30%。美国立国以来经历过数次重大的疫情,给时任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体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而今天的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仍然重蹈覆辙。
开国总统回老家6个星期躲避黄热病
1793年夏天,在美国宣布独立17年后,当时的首都费城,有一位著名的医生,也是《独立宣言》56位签署人之一的本杰明·拉什发现了“异常数量的头痛发烧病例,伴有不常见恶性症状”,患者的眼睛与皮肤变黄,许多人在染病后几天内就死于内出血。拉什认为,这是“胆汁过多黄热病”。
关于黄热病的病因,当时的医学界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病由商船自海外输入,主张对往来商船延长检疫期,禁止疫区船只靠岸;以拉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病是由城市肮脏环境所产生的瘴气所致,主张改善费城的环境卫生。
围绕黄热病的争议,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以开国元勋、时任亦是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主张工商立国,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美国必须发展和保护本国工商业,应对海外商船实施严格检疫制度。而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等民主共和党人则主张农业立国,要建立由自由农民构成的民主国家,大力发展农业,避免走西欧工商业、大城市的老路,认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是瘟疫横行的温床,所以极力宣扬黄热病的城市环境起源说。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的分野,是后来美国两党政治的雏形;他们在疫情上的各执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民主党州、共和党州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行其是。(美国联邦党于1815年瓦解,民主共和党于1825年分裂,先后形成共和党、民主党)
回到1793年,面对疫情造成的恶劣局面,当时美国政客还出有一个恶劣行为:将黄热病的暴发甩锅给黑人。有美国出版商宣称,是肮脏的黑人造成这场黄热病疫情。近日,曾在美国天普大学任教多年的公共卫生史专家莫里斯·沃格尔接受采访说:“1793年黄热病对今天我们最大的启发就是:政党想利用疫情获得支持。今天,还是有人只会指责外人,而不采取有效行动,有政治领导人会指责一个群体是导致问题的罪魁祸首,哪怕他们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公民,这种危险的做法会加剧仇外情绪。”这是黄热病留给美国的第一个政治烙印。
时任美国总统华盛顿是个温和的中间派,一向注重在汉密尔顿、杰斐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党派纷争。当时,法国正在经历大革命,英国等欧洲国家组成反法同盟,欧洲战火正浓。美国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刚刚成立共和国、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华盛顿则主张在危机时期应当以安全和发展为主,并宣布美国保持中立。亲法的杰斐逊和很多费城人反对华盛顿的做法。后来出任第二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曾回忆:“1万人日复一日地挤在街上,威胁说要把华盛顿拽出其房屋,在政府中发动一场革命,或强迫其站在法国革命的立场上发动一场战争以对抗英格兰。(此时,)没有什么东西比黄热病更能有效地把美国从一场政府革命中解脱出来。”
疫情成為压倒一切的社会危机。拉什医生在1793年9月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孩子被传染,他们的父母就丢下了他们。(同时)许多人在父母抱怨头痛时就把他们丢到了大街上。”据统计,这场疫情导致费城约5000人死亡,而这座首都当时的总人口约5万人,即每10个费城人就有一个死于黄热病。汉密尔顿也被感染,险些丧命。财政部6位职员患病,邮政部病倒了3位,海关7人病倒。
“黄热病由黄热病病毒引起,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直到现在仍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三大国际检疫传染病之一(其他两种是鼠疫和霍乱)。这个病毒主要由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携带,通过叮咬传播给人。病毒感染人以后引起的主要临床症状就是出血热,损害肝脏,导致黄疸,浑身发黄。当时人们根据临床症状,把它称作黄热病。这个病原产于非洲和南美洲,后来美国兴起黑奴贸易,病毒就随着奴隶船到了美国,从东部向西部、南边向北边扩散,最终美国全境暴发黄热病流行。费城是当时的一个主要疫区。”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程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00年,美国军官沃尔特·里德(俯身者)在古巴调查黄热病疫情。他证实了黄热病通过蚊子传播。
然而,当时人们对疫情的真相并不了解,加上医学界和政界的纷争,费城百姓无所适从,只能逃命。汉密尔顿避城而去,打算前往纽约市避难,却被拒之城外。不得已,他漂泊到纽约州奥尔巴尼市附近的格林布什村,投奔岳父家。然而这里也戒备森严,人们把部长大人夫妇俩的衣服和行装付之一炬,对其侍从和车驾也彻底消毒。9月10日,总统华盛顿也弃首都而去,躲到家乡弗吉尼亚州弗农山庄。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市政府大部分官员在内的约1.7万人逃离费城,许多市民甚至来不及锁好房门便仓皇出逃。华盛顿原计划只离开十几天,所以没有携带官方文件。但随着疫情越来越糟,他一次又一次推迟返回时间,整整6周没有离开过弗农山庄。
黄热病留给美国的第二个政治烙印就是迁都。随着气温降低,蚊子逐渐销声匿迹,疫情在当年11月消逝了。然而,由于人们主动投降,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黄热病疫情在后来又多次袭击美国。1800年4月24日,目睹了黄热病惨状的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在关于迁都华盛顿的法案上签了字。“迁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黄热病疫情在费城得不到有效控制。”程功说:“直到19世纪末,美国军官沃尔特·里德证实了黄热病通过蚊子传播,人们才知道怎样阻断它的暴发。离首都华盛顿不远处的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就是以这位军官的名字命名,特朗普每年到这里例行体检。虽然黄热病疫苗已研究出来了,但传染源是无法消灭的,黄热病病毒直到今天仍存在,在南美洲、非洲丛林中的蚊子和灵长类动物之间传播,随时有可能再入侵人类社会。”
威尔逊把大流感甩锅给西班牙,但自己也被感染了
和华盛顿一样,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是在欧洲战乱之时突然面对流行病的挑战。看起来,威尔逊比华盛顿更幸运——一战和大流感对欧洲强国构成了双重打击,美国借此机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威尔逊在1917年4月2日发表参战演讲。宣战后,美国开始征兵。第二年1月,美国堪萨斯州哈斯科尔县暴发了严重流感。3月,堪萨斯州的弗斯顿军营里发现了第一例病例。两个星期内,1100名军人被送进医院,38人死亡。被感染的官兵又将流感病毒从弗斯顿带到了其他军营,当时美国36个大军营有24个暴发了疫情。
美国向欧洲输送了约200万名远征军,病毒随之到达了欧洲,战场上密集的人群又加速了交叉感染。当年4月,法军有士兵被感染;5月,英国舰队的医生诊治了上万名病患。为避免影响军心,交战国都对疫情避而不谈。6月29日,西班牙卫生部长尴尬地向民众宣布,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并未发现肆虐西班牙的流感病毒。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只不过西班牙是中立国,媒体可以报道传染病,大流感的信息首先在西班牙发布。
大洋彼岸的美国威尔逊政府,考虑的是如何打赢战争,不愿意启动大规模的防疫。为了维持战时士气,美国政府官员主动把疫情叫作“西班牙流感”。这套甩锅术流传至今,堪称大流感留给美国政客的一大“财富”。
1918年9月,费城市政府还在召集20万市民集会为战争募捐。仅三天后,全市31家医院都被病患塞满。仅仅一个月内,费城就有超过1.2万市民死亡。这终于引起官方重视,开始加强隔离,要求市民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等。10月3日晚间,费城市议会下令关闭所有学校、教堂和公共娱乐场所。

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至1921年3月任美国总统。

1918年大流感期间,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美国波士顿军营中制作口罩。

1918年大流感期间,美国旧金山军营内的士兵纷纷挂起床单,相互隔离。
一战导致800万人战死,600万平民死亡。而1918年至1919年大流感的全球流行,造成约5亿人感染,5000万至1亿人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之一。比爾·盖茨旗下的疾病建模团队,曾采用1918年大流感的真实数据,在现代社会中模拟了该病毒传播的过程。结论是,由于今天社会的交通发达程度是1918年的50倍,可能短短300天,全球将被病毒击垮。盖茨警告说:“这是目前为止,能够在一年内杀死1亿人的唯一可能。”
威尔逊也被感染了。1919年初,战胜国的首脑召开巴黎和会,威尔逊带着美国夺取世界霸权的“十四点计划”和国联方案而来。2月,威尔逊的女儿染上了流感。随后第一夫人、第一夫人秘书以及威尔逊的私人医生都病倒了。3月底,威尔逊对妻子说:“谢天谢地我仍可战斗,我会赢的。”4月3日下午傍晚6时,他却“猛然咳嗽起来,频繁而严重的咳嗽使他无法正常呼吸”。白宫医生格雷森给国内拍回电报:“总统昨晚染上重感冒,卧床。”
威尔逊本打算借巴黎和会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通过建立以其为领导的国联实现全球统治。而实际谈判的效果与期望相差较大。生病前,威尔逊扬言,如果要他放弃原则的话,他宁可不签订协议就退出和会,打道回府。生病后,他的秘书写道:“我从没见过总统先生的性格像现在一样别扭。即使他躺在床上,他还是表现得极为古怪。”例如,臆想自己家中满是法国间谍。白宫首席礼宾官欧文·胡佛说:“我们只能猜测他的精神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医学研究表明,大流感存在影响大脑及神经系统、破坏脑细胞的可能性,进而影响到思维活动,干扰判断,还可能导致暂时性精神疾病。1918 年的尸检报告中,经常能看到有关脑部血管损伤的记录。再加上国内的党争分歧和对威尔逊计划的反对,有人认为“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一天,在没有事先知会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之前恪守的原则,对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提出的所有主张都妥协了。妥协的产物就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它对德国的严苛,加速了德国的经济困难、民族躁动等,间接导致二战的发生。
里根厌恶艾滋病,却不得不面对它的大流行
艾滋病是美国历史上又一大规模流行的传染病,以总统里根为首的美国政界再次选择了掩饰、回避和偏见。
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发布《每周发病率及死亡率报告》,记录了卡氏肺囊虫肺炎的发病案例,称这“可能是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这种罕见的肺部感染在洛杉矶的5名年轻男同性恋身上发现。这是第一份关于艾滋病的报告。几周后,另一篇报告报道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和一种非同寻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这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纽约时报》发表题为《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的文章。《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一文。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

罗纳德·里根,1981年1月至1989年1月任美国总统。
时任总统里根的高级别政策制定者,在整个1981年和1982年都没有对此疾病做出任何评论。1982年9月,CDC正式命名此疾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中文简称“艾滋病”)。一个月后,里根的新闻秘书被问及总统是否对于“艾滋病现在是一项流行病”有任何反应,发言人冷淡反问:“什么是艾滋病?”记者回答“这被认为是一种男同瘟疫”,并补充道:“我是指,这是一种特别严重的病,每三个得这病的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发言人说:“我没得这病。你得了吗?”当被问及白宫是否了解这病时,发言人说:“我认为没有。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得过这病。”这是在公开场合,白宫第一次对这个神秘流行病的表态。
随着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人们发现,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和异性恋男女等更多人群开始患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艾滋病虽起源于非洲,但在美国被最先发现,要不然世界可能知道得更晚。但艾滋病的潜伏期不像急性传染病只有几天或一两周,而是长达8到10年。有了多年的感染人群积累之后,大量感染者才开始发病,也就是把一个慢性病在温箱里培育了多年,这就造成了它能产生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急性传染病的致病力度。艾滋病被发现后,美国每年有几万人死亡,持续了约15年,达到每年死亡5万人的峰值。随后由于抗病毒药物的突破,年死亡人数大幅降至1万左右。存活的感染者则持续升高到120多万。”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后,一些民间组织呼吁维护患者权利。图为美国某民间组织发起集会,要求尽快批准艾滋病治疗药物。
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艾滋病政策协调员的格里格·贝尔曼撰书写道,美国行政部门在全球艾滋病防治中的投入实在少得可怜,在里根政府主政的上世纪80年代,保守派政客们对艾滋病避而不谈。此后政府在一系列全球性艾滋病公开行动中,推行“禁止国外HIV感染者进入美国”等没有实际益处的公共卫生政策,显露了美国政府只顾维护自身利益的丑恶目的。
与华盛顿、威尔逊一样,里根当时的头等大事是军事战略。他正忙着和苏联搞军备竞赛,医疗开支被削减。全社会对新冒出来的流行病表现得很冷漠。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人员,为了从卡波西肉瘤患者血液中寻找致病因子,向学校申请购置必要的安全设备——一个净化罩,配上1500美元的新过滤器,被学校拒绝。最后,科研人员找到了国会的一位议长,议长给校长打了一个电话,这笔钱才在拖了6个月后到账。事后证明,这千余美元花得很值,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这个实验室成为全球前三个分离出致病因子的机构之一。如资金能早一点获批,无疑将挽救更多生命。
“美国在建国的《独立宣言》中时就宣称人人生来平等,但他们对弱势人群的歧视根深蒂固,在建国140多年后才允许妇女投票,建国近190年后才给黑人投票权。作为艾滋病高发的男男同性恋和吸毒人群都是社会弱势群体,曾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这既阻碍了防治工作的开展,又加重了艾滋病患者的疾苦,还助长了疾病的流行。直到一些社会名流如电影明星哈德森、网球明星阿瑟阿什等因艾滋病死亡震动社会,弱势群体站出来维权,一些名流加入维权运动后,美国社会才开始转变观念,逐步转向社会同情和科学防治。”邵一鸣说。
1985年,好莱坞著名男演员洛克·哈德森因艾滋病去世。这年9月17日,出身好莱坞的里根第一次公开提及艾滋病,呼吁把艾滋病列为政府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他又在公开讲话中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天谴”,“生活在罪恶中的人应该在罪恶中死去”。一部名为《里根一家子》的电视剧告诉观众,里根夫妇对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没有任何同情心,简直到了十分憎恨和厌恶的地步。这也被视为里根形象的污点之一。
今天,艾滋病已经成为美国“政治正确”的话题之一,每逢選举常见艾滋病议题。通常,站在自由主义光谱上的民主党人更呼吁加强艾滋病研究和防控,而站在保守主义光谱上的共和党人也会表现出“政治正确”。邵一鸣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目前,全球7000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3000多万人已经死亡。全球每年艾滋病死亡人数从本世纪初高峰时的170多万人,已降现在的70多万人。这得益于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前者制造出30多个特效药物,后者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下建立了全球艾滋病防治基金,各国踊跃为其捐款,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免费抗艾滋病治疗。美国小布什总统执政时也受到此运动的影响,启动了一个美国总统紧急援助计划,在第二任期时拨款300多亿美元用于援助全球疫情最严重的非洲艾滋病的治疗。这个计划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延续下来了,至今已拨出850多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艾滋病防治。”一种旷日持久的大规模流行病,从总统的漠视,终于变成总统们的“政治正确”。
“形势比人强。在全球应对艾滋病大流行中出现的正向发展,值得国际社会加以借鉴,推动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走上国际合作的正确轨道。”邵一鸣说。
(实习生刘嘉颖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