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生活在词与物的午后(中)
2020-05-26
这其实跟李洱平时给人的印象多少是有些差距的。他在人前表现得更多的是健谈和幽默,不太喜欢说自己的个人经历。“《应物兄》删掉了1 35万字。”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他接着说道,“批评家黄德海到我家里,说想看看那些被删掉的部分。我打开电脑给他看。他说,你真的写了这么多字啊?我们还以为你在玩行为艺术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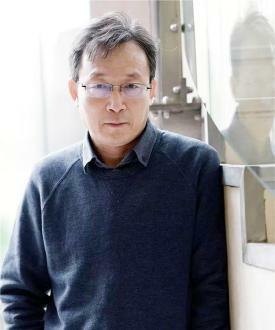
永远的贾宝玉
在北山讲堂旁的一个房间里,李洱在忙着给几大摞《应物兄》签名,我跟黄平在旁边说起了《花腔》。黄平仿佛是历史悬案的调查者,他像侦探一样发现了李洱小说里那些和历史的对应之处。比如说,葛任的原型是不是瞿秋白?还有那本叫《逸经》的杂志,在小说里,刊登了《蚕豆花》,在现实里,刊登了《多余的话》。黄平找到了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李洱则说,《逸经》完全是虚构的,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本杂志。“黄平告诉我时,我被吓到了。”若如此,这将吓到所有人,一本虚构的杂志在现实中,登载了与同名杂志相似的内容,换谁置身其中,都会被吓到。
黄平并不如此认为,“李洱老师不承认啊。”李洱在几米之外,边签字边说:“我不承认。”李洱曾在很多场合都对黄平的研究表示过赞许。他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就说到了黄平是极少数注意到《花腔》与贾宝玉之间有联系的研究者。“他看到了《花腔》里的大荒山和青埂峰,這些之前都被读者忽略了。”他觉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一部作品获得了这样的读者,才算真正完成。
李洱认为葛任就是贾宝玉,瞿秋白就是贾宝玉,应物兄也是贾宝玉,无数贾宝玉都在不同的时代中处理着知识人和时代的关系。《红楼梦》的续集一直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续写。而如何续写《红楼梦》,才是合适的呢?因为在不同的场合,经常提起《红楼梦》,不断有人拿当代人续写的《红楼梦》给李洱看。“这些书都写得非常好,我一时也分不清是当代人写的,还是高鹗写的。”李洱说,“我就问,作者有没有写实的小说。有的还真拿来了,但完全不能看。我以为一个真正的小说家是不能用《红楼梦》的方式来续写《红楼梦》的。”
在北山讲堂,李洱还讲起了施蛰存的《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的肉身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舌头变成了舍利。他并不纯粹,他带着情欲。“一个能像玄奘一样留下舍利的高僧,在我们的印象中,一定跟肉欲没有关系,跟权力没有关系,但在鸠摩罗什身上,外界的一切诱惑跟他都有关系。”李洱用他感冒的嗓音艰难地说道,就像是鸠摩罗什在凉州城里表演吞针。他把很多根针在众人面前拿出来,一一吞掉,但最后一根针没吞下去,卡住了,没人看见,他用手掩饰,巧妙地从舌头上拔出了针:你看,我全部吞了下去。
如果把现实比作针的话,舌头说出了很多传统。舌头忍受了现实中的苦难、情欲和折磨。每根针都是对自己的诫勉和惩罚。“为了保留一口气,我要把这根针从舌头上拔出来。我保留了这个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小说。”李洱在说鸠摩罗什,也似乎是在说他自己。这是《鸠摩罗什》结尾的“针”,也是《花腔》结尾的“爱”,还是《应物兄》结尾的从远处飘来的“声音”。肉身与灵魂在那一刻“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这是李洱提出的疑问,这也是他的小说。
除了《鸠摩罗什》,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将军的头》,处理的仿佛是久远的故事,但仍令观者觉得新鲜。施用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方式,写了最流行的小说。高僧的语言完全是现代的语言,不是高僧的语言。“这是最现代的戏仿。”李洱觉得这表明了施的写作是在场的。施的写作是可以介入到当代写作的所有问题中来的。还用《红楼梦》来做类比,就是他用的不是《红楼梦》的方式,续写了《红楼梦》,贾宝玉在现代,获得了新的肉身。
“小说家的工作就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小说家的生活就在词与物的罅隙之中,穿行而过。”李洱坐在华东师大的讲台上说。
他的师承
与李洱的电话访谈,一直在现实的疫情和小说的文本之间来回切换。某些时候,又会忽然融为一体。他对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非常感兴趣,那是一颗“洋葱”的核心。他说:“葛任的代号就是零号啊。零号就是趋于无,让他消失。零号有巨大的隐喻。代表的是一种像气溶胶一样的东西,若有若无,似有似无,感觉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关心新闻,会对其中的进展情况做自己的分析。
在李洱看来,写作者可以分成感性的和理性的两类,或者还有一类是知性的,在感性和理性之间。“那你是哪一类的?”我问他。“我大概也是知性吧。”他说。
李洱很欣赏库切的《耶稣的童年》。耶稣在《旧约》和《新约》里是两种形象。耶稣的形象是变化的。库切思考的是耶稣在此时代,又会是怎样的形象?在库切的笔下,耶稣的故事成为了现代移民的故事。《旧约》《新约》和现代的土壤连接成了一体。历史从源头流淌到了现在。
“我们必须从中国文化源头开始思考。”李洱说,“我们一直在半世俗半宗教的儒家体系里,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如何跟知识相处?”这个问题在他的思考里,可以具象为———贾宝玉不断切换的肉身。那个出现在现代社会的“耶稣”,就像是出现在李洱小说里的“贾宝玉”。
李洱在澳大利亚悉尼图书馆开讲座的时候,库切也去听了,李洱事先并不知道,他是在台上讲的时候,发现了他在下面。库切听完就走了。李洱追出了图书馆,看到了他“一个人行走在街道上,背影显得非常孤寂。”
“我写库切的一篇文章《听库切吹响骨笛》,估计他看到了。”李洱说,那篇文章曾被作为上海市的高考语文模拟题。“我想很多人读他的小说或许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对经验进行辨析的作家,往往是‘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因为失去了‘道德原则,你的怀疑和反抗便与《彼得堡的大师》中的涅恰耶夫没有二致了。顺便说一句,涅恰耶夫的形象,我想中国人读起来会觉得有一种‘熟悉的陌生: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
阅读题在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经验的熟悉”和“文学的陌生”?
李洱的答案是:“‘经验的熟悉是指这里面所说的革命者的形象。‘文学的陌生是指我们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处理。在我们的小说里,革命者的形象往往是高度简化的。”不知这是否符合标准答案。
(未完待续)
据中国作家网,卫毅/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