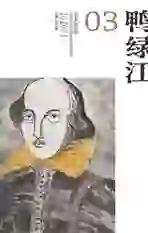试论汉孝惠帝之早逝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关系
2020-05-25田忆薇
田忆薇
摘要:探讨西汉历史时,自汉高祖刘邦之下,往往会忽视身为汉王朝正统继任者的“汉二世”汉惠帝刘盈。而谈论刘盈时,又时常会将刘盈归于昏庸无能之主一类。然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汉惠帝不仅并非昏庸无能,且其在位时,为文景之治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其史料记载的缺乏,或许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也或许由于惠帝英年早逝,在位仅仅七年。而在七年之中,惠帝已为汉王朝定下以“孝”为基调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延续做出了保障。本文中将论证汉惠帝所尊崇的“孝道”对其本人的影响及令他与母亲吕后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正文
首先,笔者认为如果要去揣测历史中人物的心思,必要的一点是将其作为一个人看待,而非一个在历史舞台上活动的无感情的木偶。即使是当时的政治人物,首先亦是一个人,而非一个纯粹理性的政治机器。他们虽有关于政治利益上得失的考虑,但终归不能违背人情的常理。
下面我会用以下几点来论证孝惠帝对于吕后,应当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无法选择顺从某一方而舍弃某一方,最终“自促其生”的观点。
1、从孝惠帝的政治举措上看
孝惠帝作为汉的第二任国君,虽然“享国日浅”,只在位短短七年,然而这七年之中,多有值得称颂之事,譬如弛商贾律,发展汉王朝初期凋敝的经济、废除挟书律,使民间恢复藏书的自由和令汉政府与少数民族及边疆政权恢复和平等一系列的举措(有说法认为这一系列政策是惠帝之母吕太后所为,但已有多位学者驳斥此种观点。孝惠帝生时,最为明显的正是吕太后不能任用自己的近臣,这与孝惠帝死后吕太后重用诸吕、审食其及宦官是截然不同的。且曾与吕太后‘为敌的赵尧,在孝惠帝生时一直为御史大夫,而在孝惠帝死后,被罢官除国。王陵与吕后的矛盾,也是在吕后临朝时爆发。故而笔者认为,孝惠帝是颇有政治能力的,且在朝政之上,应当是‘未央、长乐二宫分庭抗礼的)。因为与问题干系不大,暂且不提,且看其即位之初,便“令郡诸侯王立高庙。”可谓是开后世帝王之先河,而在孝惠四年,又为高祖立“渭北原庙”,而后惠帝五年,又将“沛宫”改为高祖原庙,如此种种,倒也是千古未见,而后的其他皇帝,也再不见有“原庙”。说明孝惠帝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如此行事的,自然,这一系列做法,也将汉高帝的形象深入当时百姓的内心,使百姓普遍崇拜汉高帝,继而也使汉王朝的统治更为稳定。在这诸事之间,还有根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以水果供奉宗庙,亦是始于孝惠帝之举动,是为后世之先河,不啻为一项创举。
特别注意的是,孝惠帝在位时,大兴“孝治”,由皇族至百姓,莫不以孝为先。汉朝“以孝立国”的根本,可谓是出自于他(高帝时期多为分封同姓诸侯和尊太上皇,并未惠及平民)。季乃礼先生曾指出:“真正汉家意义上的“孝治”始于惠帝。惠帝开始注重用‘孝悌教化人民,给‘孝悌者以好处:‘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季乃礼《论汉初的“孝治”》)此后高后、文帝等,对这一举措也多有阐发,之后“孝”逐渐成为汉的整体意识形态,为汉朝奠定了数百年的“亲亲,尊尊”的状况,使汉朝有百年的安稳,我认为惠帝在这件事上,是称得上“功不可没”的。
而其主持修建的汉长安城,某种程度上与其父亲的想法应当是相符合的。汉长安城广大,且为斗星之形,合长乐未央二宫,正如天之紫薇垣,当年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时,理应也有此观念,否则不会有萧何与刘邦关于宫室大小之一系列的论辩。
汉时本质上是一个性别并不平等的社会,孝惠帝的老师是叔孙通和张良,而商山四皓也辅佐他。叔孙通之学本于荀子,可知孝惠帝的观念应当同荀子,以及后世的儒生是相若的,即将父亲视作是不可以忤逆的神明。这一点从前文论述其为父亲刘邦广立祭庙,时时祭祀也可看出,再者,孝惠帝在位时,也是严格地遵循着其父刘邦规定的“非刘不王”之政策,至死而未变,甚至封侯,也无一姓吕。而孝惠帝尸骨未寒之际,诸吕相继称王。
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孝惠帝时,吕后便“欲王诸吕”,而陆贾自度不能争之而隐退,然而归根结底,到底没有使诸吕称王,若说其中没有孝惠帝对于父亲的忠诚和与母亲的抗争,我是不能相信的。
2、从惠帝对于自己亲人的表现上看
下面论述惠帝对于母亲的敬爱与对待其父是相当的。
暂且撇去如意,看一看孝惠帝对待自己其他兄弟的态度,当可知他对于“仁孝”、“伦理”之类的重视之情。
汉惠帝二年冬十月,惠帝的庶兄齐悼惠王刘肥来朝,惠帝“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礼”,可见他在面对亲人时,并不以自身皇帝的身份为骄。自然,这一点使得他的母亲吕太后恼怒,因而“乃令酌两卮酖,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通过后文,我们可知那酒中应当是有毒的,而孝惠帝当时也许看出母亲的所思所想,故而“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这已可堪称是决心“死谏”了。而不得不承认,孝惠的方法十分有效,最终“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而后齐王明白事件的怪异,佯装酒醉,脱身而去,最终献出城阳郡给鲁元公主作为汤沐邑,换取了自身的太平。
需要补充的是夏侯婴事件。据《汉书》记载,刘邦在彭城之败后,逃亡时遇上鲁元公主与孝惠帝,而刘邦为逃命曾数次将公主与惠帝从车上踹下,而夏侯婴则数次将其抱上车。孝惠帝即位后,任命夏侯婴为“太仆”,并且赐给他“北阙甲第”以示感谢,对于在自己六岁时对自己有恩的夏侯婴,惠帝尚且如此厚赐,这表示孝惠帝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而对于夏侯婴尚且如此,何况是对自己有养育之恩且为自己的太子之位殚精竭虑的母亲呢?我在前文已表明,揣测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首先应当把他们当做是一个人。孝惠皇帝年幼时,汉高帝刘邦尚未发迹,母亲吕后带着姐弟二人辛苦劳作,而父亲则常年在外闯荡,我认为,即使汉代是一个男权的社会,但儿童的人格养成理当与今人相差不多,在下意识里,童年时所形成的对于母亲的爱,应当不会比成长中所受到的以父为天带来的对于父亲的忠诚与敬仰要逊色。
而由此事件可以看出,孝惠帝充分顾及了兄长的安危和母亲的颜面,并没有直接说出其心中猜想而令母亲背上骂名,也没有放任母亲毒害庶兄,而是“取卮欲俱为寿”,以自身的性命为赌注救下了其兄长,这充分的说明了,孝惠帝并非如传言所说是软弱之人,他对母亲的孝敬,也理应并不亚于对其父亲的孝敬。
而后,孝惠帝四年,吕后“欲为重亲”,聘娶宣平侯女张氏为皇后。这里将张氏归于孝惠之亲人,乃是由于宣平侯张敖尚鲁元公主,张皇后是否为公主亲生,如今众说纷纭,本篇不做讨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汉时理应如此(孝惠帝的侄儿孝景帝皇后亦为祖母薄太后所指派,而景帝并不宠爱她,最终薄皇后被废黜。可见孝惠帝以张氏为后并不能说明他是软弱无能的),纵使孝惠不愿,也不得忤逆母亲,否则即为“失德”,而从叔孙通谏惠帝“作复道”一事惠帝的反应上看,惠帝自身应当是对德行十分在意的。因此,他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忤逆母亲,而从他童年时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情况来看,大抵其自身心中,也是将母亲的悲喜看得很重的。
然而从前文中他对待齐王“如家人礼”可看出,他自身非常重视人伦道德,无论张皇后是否是其姐鲁元公主亲生,她的身份始终是孝惠帝的“外甥女”。故而张氏成为皇后后不久,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灾:丙子,织室灾… …是岁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鲁元公主女为皇后。其乙亥,凌室灾;明日,织室灾。凌室所以供养饮食,织室所以奉宗庙衣服,与春秋御廪同义。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庙之德,将绝祭祀。其后,皇后亡子”。须知秦汉时期对于天象十分看重,高帝刘邦起义之时,也将自己神化为“赤帝之子”,而汉武帝更是以祭祀时获“白麟”而改元作歌。然而天象之说,我们今天看来,是迷信的,因此,或许这两次相隔时间极近的“灾”乃是人为,是孝惠帝以天象来讽谏其母。而后张氏作为皇后的三年多近四年的时间以来,纵然“太后百般欲其有子”却“终无子”,以至在晋时传出“孝惠张皇后至死仍为处女”之说,虽然其是否为处女今人是不可知的,但无论如何,这应当是孝惠帝对于其母的不伤尊严而不违背人伦的反抗,只是可怜了张皇后,最终在北宫孤独一生。
3、从孝惠帝对待戚姬、如意母子的态度上看
上文论述了孝惠帝对于除却如意以外的亲人的态度,现在便来说一说如意。
如意与戚姬这对母子,我之所以单独拿来说,是因为他们对于孝惠帝和吕后的母子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倘若没有史上著名的“人彘事件”,孝惠帝也许不至于在廿四的年岁英年早逝。
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赵王诛之”可知吕后即使十分憎恨戚夫人,最初也并未起到杀之的念头,而是“囚于永巷”,令其做苦役罢了。而在听到戚夫人之歌后,也许吕后想到当年刘邦对戚夫人母子的宠爱和赵王如意独享一国的威胁(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之夫宣平侯张敖本为赵王,后因贯高事件被废黜,而后如意被迁为赵王,也许这件事亦被吕后算在如意头上),因而“乃召赵王诛之”。而赵王如意曾与孝惠帝有储位之争,吕后杀之,从历代皇帝对于争储对手的行为来看,吕后似乎并不过分。然而虽有周昌鼎力相护,最终赵王却仍旧前去长安了,孝惠帝了解其母,因而“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
北宋《古文苑》中有一篇题为《汉高祖手敕太子文》,文章最后说道:“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馀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虽不能定此文是否真是汉高祖刘邦所写,但此句确实表明,高帝去世前,或许是知道孝惠帝仁孝,而顾命其照拂如意。因而孝惠帝忠于其父,乃与如意共卧起数月而吕后不得间,最终却因为如意不能蚤起而功亏一篑。从这时起,想必孝惠帝心中对于父亲的愧疚已然开始无时无刻地折磨他了。
而拔出了赵王如意这根刺后,吕后将矛头指向积怨已久的戚夫人。“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并在数日后,“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这一段描写,或有人说,孝惠帝胆小,不足为帝王,然而我要反驳这一说法。第一,孝惠帝当时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放到现代来看,是一位初高中生,見到如此恶心的“人彘”,被吓到是在情理之中的。可细看着一段的描写,却是孝惠帝见之,并未有恐惧,且还“问”,知是戚夫人后,方才“乃大哭,因病”。可见这位生长在乱世的尸山血海中的年轻皇帝,并非是胆怯之人,而且因为知道人彘便是其父的宠妾戚夫人而“大哭”。
从此前吕后“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而孝惠帝并未明确的做出什么反应而言,有理由相信孝惠帝本人对于戚姬也并无好感,他所要保护的,只有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如意而已。而得知是戚夫人后的大哭,我想是哭他自己,哭他的父亲刘邦,也哭他的母亲吕后。而从孝惠帝“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也可以证实上述猜想。《荀子·子道》说:“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我认为孝惠帝力保如意,可能也有此打算。假如他顺从母亲的心意,放任母亲杀死如意,那么,吕后终究会背上残害庶子,残忍悍妒的骂名。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惠帝深爱着母亲,自然不会愿意母亲受人非议,然而他最终未能成功,如意与戚姬相继被吕后所杀,年轻的孝惠帝既对于母亲的行为抱有强烈的不解和质疑,也自责于自己为什么没能做得更好。
也许他痛苦于母亲的扭曲,也许他羞愧于自己没能完成父亲临终的嘱托,也许他感到异常的无力,自己身为帝王,却连平民百姓所做的“孝敬父母”都做不到。这诸多的痛苦与不甘之情,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能够全然体会的。
4、总结
在高帝去世后,因为戚姬母子的问题,吕后与自己的丈夫站在对立面上。而孝惠帝作为二人的儿子,统御天下的皇帝,如何选择是忠于父亲还是母亲?选哪一个都会使他陷入“无德”的骂名,而在本心上,在他那受儒家思想熏陶而产生的强大的良知之下,他也明白,自己绝不能在父母二人之中,选出一个人对其偏私。
孩子对于父母与生俱来的爱与依赖,在刻意引导下,很容易变成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会被内在化,与父母的关系会变得不平等,类似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这种心态,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称之为“权威主义良心”。而权威主义良心的内核,是利用人们对于权威的心向性,使其所宣传的理念逐渐成为人心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理想和目标。内在权威与外在权威相互滋长,最终令被宣扬的理念变得坚如磐石。自小受儒家教育熏陶的汉孝惠帝刘盈,理应将儒家经典视作最高权威,而因此,将“孝”视作高于自身的最高理想。
于是在良心的折磨下,本该有所作为的大汉第二任皇帝在廿四盛年而亡。死后,他的母亲也许大悲无泪,也许是更看重权势,竟在他的葬礼之上,干嚎而不落泪。他一生遵从良心,以自己的方式孝敬着父母,然而最终,他的母亲也因为他的忤逆而与他变得疏离,而父亲的嘱托,他亦没能完成。
他死后,以“孝”为谥,开汉代帝王谥号为孝之先河。汉之孝何其严厉,悖逆父亲,悖逆母亲,皆为不孝。而他努力的找到的平衡,在如意母子死后,终于再不能复原如初。纵然表面上并无改动,但在午夜深梦之中,想必孝惠帝那过于理想主义的良心仍因为他没能护如意无恙而苛责着他吧。
晚清洋务运动的先锋者薛福成先生说:汉高帝欲废太子,常曰:“太子仁弱,不类我。”四皓对高帝曰:“太子仁 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者。”班氏赞惠帝曰:“可谓宽仁之主。独悲 其遭吕太后,亏损至德。”薛子曰:“人主之美德,莫如仁,仁之失毗于弱。然惠帝实 三代下守成令主,惜乎其享年不永也。”世或以惠帝不能防闲太后,为仁弱之明证,误 矣!夫太后佐高帝定天下,制韩、彭辈如缚婴儿,谪诈悍戾,用事已久。为之子者, 欲力制之,必受奇祸;欲婉谏之,又不见听。设令文帝处此,亦惟养晦避祸而已。大抵家庭之变,虽圣人遇之,未必无遗憾。惠帝所遭之艰,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且 帝之处太后,亦何可及哉?帝怒辟阳侯行不正,则下之狱,而太后惭不能言也。在位 七年,诸吕未尝用事;及帝甫崩,而台、通、产、禄相继封王,高帝诸子相继幽死, 辟阳侯且为右丞相,居宫中矣。则知惠帝在时,太后犹有所严惮,而不敢逞県维持 匡救之苦心,后世所不尽知者也。至其内修亲亲,外礼宰相,闻叔孙通之谏则瞿然, 纳曹相国之对而心说。虽三代贤主,无以过之。七年之间,如除挟书律,议除三族罪、 妖言令,举民孝弟力田者,省法令妨吏民者,若令享国长久,其治当不在文帝下。且 帝天资仁厚,殆非文帝黄老之学所及也。若乃亲睹太后之暴,忧伤感愤,自促其生, 此则仁者之过耳,惜哉!惜哉!班氏赞之曰仁主,曰至德,所推尊者盖至,而悲之者微矣。
笔者认为,这是对于汉孝惠帝刘盈非常中肯的评价。正如他的老师叔孙通所教他的,“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他不被自己的父亲喜爱,在年仅六岁时便被父亲数次从车驾上踢下以求车能疾行,在终于不必苦于战乱之后,仍被父亲厌弃,说出“不类我”而欲将他废黜。刘盈本身看重人伦道德,渴望自己成为儒家所称道的“仁者”、“君子”,而“孝”也可算是君子的立身之本。以此来看,刘盈的确算是成就他的理想,即成为一个“仁者”。
弗洛姆在其著作《自我的追寻》中说:“如果父母彼此不相爱,孩子应该负责爱的补偿。如果他们觉得在社会生活中缺乏权势,他们便要统治与支配孩子而取得满足。即使孩子符合这些指望,他们仍会感到有罪.......觉得令父母失望是由与父母有所差别的感觉而形成的。掌握支配权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在脾性与性格上与他们一样......”或许这正是汉高帝刘邦不爱自己的儿子,而吕后总是渴望支配的真实原因。而刘盈又因为将“孝道”视作至高理想而渴望令父母欢欣,最终却因为无法打破自己原有的性情而痛苦不堪,最终只能“自促其生”。
刘盈自己甚至渴望以“孝”来教化平民,可知其对于孝道的重视。然而当时的孝道,许多时候,却往往成为对于子女的一种压迫,阻碍他们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内心完整的人。一旦父母感到丝毫的不悦,子女便会认为这是其自身的“罪过”进而恐惧,忧虑,不知所措,最后大程度上会违背本意,向权威,亦或是秉持权威的父母妥协。
心理学家苏珊·福沃德认为:“父母的操控将很多子女逼入了死胡同:选择反抗,他们就会伤到自己‘只是出于好意的父母。对于多数人来说,选择屈服似乎更容易些。”须知汉代对于“孝子”的标准,远比我们所处的时代要严苛得多。然而汉孝惠帝刘盈却并未选择屈从于母亲,正如上述所说,他认为不顺从母亲的意思,(如保护兄弟刘肥、刘如意,不封诸吕为王,欲杀审食其等)能够让世人不对母亲产生非议。然而他的母亲也势必与他产生冲突,这又令他感到痛苦,认为自己因为忤逆而伤害了母亲的感情,进而陷入自责的泥淖中不能自拔。即使一个原本心理十分健康的人,在长时间被两股矛盾的情绪冲击后,也会感到异常的痛苦和无力,又何况是如刘盈一般自幼生活在恐慌和惊惧之中,稍有不慎也许会死于战乱的人呢?童年的经历,对于任何人的影响都是极为强大的。而刘盈自己并未因为年幼时的战乱之苦而成为暴戾好战的君主,他在位时废除挟书律,驰商贾律,修建长安西市,复十五税一,无不是宽仁爱民的政策。甚至在一件小事上,即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作复道,其原因也是“数跸烦民”,即“到束边的长乐宫去朝见太后,以及平时往来,都要惊扰老百姓”。由此可见,其谥为“惠”是非常契合其本人对于人民的态度的。案《谥法》所云:“柔质慈民曰惠”。
而其谥号的全称为“孝惠皇帝”,西汉自孝惠皇帝刘盈以下,皇帝谥中皆有一“孝”字,于彼时对于孝子概念之严苛而言,刘盈成全了自己的理想,留下了“孝子”之名,進而影响了整个汉朝,乃至于后来其他王朝对于“孝道”的重视。而他自己,也是因为在父母与孝道无法调和的矛盾下牺牲,在年仅廿四的年纪便英年早逝,而最终,他的母亲在他死后也没能逃过千秋史笔如刀,如他所忧虑的一般,留下了“擅权暴戾”、“癫狂悍妒”的骂名。
“殉道”之意,是“为所尊崇的理想而死”,如汉孝惠帝刘盈,短暂的一生中,尊崇儒家、黄老,尊崇孝道,亦不愿屈服妥协,违逆本心,最终导致心中的悲哀郁积,令他英年早逝,哪怕是如此,他仍在政治上做出许多足以被后世称道的“德政”。如和睦外族,废除挟书,坚固国都,虚心纳谏等等,皆属符合儒家思想的政策。如《荀子·强国》所说:“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礼义、辞让、忠信 是也”其说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而下达这些政令的汉孝惠帝本人,一生信奉仁义之道,所作所为皆未违背“仁义”法则,却也是由于尊崇仁孝,心中的矛盾过于强烈而“自促其生”。在这短暂的廿四年的一生中,他从未有所作所为违背了儒家的道义,即使最终盛年而陨,在权威主义良心之下成为能得到真正的健康的自我,这是可悲的。而即使在诸多痛苦和艰难之中,亦能坚持理想,却也是可敬的,汉孝惠帝的一生,不正如宗教中的殉道者,为自己所信仰的神明而自愿放弃自身所有,乃至于生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