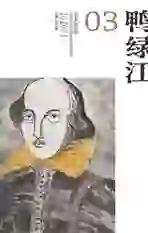车祸
2020-05-25蒋九贞
小媚紧紧搂着单喜的腰,伏在他胸前,肩头耸耸地哭,哭得天公也跟着悲了,哗哗哗下起大雨来。
单喜并不觉得下雨,他只感到小媚的热泪浸透他胸襟后的滋润和疑惑,感到今天的不正常与模模糊糊的不祥之兆。
突然,小媚松开单喜,并且推了他一把,把他推了个趔趄,张开的嘴里就进了一大捧雨水。
小媚不哭了,呆呆地站着,任凭大雨往身上泼。
单喜想像往常一样,在没有带伞的雨中把小媚揽在怀里,用自己的胸脯和衣服为她遮风挡雨,保护她单薄的身体。他走上一步,拉了拉小媚。小媚一甩胳膊,又把他甩出去半步。他脚下一滑,差点儿摔倒。
今天的雨没有闪电雷鸣,却出奇的大,雨帘挡住了他们的视线,他们看对方都似乎模糊了,每个人在雨水的击打下都变了形:小媚像半截檾杆,单喜像锯掉冠的树桩。
小媚好像没有看单喜的脸,她专注的是他的脚,脚上那双网状的棕色皮凉鞋,雨水充满了一个个孔,从鞋里流出来,流到地上,与溅着花儿的流水汇在一起,形成小小的浪花,冒着泡流进村边的那条河。小媚张了几张嘴,她好像要吸吮天雨的琼浆,吸吮雨中的清气,吸吮天地相吸相拒时产生的看不见的物质,吸吮一种叫做力的东西,为她欲言未言的话语撑腰打气。她好像痛苦极了,又淌起眼泪。泪与雨在朦胧的雾气里纷飞,脚边的小草仿佛被感染,匍匐着,随着雨的节奏,在泪水里洗涤。她猛可抬起头,对着单喜的方向,朝着对面,大声说,咱——分手吧!
她有点儿不相信这句话是从自己嘴里出来的。可是,千真万确,是她说的,那声音有些尖細但浑浊,也许是落雨的声音太大了,还有点儿不甚清晰。
她希望这声音能被单喜听见。这是她不想吐出第二次的声音。她哭了好半天,就是这句话憋的,这句话对于她太难出口了。为了说出这句话,她准备了半年时间,每天夜里躺在床上哭,哭着念叨,可就是难把脑子里的这个东东变换为词语,念叨半夜,甚至一夜,也念叨不成句子。
今天,终于说了出来,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今天怎么就说出来了呢?是刚才即将瓢泼的雨柱带来的抑郁催生的结果吗?或如“地皮”(方言,一种黑色菌类植物)在刚刚合适的条件下遍地开花?亦如铁树孕育了数十年恰逢其时就开放了?她在肚子里装了半年的一句话,此刻竟这么说出来,似乎没有费太大的劲,也没有惊天动地。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只要单喜听见就好,只要他能领会,不让我再重复,哪怕我此刻消失,也是情愿的,也是对于我和对于他的解脱。小媚这样想着,偷偷看了单喜一眼。
单喜木然地站着,雨水顺着他的头顶往下流。他的眼睛宛若死人的,暗暗地发着绿光,在雨帘的遮挡下如幽灵手里的火把,若有若无,然而更加恐惧。忽而,他的眼睛变成两个裂开的蚁穴,继而被强劲的大水冲决出两个洞,汹涌而出的大水把两个洞变成永远不会枯竭的泉,比农家安装在北河里的两个二十五寸大口径水泵还澎湃。他蹲了下去。
还好,他听见了,不需要我重复了。小媚想。如果单喜此刻让小媚重复一遍刚才那句话,她可能会立即扑倒在地上,寻找一个或许会出现的地裂钻进去,就此了断自己的生命。
她注定不会结束生命,因为他听见了,他听懂了,他在悲伤地哭,他捂住眼睛,两条水柱冲开他的手掌,比雨声还大的声音带着哨儿倾泻到地面,然后汇合积存的雨水流走。
听懂就好,知道就好,快熄了那个念头,不要再考虑结婚的事情。感情与婚姻是两回事。感情不就是婚姻,婚姻也不就是感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都是相等的,有时候可能会大相径庭。爱,不等于就必须结婚;结婚,也不等于因为爱。小媚脑子里也如这雨帘,莫名的模糊,她的思想此时在爱之外徘徊,而她的情感却无法脱离爱的羁绊,更无法挣脱自我谴责的锁链。
实际上,单喜蹲在地上的时候,他本人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雨声好像也没有震动他的耳膜,他进入了一个相对无声的世界,周围的一切都悄然无规律地进行。他紧紧绷着嘴唇,不做丝毫活动。鼻子的呼吸当然没有停止,只是,两个鼻孔也和嘴巴一样没有声息,空气是在两个泉洞里的水中自动钻进他的肺部的。雨水弹着地面生出的味道有点醇,有点咸,有草的清香,还有泥土的腥气,以及田间残存农药和化肥微微刺鼻的酸臭味。雨水拍着他的背膀,像为了哄不乖的孩子睡觉而拍着他(她)的背一样,雨声正好成了他的催眠曲。他觉得真的累了,困了,想好好睡上一觉。
他的身子慢慢缩下去,缩下去,缩成一个沙袋,一个泥坨。
小媚油然而生一种恐慌。
忽然,她弯腰拉起单喜,拉着他踉踉跄跄地走,如同拖着一只旅行箱,在雾气腾腾的雨中,也像幼鹰抓着一只偌大的公鸡,她的急促和疲惫都显而易见。
被拉着的单喜终于像一个人一样直了身子。
大雨倾盆。远处有汽车的鸣笛声,那是一公里开外的县道上行进的车辆在提醒行人或者其它车辆,不要因为它的到来而发生意外。
直起身子的单喜一下子站定,小媚拉不动了。拉不动就不拉,我本来也没想拉你。小媚想。她松开他,也站住。稍停片刻,她看看他的侧影,瞄了一眼他的脸和眼,觉得他的脸色有些发绿,犹如冻僵的坏猪肉,他的眼洞洞里没有了生气,瞳仁失去了光泽,像死鱼的眼睛,也像瞎子纯粹做摆设的眼球,有点儿可怕。这,增加了她的恐惧感。
她犹豫了一下,车转身,噗噗嚓踩着雨水拔腿而去。
单喜见小媚走了,也尾随其后,跟着她噗噗嚓噗噗嚓的走着。
小媚原想就这样甩掉单喜算了。痛苦总是要痛苦的。几年的感情,如胶似漆的缠绵,怎么会说散伙就散伙呢?可是,狠狠心,与其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分手不失为最好的选择,反正,分手的话也说出来了。她趔趔趄趄,一边流着泪一边往前跑。是的,小媚是在跑,她不顾一切地跑,没有回头,没有犹豫,她怕她的回头会引出“车辊轮战”,怕再回到原点。她急促的脚步带起无数泥浆和水珠,溅得她整个后背都脏兮兮的。
解脱了,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单喜他会好的,会走出这个糟糕的阴影,过上他自己的日子,无论这日子好坏,都是他的命。
身后噗噗嚓的声音越来越大。随着一阵唿嗵唿嗵的喘气声,小媚的右手被抓住了。她下意识地一甩手,才又恢复了她独立身躯的自由。她想甩掉的那个主儿跟来了。她知道,甩不掉他了。
小媚停止了奔跑,也喘着粗气,静静地看同样喘着粗气的单喜。但是,这一回她不敢再看他的眼睛。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他的眼睛怎么会那样呢?难道,他的心死了吗?小媚先自胆怯了,不敢想下去。
然而,她必须走,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单喜,她想让单喜一个人平静下来,好好想想,慢慢疗治心头的伤。他心头肯定有伤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情有可原。可是我……我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她想张嘴说些什么,可是没有说,她觉得自己先说话就失败了,就会前功尽弃。
她又走。这一次不再跑,而是不紧不慢地走,淋着大雨,踏着泥水,噗嚓、噗嚓、噗嚓。
你,去哪里?
单喜说话了。他先说话好,他先说话证明他的痛苦程度已经有所减轻,说明他心里已经有了回旋余地。退一步海阔天空。为什么要一条道走到黑呢?树多的是,何必一棵树吊死!
到县道那边。她回答。她是信口回答的,没有经过大脑。
到那干啥?
看看。
哦?
你回家吧!
不!我不放心你。
我没事。
不管你有事没事,我都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样走。
你想怎样?
不想怎样。
我不要你跟着,我有我的自由。
我也有我的自由。
哼,不识抬举!
不想识这样的抬举。
小媚皱皱眉头,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雨水是擦不尽的,只能暂时拨开先泼下来的那层水,手还没有离开,雨水又弥漫了一脸,因为雨还在下,天仿佛漏了似的,也仿佛为了掩饰他们各自脸上的那两泓不时喷发的清泉而益发凶猛。她不再说话,只顾走自己的路。她倏然想到,既然他跟着,就索性真的去县道,让他懂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道理,懂得各走一边了才能不撞车,不发生事故,才能各自平安,各享其所。
他們默默地走着。此时无声胜有声。唯有雨声依旧,杂有汽笛微弱的嘶鸣。
穿过一座沟渠上用水泥管子搭成的小桥,三米半宽的田间水泥路被他们甩在了身后。县道上的车辆实在不多。他们所在的乡镇是该县比较偏僻的乡镇,这里又是这个偏僻乡镇里比较偏僻的村落,好晴天公路上的车辆也不会太多,何况现在是大雨如注的天气?小媚站下,她头顶早已被雨水击打得生疼,等待她的必是一场严重的感冒。这会儿她顾不了这么多,也不觉得雨水有多大的威胁,反正是淋了,就索性让它淋个够吧,谁叫出门没有带伞呢?出门时候是一片蓝天,蓝天上飘几朵带黑边的白云,太阳也不是怎么厉害。再说了,农村女人,有几个出门打阳伞的?那是城里女人的享受,农村女人不行,农村女人晴天出门打伞,那是要受到舆论的攻击的。小媚不想做“靶子”,不想被人戳脊梁骨。可是,她还是要被戳脊梁骨,和单喜谈了这许多年,说散就散了,那一定要被人说的。嗨!说就说吧,如今也不是老爹老娘那个时代了,任你说又怎样?她没想到大雨竟这样容易就下了。她又张了几张嘴,而这一次张嘴,不是想说话,而是想打喷嚏。
单喜过来,把上衣脱下,给小媚顶在头上,遮着她不被雨淋。他自己光着膀子,雨水就像开闸的浪潮,把他冲得七倒八歪。
小媚感到一丝温暖。她张眼望着单喜。单喜那有角有楞的国字型脸此时竟有了几分舒缓,眼睛里也有了光,只是雨水的倾注让这双眼睛多少还有些幽灵般的感觉,脸色也还有点绿,是那种紫里透黑的绿,浅浅的墨绿。头顶上的衣服里散发着温馨的热气,一股男人特有的气味直冲她的鼻翼,冲进她心肺。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咽下那股她熟悉的气味,带着他体香的浓郁的气息。
她几乎被感动了。
她立即警觉起来。她必须控制感动,她不能感她认为贻害无穷的动。她正经观察了一会儿,单喜非常平静。他一定是撑过去了,彩虹总在风雨后。看,他脸上有了欢快,好像完全忘记了“分手”这件事,好像他们之间以前根本没有过恋情。好,就该这样,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唉,忘恩负义的男人!你就这样轻易忘记了吗?幸亏,幸亏我和他分手,不然,跟着这样的男人,以后还不定怎样呢!小媚的思绪里又多了另外的矛盾和斗争。她恨人的无情,恨人性之恶,恨世上没有了相守终老的真情真爱,恨眼前这个薄情男人。她忽然想疾呼,敢问世间情为何物?竟然是,前一分钟爱得死去活来,后一分钟忘得一干二净!但是,她的举动还是比刚才温柔了许多。她想说话了,想主动打破这一回的沉默。
她说,也像对自己,咱们,好搁好散,都修复一下创伤,好好规划自己吧!
单喜愣了,没有听懂似的,怔怔地看她。
什么?你说什么?
雨声将他的声音固定在半径一米多的范围内,小媚刚好能听见。她有点瑟瑟发抖,毛骨悚然的样子,双臂紧抱着膀子,缩在单喜上衣里的头颅也好像因了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变小了。
她怯怯地,嘴里含糊不清的唔噜了一会儿,终于鼓足了勇气,再一次明确说,分手。
单喜的脸扭曲了一下,他的眼睛混沌了片刻,又发出幽暗的绿光。雨下得更大了,他险些被无情的大雨冲倒。他稳了一下,站正了,狠狠瞪着小媚。
为什么?他问。
不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什么要分手?
单喜,求求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好吗?
不好!我一定要问。
如果我不回答呢?
我不会让你走掉的!
小媚有点害怕了。她想起一个时期以来诸多因感情破裂而发生的凶杀案件。眼下的单喜,已经被魔鬼缠身,他会杀了我的!她脑子里闪了一下这个念头,便呜呜的哭了。
你以为你是大学生村官了,就高人一等了?你以为我爹下岗了,回老家来了,就忘记咱俩几年的感情了?你以为我没钱上学退学了,没有前途了,就嫌贫爱富了?或者,你另有新欢,你一直在欺骗我,玩弄了我的感情,利用了我的肉体?梁小媚,我告诉你,你不说明其中的原因就别想离开这里!
小媚好为难,停了啜泣。她想了半年的理由,半年啊,六个月,一百八十多天,那些一二三四的理由今天竟然无从说出,也感觉全不再是理由。她嗫嗫嚅嚅老半天。
你说啊?你为什么不说?单喜穷追猛打。
小媚不能不说个子丑寅卯出来。她不说,即使单喜不杀死她,她也会被大雨浇死。老天啊,你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雨?你为什么今天要下这样的雨?县道上的车来车往并不频繁,偶尔的笛声冲破雨帘灌进她的耳室。还好,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也只有它们才是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真的希望县道上多些车辆,多些,再多些!
两辆相向而行的车交会了,它们擦肩而过,而又分道扬镳,安全运行。
单喜,你看,它们,各行其道,不是很好吗?如果硬碰,那就是车祸,惨烈无比……
我不听你说这个!我要你说说为什么,为什么分手?单喜吼道。
我的比喻,希望你能明白。
我不明白!
单喜,我是爱你的。
鬼话!爱我还要分手?离我而去就是爱我吗?你!
单喜,你听我说,婚姻、家庭不能建立在空着楼阁上,也不只有卿卿我我,我们终究要回到现实中来。
梁小媚,你不要耍嘴皮子,我不爱听官腔,我要干的,真的,实在的!他又大吼起来。他的声音和如雷的雨声分贝不相上下了。
小媚又打了一个寒噤。
我,我是俗人,我脱不了世俗,单喜,你听我说,现在,你们家是这种情况,伯母生病,去世,欠下巨债,伯父下岗,没了收入,贫贱夫妻百事哀,你不为我想,也该为以后的孩子想,他们如果出生了,会有幸福吗?能得到好的教育吗?咱们有钱供吗?这些,不都是问题吗?单喜,婚姻不是儿戏,不是空想乌托邦,婚姻是实际的,我们必须现实。
小媚断断续续说了这么多,她觉得心里舒畅了不少。当然,这比起她半年来准备的理由,简直是九牛一毛。可是,当下,她搜肠刮肚,只能说这些了。
平静的雨帘忽然掀起一阵风,被风掀起的雨帘竟有无穷的力,把单喜一下子裹倒了。他趴在地上。这时,一辆小型货车从西边没命的驶来,它靠着路南边,一路朝东。它的后轮几乎碰着单喜的头,幸好,他倒地的地方距离县道还有半米多,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小媚激灵灵颤栗了一下,出了一身冷汗。
她向前拉他。
單喜挣脱了她。
小媚又去拉,她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把他拖起,拉到县道以下的田间水泥路上。单喜半蜷半蹲地趋就在那里,嘴里咕噜着,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是对的……
大雨没有减弱的迹象。此时,小媚有点可怜单喜了。再说,这样大的雨,他这样的状态,怎么能够禁得住如此的打击呢?她想把他拉走,各回各家。
你给我滚!滚!我不要你的安慰,我要冷静冷静。我要独自清静一会儿,听到没有?给我滚,越远越好!
单喜的面目狰狞,连脸型都变了,变得真的像一个魔鬼。冲动是魔鬼,情绪激烈也是魔鬼。魔鬼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小媚的心忽嗵忽嗵地跳,就要跳出嗓子眼儿了。
她不敢再多看他一眼,从头上拉下他的上衣,给疙瘩在那里蜷缩着的单喜披上。单喜脸上曾经如喷泉一样的两个洞洞里,现在不仅没有了水柱,而且干涸了,如两眼枯井。他把“枯井”对准小媚,像狗一样窥着她,然后关闭。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扯下她给他披上的他的上衣,扔出去。衣服随了风雨被卷到县道内侧,很快又被雨水淹没。
滚——
小媚拔腿就跑。
风和雨追着她的后背,也阻挡着她的脚步,她的腿怎么也使不出更大气力,她被前面的风雨和后面的风雨夹击着,差不多失去了自主能力。
“吱——!”一个紧急刹车声从几百米远的地方传过来,这声音那么急湍,那么尖利。她连忙捂住耳朵。一阵疾风暴雨袭来,她栽倒在田边的水沟里。
风裹着雨,把天地间变作了白浪滔滔的海。
2019年8月8日 于徐州
作者简介:
蒋九贞,本名蒋广会,又名蒋岚宇,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各级文学刊物发表各类作品300余万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和评论集、古体诗集等十多部图书出版发行,并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馆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