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症时代的爱情
2020-05-21王颖
王颖
当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而发生著质的剧变,越来越多的工作只需要通过网络在电脑前就可以完成。全世界发达国家有六千七百万的孤独症患者,在过去二十年里继续呈现爆发式上涨的趋势。在数码世界中,你可以找到最性感的虚拟伴侣,所以很多孤独症患者愿意彻夜地尬聊,只为了确认屏幕后面是否就是那个最懂自己的人。

人类的情感需求从未改变,每个在繁华都市中奔波的疲惫心灵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温柔港湾。2019年11月中旬,“爱情”这一永恒的题材在女作曲家查娅·捷诺文(Chaya Czernowin)的编排下以近乎透明的形式呈现在德意志歌剧院(Deutsche Oper)的剧场中。空旷的舞台、巨大的投影屏幕、男女主人公日常生活场景以及内心深处的喜怒哀乐,无限放大的自我,被毫无保留地投射在大屏幕上,这与坐在舞台前的真实演员在空间和视觉上形成巨大的反差。
音乐戏剧《心房震颤》(Heart Chamber)的剧情大致是一对陌生男女在闹市区偶遇,并由此展开的一段悲欢离合的心路历程。走在阶梯上的她忽然从手提袋中掉落了物品,恰巧经过的他快速将其拾起并递回她手中。这一过程中肌肤无意间的接触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然而等待他们的除了爱情之外还有怀疑、剥离、愤恨以及忧怨。投影中,他们的身影时常出现在同一条街道上,同样的阶梯,同样的路人,一次次的擦肩而过,而他们却不曾相遇。直到命运的时间线将他们聚拢,时空停滞在他们相遇的那一刻。四目相对,四周的一切忽然静止,而他们内心却在大声呼唤出对爱的渴望。
歌剧的脚本由作曲家亲自撰写,四位人物的内心写照以对位般的手法穿插于舞台上的四位主角之间。心灵的独白以及灵魂的对话在潜意识与真实的世界各个层次之间相互流动。当男女主角初遇的时候,女主角如同耳语般地唱出“易碎品,捡时当心”,而她的内心角色则被男主角炙热的目光所吸引,唱出“你的目光如此炙热”。电声同步传送出预制音效,来表达最深层的潜意识感受台词“你是谁”。
除了乐池中的三管乐队之外,舞台左右两侧是两个独立的室内乐演奏家小组。右侧是低音提琴演奏家福森艾格(Uli Fussenegger)以及声乐演唱家奥尔伯特(Frauke Aulbert)。左侧是Ensemble Nikel的四位演奏家,他们演奏的乐器分别是钢琴、打击乐、电吉他和萨克斯,透明的黑纱网将他们与观众席隔开。剧场两侧的二层包厢中安置了十六位声乐演唱家小组,他们除了营造剧中各场景所需的气氛外,同时也肩负打击乐演奏家的职能,承担了作曲家完成剧场声学中立体且生动的层次感的重要职能。
用声音传递人物内在的心理状态和感觉的细微变化,是这部剧刻画的核心。作曲家选择诠释潜意识的方法,是为剧中的两个主人公分别设定一个幻影般的内心角色。剧中的他和她都分别由两个演员完成:真实的自我身着彩衣,他们的图像与投影中的角色相吻合;而潜意识的自我则分别由身着黑衣的另两位歌唱演员扮演,唱出男女主人公潜意识中的心理变化——她和她的心声,以及他和他的心声。
大幕升起,低音提琴独奏在极端音区奏出超乎乐器音域的极速音流。舞台上的他们僵直地坐在椅子上,两盏聚光灯投下毫无生气的白光,显得凄冷而空虚。声乐独唱家以及室内乐队逐渐进入到低音提琴精致且细密的音流中。舞台的大部分被黑暗所笼罩,灰色的阴影正是他们的心灵被孤独和空虚吞噬的写照。序幕结束,独奏家们营造的细密的音流逐渐转移到弦乐队上,在高音区稠密的微分音群的烘托下,舞台开始旋转,一座简约的包豪斯风格小楼被转到舞台的前方。同时,这座建筑的微缩模型也在剧中建筑师男主角的书桌上反复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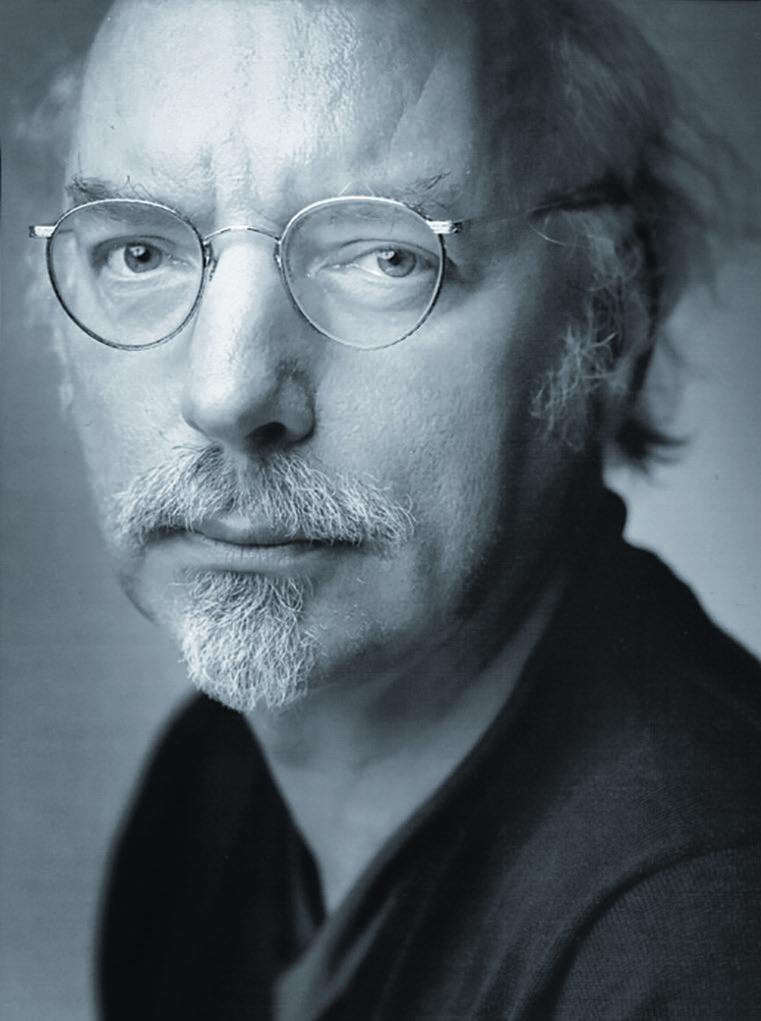
作曲家极其注重人物内心的描写。乐队在大部分时间中用细微的层次、极端的音区和大量的分部演奏来描绘人物内心的意识流。音乐上内在张力的延伸,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弦乐勾画的几乎宁静的力度瞬间达到铜管风暴般的爆发。这种对比展示了爱情中不经意的一句话在爱人心中卷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全剧由十三个场景组成,其中三个由梦境为内涵的场景穿插在其他日常生活场景之中。整部歌剧使用了如同耳语般安静的歌唱风格,每位演员发出的气声音节,及其细微地描绘内心丰富情感的音色都被调音台放大,并通过扩音设备传送到剧场的每个角落,形成多相位的复调声场。歌剧的对白近于口语化,“嗨!拿起你的电话!你在家里吗?”简单的词汇让音乐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管弦乐队在如此清晰的对白下爆发出如洪水般强大的音响,同时夹杂着钢琴用手臂敲击键盘的音簇,来描写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处对爱的强烈渴望及无比恐惧。
另一个场景中,投影屏幕上展示了黑色的蚂蚁在建筑模型以及女主餐具上探索爬行,声乐演唱家们发出婆娑细碎的气声音流,来模拟蚂蚁的触角相互接触摩擦的声效。同时女主人公仔细审视自己手臂皮肤的动作诱导了观众的联觉,连同剧场营造的寂静氛围,传达了女主内心世界对于爱情的渴望和煎熬。指挥家、作曲家卡利斯卡(Joahnnes Kalizka)把这些写在两百页谱纸上的固态音响,还原为流动的液态音效,将作曲家头脑中的音效还原在剧场中,并传送给听众。
舞台导演为1964年出生在法兰克福的克劳斯·古斯(Claus Guth),这位在欧洲戏剧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的大多数作品以探索性和前卫性著称。在《心房震颤》中,他已近乎实验电影镜头的视角在舞台上展示了一系列对比鲜明的画面。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观众的内在感觉与舞台的外部呈现保持同步。极富艺术感的黑白画面与舞台上的冷色调保持一致,而在场次切换时色彩的反转却在猛然间把观众从梦境带回了现实。孤独、怀疑以及恐惧,对真爱渴望的同时望而却步,心与心的距离既是世间最远的距离,同时也近在咫尺。“火星”与“金星”(代指男人和女人)在剧中的最后一幕回归了彼此的灵魂居所,女主角温情无限地望向她的建筑师,缓缓地唱出“我爱你”。冷漠的大时代反而需要更多爱与温暖,无论严冬还是盛夏。

女作曲家在我们时代中的地位和影响
捷诺文1957年出生于海法,这座位于以色列北部的第三大港口城市目前拥有近一百万人口。“和律师或者医生不同,没有一条清晰的道路告訴作曲家该如何成长。成为艺术家是一条异样的道路,而且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尽相同。”当时的以色列没有任何对于艺术家的支持。捷诺文二十六岁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来到柏林艺术大学(UDK)后,她并没有进入作曲专业学习,而是跟随施内贝尔(Dieter Schnebel)进入了实验音乐专业,并开始学习作曲。女性作曲家的道路尤其艰难,在很长的时间中,虽然作品在音乐会上演出,但是她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委约创作。直到四十二岁那年,她的歌剧《最深处》(Pnima...ins Innere)在慕尼黑音乐双年展上演出获得成功,才真正受到了瞩目和关注。捷诺文一直小心避免在德国被贴上犹太作曲家的标签。之后,她的音乐逐渐蔓延到世界各地的音乐舞台上,作品的演出遍及几大洲。
我向捷诺文约了采访。当我到达约定地点时,咖啡馆门口捷诺文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身着黑衣的她站在柏林冬日难得一见的阳光中,显得平静且舒展。因为参加歌剧院的排练,她已在柏林逗留数周。五天之后便是首演的大日子,然而她身上仍旧透露出淡定以及从容。坐定之后,她用平缓清晰的语调叙述着她和她的《心房震颤》。
“这不是一部拘泥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虽然我们在剧院中看到的是舞台上的一对男女渴望爱情,同时被爱情中的不确定性相互伤害的故事。每个角色在剧中的台词并不多,这在戏剧时间中留出了大量的空间,使得他和她以及他们各自的内心角色有足够的空间来展示心理变化。这种写作台词的风格如同写作总谱一般,让乐器和声部之间留出大量空间,使得更多的声音可以通过这些缝隙被听见。这种对位的写作手法也正如爱情中的口是心非,平行复调空间展示了潜意识之间的对话。”在创作初期,作曲家本人头脑中绘制了一幅结构细密的蓝图,只有她知道通过这些词藻来表达情感的正确途径,同时将意图嵌入相应的空间中。二十一世纪很多人开始喜欢独居,生活中不再需要唯一的伴侣,独行侠们很难向另一个人全面展开自我,这使得“冷漠”的时代中,爱与选择孤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和复杂。
在生活中,捷诺文既是母亲又是妻子,同时还是哈佛大学的作曲教授。而生命历程中,她总在不断地前进,寻找新的生命律动。她把这种诉求解释为以色列民族对于寻找新鲜事物的传统:“你在世界各地任何角落都会碰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总希望找寻一些新的东西,这个民族有一种对于文化的饥渴。”
在写作《心房震颤》之前,捷诺文已经有另外两部舞台作品问世:第一部是2000年首演于慕尼黑双年展的《最深处》,以以色列最负盛名的作家格罗斯曼的小说《证之于:爱》(See under: love)为基础,描述了1960年生活在以色列的男孩与他的祖父在了解大屠杀的历史创伤后成长的故事,此剧亦侧重于音乐对心理活动的刻画描写。第二部是2017年描写战争之恐怖的《现在即永恒》(Infinite Now),剧中她将比利时戏剧作家佩策瓦尔(Perceval)的舞台戏剧作品与中国超现实女作家残雪的小说融合在一起,叙述了一位残暴的欧洲男性以及一位在逃亡中寻找世界尽头的女性的故事。
我认为,《心房震颤》的首演向观众展示的是一种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简约的舞台设计在不断反转之间构筑了清晰的戏剧结构。激进的乐器音色调制出来的声音和图像搭建了视觉与听觉双向的意识流。全剧在多方面打破了我们在常规认知中对于舞台声乐作品风格的传统认知。一对无名的人类男女,在舞台上赤裸裸地展示了内心的各种骚动、不安以及渴望,多方位地展现当代人与孤独、空虚以及爱情之间的关系。也许通过戏剧的启示,城市中更多寂寞的心灵会敢于走出自己狭小心灵的居所,同时面对真爱付出自己的勇气与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