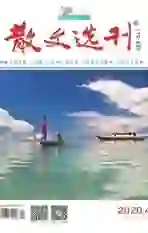烟雨中山路
2020-05-20罗星航
罗星航

雨,瓢泼似的,鼓槌般敲打着房屋和地面,惹人牵挂。
早晨,我走在沙市中山路上,风一阵紧似一阵,街面若隐若现,雾气弥漫,路旁青草微晃,树枝慢摇。东西走向的中山路略显苍老,南北接洪家巷、觉楼街、共和巷、巡司巷、杜工巷、青阳巷等二十多条街巷,恰似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的道道皱纹。
据记载,全球以孙中山命名或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道路达360条。而沙市中山路,始建于1932年,1934年竣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为中山大马路,1953年铺设沥青路面,后多次修整,如今为刷黑路面。据《中国城市建设史记载》,明中期,沙市已成为全国十二大商业都会之一。《广阳杂记》称“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条,及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沙市整体的市政建设始于1928年。中山路一带早期并没有路,一些商埠、酒楼、茶社集聚在此,渐渐形成闹市,商圈不断扩大,早已满足不了居民需求。中山路建成后,两侧分布着全市大部分商店、餐馆、茶社、银楼和银行,宽阔的马路人流如潮,商业门楼星罗棋布,许多建筑物具有欧美风格,三四层高的尖屋顶楼房比比皆是,八十八行十三帮商会都在此设有商号,老天宝、老同震、老万年、老丹凤、老宝成、新凤祥等银楼,荆江春、鸿运、珍海、好公道等酒楼,陈洪泰、同兴裕、大吉祥、裕生圆等百货店,公和、公益钱庄,徐万源匹头号,振太昌、吴庆昌酱园等知名商号都在此开店。
中山路的百年老字号生意都很旺盛。位于中段的老天宝格外引人注目,相当于五层楼高的建筑大体呈红色,底层门面宽大高耸,二层中间开欧式前沿立柱小门,配四个窗户,顶层两侧各有一个单立天窗,中间空出部分镶有银楼字号。早前卖金银首饰的都称银楼,开设银楼的人购买金条、收购旧金银器熔炼成首饰后出售。沙市金银店号大都由浙江人和江西人开办,浙江人创办的老同震是沙市银楼业第一块招牌,周转金量在400两左右。遍布中山路的金银楼、水运业和百货店,给沙市带来了商业繁荣,应运而生的便是银行业。英、日等国最早设立了怡和、太古、日清、吉田等公司和洋行,清光绪末年,沙市的钱庄就有三十家。1906年,湖北官钱局为推行铜圆兑换官票开设了沙市分局,这是沙市第一家地方官办金融机构。八年后,设在中山路刘家场的中国银行沙市办事处成立,是沙市第一家银行。到了1927年,沙市有大大小小钱庄104家,1200多名从业人员。
如今的中山路,依然是沙市的商业中心和人口集聚地。
不吃早堂面,则白来中山路一趟。
天刚蒙蒙亮,门口就排起了队。“来一碗大连面”,师傅接过牌子,另一位师傅手抓一小把碱水面,放进一个锥形的篾漏斗里,再沉在开水锅里掂了三下,然后盛入碗中。之前接牌子的师傅舀上翻滚的面汤,肉块、鸡子浮在水面,好像还有大骨头。师傅用大拇指、二指和中指拈起五片猪肉,一小撮鸡丝,一小撮油炸过的鳝鱼骨头,再递给客人。顾客也用汤匙挑起一小撮香葱撒在面上,便往里找凳子坐下,终于可以专心吃这碗面了。这是大连面,中连面里面放的是猪肉片加油炸鳝鱼骨,一般的早堂面就只有猪肉片。
一碗面吃舒服了,全天都舒服。吃沙市的早堂面有讲究。一般不能先吃肉片,因为肉是事先做好的,有点咸,必须在汤里泡一会儿,还有,鳝鱼骨头也要多泡,面汤才更鲜美。你得先来一碟泡菜,开开胃,再一筷一筷地吃面,吃了大约三分之一后,便可吃肉片、鸡丝,再后嚼嚼鳝鱼骨头,将面吃完。最后喝那用肉块、骨头和鸡熬出的汤,那汤,加上鳝鱼的香,啧啧,乳白乳白的,油花飘荡,香葱拂面,热气阵阵,暖意缓缓弥漫肺腑,你不来个一喝见底才怪呢?
吃早堂面不能慌,得慢慢来。吃快了会烫嘴,慢了汤则变冷,面上会凝一层油。也不光只低着头吃,一般情况下,吃一口,会瞅瞅周边,对面的也瞅瞅你,一来一往,就显得十分亲热。吃面的都是常客,久而久之,再相见就打起了招呼,一句问候,又亲近了许多,真是养性。
沙市的早堂面很有讲究。据史料记载,大约1830年,沙市的早堂面是一个叫余四方的咸宁人开的。他当时总结沙市人有三多:起早床的多,爱油大的多,在外面过早的多。因此,每天半夜开始,他便将鸡架、猪大骨和鳝鱼骨放在一起熬汤,直至熬成乳白色,汤味鲜而不腻。然后选用鸡脯肉、瘦猪肉、鳝鱼做大码,用肥猪肉做小码,这样做出来的早堂面鲜嫩可口,味道绵长。从此,沙市的早堂面传扬开来,百多年来一直具荆沙地区早餐榜首。
好公道酒楼不大,一层摆几张简陋的桌,几个矮小的凳,墙壁上基本没粉刷,许多面馆的窗户,冬天还飘进雪花,老板用油布遮挡着。无论多大官员,无论身價多少,走进了这家面馆,都是食客,都一样端着碗吃面。不需客套推让,忘记了世态炎凉,只记住一件事,吃饱,吃好。
中山路上的杜工巷,是人们为纪念杜甫而建。巷内茶楼遍布,戏院林立。
一个叫江津茶馆的,砖木结构,十张可坐八人的方桌,一条条长板凳因客人众多,早已被磨得锃亮锃亮的。一尺来高的土台子上,摆着一张长桌,穿长衫的说书人在上面借古喻今,推波助澜。那时的人们到茶馆就是喝茶、听书。说书人大都念过几年私塾,拜过师傅,八分钱一杯茶,一场评书分三场,中间休息15分钟时,跑堂的便把茶客们的杯盖收集到说书人看得到的地方,以便他知道今天来了多少客人,收入多少。茶馆里既有绿茶的绵香,又夹杂着烟卷的混合味道,好在客人们专心致志听书,顾不了许多了。
沙市以说书为主要内容的茶馆一直开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记得白阳巷附近有一家茶馆,31个桌子,人数最多时达四百多。八分钱一杯茶,说书人得3分,一本《水浒》讲下来得两个多月,客人们手捧一杯茶,听得津津有味。长江的水用明矾沉淀后,再用铁皮壶烧开,炉火很旺,上面“扑哧、扑哧”冒着水汽,九个水壶还不够用,老板经常到邻居家借篾制的暖水壶救急。茶水由香浓到寡淡,由滚烫到温热,茶客们全然不知,真是如痴如狂。
老街巷,老字号,这些承载着中山路的兴衰、人文的历史,总是那么神奇。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