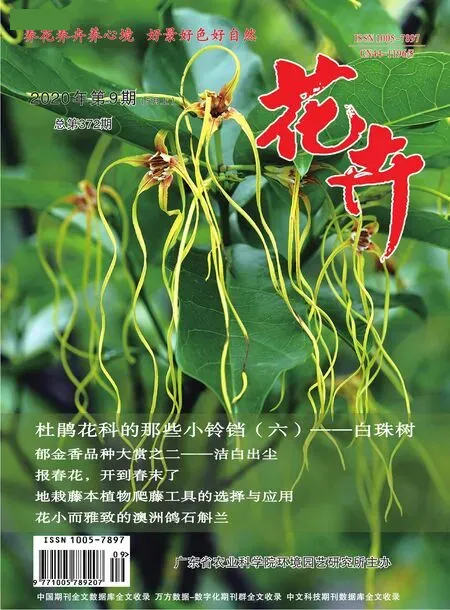杏花春雨江南
2020-05-19福建胡冬平
福建/胡冬平
中文就是这么神奇,有时简单几个方块字,就会构造出一个意蕴无穷的迷人世界。
“杏花春雨江南”可为绝佳例证。三个词,六个字,单看很普通,组合在一起,却威力惊人,立刻会引发出无穷无际的联想。特定空间、特定节气的许多经典景象,如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白墙黛瓦,烟雨迷蒙,山似眉峰,江水如蓝,诸如此类,瞬间浮现脑海。甚至可以说,要找出比这更好的句子来形容江南春日之美,有点困难。
然而,我又时常疑心这句诗有误,杏花是否该替换成桃花呢?桃花在江南随处可见,杏花却似乎没有见过。作为工作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几十年的江南人,在江西没见过杏花,没吃过杏子,在宁波同样如此。江南有杏花么?或者古时候有,现在没有?
后来,我查了该句的出处,人家元代诗人虞集明明白白就是这么写的。可巧,这位作者也是江西人,生于才子之乡抚州崇仁,为元诗四大家之一。他在一阙寄给朋友浙江仙居人柯敬仲的词《风入松》 中,写下了“凭谁寄、银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这样的句子。
浙赣两省地域相邻,物候相近,“杏花春雨江南”应该是他们两人关于家乡的共同记忆吧,故被词人用来作为“乡愁”的意象代表,这和晋人张翰的“莼鲈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虞集的言外之意,是想用张翰这句警语,安慰被谗言落职的柯敬仲。
后人不一定记得全词,但这六个字,却被广为流传,甚至成为很多书、画、印、文的重要题材。著名画家徐悲鸿就曾自题一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一雄奇阳刚,一秀丽温婉,可谓绝对。诗人余光中在其散文名篇《听听那冷雨》之中,也阐发了此一意蕴。如果说张若虚是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那虞集则是凭这六个字“横绝千古”。
在江南,杏花和春雨,好似一对佳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前代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里,亦可印证这一点。南宋陆游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写的是临安杏花。“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是陈与义的名句,曾得到宋高宗激赏,写的是湖州杏花。而南宋诗人释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直接就把二月春雨唤作杏花雨了。


北方农历二月,“春雨贵如油”,描绘杏花的作品,少了雨的湿润,倒是多了些月光的轻盈。东坡先生知徐州时,写过一首《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诗曰:“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萍。”在他笔下,人与花与月,都是有生命的,杏花飞帘,明月入户,主动来找诗人,诗人欣然赴约,携客置酒踏花影,醉舞于杏花之下,场面实在太美,难怪人家称他为“坡仙”。陈与义另一名作《临江仙?忆昔午桥桥上饮》,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之佳句,亦是描绘月下杏花。
在古代文学作品里,杏花是南北皆有的。那么当代呢?之所以会提出怀疑,估计很多人和我之前一样,因为不认识杏花,以至于视而不见。现实之中,分不清桃李梨樱梅杏的人十有八九,故曰无杏花。另一方面,可能真没见过。我和不少园林界专业人士聊过,他们都说,南方园林很少用杏花,因而南方城市人要想在自己的城市见到杏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宁波,杏树也是有的,不过多在乡间。2018 年3 月份,去宁海茶山看二叶郁金香,回程路过龙潭村,瞥见路边人家院子里有几株红萼白花的花树,初以为江梅,转念一想,花期不对,此时梅花早已落尽,甚至有些已枝间有子初成了。于是停车观察,当看到花朵背面反折的萼片,才知道原来这不是江梅,就是我苦苦寻觅多年的杏花,那一刻真是欣喜异常,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应该就是这样吧!
车继续往象山方向行驶,去往另外一个目的地。在路边一个村落,又看到了两树粉色云霞,这又是什么呢?细细观察,居然还是杏花,颜色比龙潭村的更加娇艳。不知是品种不同而致花色有异?还是花开不同阶段而导致颜色有变?
忽然想起,古人“红杏枝头春意闹”“一枝红杏出墙来”之“红”,也许就是这种淡淡的粉红,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那种深红、大红。诗人杨万里对杏花之色,有十分经典的描述:“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宋徽宗《宴山亭·北行见杏花》也有精彩描述:“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杏花的颜色,就好比绝色佳人的脸颊,白中带粉,粉里透白,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美。
在北方,杏花却是城乡常见树种,轻轻松松就可以遇见。2018 年6 月去烟台出差,在毓璜顶公园附近一户人家院子里,看到一株果实初黄的大树,主人告诉我这就是杏树。春天在宁波初识杏花,夏天就在烟台看到杏实了,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么?前段时间出差河南,在漯河市舞阳县一个村落走访,看到好些农家小院里的高大杏树正含着紫红色的花苞,在蓝天丽日下非常引人注目,可惜没带相机。返程那天早晨,我信步走到沙澧公园,忽然偶遇十来株颇有些年份的杏树,且二三株正芳华初绽满树如雪。这个意外惊喜让我猝不及防,赶紧跑回宾馆去取相机,留下了一些满意的图片,算是为这次河南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宁波城区,我只在鄞州公园东南角的梅树中间,看到一些杏树。这也是那次茶山之行后的新发现。认植物就是这样,一旦熟悉了,它们也就随处可见了。不知是园林工人搞混了,还是有意为之,里面梅杏比例几乎各半,倒为我观察杏树提供了不少便利。这三年来,我年年留心观察,期待一睹盛况,拍点春雨杏花之类的图片,但这些杏花总是开得稀稀疏疏,今年亦然,连拍张像样的花枝都很困难,殊为憾事!
也许杏树是归属于乡村的,它们习惯了在村头、在河岸、在院落自由自在生长,不喜欢城市的喧嚣,不习惯这样被圈养着。说来也是,离开了乡野自然的杏花,还是那“春雨江南”的杏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