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四种身份与多元起源论
——结合Akchakhan-kala遗址考古新证①
2020-05-19程雅娟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江苏南京210013
程雅娟(南京艺术学院 艺术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13)
近十年以来,对于入华粟特人葬具中出现的“人鸟祭司”的母题、身份、文明来源、宗教内涵问题一直是观点辈出,主要研究观点如下:《考古报告》称:史君墓所见半人半鸟形象为“人身鹰足祭司”;韩伟将安伽墓墓门所见的半鸟半人形象与虞弘墓图像及中亚苏尔赫考塔尔遗址所见图像做比较,认为“此类图像为专司祭祀的神祇”[1]108-109,[2];法国考古专家葛乐耐教授F. Grenet 曾将其比定为琐罗亚斯德教神祇达曼•阿芙琳 Dahmān āfrīn[3]35-38;张小贵认为:“半人半鸟形象应为护持火坛的祭司,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象征,其创作意匠乃受古波斯“神赐灵光”的影响”[4]131;姜伯勤先生认为:“安伽墓门额所见‘人头鹰身’图像为祆教‘赫瓦雷纳神’”[5]92-95;法国学者黎北岚认为:“人鸟母题的创作与中国墓葬中的鸟形象以及天门主题有关。”[6]95
以上众多观点基本都是从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的观点出发提出对“人鸟祭司”身份的推断。至今为止,还未有对于其图像演变的系统分析的论文,也使得对其图像学的研究结论较为薄弱。另外,几乎所有观点都建立在同一个共识之上:入华粟特人葬具中发现的“人鸟祭司”身份是单一的。而众所周知,受到早期波斯艺术翼兽艺术影响,中亚地区出现过大量不同类型的有翼兽或人的复合形象,入华粟特人葬具中出现的“人鸟祭司”双翼特征明显存在多元性。另,所有研究都不可避免一个问题:目前所有研究结论基本依据的都是国内发现的实物图像,而作为“人鸟祭司”的家乡—中亚的考古材料缺乏,导致了无法建立完整的传播体系,更无法将中原与中亚的“人鸟祭司”进行系统比对。而本文主要结合中亚Akchakhan-kala遗址新发掘的“人鸟祭司”考古图像,从中亚至中原完整的“人鸟祭司”图像进行系统化类别化分析研究,以期从其发源地文明中归纳出“人鸟祭司”的多元身份以及传播演变特征。
一、中亚的“人鸟祭司”的多元起源
首先,从考古发现来看,早期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多种复合生物图像体系。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自1870 年成立不久,就开始大量收藏萨珊国的印章,据《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萨珊印章》[7]一书中记录,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的200 个印章中有着大量萨珊文明的复合型动物图像。这些复合动物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清晰的原生动物特征或者独立的神格,如拉玛苏(具有翅膀的公牛或狮子和人类雄性的头部)、格里尔勒丝(人首公鸡)②格里尔勒丝Gryllus, 源自意大利语gryllus. Gryllus 在拉丁语中是“怪物”的意思。原指各种各样的人类与动物身体或头部组合的复合形象。——Gisela M. A. Richter《Catalogue of Engraved Gems: Greek, Etruscan, and Roman》,第114 页。、人首马身(男性上身与有翼马的混合形象)、森鸟(狗的耳朵、鹰的喙和翅膀,狮子的身体)、翼羊、翼马等等;另一类则依靠想象力将原生动物特征完全重组,呈现完全混合的装饰形象,如动物上身的混合体、三个动物头部的混合体、动物头部组合成的绳结等等。
其次,从文明传播角度来看,来自波斯文明的多种复合生物图像也曾传入中亚地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居鲁士大帝于公元前553 年—前550 年击败了当时统治波斯的米底王国,使波斯成为一个强盛的君主制帝国。公元前546—前540 年,居鲁士大帝向东,武力入侵,征服了帕提亚、阿利亚、巴克特里亚、德兰吉亚那、格德罗西亚、阿拉霍西亚、马尔基安娜、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索格狄亚那)等地区,使得波斯艺术对中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波斯复合生物图像体系传入中亚地区,催生出了中亚本土化的复合生物图像体系。
最后,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化艺术也对中亚地区的“人鸟祭司”产生了影响。公元前334 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率军进攻波斯,继而开始了著名的东征,历时十年,经过伊苏斯之战、高加米拉战役、吉达斯普河战役,亚历山大征服了波斯、埃及、小亚细亚、两河流域。亚历山大的东征将希腊文明与希腊化艺术带入中亚,自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开始与中亚本土的造型艺术结合,产生了中亚化的希腊艺术。贝格拉姆发现的一座有着典型希腊艺术特征的人首公鸡青铜像(图2),具有男性头部与公鸡的身体,而该“人首公鸡”的身份则代表了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是希腊神话艺术与中亚复合动物形象的混合代表。
综上所述,来自古代波斯艺术中的多种复合生物图像体系,在波斯帝国疆域版图扩大至中亚时期传入中亚地区,与本土艺术融合产生了中亚多种复合生物图像体系,之后又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使得来自中亚的入华粟特“人鸟祭司”存在复杂的多元起源。
二、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的四种身份
1.代表中亚“斯罗什”之鸟的“人首公鸡”
第一类是来源于中亚地区代表“斯罗什”之鸟的“人首公鸡”。在琐罗亚斯德教中公鸡具对抗恶魔的神格特征,反映琐罗亚斯德教的宇宙观和宇宙学集合的经典著作《Bundahishn》的第19 章曾写道:“公鸡是与恶魔和巫师为敌而创造的,与狗合作;正如启示录所说,在世上的生物中,与斯罗什合作消灭恶魔的是公鸡和狗。”琐罗亚斯德教的重要著作《万迪达德》(也称《驱魔书》,中古波斯语称“维迪弗达特”,意为“祛除魔鬼的方法”)FARGARD 18 中写道:“人们称呼公鸡为正直的斯罗什之鸟,当他鸣叫时,会驱走不幸,使之远离奥尔马兹达的造物”。“斯罗什”是琐罗亚斯德教的“良心”和“遵守”教义思想的阿维斯坦名字,代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一种神性。
Mohsen Foroughi 收藏的一枚印章上,表现了一个有胡子,头戴耳环的男性向右走的图像(图1),颈部以下为公鸡的身体,四爪形态与贝格拉姆发现的青铜公鸡人像十分接近,公鸡尾巴被描绘成三条尾翎并列,拱起呈弧度并自然垂下,尾巴上方有一颗六角星,此应该是中亚地区早期以人首公鸡为特征的神祇。

图1 Mohsen Foroughi 收藏的印章(来源:Judith Lerner:A NOTE ON SASANIAN HARPIES[J],Iran, Vol.13(1975):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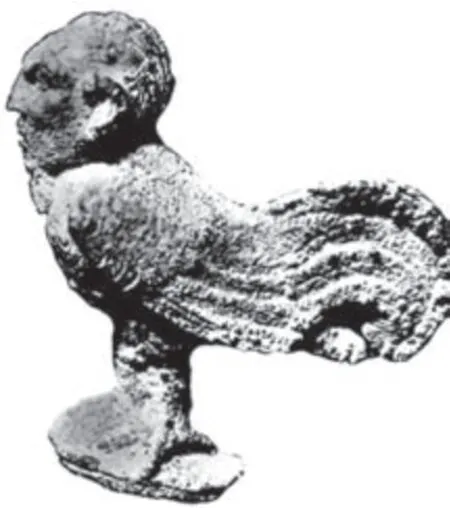
图2 贝格拉姆发现的青铜公鸡人像,现存于喀布尔博物馆
不仅如此,中亚地区这种代表斯罗什之鸟的“人首公鸡”还影响了来自希腊的神祇造型。贝格拉姆发现的一座有着典型希腊艺术特征的人首公鸡青铜像(图2),具有男性头部与公鸡的身体,公鸡尾翼较长,分成均匀的几缕翎毛并在尾端隆起,形成一个旋涡形状的公鸡尾巴,大部分研究结论都认为其极有可能代表了希腊神话人物“赫尔墨斯”。另外,在希腊罗马宗教中,“赫尔墨斯”还掌控了另外一个神祇“水星”,“水星”被作为“逝世神”能确保亡者灵魂安全通往后世。一个罗马宝石上表现了“水星”(图3),它被描绘成戴罗马宽檐帽的半人半鸡的“绅士”,它的尾翼与贝格拉姆发现的青铜雕像十分相似,三层翎毛组成的弯曲的尾巴,翅膀较长,左翅夹持“使节杖”。可见这类起源于希腊的神祇在传入中亚之后,与中亚本土的“人首公鸡”神祇形象混合,产生了全新的具有中亚特征的“人首公鸡”式的“赫耳墨斯”与“水星”。

图3 印章上公鸡人身的水星(来源:Judith Lerner:A NOTE ON SASANIAN HARPIES[J],Iran,Vol.13 (1975):168)
多年以来,很多学者都断定,此类“人首公鸡”复合型母题图像作为祭司的形象只在中国境内的北方粟特墓葬中陆续发现,近年终于在中亚本土也发现了完整的“人首鸡身”的祭司图像,证明了此图像来源于中亚地区的事实。2012 年,悉尼大学的Alison Betts教授在《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发表的一篇关于Akchakhan-kala 拜火庙遗址的报告中阐述“在中亚文明最北部的土地上发现了完整的‘人鸟祭司’壁画图像”。Akchakhan-kala 是位于阿穆达尔亚三角洲地区的一个大型防御基地,在古代被称为Chorasmia①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北部,部分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土,花拉子模部分地区,以及土库曼斯坦的西北部地区。Akchakhankala 建成于公元前3 世纪末或2 世纪初,并在贵霜早期被遗弃,在贵霜至Afrighids 时期十一区城楼在早期被破坏的基础上被重建,之后成为了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的附属之地。。Akchakhan-kala 遗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宗教仪式建筑复合群,被“卡拉卡尔帕克澳大利亚探险队”标记为“第10 区”②在中断近二十年后,而这一地区受到了悉尼大学中亚计划(USCAP)的资助,悉尼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卡拉卡尔帕克分会组建了“卡拉卡尔帕克澳大利亚探险队”(KAE),主要致力于Akchakhan-kala 遗址的发掘。因为考古学数据非常丰富,这些数据对国内研究入华粟特人的丧葬宗教图像艺术有重要启示。。此区域中心为一个60米乘60 米的正方形广场,双层墙形成一个连通四个方向的通道,南门进入中心建筑之后为一条走廊,末端右侧为一个主要中心祭祀点,左侧则进入一个“柱式建筑”,该柱式为重要仪式殿堂[8]125-127。从柱式大厅中回收了一组连续的大块石膏。当清洁并重组后显示出一幅身穿长袍的巨大男性壁画形象(图4)。他穿着一件长上衣,上衣中间部分有一个宽阔的长条板,被分成更小长方格单位,每单位里都是一对相对站立的“人首公鸡”的重复图案(图5)。它们所戴的特殊面具显示:他们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牧师。一只手拿着与琐罗亚斯德教仪式相关的一束巴罗姆树枝(图6),“人首公鸡”祭司上还出现了“卐”字纹饰装饰。在巨型人像右大腿上,长袍被吊带支撑着剑展开,露出裤子,上面装饰着长腿长颈鸟的重复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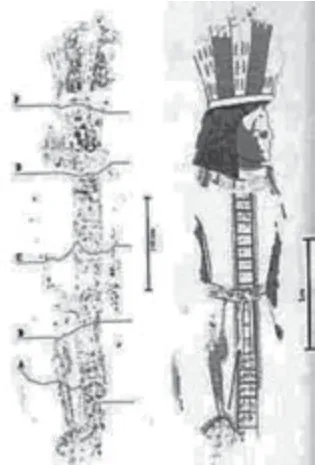
图4 第10 区柱式大厅中的巨大人像复原图(来源:Alison Betts:The Akchakhan-kala wall paitings:New perspectives on kingship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orasmia[J],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12:156)

图5 巨大人像上衣前身中间的“人面公鸡”祭司(来源:同图4)

图6 修复重建后的“人像公鸡”祭司图像(来源:同图4)

图7 中亚苏尔赫- 考塔尔遗址
而在中亚苏尔赫—考塔尔火坛遗址之火坛一侧也发现了接近“人首公鸡”祭司的图像(图7),下半截与Akchakhan-kala 拜火庙巨型男性壁画上衣上的“人首公鸡”图像极相似,可惜上半身漫漶,但是其遗存中的双翼为“弯月”形双翼,双足短而纤细,爪也不类鹰爪巨大,从其残存图像判断应属Akchakhan-kala 拜火庙的“人首公鸡”体系。
在琐罗亚斯德的传统中,金瓦特大桥是所有死者的灵魂都必须跨越的“判断之桥”,“斯罗什”神(Sraosha)是金瓦特大桥的三个守护者之一。虽然斯罗什只是三个通过判断的神之一(另外两个是Rashnu 和Mithra),但是只有“斯罗什”陪伴着灵魂穿越大桥。③The cock is created in opposition to demons and wizards, cooperating with the dog; as it says in revelation, that, of the creatures of the world, those which are cooperating with Srosh, in destroying the fiends, are the cock and the dog.中原地区发现的粟特墓葬中最接近中亚“人首公鸡”祭司的图像为北周安伽墓门额浮雕上的“人鸟祭司”(图8)。安伽墓半圆形门额上正面减地刻绘袄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下方各有一祆教“人首公鸡”祭司:卷曲的头发,深目高鼻,胡人面庞上戴着“帕达姆”口罩。鸟身横向身体长度要大于纵向长度,上身着胡袍。胁下生出弯月般的双翼,与Akchakhan-kala 拜火庙巨型男性壁画上衣上的“人首公鸡”双翼一致,都属于公鸡双翼,但与后者不同之处在于,双翼为打开状,尾巴仅仅几撮短小的羽毛表示。两位 “人首公鸡”祭司双腿分立,双足略短,足爪犀利未及鹰爪粗壮,手执树枝指向供案,作祭祀状。

图8 北周安伽墓 门额浮雕,来源(来源:单海澜:祅教祭司鸟神与千秋、万岁图像之比较研究[D]:3)
综上所述,中亚地区代表“斯罗什”之鸟的“人首公鸡”形态图像上具有一定的程式性特征:首先,公鸡横向身体长度要大于纵向长度,显示出与中亚地区鸟类不同的体型特征;其次,“人首公鸡”祭司尾部具有卷拱呈旋涡状的重要特征;“人首公鸡”祭司双翼体量较小,多为水滴倒置形状且收至身体两侧,并不表现出展翅翱翔的状态;“公鸡祭司”的双足有明显弯折,且较鹰类纤细,鸡爪也较鹰爪小很多,爪子有四个脚趾头,前面三个大的,后面一个小的。
2.源自古希腊的有翼女性祭司的“人鸟祭司”
第二类是来自古希腊神话的“哈耳皮埃”(Harpies)与“塞壬”(Siren)两位神祇。它们都是具有人头鸟身形象的神祇,其中“哈耳皮埃”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圣之母,常被描绘为女人身体,翅膀、尾巴及爪似鸟的怪物。他们经常是惩罚、绑架人,并在去哈德斯领地的路上折磨人,被上帝用作惩罚罪犯的工具。另外一位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她常站在岩石岛屿的海岸上,用迷人的音乐和歌声引诱附近的失事船只的水手。

图9 哈尔比亚之墓,公元前500年-前475 年,伦敦大英博物馆藏(来源:作者拍摄)

图10 弹奏里拉(琴)的塞壬,公元前370 年,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来源:作者拍摄)
哈尔比亚之墓座落于被遗弃的Xanthos 市大理石墓穴,建于波斯阿契曼尼德帝国,属于利西亚文化。①古利西亚的首都,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现在的土耳其。大约公元前480-470 年,该墓室顶部有一根高大的柱子,装饰有大理石板,上面刻有浮雕。陵墓是为一位伊朗王子或Xanthus 州长建造的,也许是凯伯尼斯。大理石室是古希腊风格的。它深受希腊艺术的影响,但也有迹象表明,在雕刻中没有希腊的影响。这些浮雕让人想起波斯波利斯的浮雕。这座纪念碑取名于四个雕刻的女性翼形雕像,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哈耳皮埃”(图9)。利西亚人把希腊神话中的大部分内容吸收到自己的文化中,这些场景可能代表希腊神话,但也可能是未知的利西亚神话。另一种解释是,它们代表了来世的审判场景和向利西亚统治者祈祷的场景。利西亚占据了欧洲和西亚之间的战略位置。希腊和波斯的世界在利西亚相遇,而利西亚人则深受两者的影响,甚至成为两者的混合体。而这种女人身体、翅膀、尾巴及爪似鸟的怪物形象极有可能是通过利西亚这一中间地带向中亚地区传播。
另外一位则是来自古希腊神话的神祇“塞壬”。早期的希腊神话中的“塞壬”被描绘成有着女人头部、鳞脚,浑身长满羽毛的鸟。沃尔特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只希腊式的塞壬形状的古香水瓶(公元前540 年):整个形象除了头颈部为希腊式的女性头部,颈部以下皆为鸟身,尾翼长且扁,双翼收至身体两侧,鸟爪曲折收至身体下方。“塞壬”后期逐渐演变成腰部以上为女性身体,鸟腿,有或没有翅膀,演奏各种乐器尤其是竖琴的女性形象。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有一只潘泰列克大理石制的弹奏里拉(琴)的塞壬(公元前370 年)(图10),是在雅典的一座墓地发现的,塞壬正在哀悼死者,双翼折叠,正在弹奏古希腊的里拉琴。值得注意的是:希腊艺术中表现的无论是翼兽,或者人与翼兽的混合体,其双翼通常是平展作翱翔状,以“弹奏里拉(琴)的塞壬”为例,即便是作站立哀悼状,双翼丰盈,依旧作展开状,这是希腊化羽翼区别于其它地区羽翼形象的重要特征。古代安息王国时期的尼萨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只塞壬形式的镀金银杯(图11),其头部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藏的弹奏里拉(琴)的塞壬非常接近,发髻朝后属成高髻,是希腊时期盛行的女性发髻,羽翼也是希腊式的丰盈,两翅平展上扬的翱翔姿态,细致描绘了层叠的羽毛。该形象腰部以上为接双翼的女性身躯,腰部以下则接四条鸟腿,布满麟甲。

图11 塞壬形式的镀金银杯,土库曼斯坦的历史博物馆藏(来源:作者拍摄)

图12 尼姆鲁兹的AB 号房间内发现的(来源JOHN CURTIS:Mesopotamianbronzes fromgreeksite stheworkshopsoforigins[J]:13)
学者Stephanie Dalley 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语中有一个单词“samusarri”,这个单词在阿卡德语中曾经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是出现在一份并非亚述古语的文献中,可以翻译成“塞壬装饰”。②关于大英博物馆关于此物品展出记录在早在1884 年,Perrot 和Chipiez 就已经记录了这个位置(1884 年,第734 页,第2 页)。在希腊遗址发现了三个青铜锅的装饰物现在被认定出自亚述文明。其中一个似“塞壬”的青铜器(图12),是Layard 在尼姆鲁兹(西亚古城卡拉 Kalakh 的现代名称)的AB 号房间内发现的。有着典型美索不达米亚式的女性面貌和发型,背后平展的双翼,身后有一个环扣。它曾在大英博物馆的尼姆鲁德展厅展出过,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个物件的具体发掘档案已经遗失了。尽管如此,这个人物造型与面部细节无疑是美索不达米亚风格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 世纪,因为她的发型与丰满的身材更接近亚述时代末期风格,它证明了“海壬”这种希腊神话中的人面鸟身女神已经传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来自希腊的“哈耳皮埃”与“塞壬”皆为女性形象,从希腊本土至美索不达米亚,“塞壬”从人体头部和身体从女性逐渐转向男性,而且在希腊化时期的早些时候,甚至出现过雌雄同体的“塞壬”。在受到希腊文明影响的萨珊艺术中,出现了将“哈耳皮埃”“塞壬”转变为男性的现象,可能是由于萨珊波斯文明偏爱男性神话般的复合生物。绝大部分萨珊波斯的神话形象无论是纯动物或者人与动物的复合生物,似乎都是雄性居多。并且这种希腊式的母体图像还催生了巴比伦地区本土的人鸟神祇。在德尔菲地区发现了一只青铜男性雕像(图13)(现藏于丹麦博物馆),这个男性依旧有着亚述男性的特征,头发和胡须的细节与公元前8 世纪末至7 世纪初的亚述男性特征相符。这名男性身后有平展的双翼,背部至尾翼部分设计为倒置的棕榈叶花纹代替羽毛纹样,此类花纹在亚述青铜家具套筒上也出现过。大英博物馆的一枚印章上刻了一个人鸟复合体,上身为裸体男性人物,拿着一枚绶带装饰的戒指,腰部以下则为鸟身体(图14)。MAFOuz de Sogdiane 联合考古团在撒马尔罕地区发现了一块公元前6 世纪无釉赤陶尸骨罐,其上描绘了“人鸟祭司”图像,现收藏于Afrasiab 博物馆。嵌在联珠纹组成的倒三角内的“人鸟祭司”(图15):戴着萨珊波斯盛行的圆帽,耳朵上戴古代阿富汗地区常见的圆柱状耳珰,手臂上戴臂钏,嘴巴上戴“帕达姆”以确保祭司火焰的纯正性,双翼是典型的希腊“M”形状翱翔状的鸟羽双翼,这种羽翼分为内羽与外羽,羽翼丰盈,特别是外羽由由短至长的条形的翎毛构成。它左手似搭于右肩,右手伸出食指,似为琐罗亚斯德教中一种致敬的手势。

图13 青铜男性头像,德尔菲地区发现,丹麦博物馆藏(来源:JOHN CURTIS:Mesopotamianbronzes fromgr eeksitestheworkshopsoforigins[J]:15)

图14 大英博物馆所藏印章上,浮雕一上半身为男性,下半身为鸟的复合人物(来源:Judith Lerner:A NOTE ON SASANIAN HARPIES[J].Iran, Vol. 13 (1975):168)

图15 撒马尔罕地区的无釉赤陶尸骨罐上的“人鸟祭司”,公元前6 世纪,Afrasiab博物馆藏(来源:Alison Betts,:The Akchakhan-kala wall paitings:New perspectives on kingship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orasmia[J],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2012;163)

图16 西安北周史君墓南壁左侧的祭司与火坛(来源:作者拍摄)
中原地区与“哈耳皮埃”或“塞壬”最具关联性的祭司图像,即今西安市未央区井上村东发现的北周史君墓出土的石堂上的“人鸟祭司”。该石堂南壁窗上各有四个伎乐,两个直棂窗下分别各有一个戴口罩的“人鸟祭司”(图16),考古发掘报告上称呼其为“穆护”,祭司各手持树枝,面对火坛进行火祭。这名祭司腰部以上为人像,腰部以下则为鹰身,头戴1-4世纪波斯地区常见的头巾,头部蓬松卷曲成圆髻,未戴“帕达姆”口罩,身着粟特圆领窄袖袍,腰部系带。肩膀处伸出希腊“M”形式双翼,羽翼丰盈,内羽由凸起的圆形短羽毛组成,外羽由条形的羽毛构成。其羽翼与撒马尔罕地区的无釉赤陶尸骨罐上的“人鸟祭司”几乎完全相同,究其源头都受到了来自古希腊的“哈耳皮埃”或“塞壬”祭司形象的影响。祭司下半身与大英博物馆藏的印章上“人鸟祭司”接近,四条羽翎组成的尾翼上装饰联珠纹,足似公鸡足般弯曲,不似鹰足粗壮笔直,爪更接近鹰爪般锐利。
综上所述,北周史君墓出土的石堂上的“人鸟祭司”是一个特殊案例,极有可能是中原工匠在综合了中亚地区源自古希腊的有翼女性祭司的多种特征,并添加想象而成的特殊祭司形象。这并不是孤例,日本MIHO 藏的粟特葬具图像中也出现了人物镜像和宗教图像内容的错误,日本专家因此认为,这是由于中原工匠不甚了解琐罗亚斯德教义导致。
3.来自古伊朗“神赐灵光”的鹰类祭司famarh
第三类是来自古伊朗“神赐灵光”的鹰类祭司famarh。沙赫巴滋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出现的有翼人像并非是阿胡拉马自达,这些被赋予了神赐灵光的形象都满足了以下条件:1、与伊朗国王有着私人的亲密关系;2、与猎鹰有特殊关系,因为很多羽翼表现为猎鹰的平展的双翅;3、佩戴皇家徽章,尤其是王冠……” 沙赫巴滋认为,这种平展的双翼即为“猎鹰”之翼。关于有翼人像的身份,沙赫巴滋认为,满足这些条件的只有来自古代伊朗传统的“神赐灵光”概念,即“Hvarnab”,“神赐灵光”化身为一个独立的神祇即“famarh”(FARR(AH),XᵛARƎNAH)[9]2。来自阿胡拉马自达的居所之地,并以物理可见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它移动非常快,通常地球上与天空中能快速运动的动物如猎鹰被视为它的化身。在一枚贵霜钱币上刻有famarh 神,男性形象,头戴圆帽,后有发带飘荡,肩膀上燃烧着火焰,左手持权杖,伸出的右手上端着一碗火(图19)。

图19 贵霜银币上的famarh 神祇(来源:Shahbazi, A. S. 1980 An Achaemenid Symbol,II Farnah (' God Given Fortune Symbolised')[M]:11)
沙赫巴滋认为,古老伊朗人继承了埃及人与亚述人将鹰象征为王权的习俗,但却采用了全新的诠释,伊朗人将鹰视为神圣恩典的象征。“鹰”对于中波斯国王诞生之地阿契美尼德王朝来说意义重大,古代伊朗皇权的概念与“鸟王”即鹰有着密切关联。传说中,古代波斯国王阿契美尼德是被一只鹰抚育的,因此展翅的雄鹰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旗帜的标志。伊朗王后阿托撒曾梦见雄鹰化身成了伊朗国王。居鲁士大帝在《Ecekiel》(XVII,13)中甚至被称为“东方之鹰”。哈特拉是位于今伊拉克尼尼微省的一座古城,位于美索不达米亚贾兹拉地区,旧时也曾为大波斯一省的省会。古城内的供奉亚述贝尔卡拉①亚述贝尔卡拉:中亚述时期的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之子,继承阿沙里德-阿帕尔-伊库尔之位。他在位17 年去世,葬于亚述古城。的第五号神庙中,有一座“希腊伊朗式”的“亚述贝尔卡拉”雕塑(图18),“亚述贝尔卡拉”两侧面各站立一只“哈特拉之鹰”(图17),他脚下还站了另外一位希腊的 “命运女神”堤喀。“哈特拉之鹰”显然已经被赋予了神性,以一种高傲的姿态站立并平视前方,头部饱满,颈部有项圈,羽毛上部分呈层叠的鳞片状,羽翼一半以下刻绘细长的羽毛,双翼袖长脱垂至地面,似为鹰所着披肩一般。鹰的两爪笔直无弯曲,而公鸡祭司腿部则有明显的弯曲。

图17 哈特拉之鹰,“亚述贝尔卡拉”雕塑,公元2 世纪,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来源:Stuart GilbertandJames Emmons:Roman ghirshmanpersian art[M].1962:1)

图18 “亚述贝尔卡拉”雕塑,公元2 世纪,巴格达,伊拉克博物馆(来源:Stuart GilbertandJames Emmons:Roman ghirshmanpersian art[M].1962:2)
“famarh”与“鹰”有何密切联系呢?在《Avesta》中,“神赐灵光”有几种形式,其中之一是一种名叫“瓦雷纳”的猎鹰,它总是展翅翱翔的姿态,与伊朗战神Bahrām 有关,“瓦雷纳”还被装饰在萨珊国王Bahram II 王冠上。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晚期,猎鹰“瓦雷纳”被赋予了神话中的角色“鹰龙”,且命名为“Saena.murya”,继而演变成了“Semury”,而根据《ZAMYĀD YAŠT》XIV②《ZAMYĀD YAŠT》是Yašt hymn 所搜集的有关早期阿维斯塔的赞美诗集的最后一部曲。《ZAMYĀD YAŠT》XIV, 35—38。记载:“‘Semury’的翅膀承载‘famarh’神四处翱翔。”《阿维斯陀中的祅教祭司》一文指出,第一个取得祭司头衔的是Ahumstuta 之子 Saena。而Saena 一词有鹰的意思。[10]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一座6 世纪围屏石塌前板中央雕刻圣火坛与鸟祭司(图20),具有中原艺术特征。圣火坛与中原发现的琐罗亚斯德圣火坛一致,圣火坛两侧各侧身站立一位人鸟祭司,头戴圆形帽,口鼻处戴“帕达姆”口罩,从肩处伸展出饱满圆形的双翼,翼根处羽毛较圆短,下接细长舒展的长羽毛。人鸟祭司挺胸作直立站姿,双腿较直,膝处并不似公鸡有明显转折,下接尖锐而体量较大的爪,整体造型与“亚述贝尔卡拉”雕塑哈特拉之鹰非常相似,可以判断其来源于“鹰”的母题,而非其它鸟类或公鸡。而且戴圆帽的侧面,持棍的特征又与贵霜银币上的famarh 神祇十分接近,不由得让人产生对于famarh 神与半人半鹰祭司之间关联性的联想。famarh神对中亚产生过巨大影响,HERZFELD, Ernst Emil发现的硬币上famarh 神焰肩以及手持火盆都显示出了其与火之间的紧密关联,而硬币反面则是国王侧面像,可见,famarh 神代表的“神赐灵光”对王权的守护性。总而言之,famarh 神持火以及守护神的神格都符合半人半鹰祭司的特征。且根据《ZAMYĀD YAŠT》XIV记载:“瓦雷纳”的猎鹰所变的‘Semury’翅膀承载‘famarh’神四处翱翔。”综上所述,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6 世纪围屏石塌前板中央雕刻半人半鹰祭司应该是“具有瓦雷纳猎鹰所翅膀‘famarh’神”,它们具有王权赐予的灵光,而用祭司火坛的琐罗亚斯德习俗来守护逝去的亡灵。

图20 第一块围屏石塌前板上圣火坛与半人半鹰祭司,6 世纪,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来源:PENELOPE RIBOUD:Bird-Priests in Central Asian Tombs of 6th-Century China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Funerary Realm[M]: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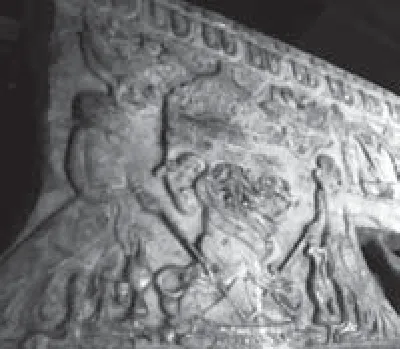
图21 隋代安备墓彩绘贴金石棺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来源:葛承雍:祆教圣火艺术的新发现——隋代安备墓文物初探[J].,美术研究,2009-08,彩图版)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征集一座隋代安备墓彩绘贴金石棺床(图21),从墓志记载可知安备及其先人来自中亚“安国”。在石棺床下栏之显要位置彩绘浮雕人鸟祭司与火祭坛的场景。戴着“帕达姆”的半人半鸟祭司站在火坛两侧,两人手执树枝或杖伸向盛食物的托盘。颈部戴项链,上身为人身,着紧缚服装,腰部系飘带,下半身为鹰身,翅膀表现为狭长的羽翼,从腰部贴于身体两侧并垂于地下。粗壮的鹰爪则与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石塌前板中央所雕刻鸟祭司完全一样,鹰足通常表现非常粗壮且饰层层鳞片,鹰爪十分宽大且有呈锋利钩状趾,仔细比较不难发现,这是鹰类祭司与其他杂居鸟类祭司最大不同,通常杂居鸟类祭司爪细长,且爪较小巧。值得一提的是,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围屏石塌前板中央雕刻圣火坛与隋代安备墓彩绘贴金石棺床下栏显要位置彩绘火祭坛造型非常相似,巨大的莲花火坛下方垂饰珠宝,巨大的火焰表现得如伞盖一般,火坛底座为束腰形状,火坛两侧摆放水壶的构图也完全一致,两者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程式性。
4.波斯地区以杂居鸟类为原型的“阿索祖什鸟”祭司
第四类是以中亚地区的杂交鸟类为原型“阿索祖什鸟”祭司。这类复合型杂交鸟类图像在公元前3 世纪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大都会博物馆藏一枚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石制印章(公元前6-前4 世纪),上面浮雕一花枝上站立的“半人半鸟”(图23),头戴典型波斯束发带,其形象不禁让人想起了Shami 神庙内的帕提亚王子雕像(公元前2 世纪),发型几乎无异,可见,“半人半鸟”身份地位较高,形象上夸大了鸟的圆浑臀部与拖长尾部,显得有些许累赘。赫尔米塔什博物馆藏一枚印章上,一只半人半鸟的侧面形象有着萨珊波斯地区常见的圆帽与长胡须(图22),夸张的饱满腹部,后仰的姿态,后折的双翼以及撅起的短直尾翼。大都会博物馆藏一枚石制萨珊印章(公元3-7 世纪),半人半鸟侧面与赫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印章上形象仅仅是人物发型不同,体态特征都较为相似。在德黑兰博物馆藏一只6 世纪的装饰舞蹈女性的银制水壶,其珍贵之处在于它在伊朗本土被发现。银制的壶上清楚描绘了四位舞蹈女性与“西牟鸟”(图24),以及周围的一些其它动物。“西牟鸟”来自于中古波斯语sēnmurw,它是古代伊朗神话和文学中常出现的一种仁慈的神话鸟,银壶上的“西牟鸟”被描绘为侧立昂首的站姿,具有修长的脖颈,丰满的腹部以及短直的尾翼,显然与之前描述的“半人半鸟”属于同一原型,这种鸟的原型一定是公元3-7世纪,萨珊波斯地区常见的一种杂居鸟类,而这种当地自然界常见的杂居鸟类,成为了波斯地区不断演变的“半人半鸟”祭司系统的图像来源。

图22 赫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印章(来源:Judith Lerner:A NOTE ON SASANIAN HARPIES[J].Iran,Vol.13 (1975):168)

图23 石制萨珊印章,大都会博物馆藏,公元3-7 世纪(来源:Judith Lerner:A NOTE ON SASANIAN HARPIES[J].Iran,Vol.13 (1975): 168)

图24 装饰舞蹈女性的净水壶,6 世纪,德黑兰博物馆藏(来源:Stuart GilbertandJames Emmons:Roman ghirshmanpersian art[M].1962:214)

图25 阿富汗巴米扬东大佛佛龛天井壁画线图中人鸟祭司放大图,名古屋大学调查队,宫治昭绘制(来源:前田耕作.古代巴米扬遗迹写真集[M].每日新闻社,2003:129)
至于这种“半人半鸟”祭司所代表的神祇,对照中古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义可得出多种推论,其中最有可能的是“阿索祖什鸟”祭司。反映琐罗亚斯德教的《Bundahishn》Chapter XIX 曾写道:“关于阿索祖什鸟,也就是佐巴拉-瓦赫曼和肖克鸟,他们被赋予了《阿维斯塔》的语言;当它一旦讲述时,恶魔‘胆战心惊,无可逞其伎’。当它没有祈祷时,恶魔和巫师会用一种‘修剪指甲的工具’抓住它,像箭一样射杀那只鸟。这样,鸟祷告结束时候就把这个工具吃掉,使魔鬼不能使用它了;如果它祷告的时候不吃掉,魔鬼就会进攻它。还有其他的动物和鸟类都是在邪恶生物的对立下被创造出来的,正如上面所说,当鸟类和兽类都与邪恶生物和巫师相对立时,乌鸦(瓦拉)也是最珍贵的鸟类。关于白隼,它说,它用翅膀杀死蛇。喜鹊(卡斯基纳克)鸟杀死蝗虫,并与之相反。居住在废墟中的喀尔喀人,也就是秃鹰,是为吞噬死物(纳赛人)而创造的;乌鸦(瓦拉克人)和山鸢也是如此。”
根据名古屋大学调查队宫治昭1969 年绘制阿富汗巴米扬东大佛佛龛天井壁画线图,在东大佛的头顶的佛龛壁画上描绘了一尊巨大的驾马车的太阳神。太阳神躺在由四匹翼马拉着的战车上。在战车的两侧,描绘了一对戴着头盔和光环的有翼女神。在这些女神的上方,各停留了一只“人鸟祭司”(图25):头上戴着装饰彩带的帽,右手拿着火把,庄重地平举至面前,左手持一个类似长柄勺形状的权杖,收至腋后。虽然上边缘被严重损坏,但一些神圣的哈萨鸟排成一列走向太阳神,两边都有一对握着风囊的“风神”。而该“人鸟祭司”极有可能是《Bundahishn》所描绘的“阿索祖什鸟”,它收至腋下的“类似长柄勺形状的权杖,”则有可能是恶魔和巫师所用来捉捕它的“修剪指甲的工具”,它必须在祷告结束时候就把这个工具吃掉。
(1)第一类:以中亚杂居鸟类为母题原型
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第二块围屏石榻前板上(6 世纪制作),也出现了圣火坛与鸟祭司(图26)。巨大火坛建立在一个由小鬼托举的复杂莲花底座上,底座上有两只凶猛的豹类动物缠绕装饰。火坛两侧站立两名严肃的半人半鸟的祭司,脸上戴着“帕达姆”口罩,它们都戴着精致华丽的萨珊式有翼冠,王冠上有星星象征图案。脑后有丝带飘垂下来并缠绕肩部。上身为赤裸的人体,腰间系带,腰带以下为鸟身。鸟的翅膀在上半身人身部分并未体现,但是下半部鸟身两侧有折叠的双翼,羽毛刻绘细腻,与大都会博物馆藏石制萨珊印章上半人半鸟双翼非常相似。身后的尾翼短直且垂至地面,此为萨珊波斯艺术中所表现的杂居鸟类常见的共同特征。半人半鸟一手拿着树枝或杖,另一只手拿着一只小包,里面放了供火的易燃物。从整体而言,Shelby White and Leon Levy 收藏的第二块围屏石塌前板上的半人半鸟祭司,属于3-7 世纪萨珊波斯地区常见的杂居鸟类,其体态特征与萨珊波斯地区发现的印章上鸟类十分相近,但是服饰与造型似兼有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应该是杂糅了中亚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的综合特征。
(2)第二类:糅合了“千秋万岁”的艺术特征
在中原北魏至隋代的部分墓葬中,还出现了一类来源波斯杂居鸟类形态,又结合了中原墓葬中常见的“千秋万岁”特征的特殊人鸟祭司。自[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卷三的“对俗篇”中记载:“千岁之鸟,万岁之禽,皆人面而鸟身,寿亦如其名。”[11]41中原人的丧葬习俗中惯用“千秋万岁”,是取其寓意,喻示着人死后魂魄还继续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永生。中原人的丧葬习俗中惯用“千秋万岁”,是取其寓意,喻示着人死后魂魄继续在另一个世界永生,且墓葬出土的榜题中也说明该“人面鸟”即“千秋、万岁”。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中(图31),“千秋”为高髻,长尖耳(中原汉代羽人皆为长尖耳),宽衣博带,翅膀似弯刀般向上,尾部为凤尾或孔雀尾般飘然于空中。“千秋”为人面鸟身,“万岁”则为兽面鸟身,“千秋”为高髻,长尖耳(中原汉代羽人皆为长尖耳),宽衣博带,翅膀似弯刀般向上,尾部为凤尾或孔雀尾般飘然于空中。
北魏时期粟特后裔或者说汉化的粟特人墓葬中,已经出现了使用了“千秋万岁”替代了波斯萨珊地区的“人鸟祭司”的现象。如北魏苟景墓志可知:苟氏盖出粟特,尔朱诸部落为羯胡,北魏时居住肆州和并州[12]28。苟景墓志盖绘刻则更是显示出胡风与汉风的结合:志盖下侧为方形火祭坛,升腾着火焰,两侧各有一只半兽半鸟神,上侧石刻中有一莲花状物,有两位人鸟祭司,男戴小冠居左手捧高足杯,女盘发髻居右手捧莲花,均着汉人褒衣博带,他们有着M 形双翅,舒展、升腾且卷曲的孔雀尾,似鹰般的足爪。
英国V&A 博物馆藏一块从中国流失出去的石棺床板(制作时间约公元550 年),这件物品来自希腊商人之子乔治•尤莫福普洛斯(1863-1939)的收藏品。①这幅作品曾被认为是佛教寺院的一块寺庙栏杆。2007 年,贝丝·麦基洛普(BethMckillop)进行了一项研究,判断它可能是中国制造的绘制琐罗亚斯德火坛的石棺床板。在这块石棺床板中央,浅浮雕一个巨大的琐罗亚斯德圣火坛,已经漫漶。火坛两侧各站立一名人鸟祭司正对着火坛进行祭祀(图27)。两名祭司身后有头光,赤裸上身,仅在腰间束带并着襦裙,腰带以下为鸟身与鸟爪,其服饰与片治肯特发现的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石膏画中人物所着粟特常服相似。而在圣火坛与人鸟祭司外侧左右各浮雕一组舞蹈人物,左侧为典型的着长袖善舞的中原女性舞者形象,而右侧则为穿胡袍戴胡帽的粟特舞者形象,显示了该葬具主人为在汉化的粟特人或粟特后裔。而这一混合型文明特征在“人鸟祭司”上也得以充分体现:首先,祭司不是手持木棍进行火祭,而是端立双手捧供奉之物,更接近中原祭司图像传统;其次,与来自萨珊波斯地区的半人半鸟祭司短直的尾翼不同,采用了如同河南邓县彩色画像“千秋、万岁”人面鸟一般蜿蜒如帛带般的长尾翼。

图27 石棺床板上的人鸟祭司,公元550 年,英国V&A 博物馆藏(来源:“英国V&A 博物馆”官方网站,网址: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34814/marble-panel-funerarycouch-panel-unknown/,浏览时间:2019.05.20)
太原隋代虞弘墓是一座入华中亚人的墓葬。虞弘墓石棺上的祭司也明显受到了汉地“千秋万岁”特征的影响(图28)。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上的祭司,头戴波斯地区常见的冠,片治肯特发现的《摩柯婆罗多》石膏画中,赤裸左侧与下侧的人物则戴粟特特征的宝冠(图29),这种宝冠由三个圆珠形的装饰件串联而成,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上的祭司头戴宝冠与之属于同类,皆为粟特式的。身着的紧身窄袖上衣也与图中人物一样粟特式的。而祭祀的尾翼则为“千秋万岁”的三股尾,双翼位置非常低,从后背处舒展开并跃然于空中,其三股尾与背后伸展的双翼与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千秋万岁”如出一辙(图30)。

图28 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上的祭司与火坛(来源《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M].2005)

图29 《摩柯婆罗多》场景,片治肯特一个富裕家庭客厅里的石膏画,8 世纪上半叶(来源Mikhail Piotrovsky:The State Hermitage: Treasures from the Museum’s Collections[M].Booth-Clibborn Editions.2014:289)
三、结语
早期波斯帝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多种复合生物图像体系。随着波斯版图的扩展传入了处于欧亚十字路口而呈现文明多样性的中亚,再随着粟特商旅带入中原文明,使得来自中亚的入华粟特“人鸟祭司”存在复杂的多元起源,并可以从入华粟特“人鸟祭司”形态特征找到原生文明的种种端倪。

图30 高句丽墓室壁画中的“千秋万岁”(来源:单海澜. 祅教祭司鸟神与千秋、万岁图像之比较研究[D]: 9)

图31 河南邓县彩色画像砖中的“千秋”(来源:同图30:8)
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多元而非单一的起源。从图像学切入分析,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可以归结为四种身份:代表中亚“斯罗什”之鸟的“人首公鸡”,源自古希腊的有翼女性祭司的“人鸟祭司”,来自古伊朗“神赐灵光”的鹰类祭司famarh,波斯地区杂居鸟类为原型的“阿索祖什鸟”祭司。这四种文明来源的“人鸟祭司”都与早期波斯艺术、希腊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粟特商人把它们带入中原之后,都或多或少“中原化”或“粟特化”。创造这些入华粟特葬具上“人鸟祭司”,中原工匠在参照了来自粟特本土的粉本后,加入了中原地区熟悉的墓葬“千秋万岁”等类似外观的特征,甚至还将不同文明源的“人鸟祭司”“鹰类祭司”“人首公鸡”的部分特征混淆重构出了新的形象,也折射出了穿越欧亚大陆的丝路上,图像艺术传递过程中的所发生的融合与借鉴现象,以及所催生出的新的艺术形式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