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学所的日月
2020-05-19蒋寅
蒋 寅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9年6月我正届还历之年,如果一直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在已是荣休之人。每天悠闲地读一些喜欢读的书,写一些想写的文字。每年以老干部的身份去所里一次,听听通报全院发展的大好形势,再和古代室新老同人聚一次餐,聊慰契阔之情。如果愿意继续做研究,也可以在院里申请课题,获得资助出书,评奖,老干部和在职学者享受同样的待遇。这就是社科院学者紧张工作几十年后自然的放松,也是他们安享的幸福晚年。也许正因为太自然了,大家或许都体会不到这种悠闲的可贵;也许只有隔开一段距离,才能看清中国社科院这样一个特殊的学术机构,所形成的学风,所造就的学人。
回顾一下自己在文学所工作近30年的经历。对文学所的学术传统而言,我的学术算不了什么,但对我个人来说,在文学所的工作却是履历表上的主要内容,对我学术和人生的意义不言而喻。人事倥偬,指顾之间,已为陈迹。现在回顾这一段颇为漫长又似十分短暂的时间,竟至百感交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是1988年3月在南京大学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到文学所报到的。此前程千帆先生在开会时见到刘再复先生,推荐我来文学所工作,所里经过研究,接受我进古代文学研究室,做一名助理研究员。当时经办此事的是古代室副主任陆永品先生。主任沈玉成先生则是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之前他到南京师大出差时,曾专门约我去宾馆面谈,也算是考核的一个程序吧?后来程先生请他出席答辩会,沈先生在赞同其他先生的评价之余,特别指出论文鲜明的理论意识和研究方法的独创性,让我深感知音,觉得文学所的专家眼光毕竟不同,更有学术前沿意识。我们读硕士、博士的80年代,正是新理论、新方法最热的时候,许多前辈学者视之为不接地气的花架子,通达如程千帆先生,虽也鼓励各种探索,但总体认为提倡新理论、新方法者空洞口号多、成功实践少,沈先生在其他先生肯定论文的具体分析、论断之外,更肯定了理论意识和方法创新,这就意味着本文也是新理论、新方法的成功实践,这样的肯定,对任何一个年轻学人来说都会是深受鼓舞的。
我进古代室工作的时候,全室人员虽不及鼎盛期的40 人之多,但也有25名研究人员,老一辈学者是曹道衡、刘世德、邓绍基等“文革”前入所的先生,中年一辈是施议对、石昌渝、董乃斌等本所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俗称“黄埔一期”,剩下就是刚过40 的杨镰、不到30 的郑永晓和我三人算是青年研究人员。退休的老前辈或许也有见过的,但不肯定。我那时经常一个人在研究室工作,偶尔有先生进来,只是点头致意,看看信箱拿了邮件就走了,我也不知道是谁。现在想来可能是吴晓铃先生或余冠英先生。在职的先生,虽然乍到不太熟悉,加上每周只是周二返所日见一面,很少交流,但我还是感受到前辈学者们的关爱。当时正值室里编撰14 卷本《中国文学史》,唐代下卷主编吴庚舜先生知道我博士论文题目是《大历诗风》,便嘱我撰写第一章“大历贞元诗歌”,我根据自己研究中唐前期诗歌的积累,用了几个月时间写出了四万多字文稿,得到吴先生首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责编的宋红女士,也说下卷审稿时读到我写的第一章,感觉颇有新意。但写文学史受体例的限制,有很多想法写不进去,而程先生也曾嘱我继《大历诗风》的综合研究之后,要进一步对中唐前期诗歌做一个整体性的历史研究。为此,我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历诗派和诗人》,并获得立项。由此开始做大历、贞元诗歌的全面研究。
在古代室工作没多久,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一天施议对先生找我,说所里要成立一个诗学研究室,由他牵头,他预定的成员首先是理论室陈圣生先生和我两人,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于诗学,心底又存有创办一种《中国诗学》丛刊的夙愿,觉得诗学研究室是所里体制创新的探索,专业方向明确,施先生又很有想法,且交际广泛,将来或许能按自己的意愿做一些事,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没过多久就知道,所里虽然有刘再复所长支持这个想法,并正式宣布诗学研究室成立,但硬件不能落实,没有办公室,施先生和我仍只能在古代室行走,大家也觉得我们还是和古代室的人一样。但我们很快就按事先的设想,做了两件事:一是编辑出版当代学人诗词丛刊,出版了旅美学者李祁和萧劳之子萧豹岑的诗词集;二是创办《中国诗学》丛刊。80年代毕竟是个有理想有热情的时代,有许多现在看来很天真的想法。我们的总体计划是出一个诗学丛书,分为三个系列,除了当代诗词丛刊、《中国诗学》之外,还包括诗学研究资料丛刊,我心目中有计划还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创办《中国诗学》译丛,而施先生描绘过愿景的是诗人咖啡馆,说可以由家属来经营,为联络学界和创作界提供一个沙龙。
1989年,我写了一些大历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文章,如独孤及、梁肃年谱补正,权德舆作品编年考证之类,并将博士论文《大历诗风》修订完毕,由程千帆先生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我和汪晖奉命到院扶贫点陕西商洛地区山阳县锻炼,我被分配在粮食局办公室工作。白天坐班,办公室经常没人,也可以自己看看书。但事实上没什么书可看,带去的书很少,除了《全唐诗》收录大历诗的几册外,就是一本《谈艺录》,还有一本岩波文库本的和哲郎《风土》,及大厚本的小学馆《国语大辞典》。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我以前就读过两遍,但不太懂,想趁这段时间清闲细读一下。《风土》是我很喜欢的书,一直想译成中文,在山阳陆陆续续翻译了两万多字,年底一回京就再没时间接着做。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力卫先生的译本,我那两万多字译稿便懒得发表了。
倒是读《谈艺录》颇有心得,以前读作品少,看钱先生的议论只是喜其涉猎广博,譬说风趣,等自己研究了一番唐诗之后,就能欣赏钱先生的一些真知灼见,理解其深刻隽永的意味了。这一年正值钱先生八十寿诞,《文学遗产》拟发一组纪念文章,得知我正读《谈艺录》,便约我就《谈艺录》写一篇文章。以辍业废学之身,远放商洛山中,阅读这“侍亲率眷,兵罅偷生”的忧患之书,不免感慨系之。文章写就,题作《〈谈艺录〉的启示》,刊登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文中对钱先生超然的学术态度、不随波逐流的学术品格、深刻的洞察力和透彻的表达能力列举了丰富的例证加以推崇,同时对照我们一代人的切身境遇作了些意在言外的发挥。也不知小文是否为钱先生寓目,知我罪我,当时并不在意。倒是日后有所里前辈先生私下里对我说:“你对钱先生的评价有点拔高,你还不太了解他的为人。”这是很自然的,那时我真是很欣赏钱先生对学问、对世事的超然态度,除了学问之外,我对他确实一无所知。我生性腼腆,拙于应酬交际,从来不拜访名人。有一次程千帆先生嘱我送一本书给钱先生,我听说他不喜欢被人打搅,一般不开门见客,便将书放到院里,由他秘书转交,并附一札,大意说本应登门送呈,因怕打扰,且我住处甚远,与其两不便不如两便云云。不知道钱先生是否会责小儿无礼,但他只是回了一信,说没有程先生的地址,一封复函嘱我代寄。90年代初,钱先生身上还没有那些光环,完全是电视剧《围城》的热播,使钱先生和他的学问妇孺皆知,并渐成为一个神话,各种流于庸俗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为此我写了《在学术的边缘上》一文,希望还原他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孰料《南方都市报》(1996年11月1日)发表时径取小标题充作题目,改为《解构钱锺书的神话》,某报转载又改作《请还钱锺书的本来面目》,一个比一个更耸人听闻,引起很大反响,后来甚至被翻译成日文,刊登在大阪女子大学《国际文化》第2号(2001年3月)上。当时钱先生虽健在,想来不会在意媒体上的这些波澜。但他在钱粉眼中已是神一样的存在,任何批评都会被视为大不敬,一时对拙文的讨伐之声四起。针对各种反应,我又在《博览群书》2001年第11 号发表《对〈如何评价钱锺书〉的几点“声辩”》表明我对钱锺书学术品格的认识,其中根据我对大师的理解,认为钱先生不能算是大师。这一下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种讥诮、鄙斥之辞蜂起,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目我为无知狂徒,但也颇有不少人赞同我的看法。无论如何,彼此都很少意识到我是钱先生同一研究室的后辈学人,我写这些文章时也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就事论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程先生,我也没有称他为大师,我们师门里好像也没见有人称过千帆先生为大师。
1990年11月,我们结束锻炼回京,恢复正常的研究院生活。年终,我以27篇论文的业绩申请副研究员,由于所里积压的待评人员太多,我们几个新入所的博士都是以承认副研资格的方式对待的,即名片上可以印个副研究员了,但没有相应的工资待遇。这也没什么,比我们年长的“黄埔一期”也还有不少人没晋升副高。只是半年过去,人事全非,由于刘再复所长离任,诗学研究室就自然归于无形,施先生和我仍旧在古代室工作,仿佛那个诗学研究室根本就没存在过。
那时候因为没有经费,要做一点事很难,当代诗词丛刊的两种基本是作者自费出版的。没有经费支持,《中国诗学》第一辑稿齐后,一直不能落实出版。我曾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商谈,社方已同意接受,还打算争取台湾方面的资助,在两岸分别出繁、简字两种版本,可始终未能落实。不久,施议对先生到香港就职,我孤掌难鸣,更无办法。后来听到江苏古籍出版社要出版《文学遗产》,我觉得更无希望了。同学张伯伟闻知此事,建议交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蒙他同门左健副总编的支持,创刊号终于在1991年12月问世,比《学人》晚一个月,同为当时最早的民办学刊。开始几辑都以约稿为主,带有同人刊物的性质,为的是提倡一种扎实而有积累意义的学术。慢慢地它在学术界越来越为人瞩目,年轻学者投稿踊跃,逐渐就变成多发表年轻学者论文的诗学专门刊物。80年代是丛刊遍地开花的时节,当时涌现了很多不定期丛刊,《学人》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但它只出到15 辑就停刊了,其他更多的是短命刊物,没出几辑就悄无声息了,只有《中国诗学》坚持到现在,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后话不表。
从1991年到1993年,我一直在做“大历诗派与诗人”的研究工作,每年发表约10 万字的论文。除了课题内容外,还涉足于三个不同类型问题的研究,成为我后来倾注精力的三个研究方向的开始,一是《〈渔洋诗则〉的真相与文献价值》,辨析一部与王渔洋有关的汇编诗话的真伪与文献价值,这是我涉足诗学文献考索的开始;二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由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文化选择思考文学与精神史的关系,这是留意文学的精神史研究的开始;三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思考唐代文学繁荣的机制,以现代文学社会学的眼光重新诠释古代文论的基本命题,这是我从事古代文论基本概念和命题的现代诠释最初的尝试。
1992年博士论文《大历诗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翌年《戴叔伦诗集校注》续由同社刊行,都受到学界的好评。1995年《大历诗风》荣获本院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那个时候,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著作是很不容易的,我大概是当时最年轻的作者吧?《大历诗风》能被接受当然与程千帆先生的推荐有关,《戴叔伦诗集校注》是我硕士论文《戴叔伦研究》的附录,读博士期间加以修订后自己投稿。当时社里积压书稿很多,经赵昌平先生力保才没被裁减,最终得以出版。为此我对赵昌平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后来我晋升副研究员就是以这两部著作申请的。从1990年获得副研资格后,翌年并没有机会转正,1992年不知道什么缘故全院不评职称,所以我到1993年才正式晋升。
这时,我发表的唐代文学论著和古典诗学研究论文开始受到学界关注,日本学者赤井益久在《中国文学报》第47期(1993年10月)发表《评蒋寅著〈大历诗风〉》一文,对《大历诗风》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一一作了评述,而罗宗强先生《我们非常需要不尚空谈的书——读蒋寅〈大历诗风〉札记》(《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一文在当时竞谈方法论的风气下,对《大历诗风》的创新所给予的充分肯定及对年轻一代学人群体的远大期许,更让我受到莫大的激励。我先后被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这两大学会增补为理事,当时同为两个学会理事的只有程千帆、詹、王运熙、罗宗强、陈伯海等几位前辈学者,我是唯一的后辈学人和副教授。

蒋寅著《大历诗风》
“大历诗派与诗人”课题于1993年结项,后与历年所撰大历、贞元诗人事迹、作品考证成果合编为《大历诗人研究》上下两卷,共50 余万字,托傅璇琮先生和徐俊兄的福,得以在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我大概也是中华书局最年轻的作者。这部专著后来在1997年荣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奖专著优秀奖(最高奖)。这部书稿的完成,让我的唐代文学研究告一段落,转而开始清代诗学文献考索和古典诗学概念和命题的研究。
从山阳锻炼回京后,我就开始阅读历代诗话,一方面为研究大历诗歌寻找评论资料,一方面充实自己的诗学修养。从1982年读硕士开始研究唐诗,十年下来越做越觉得有一种学术储蓄被用尽的感觉,很想通过阅读一些诗学论著来充实自己。文学所图书馆收藏的诗文评类书籍异常丰富,有几个书架装满了清诗话。除了国家图书馆外,文学所可能是国内收藏诗话最丰富的单位。历代别集、总集的收藏也很丰富,多有珍善之本。看到这些书很少被使用,不免让我有一点明珠暗投的感叹,心想既然要读点诗话,何不趁此机会做一点清代诗学研究呢?我考察了一下文献目录,发现清代诗文集和诗文评文献竟还没有专题目录,便打算先编个清诗话目录再说。于是我从1992年就开始有计划地浏览一些书志、目录类书籍,留意搜集清诗话文献。到1993年“大历诗派与诗人”课题结项后,更是全力投入到清诗话的访求和阅读中,不光翻阅大量的公私图书收藏目录,还尽可能地到各大图书馆查卡片,阅读原书。那两年间,只要不是周二返所日,就去图书馆看书。北京各大图书馆的藏书,除了不对外开放的北大图书馆外,我都一一读完了它们收藏的清诗话和作者的相关著述,每读一种都做详细的笔记,不断补充资料,慢慢写成提要。所里的普通古籍因为可以借出,每次上班都用一个军用防雨行李包装了自行车驮回家,一周换一包。就这样,到1994年底,我已编成一个收录见存书700 余种的《清代诗学著作简目》,翌年刊登在《中国诗学》第4 辑上,另外还记录了数百种亡佚书籍的资料,存目待访。

2005年,古代文学研究室新春聚会
随着清代诗学书目的编成,对清代诗学文献心中有底,一个通盘研究清代诗学的计划日渐浮现出来,准备一面考索、搜罗清诗话文献,做著录和提要,一面从清初入手研究清代的诗学史。由于对清代文史研究夙无基础,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选了清初诗学著述最丰富且影响力最大的王渔洋为突破口,希望以他为中心切入清初诗坛。要熟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和交游关系,最方便的莫如编年谱。鉴于王渔洋的资料过于丰富,多数也不难找,我采取了不同于一般年谱的编纂方式:凡出自本人著述的资料,仅记出处不录原文,只有集外资料才采录参证,比起一般年谱的体例具有“文省于前,事增于后”的优点,书名也定为《王渔洋事迹征略》而不名年谱。
工作虽一直在做,但毕竟王渔洋著述量太大,集外资料更多得难以一网打尽,因此我没有急于成书,倒是就手边的一些论文加以拓展,想做一个与心态史相关的研究。我从读博士期间就对心态史问题感兴趣,《诗经》《楚辞》作业都是从心态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提出问题的。于是我在1995年以“中国古典诗歌的心态史研究”为题,申请了院青年基金项目。因为有一部分前期成果垫底,只用了两年就完成课题,但结项后自觉比较单薄,就放弃了出版专书的打算,只将新写的一些论文收入《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中。不过这个题目一直在心头盘旋,想着总有一天要好好做一下。当时我对文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内容、形式二元化的传统观念上,始终有一种意识,要将文学的内容和体裁分开来研究,各成一个系列。
研究清代诗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文献浩瀚,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才能进入其中。1994年和1995年,两年内我都在埋头读书,读了大量的清诗话和清初别集,除了诗话提要之外,没写什么论文。到1996年,两年读书的积累开始开花结果,古代文论、清代诗学乃至已疏离几年的中唐诗歌,都在这两年的阅读中酝酿出丰富的成果。古代文论研究有《至法无法:中国诗学的技巧观》一文,中唐诗研究有《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权德舆与唐代的赠内诗》二文,清代诗学研究有《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之关系》二文。《古诗声调论的历史发展》是迄今为止无人做过的对清代古诗声调学说及其文献的完整梳理,《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则是上文的副产品,我想通过韩愈作品的细致分析来验证一下清人的论断是否能成立。这是有开创意义的工作,我设计的分析模式为后来研究唐宋诗人古诗声调的学者所沿用。同年,我受邀出席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唐代学术国际研讨会,这也是台湾唐代文史研究界第一次正式邀请大陆学者参会,文学方面四位代表——傅璇琮、周勋初、葛晓音先生和我,后来傅璇琮先生因病未能赴会。我在大会报告的论文就是《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多位学者提问,引起热烈的讨论。王基伦教授在会议综述里提到,这篇论文虽然篇幅不大,却颇有学术价值。用从来没有人用过的方法,对韩愈诗歌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
1996年应该说是我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不仅去台湾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秋天又收到来自京都大学文学部川合康三教授的邀请,希望我来年能去京大担任一年研究生院的客座教授。接到川合先生的信,我很惊讶,我的职称还是副研究员啊!幸运的是,我在年底的职称评聘中,凭《大历诗人研究》两册和若干论文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当时我37 岁,在社科院大概也是最年轻的研究员了。
1997年1月,我东渡扶桑,赴京都大学,开始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生活。这一年是我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第一次到异国任教,第一次深入地了解一个不同于国内的学术生态,第一次有如此高效的研究条件。我只担任一门中唐文学讲义,每周上半天。本来我只需要讲大历诗人研究就好了,但不愿意炒冷饭,另写了一个元和诗歌研究的讲义,一边读元和诗歌一边讲,自觉比较肤浅,好在这主要是硕士生课。中国文学专业的四位老师兴膳宏、川合康三、平田昌司教授和木津祐子副教授都对我很照顾。我除了上课,每天都在研究室读书、写作。没多久文学部搬入新楼,图书馆就在楼下,所有书籍包括古籍都可以任意借出,拿到研究室去用,工作效率极高。我利用这个使用图书最方便的机会,将《王渔洋遗书》中的资料全部录入电脑,初步完成了《王渔洋事迹征略》的初稿,又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几篇王渔洋研究论文,同时还写作了几篇有关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的论文,慢慢形成一个持续多年的系列研究。
京都大学是国际著名的汉学重镇,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拥有一批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学者,更以丰富的汉籍收藏吸引各国学者前往访问、交流。日本的大学以前没有客座教授制度,只有以外国人教师的名义招聘的外籍教师。1996年文部省开始在研究型国立大学的研究生院设立客座教授职位,京都大学文学部有两个职额。我是中国文学专业首任客座教授,兴膳宏先生在京大的中国文学会年会上郑重地介绍我,说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文学专业首任客座教授蒋寅先生。另一个职位先是以研究中国绘画史著名的德国学者雷德侯教授,接着是一位来自波兰的历史学家,再后来一位是研究英美当代文学的批评家约翰·斯泰普先生。我至今仍以这段学术经历为自豪。一年间见过多位不同国家、港台地区的著名学者前来访问。访问是很方便的,但受聘为客座教授却是很高的待遇。2002年,李鸿镇教授邀请我去韩国庆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会讨论时李教授介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个什么机构,李教授接着说我几年前在京都大学任过客座教授,其他教授马上同意,说那就没问题。
在京大任教的一年间,我多次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演讲会、读书会,也受邀到不同的大学演讲。刚到京都不久,大阪市立大学的斋藤茂教授为我举办一次关于大历诗研究的演讲会,中唐文学会及日本各地的学者前来出席的也许有上百人吧,一个中型教室坐得满满的。后来我受邀参加川合康三、加藤国安、丸山茂等教授主持的读书会,以及川合先生主持的共同研究课题“中国的文学史观”,认识了许多日本学者,结下长久的友谊。与日本同行的亲近交往,让我对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不仅认同他们对古籍原典的深入解读,后来形成以读原典为主的研究生教学方式;也认识到日本学术的精深和厚重,促使我在日后的研究中更加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有意识地加以翻译介绍。前后做了三件事:一是将历年翻译的日本学者的论文编为《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出版;二是约请刘维治、张剑两位学者合作翻译了川合康三教授的力作《终南山的变容》;三是策划了一套《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丛刊》,将日本中唐文学会10 位中坚学者的论著译介到国内。我想这些著作会改变国内学界对日本学术的一些偏见,看到日本学者在很多问题研究上的领先意义和启发性。

与古代文学研究室同事合影
1999年4月,我被任命为古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做刘扬忠先生的副手。我和刘先生原是酒友,性格相投,平时我尊重他,他信任我。搭档几年,我包揽了各种事务性的工作,不让他费心,合作非常愉快。有什么活动,室里的年轻人都能分担各种杂务,减轻我不少负担。担任副主任后,有两件影响深远的事是我倡议的。第一件是创设每月一次的本室学术论坛,从入所以来,我在喜欢时间宽松之余,又不免感到同事之间有点疏远,对彼此的研究不太了解,缺乏应有的交流。更有的先生说自己写论文,从来不看别人的文章,保证全是自己的独到想法。我觉得这是不对头的,有必要以某种形式来增加大家的交流,于是向刘先生建议每月搞一次论坛,大家轮流报告、讨论,刘先生认为很好,就定于每月第二个周二返所日举行。几年下来,举行了一百多次,浏览目录,真是颇为可观。通过论坛的报告、讨论,彼此对所从事的研究有了了解,讨论中也培养起善意的批评风气和有建设性的论争方式,一篇篇论文讨论下来,大家都有所收获,报告人更是收获了众人的意见,使论文水准多有提升。我至今认为这是整体提升研究室水平的有效措施。第二件是为退休的先生举行一个纪念仪式。我出去开会,经常有人问我,某先生退休了吗?我往往答不上来,只能凭印象,说好像有一阵没看到来上班了。想想一个人在这研究室工作几十年,到了退休就是人事处把名字往老干部那边一划,悄无声息地谁也不知道,未免太没有人情味了。我在京大客座时,赶上人文科学研究所梅原郁教授的荣休纪念会,同事门生济济一堂,梅原教授演讲后,老同事老朋友即兴发言,讲很多梅原先生的逸事,一室笑声不绝,晚上再举行恳亲会,亲切气氛令人难忘。我向刘先生建议,以后每位先生退休都搞个纪念会,刘先生非常赞许,后来就成为定例,常假论坛之日举行,纪念演讲后一起去吃饭庆祝。
90年代潜心读书的收获,进入新世纪后形成较集中的出版,2001年我就出版了《中国诗学的思路与实践》《王渔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三部著作。后两部作为清代诗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博得学术界的一致称赞。《征略》虽存在一些疏误,但专家们还是对它搜集资料之勤、体例之善给与了相当高的评价。《诗坛》则以提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的学术理念为学界所赞同和响应,其中关于王渔洋与清初唐宋诗消长的论述为学界所采信,有关王渔洋藏书与其诗学的关系的探讨在当时也是有创新意义的。2003年《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2005年《清诗话考》相继在中华书局出版,基本上总结了我到此为止的三个研究系列的工作:一是清代诗学文献考索;二是清初诗学,主要是王渔洋诗学研究;三是古典诗学基本概念、范畴研究。这也是我学术积累和研究问题的自然状态的结束。
本来我有了研究王渔洋诗学的基础,在2000年申请所重点项目“清代前期诗学史”,还是顺理成章的,开始也很顺利。但两年后就被横插进来的两个项目冲乱了我的计划:一个是和刘扬忠先生共同主持的“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另一个是和傅璇琮先生共同主持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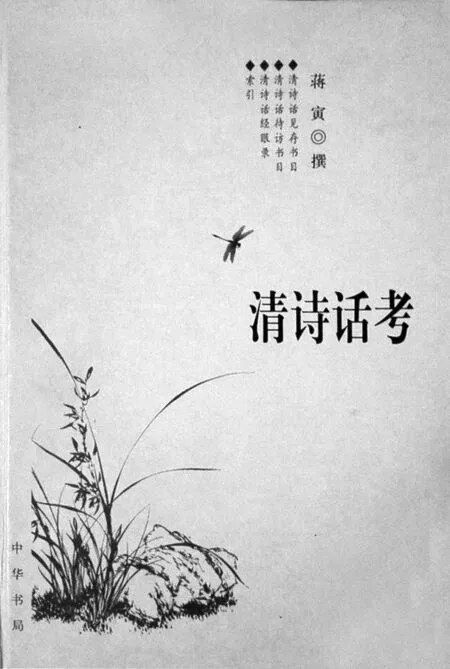
蒋寅著《清诗话考》
2002年初,我从科研处获知,院里计划在全院遴选30 个左右的研究室加以重点扶持,每年提供一百万元经费。严平处长认为本所只有古代室和理论室比较有希望,但古代室有个短板,就是没有院重大课题。我马上与刘扬忠先生商量,古代室赶紧要申请一个院重点课题。当时正是国家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际,我提议不妨以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为题,申请院重大课题立项,刘先生欣然认可,并马上议定参与课题组的研究人员,经征求各位意见后,确定本室为王学泰、韦凤娟、王筱芸、刘倩四位,外单位为北师大李山、清华大学谢思炜两位,共八卷。我草拟了项目申请书,经刘先生改定,最终以“中国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为题获得当年院重大课题立项,课题经费39 万元,计划四年完成。我承担的是第一卷,是全书的总论,因为涉及问题比较大,除了导论粗略地回顾了历史学和文学中的心态史、精神史研究,全书的框架也没有很好的构想。书名起了《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镜与灯虽与艾布拉姆斯的书同名,但取意并不相同。我的想法是,文学同时具有镜和灯的双重意义。镜意味着它是华夏民族精神的投射和反映,灯意味着它具有一种辐射力和影响力照亮了华夏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引导着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对这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好的论述框架,最后决定从个人与宗族、个人与社会、男性与女性、故国与新朝四个角度来展开人们所要面对的四个基本关系,以及它们在相应历史时期的文学表现,由此呈现古典文学和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因为这些宏大叙事只能通过具体的人物和作品来认识,所以论述触及的都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些老生常谈和人所共知的人和事。既然我们的课题是在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下展开,就必须从这个独特的视角谈出一点新的东西。在这些章节中,我力图提出自己的问题,谈出一些新想法、新判断。即使是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这样一些经典作家,我仍然从民族精神建构的角度揭示了他们在文学史和精神史上的双重价值。《镜与灯》是我迄今为止写得最艰难、最费心思的一部书,结项和出版后也受到好评,2016年还获得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但是我自己对这部书实在不太满意。
和傅璇琮先生一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也是很偶然的事。当时要以人大常委会的名义编一套《中国现代科学全书》,相当于一套当代各科学领域的学科概述,每个学科一册。文学由文学所承担,古代文学又让古代文学室负责。隋唐五代文学一册,本来是请陈铁民先生主编的,陈先生因为忙,辞不能承担,最后让我负责。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有意义的,可以借这个机会将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学界所取得的成绩,好好做一番总结。当时我想,如果能约请一批优秀学者,各就自己研究的领域写一个章节,合成一本唐代文学研究概述,一定很有价值。作为一种学科入门书,对于想研究唐代文学的年轻学者,对于研究生,都是一个很好的引导。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对这项工作倒是蛮有兴趣的,也很用心。后来果然约请到学界一批学有专攻的优秀学者,共同来完成这本书。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分文体来概述唐代文学的总体风貌,其中诗是主体,按初盛中晚四段来写;中编分别从唐代文学与政治、传统思想、宗教、科举、艺术、交通、幕府、妇女的关系来论述唐代文学的文化生态;下编介绍唐代文学的基本文献,分为文学、历史、敦煌、海外、工具书几章。书后附录一个很详细的参考文献目录,无形中也是对唐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检阅。因此,全书不仅代表着当今对唐代文学的认识水平,也具有一种学术史总结和综述的意义。
因为约请的都是真正的专家,每人承担的字数又不多,书稿很快就完成。我写了绪论、上编第三章“中唐诗歌概述”及结语“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三部分。书完成后却不知道往哪里交稿,一问说是项目已黄了,编委会的人也找不到。这让我很懊丧,请了那么多前辈和同辈的专家一起来写,怎么向大家交代呢?徐俊兄建议我把稿子送给傅璇琮先生看看,或许可以推荐给什么出版社。没想到傅先生看了稿子颇为称赞,认为体例很有特点,完全可以做成一个系列,就和一些学者谈了谈,征求意见,大家都赞成并建议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是傅先生嘱我以这部书稿为蓝本,拟一个七卷本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研究计划,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特聘研究员的身份,由我协助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作为2003年度重点课题立项。各分卷主持人分别由谭家健、赵敏俐(先秦两汉),刘跃进(魏晋南北朝),蒋寅(隋唐五代),刘扬忠(宋),张晶(辽金元)、郭英德(明),蒋寅(清)担任。本来我只负责隋唐五代卷,清代卷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主持人,傅先生便嘱我承担。当时我做清代诗学研究时间尚短,对清代文学及研究者都不太熟悉,不敢应承。经傅先生再三鼓励,我实在无法推辞,只得勉为其难。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全稿七卷杀青。在与辽宁人民出版社商谈出版时,傅先生提出让我也署名主编,我感到很惶恐——虽然在项目申请和进行过程中,我做了一些统筹工作,但那都是遵照傅先生的指示,做一点秘书工作而已;况且我在所有分卷主持人中年纪最轻,怎么能与傅先生并列,僭署主编之名呢?我坚执不可,出版社也认为总主编宜傅先生独署。但傅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社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我署副主编名,各位分卷主持人也予认可,这才议定。谁知几个月后书印出来,封面上我的名字竟然与傅先生并列为主编,这不用说肯定是傅先生坚持的结果。自走出校门以后,我从傅先生那里受到的关爱、教益、提携是最多的,我在《其学百代者,品量亦百代——追忆傅璇琮先生》一文中曾谈到这一点,行文及此,借这个机会再次表达对傅先生的感谢和缅怀!
如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就逐渐陷入到集体项目中,不同课题多线作战。2011年担任研究室主任后,行政工作和学术活动越来越多,很难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研究,虽然自己从未松懈,但“清代前期诗学史研究”和“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两个课题都逾期几年,迟迟不能结项。如果不是2008年受聘为台湾逢甲大学客座教授,得以在课余从容写作,四个月内将两个课题各写了七八万字的初稿,还不知道何时能结项。的确,近十多年来,感觉事情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会议,论文、项目评审,带研究生,接待博士后、访问学者……种种事务使做研究的时间大为压缩。因为社科院薪水远低于大学,我还不得不去大学兼职,先后担任北师大“京师学者”特聘教授、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特聘教授、安徽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也分占了一部分精力。到后来几年,我学术著述的写作基本都得益于到港台的大学客座、访问,只有在外客座的学期,我才能静心写作一批论文或部分书稿。《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和《清代诗学史》第一卷各有七八万字是在逢甲大学客座期间写的,《原诗笺注》是2012年秋在台湾东华大学客座期间完成的,《清代诗学史》第二卷主要是在2013年、2015年两度在香港岭南大学客座及2016年在浸会大学访问期间写作的。随着院里搞“创新工程”,研究室逐渐空心化,以研究室为单位的学术活动越来越少,我获得首批“长城学者”计划资助,也和室里的创新团队分道扬镳,成为标准的单干户。除了策划和编集《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6)算是室里的集体成果,此外与林宗正教授合编《川合康三教授荣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凤凰出版社,2016),与张静、唐元合著《权德舆诗文集编年校注》(辽海出版社,2013),与宋清秀、刘美燕合作点校《全浙诗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就都是随机而作的临时性课题了。事实上,年届耳顺,自己也确实感到应该退出学术舞台,让更年轻的学者去担当重任了。
从1988年3月进入文学所古代室工作,到2016年7月调离,前后28年多,我享受了社科院学者的清闲,也品尝过社科院学者的清贫,更目睹了社科院由超然于学界各种繁文缛节到主动追随高校的各种规则甚至变本加厉的经过,感今抚昔,不禁感慨系之。回顾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我对社科院对文学所始终是心存感激的。这里毕竟是一个最好的从事学术研究的机构,在那个古籍图书可以自由借出使用的年代更是如此。除了图书以外,文学所始终有一批学者维持着学术至上的正气,有一批杰出的前辈在各方面做出楷模,有一批优秀的同事互相砥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学术环境呢?我们这一辈学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成长在80年代自由探索的求知风气中,培养起不同专业学者经常切磋交流的习惯,这是文学所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我的研究和同门师兄弟、和学界同道相比,还有什么个人特点的话,就缘于与所里不同专业的朋友们的亲密交往。从担任北师大“京师学者”特聘教授、正式在大学任课起,我就体会到社科院学者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和熟悉是大学教师很难比的。在大学里,学术交流都以教研室为单位,不同专业的老师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同一教研室的老师平常也难得见面。而社科院的学者每周都见一面,平时各自在家里忙,上班的这一天倒像是休息,借书、论坛、读书会都在这一天,各研究室毗邻,串门聊天很方便。读书会上,不同专业的年轻学人,一起读福柯的《什么是作者》;过一段时间,就聚在谁家喝酒神聊,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电光火石地交锋;评职称、评奖时的个人陈述,学术委员的介绍评议,都是不同专业切磋交流的机会。能与不同专业的优秀学者保持如此频繁的交流,是我深感受益的难忘的经历。每周二返所日的聚餐,更是朋友们亲密交流的例会,它使我们始终保持对彼此学术研究的关注、熟悉和尊重,同时蒙受无形的启发和影响。置身于一批杰出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中,你想要拒绝来自现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影响都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怀抱开放的心态互相倾听了。许明、汪晖、孟繁华、陈晓明、赵京华……从文学所走出去的朋友,对文学所的怀念可能都集中于此。伟大也要有人懂,我们最初获得的认可和肯定都在这里,都在这群朋友中间。至于我,从各位身上学到的一定更多。关心理论问题、重视批评方法、留意文学史问题及相关学说,我的学术倾向与文学所这一学术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文学所同事靳大成、彭亚非

在院部大楼前
我博士毕业将赴文学所就职时,周勋初老师曾叮嘱:“你到文学所工作,自己一定要抓紧。不要看社科院的人时间多,都写不出东西的!”当时我还不明白,后来才慢慢知道,文学所的研究人员的确是著述偏少的,古代室也只有少数几位先生勤于著述,大多数人身后都没留下多少论著。至今我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或许时间宽松真的容易让人懈怠吧?就是现在的年轻学人,在我看来也写论文太少。我入所后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年发表10 万字的学术论文,28年来基本是做到的,最多的一年曾发表13篇论文。都是长篇论文,不算随笔、札记之类的短文。这不是说写得多就好,但多写肯定比少写好。除了老师强调的勤奋之外,我更将写作视为一个知识酝酿和思想激发的过程,肤浅的认识和粗糙的想法可以通过写作过程的充实、磨砺、锤炼而臻深厚精善。对于学者来说,不带有问题的广泛阅读和抓住问题思考、写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广泛阅读,思维空间就狭隘;不带着问题思考、写作,知识就浮泛而不成系统。我所有的论著都是在论文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写得慢点,但比较结实,有学术含量,因此也有较高的征引率。我的论文至少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过55 篇,专著和论文先后在院内外获得二十多次学术奖,除了前面提到的《大历诗风》和《大历诗人研究》外,还包括:《王渔洋事迹征略》《清诗话考》获得院优秀成果奖专著三等奖,《清代诗学史》(第一卷)获院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获本所首届“勤英文学奖”优秀论著奖,《原诗笺注》获第十八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镜与灯: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这无疑得益于社科院和文学所宽松的学术环境,有弹性的项目管理制度,鼓励发展学术个性的多元化学风,重视基础研究的正确思路。这一切都保证了学者能以从容的心态踏实地从事长时段课题的深入研究,使各类研究成果的质量普遍超出学界的水平线上,多数成为相关领域的一流成果,成为学界引重的必备参考文献。为此,我很感谢社科院和文学所为我提供的研究条件及给予我的荣誉,感谢所有帮助过我、支持我工作的同事和各级领导。借这个机会,容我将长久酝酿在心中的尊敬和感谢献给这个拥有优秀传统的学术机构,愿这优秀的学术传统能够薪火相传、常葆青春活力!这里将永远是我学术的故里、心灵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