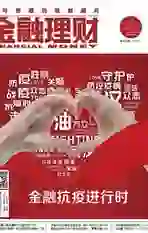保险到如今——香涛笔记体小说
2020-05-18
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保险,是贸易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中外交流的自然而然。直到几百年后,中国试图加入WTO,保险业的开放仍然那么自然而然地最先、最大敞开开放的大门。这是一种宿命,也是行业特性使然。中国的保险毫无疑问,属于舶来品,所以它与世界联系最紧密。这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更像一条纽带,它把古老的变幻的中国与世界连在一起,历经百年风雨,似乎暗淡过,但一经开始,就再没有完全断开。
让人好奇的是,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再到现如今可以说得上是发展得如火如荼,这期间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恐怕也只有亲历者,以及足够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能把故事讲述得生动且透彻。作者香涛是中国银保监会的资深官员,熟稔中国保险业的成长史,他在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才有这一笔记体小说的问世。他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把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把那些精彩的片段按照历史的脉络整理成集,以小说的风格娓娓道来,讲述了中国保险业自19世纪到如今的发展历程。本期《金融理财》杂志摘录了《保险到如今》中的第一篇《广州·谏当保安行》,之后会持续刊登后续的文章以飨读者。
第二篇 李鸿章·民族保险业
1873年冬日的上海,与147年后的上海相对照,显然发生了甚至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巨大变化。在如今的上海市规划馆,仍能看到很多今夕对比的照片,从近乎小渔村到一座世界著名的超级大都市,这种超长时间跨度的变化无法让一个人,通过生命的轨迹,来印证天翻地覆。然而,今天漫步黃浦江边,任头脑中的近代史思绪飞扬,你会从那嵌入中国经济腹地的地理位置,滔滔黄浦江,以及这座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城市所具备的担当,自然而然地串起百年振奋图强的脉络。
从广州到上海,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脉络是清晰的,研究保险史的专家,已经找出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发端。这其实有些耐人寻味,查证出“谏当保安行”那样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土地上经营保险的肇始,似乎觉得不过瘾,非要确认民族保险业何时出现才算罢休。这或许是一种民族感情爱国情绪,然而令这些人士颇有些尴尬的是,在孕育和诞生中国民族保险业的最主要、最有名的推手当中,一位历史人物的出现,使得那种美好、民粹的情绪受到一点影响。李鸿章,这位在中国历史上被贴上鼎鼎大名的卖国贼标签、甚至无出其二的大清重臣,竟然是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始作俑者。
李鸿章,中国历史上极有名声,毁誉参半的人物。他182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所以时人恭维他作“李合肥”。作为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洋务运动的领袖、在1861年至1894年间,已近中年的李鸿章,倡导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自强和改良运动。为了“自强”、“求富”,这位朝廷重臣在他后半生坚持办了许多他最为自负的洋务事业,在中国创建了很多个第一。毫不夸张地说,近代工业的发展,基本是由李鸿章这里开始的。他创办了中国当时最大的3家军工企业。19世纪80到90年代,他开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等一大批民用企业;修建了平汉、津浦等铁路,推动中国进入铁路大发展时期。
洋务运动没有真正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但是却通过一系列工业、农业、军事、教育的近代化探索,使中国逐渐迈入了现代化的征程。
促使李鸿章关注保险事业的,与他着力推进的洋务运动有关。19世纪中叶,由于国内水上运输工具主要是旧式沙帆船。这种沙帆船的模样,我们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影业拍摄的电影中,会经常见到,常常是几位船老大浑身赤黑操弄着桅杆和船桨,风里来雨里去,吱嘎吱嘎的船桨与哗啦啦的水声,构成了中国最早的航运业。当时的外国水险公司不愿意承保中国的帆船,是中国木头船比不过外国的大铁轮,也是挤兑中国的船运业,结果就是中国商人只好普遍地使用外国船只。据说当时上海有成千上万的帆船闲置在黄浦江上,闲置的都快要烂掉了。
中国的船运业(也就是当时书籍上说的轮运业,也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航运业)被外国人捏住脖子,令清政府难以喘过气来。外国商船的高昂费用,使得每年财政收入不过9000多万两白银的家底,承受不住漕运的费用。1871年,江海关机器局道员吴大廷禀告李鸿章,称创办轮船招商局面临“窒碍难行者五端”(招商难、设埠难、保险难、揽载难、用人难)。五难,确是当时发展实业经济的艰难所在。所涉及的经营机制、风险管理、市场竞争、资源配置以及人才建设等,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短板。1872年6月,李鸿章逐条批复,重申兴办新式轮业,并将吴大廷的禀报及批复送交总理衙门。清廷总理衙门批文如下:“遴谕有心时事之员,妥实筹维”。当月,李鸿章上奏《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指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狭重赀以倾奇,则须华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请注意,在官方文件往来中正式出现了“保险”两个字。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僚,矢志自办保险业,这种情形令人感慨。
这里想说明的是,保险是一种商业机制,也是一种近现代生活理念。这样的理念,其实和国人传统的观念有些格格不入。保险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整天假想客户出各种不测之事,翻船、火灾、死亡、伤病、毁坏、失窃、意外等等,听上去很不吉利,与国人信奉的天天挂在嘴边的祝福、安好、平安、康泰、吉祥如意等等截然不同。因此,在长达上百年的过程中,保险概念、保险理念、保险知识,是这个行业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甚至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当保险业务员向客户宣传推销保险产品的时候,有位老人听不惯耳,竟然破口大骂,诅咒儿女和保险业务员不敬不孝。那时候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对保险发展的瓶颈和困难进行摸底。结果是“保险观念难以接受”被排在了第一位,高达73%。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保监会)成立之后,很快开展的一项工作就是推动保险知识普及,包括在中央电视台推出首个专业资讯栏目《幸福保险》,包括由时任中国保监会主席马永伟主编的《领导干部保险知识读本》。连党政干部都不了解、不理解的保险行业,何谈发展。可是,这样的概念,李鸿章在两个世纪之前接受了,似乎有违常情。但是细细探究李鸿章的经历,其实也不难理解。他多年办洋务熟络西方,又对民族轮运业发展的困难非常了解,在眼界和利益面前,保守的东西并没有想象中的顽固。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保险业在近现代经济发展中难以绕过、逾越或者漠视。
1873年1月17日,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轮运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公局”在上海正式成立。关于新企业的管理机制,在筹办轮运之始就存在两个矛盾: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主张“官办”,洋务运动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盛宣怀坚持主张商本商办,与洋商争利,但盛宣怀主张被否定。只是经营不到5个月,上海轮船招商公局亏损4万多两银。现实的教训,让李鸿章迅速调整,由官商合办改为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这是一个重大改变。正是由于官督商办,招商局走上了成功的经营道路。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仿西法以集公司”的企業,该局不仅开中国企业发行股票之先河,而且为此后各家“官督商办公司”,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提供了较多示范。虽然关于“官督商办”机制,尚有许多批评之声,但李鸿章在助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由于李鸿章采用招商集资的方式来解决经费问题,因此把上海轮船招商公局改称为“轮船招商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轮船招商局的共8款章程规定:“栈房轮船均宜保险,以重资本也。栈房原为轮船利于装卸起见,客商货物,应有原人自行保险。惟有存漕粮,一时未能运竣,万一失火,关系非轻,应由商局向保险行保火险。至海面水险一层,保费较重,虽经入奏有案,并未奉准,应请仿照宁船定例,遇风沉没,准商局禀情豁免。至轮船价甚巨,亦应保险。惟每年每船约需保费万金,决非长策,应请俟三年之后,将所得余银,除提利息花红外,另立一保险公款,自行保险,俟保险资本积有巨款,不但可保自船,即他船亦可兼保,一起两得,其利自溥。”“轮船宜选择能干之人,学习驾驶,以育人才,而免掣肘也。夫不精于针盘度线风潮水性者,不足以当船主,不识机器水器者,不能管机器,此辈中中士不多,即中士有可用之人,洋行亦不保险。开办之初,似应向保险洋行雇佣外洋人船主等项三五人,应派能干华人副之,捭可留心学习。将来学有成功,商船所提保险资本,又积有巨款,则可全用华人驾驶矣。”将保险的细节写得如此详尽,可见保险,已经成为经营轮运业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1875 12月28日,经北洋大臣李鸿章特批,洋务派和民族商人开始筹办“保险招商局”,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应运而生。
然而所谓的“运”,其实是两件痛彻肺腑的事件。史料记载,创建保险招商局主要缘起两件事情。一是“伊敦”轮被洋商拒保。1872年11月,轮船招商局在筹建过程中,向英商购买“伊敦”轮,并先行向洋商承保。但各洋商保险行为了扼杀中国航运业,以伊敦轮悬挂中国龙旗及招商局双鱼旗为由,拒不给予保险。招商局无奈用巨资向英国怡和洋行与保安行投保,但条件十分苛刻。双方各自只同意承保保额不超过1.5万两,保险期限不超过15天。这次保险期满后,轮船招商局直接电告国外保险行另行承保,合计保险费节省了一半,但还是十分昂贵。招商局后来与保家行订立保险合同。后者规定,每船限保6万两,超过部分归招商局自保。保费按月“一分九扣”,“值10万两之船,每年保费须纳1万两有余。”“保险难”加速了民族保险业的诞生。
第二个事件,是福星轮被澳顺轮撞沉案。1875年4月3日,也就是清光绪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10时40分左右,招商局“福星轮”由沪赴津,行过佘山,一路放响汽笛冒雾而行,至烟台黑水洋海面,被南下的英商怡和洋行的澳顺轮从斜右撞沉。福星轮所载漕米7270石、绸缎、布匹等货物849件以及旅客、船员等随船沉溺。该案共溺死65人。这是招商局成立后第一起船舶重大碰撞事故。事后时任招商局总办唐廷枢有这样的经典描述:“福星轮在雾中航行,按章每2分钟拉汽笛1次,时速5~6海里,且派水手了头;发现来船澳顺轮时,又急令后退并转舵避让,都是正确的;而澳顺轮雾中航行既不减速,又没按章施放雾号,也无人了,待两船互见时,操舵错误,硬向福星轮撞来而致沉没,溺毙人命,澳顺轮应负全部责任。”李鸿章也指出:“英人显系有意徇纵”,并指示“此时如照每吨赔银八镑,不照命案议偿,则抚恤一层恐未必照给,……尚须留心防范”。但此案几经周折,最后仍然以“两船皆错,两船被失致损合算均分其失。”了结。“澳顺”船商本应赔偿1.1万两,但“澳顺”轮船主闻讯后逃走,招商局无奈支付抚恤费2.4万两。两年后才追赔到1000英镑(折合白银0.36万两)。这一近代中国损失最惨重的海难事件,对当时的清政府和招商局刺激都很大,大大加快了保险招商局建设的步伐。
近代历史似乎总是给中华民族出一道难以描摹的题目,屈辱、难堪、重压多半会与图强发展的机遇一并送到国人面前,中国人往往需要在国家危亡的最后关头才可以团结起来,振兴起来。由于李鸿章的号召力和轮船招商局的成功经营,《保险招商局公启》发布后,“各口来股更多”,华商投股踊跃。成立一年后,清政府太常寺卿陈兰彬上奏折,赞扬轮船招商局“此实中外大局一关键”,三年来,因有招商局与洋商抗衡,“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保险招商局的开办,打破了外国保险业的垄断,保障招商局免受盘剥欺诈之苦,实现了创业者“减少外洋一分之利,就是增加中国一分之利”的初衷。
王韬,清朝后期一位深受西方现代文明思想影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了《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他著有《弢园尺牍》一书。著述中有关于轮船招商局“招商、保险二者要应当相辅以并行”的理论。《弢园尺牍》论述到:“夫运粮不过在春时数月耳,其余专载客附货以相流通,则必有取信于货客者,乃可行之久远,不有保险,则货客且为之馁。”王韬因此提出:应在各通商口岸,以及世界各港口,凡我轮船所到之处,设立保险公司;这样,既能保障我海外百万生灵,并且借以扬我国威;以中国之人保国之货,不必假手于外洋,而其利乃得尽归于我;保险之利开,而商贾之航海者,无所大损,且华人之利仍流通于华人中,而不至让西人独据利薮;若依赖洋人办保险,则难免寄人篱下,权自彼操。
在王韬这一理论的指导下,1876年7月,招商保险局又开设仁和水险公司。由于仁和水险公司只保船舶险和运输险,不保码头、栈房和货物的火灾保险,随后济和船栈保险局的成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878年4月17日,济和船栈保险局正式设立。主要为轮船招商局的码头、栈房和货物投保。其资本额为20万两。仁和、济和两公司相继设立后,资本达到了100万两,承保和竞争实力大大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商对中国保险业的控制,充分发挥了分散风险、经济补偿的保险功能。当年,“厚生”轮在厦门附近沉没,计提7.75万两进行赔偿;从1879年到1883年,由于多种原因,招商局相继有“江长、伊敦、和众、汉广、美利、兴盛、怀远”等轮船失事,大多以保险费进行赔偿,稳固轮船招商局运营基础。
上述史料的寻觅者,在多方考证和印证下,披露的历史事实,令我们得以清晰地发现,李鸿章和他任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创了民族航运业,也带动起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诞生和发展。我们观察历史也可以发现,民族保险业的发端,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实业的发展。在对外开放的贸易往来中,中国人逐步认清了发展实业经济,必须要有保险机制的护佑。而且这个行业,决不能被洋人所把持,否则实业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就会被无情扼杀衰微泯灭。其实,也不仅是保险,我们民族的任何一个行业,都不能完全被别人控制,否则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当然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外开放和外资进入中国,这完全是在中国人自主开放和稳妥有序情形下的做法,与经济失控有本质的区别。这份对民族产业的担当,应该就是保险业的初心。只是,这样的初心在整整140年后,变得模糊不清,一些保险公司肆意举牌实体经济,以“野蛮人”的吃相,侵蚀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那种光怪陆离的闹剧至今令人深思。
历史有时候是最好的教科书,不懂历史的人往往会栽跟头,正所谓殷鉴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