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旦》到《主角》:50多年的积累
2020-05-15何映宇
何映宇

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
2019年10月14日晚,陈彦站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的现场,心潮起伏。“我要感谢我的戏剧,感谢让我阅历了几十年的中国戏曲,尤其是秦腔。”
2019年8月16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公布,陕西作家陈彦凭借长篇小说《主角》获奖,这是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之后,第四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陕西作家和作品。颁奖典礼上,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和贾平凹一起为陈彦颁奖,贾平凹、陈彦两位陕西茅奖获得者同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见证了陕西文学的传承。
陈彦1963年出生于陕西省镇安县,陕西这方水土养育了他,不论是编剧还是小说,他都扎根于土地,书写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事。自17岁发表第一篇作品以来,他在文学和戏剧创作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四十年。2018年1月,陈彦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角》由作家出版社推出。陈彦上承中国古典文学及思想流脉,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写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气象博大。同时,通过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展现出当下中国的时代变迁。他说:“这是我50多年的生命积累。”
公社书记之子的文学梦
《新民周刊》:你的父亲是公社书记,剧团巡演到公社,你每次必去,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戏曲的吗?
陈彦:那时候也无所谓喜不喜欢戏曲,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活动非常少,来公社巡演的剧团是我们当时极少有的娱乐活动,有戏来自然都会去看。
《新民周刊》:《主角》里边写到最大的场面,10万观众看忆秦娥演出,是根据你的真实经历创作的,是这些剧团来演出的事吗?当时的情境是怎么样的?
陈彦:确实是我亲身经历的事,但不是在我童年的那个年代,禁锢年代不可能有那么多观众。真实情况是1997-2000年前后,政府经常办一些物资交流大会,规模特别庞大,有时候在三省交界处搞一个物资交流大会,什么地方人多,政府就在什么地方吸引人,剧团会去那些地方演出。我当时在省戏曲研究院担任一个团的团长,带一个团在那种场合演出过好多次,所以印象非常深。有时演出一会儿,观众就把舞台挤垮了,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真正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孩子们来玩的,站在树上的,钻在舞台底下的,进行物资交流的,人声鼎沸。有时候,他们会请多个剧团同时在这里演出,哪一家的演出好,观众就拥到哪边,这样的情况,我是亲历过多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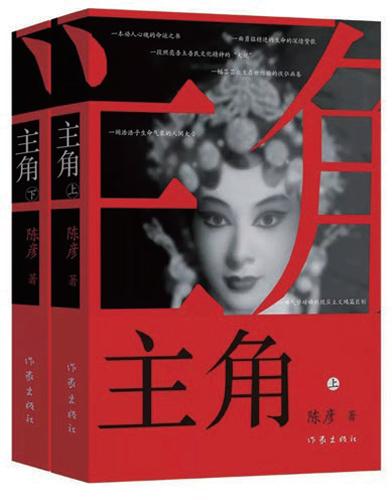
《主角》的名字本来叫《花旦》。
《新民周刊》:你的青年時代,镇安县的文学氛围很浓厚,那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吗?
陈彦:那时候我的家乡陕西镇安县,文学氛围特别浓,《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以及我们陕西当地的文学期刊《延河》大家都爱读,好像当时的年轻人都在做着文学梦,这是补充自己的一种方式,补充,就可能从文学介入了。
《新民周刊》:哪些小说对你影响比较大?有读到柳青的《创业史》吗?
陈彦:那时候还没有读到,我读《创业史》是比较晚的事。那时先读各种连环画,“文革”结束之后,1980-1985年左右,能读到一些外国小说了。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司汤达的《红与黑》、果戈里的《死魂灵》、《莎士比亚全集》等。苏联的小说读得多一些,在文学青年中间广泛流传。当时“伤痕文学”已经开始流行了,出了一系列的中短篇特别吸引人。还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我们都是传着看。到后期,读外国小说就越来越多了。
戏剧的生命力
《新民周刊》:最早开始戏剧创作是因为当时陕西省发起“学校剧”评奖,你创作的话剧《她在他们中间》获得二等奖,从此开始戏剧创作。你觉得戏剧创作对于小说中的对话、人物、戏剧性冲突的把握是否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陈彦:我一开始写小说,也写散文。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让我试一试,看是不是能写个舞台剧,算是完成一个任务吧。我就写了《她在他们中间》,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和她的学生的故事。油印了一份,报到省上,我也没有当一回事,结果四五个月之后,得了二等奖。从这时开始,我就进入了戏剧创作,写了很多舞台剧,有话剧、戏曲。其中四部推到了舞台上。然后我就调到陕西省一个大剧院担任专业编剧了。
我最近老讲这个观点:世界上很多小说家同时也是戏剧家,是诗人。戏剧和小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你看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就是这样,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这一类的作家还比较多,萨特、加缪、毛姆、君特·格拉斯、塞缪尔·贝克特都是。戏剧的这种言说方式、戏剧的凝练、生活提纯和概括能力,我认为对于小说也是适用的。小说虽然打开了生活的一条长河,但也需要像戏剧一样对生活进行高度概括,概括能力越强,小说的容量就越丰富,干货越多。同时我认为阅读小说对戏剧创作也大有好处,戏剧需要对小说借鉴,戏剧有时候提取过纯、抽取过干,它需要稀释,需要毛茸茸的生活质感,这就需要向小说学习。
《新民周刊》:我知道你创作非常的认真,为写上海交大西迁西安的舞台剧《大树西迁》,你先后到上海交大住了35天,采访了100多个与西迁有关的人,采访录音几十盘;为创作舞台剧《西京故事》时,你深入生活做了大量笔记。深入生活是不是一直是你的创作原则?
陈彦:我到西安后写了很多戏,这三部的生命力比较长,像《迟开的玫瑰》推上舞台已经有22年了。《大树西迁》描写的则是上海交大西迁到西安的故事,一开始准备拍影视剧,我去深入生活,在西安交大4个半月,在上海交大外教楼还是博士楼我住了30多天,采风下来感觉影视剧都不太好弄,主要是西迁过程中,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分开之后,两校在认识上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影视剧不好写,那我就先写一个舞台剧,现在这部戏也已经上演17年了,观众也仍然非常认可。我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会做很多功课。《西京故事》后来我之所以会写成长篇小说,就是因为收集的资料特别多,生活笔记写了很多,舞台剧就只有两个来小时的长度,两万多字,容纳不下,后来我就又写了50万字的长篇小说,都是因为生活积累,觉得舞台剧展示不完,才写成小说。像我的小说《装台》和《主角》,都是我几十年亲历的生活,都可以说是浸泡式的写法把它写出来的。
要用当地的方言
《新民周刊》:《主角》动笔最早是在2011年,那是你还在大剧院的时候,当时定的名字叫《花旦》,后来怎么改名叫《主角》的?最初写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表现秦腔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吗?
陈彦:一开始以“花旦”的名字写了5万多字,当时我在文艺院团当院长,觉得生活扑面而来,有点不识庐山真面目的感觉。后来我从剧院出来后,跳出这个圈子,看问题逐渐清晰起来。李敬泽先生看了我的《装台》后给了比较高的评价,后来他说你应该写角儿,你在文艺团体呆了这么多年不写角儿可惜了。我说我原来写了一个,放在那了,现在我思想清晰了,又准备写。我觉得“花旦”更像是一个行当的叫法,“主角”更有象征和隐喻,涵盖面更广一些。我调到陕西行政学院之后,有了寒暑假,时间相对宽裕一些,我也想对自己几十年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做一个回眸。虽然不是写自己,但是很多人物的奋斗经历、困境和突围,都有和自己生活这一方面和那一方面的联系,特别熟悉,所以写起来也就特别得劲。写起来也很自然,如果一部小说只是写一个角儿的励志故事,那就太简单了,不是我想要写的东西,总是想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带进来。它对读者有带入感,而且我们也经历了这种社会变化历程,的确心里也有想法想表达,借这些事件、借这些人物把它们展示出来。如果完全正面来写改革开放是一种方法,可是像我这样,从一个乡村的放羊孩子一步步成长为秦腔皇后的历程,由此牵连出来的社会生活信息会更加丰富。它把中国整个的乡村、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乃至首都和百老汇的生活都勾连出来了。我希望有一个博大的气象。包括小说中涉及的乡村的三五个演员在土台子上的表演、几十个老太太看戏,一直到十万观众这样的大场面,方方面面都涉及了。我觉得还是写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渐变,在这个渐变过程中,人的生命、际遇的改变。
《新民周刊》:女主角的名字叫“忆秦娥”,怎么想到用一个词牌名来为女主角命名的?这个人物现实中有原型吗?
陈彦:没有原型,那应该说是多个人物的综合体。我觉得用词牌名也比较特别,字面上看这三个字,也有意味在其中。在历史上,李白等诗人词人用“忆秦娥”这个词牌名留下的词,也已成为“忆秦娥”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主角》里面出现了很多具有陕西特色的民间语言,为小说增色不少,这方面是怎么考虑的?对其它的方言小说,比如沪语《繁花》你怎么看?如果不请教懂沪语的朋友,阅读时会不会有障碍和困难?
陈彦:我们的小说用翻译语言多一些,城市化之后,乡村的记忆、地域性的文化记忆越来越少。比如我们看中国传统小说,不管是《金瓶梅》《红楼梦》还是《水浒传》《西游记》,其中有很多地方方言,今天我们已经不懂了,可是我们揣摩字的意思,会觉得它非常美妙。今年我又在重读四大名著,我反复在想其中的语言,应该说带着地域性的、民族性的语言非常多,读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写三秦文化,肯定要用当地的方言。我觉得语言是一个地方最大的特色,就像戏曲如果不用方言,这个剧种就不存在了。现在有些剧团在探索,用普通话来说它那个剧种,那是自杀。小说也是这样的,我想追求中国的审美、民族的审美、中国传统文学的审美,总是要在语言上有一些特色,如果随大流,这小说读起来就没味道。《繁花》我读了,写得非常好。一般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我都会找来阅读,学习借鉴一下,《繁花》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我也特别阅读了这本书,非常快意。但是上海的方言用得过多,我们北方人有些地方有阅读障碍,有些话读半天读不懂,理解不了。当然,这不影响小说的美。

西安易俗社青年演员秦腔特技展示。
《新民周刊》:你戏曲研究院工作这段时间,一直专心致志地研究秦腔的继承、创新和发展,秦腔在今天遇到了怎样的困难?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扶持,秦腔是不是越来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陈彦:我离开秦腔剧院已经这么多年了,7年了吧,近期关注的就少一些。近年国家对戏曲艺术的发展的确是重视,但是这种文化传统到底怎么继承发展建设好,其中很多问题是需要认真研究探讨的,不是说给了很多钱就能做好。我觉得可能还要认真研究怎么按规律做好的問题,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断认识,不断探索研究。时间会让事物变得清晰起来。
《新民周刊》:现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担任分党组书记的工作,会不会很忙?
陈彦:现在的工作还是挺忙的,中国戏剧家协会有很多事要干。再加上现在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要求很高,要做的事就很多。我差不多大半生都在做这个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专业回归,挺好。
《新民周刊》: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什么样的感受?
陈彦:还是感到很欣慰,这也是自己50多年的生命积累,《主角》把我该装进去、融进去的都装进去、融进去了,还写得比较顺,毕竟是自己经历过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