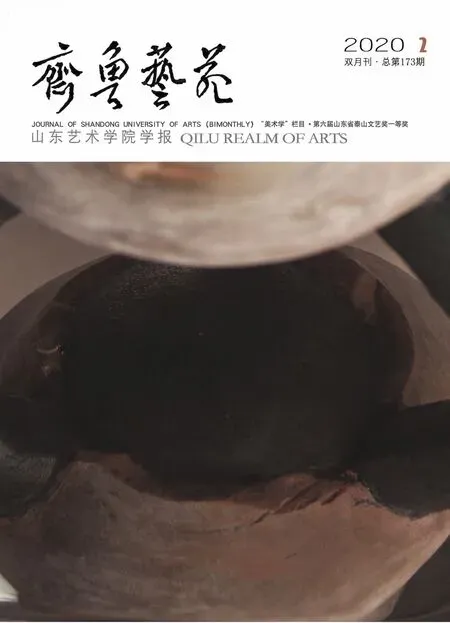陈洪先生早期文论中的“国乐观”述评
2020-05-15王小龙
王小龙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江苏 常熟 215500)
陈洪先生(1907-2002)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翻译家。他对我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和师范音乐教育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同时他又因是著名学案“重写音乐史”的“个案”而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所熟知。笔者发现,现今文献中涉及陈洪先生“国乐观”的专文尚属阙如,而这又是理解陈洪先生学术思想和经历的一把重要钥匙。故撰此文以为引玉之砖。
一
陈洪先生1929年秋从法国南锡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后,即开始了他大半生的音乐教育生涯。他先是在广东戏剧研究所从事音乐研究和教学工作,1932年在广州与马思聪合作成立广州音乐院(私立学院,今星海音乐学院前身)。1937年8月,应肖友梅之约请,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前夕赴上海接替患病的黄自先生的职务,任国立音专教务长、教授。1941年底,国立音专由汪伪政权接管。陈洪先生遂“教一些公共课,同时在校外另谋生计”[1](P99)。抗战胜利后,陈先生赋闲在家(1)1945年9月抗战胜利到1946年8月陈洪接到邀请出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中间这一时间段陈洪先生所任何事各大史料并无记载。笔者询问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李岩研究员,他告诉我此时陈洪与家人以织布为生。。1946年8月任南京国立音乐院教授、管弦系主任,1947年11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1949年8月任国立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音乐组(不久独立为音乐系)主任。
陈先生早期(回国那年他22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42岁)辗转于广州、上海与南京从事音乐办学和音乐教育实践。同时他不停地著书立说、办刊办报,创作音乐作品,译介西方音乐理论和名曲名作。这些早期的著作、文论成为了我们了解中国专业音乐教育发轫的生态面貌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料之一。
纵观陈洪先生的履历,他与“国乐”实践很少交集,从求学经历到后来的音乐办学、音乐教学和研究,基本上做的是将西方音乐传入到中国高等音乐教育领域的事。但是,在他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陈洪文选》(下文简称“文选”)里,有不少篇目涉及对中国音乐的评述,以及对“国乐”独特的看法,大多还是这方面的专论。主要篇目有:
《假洋鬼子与中国新音乐》(1934,“文选”pp20-21)
《国乐的定义》(1934,“文选”pp35-38)
《新国乐的诞生》(1939,“文选”pp39-45)
《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技术问题刍见》(1946,“文选”pp46-49)
《中国新歌剧的创造》(1937,“文选”pp64-65)
《楚辞与音乐》(1946,“文选”pp259-260)
《唐代的燕乐和绝句》(1946,“文选”pp261-264)
《诗词与音乐》(1946,“文选”pp265-266)
附录3《复兴国乐我见》(2)该文的作者,署名为肖友梅的笔名思鹤,但陈洪先生亲口说出自他的手笔。文章的内容也大多与陈洪先生其他文论一致。笔者倾向于该文为陈洪先生作。参见“文选”脚注2。(1939,“文选”pp394-396)
另外,《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第八次音乐会作》(1931,“文选”pp17-19)也有很大篇幅涉及国乐的内容。
从以上为数众多的篇目可以看出,陈洪先生早年是很关心“国乐”的前途命运的,为这个话题投入了很多精力去思考、去写作交流。虽然陈先生当年主要从事的是将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引进到中国的工作,但是透过以上这些文论可以看出他其实对建立中国新型“国乐”的事业颇为关心,很有传统士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忧天下”的风范。他论述“国乐”的时间集中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早的文论写于1931年,最迟的写于1946年,跨度15年),正值他二三十岁“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也正好是他早年专业音乐办学和专业音乐教育的时期。笔者注意到,建国以后他对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相关论述。
二
陈洪先生关注“国乐”话题,可能是源于归国后国内音乐现状对他的刺激:“父亲23岁从法国归来,他用新的眼光审视‘礼乐之邦’,发现它的音乐已经大大落后,辉煌不再了”[2](P342)。确实,从《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为广东戏剧研究所管弦乐队第八次音乐会作》(3)本文文题,《绕圈集》目录列为“音乐革新运动之途径”,正文文题是“新乐革新运动的途径”,页眉则为“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文选”最后选列为“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笔者以“文选”文题为准。的一段论述中可以强烈感受到陈洪先生青年时期对中国音乐衰亡的切肤之痛:
其实我国的艺术不仅是落后,并且是由衰而亡了!别的我不讲,且把音乐说一说吧。要证明我国音乐的衰亡,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用不着把我国的社会经济技术来检讨,也用不着审察国乐的内容,单看奏乐的人和所用的乐器,便可以下一个肯定的断语。走进欧洲的戏院去,一眼便看见几十位穿着制服的乐师,整整齐齐的坐在舞台前面,指挥者的棍子一动,乐声便悠然而起,高低抑扬无不尽致;回看我国的戏院,里头的音乐家,类多袒着半边肘子,盘起一条腿,拿起棍子来,咬牙切齿地痛击痛打,好像和他们的乐器都有了不共戴天的深仇,非把它们一朝打完不可!虽云痛快之至,究亦野蛮之极,如果这样也可以说是音乐,那么猫屎也可以算为香饵了。
试问六个洞尚不完全的洞箫如何比得上人家十三个洞的Clarinet?两根弦老是“合尺合尺”的胡琴如何比得上人家四根弦的Violin?其他如Piano,Doublebass之类,我国不独没有乐器能与比拟,简直连做梦也不曾梦见这么伟大的东西!没有乐器如何发出声音?没有好乐器如何发出好声音?我国的音乐究竟好在何处?
……
闲话少说,且问中国的音乐是否衰亡?确已衰亡了!我国音乐最隆盛的时候是在唐朝,那时有五十余人合奏的谱子,有主调还有和声(据说日本宫内还藏有此项乐谱);现在呢,和声早已没有了,至于主调则从年头到年尾总是那几个滥腔,此外如拍子之平淡,节奏之单调,音色之庸俗,都到了不能再听的地步,其有待改革,是很急迫的了。[3](P17-18)
陈洪先生从观察国乐所用乐器,感觉到了制造工艺的落后,又从舞台演出的效果,感受到了中西音乐音质上的巨大差异,他与同时期大部分有识之士的看法一致,都基于“社会进化论”的立场,认为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这是他对于“国乐”的基本态度。陈洪先生认为“国乐”已经衰亡,非要进行改革不可,“其有待改革,是很急迫的了”。所以他是坚定的“国乐”改革派。
其后他接受了唯物主义哲学观,又据以确认了这些看法:
艺术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这上层建筑之高或低,左或右,伟大或渺小,繁盛或凋零者,不消说的是社会的底盘——技术和经济。技术落后和经济衰败的社会,是决不能产生伟大和繁盛的艺术的。
我国的技术落后和经济衰败到什么田地,是谁都看得清楚的。但是只要一谈到艺术,便有许多人相信中国的艺术便是东方的宝库,也有许多人,以为中国什么事情都不行,只有艺术却可以和西洋人比赛一下。这种观念深深支配着一般人的思想,甚至于谈艺术改革者也还逃不出这个圈套。因为中国的文明以“精神”胜,艺术是“精神文明”之一种,必是胜人的好东西,檀香是檀香,化成灰也是檀香化的,当然非保存不可;如果要改革,也只宜“合中西艺术于一炉而冶之”,炼成“折衷派”的艺术来。固已炼出来矣,只可惜不中复不西,画虎反类犬!这都是不明白决定艺术的条件,不承认我国艺术落后的结果。[4](P17)
由此可见,陈洪先生理解的“唯物史观”,是简单对应的机械唯物史观:技术落后和经济衰败必然导致文化的落后。因此,从感性和理性两方面他都越发感到国乐积弊严重,急需改革,为此他呼吁,“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旧戏旧曲之自然淘汰,同时又须预备新音乐的诞生”[5](P18)。
三
然则陈洪先生理想中的“新音乐”,抑或说是具有时代精神的“国乐”(“新国乐”)是怎样的一种音乐存在呢?
尽管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是陈洪先生喜用“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在《国乐的定义》一文中,他首先认为音乐具有“内容”“形式”“演出”这“三个元素”:
倘若我们把音乐的本身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出音乐的三个元素来:①音乐的内容,即思想、情绪和曲意;②音乐的形式,即曲式、旋律和声与节奏;③音乐的演出,即乐器和演奏技术[6](P36)。
而且他认为,“内容”是音乐三个元素中最为重要的元素:
最重要的当然是音乐的内容。这好比作一个人的灵魂,他的性格在这里已经确定了。有了音乐的内容,如何把它记录起来呢?这里便需要有音乐的形式。但这形式还仍然是空空洞洞写在纸上的东西,如何把它实现出来呢?这里便需要有音乐的演出。音乐的演出是为着音乐的形式而存在,音乐的形式则为着音乐的内容而存在;归根结蒂,音乐的生命寄托在内容的上面,形式是躯体,演出则不过一些工具的运用而已[7](P36-37)。
在《新国乐的诞生》一文中,他更加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他首先探讨了音乐——声音的艺术——“便是人类应用声音的方法以传达情绪的活动”[8](P40)。传达情绪是动机和目的,应用声音则是手段或工具。因此他认为要把“内容”和“形式”分开观察。而内容决定国乐,国乐的内容要能够同时表现中国的时间和空间。
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探讨国乐的“内容”是“研究国乐”“首先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国乐”应有的内容,“便是带有中国人现阶段的时代精神和本国的地方色彩的思想情绪和曲意”:
比方说,中国人是和平的、宽大的、博爱的;或者说中国人是被压迫的、苦楚的、革命的;这都可以叫做中国现时的时代精神,作曲者便应该深深地体会了这精神,把它放进曲里面去。又比方中国有许多美丽的传说、风俗和自然景色,作曲者便无妨把这些应用于作品里面,使作品带上了中国的地方色彩。中国的国乐作家须是一个真正认识中国,并且对于中国深表同情的人。由于认识和同情,他才能够于不知不觉之间把许多中国的东西放进作品中去,而成为中国的国乐[9](P37)。
这就是他心目中“国乐”的理想模式。
接着,他进一步阐述了心目中“国乐作家”(即作曲家)的理想人格:
国乐作家应该是地道的中国人民,是纯粹的爱国者,他了解中国的一切,同情中国的一切奋斗,他自己也是奋斗的巨轮内的一个轮齿,不断地和各方面有亲切的接触;由于这了解、同情和接触,加上他的如火如荼的热情,新艺术的种子乃能在他的心中成了胚胎,借了适当的技术表现于外,在声音方面的,便是我们所期望的“国乐”。[10](P40)
针对“音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音乐的内容不容易把握、音乐不容易表出社会环境的精神和色彩”的观点,陈洪先生认为,凡是音乐必有情绪,这是认识音乐内容的一把钥匙,“试问哪一种情绪之形成,能够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11](P41)
因此,通过这一层层推进的思辨,陈先生最后认为:
国乐是中华民族的呼声,是要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灵魂的,才配叫做国乐[12](P37)。
什么是国乐?
顾名思义,中国的国乐,应该是可以代表中国的音乐。
……
国乐的内容究竟应该怎样?具体一点,可用以下三点来说明它:
(1)国乐是活的音乐,它的内容应当敏锐地跟随着时代不停前进。
(2)国乐是中华民族的呼声,在目前,这呼声应当是极度振奋的、壮烈的、战斗的。
(3)国乐产生于中国的环境里,应当尽量反映着中国的民情、风俗、文物和景色。
这可以说是我们对于国乐内容,具体地提出来的要求:必须有此内容,才配得上“国乐”的名称。[13](P41)
对于国乐采用的形式,他认为,国乐的形式和演出,用中国式或用外国式都可以。因为这是“选择工具的自由”。他认为近世西洋的音乐形式和演出,比我国大有进步,因此,陈先生认为“创造新国乐时,在这两方面,不妨尽量采取西洋人的长处,西洋的和声学和曲式学大可以全盘采用,西洋的管弦乐队也应当整个搬过来;这些犀利的工具应该绝不客气的拿过来就用,才希望能够把西洋文化‘迎头赶上去’”[14](P38)。
在其他多处论述中,陈洪先生也表达了类似于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的主张。他认为,西洋音乐有许多现成的工具,如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及各种乐器,都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对于现成的工具应当毫不客气地拿过来就用,这样才有希望赶上人家的文化[15](P18)。
陈洪认为,在他持论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没有可以代表他主张的实际音乐作品问世:
倘若有人问我,我们的理想的新国乐在哪里呢?我只好回答他说:新国乐尚未诞生,或正在诞生之中[16](P41)。
因此,在《音乐革新运动的途径》一文的结尾,作者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而充满感情的话:
今日还不是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时候,不过我们应该积极预备它的诞生。据种种情形看来,中国新音乐之产生当在五十年后,从今天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是过渡时代之一段,我们都不是创造的人物,我们是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们的责任是筑一条从此岸通到彼岸的桥,各个人都化作桥中的一块砖;要把这桥造得又平又稳,后起的人乃能够安然从死的此岸踏到生的那边去:这是我们认定的工作,和我们认定的工作的意义[17](P19)。
陈洪先生认为的“桥”和“砖”的过渡工作,就是“接受比我们先进的西洋音乐”,理由有三:第一,西洋音乐有许多现成的先进工具;第二,文化需要相互交流相互碰撞,才能有新的文化产生,“这是世界进化的公例”;第三,因为我国音乐衰亡,必然出现音乐的真空,此事需要借西洋音乐来补充一下。[18](P18)
由此可见,陈洪先生主张和践行将西洋音乐引入中国社会,其最终目的乃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新音乐,为了给“新国乐”的诞生作预备。这是一种很崇高的事业。在这一点上,他的主张与王光祈的“吾将登昆仑之巅,吹黄钟之律,使中国人故有之音乐血液重新沸腾。吾将使吾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19]的理想、目标是一致的。
确立了国乐的内容和形式后,陈洪先生进而反思阻碍国乐诞生的最大因素。陈洪先生认为是中国“复古思想的作祟”:“我们须知复古思想的危害既是及于‘文化的全部’,所以它不但直接阻碍音乐的进步,间接的阻碍也是很重大的”。随之陈洪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特别提出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在准备创造新国乐的时期,最需要“急起直追”和“迎头赶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最大敌人便是“愈古则愈好”的复古思想。
陈先生引用了胡适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警策之辞来申述他“急起直追”和“迎头赶上”的主张:
林语堂先生在《新中国的诞生》里说:“事实是这样的,我们都极愿意保全我们的旧文化,但我们的旧文化却不愿意保全我们”。[20](P43)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的文化改造实际上是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抉择。这也从侧面道出了陈洪先生主张抛弃“旧国乐”而大声疾呼“新国乐”的缘由。
四
虽然陈洪先生认为在他持论的当时,国乐还不可能诞生,但是他已经为建立“新国乐”或曰“中国新音乐”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思路和主张。
以“拿来主义”的眼光,陈先生认为,乐器上可直接采用西洋管弦乐器,理由是:
既然世界上有现成的飞船和高射炮,我们也一样可用,对于这些工具,又何必斤斤于“人家的”“我们的”呢?[21](P44)
和声,陈先生认为:
新国乐的和声固然不必——而且不能——完全采用欧洲的和声学,但其中属于音响学(Acoustics)的基本理论,如泛音的原理、音程的构成、和弦的构成等,纯属于客观的、物理的部分,我国音乐也当然可以全盘接受而利用之,用不着再费人力时间,去另起无谓的炉灶。[22](P44)
陈先生还指出,国内曾有不少音乐同志,作过用西洋和声配中国曲调的尝试,结果亦皆满意。新国乐的和声问题应如何解决,从这里应该可以找出端绪。[23](P44)
陈先生所说的作中国曲调配和声尝试的人有哪些呢?在《歌曲、伴奏与和声——高师音乐系科教学改革的一点意见》一文中他披露道:新中国成立前我曾是江定仙教授的邻居,我听见他为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配了优美的钢琴伴奏,使这首民歌大为生色,我听后印象深刻,至今仍有“余音绕梁”之感。[24](P109)
也就是说,陈先生当时虽认为新国乐不可能问世,但他心中也有少数几个是为改造新国乐榜样的实例,如改造和声为我所用方面做得好的作品,当如江定仙《跑马溜溜的山上》这一类。
这说明,陈洪先生的“拿来”并非简单照搬,而是用西方音乐的先进形式,合乎“音响学”原理的形式尽可“全盘接受而利用之”,来表现中国音乐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灵魂,所以陈洪先生说:
国乐之所以为国乐,赖它的内容能够保有中国的特色。这特色不是古典的、无意义的,或仅抄袭前人的残章断曲,便算了事,却是活的、现代的、革命的、奋斗的、复兴的、伟大的,是中国民族的情绪、意识、观念和思想的表现。至于国乐的外形,既然不过是一些工具,便绝对不宜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应该尽量接受世界的文化遗产,赶上世界的文化水平,同时也便是提高国乐的效能。[25](P45)
上文写于1939年。在1946年的《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技术问题刍见》一文中,他直截了当地“条陈”他的主张:一、音律,采用十二平均律;二、乐谱,采用五线谱;三、音阶,采用七声十二律八十四调音阶;四、和声,尽量接受世界遗产;五、曲式,以自由发展为原则;六、乐器与乐队,工具世界化,以现代的键盘乐器和管弦乐队为主体,可随时加用音色特殊而富于地方色彩的乐器,为二胡、琵琶等;七、标准音,黄钟律345。作者原注说“黄钟为Fa(振动数每秒钟345)经顾毓琇提请教育部定(廿四年?)”。可见是沿用了古琴的正调,即现在常见的1=F。
关于音阶,为什么陈先生不沿用欧洲大小调体系,而提出八十四调的主张呢?他说,我国的音乐,向来是多调的。他引用朱载堉的一段话,诗经三百篇中,凡大雅三十一篇皆宫调,小雅七十四篇皆徵调,周颂三十一篇及鲁颂四篇皆羽调。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皆角调,商颂五篇皆商调。又引用史记中“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然后作者说,可见古人对于调的运用是很注意而且很有效果的。欧洲中世纪十二调被淘汰成为二调,我认为是欧西音乐的不幸,希望我国新音乐家对于我国的八十四调能好好地运用。[26](P48)
这一主张即使今天看来也颇前卫。黄翔鹏先生2003年出版了《中国传统音乐一百八十调谱例集》(4)黄翔鹏.中国传统音乐一百八十调谱例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以“同均三宫”理论逻辑又推演出一百八十调(5)一个均有三个宫,一个宫有宫商角徵羽五个调,一个均则有十五个调,一个八度有十二个半音,所以共有一百八十调。,并以谱例加以证明。问世后虽然学界褒贬不一,但此举将中国音乐多调的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则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和声,陈先生首先认为要尽量接受世界遗产,但也认为欧西和声中有不近情理的部分,如禁用平行五度,禁用“False Relation”之类,当然我们不必全盘接受。他还认为,现世欧洲的和声是应用于大小两音阶的,对于我国的许多音阶也未必完全合用,这一端我们必须另辟蹊径。但科学的部分应尽量接纳。这篇文章相较1939年的口气已有所变化,由 “全盘接受”变为“尽量接纳”。这也说明,陈洪先生看待问题也随着时日的变迁不断深化,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还持激进的“全盘西化”观的话,40年代后,陈洪先生的看法则更为稳妥和切合中国实际。随之他说了一段话,是他对中国音乐织体风格的大胆预测,笔者认为也是他因“对位化和声”的主旨发挥而来:
有人预料下一代的和声将为“复调化的伴奏式”(Polyphonic accompaniment),这可以说是集欧洲复调音乐时期(十五世纪以前)和主调音乐时期(1600年以后)的大成。便是:有一个主调,另外加伴奏,(这是主调时期的特征),但这伴奏的自身乃由许多个曲调所组成(复调音乐的作风)。这也许是中国音乐该走的路。[27](P48)
联想到现当代作曲家所作的中国风格的钢琴曲和各种管弦乐队作品,从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到现如今谭盾、陈其钢的作品,大部分成功之作都是多线条的,而非沿袭西方主调音乐块状和声的织体思路,因此,陈先生的预言可以说是准确的。
在《中国新歌剧的创造》(写于1937年)一文中,陈洪先生对中国新歌剧发展的一些要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话剧是文学、美术、舞蹈的综合艺术,歌剧还要加上音乐。单就音乐而说,歌剧的音乐也比普通的音乐复杂得多,可以说是综合一切声乐和器乐的大成。再加上话剧的全部成分,其复杂情形可以想见,不论在剧本创作上或在演出上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事。
陈洪先生又认为,中国需要歌剧:国人需要歌剧是很迫切的了。乡下的老百姓虽然仍可以和旧的锣鼓戏相安,但这种锣鼓戏一日不肃清,封建思想和宗法思想的毒便一日不能消灭。所以创造新歌剧来代替旧剧,不仅是站在艺术的立场上来说的,却也是站在政法和道德的立场上应该说的话。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是应不顾任何困难,马上负起这个责任,把新的歌剧创造出来。[28](P64)
陈洪先生认为Melodrama最适合中国的新歌剧样式,因为是歌唱与说白并用,“与中国的锣鼓戏有多少相似”。但是“到底歌唱的成分比说白的成分强,并且全剧用管弦乐队配音,所以仍然是一种歌剧”。[29](P64)
接着作者从“剧本”“曲谱”“乐队”“演员”四个方面探讨了新歌剧如何创造的问题。
关于剧本,陈洪先生认为从外观到内容,特别是内容,他主张要彻底改造,绝不能妥协。他补充说,“改良”的办法完全不能用,那是等于自杀。
关于曲谱,陈洪先生认为旧戏音乐的失败,其主因在于没有创造性,来来去去总是那一套曲谱,什么戏都适用。这里陈先生其实说的是中国传统戏曲“一曲多变”的现象。陈先生认为,这样的做法,音乐的本身有没有价值姑且不说,和戏剧的内容没有关系已经是一个致命伤。他认为,新歌剧的音乐应该完全重新创作——根据各剧本的内容去创作——绝对不容抄袭或套用。这样音乐才能够在戏剧中发挥效力。[30](P64)
他还补充说,有人主张相当地采纳中国固有的旋律或调子,这点我也不反对,但我以为不能够把整个的旋律或调子采用,而只可取其音调,或者“断章取义”,以求造成一种中国化的气氛。但这办法仍然是对于高雅的古调而言,其他锣鼓戏的烂调和流行的下流的东西都应该一律摈绝。[31](P65)
关于乐队,他认为当以时代性为第一要点。他说乐队是一种工具,工具是没有国界的,应该选择最优良的来使用。这也符合他的一贯主张。
关于演员,他说“这是最成问题的一项”。中国人受过正当的声乐训练,能够正确地唱一下子的真是少到凤毛麟角。
最后,作者认为,“现阶段的歌剧仅是一个过渡阶段的东西,内容简陋是在所不免的”。但是目前只要把这做得好好的,我们便应该满足,然后,自然会有中国的新Opera。[32](P65)
陈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还短暂研究了中国音乐历史中的某些具体音乐形态问题,并撰写了专文进行讨论。主要有三篇《楚辞与音乐》《唐代的燕乐和绝句》以及《诗词与音乐》。

此文发表于1946年6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比《关于中国新音乐的技术问题刍见》一文(《音乐杂志》1946年12月第2期)早半年,由此可以得知陈先生主张八十四调的由来。
另有《唐代的燕乐和绝句》及《诗词与音乐》两篇均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前一篇认为唐代的文学与音乐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受音乐的影响。后一篇认为历代诗词与音乐是不可分离的:
纵观我国诗词演进的路线是:诗经——楚辞——魏晋乐府——唐代律诗——宋词——元曲——传奇昆曲。其间除唐诗曾暂时离开过音乐外,其余都是和音乐不可分离的,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是“音乐文学”。[34](P266)
而且陈先生对于新诗创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诗不一定是可唱的,但诗是音韵和节奏的文学,有了音韵(不一定是脚韵)和节奏……才能远垂于后世。这从历代诗词和音乐的关系上是可以见得到的。让我们再抄一遍黄山谷的话:“比律吕而歌,列干戚而可舞,是诗之美也。”[35](P266)
五
作为时代骄子,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能够站在振兴国家文化的高度思考中国“国乐”的发展大计,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读着七八十年前陈洪先生关于国乐的议论文字,笔者不禁为他的满腔热情所感染,又对他为国乐的深谋远虑所深深感佩,联想到他其时尚是一个毛头小伙,又为他的智慧早熟而赞叹!一如冯长春所说,“不管怎样,陈洪的新音乐观是和塑造新的国民性、改良社会风气,乃至与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的崇高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所透露出的深深的爱国情怀与正义感,也会打动今天的每一位读者”。[36](P381)
陈洪先生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即他的世界观,大多是唯物主义的、辩证的世界观。他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在他的很多文论中都有反映,比如他说“音乐的形式完全是跟着社会经济和制造技术之进展而决定的”[37](P17)、“先有社会然后才生艺术,犹先有物质然后生精神。艺术不是超人的,不是个人的,它是社会的、大众的。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于作为社会的底盘的经济条件,比较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它到底是社会的产物,和法律、道德等一样地是为一般状况所决定了的。”[38](P5)正因为在那个时代下,他的世界观总体而言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先进的世界观,与当时诸如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的“为劳苦大众的文艺”不谋而合,所以他分析国乐的问题以及开出的药方基本是准确的。
正因为持有符合时代精神的正确的世界观,他才能准确抓住国乐的本质在于“代表中华民族的灵魂”,才能准确判断出当时国乐的一些弊端,如音乐环境、乐器制造等问题。陈洪先生对“国乐”的看法也是自成体系的,包含对国乐的精神内核的看法,实现“国乐”新途径措施的建议等等。他有关国乐的讨论,可与刘天华的《国乐改进社改进计划》这样的文献并置而论。
他提出的“工具全盘世界化和现代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现代戏”运动中广为贯彻设施;他主张的音阶要多使用中国的“多调”,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构建的“五声性调式体系”中得到系统阐发,也涌现了大量作品;他预见的“复调化的伴奏式”在建国以后大量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和其他作品中成为织体的常态;他指出的中国新歌剧要走“歌唱与说白并用的Melodrama”的道路的预言,后来在解放区“新歌剧”的诞生中变成了现实。由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洪先生也是探索新音乐道路洪流中的急先锋,他大声疾呼国乐必须改革,这与刘天华、王光祈、郑觐文等的主张形成了一股时代合流。他的业绩应该被历史所承认。
当然,今天来看陈先生的论述,有些言论也有着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他认为音乐以内容为最重要,但是纵观音乐历史发展的长河,音乐的内容和形式的重要性是此消彼长的,西方音乐在巴洛克时期,形式的重要性就大于内容的重要性,20世纪很多信奉音乐自律论的作曲家也是将形式的地位大大抬升了。因此,以“内容第一”的观点来判断是不是国乐,本身是有缺陷的,试问阿隆·阿夫夏洛莫夫的作品是不是国乐呢?这让笔者联想到了文学界《大地》的作者赛珍珠(Pearl S. Buck),她的作品尽管对中国充满了同情,而且也很有中国味,文学性很强,还得过诺贝尔奖,但不能就据此说她的作品是“中国新文学作品”。
他对中国乐器的指责也似为过激之辞。因为他其时尚未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国乐的一些现象。不过,这也是当时国乐落后的实际迫使他不能从容思考,不能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分析提取优秀的成分所致。但20世纪40年代他的文献,在客观、辩证方面得到了加强,说明他的判断也在不断朝着客观公允的方向努力。
还有,陈先生虽然注意到了国乐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但是不可避免地忽视了国乐的文化性和历史性特征。国乐是一种文化,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和行为模式的积淀,是有历史继承性的存在。如果撇除了这种历史性,就会只看到利用西方的器物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而看不到西方器物的这种文化殖民性。也就是说陈洪先生只看到了文化“进化论”的一面而忽视了“文化价值相对论”的一面。当然,对陈洪先生作这样的要求,事实上是用现代眼光苛求古人了。
余论
陈洪先生因《论战时音乐》而被历史冷落了半个世纪,现在确实需要对他进行很好的纪念。我们有必要研读他的存世著述,尽量以“理解的同情”的眼光去揣摩当年他提出这些主张的“历史语境”,从而对他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世纪之交的时候,上海以陈思和、王晓明为代表的文学界人士,发起了“重写文学史”的倡议,随后引起的大讨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其中有学者提出:“五四运动”的精髓在于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二三十年代大部分时代精英分子都投入到这一运动的洪流中,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难当头,形势紧迫,所以很多人又转向了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启蒙”与“救亡”因而成了那个时代“双主题变奏曲”。随之也出现了阵营的分野以及路线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的错误,将前一批人定性为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胡风首当其冲。陈洪先生被历史冷遇了半个多世纪,应该也是因这种“左”的思想引起的。今天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第3个十年,我们的看法应当超越历史:事实上无论是开启民智还是抗日救亡,都是为了挽救危亡的旧中国,都为了试图建立新中国。用最新的表述概言之,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都是仁人志士,都应该得到肯定。冯长春认为,20世纪上半叶存在两种不同思想实质的“新音乐运动”,一种指称无产阶级革命音乐,抗战时期则指称为抗战音乐,现在通行的教科书往往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一类新音乐。但是对由陈洪、欧曼郎、肖友梅等人提出的旨在强调学习借鉴西方音乐文化、创造类似于俄罗斯国民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的“新音乐运动”却关注很少。这是今后学界应该加以重视和“重新审视和思考”的必要课题[39](P384)。
陈洪先生秉持的是唯物主义的艺术发生论,因此他特别在意大众的文艺,适时地提出“武器艺术论”(6)见“文选”或《绕圈集》第一篇。,这与左联的主张,与其后“毛泽东思想”其实是合拍的,因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名言“文艺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被后人称之为“文艺武器论”。主张一致,按说应该是同一阵营的才不属意外。但是为什么陈洪先生却被蒙冤半个多世纪而不能“还历史本来面目”呢?有人认为恐怕是党内历史上的宗派主义以及“阵营”意识在作怪。因为陈洪先生曾跟马思聪、肖友梅等人走得那么近,“是肖友梅的得力助手”[40](P341)。“人以群分”,他自然归属于历史上的“学院派”,而与“救亡派”形成了质的分野。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撰写新的音乐史时,就预先将陈洪先生的《论战时音乐》找出来,并特意修改,给陈洪“定了调”。
笔者还认为,将陈洪先生拿来作为后来教科书批判的“靶子”,也显示出一种“批评的安全模式”,因为据很多人回忆,陈洪先生性格有点软弱,为人又特别宽容、厚道,当时又并不属于位重权贵者,拿他开刀不会有多少“后续效应”。
“批评的安全模式”是傅谨《老戏的前世今生》这本书提出的一个名词。傅谨在其中《没赖场,赖和尚》一文中说:
正是由于出家人的实际社会地位并不高,他们之成为社会道德秩序遭受毁损时承担责任的替罪羊,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使一般人可以很方便地将破坏社会道德的责任,归罪于他们,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既可以反衬出自己的道德优势,同时又不需要为这样的责任误置而付出太大的代价。出家人很少有机会、有能力反抗这类有意的误解,他们没有多少洗刷的可能。因此,我把这种行为方式称作“社会文化批评的安全模式”,在多数场合,直言批评社会文化现象是需要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勇气的,然而那些既想体现自己在道德上的优势,又不愿意冒风险的聪明的批评者,总是会想方设法寻找某些批评的安全模式,就像通过无端和放肆地嘲讽和尚道士的偷情欲望,以标示清高一样。[41](P239)
正像戴鹏海老师所详细分析的那样,《论战时音乐》这篇文章“即使读者是初中文化程度,只须稍具判断力而又尊重事实,……无论谁都决不会得出陈老发表了怀疑‘音乐服务于抗战这个方向’的论调和散布了‘音乐与抗战无关’的错误论点的结论”。但为什么持此论者会横行半个多世纪呢?用“批评的安全模式”去理解,就会顿然冰释。合理的解释是:革命者的“新音乐运动”需要靶子,靶子可以是现成的,也可以直接造一个,所以才会将陈洪原文篡改为“需要在救亡音乐之外另找出路”[42](P305),又因为陈洪先生当时正好不在权力中心北京,历史上还跟马思聪、肖友梅走得那么近,把他树为靶子,既有一定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非常安全。因为陈洪自己“几十年从不涕泣,只是默默隐忍于心”,因为他明白,“真理”和权力是掌握在领导手中的。“任何有悖于主流论点的解释和辩白不但不能讨回清白,反而会引来诸如‘斗争新动向’之类的新帽子”,“所以他既不反驳,也不承认,沉默以对”[43](P341),这样的结果真是令后人唏嘘不已!
今天诋毁陈洪先生的声音已经远去了,但是我们也应当防止另一个极端,就是将对类似陈洪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人为抬升到一个不应有的程度,而应当实事求是的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比如,对黎锦晖的评价,过去说是黄色音乐鼻祖是不对的,现在拔高到现代流行音乐之父的程度笔者觉得也不是很合适。回到陈洪先生的国乐观,我们既要看到陈先生振兴国乐的呼喊努力,同时也要看到当年他认识上的缺陷,以光大他的宏愿,弥补他的不足。这才能告慰先人,继往开来。
作者附言:本文原为2017年11月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陈洪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发言稿。其后又得到了朱晓红、朱建萍、韩中健、邓林、李岩等老师的指点,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