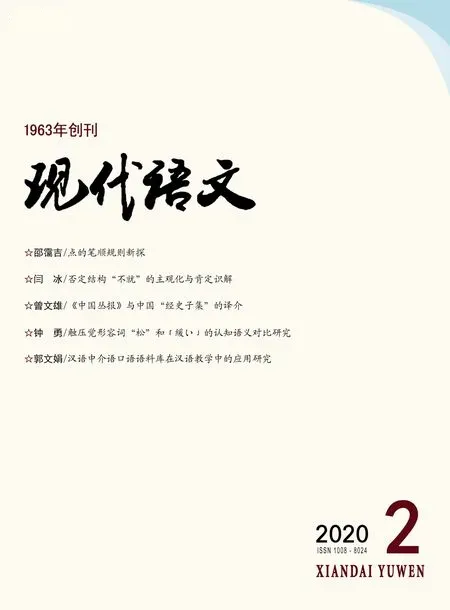《中国丛报》与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
2020-05-11曾文雄
曾文雄,刘 青
(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一份较早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英文刊物,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于1832年5月创办,后于1851年12月停刊。1833年,美部会另一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开始在广州负责主管《中国丛报》的刊行事项,1847年之后,该刊的编撰即由卫三畏替代裨治文负责。该报在美商同孚洋行老板奥利(D.W.C.Olyphant,?—1851)的赞助下得以印刷出版。《中国丛报》最初在广州印刷;1836年,印刷所搬至澳门;1844年10月,迁至香港;1845年7月,再次迁回广州。在发行期间,《中国丛报》刊载了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商业和对外贸易、自然气候、风土人情、宗教等方面的文章。其中,《中国丛报》也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进行了译介,为当时的西方世界勾勒出一个大致的中国形象,对了解当时的中国经典外译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试图考察目前较少涉及的《中国丛报》对“经史子集”的英译情况,描述中国经典译介的动机、类型、传播方式以及在译介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缺憾。
一、《中国丛报》“经史子集”的译介动机
19世纪30—50年代,《中国丛报》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一些固定的“文化场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流通的范围广及欧洲社区、尤其是在香港和上海的欧美租界等,“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超出了其设计师的原来预期”[1](P53)。在发行的20年间,《中国丛报》以较为固定的栏目,以书评、节选出版物的内容、杂记游记、时事报道及文艺通告等方式,展现涉及中西方的各类信息,其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
从《中国丛报》初期的序言介绍以及它所刊载文章的内容出发,我们将丛报的创刊动机及对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动机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19世纪初、中期,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已开始意识到,“在基督教国家与东亚国家的交流过程中,几乎还没有涉及精神(intellectual)或道德(moral)层面的文化产品;过去无人能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2](P1)由此而见,翻译人才的出现为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提供了可能,传教的使命成为《中国丛报》创刊的最大动机,也是它译介“经史子集”的主要目的。
第二,当时的西方人也意识到,“作为一种交流媒介,汉语无疑是地球上存在的语言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3](P1)。不过,地理空间的距离却增加了中西交流的障碍。就此而言,西方读者了解汉语的需要便成为《中国丛报》创刊的另一动机,译介“经史子集”也是为了向西方读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化产品”的“窗口”。
第三,从刊载的文章内容来看,《中国丛报》的一大特色是致力于对中国出版物的评价,十分关注这些书籍所发生的变化及其成因,并理清其真伪。序言中提到,中国一些古籍的内容是颇有价值的,也有一些却是乏善可陈;这种辨别可避免后者一再出版[2](P2—3)。
此外,是由当时闭关锁国的晚清政府给西方国家留下的神秘印象所激发的,诸如“整个国家都在沉睡当中,幻想着天朝的繁荣与伟大”以及“我们是西方世界唯一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国家”[3](P3—5)。因此,《中国丛报》的创刊既可以使中国读者了解中西关系的情况,同时也可以让西方读者了解其贸易国家的状况。
综上所述,《中国丛报》译介中国“经史子集”的动机并不单纯,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译者的传教任务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对中国经典的征引和译后的评述中,带有明显的基督教倾向与传教士视域。同时,其译介动机又是多元的、复杂的,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中国丛报》“经史子集”的译介内容
《中国丛报》的主要撰稿人包括裨治文、卫三畏、马礼逊(Robert Marrison,1782—1834)、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和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等。其作者群体除了传教士之外,还有外交官、商人、旅行家等人士,如:伦敦大学首任中文教授基德(Samuel Kidd,1799—1843)、中文韦氏拼音创始者韦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英国汉学家、第二任香港总督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外交官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等。
在1834年以前,《中国丛报》的体例设置比较固定,基本上是由以下栏目组成:(1)书评(Review),主要是对新旧出版物的学术评论;(2)节选出版物的内容,包括游记、日记的译介;(3)杂记(Miscellanies),主要是对相关知识的介绍与读者来信;(4)宗教信息(Religious Intelligence),报道各地传教士的传教活动;(5)文艺通告(Literary Notices),主要是有关文学和出版物的介绍;(6)时事报道(Journal of Occurences),报道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由此看出,《中国丛报》刊载的文章主题涵盖面较广,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法律、贸易、文学、教育、宗教、博物、语言等方方面面。这里,我们将聚焦于《中国丛报》对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层面,从这一角度来透视当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典籍译介的选择倾向。
“经史子集”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各个领域的著作。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这里,我们将文学的著作归在“集部”。根据上述分类原则,基于《中国丛报》的原文内容及《〈中国丛报〉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4],我们对《中国丛报》对“经史子集”的译介情况进行了整理,具体如表1所示(见下页):
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丛报》对“经史子集”的译介包括对著作的翻译、介绍与评述。其中,对中国“经部”的译介集中于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其译介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采用概述的方式,概括性地介绍和评述“经部”著作的核心内容与概貌;二是采用亦译亦评的方式,既有翻译,也有评论,如裨治文对《孝经》的译介;三是采用全译加按语的方式,如裨治文对《小学》的译介。
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史部”,体系庞杂,内容丰富,它包括正史类、编年类、地理类、职官类、史评类等。不过,《中国丛报》对“史部”的译介侧重于地理类,内容涉及中国海岸、舟山群岛、白河介绍、浙江地志、安徽地志、江西地志、直隶地志、山东地志、山西地志、福建地志、广东地志、香港地志、西藏地志、广西地志、贵州地志、云南地志、湖北地志、湖南地志、陕西地志、黑龙江地志、四川地志、河南地志、甘肃地志与广州、上海、厦门、福州等中国各省、府、县的概要,以及珠江、黄河等水系的概貌。限于篇幅,这些地方志的译介并没有在上述表格中全部列出。同时,《中国丛报》对“史部”的译介还涉及到“中国历史著作研究”“中国及其历史”,以及对唐、宋、明、清等朝代的历史与这些朝代部分皇帝的介绍,如对“三皇本纪”“中国女皇武则天”“洪武正传”等的译介。“史部”的译介方式多为摘译、简介或连载式介绍,也有一些内容是从其他语种转译的,如:《明太祖传记》即译自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的法文原作。

表1 《中国丛报》“经史子集”译介概览
《中国丛报》“子部”的译介领域广泛,涉及到宗教、哲学、农学、兵学、医学、艺术等多个门类。首先是聚焦于对中国宗教学说和信仰的译介,主要有中国人的宗教、中国的神学、佛教体系及《黄教教义问答》等。《中国丛报》“子部”的译介亦涉及一些中国哲人的言论,如对孔子、孟子、朱熹等人的学说的译介;同时,还涉足到农学、科学等领域,如:对《农政全书》、中文活字印刷术、中国经络图说的译介。艺术类的有“南京琉璃宝塔画”的译介,兵家类的有《士兵指南》的译介。
《中国丛报》对“集部”的译介涉及到三十多部中国古代作品,如:《押韵幼儿诗集》《二十四孝故事》《平南后传》《王娇鸾百年长恨》《春园采茶谣三十首》《搜神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涵盖了小说、诗歌、戏剧、神话等各类文学体裁。《中国丛报》中的“集部”故事大致可以分为历史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正德皇帝游江南》《南宋志传》等;神魔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聊斋志异》等;世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如《王娇鸾百年长恨》《红楼梦》等。译者有郭实腊、卫三畏、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1812—1863)、米怜(William Charles Milne,1815—1863)、帕维(Theodore Pavie,1811—1896)等。其译介内容主要是对这些作品的介绍和评述。译介方式大多是介绍和评论相结合,有时也采用摘译的方式,很少采用全译。其中,卫三畏采用全译的方式翻译了李亦清的《春园采茶谣三十首》,并有简要的介绍。《中国丛报》对“集部”的译介,使西方读者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主题、体制风格,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人文精神,同时还可以为中文学习者提供汉语入门教材。
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1897—1951)指出,“《中国丛报》是一份完全的世俗刊物,一反以前杂志的惯例,刊登大量的重印内容”[1](P52)。总的来看,《中国丛报》对中国经典译介的涵盖面较广,包罗万象,林林总总。它主要采用三种方式进行译介:“摘录并转译中国文献外译本的章节,征引中国典籍外译本的句子和段落,自行翻译中国文献”[5](P95)。可以看出,其译介方式多种多样,以简介和评述为主,有时也采用摘译、节译、全译、转译等方式。
三、《中国丛报》“经史子集”译介的缺憾
在《中华帝国的现状》(《中国丛报》第十二卷第一期)一文中,作者曾和盘托出了《中国丛报》译介的总体宗旨,就是让外国读者“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向海外报道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南京条约》前后的变化及其带给中国的影响”[6](P1)。可见,《中国丛报》一方面将刊物作为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媒介,另一方面,又为西方读者提供有关中国的知识与信息。总体上看,《中国丛报》在译介有关中国作品的过程中,“除少数者外,一般不像《广州纪事报》或《广州周报》上的文章那样采取激烈攻击甚至谩骂的方式讨论中国,而是以客观评述或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7](P325)。《中国丛报》力图以认真客观的态度来研究、评述中国的“经史子集”,描述一个完整的、立体的中国,以此吸引读者对中国的关注。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丛报撰稿人或者是由于认知能力、知识结构受限,或者是出于主观性的偏见,在译介和传播中国“经史子集”著作的过程中,他们很难全面正确把握这些知识体系的内涵,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经典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这里以中国儒家经典的译介为例,来具体考察《中国丛报》对孔子、孟子与朱熹等儒家学者和学说的译介情况。在《中国丛报》第十一卷第八期,刊载了《圣人孔子生平》一文。此文较为客观地描述了孔子的主要事迹与重要贡献,他在民间创办私人教育,为学徒、乡人传道授业,解疑答惑;他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恪守孝道,具有严于律己的品质;他刻苦钻研古书,总结出一系列用于约束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等。此文还将孔子比作苏格拉底等善于游走思辨的西方哲学家,褒奖其天赋与品行,并列举了孔子与其弟子互动交流的画面。最后,作者评论说:“孔子经常以一种受上天委命的口吻说话,似乎他是上天派来指导众生的”[8](P419)。客观地说,这一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失偏颇的。译介者之所以在评价孔子时如此表达,主要是考虑到将中国圣人的形象与西方耶稣救世主的形象拉近,从而达到传教目的的。由此可见,撰稿人根深蒂固的传教士思维及其行教、布教之宗旨。我们认为,《中国丛报》作为当时中西方交流主要的平台,发表诸如此类的评价无疑会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儒家思想及中国形象构建的误读。
在《中国丛报》第十五卷第七期,撰稿人译介了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仁”。由于当时西方传教士汉语知识架构的局限,对孔子所主张的“仁”学含义无法准确定位,而是先解释“仁”字作为“果核”等的意思[9](P329)。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方读者理解孔子思想的难度。此文接着对“仁”字进行阐述,引用了当时罗马东正教使者对“仁”的界定“博爱”,又引用了马礼逊对“仁”的定义“乐善好施”,并指出“乐善好施”是外在的、物质的,而“仁”和“人道主义”是内在的[9](P330)。随即列举多处包含“仁”的语句,来全面解释“仁”之含义。在提及人性(human nature)时,作者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性纯洁、否认原罪”,即“性本善”这一信条[9](P332)。这种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比附,无疑是牵强附会的。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天生是带有罪恶的,他们的罪恶来自祖先亚当和夏娃;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作者还评论说:“这一性本善的信条与我们的经验以及《圣经》的观点都背道而驰;我们现在的目的并不是要反抗该信条,但是我们有必要牢记这一观点对我们学习的影响”[9](P333)。就此而言,此文未能够充分地解释中西文化的哲学差异,其间的偏误仍是出于其译介的根本动机与总体宗旨。
在《中国丛报》第十五卷第八期,撰稿人译介了《孔学小册子》中的一些言论。其中,在论及人心的演变时评论道:“人有正骨,胜过苦读万卷书,会等得到上帝的庇佑,得以绵延子嗣”[10](P380)。这段论述在强调人们需要心怀善意、不可起邪念的同时,又借助“上帝”的名义来褒奖正直的重要性。显然,这又是将中国的儒学与西方的上帝相比拟,在一定程度上就模糊了二者的界限。
在《中国丛报》第十卷第四期,刊载了《孟子及其门徒著作中常用字的解释》。此文对《孟子》一书中的常用字的解释较为恰当,并引用了《孟子》中的很多例证予以证明,治学态度可谓十分严谨,也适合于当时西方学习者对汉字及儒家思想的理解。不过,在解释常用字“以”的意思时,文中引用了《孟子》中的一句话“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作者将其译为:“不吃母亲带来的食物,却吃妻子带来的食物”[11](P230)。《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这里是孟子用以评价陈仲子的,批评他不能算作“廉士”,因为他的所做作为已走上极端。我们认为,译介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应标注清楚孟子的态度与立场,以免引起读者对其所传达价值观的误解。
《中国丛报》对宋代理学大师朱熹颇为关注,对他的译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36年到1838年,主要以传播朱子的教育教学观念为主,具体表现在对《小学》的译介上;第二个阶段是从1844年到1849年,这一阶段主要以传播朱熹的理学思想为主[12](P68)。《小学》是在理学观念指导下,由朱熹编纂的一部启蒙教材,用于教导蒙童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尊敬长辈,如何待人处事,如何应对进退。通过《小学》的译介,西方读者可以获得关于朱子学的基本教育观、教学观。《中国丛报》在第五卷第七期、第六卷第四期、第六卷第八期、第六卷第十二期,曾对《小学》的英文译介予以连载。译介的方式是翻译为主,简短评论为辅。如在提及父子纲常时,译介者在译文末尾评论到:“我们质疑,在这堕落的时代(degenerate times),古代圣人所反复强调的这些个人行为规范,是否能不被人们忽略。”[13](P307)这里,译者将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定位为“堕落的时代”,同时对儒家纲常的生命力提出强烈质疑,其中所包含的意味耐人寻思。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是存在缺陷的,主要是缺乏“对上帝的敬畏”[13](P87)。与此可以相互参照的是,在《孝经》的译文结尾,撰稿人也同样指出,希望能从这些典籍中寻找到中国众生的风俗习惯、行为方式、道德标准和宗教信仰的源头,而且应从影响中国人最深远的典籍中的“上帝”“天”等词汇中探寻基督教的痕迹[14](P353)。由此可见,他们对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是与其传教士的身份、视野与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仍然是以传播西方宗教为旨归的。
以上主要是论述了《中国丛报》在译介中国儒家经典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其实,在译介其他中国典籍时也存在着类似的误读、错译现象。这些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可能是由于撰稿人的认知能力、知识架构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也有可能是由于作者一以贯之的成见、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关于《中国丛报》“经史子集”译介所出现的误读、错译、漏译现象,我们将会专门撰文另行讨论,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总的来看,《中国丛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再现了传教士所理解的中国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形象画面,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信息来源,也影响着西方读者对中国形象的构建。《中国丛报》在译介和传播中国“经史子集”中充当着重要媒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经史子集”在西方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载体。尽管《中国丛报》在译介中国“经史子集”的过程中亦存在误读、误译等现象,但它折射出编者、作者对中国经典译介与解读的特定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促进了中国经典在海外的传播,值得汉学界和翻译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