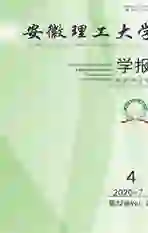从历史意识谈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
2020-05-08韩苏桐
摘 要: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以历史意识规定效果历史,同时他又以效果历史原则中的视域融合阐述历史意识的变化与生成。二者的相互规定反映了理解者从自身主观性出发认识历史对象的过程,彰显了历史意识的有限超越性,揭示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然而,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存在着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它尊重理解者的数量和前见在形式上的特殊的“普遍性”而缺乏对具体历史阶段下个人历史意识内容的普遍联系的深刻洞察;二是放大了个人意识的作用却忽视了意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我们需反思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既要认清它在文本诠释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要明晰效果历史和社会历史的区别。
关键词:伽达默尔;历史意识;效果历史
中图分类号: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20)04-0001-06
收稿日期:2019-12-27
作者简介:韩苏桐(1995-),男,江苏淮安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现代西方哲学。
Abstract: In Truth and Method, Gadamer stipulates effective history with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t the same time, he explains the change and 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 the fusion of horizons in the principle of effective history. The mutual stipulation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 objects from their own subjectivity, highlights the limited transcendence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nd reveals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human spiritual activities. However, Gadamers theory of effective history has two limitations in the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first, it respects the number of understanders and the special “universality” of antecedents in the form, but lacks a deep insight into the universal connection of individu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s; second, it magnifies the role of personal consciousness but ignor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reflect on Gadamers theory of effective history, not only to recognize its important role in text interpretation, but also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ffective history and social history.
Key words: Gadamer;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Effective history
上個世纪八十年代,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传入我国,国内掀起了诠释学热。部分学者利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在历史研究、文学研究以及艺术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部分研究成果也引起了混乱,尤其是涉及到历史意识与效果历史、效果历史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伽达默尔所提倡的理解活动是否放大了历史意识的作用?效果历史等同于社会历史吗?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进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
一、 历史意识、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是在批判历史主义学派和狄尔泰诠释学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效果历史,它指的是理解者的历史意识总与历史发生着效果关系。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以历史意识规定效果历史,同时,他又以效果历史原则的视域融合方式规定历史意识的变化和生成。
首先,伽达默尔在诠释学领域内重新规定了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并以历史意识规定效果历史。关于历史意识,伽达默尔认为:“它从它自己的历史去理解自身。历史意识就是某种自我认识方式。”[1]305在伽达默尔看来,历史意识不是像兰克那般后知后觉且独断地把握有意义的经验事实而寓之以世界历史目的的意识,也不是像德罗伊森那样对历史对象进行无限的“研究性地理解”而始终与该对象保持着距离的意识,更不是如狄尔泰那般按照历史对象所属时代的标准理解该对象的意识,真正的历史意识,就是理解者自身的意识以及与其所属的历史阶段发生效果关系的意识。从这历史意识出发,理解者对历史对象的理解总是按照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和理解者所属的时代的标准而不是按照历史对象所属的时代的标准,历史对象也不再只停留在某个历史节点,而是与理解者一同进入了当代,在当代获得了新的存在。因而,“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理解的实在性。”[1]387这种“历史理解的实在性”就由历史意识规定。应当看到,理解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历史意识:一是理解者的历史意识,二是历史对象的历史意识。理解者由于难以逾越时空的界限,所以“理解对象就不是某种客观意义上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意识中被构建起来、并被我们意识到的东西”[2],即理解者对历史对象的认识包括对历史对象的意识的认识其实是理解者的历史意识的分裂且以他们的当代的历史意识为主导的认识似乎有“历史对象甚至是历史对象的视域都是理解者的意识的构建”的倾向,但是,这并不是否定历史对象的真实存在,而是指它被无数人理解,成为了历史理解的实在而不是指其历史对象本身的实在,即历史对象包括其本身的实在与理解者对它的理解所构成的实在。。
在两种历史意识的交融中,理解者与历史对象不仅拥有其本来的实在,还获得了时空的存在即历史理解的实在。但是,历史理解的实在不同于历史对象本身的实在,历史理解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是已经被一定历史阶段所制约的历史理解力的有限张扬,它是从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出发使历史对象中还没有被认识到、从未被考虑到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的东西的存在”[1]388,“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387从这一点讲,历史理解所构成的历史乃是理解者与历史对象“双方”的历史意识的相互作用,历史对象的实在和历史理解的实在构成了历史对象的整个历史。在这一层面上,历史就以意识与历史发生关系的效果历史的方式发展着。
其次,伽达默尔以视域融合阐述历史意识的变化和生成。如果说历史意识是使历史对象进入当代并使得理解者与历史发生效果关系,那么视域融合就是在此基础上具体地回答了效果历史的原则和内容即阐述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如何变化、生成以及历史对象以何方式在各个时代获得新的实在。关于视域融合,伽达默尔指出:“当我们的历史意识置身于各种历史视域中,这并不意味着走进了一个与我们自身世界毫无关系的异己世界,而是说这些视域共同地形成了一个自內而运动的大视域,这个大视域超出现在的界限而包容着我们自我意识的历史深度。”[1]394在理解活动开始之前,各自视域中由于已经包括了从某一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事物和事件,所以视域的融合就不是放弃理解者的个性的自身置入,而是以理解者自身的视域为主导,实现理解者与历史对象的视域的融合。在融合过程中,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对象的历史意识发生了相互作用,它使得理解者的历史意识不再是原先的意识,也不再停留在原先的层面上,而是在融合了历史对象的意识之后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尤其是随着理解者年龄的不断增长,它上升到了更高的普遍性的层面上。
但是,两种历史意识的融合过程除了提升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外,它也以创生新的当代意义的方式使得历史对象获得新的实在。伽达默尔写道:“当某个本文对解释者产生兴趣时,该本文的真实意义并不依赖于作者及其最初的读者所表现出的偶然性。至少这种意义不是完全从这里得到的。因为这种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1]383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就是理解者所处的时代的总和。每一时代的理解者按照自身的历史处境或其所属的时代意识理解历史对象,他们所理解到的意义同时使历史对象在各个时代以新意义的方式存在。这样,从历史意识出发的理解就不再是独断论的,也不再是后知后觉的,更不是与历史对象隔着距离的。同样,分隔开理解者与历史对象的时间间距也不再成为理解的阻碍,相反,时间间距成为了意义的生长域。从这一点讲,意义的创生乃是不同历史时代发生效果关系循环的一个环节。新意义的产生,不仅使理解者和历史对象在理解中获得在世存在的意义,同时它也作为一种新的意识附属于理解者和历史对象并参与进之后的视域融合的过程中。
二、效果历史体现历史意识的特征
历史意识与效果历史的相互规定,无疑使理解活动具备了一系列的特点和品质,这些特点和品质通过效果历史体现出来。
其一,效果历史反映了理解者从自身历史意识出发进行主观性认识的过程。关于理解者主观性的来源问题,伽达默尔明确写道:“哲学诠释学的任务可能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具有这样的特征:它必须返回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道路,直至我们在一切主观性中揭示出那规定着它们的实体性。”[1]390这个“实体”就是先于一切自我认识的历史地存在着的东西,也就是前见所身处的传统和历史。[3]59伽达默尔虽然以传统和历史规定主观性,但他不是使理解者被动地接受流淌过他们的历史对象,而是以立足于传统和历史的前见规定理解者自我理解的合法性。当历史对象经过理解者的历史意识时,理解者从自身前见和处境出发构建并认识历史对象就具有了历史的权威性和正当性。这样的过程的确消解了历史对象与理解者的时间间距,使他们同时获得一种当世存在的意义,但也不可否认,此过程表明了理解者的主观性认识。彭启福教授同样赞同此观点,他写道:“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不再偏执于诠释的客观方面,而是充分肯定诠释的主观方面在诠释过程中的重要性”[4],潘德荣教授也指出:“现代读者在观照历史流传物时,乃是基于自己的现代自我意识来理解历史上的他者所诉说的东西。”[5]事实上,在效果历史理论中,理解者的主观性既来源于传统,又为现代意识不断改变并对其所处的历史阶段产生效果,视域的融合也总是以理解者的自我意识为主导。自我意识参与进理解活动中即是对历史对象进行甄别,以弄清何种历史对象能满足自身需要,进而以理解者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对象,并使历史对象的存在意义呈现出与此时代相符甚至是超越此时代的特质。
这样的主观能动的理解不仅彰显了理解者立足于传统的自我理解,而且它同时表现了一种因现实需要而进行的现实思维的自我塑造并使自我塑造融入进自我理解中。伽达默尔也写道:“甚至最真实最坚固的传统也并不因为以前存在的东西的惰性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自身,而是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1]363传统一旦能被培养,就说明了传统的可塑造性。那么自过去流淌至现在而奔向未来的传统就并非一成不变,它永远与各个时代的当下构成一种交织,成为了一种“流动的传统”,并且使得各个时代的现实思维沿着前见向传统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如此,理解者不仅获得一种立足于传统的历史的存在,更获得了一种满足当下并且要走向未来的当世的存在,二者一起构成了人的在世存在。在这种在世存在中,人既拥有了自我理解的合法性,他也能够从自我理解出发为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发起抗争。这样的“抗争”乃是展示了富有理解者主体性特征的多种理解方式和所创生的多样文本意义的统一。从这两方面铺展开来的理解就凸显了理解的多元化,也反映了理解者的主观意识作用于历史对象的效果历史的过程。
其二,效果历史展现了理解者历史意识的有限的超越性。在效果历史理论中,理解者的历史意识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它既为一定的历史阶段所限制,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超越性。伽达默尔指出:“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所谓历史地存在,就是说,永远不能进行自我认识。”[1]390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的历史意识和视域先在地拥有了立足点,它们总为此立足点和一定历史阶段所限制,不能真正认清其自身的本性,也不能就此时代和历史中的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乔治娅·沃恩克也赞同这一点,她写道:“历史永不能对某历史意识表现一个整体,因此这种意识将永远是受限制的”[6]25,孙丽君也指出:“我们总是身处于这种传统之中,从而我们处身于其中的传统和历史本身永远不能成为一种反思的对象,只能是我们的存在前提。”[3]59然而,这正是表现了历史意识的潜在的无限性。在伽达默尔看来,一项理解活动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总是立足于客观事实。[1]389为了某种理解的需要,理解者总要求历史意识必须超越其所属的时代以及所要理解的历史对象本身,以达到他认为的对此时代和历史对象的全面的客观的把握。因而,历史意识总是以自己的方式——不同于产生现有的理解内容的方式——认识历史对象。这样,历史意识不需要顾及自身是否“澄明”,也不需要顾及理解的对象是否合乎其本身,它只需要满足理解者的要求,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历史对象,以达到对“现有的理解”的超越。
但是,这种超越终究是有限的,历史意识不会无限的张扬而穷尽历史对象的全部,它总要为理解者的前见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只有这样,时间间距才能真正发挥它在诠释学中的“中间地带”的作用,过滤、筛选和完善不同历史节点中关于历史对象的理解,并以这些理解作为前见或传统应用于之后的理解活动,形成理解的循环。
其三,效果历史揭示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使理解者在理解中获得在世存在的方式。伽达默尔提倡每个理解者都可以从自身的前见和处境出发对对象作出理解。这样的理解即是作为理解者的意识与历史发生的效果而存在,它并不固定在某一时间点,确切地说,时间间距中的每一个节点,理解者的意识与历史发生的效果构成并丰富了“效果的历史”或人类精神活动的历史。由于“人类所从事的任何社会活动都是出于对人自身的需要的关注和实现”[7],理解作为附属于人的活动,它也是如此,因而这种效果就是根据与人的前见和处境相契合的现实需要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应当看到,“不同的读者往往处于不同的诠释学情境之中,面临不同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必须与这些读者面临的不同现实高度关联”[8],帕尔默也指出:“没有一种诠释与现在无关,而且它從来不是永恒的和稳固不变的。”[9]240这也就是说,理解者在理解对象之初,就已经怀有一种或几种现实的需要,这些需要是理解的先手,理解者通过对对象的理解使自己的需要得以合理存在并得到满足,继而使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得到合理性承认。理解者的某些需要更是彰显了理解者在此现实社会中的精神活动,扩大了一定时空下的人们的精神活动空间,更进一步地讲,没有现实的需要就没有关于对象的理解,没有关于对象的理解就没有具体的精神活动,没有具体的精神活动就无法彰显理解者的在世存在。
如此,在时间间距中,“历史对象”的存在与如何存在、历史对象的当世意义的创生都是由各时期各阶段的作者和理解者根据现实的需要所进行的精神活动。这样的精神活动不仅使理解的世界得以发展、丰富,也使得理解者自身在理解中获得了在世存在的意义。历史也就在这一层面以效果历史的方式发展着。因此,根据现实需要所进行的意识对历史的活动构成了一定历史阶段下人类的精神活动,使理解者在理解中获得在世存在的方式,效果历史也由此揭示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
三、 效果历史理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不足
从哲学诠释学层面看,效果历史理论是以理解者主观性为标准认识历史对象,凸显了历史意识的有限的超越性,使以满足现实需要为目的的理解在时间中呈现出来,促进了理解的多元化,彰显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发展演变规律。然而,伽达默尔所阐述的历史意识终究是从诠释学循环开始而上升为诠释学原则的意识[10],因而,他的效果历史理论只能停留在诠释学的层面,缺乏对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其一,效果历史只是揭示了理解者的数量和前见在形式上的特殊的“普遍性”,缺乏对具体历史阶段下个人意识内容的普遍联系的深刻洞察,呈现出形式与内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如果说伽达默尔对兰克的批判——“实际上兰克以此所意指的东西,根本不是这种连续性的结构本身,而是在这种连续性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具体内容的关系”[1]270——阐明了兰克只是认知到历史的内容的连续性,那么,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则更专注于历史的结构和形式上的连续和统一。伽达默尔看到了时间中的“理解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指的是不分等级的理解者及其前见。每一位理解者都可以从自身的前见和处境出发进行理解活动,没有谁的理解更有优越性,所有人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虽说伽达默尔的目的是解决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问题,但是,他以个人理解作为抗争的手段又趋向于保守。追随伽达默尔的脚步,人们只会在心中拿起武器作“臆想的抗争”而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获得自我超越。这样的理解活动就是凸显了理解者的数量和前见的形式化和普遍性。乌多·蒂茨也表现了同样的看法,他写道“伽达默尔用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效果历史原则讲述了‘理解的普遍结构要素,他想通过这一点让人注意到,诠释学意识与一定的前提紧密相连。”[11]96虽说在各个社会历史阶段下,人们的理解总是先在的受到某些传统或思想的影响,但是,人们也在支持和拥护各自所认同的共识或思想,因而,人们不可能真正实现从前见而来的主体的自由化和普遍化理解。
那么,由某个人或某些人提出的共识或思想何以能在人们原有的理解之上获得人们的理解、支持并在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因为它契合了人们的经历,迎合了现下的需要,展现了一副“光明”的前景,具有一种社会的普遍性,并且由于这些共识或思想面对的阶层的不同,它们所得到的拥护程度以及所展现的前景的侧重面各有不同,即这些思想“不是从人们的意识出发解释人们的存在,而是从人们的存在出发解释人们的意识。”[12]这也就是说,它们表达了各个社会历史阶段下某些人对未来生活的期望,是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需求的具体内容的总结和提炼,同时,它们也将人的意识和人的需要串联起来,从而以此为着力点真正构建起那个时代的全部或部分精神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从这一点看,对各个历史时期产生效果的无疑首先是反映理解者的当下意识和具体的需要的共识或思想,而不是各个理解者的主观意识。只有当理解者的意识拥护所认同的共识或思想,意识才能意识到它对此时代和历史产生的作用。但是,此时的作用还处于“未发出”的阶段,它仍然停留在意识的层面,还没有作用在具体的处境中。因此,意识对历史的效果首先在于拥护某种共识或思想之后的个人意识的普遍联系,而不是理解者的数量和前见的形式化和普遍性。
其二,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的描述放大了个人历史意识的作用,忽视了意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这一点在他对历史意识和视域融合的阐述中清晰可见。王成军教授指出:“视域融合较之于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而言,强化了现代哲学所具有的古今二者之间的联系,表现了明显的历史性。但由于缺乏真实的历史实践性和彻底的辩证精神,仍无法正确理解时间与空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了用同一代替统一、用时间代替空间、用理论代替具体历史进程的倾向。”[13]杨生平教授也写道:“他只知道人们要在不断理解中筹划意义世界,可究竟如何筹划,筹划有怎样的具体特征等,在他那里是语焉不祥的。”[14]从个人意识出发的理解的确彰显了个人独特的历史性,构成了此社会空间中的精神活动,但个人意识却“是根植于实践基础的社会历史本性的‘现实整体性—‘整体现实性。”[15]应当看到,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总是由在此阶段生活的人的纵向的实践活动和横向的实践活动的交互作用构成,同时它又反作用于此阶段的人们的意识并以意识指导之后的实践。因而,在同一社会历史阶段的制约和影响下,人们的前见和处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解活动是由现实的社会实践规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总以相同的方式——不只是意识,而是把意识与实践统一于现实生活的方式——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并且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后人的意识先在地包括了之前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实践。但是又为了突破一定的社会历史处境的限制,人们的意识和实践呈现出一种超越性。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无疑是“实践——意识——实践”的螺旋上升的普遍作用,其中就包括了所有主体的具体的意识与意识、意识与实践以及实践与实践的普遍联系。
如此,当人们进行理解活动时,理解对象就不是一种单纯的意识的存在物,而是在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意识与实践的统一体,同样,人们的理解也不再是单纯的意识的东西,它既是对意识与实践的统一的反映,同时,它又必然导致之后的基于此理解的行為,也就是说,人是即理解即改变的社会存在。伽达默尔看到了理解者的有限的超越性,却忽视了与个人意识相统一的实践,使得效果历史理论夸大了个人意识在历史中的作用、丢失了对历史发展的科学性认知,更进一步地讲,效果历史呈现出代替社会历史的倾向。
依照上述,效果历史理论凸显了历史意识的不可规避性以及历史意识在诠释学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效果历史也由于过度发挥历史意识而走向了以效果历史代替社会历史的道路。这也就告诉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只能适用于诠释学层面,我们不能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历史观,更不能以效果历史代替社会历史,否则,效果历史理论就会引起人们认知的混乱和社会历史理论的模糊,进而导致社会实践的失序。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正确地认识历史意识,明晰历史意识与不同历史阶段的关系,以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潘德荣.理解方法论视野中的读者与文本——伽达默尔与方法论诠释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8(2):42-53.
[3]孙丽君.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美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4]彭启福.现代西方诠释学与科学哲学走向之比较[J].天津社会科学,2002(4):33-37.
[5]潘德荣.论当代诠释学的任务[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5):16-22.
[6]乔治娅·沃恩克.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温皓.论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性[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8]彭启福.“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J].学术月刊,2007(8):51-56.
[9]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M].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0]何卫平.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08(2):31-39.
[11]乌多·蒂茨.伽达默尔[M].朱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林剑.论马克思历史观视野中的“历史”生成论诠释及其价值[J].哲学研究,2009(10):16-21.
[13]王成军.同与异的对立与统一——论视域融合与历史比较的关联与融通[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91-99.
[14]杨生平,李鹏.试论伽达默尔效果历史理论[J].世界哲学,2018(3):104-111.
[15]蔡成效.论实践基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及其统一[J].江汉论坛,2005(2):46-49.
[责任编辑:范 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