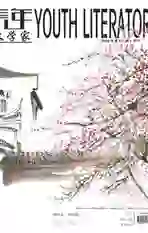浅析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怆虑情结
2020-05-06王小东
王小东
摘 要:本文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怆虑情结为研究对象,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对文本予以论述。首先是对“怆虑情结”作以界定;其次介绍了王国维怆虑情结的来源;三是《人间词话》中怆虑情结的体现;最后,综述。文章认为,王国维在创作人间词话的过程中带有深深的怆虑情结,这种怆虑情结是王国维与生俱来的带有悲观气质的生命之思。
关键词:人间词话;怆虑情结;终极关怀;境界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09-0-02
研究现状:1908年至1909年《国粹学报》刊登王国维手定《人间词话》六十四则以来,已逾一百一十六年。其间共发表研究《人间词话》的论文三百六十余篇。这些文章大多是对“境界”理论的考证和探究,以及对其手稿的校订、校注、编排等等的研究。自80十年代以来对《人间词话》研究比较著名的有叶嘉莹、佛雏、陈鸿翔等海内外学者,同时也包括笔者所参考的《人间词话》编者周锡山先生。然而这些大家都各执己见,对《人间词话》的创作目的,美学思想以及“境界”说的实在意义依然存在争议。
研究意义:本文力求避开这些争议,同时立足于周锡山编校的《人间词话》文本,对其怆虑情结和文本进行探源和简单的分类,并从中归纳出王国维在创作人间词话的过程中带有深深的怆虑情结的结论。
一、对怆虑情结的界定
“怆虑”即“悲思”,但非“悲痛思念”之意,而是“悲怆忧虑”的意思。一种建立在悲观气质之上的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和对万物的审美观照。情结指情感的郁結点,是伴随作者创作始终的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因此,怆虑情结就是带有悲观气质的强烈无意识冲动的生命之思。
二、王国维怆虑情结的来源
我认为探讨王国维怆虑情结的来源有助于我们知人论世,能更好地从他的生平去解读他的作品。这些来源主要有:
首先来源于家国的不幸和王自身身体的原因。王国维出生于1877年,逝于1927年。在他出生的第四年1880年,生母凌氏的溘然离世。对于年仅四岁的王国维是个不小的打击。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就认为:
“王国维的性格中具有忧郁悲观的天性。”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是年王国维18岁,因为时局动荡,王对科举考试心灰意冷,遂走出家门,另觅出路。1906年,王负笈北上,不幸其父王乃誉病故,是年王国维30岁。不到一年,其妻莫夫人产后病故,所生双女亦夭折。他在人间词乙稿的《蝶恋花》中写下“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的词句,,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悲痛。
1901年,王国维25岁,在罗振玉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但因身体原因不得不于同年回国治疗。他在《三十自序》中说到:
“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前。”
如果说一个四岁的孩子对于生死这样的意识还很单薄,那么已是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对于生命的思考就更加丰满了,而况现在身上又添了病疾。他说“性复忧郁”证明这种“忧郁”是曾伴他左右的,只是在某个时段淡薄了,而当他身体出现状况时,他考虑到“人生也有涯”,生老病死的问题就再也无法回避。既然无法回避,就只能求得超脱,所以他开始转向哲学,以求安慰。
哲学的探求是其怆虑情结来源的第二个途径。王国维从1904年郑重开始学习和吸收叔本华的思想,并深受其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这表现在他后来用这些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文学。本来是求得解脱的,没想到这种方式非但没有使他解脱,反而对人生的思考愈加严重了。他曾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恼。”
由此可见,王国维在哲学的探求中走入了精神的困境,他更多倾向于生命哲学意义的追问,用悲剧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但思之愈深,痛之愈甚。而在此前王国维自学了经学,深受老庄和周易的影响,顾易生先生曾就《人间词话》取名“人间”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取于《庄子》之《人间世》,而自明其写作旨趣也”。至此,王国维大致学习了中西方的哲学思想,但都没有得到解脱。
哲学的救赎行不通,遂转为文学的研究,以求“安慰”,于是有了这部《人间词话》,这是怆虑情结的第三个来源。王氏在创作《人间词话》时,十分推崇具有“大气象”“大堂庑”意象的诗句,这是因为宋词中显有的生命意识和终极关怀让他终身追随。我认为,王国维一生辗转于哲学艺术和考古学之间,都在奔着一个无意识的冲动,那就是解释世界以求得解脱。于是他既乐歆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又醉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宋词和元曲。但他一生追随却终没有解脱,他知道如何才可以得到安定,但是他始终做不到。他用悲观主义以毒攻毒,来麻醉自己;他乐于宋词中的“狂狷”“旷达”“超脱”,极力强调“真”,强调存在的意义。
三、《人间词话》中怆虑情结的体现
1.对《人间词话》的分类
有人曾把《人间词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则到第九则,认为这部分主要论述境界理论。第二部分包括第十则到第五十二则,是对于具体词的品评。第三部分,从五十三则到六十四则,共十二则词话,认为这部分是论述词的境界理论的发展。本文分类与其不同,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将其分为五个小部分,每一小部分不是完全独立的,可能会有重叠的部分。分别是:①以“境界说”的最高标准“真”来分;②以气象、词品和人格为主;③以不同词人作品之间的对比分;④以对生命的思考来分;⑤境界理论及其他。
隶属于第一部分的有:七、十六、十七、二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四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二
隶属于第二部分的有:八、十、十五、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一
隶属于第三部分的有: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五、三十六、四十六、四十九
隶属于第四部分的有:三、四、五、六、十二、十三、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七、五十五、六十、六十一、六十三、六十四
隶属于第五部分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二十七、三十七。
第一组分类共有18则,这里王国维对“真”做了集中的论述,并把这一标准视为最高标准。王国维极力推崇“真”的标准,对李煜的“赤子之心”大加贊赏,认为其为“词人之所长处”。而对使事用典不当予以批评,反对吴伟业的堆砌典故。
其中第七则和二十一则提到了炼字。这是基于“真”实的基础之上,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才可道外人不可道之语。正如其在《宋元戏曲考》所说“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这都体现出王氏求真的学术态度,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他肯定存在,反对虚无造作的人生态度。
第二组分类中共有12则,其中第十、十五、三十、三十一则直接提到了“气象”。第十九则有类于“气象”之词“堂庑”,第三十二、四十二、四十三都提到了“格”,或“品格”或“格调”或“格而无情”。第四十四、四十六同时提到苏东坡和辛弃疾,并以“狂”“旷达”之词形容。其余皆是对表现“气象”“堂庑”和“格”的诗词的称赏,大都体现了王氏对于“气象”的推举,对豪放的肯定和对词品人格的重视。王国维之所以称赏“气象”的原因是这些诗词无一例外地展现了时空的广大无限和人生的短暂无奈之间的矛盾,体现着王国维自身的悲观情绪和忧患意识。
第三组分类中凡13则。王国维习惯拿出色词人的作品相互比对,得出一个更高水平的作品来说明自己的审美态度。例如“和泪试严妆”是一种强颜欢笑的状态,“菡萏”句则是一种悲哀的意象,与其他词句相互比较,后者尤高。在这里他看出了“众芳污秽”“美人迟暮”之感比“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的苦闷更高一筹,很显然是悲观主义视角占了上风。同时在第十五则选取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这样感慨生命之境有限,而宇宙无限的带有怆虑情结意象。
第四组分类中凡23则。是这五类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组,占了整个文本的三分之一多。有对生命超脱的理解,例如第四则: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这种无我之境正是一种超脱尘世,绝然独立的状态,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因此他说:“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他欣赏陶渊明的这种勘破红尘的超脱。也有对生命价值的追索,“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等,集中体现了作者选词的这一倾向。
最后一组分类中凡11则。这一部分是对前四部分的补充,怆虑情结的体现不是十分明显,所以不多作论述。
2.《人间词话》题目引发的思考
《人间词话》的题目耐人寻味,李庆的《<人间词话>的“人间考”》认为“人间”是王国维的别号似乎不无道理。顾易生在《<人间词话>手稿影印本——序》中把“人间”与作者的写作旨趣结合起来我表示十分赞成。此外,谈一个有趣的现象,王国维最终手定的《人间词话》只有64稿,而64在中国古代是和《易经》“八八六十四卦”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对于数字是相当敏感的,在古代哲学思想的视阈里数字代表着具体的文化含义,例如“五”在“五行”中代表“金木水火土”,也可以代表不同的方位。再如数字“九”,是奇数中最大的数,所以代表了一种“高贵、至尊”的含义,尤其颇受帝王喜爱,有词曰:“九五之尊”之所谓也。笔者认为王国维把《人间词话》删为六十四则而不是六十六则或六十五则是有其特定用意的。我把它假想为其哲学思想的外化,即对宇宙的敬畏和对人自身的审美观照。郑志明《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一文中说:“六十四卦是八卦的重卦,其宇宙论主要还是延续着八卦的气化交感原理。”这表明“《易经》六十四卦”“卦卦相偶”的对立宇宙论,不但穷究天地万物的起源及其演变的过程,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人为中心的生命关怀。
四、综述
《人间词话》充分体现了王国维对于生命的重视和对存在的肯定,对于无病呻吟的蔑视。这是他的学术态度也是人生态度。因为家国的不幸使他染上了悲观的气质,在学习西方悲观主义哲学后,他把这种悲观上升到了哲学的思考。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究,使得文学与哲学思考碰撞出了火花,外化在《人间词话》上,体现了他深深的怆虑情结。这种情结并不孤独,因为千百年伟大的人类都在做一次生命的追逐。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著,周锡山编校.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
[2]李艳丰.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生命之思.船山学刊.2009(1).
[3]黄伟.人间词话百年研究述评.短篇小说.2013.
[4]郑志明.《易经》六十四卦的生死关怀.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2(1).
[5]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6]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