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明传奇《琴心记》的性别空间想象
2020-05-06苏妹
苏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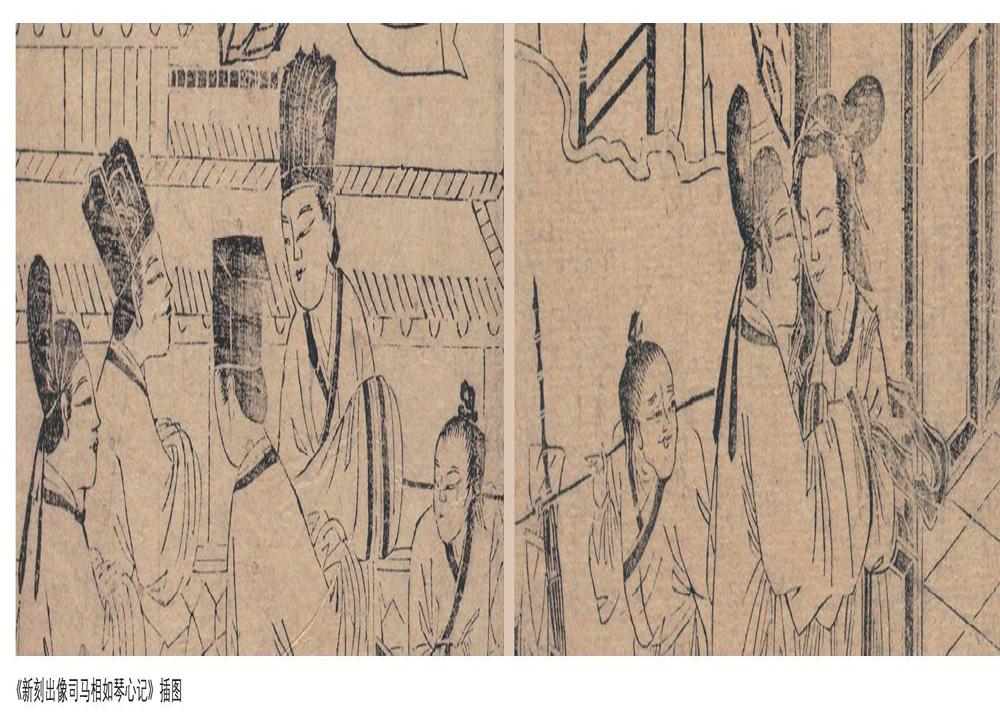
【摘要】 明万历年间戏曲家孙柚创作的传奇《琴心记》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其中出现了古典戏曲中的常见场所,如亭苑、花园、院墙、寺庙,它们已超越单纯的自然环境或物理空间意义,被剧作家注入重要的文化所指。本文将着眼于几个典型场所,探讨文人孙柚在晚明特有的文化语境下如何对汉人相如文君的故事进行新时期的空间想象与表达:卓府的后花园是相如与文君爱情萌生的起点,也是文君反叛父权家庭、走向主体觉醒的场所;京城的茂陵园是相如与文君幸福团圆的归处,也是相如男性才华魅力和志趣抱负再次得到施展的场所;峨眉山小巫山庙披着宗教禁欲的外衣,承载着收留文君、协助她延续俗世情缘的功能,在无意识层面流露出对清规戒律、封建礼教的逸出与背离。这些空间书写充满了性别意义,尽管有意或无意张扬了男性之性别优越,导致叙事陷入了男尊女卑的固有窠臼,但其闪烁的进步人文色彩仍值得肯定。
【关键词】 《琴心记》;性别;空间
明万历年间戏曲家孙柚所著的《琴心记》是其现存唯一传奇,取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所记载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在晚明特有的文化语境下对这一经典IP进行了移植与变异。
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的著作《空间的诗学》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握空间的诗学意义:“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1]23空间不再是停留于物理学或建筑学的概念,它被人为地填充了意义,是人类意识的居所。《琴心记》中出现了中国古典戏曲爱情故事常见的典型场所,如花园、院墙、桥、亭等,这些物理空间符号除了本身的自然环境属性以外,还为浪漫情爱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场所,内里承载着剧作家的丰富所指。本文将从西园、茂陵园、山庙等几个重要的故事场所出发,加以性别视角观照,探讨在弥漫着个性解放思潮的晚明社会文化语境下,文人孙柚如何对汉人相如与文君的故事进行另类的空间想象与表达。
一、禁忌与游戏:女性之主体觉醒
在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待字闺中的封建女子家庭地位较低,即便在自家仍有许多不敢轻易涉足的场所。厅堂、花园等具有社交性质的公共空间,她们需要侍女的陪伴才能进入,无形中受到封建家长制强大的监视与规训。但这些空间的神秘性、未知性又具有向她们敞开的潜在属性,引诱她们小心翼翼地介入与窥视,并唤起她们被压抑的自然本性。
在第三出“文君新寡”中,卓府女婢山茶和玉兰在后花园打扫残枝落叶,从碧梧亭到丁香亭,照例完成每日工作。由湖山花木构成的后花园景色明媚,花鸟树木等自然景物所涌动的生命气息恰好与人的生命原欲相契合,正值芳华的女婢难免“春兴发作”“花心也动”。接下来出场的文君小姐,芳年十七,未字而寡,显现“玉减香消,花慵月懒”的楚楚可怜模样。侍女孤红调侃小姐“芳姿绝世,妙韵可人,当有名贤为配”,文君立马以长时期被家庭灌输的儒家传统伦理婚姻观反驳:“忠臣不易主,烈女不更夫。”孤红比文君稍微年长,在某种程度上担任文君性意识的启蒙者和引导者,认为花样年华的女性不能囿于礼教就此守寡一生。性意识仍比较闭塞的文君拒绝了孤红的好意劝说,并因身子不快的缘由拒绝了女婢们对老相公邀请文君西园赏桂的转达,但孤红一句“娇体虽可惜,父命不可违”的正当理由迫使文君“勉强走一遭”。由此可观,占主导地位的父权制、家长制无形而又巨大的威慑力,时刻对女性强化恐惧情绪。
中国古代园林有着悠久的历史,封建帝王的宫廷或士大夫的宅院都会修建园林,以满足生活、心理或審美的更高需要。“园林建筑兼顾居住、议事、宴请、游憩,总的来说是‘独乐园,私家园林求小巧玲珑,皇家园林则宏伟宽敞。”[2]191在古典戏曲中,基于现实社会而造的园林同样具备这些功能。卓王孙在家宴请司马相如,但不容家中女眷出席。此类宴会交际成了男性内部社交对话的公共场域,封建女子为该空间所排斥,处于被剥夺话语权的失语状态。她们若想介入这个仅对男性开放的空间,只能借窥视间接参与。孤红通过“偷觑”了解到宴请时间、地点和场面,受到好奇心驱使的文君决定去堂前偷看一番。尽管封建女子丧失了参与具有社交性质的厅堂宴会的合法身份,但空间的神秘性暗中引诱着她们闯入这个女性禁地。
不能名正言顺“在场”的文君只能在宴会一旁窥看,焦点落在“清标应物,如春月之濯柳,英气逼人,似野鹤之出群”的相如身上。相如佯装喝醉,趁机借榻书斋,半夜时分向西园弹琴,隔墙以曲挑动伊人情意。此时,更深露重,月转回廊,花生暗香,花园充斥着一种氤氲不明的暧昧气氛,为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发展提供了浪漫空间。相如以一曲《凤求凰》自比,文君不禁芳心暗许。琴音、月色、花香均是古典爱情戏曲中常见的意象,此处的院墙也被赋予一定的艺术功能。花园的院墙高大森严,不仅是对相爱之人的物理隔绝,并在文化意蕴上指向了社会阶层、家庭地位、传统礼教对二人的顽固阻拦。相如本能地想大胆跳墙过去,与《西厢记》中张生夜会莺莺如出一辙,但仆人青囊建议让他替主子先行打探。文君此时亦被出外寻找小姐的孤红发现,孤红与青囊便充当才子佳人之间的爱情使者,替两家主子私结幽盟。于是与相如身份、地位悬殊的大家闺秀文君发生了第一次出走,果断与传统家庭相决裂,离开父亲的家,与爱人夜逃成都,在新的空间中以私定终身的方式重建主体性与重组人际关系。
后花园,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吊诡空间。封建闺闱女子不得随意行走,文君白天需要侍女陪伴,夜深才敢只身出现,这是一个拘束的空间;但这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它向女性的自我意识、本能欲望敞开,文君得以暂时超越礼教束缚,唤醒被压抑的情欲。文君在后花园内独自听琴,生怕被父亲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焦虑的空间;但这亦是一个充满神秘的空间,月色迷茫,暗香浮动,四周寂静唯有琴音勾人心魄,诱发文君对未知生活的幻想。这个空间因种种对立属性而具有临界点的意义,需要女性勇敢跨出一步,变“缺席”为“在场”。“作为家庭空间之附属却又不断质疑传统秩序的‘后花园,成为宣泄闺阁女性情欲的一条幽微出口”[3]55,禁忌重重的后花园在一定条件下转化成她们释放天性、挑战父权的游乐场。
虽然故事原型发生于汉朝,《琴心记》实则是剧作家在明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下做出的历史改写,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当时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对女性的道德束缚力度更是史无前例,各地修建贞节牌坊,从小灌输幼女以节烈、贞操观念,以此加强对女性肉体和思想的规训。夫死要守节,未嫁夫死亦要尽节,女子的名誉与贞节紧紧维系,天生的屈从意识乃深切宿命观之体现。大家闺秀文君于花园肆意思春,甚至与地位卑微的陌生男子蓄谋私奔,势必被社会舆论冠以淫妇之骂名,无怪其父对此出格之事予以“丑事莫轻题,贱女淫奔去”的评价。无独有偶,诸多古典戏曲亦出现了将后花园作为情欲情思萌发的典型空间,如《牡丹亭》中杜丽娘到后花园游春,在闺房中惊梦,最后春情难遣、抑郁而终。后花园的一木一草一花一鸟,涌现蓬勃生机,牵动自然人的原始生命力,足以唤起久在深闺的待嫁女子渴望自由与爱情的生命意识,主体觉醒的她们为追逐生而为人的权利勇敢走出传统家庭的牢笼。文坛之中汤显祖等人大胆提出“至情”论,以“情”立“意”,无疑是对主“理”的正统思想的质疑与反叛,在当时可谓“异端”。孙柚的《琴心记》亦顺应了主“情”的文学思潮,文君出走闪烁着反封建的进步人文主义光芒,其身上带有独立人格、自我意识的“新女性”色彩。
二、隐秘与窥探:男性之性别优越
前文主要探讨文君的女性情感空间,在这一部分笔者将着重关注相如的男性情感空间。出于种种机缘巧合,这对新婚燕尔被迫分离,且均面临人生岔路口:文君被接回父亲家中,誓不屈从其父强迫改嫁的淫威,再次出走,带着侍女逃入小巫山庙;相隔一方的相如怀才不遇,因一篇《子虚赋》得到皇帝赏识,却无奈沦入遭人陷害、撤官下狱的窘境,幸得好友救助,入狱三年最终沉冤得雪。剧作家孙柚一开始便对司马相如这一男性符号倾注了浓厚的性别想象,他以动人琴声博得才女文君之芳心,以超众才华赢取最高统治者之提拔,被构建成一个情场、官场双得意的才子形象。
二人的婚姻生活一波三折,遭遇多次困境——物质匮乏的穷困之苦、被迫分离的相思之痛,以及情感危机带来的信任问题。相如的男性魅力不仅俘获了文君,还吸引了其他女子为之倾心,这当然亦是剧作家的别有用意。官复原职的相如回到京城家中,首先受到年轻貌美东邻女的引逗示爱。在第三十七出“茂陵春色”中,东邻女同样对隐秘的后花园表示好奇,隔墙偷看茂陵园中读书的相如,被其体态、琴声深深吸引,大胆抛青梅表达爱意。面对这般“勾引”,相如将卖弄风情的东邻女蔑称为“风前月下妖”,以正人君子的姿态高居,一句“只是自家妻子尚不知生死下落,那有好心肠看他”,可见文君作为人妻对婚姻越轨等潜在情感危机进行道德约束的具象化力量。才子的风流韵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第四十一出“賷金买赋”中,孤红与青囊风尘仆仆来到京城寻找相如,完成任务后青囊又折返山庙接来文君,京城家中徒留相如孤红二人独处。与尖嘴油头、下人出身的青囊相比,才高八斗、气度非凡的官人司马相如显然更受春心飘动的孤红青睐。当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时,正妻文君的缺席使得该空间缺乏有力监控,受强烈男子虚荣心和征服欲驱使的相如把持不住侍女孤红的献媚,不自觉地与妻子的侍女打情骂俏,厮缠搂抱,撕扯衣衫。
若说卓府的西园是文君的游乐场,京城的茂陵园无疑是相如的伊甸园。在茂陵园中,落魄之后重返荣尊的相如远离正妻的守候与监控,以才华和琴技吸引东邻女的注意与爱慕,也与侍女孤红开展暧昧游戏,年轻貌美女性的蜂拥蝶绕恰好侧面印证了他的男性魅力,自由的理想乐园甚至给予他大胆偷吃禁果的机会。即便是在卓王孙府,相如以琴音挑逗文君,他们幽会的后花园是文君女性反叛意识萌芽的空间,更是相如男性虚荣心理、爱情幻想得到极大满足的空间。孙柚对相如文君的故事改写跳脱不出古典戏曲中才子佳人一见倾心、金榜题名幸福团圆的叙事模式,《琴心记》对他们超越门第和阶级的爱情显然持以推崇姿态。而侍女孤红的归宿只能是被许配给同是下人的青囊,没有如愿成为小姐陪嫁、相如小妾,如此安排情节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是相如被预设为始终钟情于发妻的“好丈夫”形象,断不能喜新厌旧、三心二意;二是迎娶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名门小姐更能凸显相如男性性别身份之优越。这实际上契合了古代落魄文人的审美指归与精神理想。
后花园作为一个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场所的同时,亦是一个超越现实、充满文化想象的空间。剧作家借助这一空间书写理想,其现实人生中抱负无从实现的失落之意可以依托虚拟的文艺创作活动得以宣泄。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另类空间》中区分了两个空间——“乌托邦”和“异托邦”。前者是并非真实存在的地方,是人类虚构出来的“完美的社会本身或是社会的反面,但无论如何,这些乌托邦从根本上说是一些不真实的空间”;而后者指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真实存在但又超越现实的地方,即“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同时“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4]54。
周宁教授在《花园:戏曲想像的异托邦》一文中指出古典戏曲爱情故事中的后花园是一个充滿文人想象的意义空间,杜丽娘游春的后花园是一个承载着男女欢爱的典型浪漫场所,丽娘为情而死、为爱而生,“花园既是一个切切实实存在的现实的地方,家宅的一部分,又是一个超现实的乌托邦,沟通跨越现实与梦幻、生与死的界限的‘想像原野”,暗合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游仙或隐逸思想。[5]26后花园在《琴心记》中亦是一个等待发掘意义的“异托邦”,并非如《牡丹亭》那般超越生死、时空,而是超越阶级、身份、地位,为才子佳人的幽盟、私奔、合欢提供了自然环境与意义空间,此乃由中国文化传统决定。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所指涉的婚姻与功名,是中国传统文人向来热衷的两大乐事。《琴心记》的后花园书写恰好完成相如作为男性的双重欲望叙事:在卓府的后花园内,相如赢得了文君的芳心;在京城的茂陵园中,相如沉冤得雪后官复原职,虽然汉朝尚未施行科举制,但他凭借真才实学跻身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集团一员,可视为功成名就。因为单有爱情是不够的,“地下”的爱情需要得到象征权威的父辈认可,才可光明正大立足社会,而这首先需要通过功名换取官职,实现社会地位的进阶。两次后花园叙事,相如先后完成传统文人为之振奋的两项理想,是相如实现男性神话的重要途径,其中寄寓了剧作家对人间浪漫情爱的美好期待,亦是其对自身出路想象与营建的异托邦,它基于现实生活存在,但同时由于无法实现或暂时无法实现而被赋予超越现实时空的意义。
三、禁欲与反禁欲:男尊女卑的固有叙事困境
在《琴心记》中,闺闱女子卓文君前后离家出走两次,第一次是被司马相如的琴音拨弄情欲后,与之私定终身,逃离卓府,夜奔成都;第二次是相如“一旦高贵”,卓王孙为了面皮荣耀把文君接回家中好生侍候,但得知相如陷入麻烦,出于明哲保身考虑,应承田太尉将文君改嫁续弦,文君误会相如已死,带着侍女再次逃出父亲的家,来到峨眉山中小巫山庙。
在第三十三出“空门遇使”中,文君向尼姑比丘尼表明自己困于红尘烦恼、意欲削发为尼的心志。在她们所处的西汉时期,佛教“未入于中国,法已播于南方”,教义主张“一心淸净,两手皈依”,于是比丘尼提出遁入佛门修身静心的禁欲要求,劝说情根深种的文君勿要一时意气,“弃了在家的繁华错认了出家的清净”。山庙作为一个禁欲的宗教空间,将文君这种留恋俗世、未断尘缘的“伪”信徒排斥在外;然而,掌门人比丘尼还是同意收留文君等人安歇,支撑比丘尼这一举动的是寺庙为行人提供食宿的类“客栈”功能。在文君走投无路之际,尼姑及其山庙拯救了文君,文君逃避专权父亲对自己安排亲事、插手人生而在山庙住了三年。在相如重返荣尊之后,比丘尼一路护送文君回到京城与夫君团聚,相如为表答谢赠予尼姑白金百两助修神庙。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受到父权压迫的文君得到同是女性的尼姑援助,女性之间相互成全、相互拯救,在女性普遍失语的封建传统社会,同处劣势地位的同一性别内部的惺惺相惜显得尤为珍贵。
此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主张禁欲主义的佛教为实现俗世情欲提供了特殊载体——山庙。位于深山的寺庙原本就远离闹市的繁华,它的边缘位置却暗含冲击“灭人欲”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无独有偶,中国古典戏曲不乏在宗教场所中发生、发展的青年男女爱情故事,比如《西厢记》中的普救寺、《玉簪记》中的女贞观,剧作家构建出来的这些反对人欲的寺庙宫观流露出肯定人欲的无意识倾向。宗教性质的寺庙宫观,是“服务和服从于宗教仪式和活动的,是善男信女们集聚于此祈求神佛庇护与保佑的地方”。在剧作家的想象中,“它们虽然有现实社会寺庙宫观建筑的形制、格局、环境,有宣讲教义和满足僧俗日常生活的功能,但内里却是对宗教精神的反叛和背离”,成为挣脱宗教清规戒律的知觉与想象空间。[6]29《琴心记》的峨眉山小巫山庙尽管欠缺《西厢记》、《玉簪记》那样成为见证男女主人公爱情萌芽发展的典型空间意义,但是在维系、延续文君的日常生活与婚姻爱情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介质作用,同样是在禁欲的外衣之下无意中宣扬了人欲。
文君的两次出走,均是逃离自封建礼教层层束缚的父权家庭。卓王孙未经女儿同意私自将她许配他人,再现了封建女性附属于男性、被剥夺选择权的消极地位;而强迫文君改嫁“失配”的田太尉是出于续弦的考量,换而言之,哪怕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精英女性也逃脱不了被物化为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的命运。因此,卓文君两次离家产生的空间位移具有强烈的隐喻性,象征着女性的主体意识苏醒,并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道统发起了猛烈挑战。然而,在这看似闪烁着进步人文之光的空间书写中,人们似乎遗忘了文君在禁锢、闭塞、压抑的父亲家中等待被救,她出走后奔向的归宿指向了司马相如,她从一个男性(父亲)手里走向了另一个男性(丈夫),之后所受的苦难与委屈皆源于新的家庭,她要求自己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甚至出家为尼,却未曾料想千里之外的丈夫可能在风花雪月。可见文君的性格显然是充满矛盾的,她一方面是父权秩序的反叛者,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沦为夫权秩序的固守者,始终没有逃离男权社会的樊笼、成长为真正独立自主的女性。在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关于女性解放的部分虽然具备近现代意义上的雏形但仍是不成熟、不彻底的,所以思想再前卫的剧作家在创作中依旧无意识地落入男尊女卑的叙事窠臼,此由中国小农经济传统社会决定:妇女生来便是在社会地位、家庭地位上均次于男人的第二性存在。
被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第二性》如是论述西方女性的生存境遇:在少女的成长经历中,“大家都一致同意找丈夫——或在某些情况下,找‘保护人——是她最重要的一件事。在她眼中男人是‘另一自我的化身,正如她自己是男人的另一自我。但这‘另一自我对她是基本的、主要的,而对他来说,她却视自己不基本、不主要。她要将自己从父母的家、母亲的掌握中解放出来,她要开启自己的将来,但不以主动的征服方式,却是将自己被动而温顺地献入一个新主人的手中”[7]90。关于妇女地位之认知,东西方文化上是共通的,在男性占有绝对权威并主宰一切的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女性只是“另外的一种性别”。从该视角切入,美人与荣华俱得的司马相如成为《琴心记》的绝对主角与唯一赢家,文君则是作为烘托相如男性“高光”时刻的符号而存在,尽管剧作家用大量篇幅描绘二人的浪漫情爱与相互思念以此肯定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男女之欲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无意识层面却折射出对男性性别优越的倾向,指明夫权是妇女的归宿与庇护。这无疑是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时代局限性使然,对于该叙事困境亦无法过多苛责,毕竟剧作家在挣脱礼教藩篱、高举“主情”旗帜的路上已迈出勇敢一步。
结 语
剧作家基于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与洞见,在广袤的想象原野上自由馳骋,创作出来的作品具有现实与超越现实(即虚构)的双重属性。古典戏曲作品中的空间,不再仅停留于物理学或建筑学层面,更多的是心理学、人类学概念,它们向历史开放、向社会开放,为之内涵增值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土壤。
《琴心记》的空间书写充满性别意义。卓府的后花园是相如与文君爱情萌生的起点,亦是文君反叛父权家庭、走向主体觉醒的场所,后花园的闯入者——相如打破了这个封闭空间原本稳定的父慈子孝伦理秩序,后花园的出走者——文君以自身的叛逆试图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京城的茂陵园是相如与文君幸福团圆的归处,亦是相如男性才华魅力和志趣抱负再次得到施展的场所,除了东邻女示爱、孤红献媚等来自女性的侧面肯定,相如在茂陵园中为被废的陈后作赋使其重获恩宠、恢复后位,皇帝的二度封赏与现实中失意文人对“翻身”结局的理想期待相契合;峨眉山小巫山庙披着宗教禁欲的外衣,承载着收留文君、协助她延续俗世情缘的功能,在无意识层面流露出对清规戒律、吃人礼教的逸出与背离,然而山庙中等待丈夫音讯的文君俨然一个苦守寒窑、坚守贞操、待夫归来的传统妇女。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宋元明清以相如文君为题材的剧目不下30本,对反封建主题的处理大多难免受困于时代。《琴心记》亦然,剧作家孙柚对男性霸权的不自觉倾斜导致文本陷入了男尊女卑的固有叙事困境,但其彰显的女性反叛意识、男女恋爱自主观念高举了主“情”反“理”的旗帜,在当时看来亦足够震撼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