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
2020-04-20云兮
云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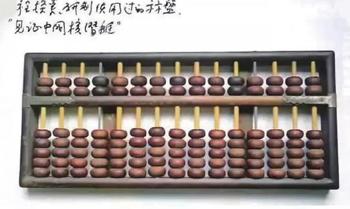

在惊涛骇浪的孤岛,他隐姓埋名,甘心做沉默的砥柱:在一穷二白的年代,他挺起胸膛,成为国家的栋梁。他的人生,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他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所属719所名誉所长,他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次)、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及成就奖等荣誉,2019年获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共和国勋章。
今天,已经95岁高龄的黄旭华,站在了象征着我国科学技术最高荣誉的领奖台上,其科学成就得到举国认可。在他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中,是什么经历让他成为顶尖科学家,又是什么精神支撑他为我国的核潜艇事业执着一生?
颠沛流离立救国之志
1926年,黄旭华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父母一生悬壶济世,仗义疏财。看到父母的善举,黄旭华自小立志继承衣钵做个医生。可时代洪流将他人生计划全盘打乱。1937年,战火纷飞,山河飘零,连天的战火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黄旭华的中学时代不得不辗转广东揭西、梅县和桂林、重庆等地求学。于是黄旭华决定:“我不学医了,我要造飞机、造大炮、造军舰。”总之什么能对付敌人,他就学什么。
1945年,21岁的黄旭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航空系,但他的志向是造船,因此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1954年,他在外国专家的指导下,设计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艘扫雷艇和第一艘猎潜艇。
1958年是中国核潜艇事业元年。一天,时任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设计二处潜艇科长的黄旭华,突然接到去北京“开会”的通知,和他一起“开会”的共29人,他们都是舰船方面的专门人才。直到几天后,聂荣臻元帅亲自给大家开会,黄旭华才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几天后,他走进了海军舰船修造部和一机部船舶工业管理局联合组建的核潜艇总体设计组,这才知道是“天字第一号”绝密工程选中了他。
黄旭华至今记得,报到时领导找他谈话说了三条:一是“你被选中,说明党和国家信任你”;二是“这项工作保密性强,这个工作领域进去了就出不来”;三是“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黄旭华毫不犹豫,“一辈子出不了名,当无名英雄”,这与“党和国家信任你”相比,算得上什么啊!
1965年春天,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第11次中央专委会议,正式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列入国家计划。中央决定成立719所,黄旭华和尤子平担任副总工程师。
攻坚克难铸国家重器
核潜艇,是集海底核电站、海底导弹发射场和海底城市于一体的尖端工程。在开始探索核潜艇艇体线型方案时,黄旭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艇型。
1966年1月,719所繪制的第一张图纸画的仍是在役的苏制常规动力潜艇的那种普通线型。美国当年就是从常规线型开始,分3步走才实现向水滴线型的过渡。但黄旭华一直钟情于水滴线型。早在1959年至1961年,他就和钱凌白在上海交大、无锡702所的水池里做过无数次试验。虽然因为水池不够大,试验的大部分结果只能定性、还达不到定量分析的要求,但已经证明水滴线型具有明显的优势。有资料说,两艘吨位和动力相同的潜艇,如果一艘采用水滴线型,另一艘采用常规线型,前者在水下的航速要比后者快16%。
最终他选择了最先进、也是难度最大的水滴线型艇体。美国为建造同类型核潜艇,先是建了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后把核动力装到水滴型潜艇上。黄旭华通过大量的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试验数据,为论证艇体方案的可行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时,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的黄旭华及同事们,经常为得到一个正确数值而组织3组人马同时计算:如果3组人的计算结果都一样,那便可以通过;只要3组数据有一个不同,就必须重算,必须算到3组人得出的是同一个数值。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除了用算盘计算数据,他们还采取用秤称重的方法: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吻合。
计算之难,还因为设计时很多配套的设备尚未研制完成。只要一个数值变化了,所有的重心、力矩都要从头算过。行业的一位资深专家透露,黄旭华带领719所的核潜艇设计专家团队,从最初的方案论证开始,到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设计,总共为“404”艇画了4万5千张设计图纸,连接起来大约有30公里长!
正是这种执着严谨的精神,激励黄旭华团队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研制出我国水滴型核动力潜艇,其各项性能均超过美国1954年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周期之短,在世界核潜艇发展史上是罕见的。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顺利下水,黄旭华禁不住热泪长流。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伟大誓言,新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
惊涛骇浪显报国之心
1988年4月,中国核潜艇“404艇”在南海准备向“极限深潜”的目标冲刺。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便在于极限深潜。然而,极限深潜试验的风险性非常高。1963年4月份,美国的长尾鲨号潜艇进行最后的最大下潜深度能力测试时遭到了不幸,潜艇上100多名参与试验的人员无一幸免,潜艇入海后再也没有上来。因此,在深潜试验前,船厂为参加此次试验的十几位同志拍了“生死照”,以防万一失败后留作“最后的纪念”。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队伍中弥漫着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氛。黄旭华心想,极限深潜试验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任务,就更加危险。
“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次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黄旭华亲自去和战士们座谈,缓解紧张情绪。接着,他语气坚定地说:“不怕牺牲是崇高品质,但我们深潜不是要你们去牺牲,是要完成任务、要拿到深潜的数据再回来。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他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这句话立即威震全场,让悲壮气氛一扫而光。
于是,核潜艇载着黄旭华和100多名参试人员,一点一点下潜。快到300米时,潜艇顶壳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多个位置咔咔作响。这样的声音在水下300米深处令人毛骨悚然。
黄旭华镇定自若,了解数据后,指挥继续下潜,直至突破此前纪录。新纪录诞生,全艇沸腾了!黄旭华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赋诗一首:“花甲癡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而黄旭华亲自下潜300米,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从此,中国核潜艇劈波斩浪,邀游在深蓝的大洋之中,为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释放出巨大的震慑力。在黄旭华的带领下,我国仅用了13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至少要用30年才能走完的核潜艇研发之路。
隐姓埋名30余载
研究核潜艇得去海上,因为机密和危险,必须远离人烟。因为保密需要,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被调到了北京。从此,黄旭华一家就在父母面前“消失”了,唯一的联系方法就是一个编号为145的内部信箱。
黄旭华回忆:“在海上奔波了几个月后,我们在黄海和东海的中国海域分别选择了一个荒凉的小岛,小岛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在地图上也查不到。为了保密,不通邮,不通电话,偶尔只有经过伪装的民船靠岸送给养和信件。我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带着团队到岛上扎下了根。大家以苦为乐,互相关心,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黄旭华让中国人的脊梁挺得更直了。可他却在父母和兄弟姐妹面前愧疚难当。在开始研究核潜艇前,黄旭华回老家过春节。母亲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爸也老了,你们要经常回来看看……”黄旭华点头答应。可从1958年到1986年,整整30年他再也没回过家,与家人亲友彻底断绝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在北京哪一个单位?到北京去干什么工作?黄旭华一直闭口不答。
由于不能回到父母身边尽孝,黄旭华每逢年节都会给老人寄去10元钱,他只能以此表达孝心。可父亲生气地把黄旭华寄的钱退了回去,姐姐也写信骂他“越大越不懂事”,面对那张退回来的汇款单,黄旭华心中五味杂陈,欲哭无泪,还不能多解释。后来,父亲因为脑梗到北京看病,父母和兄弟姐妹除了145号信箱外,完全没有其他任何联系方式。等半年后他收到信时,父亲已经去世多日……
父亲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做什么,老人家是带着埋怨和不解走的。在父母兄妹眼中,这样的黄旭华,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不孝子。
1986年,当黄旭华回到阔别的家乡时,父亲、兄长已经去世,看着已是满头银发的90多岁的母亲,黄旭华不禁跪地痛哭流涕。而这次重逢,家人仍不知道他这么多年在干什么。直到一年后,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至此,黄旭华这三个字才终于被“解密”!
黄旭华把杂志寄给了母亲。母亲一看,里面所讲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要家,忘记了养育他的父母,不孝的三儿子。母亲满脸泪水,自豪不已。她把子孙们召集过来,郑重地对大家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都得谅解!”母亲这句话让黄旭华非常感动,黄旭华说,母亲这句话对自己非常有意义,每次想起来,他都忍不住流泪。自古忠孝不能两全,黄旭华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老骥伏枥壮志依旧
“‘痴和‘乐两个字是我一生的写照。痴迷核潜艇,献身核潜艇,无怨无悔;乐观对待一切,在生活与工作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苦中有乐、苦中求乐、乐在其中。”黄旭华如是说。1988年,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将国家使命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退岗不退休,几十年来,黄旭华言传身教,培养和选拔出一批又一批技术人才。
1994年,因其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功勋卓著,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媒体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14年,黄旭华荣获“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当时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时代到处是惊涛骇浪,你埋下头,甘心做沉默的砥柱;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在颁奖现场,87岁的黄旭华十分动情地说:“若干年之后,我的工作可以公开了。我在父亲的坟前说:爸爸,我来看你了,我相信你也会像妈妈一样地谅解我。”
2019年,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黄旭华说:“共和国勋章授予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这份光荣属于核潜艇战线的每一员……核潜艇事业是国防事业发展的缩影,我为祖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历史性变革而骄傲,为自己是一名国防建设的老兵而自豪。‘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我和我的同事们,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核潜艇是黄旭华一生的事业。他所呈现的精神品质,是一颗共产党员的初心,是一个科技工作者的爱国情怀。新时代更需要老一辈核潜艇人那不惧艰难、无私奉献的精神,更需要他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独特的创新基因。他们所开创的核潜艇事业,继续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编辑陆思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