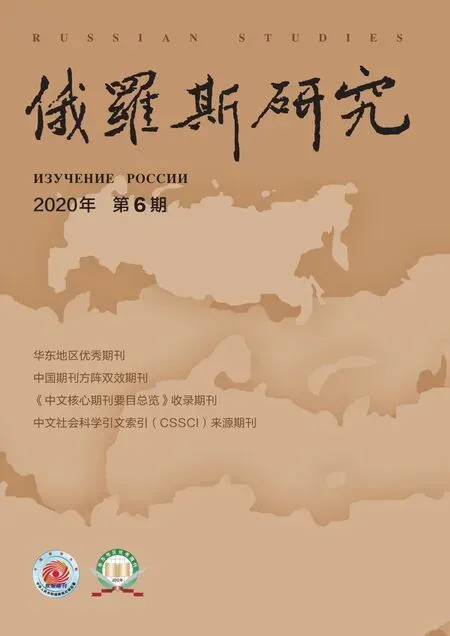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
——基于认知相符理论的解析*
2020-04-18吴大辉
吴大辉 王 洋
【内容提要】美国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机构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但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本文借用国际政治认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错误知觉研究中的认知相符理论,解析美国战略界集体预测中对苏联解体的全方位误判。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基于苏联1950 年开始的20 年间经济整体向好的历史经验认知,对苏联未来经济走势判断持过分乐观态度。在军事方面,他们高估了苏联军队在政权稳定中守护者的作用,低估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坚信戈尔巴乔夫可以在最后关头动用武力来保卫苏联。在外交方面,他们认为东欧的和平剧变对苏联而言是一种解脱,忽视了东欧政治进程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的“影响循环流”,以及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鼓舞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末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衰落被错误解读,意识形态构成苏联政权主要合法性的事实被忽视。有鉴于以上对苏联判断中全面的认知相符,最终导致美国战略界未能预见苏联解体。
美国战略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但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创始人、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却预见到了。他早在1980 年就曾预测“作为帝国最薄弱点的柏林墙将在十年内倒塌,紧随其后苏联帝国将崩溃”,因为苏联精英对“苏联和卫星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城市与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资金流动性和商品匮乏现象”“共产主义乌托邦神话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六大矛盾,无能为力。①[挪]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0 页。1980 年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盛时期,加尔通在此时断言苏联即将崩溃,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事实上,在苏联骤然解体之前,人们对强盛帝国可能会突然崩溃这一假设,实在缺乏想象力。美国冷战战略的主要设计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将苏联“突然而彻底”的解体,称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奇怪、令人震惊、使人费解的事件”。②Owen Harries, “A Special Issue”,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3.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在1993 年推出过一期探讨苏联解体的文章,而这一特辑被冠名“苏联共产主义的离奇死亡”。③“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The Special Issue of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1993-06-01/strange-death-sovi et-communism-special-issue-national-interest-no
所谓“离奇”有两层含义,即苏联解体的时间和方式。“离奇”的时间层面含义在于,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依然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但为何在短短六年之后就分崩离析?一般而言,庞大帝国的衰亡总是漫长的。在凯末尔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改造成“欧洲病夫”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拼凑帝国受到1848 年革命的剧烈摇动后,又延续了80 年;而中国的王朝在度过兴盛期之后,一般还要残喘度过百年才会最终崩溃。④[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3 页。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西方战略界对苏联面临的各种顽疾了然于胸:经济长期停滞,外债高筑,生活用品奇缺,物价不合理,黑市猖獗,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加剧,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尤为严重……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创刊的《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苏联解体后改为: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长期全面探讨苏联面临的经济、社会及民族等问题。但是,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问题会危及苏联的生存,至少不会立即导致苏联解体。苏联为什么不像其他帝国一样,在经历权力顶峰期之后,在诸多经济、社会、民族问题的消耗下,慢慢衰亡,而是以如此“离奇”的方式迅速地突然解体?
所谓“离奇”的方式层面含义在于,苏联为什么以如此平静的方式解体?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越改越乱、苏联颓势渐渐明显时,美国战略界开始预测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并列出了这种可能性的四种走势:其一,苏联完全充分解体,但过程和平,解体后转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最优);其二,苏联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拥有一个形式上的中央,以保持控制核武器,同时放松对加盟共和国的管制(次优);其三,苏联以血腥暴力的方式解体,战争和冲突蔓延到边界之外(不利);其四,苏联避免了解体,经济止跌回升,实现中兴,并再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①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年,第388 页。在苏联后期,美国一直将次优选择即第二种走势作为政策目标,却意外地得到了最优结果。苏联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刀兵相见,民族冲突也并未失控蔓延,苏联平静解体,庞大帝国的崩塌没有引起剧烈余震。
美苏两国冷战缠斗数十年,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彼此,以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估计,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机构在顶峰时期达到40 余家,专门研究人员最多时达3000 余人,有80 多所大学进行有关苏联的教学和研究。②于滨:“从X 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1 期,第69-86 页。在政府、军方、情报、学界的努力下,苏联研究界已成为美国最庞大的“国别/地区研究体系”。如此规模庞大、投入甚巨的研究工程,最终仍以预测失败告终,让“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在“美国衰落或崩溃”成为热门研究话题的当下,通过对“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析,我们可以吸取美国战略界的教训,避免在“美国衰落或崩溃”的研究中产生错误知觉,出现类似的认知相符。
一、对美国战略界的既有批评反思与本文解析的理论范式
由于未能预测到苏联解体,美国苏联学界(Sovietology)和情报界都受到了广泛批评,其自身也进行了反思。这些批评和反思是对美国战略界①本文的“美国战略界”主要包括学术界、政策界和情报界。三者之间都存在交集,但学术界与政策界的交集最大。在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的苏联学界与政策界联系紧密,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成果常常转化为政策界决策的基础性依据,而且政策界常常向学术界提出研究要求,甚至杰出的学术界人士直接被吸纳进政策界。因此本文也使用“苏联学界-政策界”的概念。自身预测失败原因的解释性总结。
(一)对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之批评反思
苏联轰然倒塌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苏联学界-政策界——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到分析视角,甚至包括研究者个人的政治倾向,都被严格而彻底地审视。
其一,反思社会科学预测的可行性。如此规模庞大、投入甚巨的研究工程,最终仍以预测失败告终,这不禁让人怀疑:社会科学究竟能否有预测能力?约翰·李维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否认社会科学预测的可行性。②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2, Vol.17, No.3, pp.5-58.他认为当少数变量在可控或已知条件下相互作用时,预测是可能的,但只要变量数量有些许增长,或操作条件变得复杂,预测将变得不可进行。兰道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态度较为温和,认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不同。③Randall Collins, “Prediction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Soviet Colla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Vol.100, No.6, pp.1552-1593.一般来说,对宏观历史进行预测是可能的,学者可以同时提供理论和实证信息。但对于国家的建构和消亡这样的“中观事件”,地缘政治理论能够提供的可预测时段是三十至五十年,而且学者只能提供发展方向,无法判断事件的爆发节点。
其二,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约翰·李维斯·加迪斯在其影响甚广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终结”一文中宣告:“冷战的突然终结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失败”。④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而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当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模仿自然科学,追求理论的客观(objectivity)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时,殊不知绝对确定的科学从20 世纪之初就开始褪色,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正在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阂而担忧,试图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纳入其研究方法中。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对美国高校博士候选人于1976年至1986 年间,以苏联政治为主题写就的毕业论文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不掌握俄语”“不具备研究苏联的资质”。①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Notes for a Post-Mortem”, The Na tional Inter 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p.109-122.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一直存有一些程序化的研究和分析模式。苏联解体的突如其来,显示了这些分析模式的局限性。
其三,反思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的分析视角。康纳(W. R. Connor)认为在经济理性假设当道的西方学界,传统与观念——这些对人类行为具有塑造作用的因素——几乎没有生存空间。②W. R. Connor, “Why Were We Surprised?” The American Scholar, 1991, Vol.60, No.2, pp. 175-184.长久以来,西方的苏联学家所依赖的分析视角都太过局限,他们总是着眼于可量化的因素,例如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农业产值等。这种模式化的研究忽略了苏联社会以及东欧国家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民众的民族情绪,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渴望,或对当局的不满心理,认为政府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这些因素被认为“太软”(Soft)、“不够科学”,而被选择性地屏蔽和忽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里亚(Martin Malia),曾化名为“Z先生”发表长文“通向斯大林的墓地”,指责美国的苏联学界关注社会和经济等“底层问题”研究,却忽视了对集团模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高层问题”的专注,以“社会研究”取代了“政权研究”。③Z, “To the Stalin Mausoleum”, Daedalus, 1990, Vol.119, No.1, pp.295-344.
其四,反思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研究者的政治倾向。彼得·拉特兰认为,美国的苏联研究者持有的政治偏见(Political Bias),是他们产生误判的原因。④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Notes for a Post-Mortem”.活跃于20 世纪80 至90 年代的苏联研究者成长于60 至70 年代,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怀有强烈的左翼政治同情(Left-Wing Political Sympathies)和左翼偏见(Left-Wing Bias),不同于经历过二战、对美国怀有深切自豪感的老一代研究者。这些新一代研究者经历了越战、经济滞胀,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对资本主义怀有强烈的怀疑,对苏联心怀好感。他们将1917 年革命定性为“由有觉悟和理性的工人及农民发起的大众革命”,这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倾向。美国研究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可,使他们无法准确评估苏联的实际历史进程。
(二)对美国情报界之批评反思
苏联骤然解体之后,美国情报界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主流媒体,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等,都猛烈攻击中央情报局,批评它是“最愚蠢无能的政府机构”,“从没对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做出过正确判断,在苏联解体上尤其无能”,“让国民为他们愚蠢而昂贵的错误买单”,“未能完成既定使命”。参议员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甚至提议将中央情报局解散,将其并入国防部的情报部门中。①Bruce D. Berkowitz, Jeffrey T. Richelson, “The CIA vindicated: the Soviet collapse was predic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5, Issue 41, pp.36-47.具体而言,对美国情报界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批评情报界在信息搜集方面的不足。美国知名政治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对中情局的评价是:优质的政治情报,如反映克里姆林宫情况的政治情报,基本不存在。1991 年8 月18 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行使国家全部权力”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当天晚上11 点播报了这一消息,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看到新闻后转告了老布什,而中情局的报告第二天才送达白宫。②[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 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472 页。中情局的信息搜集能力到底如何?其工作失误源于何因?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驻美国华盛顿事务部主管阿尔贝尔(David Arbel)给出如下评价:中情局的技术情报来源十分先进可靠,但缺乏可靠、充足的人力情报来源。③[美]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孙成昊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261 页。人力情报来源的缺乏,导致无法洞察苏联政治进程。中情局依靠卫星等获得丰富的技术情报来源,可以对定量问题——例如苏联军事设备全方位和精准的细节——做出判断,但人力情报来源,尤其是对苏联身居高位者的人力情报信息,却非常缺乏。这就导致美国对苏联的基本生活状况以及高层政治进展,缺乏系统性的感知,而且极容易下“肯定性的结论”。这种认知相符基于以下判断:与修改或推翻现有信念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坚持它或证实它;一旦情报界对其既定框架充满信心,那么在这种框架下形成的结论,注定是被不加批判地认作“已证实”。①Matthew Herbert, “The Intelligence Analyst as Epistemolog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06, No.19, p.678.这是当时美国情报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其二,批评情报界在信息处理上的问题。伯科维茨(Bruce Berkowitz)认为,中情局的“预测无能”并非是其机构本身的错误,因为中情局“所做的预测是分领域的,但苏联的崩溃是一个整体现象”。阿尔贝尔也认为,尽管中情局和情报机构紧盯着苏联,但始终未能理解苏联变化的重要性。②[美]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51 页。事实上,美国情报界始终强调结构性论证(structured argumentation),即对问题的定义总是始自于分解问题,然后对问题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分析。③Jill Jermano,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d Argumentation”, Project Genoa Technical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2.但在对苏联是否会崩溃问题的预测上,美国情报界并未将各个分领域的预测有机地整合起来。情报搜集人员、处理人员、分析人员和用户之间的屏障仍然牢固,门户之见制约了合作。④[美]罗伯特·克拉克:《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马忠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 年,第25 页。
(三)本文的理论解析范式:认知相符理论
本文尝试使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认知相符理论,解析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的误判。杰维斯是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的领衔学者。“错误知觉”是杰维斯引入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判,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导致的结果与决策者的原本意愿不相符。意即,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这实际上形成了螺旋逻辑,即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那么即使有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印象仍然得以维系。杰维斯认为,导致错误知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在认识过程中的呈现。所谓“认知相符”,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接收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使新获得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而回避、抵制与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简言之,相符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到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之中。①[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27 页。
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记忆之中,形成了在接收新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这其中还包括诱发定式(evoked set),即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式,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一个人会根据即时的联想去认识和解读刺激因素,所以要推断一个人从某种证据之中得出什么推论,我们往往要知道这个人正在关注的问题和他刚刚接收到的信息。②同上,第223 页。
二、美国战略界对苏联经济增速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苏联解体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军费负担过重、政治改革以及领导人特质都值得追溯。这一事件跨越多个领域,指责某个领域的学者未能预见苏联解体并不公平。然而,即便仅考虑经济领域,美国的苏联学领域经济学家们也仍然难辞其咎。他们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现象,包括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军费在国民经济中的畸形地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济后果,以及1980 年后的货币性不均衡,这些现象构成了“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始于20 世纪70 年代的经济停滞,是戈尔巴乔夫急于推行改革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期因为经济改革不顺而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并没有预见到苏联经济在70 年代急转直下的趋势,对苏联经济持普遍的乐观态度。因为自20 世纪50 年代之后,苏联经济有近20 年的较快增长期,使得美欧战略界已经对苏联经济形成固定认知,即苏联计划经济具有强大的可持续力和自我修复调整的能力。①Michael Ray, “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Bratainnica, https://www.britannica. com/story/why-did-the-soviet-union-collapse美国战略界由此形成了“苏联经济发展向好”的固定认知,甚至认为,在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都能与美国匹敌,因此与西方国家市场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苏联计划经济似乎是可行的经济选择。②Rand/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International Behavior, “Soviet Economic Grow: 1928-1985”,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220336.pdf这导致对1970-1990 年苏联经济的危机因子认识不足,认为危机症候尚不会转化为导致国家解体的经济崩溃。例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1982 年推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1979-1982 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五年计划制定的指标趋势,1979 年创下经济增长新低(0.8%)。但该委员会在分析这种经济颓势的原因时指出,是恶劣的气候周期导致农业发展差强人意,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苏联外贸收入减少。该报告相信这些消极因素都是可以逆转的。③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rt 1, December 31, 198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这种基于历史类比而产生的认知相符带来了误导作用,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重大的知觉错误。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说:“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偏见。”斯坦利·霍夫曼同意费正清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往往把历史当作“杂货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出‘经验’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说明,人们只是利用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支持自己已有的认识和偏好。④[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239 页。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基础数据的预测失误,就是一个此类认知相符的典型案例。
有学者统计了美国经济学家对1970 年至1990 年苏联经济数据的预测,发现无论是以中情局测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工业增长,还是以苏联官方发布的净物质产值(Net Material Product,即NMP)为预测指标,高估苏联经济增速是美国苏联研究界犯的普遍错误。例如,孔托罗维奇(Vladimir Kontorovich)对1970-1990 年发表的关于苏联GNP增速的文章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27 篇增速预测文章中,有25 篇高估了苏联的经济增速,高估比例高达93%。在这些研究中,既有针对特定年份的增速估计,也有三年或五年的平均估计。而所谓的“高估”或者“低估”,是将预测数据与中情局公布的实际数据比较得出的。在27 份预测研究中,仅有斯坦利·科恩(Stanley H. Cohn)于1970 年对1971-1975 年经济增速所做的预测(3.5%)略低于实际增长值(3.7%),以及亨利·罗文(Henry Rowen)于1982 年对1973-1988年经济增速所做的预测(1.0%-2.0%)低于实际增长值(2.2%)。①Vladimir Kontorovich, “Economists, Soviet Growth Slowdown and the Collapse”, Europe- Asia Studies, 2001, Vol.53, No.5, pp.675-695.
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预测中的集体错误,归根结底是基于历史类比的认知相符。本文认为,可以从研究者使用的预测方法、数据来源,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中探寻原因。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失误,是美国战略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忽视苏联的特殊性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未能意识到苏联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从1970 年到1990 年,美国经济学界的集体预测失误可谓旷日持久。当1970 年到1980 年的实际增长值揭晓之后,经济学家们理应意识到此前的高估倾向,并及时调整预测方法。②Rand/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International Behavior, “Soviet Economic Grow: 1928-1985”.然而,理论上的及时纠偏并没有发生,1980 年到1990 年的增速预测仍然整体偏高,经济学家们重蹈70 年代的覆辙。这场集体误判之所以出现,与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有重大关系。纵观西方经济史,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经济增速均呈现周期性波动,这一现象得到现实的反复印证,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和基本信条。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和指令式经济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占据着两个极端。③Leslie Kramer, “Market Economy vs. Command Economy: What’s the difference?” Investopedia,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sk/answers/100314/whats-difference-between- market-economy-and-command-economy.asp用市场经济的共识与信条审视计划经济时难免出现严重纰漏。
基于历史类比的经济预测固然以客观数据和预测模型为基础,但学者所持的个人观点和信念仍对预测结果具有重大影响,否则诸多研究者的预测数据也不会呈现出如此强的多元性,毕竟他们使用同样的数据,以及近乎雷同的预测模型。由于将西方市场经济增长规律应用于苏联经济增速预测,保留了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强烈信念,而未能注意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性。①Matthew Johnston, “Why the USSR Collapsed Economically?” Investopedia, https://www. 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21716/why-ussr-collapsed-economically.asp美国的经济学家无法想象苏联经济会出现20 年以上的持续下滑,这种信念让他们在预测模型使用和数据诠释中,有意无意地对苏联经济增速进行高估,并选择性地忽视70 年代的预测失败,在80 年代继续一路狂飙。可以说,对研究对象(苏联经济体制)的认识不足,是经济增速预测失败的重要原因。延伸来看,研究者的预测和判断均以历史经验和常识为基础,而历史经验和常识源于研究者的过往经历和所见所闻。加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苏联是一种崭新的存在,亦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既有知识边界之外的全新领域,这也增大了预测难度。
(二)长期存在的高估倾向加剧认知相符
在美国,当时存在着大众对苏联经济高增长的预期,美国战略界对苏联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在此问题上形成认知相符。当两个国家处于持续且激烈对抗时,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失败要低得多。因此,在国家间对抗中,低估对手的实力绝非明智之举。“宁可高估,绝不低估”的竞争心理在美苏冷战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1984 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提出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有“高估苏联的习惯”,这导致美国丧失谈判优势,即使是在“美国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②Joseph Nye, “Can America Manage Its Soviet Policy?” Foreign Affairs, 1984, Vol.62, pp. 857-878.对于美国战略界的这一心理,以色列摩萨德驻美国华盛顿事务部主管阿尔贝尔做过十分精辟的总结:美国有一种看法,或者是“理念”,一直存在到苏联帝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天,那就是苏联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无论是苏联的疲态尽显,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悲伤哀求,都无法削弱这种理念的影响;这种“理念”使得华盛顿直到苏联崩溃前都把它当作平起平坐的强国,指出当局过于夸大形势的情报官员,都被认为是“扫兴的人”。①《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51 页。1982年,美国参议员Y·普罗克斯迈尔在概括中情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工作报告时曾说:“可以从这类研究得出三个关键性的结论:第一,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减缓,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增长仍将继续;第二,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经济已丧失活力和动力;第三,虽然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即便从长远看,苏联经济也未必会崩溃。”②转引自[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146 页。
从情报人员所受的质疑,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民众、学者及政府官员都倾向于相信苏联前途光明,坚不可摧。只有极少数美国的苏联学界经济学家,在苏联解体前夕清醒地指出了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苏联的资源可能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工业界的经理人缺乏运作市场所必需的知识、长期的国家命令限制了工厂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的生产能力。③Robert D. Grey, Lauri A. Jennisch, Alanna S. Tyler, “Sovie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orbachev Reforms”, Slavic Review, 1990, Vol.49, Issue 2, pp.261-271.但多数美国的苏联研究者在苏联解体前,仍然认为其经济形势远未达到导致国家解体的境地。处于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之下,如果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前景做出悲观判断,其个人要承担舆论压力甚至利益风险,还有可能被指责因为低估竞争对手而误导政策的重大风险。因此,无论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考量,对苏联经济增速做乐观判断,都是合乎时宜、符合“战略清醒”原则的明智选择。
(三)苏联的数据虚高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经济数据预测的第一步,是获取并处理数据源。经济生产活动的衡量与统计是极为复杂的国家内部事务,需要专门的政府部门进行信息搜集和数据统计,除主权国家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要获得翔实可靠的经济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处在冷战状态下的美苏两国而言,获取对方经济数据的唯一可靠渠道,便是彼此发布的官方数据,而苏联的官方数据收录于每年发布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之中。然而,美苏两国在经济统计指标、价格计量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这给双方学者造成了新的挑战。在经济统计指标上,苏联采用国民收入,该概念基于马克思对劳动和经济生产活动的定义,被社会主义国家广泛采用。1960 年以后,苏联经济部门又开始采用社会生产总值作为经济衡量指标。①金飞:“前苏联经济增长的TFP 讨论——苏俄与西方序列的比较”,《俄罗斯研究》,2014 年第4 期,第165-191 页。美国方面则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在价格计量上,苏联所采用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s)未能有效排除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一步整理。美国经济学家固然可以在不同的经济统计指标之间实现符合经济规律的转换,也可以有效排除可比价格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然而,由于经济预测依赖于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年鉴,一旦数据源本身的质量存疑,即使数据经过纠偏和格式化,也无法产生可靠的预测结果。美国的苏联学界专家甚至这样为自己的预测失误辩护:如果我们弄错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不这样做,要预测苏联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专家群体中广泛流行的看法是:所发生之事的原因具有主观性质,是由1985 年之后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所决定的。②[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第147 页。言外之意,不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界预测错误,而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导致预测失败。苏联的统计数据失实到什么程度?以美国战略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数据为例,经济学家库尔茨威格(Laurie Kurtzweg)在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直言:西方自己着手对苏联经济增长进行测量,本身就是出于对苏联官方所公布数据的怀疑。③Laurie Rogers Kurtzweg, “Measures of Sovi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1982 Prices: A Study for the Use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英国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是麦迪森数据库(Maddison Database)的创建人、《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作者,是苏联经济增长测算领域大有权威的西方学者之一,其对苏联数据的评价是:总是低估通货膨胀因素,而夸大增长水平。④Angus Maddiso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Communist Command Economy: An Assesment of the CIA Estimates for USSR”,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8, Vol.44, No.3, pp.307-323.事实上,对于统计数据虚高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学者和官员是承认的。1987 年7 月17 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根本改善国家统计工作的措施》的决定,强调“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制杠杆开展反虚报和瞒报的斗争”,“对虚报瞒报及其他歪曲国家报表行为的责任者追究纪律上、物质上、刑事上的责任”。①王毓贤:“苏联成立国家统计委员会”,《经济与管理研究》,1988 年第1 期,第62 页。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的认知相符,在于始终相信苏共对苏联军队牢靠的掌控力,始终相信军队是苏联政权最后的守护者,过滤掉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杜克大学教授杰里·霍夫1992 年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战略界在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认知相符的严重程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军方会让苏联解体,甚至没有严重的流血事件。我至今仍然不相信。”他不认为苏联应该崩溃。按照他的认知,只有苏联军队先行崩溃,或者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苏联才会崩溃。他认为军队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最令人费解的因素。②Brian D. Taylor, Po litics and the Russian Army Ci vil-Military Relations, 1 689-200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06-208.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裁军之后,美国战略界密切关注军方的反应,就苏共对军队的掌控力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认为,苏联军队服从文官统治,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会影响国家政治进程,苏共牢牢掌控着苏联的军事决策权。然而,苏联国内对军事政变的担忧情绪,以及在“8·19”事件中执行控制叶利钦支持者的军事人员,其不作为甚至倒戈,都说明苏联军队并非政治家的“牵线木偶”。在综合考虑法律传统、政治风险之后,相当数量的军人在“8·19”事件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苏联军队事实上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多次违法、违背传统地使用军队充当灭火器,事后又推卸责任,戈尔巴乔夫与军队的关系走向破裂,军政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战略界对苏共掌控军队能力的高估、对苏联军队自主性的低估,使得他们始终将苏联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视作苏共保存苏联的政治资本。
(一)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的固有判断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军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军事安全和民生经济之间寻找平衡,并为内部改革营造缓和的外部环境。在“黄油与大炮”的困境之下,苏联的海外利益迅速收缩,相继从阿富汗和蒙古国撤军,武力不再被作为首要的冲突解决手段。在美苏缓和的大氛围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裁撤,并逐年缩减军费和军备生产,资源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源分配上,苏联舍弃了传统的“最坏情况假定”(Worst-Case),转向“合理充足论”(Reasonable Sufficiency)、“防卫性国防”,试图降低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①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 Current History, 1989, Vol.88, No.540, pp.337- 353.在人员方面,苏联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人员调动和裁减。1988 年12 月7 日,戈尔巴乔夫在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冷战结束,并宣布单方面裁减军队人数50 万。②殷卫国:“对苏联亚洲裁军的初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 年第9 期,第45-47 页。中高层军官同样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减,据估计,将近1400 位将军被裁,11000位上校及以上军衔的军官被裁。高层军官中,15 位国防委员会成员(共17位)、15 个军区司令(共16 位)被替换。被替换的军队高层人员中,只有少数被调任新职,多数失去职位,从此隐退。③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to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s Subcommittee of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The Soviet Economy in 1988: Gorbachev Changes Course”, April 1989, DDB-1900-155-89, p.15, https://www.cia. gov/library/ readingroom/docs/DOC_0000292349.pdf如此大范围地替换军队高层人员,这在前戈尔巴乔夫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自公开化政策实行以来,不仅党和政府受到了猛烈攻击,军队亦未能幸免,被冠以“腐败之军”的名号。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愤怒谴责媒体“错误地使用公开化原则来诋毁军队”,陆军大将利济切夫愤慨地指责“鼓动者只看到黑暗面,诋毁军队和军人,损害军队在民众中的声誉”。④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89, https://www.rand.org/pubs/notes/N2771.html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计划、军费缩减以及声誉损失,苏联军队的利益受到了从上至下的严重损害。美国战略界对此非常敏感,密切关注军队高层人员的动向和表态,预测苏联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考量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布朗大学对外政策发展中心研究员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发现,没有高级将领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和实行裁军计划之后公开表示反对,亚佐夫甚至声称裁军计划“得到了军队的允许”,“经过了深思熟虑”。①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克莱默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全面掌控苏联国防议程的体现。由此,他做出判断:苏联不可能发生军事政变,长久以来共产党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政治领导,军队根本不构成实际意义上的威胁,军界甚至无法达成统一共识。美国前国务卿、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认为,苏联军人不会卷入政治斗争,而是服从于政治。她引用朱可夫元帅的例子来说明苏联军方的政治态度:朱可夫元帅——苏联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所遭遇的不公且悲惨的经历,时时刻刻提醒着苏联的高级将领:卷入政治斗争者,不得善终。现有制约手段足以把军方势力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共产党稳握最后王牌,随时可以把野心勃勃的军人清出场。因此,当政治家对军方意见不予理睬的时候,军队别无他法,只能咕哝抱怨而已。②Condoleezza Rice, “The Party, the Military, and Decision Auth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1987, Vol.40, No.1, pp.55-81.兰德公司研究员爱德华·华纳(Edward L. Warner)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毋庸置疑: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但军队的强大并没有提高军方在苏联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对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撤换则清楚地说明,他对军队享有绝对控制力。从建国之日起,苏联军队就在共产党严密的政治领导之下,这一点至今没有变化。③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队是否会在大规模裁撤之后发动军事政变的判断,本质上探讨的是苏联的军政关系、决策机制,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队的掌控能力。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做出了正面评价,认为苏联军队实现了政治中立化,服从于文官统治,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换言之,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牢牢掌控着苏联军事决策权,其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毋庸置疑,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与美国战略界认知不符的真实苏联军政关系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状况的误判,在于高估了戈氏领导的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
首先,苏联军事政变并非没有可能。相较于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局势的乐观情绪,苏联国内的气氛显得紧张许多。在1989 年最高苏维埃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几位代表提议该委员会应该完全由文官组成,将现有的军方人员排除在外,以确保“军队或克格勃永远无法发动军事政变”。亚佐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道,“我们的国家是否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亚佐夫当即否认,说“绝无可能”。①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以上例子均表明苏联国内对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有很强的担忧,当自身利益受损时,苏联军方并不像表面上那般平静顺从,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和政治稳定的判断过于乐观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在“8·19”事件中许多被派去镇压叶利钦支持者的军方人员都临阵倒戈。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犹豫踌躇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围攻白宫时,负责执行任务的军官却拒不听从亚佐夫的命令。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门口搭起防护栏,自发保卫白宫。②王国杰:“‘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1 期,第43-52 页。面对这一形势,被派去打头阵的空降兵师长列别德认定“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这个罪责”;卡尔普辛将军负责这次围剿行动,当部下表示“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我们将拒绝执行”时,他默许并表态“我不准备参加行动”。③[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206 页。军令无人执行,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了了之,亚佐夫最终只能下令撤军,以武力挽救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用亲历苏联解体的中国原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杨恕的话说,“不开枪,就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④张鹏:“试析军队为何未能挽救苏联”,《理论与当代》,2014 年第11 期,第27页。
党和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力并非外界以为的那般严密,苏联军队在“8·19”事件中的不作为甚至倒戈说明了这一点。戈氏因何失去了军队?
首先,卷入政治斗争不符合苏联宪法对苏军行动范围的限制。苏联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保卫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就与和平劳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建立苏联武装力量,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苏联武装力量对人民的职责是可靠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经常保持战斗准备以保证立即反击任何侵略者。总之,苏联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外御强敌,而非在国内维稳、镇压起义。这就意味着,从法律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其实无权调动军队来镇压国内叛乱、维持政治稳定。传统的军事教育也强调军队负有守卫人民的光荣职责,将枪口对准民众、造成流血冲突更是有损军队的荣誉。①Julian Copper, “The Military and High Education in the USS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9, Vol.502, No.1, pp.108-119.
另外,戈尔巴乔夫多次将流血事件的责任推到军队头上,造成关系破裂。尽管苏联宪法对苏军行动范围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军队经常被用作灭火器,前往各地镇压政变和起义:1986 年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1989 年4 月的第比利斯事件、1990 年1 月的巴库事件、1991 年1月的波罗的海事件。②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第260 页。在这些事件中,均有军队出动,且造成人员伤亡。频繁的军队调动和流血事件,不仅有违苏联宪法对军队使用的限制,也严重破坏了苏联军人的荣誉感。更加严重的是,每每发生流血事件,戈尔巴乔夫都将责任推到军队头上。事实上,在以上每次事件中,戈尔巴乔夫都亲自批准了进行军队部署的决议,但他的命令总是含糊其辞:不要造成对抗局面,忽视抗议中的过火行为,重点是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他给自己留了充足的余地,一旦镇压失败或发生流血事件,从未承担过责任,而是默许人民代表大会对军队高层进行质询,放任新闻报刊对军队进行口诛笔伐。③刘振:“苏联军队的心理是怎样崩溃的?——从群体视角看苏军的瓦解”,《社会心理科学》,2010 年第11-12 期,第51-56 页。开赴加盟共和国进行武力镇压,本就不合宪法,也有违苏联的传统军事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推卸责任,更使得军队对其彻底失望。1989 年的第比利斯事件,被视为“军队信任丧失的分水岭”。④刘向文:“苏军的非政治化与苏共的崩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 年第2期,第46-49 页。在此次事件中,军队武力驱散示威群众造成了重大伤亡,国内外舆论哗然,要求严惩凶手。戈尔巴乔夫选择高级军官罗季奥诺夫作替罪羊,当即解除了他的职务。①左凤荣:“第比利斯事件的前因后果”,《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 年第4期,第122-127 页。罗季奥诺夫是南高加索地区的军区司令,在军中声望甚高,戈尔巴乔夫推卸责任的行为引起军队的极大愤慨,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十分失望地说:“这是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②张鹏:“试析军队为何未能挽救苏联”。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认知相符产生的原因
美国战略界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苏联军队的异动,以致对苏联的军政关系做出误判?本文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忽视单元主体属性。美国战略界之所以认为军队可以成为保卫苏联的最后底牌、能在最后关头镇压挑战者、保障苏联的政体安全,是因忽视了苏联军队在对国内起义进行武力镇压时所承担的法律风险。③[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766 页。然而,如果政治学家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独立的国家单元,而宪法法律、军队传统、军政关系,均是国家单元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进而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
第二,忽视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角色。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处理与军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逃避和推卸责任,深受其过往经历与价值观的影响。费尔班克斯(Edward H. Fairbanks)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军事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④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利加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被开明君主的光环所吸引”。⑤[苏]叶戈尔·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王廷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04 页。作为一个颇具新貌的苏联领导人,戈氏成了西方媒体的宠儿,所到之处鲜花掌声不断,收获各类奖项和荣誉。⑥包括1990 年1 月戈尔巴乔夫获评《时代周刊》“十年风云人物”,同年10 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醉心外交成就的直接后果,是将外交日程置于国内问题之上,关心国际评价甚于国内舆论。在苏共二十八大上,阿尔泰边疆区区委书记在发言时呼吁总书记埋头国内事务,少到国外周游。更严重的是,在西方受到的赞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亦是一种牵制,维护自身和平声誉的个人需求,是他在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极力推卸责任的重要原因。
总之,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存在严重的认知相符,充分相信苏联军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令行禁止的统一整体,是苏联政权最后的守护者。这种认知相符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苏联宪法关于苏军行动范围的限制、苏联军人不针对平民的信念、戈尔巴乔夫与军队关系的破裂等政治规制与现实,缺乏足够系统的了解。因此,他们始终将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视作拱卫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本。①John W. R. Lepingwell, “Sovie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August Coup”, World Politics, 1992, Vol.44, Issue 4, pp.539-552.戈尔巴乔夫经常被颂扬或被指责“未使用军队镇压挑战者”②左凤荣:“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12 期,第22-24 页。,殊不知宪法并未赋予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权力。“未使用军队镇压挑战者”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仁慈,也不是他的政治失误,而是法律、传统、情势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由于多次违法、违背传统地使用军队充当“灭火器”,事后又推卸责任,军队早已经对政权高层失去信任。苏联军队并不能、也不愿挽救苏联的存在。这并非像美国战略界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所言的,“苏联军队未竭尽全力挽救政权,主要是由其高度的职业精神决定的”。③John W. R. Lepingwell, “Sovie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August Coup”, pp.564- 572.对以上事实的忽略,使美国战略界无法想象包括手握兵权的国防部长在内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何会败给无一兵一卒的叶利钦。
四、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外交最严重的认知相符,在于将东欧国家视作苏联沉重且危险的负担,而东欧和平剧变则是苏联的一种解脱。诚然,以上判断并非没有依据,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美苏关系的缓和,让东欧国家作为苏联安全和意识形态屏障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又让以往的安全地带变成了潜在的祸乱发源地,苏联对东欧共产党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让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东欧之于苏联,可谓地位下降,而维系成本骤升。
然而,这种认知相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进行精明的收益-成本分析时,忽视了东欧政治剧变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东欧政治进程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的“影响循环流”(circular flow of influence)①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转引自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7 期,第57-75 页。,以及东欧成功脱离苏东集团对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鼓舞作用,未能预见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和分离主义将被催化加速,最终也未能成功预测苏联因此解体的可能性。
(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
若以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东欧剧变的历史,八个国家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几乎没有流血冲突,实在是一大幸事。
但对苏联而言,后来的局势证明:拱手出让东欧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东欧剧变吹响了苏联解体的前哨。
其一,东欧剧变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苏联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意识形态是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②[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 页。而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需要被证明、可能被证伪的。当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无法为社会经济提供有力支持,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吸引力时,苏联模式就被证伪了。③[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09页。东欧各国脱离苏联、重归欧洲的强烈愿望,固然受与苏关系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是对苏联模式的失望所致。但细观剧变,可总结为“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与苏联体制下的“一党执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大家庭”几乎完全对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东欧的政治进程仍是一场意识形态抉择,是对苏联模式的极大否定。④郑智超:“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与苏联模式化的东欧——东欧剧变根源的历史再考察”,《社会科学动态》,2019 年第1 期,第13-20 页。
其二,东欧剧变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存在“影响循环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推行的“新思维”实践,对东欧国家剧变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他的自由化政策对欧洲共产主义政权覆灭的时间和节奏至关重要。①例如,1989 年5 月,戈尔巴乔夫在布加勒斯特演讲中鼓励罗马尼亚人走上苏联已开始落实的民主化道路,几个月后的12 月25 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 年2月26 日,戈尔巴乔夫答应捷克斯洛伐克新当选的非共产党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要求,加速苏军的撤离。这导致该国全面的去苏联化。几天之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与其共同宣布“只有德国人民有权决定是否想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参见[美]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20-221 页。东欧剧变也同样鼓励了苏联国内的改革派。马克·克莱默曾发表三篇系列文章说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认为东欧与苏联的改革具有“双向引导效应”:东欧国家最初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引导,在苏联的允许、指引、鼓励下探索改革;但在后期,引导方向发生了调转,东欧“以一种示范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苏联走向解体”。②Mark Kramer, “The 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the Repercus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Part 1)”,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Vol.5, No.4, pp.178-256.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则以“影响循环流”来形容东欧改革浪潮向苏联的回流。③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转引自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第57-75 页。在东欧如火如荼的改革事业影响下,改革气氛笼罩整个苏东集团,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派受到鼓舞,传统派则成为不合时宜的守旧势力。失去传统力量的牵绊,也意味着失去传统政治智慧的约束和谨慎审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呈现出急躁轻率的势头。从政治技术上说,改革从来都是一项高度精密且危险的事业,急躁和轻率向来是改革大忌,频繁且大量地调换高级官员、撤销重组政治机构,必然会影响政治运作的稳定和效率。
其三,东欧剧变鼓舞了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处理东欧事务的基本原则是“不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此外,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强调“民族自决权”,例如在两德统一前声明“德国人有权决定他们本民族的命运”。④“戈尔巴乔夫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件: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1986 年6 月28 日。转引自崔海智:“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 年第2 期,第385-410 页。这一温和的处理方式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让他们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不会用武力镇压自己的分离行动,甚至会理解他们的分离诉求。受此影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几乎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同步展开,从1990 年开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 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将苏联官员驱逐出境。①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1期,第85-90 页。作为苏联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俄罗斯的独立事实上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总之,苏联的解体,首先源于其帝国外部的叛离。因为东欧国家的政治进程是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苏联造成极大挫伤。在实践层面,东欧的改革浪潮向苏联回流,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东欧国家的和平分离,则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均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东欧剧变是苏联解体的前哨战。②Johnson M Sesa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https://www.academia.edu/11257342/The_Collapse_of_Communism_in_Eastern_Europe_and_the_Soviet_Union
(二)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的误判
东欧剧变给苏联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对于苏联自身而言十分隐蔽。在剧变的酝酿和进行之时,苏联高层并没有意识到东欧政治进程的示范效应和鼓动作用,而是以“甩包袱”般轻快的心情默许并支持这一系列变革。对于美国来说,东欧剧变给苏联带来的种种微妙反应,更难以察觉。美国战略界并未预见到东欧会如此迅速地、出现如此规模的剧变。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网站上,至今仍保留着关于东欧剧变的这样表述:当1987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乐观地呼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时,也未曾想到两年后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③“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1989”,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89-1992/fall-of-communism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内,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直到2000年后,这一问题才引起了重视。④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与苏联的“甩包袱”心理类似,美国也认为东欧对于苏联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东欧剧变对苏联来说有利而无害。⑤Johnson M Sesa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美国战略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有所下降。美国战略界存在的一种固有观点认为,二战之后,斯大林在苏联西部构筑起缓冲地带,将东欧国家变为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屏障区域,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①郭春生:“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2 期,第64-69 页。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领土的战略地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当苏联对东欧进行取舍选择之时,其成本收益分析已经发生显著变化。②高歌:“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3 期,第5-25 页。此外,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力促缓和,而非对抗。冷战与苏联解体并不等同,欧美学者认为,美苏两极对抗的历史在1986 年雷克雅未克会晤或1987 年华盛顿会晤之后便已结束。③[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第314 页。苏联不再同美国展开竞赛和对抗,更多地强调合作,甚至向美国请求援助以支持其国内的改革事业。如果中心地带无意开战,对抗的前沿阵地也就失去了战略意义。莫戈莫洛夫向苏共中央所提的建议清晰地说明了苏联对东欧战略地位的新定义:中东欧国家只需成为苏联“西部边界地带存在的友好国家”,而非“缓冲国”或“免疫地带”。④“莫戈莫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新构想”,1990 年1月。转引自崔海智:“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 年第2 期,第385-410 页。
另一方面,政治动乱使东欧从安全屏障变为祸乱发源地。当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面临反对派和群众的挑战时,苏联便成为它们求助的对象。执政当局寄希望于苏联,希望苏联能够动用驻扎在当地的军队来帮助他们镇压游行示威,甚至清剿反对派,一如它过去所做的那样。⑤郭洁:“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 年第9期,第41-53 页。然而,彼时已不同于往日,且不论东欧之于苏联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东欧政治动乱所涉及的范围已然不同:以往的政治动乱属于偶发事件,在单个国家零星爆发,而1989 年前后的政治动乱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在东欧八国均有发生。可以说,东欧已经从苏联的安全屏障,变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如果苏联进行干预,就只能把军队如同救火队一样派去各地灭火。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强力措施的巨大成本。在戈尔巴乔夫急于修复与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武力镇压所带来的成本更是难以承受的。①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 期,第45-76 页。正如莫戈莫洛夫所指出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动荡使得“以前的安全地带”变成了“不稳定的地带”“潜在的危险源泉”;而中东欧共产党政权希望苏联出兵镇压,这种潜在的维稳义务与苏联的缓和政策背道而驰。②“莫戈莫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新构想”。
作为与苏联缠斗了数十年的对手,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布局和考量了如指掌,能够感知东欧之于苏联的战略地位下降、而维系成本攀升,因此同苏联高层一样,将东欧视作“包袱”和“火药桶”,认为东欧的和平剧变对苏联而言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解脱。美国战略界从而忽视了东欧政治进程的示范效应和鼓动作用,未能预见到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和分离主义将被催化加速,进而导致苏联的解体。
(三)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产生误判的原因
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忽视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拱手让出东欧的行为,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他将新思维应用于苏联的外交中,认为全人类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间竞争应该让位于全人类利益。③Peter Zwick, “New Thinking and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89, Vol.22, Issue 2, pp.215-224.上述思想被赞为国际主义,也被贬为空想主义。赞誉者列举戈尔巴乔夫为推动冷战终结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1990 年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批评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为苏联解体负责。例如,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认为,“如果我们要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④[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766 页。维护自身和平声誉的个人需求,是否会影响他的东欧政策?允许东欧和平剧变,或许并非出自对民族自决权的尊重,而是爱惜羽毛使然。无论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是出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⑤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政治与道德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8 年第4期,第42-46 页。,抑或“对自身声誉的渴求”①[苏]叶戈尔·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04 页。,东欧剧变都是苏联解体的第一声丧钟,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敲响。对戈尔巴乔夫个人角色的忽视,使美国战略界无法理解苏联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所做出的反应。
其二,选择性漠视东欧剧变的影响力。从现有的关于东欧剧变的研究分析,苏联在放弃东欧时尚未充分认识到东欧剧变会助推苏联的解体。美国战略界也有一种与此相关的认知:既然苏联对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所负的“道义责任”正在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那么戈尔巴乔夫放弃东欧就是客观上为苏联帝国减负;如果过多推演东欧剧变是苏联帝国外部崩溃的起点这一显见的事实,那么将诱使苏联重拾对东欧的控制;②Rey Koslowski, Friedrich V. Kratochwil,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48, Issue 2, pp.215-247.仅仅专注于东欧剧变后的“民主化”“市场化”和“西化”,就已经完全契合美国的利益与期待。这让美国忽视了苏东关系破裂对苏联政体安全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陷入将有大批国家加入“第四波民主浪潮”③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 e World: Perestrokia in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18. 转引自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3 期,第87-99 页。的盲目乐观之中。东欧演化方向符合理论期待所导致的盲目乐观,是美国战略界在东欧问题上产生认知相符的重要原因。
五、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苏联解体以来,当人们试图总结这一庞大帝国轰然坍塌的原因时,经济崩溃、民族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美国的石油价格阻击导致苏联经济崩溃,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等等,都是经常被列举的原因。④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Policy, 2011, Vol.187, pp.64-70.经济困难和民族问题固然是苏联后期的顽疾所在,也是最终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然而,近些年来,意识形态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①如[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I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p.64-70; Francis Fukuyama, “The Modernizing Imperative: The USSR as an Ordinary Count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p.10-18; 薛小荣、邬沈青:“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 年第1 期,第74-81 页;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政治学研究》,2010 年第3 期,第16-25 页;郭艳:“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4 期,第80-84 页。意识形态这一隐蔽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反思苏联解体原因时容易被忽视。当国家尚存之时,要准确识别意识形态的崩坏程度及其对国家肌理造成的腐蚀,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苏联末期百病丛生,经济、民生、民族、军事等显性问题不断浮现,美国战略界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隐蔽性。意识形态问题固然难以察觉,但在苏联解体前,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迹象,例如新闻审查制度的放松,以及报刊新闻对政府的公开批评。②贾乐蓉:“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的变迁——从改革工具到‘第四权力’”,《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 年第5 期,第53-66 页。美国战略界并非没有看到这些变化,但却对其作选择性的解释,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新举措,对苏联政体而言是一种危险尝试,但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下,则是朝着“新闻自由”前进。当苏联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与美国战略界既有的认识贴合之后,即形成了如此“离奇”的认知相符:对美国战略界而言,苏联的意识形态动向非但不构成问题,不会带来崩溃,反而是增强苏联活力的一个变化。
(一)苏联意识形态衰退的事实
苏联意识形态的衰退开始于什么时候?列宁之后的每任领导人也许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斯大林极致的个人独裁和残酷的政治清洗,让共产主义蒙上一层血腥的恐怖色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破坏了党的权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③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衰退,则让“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水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期待无法实现,人们开始怀疑共产主义作为历史发展必然方向的论断是否成立。①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世界知识》,2012 年第4期,第69 页。然而,对意识形态造成最直接严重冲击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将“新思维”转化为新政策实践方面,遇到了内部政治抵抗、系统性惯性和意识形态障碍;而且“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新思维,在国际上广受怀疑。戈尔巴乔夫必须通过苏联的国家行为,使西方世界相信新思维不仅仅是声明性政策,而是可以落地的实践政策,同时还必须使苏共党内同志也认同新思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致。②Peter Zwick, “New Thinking and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首先,戈尔巴乔夫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苏联的每位领导人都有一位可长期依靠的意识形态主管,例如勃列日涅夫拥有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列宁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③李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 年1 月,第139-143 页。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的依靠,1985-1991 年间,他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叶戈尔·利加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先后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的直接后果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政策极不稳定,而舆论和人心一旦被搅乱则很难平复。
其次,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原则”应用于舆论管理。戈尔巴乔夫的第二任意识形态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改革的头脑”,属于共产党内“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开性”和“民主性”最主要的导演者。④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第87 页。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进改革,雅科夫列夫甚至被称为“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⑤孙铭:“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红旗文稿》,2014 年第11 期,第35-36 页。担任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之后,雅科夫列夫挑选了一批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各个重要新闻媒介任职,舆论氛围突然“宽松”,攻击社会主义、攻击联盟成为时髦。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本身,对苏联意识形态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共产党的政治自杀来实现苏联的政治民主:1988 年宣布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取代政治局,作为苏联政治生活的中心,一党制开始动摇。①吴大英、任允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和补充的法律”,《环球法律评论》,1989 年第2 期,第59-66 页。1990 年3 月,修改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而是变成众多政党中的普通一员,通过“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就此终结。②伍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环球法律评论》,1990 年第3 期,第56-62 页。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治自杀行为,是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最大否定。③门洪华、肖晞:“国际战略惯性与苏联的命运(1979-1989)”,《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6 期,第184-192 页。
意识形态对苏联政权稳定究竟有多大作用?意识形态的崩溃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多大影响?2011 年,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部主任列昂·阿伦(Leon Aron)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发表题为“关于苏联解体:你以为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一文,探究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④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作者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场“思想和道德追求”,认为这场改革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改革掀起了整个社会对国家历史的批判、冲破道德虚伪的浪潮;这种批判和精神追求,使得苏联的存在变得“不道德”,最后在人人厌弃中悄然消亡。
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尤尔查克(Alexei Yurchak)曾对20 世纪50-70 年代出生的苏联人进行专访,问他们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他发现,苏联人都知道几十年来苏联政府进行的宣传有多么荒谬,于是培养出两套意识形态,一套是显性意识形态,习惯性地拥护党和共产主义;一套是隐形意识形态,对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及一党执政心怀不满。⑤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I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当戈尔巴乔夫和众多政府喉舌开始提倡民主、公开、选举、无记名投票之后,民众的隐形意识形态就彻底翻涌而出,对党和政府多年的积怨集体爆发,党的合法性岌岌可危。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回顾“8·19”事件的事发始末,并反思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麦德维杰夫是苏联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亦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同时投身政界,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具有通畅的信息渠道。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衰败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因为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治合法性的全部来源,苏联的建立不是依靠民族纽带、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或者宗教思想,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心脏,正统思想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联大厦必然要倒塌。①[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 页。
(二)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问题的固有判断
回看美国战略界的苏联研究,经济和民族问题始终是关注焦点。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政治改革目标之初,苏联的报纸杂志开始公开批评政府,诸多政治家公开宣布退党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却始终没有注意到这场毅然决然的政治倒戈背后,蕴藏着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向,也未曾意识到对于苏联这样一个依靠意识形态立命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崩溃有何致命影响。
首先,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问题的忽略。自1985 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频频有大动作、大变化。苏联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让美国这个缠斗了数十年的老对手错愕不已,吸引了战略界人士的注意力。纵览此期间的学术论文、智库报告、政府文件,或有担忧苏联命运者,但大多从经济和民族问题出发,期待经济崩溃导致的民怨沸腾、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终结苏联。在这些显性议题面前,意识形态因素过于隐蔽,难以引起关注。②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意识形态的衰落是一种慢性疾病,它起作用的方式是让民众对国家逐渐失去信心,但不会导致其猝死。③Ronald H. Linden, “Reflections on 1989-and After”,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9, Vol.56, No.5, pp.3-10.苏联意识形态走向衰落、失去吸引力,也许能够令美国战略界确信苏联终有一天会解体,但无法预测会在1991 年。
诚然,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完全被忽视,苏联突然活跃的政论氛围的确引起了部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观察人士无法将“言论自由”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反而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苏联的这一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并非全然没有注意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新动向,但由于这一新变化与其信奉的价值观——公开、自由、民主——完全相符,与其所期待的“和平演变”也基本契合,因此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①[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 页。这一基本事实,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如此一来,即使有识之士观察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松动,也难以预见这一问题的灾难性后果。②Sajjad Ali Kha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fall of a state or the fall of an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008, Vol.5, Issue 2, pp.81-99.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产生误判的原因
苏联是一个依靠共产主义信仰建立起来的国家,民众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党国精英的政治忠诚的合法性皆源于意识形态。美国战略界之所以会忽略和误读这一重大现象,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对“软因素”的忽视。意识形态问题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加上苏联时值多事之秋,意识形态的衰落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经济、军事等可量化因素,而忽视意识形态等难以量化的“软因素”,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康纳(W. R. Connor)所言,西方的苏联学家所依赖的分析视角太过局限,他们总是着眼于可量化的因素(Quantifiables),例如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农业产值等。这种模式化的研究,忽略了苏联社会以及东欧国家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民众的民族情绪,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渴望,或对当局的不满情绪,认为政府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这些因素被认为“太软”(Soft)、“不够科学”(Unscientific),而被选择性地屏蔽和忽略。③W. R. Connor, “Why Were We Surprised?” pp.175-184.
其二,美国战略界犯了“由己推人”的错误。美国战略界未能认识到苏联意识形态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苏联的社会状态做出误判,也是因为这种变化符合美国的期待,由此产生认知相符。在苏联解体前夕,意识形态衰退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迹象,美国战略界看到了这些变化,但却不以为意,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战略界忽视了苏联是一个“现代”的后帝国主义国家,而保持后帝国状态的“水泥”就是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讲等级和纪律的政党、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以及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20 世纪80 年代,这种“水泥”开始崩溃。①Chaim Shinar,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European Review, 2013, Vol.21, Issue 1, pp.56-69.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新举措,对苏联政体而言是一种危险尝试,但美国战略界在对其判断中产生了基于本国价值体系的认知相符,认为这是朝着“新闻自由”前进,是增强活力的体现。美国战略界当时尚无法将“言论自由”“取消书报审查”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六、结语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的认知相符,呈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
在经济方面,苏联经济于20 世纪70 年代达到峰值,从此之后陷入漫长的停滞。美国经济学家意识到苏联经济增速的放缓,但将其与“苏联经济发展整体向好”的固有认知挂钩,对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在军事方面,借用技术情报手段,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事实力有准确和翔实的认知。但对于苏联的军政关系,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与军队的关系,美国战略界却始终缺乏了解。美国战略界忽视了苏联军政关系的恶化,高估了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队在政治进程中的自主性,认为军队是保卫苏联制度最后的守护者。
在外交方面,美国战略界低估了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将东欧视为苏联的“包袱”,认为东欧剧变事实上帮苏联减轻了负担,是为苏联帝国减负。然而,东欧剧变在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弥漫于苏东阵营的改革氛围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同时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战略界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这一重要事实。意识形态问题本身不易被察觉,苏联末期经济、政治、社会的种种剧变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力,在这些显性议题面前,意识形态因素过于隐蔽而被忽略。即使有人注意到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但也相信这种变化是苏联政府掌控下的变化,意在增加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活力,因为这与西方国家通过“公开”“自由”“民主”保持政治价值活力的做法基本相符,因此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出现了全面的认知相符,这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基于固有思维的研究方法催生认知相符。苏联学界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抽象性而忽略单元主体特性,过于强调科学性而忽略苏联领导人的个人角色。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体系研究,认为国家个性将服从于体系结构。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的误判,就是出自对国家特性的忽略。如果美国战略界的研究者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国家具体的独立单元,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以及戈氏与军队的龃龉,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如果对俄国路标转换陡然性规律有所认识,美国战略界在面对苏联解体时也许不会如此错愕困惑。
其二,苏美互动中的国家信号与传递不畅催生认知相符。苏联政治过程的黑箱特质极大地压缩了外界对于苏联的可观测空间,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且时常有意误导,统计数据的失实给美国战略界评估苏联真实状况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这导致对苏联“宁可高估、不可低估”成为美国战略界普遍持有的心理,因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覆灭要低得多。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尽管苏联疲态尽显,美国仍然把它视为最具实力的对手,无法客观准确地评估其实际状况。加之苏联演化方向符合期待,这一事实也加剧了美国的乐观态度。
其三,在美国的苏联学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缺失,催生了认知相符。当冷战时期的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追求理论的科学性时,意识形态这一“不那么科学的”“软因素”被彻底忽略了,而意识形态崩溃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为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