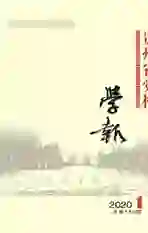程序整合视角下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研究
2020-04-17吕晓刚杨彩虹
吕晓刚 杨彩虹
摘要:国家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使得职务犯罪追诉的事实调查与审查起诉以及对物追诉与对人追诉都面临关系重构。制定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理顺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缺席审判与判决前财产没收适用位序具有理论、立法和实践正当性。通过确定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管辖衔接,完善强制措施适用对接,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强化补充调查协调配合等方面入手,形成调查与起诉有效衔接的案件事实调查追诉程序。通过明确缺席审判适用位阶的优先性,和判决前财产没收实践适用的优先性,确立不到庭审理程序的适用位阶与顺序。
关键词:监察调查;审查起诉;对人追诉;对物追诉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20)01-0101-07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以腐败犯罪为代表的职务犯罪进行有效追诉成为制度改革与立法完善的关注对象。一方面,国家监察法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事实调查主体和程序属性进行了全面重构;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修正构建缺席审判制度,应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然而,由于改革目标与价值定位的差异,导致当前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程序在具体程序衔接与整合方面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与统一之处,需要以改革所确定的关系重构为基础,进行程序整合。通过将职务犯罪追诉所涉及的事实调查、程序适用等特别措施体系加以整体协调,构建内在逻辑清晰,外部衔接顺畅的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体系。
一、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构建的时代语境
(一)改革驱动下的职务犯罪诉讼程序
1.职务犯罪事实调查的属性变迁
国家监察法第11条第2项规定,国家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据此,我国职务犯罪案件查办由检察自侦模式转换为监察调查模式,[1]这一转变不仅表现为职务犯罪调查主体的变更,更重要的是,既往职务犯罪侦诉一体的追诉格局被彻底打破,形成了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异体衔接的职务犯罪案件追诉新局面。从而彻底扭转了此前检察机关垄断职务犯罪侦查与审查起诉所面临的自侦自诉缺乏监督的正当性困局,提高了职务犯罪追诉的法治性和效率性。
职务犯罪调查权的整合,改变了此前被长期诟病的反腐败机构独立性不足问题,[2]而且可以解决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分别调查所存在的衔接黑洞,对于提高职务犯罪的惩戒力度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为确保刑事追诉能够发挥对职务犯罪预防与治理的威慑和处置功能,不仅需要在具体立法和实践层面实现监察调查与后续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而且应当以监察体制改革所形成的职务犯罪治理体系背景下对此类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进行调整。
2.缺席审判制度改革催生的程序竞合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构建解决了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确定难题,可以一并解决对人定罪和对物没收两项目标。相较于仅能“对物”,不能“对人”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无疑更能满足强化反腐败力度的现实需求。虽然缺席审判被告人不参与最终庭审,但是这一程序本质上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需要遵循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和制度规范,因而在如何实现控辩平等对抗,辩护权充分保障等方面面临的挑战要远远高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这一不直接涉及刑事责任确定的非诉讼程序。[3]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的立法体系,作为职务犯罪诉讼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缺席审判制度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同属刑事特别程序体系,二者之间在立法位阶上是平行关系,在适用上不存在先后顺序设定。缺席审判制度与判决前财产没收制度在具体适用对象上各有侧重,并且能够“两翼齐飞”,填补法律漏洞[4],但是二者仍存在明显的竞合空间,对于同时满足缺席审判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适用条件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选择适用程序,以及对于已经被裁定财产没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缺席审判程序获得立法确认后,是否可以对其叠加适用缺席审判,追究其刑事责任等问题都需要予以有效解决。
法治前沿吕晓刚,杨彩虹:程序整合视角下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研究(二)以特别程序作为职务犯罪追诉程序载体的契合性
1.理论正当性
伴隨着诉讼文明程度的提高,为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刑事诉讼程序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这种限制在特定类型犯罪领域则会导致诉讼程序对犯罪的应对能力,尤其是事实查明能力的不足。为应对刑事诉讼程序整体人权保障水平提高和特定类型案件需要强化惩罚力度的冲突,就需要通过制定特别诉讼程序的模式,在普通诉讼程序之外创设一个针对特定类型案件的“隔离区”。在这一空间内,刑事诉讼法可以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点进行适度调整,对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进行适度克减,强化刑事诉讼法对此类犯罪的应对能力。
具体到职务犯罪,尤其是腐败犯罪,作为一种腐蚀公权力廉洁性的犯罪行为,不仅损及国家的公信力,更会对国家社会秩序和公民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为应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资源调动能力和诉讼应对能力较强的特点,需要提升办案机关在办理此类案件时的事实查明能力和抵御外界干扰能力。为保证办案机关的事实调查和证据收集固定满足职务犯罪案件办案需求,除了拓展办案机关权力配置,例如赋予办案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调查权等,还可能对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进行适度的克减;例如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可以进行缺席审判,对被告人的在场权进行限制。职务犯罪刑事追诉作为最有力的惩戒机制,适度强化控诉力量,弱化辩护保障既是现实需要的必要回应,也符合职务犯罪案件诉讼推进的特殊要求。
2.立法可行性
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职务犯罪明确由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明确宣告了这一犯罪类型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地位,彰显了国家对职务犯罪刑事追诉的特别关注。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更是将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分别在侦查期间辩护人会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判决前财产没收等方面进行了特别规定,以实现强化对此类犯罪打击力度的立法初衷。国家监察法的制定以及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则进一步丰富发展了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差异性进行了规范。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缺席审判的具体适用规范等对此类犯罪诉讼流程规范进行了结构性调整,使得既有的刑事诉讼程序难以完全涵盖职务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特别规范,必须为其构建更为独立的立法框架。
3.实践必要性
针对以腐败犯罪为代表的职务犯罪设置专门诉讼程序,实现腐败犯罪打击和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必由之路和应然路径。[5]在职务犯罪事实调查阶段从刑事诉讼程序剥离的背景下,作为审查起诉主体的检察机关需要调整原有职务犯罪案件侦诉一体模式下内部权力配置和办案流程,适应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办案模式下所产生的证据、强制措施、案卷等具体程序事项衔接的实践操作规范需求。在缺席审判制度构建庭审主体结构变革的背景下,作为审判主体的人民法院需要调整既有庭审流程,适应被告人不出庭情形下如何有效进行庭审阶段的举证质证和控辩对抗,发挥好庭审的事实发现能力。
二、关系重构背景下的职务犯罪追诉程序
(一)调查与追诉关系重构
基于职务犯罪追诉的特殊性,对于此类犯罪的事实调查采取同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的权力主体配置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当前主流职务犯罪侦查存在“检察机关配置模式”“警察机关配置模式”“独立反腐败机构配置模式”“检察机关+警察机关配置模式”等四种主流模式。[6]就我国而言,當下职务犯罪调查主体模式经历了由检察机关配置模式到独立反腐败机构配置模式的转变,由于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在机构属性与权力位阶上都与此前承担职务犯罪侦查的检察机关存在本质差异,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职务犯罪事实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所依托的程序属性基础和制度规范框架,需要从程序属性和主体关系两个维度对当前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进行梳理。
1.事实发现与审查起诉流程属性关系重构
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职务犯罪案件侦诉一体权力配置模式,使得此类犯罪的侦查与审查起诉阶段衔接形成了同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异体衔接不同的主体关系。此外,在当时背景下,虽然党的纪检机关和检察机关分别负责党员干部职务违纪与犯罪调查处置、刑事追诉,但由于涉案主体和涉案事实的重叠交叉,使得大部分情况下,职务犯罪都会经历纪检机关纪律调查与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衔接过程。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将原本分散行使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调查和侦查权进行了整合,实现了凝聚反腐败合力的改革目标,对传统的职务犯罪事实调查与审查起诉阶段衔接模式进行了彻底的重构。这种重构一方面改变了既往检察机关自侦自诉的同体内部衔接模式,通过将职务犯罪调查权赋予监察机关,实现了事实调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责任主体间的互相制约;另一方面,通过职务违法与犯罪行为调查权的整合,改变了违纪行为调查与犯罪行为侦查分立的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调查权配置模式,既提高了调查效率,更使得此类行为的事实调查与刑事追诉衔接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由于监察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7]因此,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虽然在流向上同侦查审查起诉并无本质区别,但是在衔接的理论基础和内容程序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2.程序主体关系重构
一方面,当前职务犯罪调查与刑事追诉主体关系既不同于检察机关自侦自诉模式下的内部衔接,也不同于普通刑事案件中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同属刑事诉讼专门机关范畴内的衔接,而是联通国家监察机关与刑事诉讼专门机关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机关。作为政治机关的监察机关无论是主体属性,还是权责配置,都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刑事侦查机关截然不同,因此其与检察机关就职务犯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衔接过程中的关系构建应当充分尊重监察机关的特殊性。此外,对于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主体衔接还应当注意,根据当前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实践,检察机关在调查阶段提前介入也已成为常态。检察机关作为审查起诉主体提前介入到案件事实调查环节,在刑事侦查中已有先例,然而突破刑事司法领域,普遍性介入监察调查领域,就需要在这种同案件程序流向反向的主体衔接中,对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提前介入时的身份定位和职能界定等进行全面梳理与分析。另一方面,作为被追诉对象的涉嫌职务犯罪的行为人,其在事实调查阶段的主体身份,由犯罪嫌疑人转变成为被调查人,这意味着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衔接对其而言,是由被调查人转为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这种转换不仅带来称谓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其权利义务配置会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例如作为被调查人,并无明确的聘请辩护人的权利,而作为犯罪嫌疑人,这一权利是受到刑事诉讼法明确保障的。此外,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过程中,被调查人与犯罪嫌疑人的转换关系还应当关注留置与后续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由被留置人转变成为被羁押人同样需要经历羁押场所和权利义务配置的变化。
(二)对人与对物追诉关系重构
当前我国在被告人不到庭情形下职务犯罪追诉形成了以缺席审判制度为载体的对人追诉机制和以判决前财产没收为载体的对物追诉机制共同作用格局,这对于强化职务犯罪追诉力度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缺席审判程序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二者在适用范围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而且在程序目标上具有极强的互斥性,因此,为避免司法实践适用中的厚此薄彼和无所适从,就必须对缺席审判程序和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之间的适用位阶和边界进行明确界分,重构被告人缺席情形下对人追诉与对物追诉关系。
从程序效果而言,缺席审判程序相较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更为全面,不仅能够对涉案财物进行有效处置,还能够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确定,彻底解决对人和对物追诉两项实践难题。刑事责任的确定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对于刑法所追求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目标的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对于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宣告定罪所承载的刑法否定评价带来的威慑力必然要远超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所形成的财产没收决定。虽然受制于国际公约支撑缺失等因素,缺席审判程序所做出的判决可执行性将会面临巨大挑战,但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一程序的积极价值。通过对潜逃境外职务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宣告,不仅能够对其行为进行正式的法律评价,更能够对其他涉嫌职务犯罪行为人产生威慑作用,并且能够对社会公众要求惩处职务犯罪的诉求进行有效回应。因此,对于满足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依法适用,发挥其相较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更强的威慑力和强制力。
从程序的权利保障性而言,相较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缺席审判程序具有先天“权利侵害性”,虽然可以通过强制辩护等措施为未到庭被告人提供必要的辩护保障,但是在被告人未到庭情形下所进行的审判,被告人的在场权被剥夺,其自行辩护权难以行使,无法形成有效的控辩平等对抗。相对而言,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中,虽然被没收财产人同样不能到庭,无法自行抗辩,但由于这一程序仅针对涉案财产,不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进行追究,因而其“权利侵害”的风险大大降低。
三、程序整合推进职务犯罪刑事特别程序构建
(一)构建调查与起诉有效衔接的追诉程序
1.完善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机制
由于监察调查在程序属性以及具体调查措施上,都与刑事侦查存在差异,因而其对职务犯罪案件事实调查的指导方针和价值定位都与刑事诉讼存在本质差异。例如,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其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调查目标设定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与“全案查明,惩罚犯罪”的刑事偵查目标大相径庭,而根据执纪监督四种形态所确立对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选择也与“罪刑法定,除恶务尽”的刑事侦查理念存在显著区别。这决定了监察机关所调查的案件事实往往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需案件事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倾向。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互相协调,一方面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中,尤其在证据收集、固定环节,需要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满足未来刑事司法程序的标准。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后续的审查起诉和审理阶段,不能简单以刑事诉讼的思维机械衡量监察调查所形成的材料,在证据审查判断、案件事实定性和强制措施衔接等方面都需要兼容监察调查的特有规律。
(1)确定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管辖衔接
由于当前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管辖是按照组织人事管理体制确定的,而审查起诉管辖则是根据刑事管辖制度确定的,二者在地域和级别上存在冲突与矛盾。为保证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衔接的规范有序,就需要对监察调查管辖与审查起诉管辖之间架构明确的衔接进行指引。一是在地域管辖上,为提高衔接效率,便于案件相关证据材料和被调查对象的交接,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地域管辖原则上应当根据监察调查管辖进行确定;二是在级别管辖上,为保证刑事级别管辖体系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不对现行的刑事司法机关办案任务分配机制产生冲击,在与监察机关的对接上,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监察调查向审查起诉移送案件的具体接收检察机关级别。
(2)明确强制措施适用对接
对于已经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径行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并在十日内决定是否逮捕。由于留置场所与羁押场所不一致,因此在案件移送时,监察机关应当同时将被调查人移送至看守所羁押。检察机关也应当主动对接,协助完成收押。对于应当逮捕的,及时决定逮捕,对于不需要逮捕的,则及时变更或者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对于尚未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时应当将被调查人的住址、联系方式等一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接收案件后,应当及时对被移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危险性进行评估,确定是否需要适用以及具体适用何种刑事强制措施。
(3)规范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机制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作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衔接具体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法定职能的衔接协作要求,实现了办案优势与现实需求的有效对接。针对介入过程中协助调查与公诉准备的角色定位冲突,应当在追诉目标统筹下予以平衡。针对当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适用率过高,实施细则不善以及程序救济机制不健全等实践不足,应当构建提前介入案件遴选机制,完善介入流程,赋予被调查人救济权,以提高程序正当性。
2.补充调查协调配合
补充调查作为职务犯罪追诉程序特殊情形下的程序回流,本质上属于监察调查程序,因而补充调查期间应当以国家监察法作为调查活动的法律渊源,调查措施以及被调查人在调查期间的权利义务配置都应当以监察法相关规范为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补充调查发生在刑事诉讼这一制度空间内,而且在补充调查期间刑事诉讼程序,尤其是辩护活动并不因此完全停滞,因此不能将案件正在补充调查作为限制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例如,虽然按照监察法的规定,监察调查期间被采取留置措施的被调查人不能会见律师,按照这一规定,补充调查期间限制律师的会见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以案件可能需要补充调查为理由,在非补充调查期间限制律师会见,这显然超越了补充调查的辐射范围。
(二)确立不到庭审理程序的适用位阶与顺序
1.明确缺席审判适用位阶的优先性
相较于只没收财产不确定刑事责任的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缺席审判程序能够对职务犯罪行为人一并进行刑事责任追究和涉案财物处置,在程序效力上具有显著优势。通过缺席审判,确定刑事责任,一方面具有对外宣示作用,可以对潜逃境外职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通过生效裁判确定其有罪身份,不仅可以明确地发挥法律的评价功能,表明刑法对其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更可以向其隐藏地国家政府宣示职务犯罪行为的罪犯身份,表达我国政府惩治职务犯罪的决心。另一方面具有对内回应作用,通过对外逃职务犯罪行为人的有罪宣告,可以回应社会公众对于职务犯罪的深切关注,回应民众对于因不能到案而无法追究此类行为人刑事责任对刑事司法系统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强化民众对于党和国家深入反腐败的信心和认同。因此,从案件解决的完整性和作用范围的全面性而言,缺席审判程序在效力位阶上要优先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当二者存在适用竞合时,应当以缺席审判优先适用。
2.确定判决前财产没收实践适用的优先性
虽然在效力位阶上具有优先性,但是缺席审判程序相较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在实效性方面存在显著劣势。一方面,由于缺席审判程序是在被告人未到庭情形下所做出的裁判,是以牺牲被告人在场权为代价构建的程序,这造成该程序在正当性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为修正程序所存在的正当性缺陷,缺席审判程序牺牲了裁判的稳定性,规定在程序进行过程中,被告人到案则需要重新审判,程序结束后,被告人到案后对裁判结果表示异议的,亦需要重新进行审判。这不仅会影响个案裁判的权威性,更会损及刑事司法体系的公信力。因此,为避免裁判被随意推翻情形的频繁出现,就需要对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频率进行限制。与之相对应的是,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稳定性则更具优势,不仅裁定结果不会因被告人到案而随意被变更。
另一方面,由于当前所确立缺席审判程序作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制度创设,不能简单地对应到域外缺席审判立法与实践体系中,因而这一程序的裁判结果能够得到域外国家承认和配合执行的可能性极低。这决定了缺席审判程序除了发挥宣示和回应价值外,很难产生引渡、执行等现实效力。而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由于不涉及定罪量刑,在域外各国刑事立法和实践中均存在类似机制,能够得到其认同和认可。并且这一机制受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明确支持,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8]因而,对于判决前财产程序所形成的财产没收裁定,其能够得到认可并协助执行的可能性显然高于缺席审判程序。基于对刑事司法体系权威性和可执行性的考量,在缺席审判与判决前财产没收具体适用存在模糊时应当优先适用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
参考文献:
[1]李奋飞.检察再造论——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转隶为基点[J].政法论坛,2018,36(1):30.
[2]夏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J].法学杂志,2006,27(3):31.
[3]吕晓刚.刑事特别程序辨义[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0(5):32.
[4]樊崇义.腐败犯罪缺席审判程序的立法观察[J].人民法治,2018(13):43.
[5]卞建林.腐败犯罪诉讼程序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2.
[6]王晓霞.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67.
[7]林艺芳.国家监察法应科学界定腐败犯罪调查权[J].红旗文稿,2017(15):16.
[8]张小玲.问题与误读: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质疑[J].政法论坛2006.34(3):156.
Lv Xiaogang,Yang CaihongAbstract: With the enactment of the National Supervision Law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e fact investigation, review and prosecution, as well as the object prosecution and the person prosecution of the duty crime prosecution are fac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It is reasonable in theory,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to formulate special criminal procedures for duty crimes, ration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review and prosecution, and apply the order of trial by default and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before judgment. Through determi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jurisdiction of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review and prosecution,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and connection of compulsory measures, Standardizing the mechanism for procuratorial organs to intervene in supervision and investigation in advan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supplementary investigation,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the case facts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procedure is formed. By making clear the priority of the application rank of trial by default and the priority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onfiscation of property before judgment, the application rank and order of the trial procedure without appearing in court are established.
Key words: Supervisory investigation; Review and prosecution; Prosecution of people; Prosecution of objects
責任编辑:王廷国 李慧 孔九莉 李祖杰 邓卫红 刘遗伦 余爽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