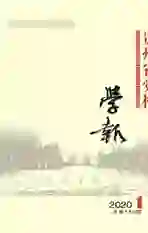罪数论的诉讼客体维度解析
2020-04-17张淼
摘要:罪数论本身是复杂的抽象规定和理论总结,而罪数论适用则是将罪数形态适用到具体“事实”之上。罪数理论与罪数论适用理论的差异非常明显,罪数论注重于罪数形态的构造与分析,而罪数论的适用理论则注重于将具体罪数形态适用于客观事实之上。实体法中的罪数论通过对各罪数形态内在的复杂结构性特征进行揭示来探寻具体的处断结果,在将具体罪数形态付诸刑事诉讼时,罪数形态的诉讼客体与单纯一罪的诉讼客体存在明显差异。不宜将具体罪数形态的内在结构与特征作为大前提进行适用,应将罪数形态进行“立体化”的解析,从诉讼客体同一性与单一性的角度对罪数论的诉讼客体进行立体化构建,同时也需要注意规范设定的具体要求。
关键词:罪数论;诉讼客体;单一性;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20)01-0094-07
罪数论以处罚不典型的复杂犯罪事实为其目标,也正是因为在既有的犯罪构成与复杂待决案件事实之间缺乏严密的“对应关系”,才需要从基本犯罪构成出发并结合惩罚之理念探寻具体的处断后果,从而实现实质合理惩罚。实体法上的探讨也必然会延伸到程序法之中,进一步说,解决程序法的问题与实体法的问题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宁可说在同一的法体系中,应将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结合来讨论。然而,实体法在实体法中,程序法在程序法中,均具有其固有的意义与机能。[1]211为了从程序上对复杂案件事实进行评价与处断,就需要从罪数论的内在结构出发,以刑事诉讼的视角“生成”具体罪数形态的诉讼客体。
一、罪数论的概念用语及外延扩张
所谓罪数,就是犯罪的单复或个数。从形式上看,罪数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至多只有算术学上的意义。在罪刑法定主义下,罪数取决于法定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后果,因为解构的工具受到严格限定,这就使得“解构工具”与“被解构对象”的外延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对应关系。一般来说,就“刑法”分则的各个条文规定而言,立法者并没有去设想,如果行为人除了构成此一罪名之外,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应该要如何同時处理两个(或几个)罪的问题。[2]正是因为这种对应关系的复杂状态,罪数论因此被称之为“刑法学的暗黑之章”,也使得原本作为简单的犯罪计数之学的罪数论,扩展为研究犯罪在实质上与形式上、实质上与法律上、实质上与处理上的犯罪个数的理论。[3]虽然罪数论是刑法理论与实践中颇为棘手的问题,但经过不断的积累与反思,我国刑法教义学上的基本框架和具体形态等主要内容也基本上得以确立。虽然在具体称谓等细节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但大多数教科书都采用了本质一罪、法定一罪和处断一罪的整体框架。[4]而且,从教义学的体系地位来看,现今的通说均将罪数论置于犯罪论之中,将其视为犯罪构成的具体运用。
严格来说,我国刑法教义学中罪数论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内容。从历史维度来考察,会发现不仅“罪数论”用语经历了演进与变更的历程,而且在具体的体系地位方面也出现过根本性的变化。就用语表述来说,由于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在刑法总则中进行规范表述,所以都只是通过学理概括或者引进域外术语从而得到逐渐推广。由于罪数论自身的体系过于驳杂,在这一时间内以德国刑法理论中的“竞合论”替代我国现有“罪数论”的主张也开始出现并逐渐得到认同。[5]在罪数论发展的早期,由于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术语体系,所以教义学上往往采用了直接描述的方式进行概括和介绍,一般将罪数论的整体结构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为:“一行为刑法上规定为一罪或处理时作为一罪的情况”“数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一罪的情况”和“数行为处理时作为一罪的情况”。[6]当时并没有将其概括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而是将其概括为不同“情况”,足见理论研究之状态尚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在表述上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其后的教义学基本上沿袭了上述的整体结构框架并进行了规范化的构建。严格来说,罪数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经历了从刑罚论到犯罪论的演进过程,80年代初期出版的刑法教材还没有把罪数与数罪并罚分开,80年代后期的刑法教材才在犯罪论中设专章研究罪数问题。[7]罪数论概念用语的驳杂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对其本质以及构成内容方面并无统一的认识,实际上罪数论的外延也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由于在实体法上仍然处于不断探索的状态,尚无明确的结论,因而在诉讼维度中也未给出具体的解决进路。
法治前沿张淼:罪数论的诉讼客体维度解析从法律用语的演进来看,罪数论这一概念术语也经受着不断的挑战与质疑,而且罪数论概念也呈现出放松的态势。放松概念会导致“概念延伸”,由此种概念将能应用于更多个案,但也可能潜在地延伸至面目全非之境地。[8]就罪数论概念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演进与发展来看,也可以将其概括为罪数论外延不断扩张的过程。经过不断的扩张,罪数论就变成了以“不典型形态的综合体”,除了犯罪论中不存在争议的典型的“单一行为”犯罪和刑罚论中明确的“数罪并罚”之外,罪数论将介于二者之间的“非典型样态”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因为刑法理论中罪数论的内在结构被认为存在着严重缺陷,我国刑法学界开始引进了德国刑法中的竞合论,尽管竞合论的研究才刚起步不久,但竞合论的价值已经为人所知,从罪数论向竞合论的转变也在悄然发生。[9]
二、罪数论地位与功能的教义学界定
我国的罪数论实际上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内容,似乎将其概括为犯罪论与刑罚论中特殊形态的结合体更加妥当。总体上来说,刑法总论中的相关内容要么属于刑法学,要么属于犯罪论,要么归入刑罚论,并无所谓的独立于三者之外的情形。对现有的罪数论的三个层级进行深入分析,实质一罪属于犯罪构成中的特殊形态,虽然特征上具有独特的禀赋,但经过深入分析其本质仍然可以得出一罪的结论;而法定一罪的本意是指本来的数罪,基于特定理由或者固有特征而在法律上规定为一罪,二者都属于犯罪论的内容;处断一罪则与犯罪构成无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犯罪人进行处罚的深层次根据和理由,属于刑罚论的内容。[10]由此看来,罪数论的性质似乎无法得以确定。
实际上,前述的分析方法存在明显不足,以横断的方式来分析问题,固然可以将其分成犯罪论与刑罚论,但是以刑法运行的角度来探讨某个特定问题,会发现这种人为的区分似乎仅具有参考价值而已,并无法真正实现其最终目的。罪数本来兼有犯罪与刑罚的双重问题,罪数的确定与刑罚的科处,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不宜也无法将二者绝对分割。[11]从刑法的运行来说,定罪之后就进入到刑事惩罚阶段,并无必要继续进行探讨,但对于特殊的犯罪形态,则需要对定罪后的惩罚后果予以重新确定,从而在本质上实现对其合理惩罚。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对于罪数论的分析就需要从犯罪论的基石范畴出发,同时结合刑罚论的相关内容进行“并合性”的总体研究。
从整体的运行过程来看,罪数论将犯罪构成或者犯罪成立理论作为其前提进行展开;罪数论后启刑罚论中的数罪并罚,亦即为数罪并罚提供适用的空间范围作为目标指向,因而具有较为特殊的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说,前半部分深受犯罪構成和犯罪成立理论的影响,后半部分则需要从更为本质的层次来探寻惩罚的实质合理要求,实际上属于对前半部分强调形式合理主义的悖反,或者说正是因为前半段的形式合理性出现了明显的缺陷,才需要对其不合理之处进行校正。亦因此,从整体上来说罪数论应该属于对犯罪特殊样态的深入剖析。[12]概言之,罪数论既以规范工具为基础,又不受规范工具的限制,需要以实质合理之要求对罪数论的相关内容进行“校准”。
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的罪数论深受日本刑法的影响,日本教义学中的罪数论往往处于犯罪论之最后,同时亦将并合罪,也就是我国刑法中的数罪并罚包括在内,实际上也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复合内容。[13]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罪数论的核心内容都可以概括为行为人犯数个罪时该如何处理,这由以下两个问题组成:一是该行为是一个犯罪还是数个犯罪;二是如果构成数个罪,那么该如何处理。此外,在科以怎样的刑罚才合理这一意义上,其性质可以说是一种刑罚论。[14]从这一维度来说,罪数论就愈加演变为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综合体。实体法维度中的罪数形态,具体的教义学内容包括了“罪数形态的内在结构”,内在结构实际上与犯罪构成一样,都是进行具体适用的前提条件。当然,内在结构需要以标准意义的犯罪构成为基础,重点强调对于标准的犯罪构成的改造与运用,从而探寻具体的处断措施与结论。[15]
将罪数论置于犯罪论之中加以研究和展开,从而丰富了法学三段论大前提的外延,简化了运算与推导过程,不必从基础的“犯罪构成”出发进行重新运算,只需要将罪数形态的内在结构作为分析的工具,然后按照处断方法予以适用即可。此时,只需要探讨诉讼客体是否符合罪数形态的构成要求即可完成性质判断与处断。
三、诉讼客体的内涵界定及展开
就诉讼的原意来说,诉为“告”,讼指“争”,无论是告还是争,均有其对象。而诉讼的核心也就是控诉双方的争议事实与法院的审理事实,亦即诉讼客体。诉讼客体在不同的刑事司法领域中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但从一般意义来说,诉讼客体是指诉讼主体实施诉讼行为所针对的对象,从法院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审判的对象。[16]刑事诉讼客体有时也被俗称为“刑事案件”,即特定被告人被指控的特定犯罪事实,有时亦被称为案件事实、公诉事实和裁判事实。而诉讼客体在最终确认之前,属于观念形态上的犯罪事实,并非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本身。从诉讼过程来看,案件事实从发生到最后得到司法确认的过程中,各种权力因素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而诉讼流程就是指各方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运行过程,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刑事诉讼过程中,不同权力机关的职能范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而也导致了“诉讼客体”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对诉讼客体具有参照作用的是案件事实本身,也就是俗称的案件。一般来说,所谓的“案件”“一个案件”“同一案件”“案件单一”和“案件同一”等问题,绝对不是单纯刑事诉讼法问题,而是刑法理论的“上帝事实”和刑事诉讼法的“认识事实”间的概念落差所形成的问题。由于“认识事实”的“多元性”与“变动性”,才使得“上帝事实”无法在诉讼中完全得以证明,亦因此,纯粹的理论刑法学所热衷的诸多问题也由于在诉讼中无法得到“真正”的证明,愈发显得光怪陆离和不切实际,而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思辨价值而已。
诉讼客体概念的确立具有保障被追诉人与限定诉讼的积极功能,但诉讼客体的外延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一般来说,诉讼客体应该是尚未具有确定结论的“待评价事实”,因而才能够成为诉讼过程中的“客体”。因此,我国刑事诉讼中更多地使用具有中性意义的“事实”一词,而理论上则进一步将其区分为公诉事实和裁判事实等具体分类。经过深入分析,诉讼客体与刑事诉讼中“事实”一词的涵义基本相通,在同一性与单一性方面更是可以相互替换。就用词的准确程度来说,“诉讼客体”显然比“事实”一词更妥当。因为“事实”一词在我国不仅具有特殊含义,而且还同刑事诉讼中其他表述造成了用词混同。
诉讼客体一词包含着“待决”之意,亦即尚未在诉讼中形成性质判断和刑罚处断的结论,而作为“争讼”诉讼客体结论的表现形式则为“罪名”。罪名原本仅仅作为性质判断结论的“代称”出现,但却因为在我国刑事司法之中的特殊作用及功能,从而在罪数论中成为具有决定意义性的要素。因此亦使得原本只应该在判决中作为最后结论出现的罪名,不断侵入到罪数形态的各个层面与维度,不仅出现在性质判断的处断层级之中,同时也出现在内部结构中的解析之上,甚至还出现在概念维度之中。[17]综上,确定诉讼客体的参照维度就不仅仅限定于犯罪构成符合性,而且还应将作为结论的罪名也纳入到考量的范畴。
四、单一性维度中的罪数论诉讼客体分析
诉讼客体具有单一性与同一性的特征,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也提供了分析的维度与解决问题的思路。刑事诉讼客体的单一性就是指从静态的横断面来考察刑事诉讼是否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表征为刑事案件之单纯且不可分割性。从罪数的角度来看,也就是强调诉讼客体内部的组成要素之间以及诉讼客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整体”与“部分”或“一部”与“他部”的关系,不论是整体与部分、一部与他部,都应是“单一事实”之组成部分,具有不可分割性。[18]
诉讼客体的单一性判断取决于被告人的单一性和公诉事实的单一性。被告人单一并且公诉事实单一,也就是一人被指控一罪时,才是单一的刑事案件;而被告人或者公诉事实为数个时,也就是数人被指控同一犯罪、一人被指控数犯罪或者数人被指控数犯罪时,均为数个刑事案件,亦即诉讼客体为复数,而非单一刑事案件。在我国,诉讼客体的数量决定着判决中“结论”的数量,也就是决定着“刑罚后果体系”的数量,形式上表现为宣告刑的数量。一般来说,所谓“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一个诉讼客体”,正好说明了犯罪事实与诉讼客体之间的关联性。在我国,诉讼客体的范围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动,亦即诉讼客体可能出现扩张或者限缩。诉讼客体之所以会出现扩张或者限缩,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存在不同见解,而在于用犯罪构成对犯罪事实进行解构时所形成的不同见解所导致。就诉讼客体确定来说,无法将案件事实等同于诉讼客体,因为案件事实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存在,需要经过思辨逻辑的整理,而且从案件事实的追诉活动一开始,或者从案件事实发生,乃至发生之前,实体法的模型构建以及处罚限定就“先验性”地存在于脑海之中了。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对诉讼客体真实性存在争议,也就是对诉讼客体是否符合刑法规范有着不同见解,才导致了刑事诉讼的发动以及展开。如果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客体本身不存在不同见解的话,那么刑事诉讼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这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核心根据所在。[19]
从刑事案件处理来说,最初呈现在司法者面前的对象“素材”,是没有经过筛选尤其是没有经过法律思维筛选的原始资料。所有的素材并非都和刑法处理有关系,因此就借助经验上的“刑法上有意义的行为”之标准,将一个普通事实“翻译”为刑法上的案件事实。[20]也就是将那些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行为或者要素组合成一个案件事实,从而接受刑法规范的评价。
单纯一罪诉讼客体的确定并无太大问题,因为犯罪事实本身相对简单,在日常生活观念与规范评价上并未出现不同见解,所以就顺理成章地演绎为单一诉讼客体。实际上,我们在运用形式逻辑思维对案件事实进行选择与取舍时,会不自然地运用规范的犯罪构成进行案件事实的初步评价。从某种意义来说,犯罪构成虽然经过系统性的“抽象思维”构建,但其原型仍然来自于生活实践,正是有识之士在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事实”进行反思才得以形成抽象的行为类型分化,也才形成分则中的犯罪构成体系。因此,对于单纯一罪来说,规范与客观事实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鸿沟,所以诉讼客体的确定与评价上都不会存在问题。
以单纯一罪的诉讼客体为基础,对于典型数罪的诉讼客体确定就演变成纯粹的数量计算。对于行为人所实施的各自独立的犯罪,可以通过对每个独立的诉讼客体单独确定的方式来实现对其追诉。当每个诉讼客体均得到确认之后,后面的问题就是数罪并罚所要解决的对象。[21]
相比于单纯一罪与典型数罪,由于具体罪数形态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也使得对于罪数论中各种样态的诉讼客体确定时相对复杂。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中的罪数论兼具犯罪论与刑罚论的内容,对于罪数论中处断一罪来说,其诉讼客体应为复数,因为各诉讼客体之间的本质内在联系,才进行一次惩罚。本质一罪诉讼客体的单一性似乎相对容易确定,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也会出现问题,尤其是复杂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处断问题。而法定一罪的诉讼客体则比较特殊,因为法定一罪是将原本各自独立的“数个法定犯罪”规定为一个“独立的犯罪”,此种情形也被称之为预设的包括一罪,其含义是指立法上将本来符合数次犯罪构成的行为预先设定在一个犯罪构成之中的犯罪形态。[22]从诉讼客体角度来说,原本各自独立的犯罪属于数个不同的诉讼客体,整合后的犯罪又属于一个全新的诉讼客体,所以诉讼客体本身也呈现出多变性的特点,本身也受到“实体法”规定的影响。实际上,此时依旧表现为规范设定对诉讼客体单一性认定的影响,只不过在适用时会涉及规范优先性及规范选择。
五、同一性维度中的的罪数论诉讼客体解析
与诉讼客体单一性强调待决犯罪事实是否可以再度分割不同,诉讼客体同一性则重在强调事实之间是否一致。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诉讼客体同一性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刑事二审的范围,关注的焦点在于“比较”前后两诉之犯罪事实是否一致,同时也适用于诉讼过程中的公诉变更权限之范围。一般认为,指控事实发生变化,指控罪名亦可变化,但审判事实与公诉事实具有同一性,则无公诉变更之必要。[23]综上,无论在哪一个维度上使用诉讼客体同一性,都是指“事实”外延之间的关系。传统刑法教义学将竞合区分成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但无论进行怎样的理解,“同一法律事实”,也就是“诉讼客体同一性”都是理解竞合的基础。[24]如果从最终判决结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则会发现“罪名”所涉及的诉讼客体有其自身的涵盖范围;从判决引用条文涉及的“诉讼客体”所涵盖的范围来看,与罪名的诉讼客体范围之间也会存在差异。此外,公诉机关指控的诉讼客体的范围也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因此,同一性维度中的罪数论诉讼客体判断有着不同的目的与角度,可以从实体法和行为自然意义两个维度进行展开。
在日本,系依实体法上的罪数论来决定公诉事实的同一性,而在德國则认为实体法与诉讼法上的行为概念并无关系。无论在德国或在日本,皆系以实体法的一罪范围来认可公诉事实的同一性,在该范围内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效果,贯彻“实体法上的一罪,即程序法上的一罪”之原则。[1]243-244我国刑事司法中并无“一事不再理”之规范制度,但对于生效判决的效力来说亦不允许随意变更,也就是存在着“相对的”一事不再理之限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之规定,只有根据法定事由才能将生效判决的内容予以变更。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似乎更强调诉讼客体单一性和同一性之间的结合关系,单一性应该以具体罪数形态的内在结构重新组合后的“再生”样态为原型,但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同一性的判断似乎更多地存在于司法者的“思维过程”之中,系司法者选择与比较的对象与结论,因而也会出现不协调之处。其原因在于刑事诉讼与刑事实体法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我国,更注重强调实体法上的合理惩罚,而对于评价,尤其是对评价过程的取舍等内容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也导致了罪数论在实体法上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但在程序法中并没有预留太多空间,尤其从罪数论的诉讼客体同一性来看,似乎更多地将重点放到了惩罚合理性之上,而对于惩罚所依托的“罪名”以及犯罪构成所涉及的案件事实外延方面,因为对于处罚并无根本性影响,所以也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实际上,诉讼客体本身也是一个受到刑事实体法影响的存在,与客观存在的事实之间并不相同。从二者的关系来说,诉讼客体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观念介入,而案件事实是多方面要素的组合,尤其是多方面“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以及要素”的进一步组合。从历史来源看,诉讼客体有时与控辩双方争讼焦点可以互换。诉讼客体源自古罗马法时期的争讼焦点,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逐步与民事权利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发展成为具有独立价值与意义的抽象概念,亦因此为其后的犯罪客体乃至法益概念的形成奠定了相对的基础。在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应该从自然意义的角度来界定“诉讼客体”的数量,亦即将数量的确定标准还原到自然行为之上。[25]但如何确定纯粹自然意义上的行为个数没有提供明确的标准,而且也存在着不同见解,因而无法成为确定诉讼客体的主要根据。与此相对,我国刑法分则所提供的规范标准也有自身的缺陷。具体来说,在采用重刑主义做法的背景下,将一般意义上的超越单一行为的二次以上的集合行为和其他情形也包括在内,[26]亦因此,在规范标准并不具有统一性的前提下,诉讼客体同一性的范围也必然受到影响。
因为罪数论的诉讼客体本身是复杂的存在,因而对其观测就不能仅仅以最后的判决结论为唯一的根据,还需要从整个诉讼流程中进行深入分析。从某种意义来说,司法者无法在诉讼过程中增加“不存在”的要素,但可以对某些已经存在的具有刑法意义的要素予以忽略,甚至是必须予以忽略。严格来说,刑法中并不会存在着所谓的“半个”犯罪,因而进行适当的舍弃就成为必然。也正是进行了舍弃,尤其舍弃了某些具有刑法意义的行为与要素的做法,才导致了罪数论的诉讼客体同一性确定上出现了复杂的样态。因此,“按照一罪”处断的前提必然“不是一罪”。当然,分析的对象不可能是“不到一罪”的东西,因为刑法上没有“半个罪”的概念。就此,以“一罪论”一定“是”二罪或二罪以上,亦即一定“是”数罪。一定“是”数罪,才会发生“一罪论”的问题。[27]亦因此,被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间的落差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些要素虽然被认为具有刑法意义而被揭示出来,但实际上并未体现于评价结论之中,这种矛盾性的做法才引发了质疑。
处断一罪之诉讼客体的自然意义表现显然是复杂的复数样态。不同罪名评价的是相异的自然行为,也有可能是一罪。对此,传统罪数论通过牵连犯、吸收犯等概念来界定一罪类型,但其背后的根据则是违法性评价,也就是承认多个“诉讼客体”的前提下按照一罪予以处断。[28]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少总则性规定,我国刑法分则以及司法解释对诸多具体“罪数形态”直接规定了处断后果,因为有刑法规范的明确规定,因而也只能严格依照具体的要求进行处断。[29]以此为标准,可以将我国刑法中的罪数形态分为法定的罪数形态和处理的罪数形态两类。[30]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罪数形态,其客体都是复杂的存在,都需要以既有的犯罪构成符合性为标准进行分析和判断。
六、结论
罪数论以解决一罪与数罪为其目标指向,属刑事实体法之内容。在将具体的罪数形态付诸实践的司法过程中,诉讼客体在其中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中介作用”。具体罪数形态的诉讼客体与单纯一罪的诉讼客体之间存在着差距,诉讼客体实际上体现着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契合,同时也具有独立的功能与作用。诉讼客体单一性判断就是罪数论运行的结论,解决的是按照一罪还是数罪定罪;罪数形态之诉讼客体同一性则是指复杂的诉讼客体内在结构的事实范围。对于具有复杂内在结构的罪数论的诉讼客体来说,无论是单一性判断还是同一性判断,都受到规范设定之影响。
参考文献:
[1]只木诚.罪数论之研究[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2]黄荣坚.基础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65.
[3]吴振兴.罪数形态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1-2.
[4]冯军,肖中华.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61-386.
[5]陈兴良.刑法竞合论[J].法商研究,2006(2):103.
[6]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10-224.
[7]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461.
[8]戈茨.概念界定:关于测量、个案和理论的讨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44.
[9]陈兴良.从罪数论到竞合论——一个学术史的考察[J].现代法学,2011(3):111.
[10]张淼.罪数个体标准的反思[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34-135.
[11]马克昌.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09.
[12]张淼.论罪数形态的隐性前提——以“罪刑关系”为视角的重新界定[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1):215-217.
[13]山口厚.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66-387.
[14]前田雅英.刑法总论讲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46.
[15]张淼.想象竞合犯结构矛盾及反思[J].检察研究,2019(2):10.
[16]龙宗智,杨建广.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91.
[17]张淼.论想象竞合犯视阈中的“罪名”及其应用[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44-47.
[18]劉仁琦.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实体限制规则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3):64.
[19]孙长永.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内涵[J].中国法学,2019(3):207.
[20]郑逸哲.法学三段论法下的刑法与刑法基本句型(一)——刑法初探[M].台北:瑞兴图书出版公司,2005:647-654.
[21]張淼,翟一平.数罪并罚原则及方法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1.
[22]王明辉.罪数论的基本原理:路径、概念与体系[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153.
[23]刘仁琦.公诉变更实体限制论[J].当代法学,2018(6):97.
[24]张淼.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界分与反思——以“三段论”为视角的分析[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9(4):93.
[25]陈洪兵.实体与程序双层次罪数论体系的构建[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6):104-106.
[26]张淼.刑罚变革维度中的罪数判断及应用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9(2):36.
[27]郑逸哲,刘柏江.法条竞合·想象竞合·实质竞合:构成要件适用方法导论[M].台北:瑞兴图书出版公司,2013:27.
[28]庄劲.机能的思考方法下的罪数论[J].法学研究,2017(3):158.
[29]张淼,高红银.罪刑法定性质辨析[J].政治与法律,2010(1):124.
[30]刘宪权.罪数形态理论正本清源[J].法学研究,2009(4):133.
Zhang MiaoAbstract: Theory of offense counting is the abstract regulation and academic argumentation which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result of punishment through analyzing structure of specific types, in contrast, the application of offense counting is the legal practice of offense counting during the criminal justice which means to practice the theory on the criminal facts. The substantial complex of specific types result in the enforcement and application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model single offense, so the tiered method shall be applied to form the litigation obj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nicity and identity with regards to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Key words: theory of offense counting; object of Criminal Justice; unicity; identity
责任编辑:王廷国 李慧 孔九莉 李祖杰 邓卫红 刘遗伦 余爽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