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自我修养的四个层面
2020-04-13朱生坚
朱生坚
在《演员自我修养》序言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申明了自己对一些术语的用法。他说:“不要寻找这些术语的科学来源,那将白费功夫,因为戏剧词汇是专属于戏剧行业的……虽然我们确实也使用‘下意识‘直觉等科学词语,但不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它们,而是在最简单的通用意义上使用。”(《演员自我修养》,陈筱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
显然,“下意识”“直觉”来自心理学,它们大概是当时的流行词。斯氏的意思是说,他用这些词只是作为“方便法门”,像道具一样,顺便借用一下而已。这不能说是不严谨的,而是一种高明而通透的态度。他的目标很明确:“我写作此书以及此后所有的书时,都不苛求具有科学性,而是希望能够指导实践。它们尝试表达的东西,都是我长期以来作为演员、导演和导师的经验总结。”这是行家里手的本色和本分,只想着把活干好。

《演员自我修养》[俄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陈筱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 年版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onstantin Stanislavski,1863-1938)
这里尝试着从《演员自我修养》(主要是第一部分)中抽取出四个关键词:真实、体验、下意识创作和人类的精神生活。从这四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看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要求的演员自我修养的四个层面—必须申明,这也只是姑妄言之。作为斯氏所用的戏剧词汇,它们同样不能脱离斯氏体系的语境,不能脱离戏剧舞台表演的场景。再者,它们并不构成逐层递进关系,而是相互交叉、部分重叠,甚至糅合在一起,不分彼此,共同贯穿于每一部戏的整个演出过程,把它们分开来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一
人世间最完美的表演是小孩子玩游戏: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想象出来的,跟周围的世界一样甚至更加真实的情境。而且,他们的表演不需要观众。这是不是最纯粹的表演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是说:“想要成为伟大演员,必须尽力理解艺术中的真实与信念,还要表达出来,就像孩子们在游戏中做到的那样。”真的,我们这些大人,从小孩子玩游戏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顺便说一句,在这里,斯氏本来可能只是说“大演员”,而真正的“大演员”,也可以是“伟大演员”的同义词。
斯氏把游戏中的孩子视为表演的典范,这是对的。可是,小孩并不都像他所举的事例那样,“只顾游戏而难以回到现实”。孩子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过家家”是假装的。他们会假装炒菜、吃饭,可是谁也不会把手中当作饭菜的沙子或泥巴放进嘴里吃下去。不过,他们绝不因为知道是假装的就敷衍了事。他们玩得非常认真。他们知道真假而不加区分。这是游戏中的“不二法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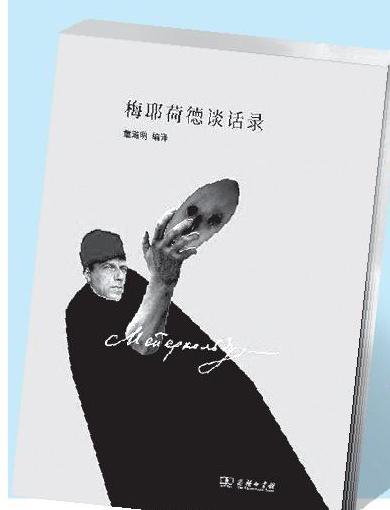
《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编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
演戏如游戏,有意弄假成真,创作一种假定的真实。深受斯氏影响的梅耶荷德有言:“一切戏剧艺术的最重要的本质是它的假定性本质。”(《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编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假定什么?假定真实。当然,这是戏剧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亦真亦假,真假不分。梅耶荷德转述普希金的话说:有一些戏剧家想在舞台上搞得和真的一样,殊不知戏剧艺术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和真的不一样。他说,普希金给出了一个非常睿智的戏剧定义。斯氏不太说到假定性,倒是常说真实和真实信念,甚至要求演员“相信舞台上和剧本里的事情和世界具有客观真实性”,当然,他也知道,“当众创作这种条件,不是自然条件”,他要让演员克服这种不自然,“达到真实的情感和体验”。可见斯氏所要求的“真实感和真实信念”,也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真实,而是如梅耶荷德所言:“在假定性戏剧的范围里我们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
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这种亦真亦假的表演也随时随地出现在生活之中。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演好自己的各种角色是每个人的本分,这些角色组合成一个真实的自我。没有必要专门以某种方式去“做回我自己”,仿佛这样那样来一下,就可以救赎自己一直以来的苟且和沉沦。每一句甜言蜜语都有真爱,不要问那是不是虚情假意。每一个瞬间的奴颜媚骨都是本色,不要说那只是不得已而逢场作戏。正如隐瞒父母病情强颜欢笑的子女,又如面对熊孩子案发现场故作镇定的父母,他们的确是在表演,却又演出了真实的自我。斯氏说:“真实与真实信念的各个部分之间,有互相支持和强化的作用……一系列逻辑的、次第出现的瞬间……将是极大的真实,将是完整的、持久的、真正的信念。”舞台如此,世界亦复如此。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其实根本用不了一千遍,因为三人尚且可以成虎。起先,某个人对某件事并非心甘情愿,但是很快就会“适应环境”,乃至于入戏太深不能自拔。这样的个人成千上万,叠加起来的蝴蝶效应非常惊人。真可谓:表演有风险,入戏需谨慎。
还有更高意义上的真实。斯氏说,演员在舞台上入戏的状态,行話称为“仿佛境界”:“所谓‘仿佛境界就是,我存在,我生活,我思角色所思,感受角色所感受”,“小真实可以产生大真实,以此类推,大真实产生更大的真实,直到最大的真实”,“舞台上达到‘仿佛境界的结果是:想要更大乃至绝对的真实”。何谓最大的真实、绝对的真实?那只能是哲学上的真实,超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上;有时候,必须通过对舞台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否定,才能达到这样的真实。据传,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曾说过:“我所描写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德斯所描写的却是真实的。”(《罗念生全集》)古人说话简洁而意蕴丰富。这句话其实也可以这样理解:索福克勒斯的理想的人物与欧里庇德斯的真实的人物,实则就是同一回事,虽然两者也理应有不同的外部表现特征。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斯氏所说的最大的真实、绝对的真实:那就是人的理想的存在。换言之,所谓最大的真实、绝对的真实,也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真实,也就是黑格尔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真实。它照亮了舞台。只要有人愿意,它也会照亮生活。
二
演员演戏,观众看戏,这两者之间可不是饭店的服务员(或机器人)端一盘菜给顾客那样的关系。演员在表演中传达他们对角色的体验,观众从演员的表演中获得自己的体验。两者都敞开自己,去接受异己的东西,都要在内心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当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工作是在演员这一边。

《我的艺术生活》[ 俄 ]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翟白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在斯氏看来,有两种舞台艺术,一种是 “体验艺术”,一种是“表演艺术”—这两个名词也是斯氏出品,有特定含义。用《演员自我修养》的两个部分即创作过程之内部体验和外部体现来说,“体验艺术”就是从内部体验出发、决定外部体现的艺术;而“表演艺术”只侧重于外部,或者说,只注重演技。斯氏认为,“体验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真正的艺术必须以体验为基础和前提,否则就是不可能的”。通常,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演员的主要工作就是表演,他们全靠演技吃饭,可是,斯氏却强调,“角色体验是创作的主要方面,演员首先应当关心这一方面。无论在哪一次演出或重复性演出中,都应该进行角色体验,即体验那些与角色情感类似的情感”。虽然你也可以说体验乃是表演的一部分,但是斯氏强调的是“体验艺术”与“表演艺术”的区别,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他说:“只有人的情感的力量充分而完全地展现出来,才会产生真正的艺术。”为此,演员要“保护自己免受机械模式的纠缠”,不要让机械的表演模式在自己身上留下“锈斑一般无法除掉的印记”。我们知道,表演有程式、有模式,演员必须经过训练,熟练运用这些程式、模式,乃至于让缺乏经验的普通观众察觉不到。但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这些机械的方法,有些能够达到一定的戏剧效果,但绝大多数的趣味是低级的,是对人的轻慢。它们对人类情感的理解是表面化的,对情感的态度很生硬,其蠢笨程度简直闻所未闻”,“任何能够唤起内部本质的东西,这些表演套路都不具备,它们只是舞台上的简单公式,一点也不像真正的生活。演员的人类天性就是这样被扭曲的”。最后,一言以蔽之:“体验就是体验,是公式化的模式无法取代的。”这些话说得相当严厉,让人感受到他的激动情绪,以及对机械模式和“表演艺术”的厌恶。
演员对角色的体验无法以模式取代,当然也不是被动地接受。“一个角色所有的隐秘特征,以及它内部生活的深度,只有舞台艺术中充满人的体验时才能得到艺术的表达。……所谓人的体验,就是演员在自身鲜活本性之下的体验。”演员固然要在表演中放下自我,但是“放下”(类似于“否定”或“扬弃”)并非完全删除,他们仍然需要也必然会带上自己的全部经历、情感和生活态度以及三观,等等。每一个人的真正的自我都不会轻易磨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没有自我了”,倘若我们停止抱怨,不再执着于自我,认真体验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或许就能从中得到“自身鲜活本性之下的体验”,并且发现原来自我一直都在那里。
再者,演员对角色的体验同样也是有技术性的。斯氏甚至说:“掌握有助于体验的心理技术,是我们研究舞台艺术的主要任务。”这些心理技术包括发挥想象力,集中和引导注意力,调动演员自身的情感记忆,等等。所有这些元素,或者说“精神内驱力”,共同编织成推动戏剧行动的线,而“连接不断的线对任何艺术来说都是首要的”。这些长短不一的线让舞台上的所有行动都指向最终的目标,构成一部戏的整体性。但是,他又说,在演出的过程中,演员不要去想整出戏该是怎样的,只要“专心表演身体上的微小现实行为,这就足够了”,就好比“在真正的生活中,普通的细小的自然行为,往往能够产生高级体验”。即使是一部史诗级的悲剧,表演也必须落实在细节,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把这些细节放大了给人看,让人看到那些寻常生活中漫不经心的东西,如何交织错杂,如何摩荡变化,如何起于青萍之末,终于狂风暴雨、惊涛骇浪。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时不时地会重复说,演员要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舞台上,而不是观众席,以至于有人以为他不关注观众的反应。显然,这是一个误解。他只是要求演员专心表演,不要想着个人魅力之类的东西,那是“表演艺术”的做派。他并未忘记“演员对观众的使命”。他信心十足地说,只有在“体验艺术”中,“观众才会完全被吸引住;他们没有进行简单的接收,而是感受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这一点才更为重要。观众的内部经验,经过这种感受才变得丰富,他对那种舞台表演的印象,將永不消磨”。如此这般的表演和体验,大大提高了精神生活的密度和强度。而如此这般地充满“高级体验”的生活,意味着尊重并且充分感受一切平淡、细微的东西,成为内涵丰富的、真正称得上高品质的生活。
三
也是在序言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宗明义:“如何唤醒本性,如何唤起下意识的创作,这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要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而无论是从文字篇幅,还是从内在结构来说,第一部分最后一章都处于全书的中心。它着重讲述“下意识创作”,结尾用一句话总结了斯氏体系之核心:“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技术在创作中调动机体天性中的下意识。”虽然,梅耶荷德说过,如果仔细考察斯氏的工作就会发现,他在不断地对自己的“体系”进行修正,但是,至少在《演员自我修养》里,这个“主要课题”或核心是确定无疑的。
何谓下意识创作?通常认为,创作是一个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的行为,它如何下意识进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是说:“一个演员最好的状态就是沉浸在剧情中。角色的生活就是他的生活,他自己的感受与思考都被排除在外了,而且这些是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起作用的只有下意识。可惜,这种创作状态不是我们的常态。”—这似乎跟前面说的舞台艺术要有“演员在自身鲜活本性之下的体验”互相矛盾?看起来是的。但是,这两边的语境和针对的问题不同,况且矛盾本是一切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常态,完全不必硁硁然纠缠于此。况且,演员的自身鲜活本性也可以保存在下意识之中。
斯氏所言,似乎就是通常所谓“入戏”—演员的基本功。斯氏给它加上了特定的条件和要求:“起作用的只有下意识。”不仅排除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还要忘掉演技。最好的表演就是不表演,如小孩玩游戏,又如角色的灵魂进入演员的身体。
要进入这种下意识创作状态,演员需要跨越自我意识的门槛。不用说,这太难了。小孩子玩游戏,自由自在,进出自如,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强硬或僵硬的自我意识。可是,对于演员来说,对于所有成年人来说,自我意识都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一道障碍,而所有知性和理性认识都在加固这道障碍。五六百年以来,整个现代思想一直贯穿着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我思故我在”的“我”)的发展,同时,也是理性(思)的发展。也许有违于通常的理解,就连探究无意识、非理性领域的弗洛伊德,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开启、影响了弗洛伊德的尼采,实际上仍然都是根深蒂固的、近乎极端的理性主义者。这个发展过程塑造着、成就着,然而也禁锢着每一个现代人。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下意识创作”,同样归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对整个现代思想的反动、对现代人的解放,虽然他从未如此标榜自己。我们只是看到,他强调:“你们要记住,肌肉的放松永远是一切创造工作的第一步。”这完全是技术性的、身体性的,却也完全可以赋予更深一层的含义:放松肌肉,也意味着放下一切执着,从而消弭禁锢和障碍。
然而,也不能忽视前面引述的第一部分最后一章那一句总结的前半句:下意识创作恰恰又是“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技术”而调动起来的。早在第一部分第二章里,斯氏就已经大致描述了这个过程:“要学会正确的刺激和引导,这需要你们去研究一些特殊的心理技术。通过这些心理技术,你们就能够给下意识以有意识和间接的刺激,并将其引入创作工作中。……这是一个从有意识到下意识、从主动到被动的过程。我们的意识要对工作生效,就应该使用有意识的心理手段,并让天性的魔法师感觉到它们。为了学会这些心理技巧,我们首先应该学会不干扰已进入工作状态的下意识。”
从有意识到下意识、从主动到被动,这个技术过程有悖人之常情,看似倒行逆施,然则真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大学》)。它需要一些特殊的心理技术(在全书各个章节都可以看到,斯氏把这些心理技术分解、转化为借助各种器物完成的具体行为,让演员循序渐进,可学可用),也需要强大的“意识自信”,把主导权交付给下意识去运作,并且不干扰已进入工作状态的下意识。但是,斯氏说:“为了激起十分之一的下意识的创作,就得付出十分之九的有意識的劳动。”(转引自姜涛《斯氏体系在中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可见下意识创作绝不意味着彻底关闭意识,它并未真正放弃“对下意识心理过程的主动控制”。梅耶荷德也说过类似的话:在表演中,“当演员的激情达到最高点时,他也始终应该是个主导者,他应该控制自己”(《梅耶荷德谈话录》)。毕竟,舞台表演不是巫术或通灵术,它是预先经过反复排练的现场创作。总之,在任何意义上,“下意识创作”都不是“放飞自我”—虽然,我们知道,后来有些先锋戏剧做过那样的即兴创作实验。我们也听说过,艺术家都是“疯子”,他们就是要打破一切常规,颠覆一切价值,如此等等。本来,这话也没错。贝多芬说,为了更高的美,没有一个规律不可以打破。然而,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乱来的。
四
弗洛伊德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人的意识比作冰山露出水面的“尖尖角”,水面之下的是巨大的无意识,处于两者之间、作为分界的水面是前意识。荣格又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上,把冰山改成小岛:高出水面的小岛代表人的个人意识的觉醒部分,在水面之下,只有在退潮之后才露出来的陆地部分是个人无意识,而所有的岛作为基地的海床就是集体无意识,如约翰·多恩(John Donne)诗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因为在深深的水底,有一个共同的海床。
那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下意识对应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界定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不重要。对斯氏来说,重要的是下意识创作的实践、过程。借用荣格的比喻来说,下意识创作就是演员从自己的个人意识的小岛,往下进入个人无意识,经由集体无意识,进入属于角色的那个小岛。这个过程包含意识与无意识、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调和。意识与无意识的调和,也就是理性与非理性、规则与反规则的调和,在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少不了这样的调和。而个人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的调和,则从有限的舞台空间通向一个无限深广的领域,斯氏称之为“人类的精神生活”,舞台艺术中的下意识创作就是要“把‘人类的精神生活在角色下的真实生活展现出来”。
问题在于,集体无意识只是一个假想的模型,它真的存在吗?甚至,有人会从根本上质疑,真的有“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样的东西吗?我们只能以康德的语气说,必须有。即使没有,也要想象一个,作为民族国家之上的“想象的共同体”。要不然,如何解释中国的演员可以排演《安提戈涅》《等待戈多》,而中国的观众可以欣赏长达八小时的俄罗斯剧团的《静静的顿河》。斯氏说:“这个时代有许多国家,它们的剧本我们都表演,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表现地球上所有民族的‘人类的精神生活。这要求我们的视野无比开阔。”“不止于此。当下时代的生活固然要表达,过去和未来时代的人类生活,也需要演员展现出来……就这样,我们的使命和工作更加复杂了,而且你们已经见过其复杂程度。”
尽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多次说到“人类的精神生活”,却从未正面描述、界定何为“人类的精神生活”。正如我们只能通过拿在手里的杯子,来理解杯子这个概念,人类的精神生活也无法像天神降临一般,直接呈现在舞台上,而只能借助于各个角色的具体行为。“从戏剧的第一幕开始,那些伟大的演员就将作品的每个部分一一呈现给观众……当各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把人类的所有情感呈现出来。”而观众则敞开身心沉浸其中。演员的体验和观众的体验虽有各自的对象,而他们的体验都超乎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关系,连成一体,都在个体与整个世界之间建立起别有意味的、截然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交流通道。
剧场中的体验让观众切身感受到,人类的精神生活虽然是非物质性的存在,却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如果不说它才是真正的存在的话。相较而言,演员的身体则是手段,是器具性的存在。演员要控制、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就像演奏者要照料好自己的乐器。《演员自我修养》从头到尾都在讲授演员调整身心的技术手段,然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它也始终不忘最终的指向。人类的精神生活是演员在舞台上,或许也是作为个体的、必有一死的人在现实中的最终的归属。而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最大的真实、绝对的真实”。
让人领悟自己最终归属于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艺术的使命之一。然而,艺术也不只是呈现,同时它也塑造着人类的精神生活。“无意识创作”终究是“创作”,在于演员对角色的塑造,正所谓“一千个演员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创作又会反过来带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起变化。我们知道,就连整个地壳和海床也不是静止不动的,集体无意识也不会是铁板一块。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断变化,而艺术历来是促成这些变化的重要媒质或场域。荣格在一九二二年的《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一文中首次提出“集体无意识”概念,这篇文章的结尾说道:“正如个人意识倾向的片面性从无意识的反作用中得到纠正一样,艺术也代表着一种民族和时代生命中的自我调节过程。”(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当然,艺术最初和最终都发生于个人。演员和观众分享人类的所有情感、人类的精神生活,对它们开放自己,把它们纳入自己,真正达到了“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在舞台上,演员塑造一个又一个完整、饱满的角色。而在现实生活中,尽管每个人都一定会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只有一种角色的人,无论是国王还是奴隶,都不免有些悲惨—但是,终究只能选择一两种、两三种主要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我们在艺术中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角色类型。”人生如戏,亦复如此。在人生中找到自己的角色类型,也就是找到自己的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