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内特夫人的玫瑰园与未名之物
2020-04-13张逸旻
张逸旻
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与第一○五街交界的范德比尔大门步入中央公园,是一片错落有致的植物保护区的南翼花园,这里有一个徽标形状的小小的睡莲池。池塘尽头的青铜雕塑来自某种相似的手法,是两个皎然年幼的希腊化神祇的造型,一立一卧。女童手托饮鸟浅盘,眼神落向另一侧,静穆雅丽;依在她脚边的男童,则捧着横笛,正欲吹响—这是小说《秘密花园》的主人公玛丽与狄高的纪念像。这个睡莲池是以他们的创作者、美国作家弗朗西丝·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1849-1924)的名字命名的。

纽约中央公园内的伯内特水池
一
弗朗西丝·伯内特于一九一一年出版的《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几乎是她最晚动笔的一部儿童作品。就情节来说,这部作品与她前期最负盛名的《小勋爵》(Little Lord Fauntleroy)和《小公主》(A Little Princess)意趣相异,俨然一部被文学语言编织得美轮美奂的儿童成长指南。故事发生在殖民时代的英格兰,玛丽是一个乖戾独断又冷漠无知的贵族女孩,从小随父母生活在英属殖民地印度,在一次瘟疫席卷后独自幸存,回到英国,投寄于其姑父米塞斯韦特庄园主柯瑞文先生的监护之下。当她在偌大而充满禁忌的莊园内悠游度日、无所事事时,便自然而然地对一个“十年来从未有人涉足”的秘密花园产生了兴趣。而在她突破一个又一个谜题,推开花园门走进去时,眼前却布满了业已枯死的玫瑰花丛与藤蔓。玛丽决心凭借一己之力救活玫瑰园。随后,她结识了乐天而友善的乡村男孩狄高,后者成为花园主要的修缮者和另一个秘密守护人。与此同时(此时全书已过二分之一),庄园中凄厉的夜半哭声纠缠着玛丽,出于英勇武断的孩子气,她循声而去,才终于让小说的第三个主人公,即长期卧病在床的庄园继承人柯林少爷露面。这对表亲在把彼此认作幽灵的高度惊愕中结下了友谊。尽管柯林的身体羸弱得多,但他的脾性、境遇却和过去的玛丽极其相似:由于不健康的父爱和几乎完全缺失的母爱,出生后基本靠仆从的伺候而在毫无心理和情感对话的孤独中长大。两人身上共有的颐指气使、乖僻易怒、自我封闭等,暗示着这种失败教养与性格缺陷之间的弗洛伊德式关联。

《秘密花园》[ 美 ] 弗朗西丝·伯内特著李文俊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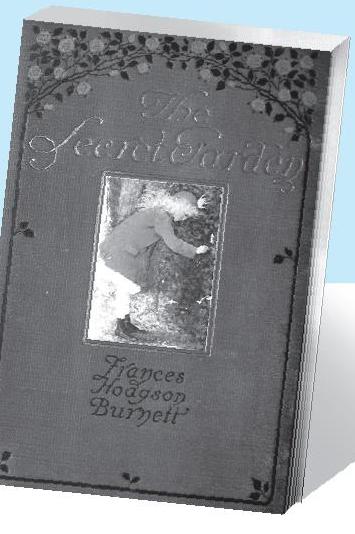
《秘密花园》1911 年初版本
玫瑰园终于成为三个孩子共同守护的伊甸宝地,供他们游戏、劳作。追随植物生长的收获与付出,使玛丽和柯林的身心发生改变。与此相伴的,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戏剧化经历接踵而至:与“通灵”的知更鸟的结交、关于苏珊·索尔比夫人的消息、春天的降临、新来的羔羊、老园丁维瑟斯塔夫的误入、唱诵仪式与“魔法”的操习……发现和守护秘密的持续刺激,与秘密受威胁的惊骇瞬间,构成小说叙事的推进与平衡机制。其中,狄高,这个在荒沼地上长大的自然之子,扮演着这趟复乐之旅的向导—小说的最后,柯林身强体健,获得了生活的尊严,就连他父亲柯瑞文先生那黯淡阴郁的灵魂也散发出新生的活力。
《纽约时报》曾有评论认为:“能写书赢得孩子喜爱的作者大有人在,能同时取悦成人的却要少得多;但只有真正凤毛麟角的童书作者,才具备充分的技巧、魅力、率真与深意,从而让作品同时适宜于年轻和年长者—伯内特夫人便是少数有如此天赋的人。”这或许与伯内特深谙成人故事的写作不无关系。她从十九岁就为妇女杂志供稿,由于故事塑造得一鸣惊人,甚至被责问是否为原创。在接下来为领取稿费不断拓深的写作志业中,她的第一部小说《洛瑞家的姑娘》(That Lass o?Lowrie?s,1876)使她在英美两地的文学圈中收获了声誉。而她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则是十年后的事了—《小勋爵》,仅仅是将小儿子维维安写进故事的一次尝试,却意外地大获成功,小说的周边产品(19世纪末的人偶玩具、香水、信纸、游戏牌和巧克力)销售一空,文字被译往十余个国家。当时甚至有评论称:“我们感到无比荣幸,因为伯内特夫人这样的作家竟用她鲜活的艺术为孩子们写故事了。”

《小勋爵》(中英双语版)北 塔译译林出版社 2016 年版
二
然而,伯内特的作品中只有《秘密花园》被人奉为经典。她还有其他五十多种小说、传记、儿童文学和改编成舞台剧的作品,却唯有此书魅力不衰。这部小说的独特成就,或可植入适当的文学传统中来描述。对于初识外国文学的小读者,《秘密花园》是这样一道彩绘玻璃窗,透过它可以观摩近现代英语文学的朦胧的概貌。这个概貌的关键词之一,是浪漫主义的自然观。
丹麦史家勃兰兑斯对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的著名定调是,这一时期的“英国诗人全是大自然的观察者、爱好者和崇拜者”。比如,“喜欢把他的癖好展示为一个又一个思想的华兹华斯,在他的旗帜上写上了‘自然这个名词,描绘了一幅幅英国北部的山川湖泊和乡村居民的图画”;济慈“能看见、听见、感觉、尝到和吸入大自然所提供的各种灿烂的色彩、歌声、丝一样的质地、水果的香甜和花的芬芳”;穆尔“以阳光使我们目荡神迷,以夜莺的歌声使我们如醉如痴,把我们的心灵沉浸在甜美之中”,凡此种种,皆是他概括为“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的鲜明示例。关于这种英国气质如何在北美新陆扎根,又如何对后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固然是文学史上的又一常识点。伯内特的写作比华兹华斯们晚了将近一个世纪,况且彼此在创作文体、精神诉求等方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秘密花园》却像“自然主义”这股激流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并非偶然的回声。
在自然的教养中健全体格并领受爱的赠予—没有什么比之更能概括这部“成长小说”的主题了。读者会发现,书中的自然景物像薄纱一样缠绕着我们的感官。尽管玛丽初来乍到时总碰上暴风雨,但冬夜中如紫色大海般无涯的荒沼地,很快便在春日里判然不同地倒映出湛蓝的苍穹—迷雾与云罩散去后,天空的拱形和闪闪动人的每一种色调,都清晰可见。我们也领略了这种荒沼地的出产—石楠和金雀花灌丛,因为它们的香味总是由洁净的风裹挟着,一次次地吹送到庄园小主人们的窗下。
秘密花园则是荒沼地之自然韵律的一个变调。它带来泥土的湿气,露出胚芽和花骨朵的柔嫩的尖顶;随着春天的降临,玫瑰藤蔓闪烁着绿意,阳光照射下的花朵和枝柯交接的树木,似乎在触摸读者的手和眼睛。而小说对一只优雅的生灵—知更鸟的着墨,则使悦耳的啁啾像小斑点一样,投洒在字里行间。等到柯林第一次来到秘密花园,小说写道:“那个下午,仿佛整个世界都在竭尽全力变得完美无缺、光芒四射,要对一个男孩子待以善意。也许是出于纯粹而圣洁的好意,春天来到这里,并把她能在一个地方集中的一切都倾注在此处。”
在玫瑰园的遐想与劳作,加之荒沼地上吹来的新鲜空气,让玛丽和柯林的病体渐渐起色;而两人摆脱“王爷公主”式的孤僻厌世,学会了爱与生活,则最大地得益于与狄高的结交,后者活脱的自然的精灵,拥有一支完整的动物跟班队伍,自始至终洋溢着赤诚的快乐;有赖于其照料,玫瑰园才真正地枯木逢春。
把儿童蜕变的决定性时刻,交托在玫瑰园复活的旋律中,这是伯内特作为“自然主义”信徒的最好说明。在小说里,玫瑰园几乎和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或“黄水仙”一样,富于净化与医治的神力。但它的表现形式不是贮藏在白日梦中的自然印象,而是一种生育力的启示、一个母爱的许诺—小说暗示,玫瑰园正是柯林母亲亡灵的寄寓之所,它提供一种共鸣,在温绿的基调里糅入种种爱的注目;而小说所塑造的母亲典范—善解人意的苏珊·索尔比太太—最终造访玫瑰园,则使拂动其中的“母亲”的魅影被充实、照亮。
玫瑰园图景喻示着自然(原始生命力)对人类社会(现代文明缺陷)的疗愈作用,这也是我们在阅读时容易联想到D. H.劳伦斯的原因—只要将“柯林—玛丽”与“狄高”这组人物置于两立,稍作原型上的简化,便不难发现,《秘密花园》与后来轰动一时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拥有异曲同工的角色构成。
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书中一段忘情的独白。这段话的迷人之处在于作者声音的僭越—掩身于叙事者背后的伯内特,似乎要将一种庄严的意识,私藏进总是在照顾小读者口味的行文中。其感情的真笃与智慧的成熟,由露水一样清新的语调转述出来,构成一段不可多得的哲思散文:
关于人生在世有很多怪事,其中之一便是,你只在某些时刻才确知你会活到永远的永远。有时候是在某个温柔而肃穆的黎明,当你起床走到外面独自站着,头尽情地后仰,观望灰蒙蒙的天色逐渐变化、染红,奇迹般的不明之事发生着,直到整个东方使你热泪盈眶,你的心在奇异、永恒而至上的日出前停止了跳动—就是千百万年来,每个晨间都会发生的一幕。你在那一刻或那一段时间是确知的。有时候是在日落时,当你独自站在林间,那神秘的、暗金色的静谧斜斜地穿过树梢洒了下来,仿佛在那枝丛的底下一遍遍轻诉,喃喃声使你无法听辨。有时候,是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深蓝色的夜空中点缀着百万颗星辰,它们等候着、俯视着,使你感到确信;还有些时候,一段动听的音乐也会使这一点变得真切;有时候则是因为人们看你的一个眼神。
这样的表达完全向每个人的现实经验敞开,是在“玫瑰园—母爱”的譬喻之外,让生命的全新感觉沁入普通读者的心田。如果说,小说有一个独特的败笔,即随着玛丽和柯林的成长,他们的个性日趋淡化,以至于人物仿佛也成为植物生命的一部分,隐没在越来越繁盛的花草之中;那么,这或许是因为,作者最感兴趣的是通过作品来还原自然界的立体与丰厚,而小主人公们则是她贯穿这种理念的神使,他们充当了感受力上的向导,在我们胸中重新燃起一种敬畏,使我们(在华兹华斯运用“崇高”论者朗吉努斯的意义上)重新仰仗、臣服于感官。
三
伯内特出生在英国,因少时家道中落而移居美国,投靠立业于田纳西州的舅舅。婚后,育有两个儿子的伯内特跟随作为眼耳科医师的丈夫四处进修,其写作收入始终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她名噪一时,曾扮演着大西洋两岸文学圈的沙龙主人,座上客中不乏亨利·詹姆斯、奥斯卡·王尔德之流。但一八九○年大儿子莱诺因肺结核夭亡,伯内特从此元气大伤,加之常年辗转英美两地,在写作和家庭事务的狭缝间艰难周转,颇有点抑郁之势。一九○四年,她回到英国肯特郡曾长年租住的梅森别墅,无意间在常春藤掩映着的门背后,发现了被废弃的玫瑰园。正是受此启发,《秘密花园》诞生了,其中柯林一角,是以她的大儿子莱诺为原型塑造的。让十六岁病死的莱诺在小说中重获新生,类似的做法在文学史上确有许多先例可循。写作《秘密花园》时,尽管伯内特遭遇了生命的无常、感情的贻误和爱的失望(彼时她竟已经历了两次婚姻的失败),但她的小说却试图命名得以驱散灵魂暗影的种种动能。

弗朗西丝·伯内特(1849-1924)
除上文我們讨论的自然伟力外,小说还借柯林之口宣称,世上存在着一种“魔法”,能使我们保持生命的勃勃向上。这里的“魔法”绝非“霍格沃茨”意义上的法术,但柯林信誓旦旦地念叨着“魔法与我同在”,并在花园里实践他的“科学试验”,又依照印度法基尔神僧的修炼,成日唱诵、打坐、列队逡巡—这些虽也出于孩子的天真,但总不乏超自然的宗教色彩。事实上,这是伯内特晚年信奉的“新思维”(New Thought)运动的折射,其主要的成分是强调精神与身体的联动性,认为人可以通过控制念头来强身健体、重塑生活。在小说末章的开篇絮语中,叙事者说道:“每个世纪都会有新的发现……上世纪的新发现是,念头—仅仅是念头—像电池那样能量巨大—对人就像阳光一样有益,或像毒药一样有害。让一个悲伤或不善的念头钻入你的心灵,就跟让猩红热病毒钻进你的身体里一样危险。要是没有及时祛除,那你可能一生一世都无法从中摆脱。”这与今天我们所遵奉的保持心理卫生的科学信条几乎别无二致,但一百年前的伯内特却以孩子口中的“魔法”为这一信条增色。而当“念头”的作用在柯瑞文先生身上应验时,伏于叙事脉络中的作者竟忍不住翘首发声,将之称作“未名之物”—那种完全被征服的失措,仿佛这是一件不便以理性加以推敲的神迹:“我不太清楚用来解释刚才这一切的神奇的未名之物叫作什么。谁也弄不清楚。就连他(柯瑞文先生)自己也说不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