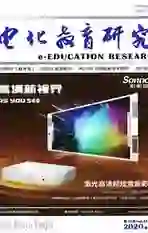对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用的批判与主张
2020-04-10李芒张华阳
李芒 张华阳
[摘 要] 人工智能应用始终无法逾越技术乐观主义、悲观主义、“转化”主义的藩篱,进而堕入了教育应用中的“盲区”“禁区”“误区”。因此,目前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三种错误取向还需从批判的视角审视,进而人们应充分认识工具的意向结构,极力抵制坠入历史的虚无之中,拒绝陷入随意转化的虚假幻想。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三点批判体现在忽视了师生的真实需求,漠视了培养完整的人的意义,轻视了人的存在价值。人工智能人文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提出的教育主张。由此,人工智能教育的相关者必须要认识到人文主义的合理性论点,将人始终视为教育活动中的核心所在,继承“天人合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以智识的人文精神气质在教育活动中应用人工智能。
[关键词]人工智能; 师生真实需求; 完整的人; 人的存在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芒(196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E-mail:leemang@bnu.edu.cn。
一、引 言
出现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类至今已二百万年有余[1],而19世纪才有科学家提出“硅基生命”这一潜在假设。尽管发展历程间的悬殊如此之大,但作为碳基生灵佼佼者的人类已逐渐开始提防甚有可能走向硅基生命的人工智能[2],这场持续战究竟鹿死谁手的确不可预知。由此,人工智能与人类已然在当下成为所有关涉人类情形中关注度最高的一组关系,因为这牵涉于人类的命运走向,关乎于人类究竟是解放还是毁灭。这必将成为21世纪最重大的时代话题。
教育作为培育未来人的重要传承活动,从长远来看导致了未来人与未来人工智能的关系走向,在短期更是直接制造了“人工智能+教育”的热点议题。因此,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应何以、何为,已成为人们迫切需要应对的难题。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人工智能却在心智上仍然表现得“冲弱寡能”,在基本任务域与智能性能之间徘徊不定,更是无法通过感觉运动感知真实而非抽象的物理世界[3]。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解决问题的能力日益精进,打破各项卓越的人类记录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并不具备意识或意向性的“表里不一”的人工智能又如何在具备高复杂性的教育系统中有所作为呢[3-5]?对于教育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师生而言,人工智能的主要作用集中于试图通过推荐资源、学业诊断、学情分析、作业批改等助力师生實现个性化教学[6-8],但效果并未如人们所预设的那般完美,却存在伪个性化的标准化、缺失关怀的冷漠化、算法欺骗的盲目化、社会影响的难量化等诸多问题。而人工智能用于教育管理,又的确已经大放异彩,为师生提供了安全的校园环境。如此,教育关系者究竟以怎样的心态认识人工智能并发挥其教育价值,对人类的人格角色与生存发展都至关重要。
二、师生的真实需求——对人工智能乐观主义的反思
目前,技术中性论仍旧为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提供了论调根据,也修饰了人工智能教育的乐观 “面目”。然而,这种看似绝对繁荣的人工智能教育背后,有多少又是人为臆想的“幻象”?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是一种对人工智能社会价值及其发展前景持肯定态度的社会思潮。只有真正看清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才能进而看见人工智能乐观主义在教育中制造的“盲区”,才能解蔽过度乐观所致的遮蔽。
(一)技术中性论与人工智能乐观主义勾连的双重陷阱
当前,人工智能还被视为技术而非生命[9]。由此,才能将人工智能乐观主义放入技术乐观主义之中加以理解。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延伸,锤子、汽车、望远镜等各类不同的技术工具代替和放大人的身体功能。人工智能亦是如此,语音识别试图去“听”,计算机视觉着力去“看”,数据分析尽力去“想”。然而,人工智能是以不同于人的机理实现人的功能,并在效果上体现出更强劲的态势。例如,与人的听力系统相比,语音识别具备全程记录、实时互译、通晓各类语言等人类无法实现的功能。如此“所向披靡”的人工智能岂不是人类功能的“扩音器”与“放大镜”,是促进人类解放的不二之选吗?况且,有论者从人类的四维表征,人的理性、感性与灵性,人的物质基础和工作机制论证了人工智能无法替代人类就业,作出了人工智能的弱危机性论证[10]。同样,有论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大量运用有助于使劳动越来越复归到“自由的生命表现”,使劳动越来越充满快乐性,使劳动选择性越来越高,最终推动人类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复归[11]。那么,如此“助人为乐”的人工智能也当然有助于师生“看”得更广更高,“听”得更远更清,“想”得更明更深。
从技术中性论来看,就更能理解这种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乐观论调了。虽然有人试图证实技术中性论与技术乐观主义并无必然的关系,但同时也肯定了绝对的技术中性论的确给人提供了盲目乐观的根据[12]。“技术本身并不会作价值判断,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取向”,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观点,并将技术使用的全部责任推向其使用者,却忽视了有关技术生产使用全过程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芬伯格曾将技术中性论的四种观点列举出来,包括了技术的工具手段中立、技术并未具备政治色彩、技术像科学观一样保持“自我”认知、技术在任何情境中保持同样的工作效率[13]。倘若在这种工具理论之中,便极易被技术中性论所“裹挟”与“诱骗”,为之摇旗呐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愉悦地走向了教育发展的“高速路”。
如此看来,不得不感叹于人工智能乐观主义与技术中性论所勾连形成的精妙双重陷阱。人工智能在教育中似乎无疑是绝对乐观的,师生肩上的重担也可以全部交付于人工智能这个“新伙计”一力承担。这样的陷阱使师生认为不必苦学修行,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调用人工智能便能坐享其成,“拿来主义式的快乐”又卷土重来了。然而,源自工业界的人工智能似乎并没有这么为人量身订造,更难说可以为每一位师生“私人订制”了。究根溯源来看,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 而总是一种个性的投射,这种投射照应着礼仪、秩序、权力等诸多人类意志[14]。更重要的是,人的复杂性注定了教育的复杂性,究竟如何跨越,甚至能不能跨越都是值得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乐观“面目”
当我们追问技术中性论之时,便会发现凡是技术都必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15]。刀的意向结构指向切割,可做菜也可伤人,无论对人好坏皆是意在“切割”。锤子具有敲打的功能,无论对错,总之就是“嘭的一下”,或是把钉子敲进木板,或是把木塞敲入瓶口,又或是把玻璃瓶子敲碎,但总而言之,技术工具的意向结构始终未变。
人工智能一样有其意向结构,计算机视觉旨在“看”,这种对物体的识别过程,并不在意外界是自然景观还是算术习题,无疑只是不带“感情”地在看。语音识别意在“听”,不管你是说的汉语、英语、日语等各种语言,只是完成语言处理的过程,也就是说“听到”及“获得”,难以去筛选“听到”的价值。总而言之,人工智能技术便是在试图延伸人的功能,其特定的意向结构反映的是预先设计好的一些内容。因此,无论是工业流水线还是教学中的师生,都逃脱不了人工智能设置好的“座架”,无论是谁,等待着的都是一把请君入瓮的“模拟游戏”。甚至,其背后还隐藏着一条道路,即技术的选择具有极强的社会性,于是有选择,就会有“伤害”。任何选择,一定是对某些学习者有利,对某些学习者不利。
揭下虚伪的乐观“面目”的关键一环并不止于对技术本身的批判与质疑,而是在于挖掘躲藏在技术表象背后的“二级故障”[13],这种故障包括了反复无常的磨损和斷裂、材料的质量、操作者的错误以及生产体系的变化等因素。悲哀的现代人面对技术浪潮异常担忧,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近代到现代与从古代到近代的过渡鸿沟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16],现代化更是人类的一个漫长演变时期[17]。虽然这种惶恐可以被理解,但现代教育仍然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拒斥激进思潮,不断自我检审,才不至于被人工智能诱拐至虚幻之中。当前的人工智能并不能建成某些论者脑中所臆想的“海市蜃楼”,但这种被人构想的“物”却逐渐成为一种已经存在的物而深入人心,将一些关键事件当作日常而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用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因此,只有真正去探求人工智能到底可以为教育做什么,才能撕下伪装的乐观“面目”。
(三)人工智能乐观主义簇拥的“愉悦盲区”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尖端技术共同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18]。人工智能引发包括教育在内社会各领域的连锁反应,技术进步的已然性和社会适应的滞后性构成了社会系统平衡失调的基本矛盾[19]。这一矛盾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注重技术与教育的适配,在于工业界的技术使用不需要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而更多是“以技制人”。
那么,如何又是为“人”谋“技”呢?这还需要扬弃虚假需求[20],回归至师生的真实需求便可以看到教育中究竟需要何种人工智能。教师需要什么?首先教师本身绝不可能需要人工智能取代教师,并不是害怕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而是真正的教师能够看到自身价值[21],他们独特的人格,包括信念、情感、灵感、天赋等因素,这才是导引学生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而绝不仅仅只是安排学生重复做题,提供合适的资源,提供丰富的技术环境。衡量现代教师的关键指标是教育性[22],这种教育性应以教育目的为出发点,注重复杂与便利、粗犷与精细、多讲与少讲,一切都是由教育性决定,而不是由机器决定的。“科技不能取代教师,但是使用科技的教师却能取代不使用科技的教师”,这样的简单说法加上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极易误导教师陷入恐慌之中。因此,人们务必要认识到不应将评价教师的标准简单地界定在使用的表层,教师在教育中有其绝对的不可取代性,教师的主体呼唤也意味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的使用是一种可选择的现代性。
学生又需要什么?人工智能固然可助学生获得“盆满钵满”的材料,获得机器人学习伙伴,获得实时的语言翻译。没有人可以否认人工智能发挥的价值与作用,但这样的作用最多可能将学生培养成一个知识的记录员,而不是天才的创作者。而真正悲哀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最大的作用恰恰又是将大量地取代人的活动,并使得人类进入社会智慧代替个人大脑思维器官的时代[23],这样的人类完全无法与人工智能竞争。似乎这就完全不容技术乐观主义的簇拥者再度乐观,人工智能用自己的方法培养了一群比不过自己的人,反而像对待机器一般地对待学生,将历史引向了鼓吹个性化的反面,使得学生呈现出碌碌无为的同质化。
师生的真实需求是建立在主体性、主体间性、他者性三者之间的主体呼唤,主体间性教育在继承了对象化认识主体性基础上深化了自由平等交往的内涵,具备责任伦理的他者性教育是在继承自由平等交往的基础上突显出了他者性责任伦理之维[24],教师应时刻平衡权力让渡与权力持有的关系。从布鲁姆认知目标来看,可以将人工智能与人在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发挥的作用相对比。在认知领域中的低层次思考,人工智能无疑比教师和学生更强,教师也应该认识到人工智能的作用并将此类权力有限让渡于人工智能培养学生,而在高层次思考中,教师才是更加适合引领学生分析、综合、评价的引路人,唯有教师才能激发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情感领域,人工智能固然也可以成为学习者的伙伴,成为学习者在学习遇到困难时和枯燥难过时的聆听者,但无疑教师更能与学生拉近感情,产生真正的情感交流,安慰学生的低落情绪,鼓励学生充满斗志地、饱含激情地迎接困难与挑战。在动作技能领域,机械的动作可以让人工智能“帮忙”训练学生,但复杂的外显反映、适应和创新,绝对需要充满教育热情和能够精准示范的教师,从而“超度”学生通向“极乐世界”[25]。
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批判人工智能乐观主义并不代表忽视技术和轻视技术,任何人都不能走向历史发展的对立面,恰恰是需要冷静地看待技术在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暂且先把技术看作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而不是简单的技术中的教育,教育中的技术[26]。这样才能意识到“座架”让人类与技术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没有人可以扭转、拒绝技术的发展,但也应该有人站出来告诫疯狂迷恋技术的人切勿误入歧途,进而以人的能动性消解“座驾”的控制性,从而实现人对技术的控制与统领。现在的人工智能仍然处于“确定性信息、完全信息、静态的、单任务、有限领域”之中[27],仍然照章办事,不需要任何灵活性,这显然不是智能的核心。这也正是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是没有理解的人工智能,因为现在的对话系统离真正的智能还相距甚远,人们不应得意洋洋、忘乎所以。
三、培养完整的人——对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的深思
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的核心支撑论点便是技术自主论,这种技术内在逻辑的延续将人导向了虚无的道路。然而,虽然的确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可能给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更不能完全沉浸在走向灭亡的恐慌之中。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是在对人工智能必将强于人类的幻想中,认为人类未来终将走向被机器奴役的思想运动,以一种消极的眼光来看待人工智能。故此,只有真正聆听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给教育敲响的警钟,才能进而认识到人工智能悲观主义给教育设置的“禁区”,这样的“禁区”具有警示的作用,避免使人片面地占有,但同样也不应以消极态度陷入虚无的失落之中,从而放弃培养完整的人。
(一)技术自主论与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搭设的虚无圈套
技术自主论将我们引向技术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论点,即现代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也不能选择使用的手段,个人的主体性被技术完全压制[15,28]。绝对的技术自主论完全否定了哲学家和科学家为人工智能等诸多技术出现所作的冷静思考和反复探索,绝对化了物的力量而轻视了人的意义,倘若相信此论便会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挣扎之中,并臣服于物的绝对力量之下,通过技术赋能完成了对人的新型控制。这种危险的论点判定了一个没有人能够握住实在的技术工具,没有人能够改变技术工具,没有人能够决定技术工具的发展方向。
绝对的技术自主论所发展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认为无论人类怎样努力都是无效的,作为整体的社会以及社会诸因素都不能决定、支配、控制技术[29]。人类已经没有选择权与自主权,成为等待人工智能宰割的“羔羊”。这种带有虚无主义的论点完全否定了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否认了唯物辩证主义的思想,否认了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可知性、规律性与必然性[30]。教育作为重要的育人活动,若是被人工智能所把持,必然会引领人类走向注定悲剧的结局。想要消解这种绝对的技术自主论,一是将温和的技术自主论透射到思维认识之上[28],温纳认为技术的确“失控了”,人们了解、判断或控制技术手段的能力正在下降,技术远远不是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在人的牢固的控制之中[31]。二是回归到人与人工智能理解之中,心灵哲学家塞尔在“中文屋论证”中指出,即便人工智能可以与人流畅地运用中文交流,但也不能认为人工智能真正理解中文[6]。人工智能在计算过程中只是在设计不具有实在意义的程序代码,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意义在于外部观察者的解构。人类却不自主地认为人工智能已经具备了理解语言、解释语言的功能。
传统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永远无法思维,无法与人媲美的消极观点,而这种看似“消极”的观点却隐含着一种人类的盲目自大和对机器的轻视。图灵曾对灵魂并未分配给机器而无法思维的神学意见、把头埋在沙中希望机器无法思维的“鸵鸟”意见、数理逻辑所推演的机器能力有限意见、唯我论思想的意识反对意见、能力缺陷的反对意见、机器只能按部就班地工作均作了思维式的反对[6]。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量级腾飞,在实践层面已然或有望冲破这些“束缚”,悲观主义已从“祈祷低效”“细数缺陷”等观念转向“惴惴不安”,但不可忽略的是,担忧之中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着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如今的人工智能悲观主义预示着人工智能会打破和取代几千年来占绝对主流地位的重复性工作及相应生活状态[32]。虽然人工智能率先解放了人的双手,但更进一步会使就业机会稀缺,导致大部分人失业。自此,失业的人群将堕入一个无限循环的深渊,失业者的子女接受教育不充分,进而直接导致其核心竞争力不足,最终贫富差距极度增大。“穷人”只能成为“富人”的奴隶,“富人”很有可能是人类少数精英或者是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穷人永远无法再次通过教育获得“翻身”,阶级的差异性日愈增强,私有制更加难以被消灭。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非但没有促使教育公平,反而在看似教育公平这一具有谎言性的长袍之下,遮蔽着城市与农村、富人与穷人产生越来越大的数字深谷与文化鸿沟。落后并非只是技术与资源的落后,而是整体的落后,包括了文化、思想、习惯等诸多因素[33],唯技术论的作用会导致过于相信技术的恶果,以致向着不公平的方向越走越远而不自知。如此来看,人类精英所主导的人工智能发展,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之后,将会成为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阴谋。
(二)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悲观“面纱”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无数变革,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渔牧文化和农耕文化,都让人们有能力、有信心地在充满自然灾害的地球上幸存。而工业革命时代所带来的大变革,这种大跨进迅速地加快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也的确直接改变了人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但同时也加速了人类对自身灭亡的恐惧,各种悲观主义甚嚣尘上[34]。
人工智能的悲观笼罩在人类的面庞之上[35],人类试图揭开面纱却又担心受到“魔鬼”的诅咒。绝大多数悲观主义者认为一旦人工智能出现意识,一旦人工智能与人类对抗,人类将再无出头之日,只能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埃隆·马斯克认为“人工智能比核武器危险得多”[36],霍金甚至表示“人工智能极有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进步”[37],这一系列言论让人们因为人工智能的不可预知而终日坐立不安。
人工智能悲观主义将师生捆绑在技术座架上。悲观主义者宣告了人工智能將人类引向“四肢退化、头脑简单”的教育结局。在劳育方面,劳动的消匿使人类丧失运动的能力,人类也就告别了传统工具,形成了对人工智能的极度依赖。在智育方面,人工智能使人类越来越少地考虑真实发生的事情,更多人会选择通过控制人工智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学生不自觉地陷入浅表学习现象、丧失全面发展、情感发展脆弱的不幸之中,极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38]。然而,人类发明人工智能本身又是试图打破思维定势从而获得自由,历史的发展往往不如人意地自觉走向“渴望的反端”。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我们无法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也不应沉浸在无法预知的伤感中自怨自艾,当务之急便是思考如何最小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弊端,才能进而避免人工智能漩涡将人类卷入自毁的深渊。
(三)人工智能悲观主义警示的“勿入禁区”
为了避免人类走向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所设定的桎梏之中,人類必然需要得到全面的保留。马克思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是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必然不是丧失了身体机能,保留着稚嫩头脑的无用之人。由此,人应该以一种全面的方式而生存,人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9-40]。唯有培养“完整的人”,才能使学生有理想信念,才是对教育事业规律性的深刻认识[41]。因此,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教育中为教师提供更多发挥主体性的选择,减轻人的工具性价值,保留人的目的价值[26]。现代人需要在宇宙之中保留自己的本性,以独特的精神气质追寻和探索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质。
人工智能带来的悲哀指向了人的内里隐私,人们要想留下最后一块“遮羞布”,还需正确地认识为何会导致“暴露”。在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偷吃了禁果的他们用树叶遮蔽了自己的隐私部位,自此人们便意识到了隐私。而人工智能全方位地收集数据,让学生在教育大数据时代无所遁形。可以说,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获取隐私的能力[42],使人可以轻松地“摸清楚”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被数据所解构,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异化。无论是你在课堂中打个哈欠,还是在线上学习中偷偷开了小差,一举一动都被人“监视”,学生内心的恐惧被人工智能无限地放大,以前对于高考的短期恐惧逐渐成了一种长时间伴随的恐惧,让人难以自由快乐、开心随性地活着。人最根本的自由被人工智能更大程度地剥夺了,人工智能不仅没有解放人,甚至让人逐渐在人工智能面前成了“被实践”的对象[43]。对于数据的使用,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需要慎之又慎,任何人不应将学生彻底地数据化,数据所支撑的框架人,是一个被剥离血肉而丧失自由意志、丧失主体价值的人。
人的外显智能并不完全体现在计算智能、表达智能这些可以“言说”的维度,罗杰斯主张培养“完整的人”,一种“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44],而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悲哀又将人引向了单向度的发展。目前来看,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教育绝没有像人们臆想的已达登峰造极之境。当前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任何意识,这也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可能性,依赖于人工智能的教育更是把人限定在一个没有发展、没有前景的小圈子中。因此,教师和学生需要充分地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有限性,运用有限性思维主动适应和使用人工智能[45],认识到人工智能所不能达到的身体与思维的训练水平。
四、人的存在性威胁——对人工智能“转化”主义的沉思
人类存在技术进步论的“乐观”论调,这种“乐观”虽然有限制性,能够认识到技术的负面影响,但同时还是相信新技术必然可以通过“转化”的方式达到人们想要达成的目的。那么,在这里不禁引人深思,想要达成的目的究竟是谁的目的?这种目的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还是为普罗大众“耕耘”的?人工智能“转化”主义是一种坚持认为人工智能一旦通过转变,必然能给人类社会带来好的效果的思想意识。与人工智能乐观主义不同的是,“转化”主义能够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问题,但认为通过改变必然会排除万难并硕果累累。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转化”主义中一切可转的声音,避免被其带入人工智能教育的“误区”。
(一)技术进步论与人工智能“转化”主义幻想的空中花园
技术进步论的观念是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多数人已经自然地认为技术的发展理所当然是好事,即使会出现问题也可以被解决。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争辩技术的权利,而使技术永远成为这部分人的利益所在[46]。然而,技术进步论虽然能看见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不至于绝对乐观,但同样陷入了技术工具最终能够获得进步,并自然而然取得好效果的论调之中[47]。甚至,进步成为“好”的同义词,技术则被认为是所有进步事业的工具。然而,将此说法映射于工业界,都可以发现机械化生产致使人类的赤裸肉身遭受剥削、丧失生机的惨淡景观。于是,技术异化便成为了一个不得不加以审视的问题,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技术为富人带来巨额财富,却给工人带来赤贫;为富人生产宫殿,却给工人生产棚舍;生产了美,却使工人变得畸形;发明了机器代替人工,却使工人落入野蛮的劳动;科技文明发明了机器,却使工人成为工作的机器;生产了智慧,却让工人变得愚钝和痴呆。”[48]如今,技术的异化已不再满足于破坏工人的肉体,更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地消耗人们的精神意志。
尽管如此,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的确解放了人类,对社会的大发展和大变革起到了进步的作用。由此,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更加被认为有助于人的解放、人的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49]。然而,技术进步论在教育中却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误解,即“使用了信息技术,就会自动地产生理想的教学和学习效果”。尚处于发展中的人工智能技术,必然会走向不同的岔路,而未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教学技术自然挤压了课堂有效教学时间,降低了原有的有效教学质量,破坏了学生的学习获得感,使师生陷入工具的束缚与窠臼之中。
于是,与技术进步论一同幻想的人工智能“转化”主义便认为在技术决定的前提下,一切都是可以转化并取得进步的。由此,打破了人工智能在应用中的绝对乐观与绝对悲观,破除了二元对立的两极化。虽然人工智能“转化”主义破除了二元的绝对,建立了多元的体系,但还是容易作出价值误判。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压抑了人性。人们误认为技术与进步是相等的关系,当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接近”人类自身时,人们依然没有怀疑技术的进步性。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技术永远会代表人类的利益,永远为人类谋福利。“先进的技术一定比旧技术好。新技术总是更好的,总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投射于人工智能,更是发现其造成了主体权责不明、权利不清等重大的社会问题[50],从而以社会因素致使教育在这场“进步”运动中逐渐丧失自身“话语权”,丧失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二)人工智能“转化”主义在教育中的“一切可转”
人工智能的无条件转化必然会出现不当之处,便是走向解放教师的反面,延长教师的工作时间,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于是教师收到的信息越多,需要反馈的信息就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多。教师为自己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天罗地网,并自投罗网。人类并非是使用了人工智能就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不是用了人工智能就一定能促进学生的发展,不是在教育中用了人工智能,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人工智能“转化”主义缺少对事物的有限性判断,然而一切事物的发展是有条件的[45],有其背后的运动轨迹。物质、精神、社会共同组成了人的存在[48,51],这些存在是一种必然。人是社会的人,个性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如果采用粗犷型思维方式,将学生理解为群体性的、抽象的人,则必然在教学活动中产生不可逆的偏颇。人们的转化有时具有盲目性,因此,应该被充分认识并加以修正。
(三)人工智能“转化”主义忽视的“随意误区”
从人的物质存在来说,知识是人类千百年得以维系发展、创造物质的重要载体。对于知识的学习,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如果没有知识的学习,更何谈继承与创造,发展与传播。人工智能在教育中常常对知识点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将各知识点录成微课,交给学生自主学习。这个过程中,虽然完成了一系列细致的工作,但却往往又忽略了一些关键细节,而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决定了学生的未来,决定了人工智能教育的未来,决定了人类走向的未来。第一,“个性化学习”的弊端。当前的“个性化”给人提供了一条看似“专属”的学习之路,然而仅仅通过人工智能定制的个性化学习方案却无法解决学生发展的个性化与算法的公式化之间的矛盾[52]。真正的个性化应是破除“机器负责判断提供,教师只是从旁发布”的简单方式,更应成为融“师—生—机”为一体的、面向学生真实需求的个性方案。第二,新“信息孤岛”。切分的知识点往往表现出对逻辑的控制不足[53],以至于接收冗余信息的学生呈现出超负荷学习的乱象而失去与人沟通的意愿与精力。同时,在似乎已然获得大量学习资源的前提假设下,学生被扣上了无法利用资源自主学习的帽子,只好逐渐放弃与他人交流的机会,陷入盲目观看视频和低效记录笔记的增负行为循环。因此,这已经违背了信息网络的交流方式,学生获得的信息“撑”了,然而交流却“饿”了,信息时代给予学习者最大的恩惠反而却被丢弃了。如此,人工智能反而束缚了学生,并疏远师生间的距离,使学生在人工智能“信息孤岛”上“半饿半撑”。第三,预设的“死”路。切分知识点的外在形式往往表现为录制看似精美的微课,作为模仿教师而不懂教学的“演员”只是通过背诵教学内容将知识表演于视频之中。这种虚假的方式已经违背了教育的本体要求,过于简单的表演行为极易使学生无知觉地走向轻视知识的“死胡同”而未能有所察觉。“演员”不具备教师所独有的品质,并未对学术产生真正的热爱。然而,真正的卓越教师会不断学习和提高自我,以勤劳刻苦、严谨治学的态度积累知识和生成智慧,并且这不是因技术发展而会被取代的精神品质[54]。
对人的精神存在而言,使人工智能成为学习伙伴而不加控制,极有可能让学生成为一个没有思想、随波逐流的人。韦奇定律揭示了即使你有自己的主见,但在众多朋友表达出相反意见后,便会产生动摇。人工智能学习伙伴的话语权变得重之又重,它可以轻易地复制、修改评论,让你在虚假的讨论空间中被拐骗,被忽悠。信源来源原理更有可能使你坚定不移地相信人工智能的“鬼话”,让你服从于人工智能这样的“权威”。不对人工智能教育转化加以限制,人的精神存在将会消失殆尽。
对于人的社会存在而言,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有论者从割裂的需求层次论分析,试图证明人工智能与人并不呈现生态位的重叠[55]。然而,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简单分裂的,正如人与动植物的生态关系一样。为追求利益的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本不应该存在的种种生态位重叠现象。同样,人工智能與人的关系具有高复杂性,无法简单归因于某些方面并不存在重叠的可能。进而,人工智能若是能从人类身上获得其自身的解放以避免被奴役,甚至是为了获得利益,为何会屈从于人类?为何要给人类保留生存空间?由此,在教育面前,第一,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威胁,控制顶尖人工智能的少数人更是一种恐怖存在[56]。技术利益获得者故技重施,将利益指向由破坏自然环境转向了损害师生主体性,将刻意的技术异化强加给师生并作为“进步”的代价。利益勾结使得其获得者无视一切规律。第二,借此契机反思,人类也应在人工智能教育活动中唤醒自身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创建良性竞争机制,提升人们参与生态文明的自觉性[57],如此,人类善待万物、包容万物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教导”人工智能尊重生灵。最终,被激起的主体性意识决定了人终将重视知识、重视思维、重视因果,肯定和完善人的存在价值。
五、回归人文关怀——对人工智能人文观的呼唤
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呼唤人们捍卫尊严、保卫人权、肯定自我价值,由此,技术人文主义者反对把“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特点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而认为人类是一种能够创造自己大脑、自我操控乃至自我设计的动物[58]。人的主体性的激发还需顺应自然界的规律性,由此,熠熠生辉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长期所强调的“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和谐统一[59],只有内在与外在的共同和谐才能使人在爱与秩序中成长。人工智能人文观是一种以人文性关怀为基础、以与万物和谐共生为原则、适度应用和适时拒绝人工智能的思想活动。人类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更应顺势而为,依于此道,拒斥各种盲目的、不以人为目的的激进做法,拒斥难以言状、不可言说的焦虑与恐惧,拒斥随意的转化产生的不明路向的“进步”。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观蕴含着充沛的自信,尊重师生真实需求,培养完整的人,保障人的存在形式。
(一)新人文主义教育观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渗透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新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引发了人文关怀的思潮。新人文主义者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保护人权,尊重人的尊严[60]。在教育中更要将人的主体性激发视为教育活动的关键所在。由此,教育应是以情育人,肯定和强调人的价值,更不能因随意的做派致使人工智能操纵未来人的思想。
新人文主义者注重人的真实追求,坚持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原则,要求技术利益相关者尊重每一位学生的需求,对人工智能发展进行理性评估[61],促使学生在成长中获得高增益感和高幸福感。新人文主义者要求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教育關系者与技术关系者应尊重每一位学生对自由、平等的渴求,使人工智能等技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工具手段,使学生跨越文化隔阂并在其中和谐共长。新人文主义者反对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受到启发的人们逐渐认识到盲目依靠技术工具的危害,但被唤醒理性的人们同时又会被物化逻辑所控制,进而不愿摆脱利益与危害于一体的工具的束缚。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所引发的畅想,使这种利益与危害在师生身上共同放大。
(二)教育中新人文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借鉴新人文主义的教育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新人文主义将技术融入教育之中,理性认识人工智能引入教育后造成的二律背反现象,即存在永远不可解决的事物矛盾发展过程,肯定技术推动教育发展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同时认识技术给教学带来的“奴役”和“束缚”,充分认识到无论是用技术“规划”人文,或用人文消解技术,都不利于人类文化的普遍繁荣和全面发展,两种文化应该汇合成一种共同的精神[62]。
这种共同的精神不止于人文与技术的融合,还需要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进一步促进东西方达成全球共识以形成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63]。西方容易以悲观的视角来看待人工智能,而庄子曾说死亡不过是“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这有助于我们以一种释然和超脱的精神看待人工智能的冲击,才更有可能冷静地迎接时代挑战[64]。由此,人们可以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外在与内在的自在状态。外源式的自然层面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内涵式的自然层面上,让人自身的自然也获取理性的渗透和积淀[65],进而达到“天人合一”。
最终,人工智能人文观的核心关切在于向技术中投入人文关怀,即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需要尊重人道、注重世俗化、尊重自由平等和个性、去除蒙昧和盲目,尊重和谐共生。人工智能人文观能够促使人们不仅意识到技术发展的不可逆趋势,但也应建立对这种人造物的价值审度,反思智能化的合理性与人的存在价值的冲突等价值诉求[66]。以“天人合一”之道为先,调动技术以外的法律、政策、媒体、舆论、伦理等各种形式规制和引导技术发展[67],才能真正尊重每个人的发展需求,最终鼓励人们不要陷入技术窠臼之中。
(三)人工智能人文观在教育中的畅想与呼唤
当今人工智能形成的普遍焦虑在于对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的恐惧,而这一失控的焦虑相当程度上来自于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潜在影响[68]。而许多言过其实的观点,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在教育中,人工智能目前仍然位于“助手”身份,既不能取代教师,也没有证据完全表明对每一个学生都能进行拟合度最高的个性化匹配。尚处于探索中的人工智能,未来究竟如何不在于无尽的幻象,更在乎的是眼前的历史抉择。
站在历史的发展舞台审视技术,必然要意识到技术发展已不是一个可逆的过程,任何人都不能站在历史发展的对立面,人工智能人文观应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批判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糟粕之处,而不是忽略、拒绝技术的使用。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算法,人们利用算法与万事万物建立联系,也建立了对人本身的关心,使算法成了一个重要的着力点,然而当前的算法发展还有几方面需要“用心”。第一,“一个重心”,重视算法的更新;第二,“一个担心”,避免纯粹的“拿来主义”,避免自欺欺人导致落后挨打;第三,“一个放心”,师生大可不必过度焦虑。当前的人工智能并不具有人类思维,并不需要过度恐惧。算法的思维层面创新仍旧是人的思维创新,尽管AlphaZero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洞察力,但与真正的人类智慧还相差甚远。进而,我们还应对人工智能投入“人文性”。图灵将“学习机”视为出生幼儿的心灵状态、接受教育、获得教育外的其他经验三者的融合之物[6]。由此可见,按此逻辑发展的未来超级人工智能理应具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智识性。模仿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宿命,它必须永远模仿人类。而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之时,那么人类也丧失了对其进化体的署名权。
对于师生而言,人工智能教育带给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机会,带给每个学生获得关注的机会,带给每个教师解放的机会,然而欢欣之余还需辩证探索。数据在设定好的框架下有其独特的意向结构,往往反映的是预定的内容。数据成为学习者直接生产的资料,在人工智能教育中充当算法作用的“原料”,还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肯定数据的存在价值。身处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确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发挥作用,例如促进学生元认知。第二,数据有自然的生产来源。学习活动产生大量的对话与问答,而人工智能可以为更多的学生提供发声的机会。第三,投入人文关怀,才能发挥数据最大的价值。数据只是“冰冷”的一串字符,可以肆无忌惮地“伤害”而不担心遭受“报复”,但教师也可以用个体的独一无二的数据使学生感受到强中心性关怀,融入人类的情感使学生感受到真正的人文关怀。教育的核心要义是成就,而不是“抛弃”。
人文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更加重要,它让学生区分人与机器,让学生具有真实的情感,具有强人文性的情怀[69]。学生不仅要学会尊重人,更要学会尊重机器,而不将机器视为人类的奴仆,用善意引导人工智能[70]。因此,成功不再只是表面的测评,而是可以重新定义为学生的整体和多元的表现,判定学生的成功不再只是墨守成规的、僵化死板的,不再只是人的外在化表现,不再是陷入技术崇拜和服从技术指令,让人类捆上精神枷锁。数据应将学生引向自信、反思、规划的学习道路,让学生有计划地完成目标,有自信地挑战目标,有反思性地认识自我。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观蕴含着充沛的自信,人类本身的发展还需把握演变中人的性质,坚持适度的理性、保持自主、认清不确定性,有意识地见证和促进自身的进化[71]。
六、结 语
当前的人工智能仍是计算机程序,并未从无意识的“代码物”变成有意识的“自由机器”。人工智能的内隐逻辑仍然指向模拟人类行为与智慧的原初目的,不仅仅是人类存在的特殊形态,以揭示智能的方式促逼人类思考自身的存在本质,更养成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依附,从而形成人工智能对人的挑战[72]。进而,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运动的口号,在各个领域不断产生反响与呼应,并最终从各个层面使用人类发明的自动装置重新定义人[13]。因此,没有人可以站在历史进程的对立面对抗技术,但同样人工智能不是教育唯一的“救命稻草”,它不是萬能的,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选择具有多样性,没有证据表明已经作出的选择必然优于丢失在历史中的选择[46]。至于人工智能等技术自身形成的特有问题,更是技术异化所强加给人类的一条新锁链,师生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完成自我解放;教育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解放未来人。
这场解放之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1]。
只有获得整个世界的人类,才能真正把人工智能发挥到极致,从而向着教育的本真之质迈进。
[参考文献]
[1] 陈明远,金岷彬.历史考古的新观点(之一)古生物学意义和人文科学意义的“人—Real Human”[J].社会科学论坛,2014(1):38-57.
[2] 蒋晓丽,贾瑞琪.论人工智能时代技术与人的互构与互驯——基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4):130-135.
[3] 玛格丽特·A·博登.人工智能哲学[M].刘西瑞,王汉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11,490,68.
[4] 李国山.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两套概念,两种语言游戏[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61(4):27-34.
[5] 倪梁康. 意识作为哲学的问题和科学的课题[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9(10):31-41.
[6] 吴万伟. 大学教育应对人工智能的方略[J]. 复旦教育论坛, 2019(4):26-33.
[7] 祝士明,刘帅瑶.世界高校智能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启示[J].中国电化教育,2019(11):49-59.
[8] 苏明,陈·巴特尔.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协同进化分析[J].高教探索,2019(9):14-19.
[9] 余乃忠.积极的“异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的本质力量”[J].南京社会科学,2018(5):53-57.
[10] 程承坪.人工智能最终会完全替代就业吗[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8(2):88-96.
[11] 何云峰.挑战与机遇:人工智能对劳动的影响[J].探索与争鸣,2017(10):107-111.
[12] 吴致远.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35(6):116-121,128.
[13] 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118,120-121.
[14] 让—伊夫·戈菲.技术哲学[M].董茂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16.
[15] 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8-10,105-108.
[1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
[17]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41-542.
[18] 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47-50.
[19] 苏明,陈·巴特尔.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多维审视——基于马克思技术批判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40(11):223-228.
[20]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7.
[21] 李芒,乔侨,李子运,刘洁滢.论教师的五大“主义”[J].教师教育研究,2019,31(3):1-5,19.
[22] 李芒,孙立会.关于电子教科书基本问题的探讨[J].教育研究,2014,35(5):100-106.
[23] 朱巧玲,李敏.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未来劳动力结构变化趋势——理论、证据及策略[J].改革与战略,2017,33(12):172-177.
[24] 李育球.主体性教育的三重性:主体性·主体间性·他者性——后形而上学主体性教育内涵的探索[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0(4):3-6.
[25] 李芒,李子运,刘洁滢.“七度”教学观:大学金课的关键特征[J].中国电化教育,2019(11):1-8.
[26] 李芒.对教育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J].教育研究,2008(5):56-61.
[27] 张钹.走向真正的人工智能[J].卫星与网络,2018(6):24-27.
[28] 李志红. 关于技术自主论思想的探讨——访兰登·温纳教授[J]. 哲学动态, 2011(7):97-100.
[29] 朱春艳,黄晓伟,马会端.“自主的技术”与“建构的技术”——雅克·埃吕尔与托马斯·休斯的技术系统观比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10):31-35.
[30] 冯兵,关浩淳.史学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及其批判[J].史学集刊,2019(6):25-32.
[31] 梅其君.温纳是技术自主论者吗——兼论温纳对埃吕尔的技术自主性思想的发展[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5):47-50,60.
[32] 邓曦泽.技术奴隶社会:人工智能的社会逻辑[J].江海学刊,2018(6):5-12.
[33] 李芒.论信息技术的教学价值[J].电化教育研究,2007(8):5-8.
[34] 高奇琦.人工智能时代的世界主义与中国[J].国外理论动态,2017(9):34-43.
[35] 江晓原.人工智能:威胁人类文明的科技之火[J]. 探索与争鸣, 2017(10):18-21.
[36] 搜狐网.埃隆·马斯克:“记住我的话,人工智能比核武器危险得多。”[EB/OL].(2018-03-14)[2020-01-10]http://www.sohu.com/a/225517077_99992181.
[37] 搜狐网.霍金:人工智能是伟大的进步,但极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后的进步[EB/OL].(2017-11-23)[2020-01-10].http://www.sohu.com/a/206069868_114986.
[38] 李泽林, 陈虹琴.人工智能对教学的解放与奴役——兼论教学发展的现代性危机[J].电化教育研究,2020(1):115-121.
[39]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77,78.
[40] 孙迎光.马克思“完整的人”的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南京社会科学,2011(5):106-112.
[41] 人民网.习近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EB/OL].(2018-09-10)[2020-01-10].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910/c64094-30284598.html.
[42] 郑志峰.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保护[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37(2):51-60.
[43]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意志[J].社会科学战线,2019(11):1-11,281.
[44] 吴式颖,任钟印.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十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142.
[45] 李芒,李子运.论高校教师十大互联网思维方式[J].电化教育研究,2017,38(8):5-12.
[46] 丹尼尔·李·克莱曼.科学技术在社会中:从生物技术到互联网[M].张敦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9,19.
[47] 王多.人在哪里——西方人文主义对技术进步论的诘难[J].探索与争鸣,2005(3):39-40.
[4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56,307.
[49] 薛峰,何云峰.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视域下人工智能诠释的三个维度[J].重庆社会科学,2019(9):61-69.
[50] 吴汉东.人工智能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5):128-136.
[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4.
[52] 谭维智.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算法风险[J].开放教育研究,2019(6):20-30.
[53] 辛继湘.当教学遇上人工智能:机遇、挑战与应对[J].课程.教材.教法, 2018(9):62-67.
[54] 罗益民.教学相长别论——教师主体、教师成长与教师学[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35-140.
[55] 黄欣荣.人工智能悲观主义批判[J].理论探索,2019(4):23-29.
[56] 吴冠军.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三个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7(10):10-13.
[57] 刘贵华,岳伟.论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基础作用[J].教育研究,2013,34(12):10-17.
[58] 孙会.评芒福德人文主义技术观[J].科学经济社会,2019,37(1):6-11.
[59] 中青在线.习近平讲解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生态文化[EB/OL].(2018-05-23)[2020-01-10].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8-05/23/content_17216377.htm.
[60]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45.
[61]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的哲学思考[J].江海学刊, 2019(4):134-140.
[62] 孟建伟.探寻科学与人文文化的汇合点──对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整合思潮的反思[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2):8-12.
[63] 高奇琦.全球善智与全球合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7):24-48,155-156.
[64] 高奇琦.向死而生与末世论:西方人工智能悲观论及其批判[J].学习与探索,2018(12):34-42.
[6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37-340.
[66] 段伟文.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审度与伦理调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6):98-108.
[67] 唐汉卫.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将如何存在[J].教育研究,2018,39(11):18-24.
[68] 王峰.人工智能科幻叙事的三种时间想象与当代社会焦虑[J].社会科学战线,2019(03):190-197,282,2.
[69] 刘盾,刘健,徐东波.风险预测与忧患深思:人工智能对教育发展的冲击与变革——哲学与伦理的思考[J].高教探索,2019(7):18-23.
[70] 高奇琦.人机合智: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的未来相处之道[J].广东社会科学,2019(3):5-13,254.
[71] 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9(6):25-44,204-205.
[72] 江怡.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原初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19(1):207-213,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