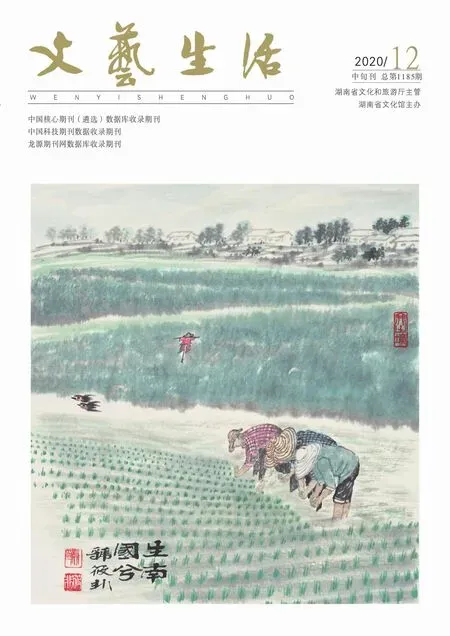借“舞俑”来一场断章式的历史激活
——浅谈“培青计划”舞蹈作品《俑2》
2020-04-08成瑶
成 瑶
(北京舞蹈学院,北京100081)
一、“断章式”的舞蹈结构:独、双、群的组舞设置
在舞蹈作品的编创过程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语言”的功能,不同于大部分舞蹈作品“起、承、转、合”的安排与布局,《俑2》这一作品采用了一种类似“段章式”的舞蹈结构。在文学文体中,有一种较为独特的文体格式—“断章式”,其特点在于没有严格意义上开头结尾的整体布局,而是抓住主题,一语中的,有时它可以是几句话,有时也可以是几段话。在《俑2》中,其组舞形式的设置与编排似乎也颇有“断章式”的丝丝韵味。
在《俑2》中,编导田湉在原有群舞的基础上,将群舞再拆分、细化、雕琢,将其呈现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十人舞的组舞形式,舞段与舞段间各自独立,都是借“汉代舞俑”的形象,在观众面前建立起一个以“汉代舞俑”为主体的鲜活的意象群。
“断章式”的舞段安排并不意味着不顾全整体舞蹈作品的风格与内容,舞段与舞段间彼此孤立,而更多地是在一种统一主题、统一题材的追求下,以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呈现出编导所要传达的观念与意图。在《俑2》长达半个小时的作品中,我没有刻意地留意过每个舞段所占用的时长,而更多的是在编导营造的氛围中感受与体悟。在独舞中,一束追光下,我仿佛看到了“破土而出”的那份倔强与眼眉微抬间“仰望星空”的期待;再到双人舞,两位舞者嬉闹调皮间抖落了尘埃,让我看到了一段“你来我往”的相遇;深沉的呼吸下,三座舞俑缓缓而出,“古朴厚重”的沉稳令我倾倒;一直到最后十人舞的出现,“联袂成云”的衣袖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历史的绵延。
或许,我们看惯了一些讲究叙事、强调结构的舞蹈作品,在看到《俑2》时会有些许不适应,可《俑2》中每一个舞姿都在陶俑、乐舞俑、汉画像中有迹可循,这样“断章式”的组舞安排,并没有打断舞蹈的意境与我们观看的感受,更多地是于“断”中寻“联”,使舞段相互独立又在整体上相互联结,把历史的样貌与编导的观念在顿挫与流畅间向你娓娓道来。
二、“复活了博物馆”的舞台:光、影、多媒体的跨界结合
编导田湉常认为自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导”与“学者”,更多地认为自己是一名“斜杠青年”,而她的学习经历以及包括《俑2》在内的作品,也的确印证了她对于自己的定义与评价。就像梁戈逻老师说到的“田湉,是一个让我觉得很“珍贵”的舞蹈人。她对世界拥有好奇心,她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她往来于实践与理论之间,丰富彼此,营养彼此。”的确,对田湉老师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之后,我发现她的实践与理论不仅仅局限于舞蹈,她学习设计、灯光、影像,还积极与沙画师、泥塑家等合作创作,《俑2》便让我看到了一些舞蹈创作中跨界合作的可能性。
《俑2》开篇的独舞片段中,编导采取了舞者与影像对映成舞的方式,舞者站立剧场中央,一束顶光从头顶落下,随现场的鼓声响起,我们看到舞俑以一种正面的朝向舞动,而与此同时,饶有趣味的是,舞者背后的大屏幕上借助投影仪所映射的却是舞者的背面。一正一反,一前一后,一种类似3D 的视觉效果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这不免让我想起以前每每去往博物馆、展览馆时,我们总想围着一件文物360 度的看一圈,彷佛这样才能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而在《俑2》中便实现了我的这种“好奇心”,我们坐在剧场不用移动、不用探头,就可以清晰地欣赏着舞台上这座“舞俑”,时不时地还能感悟到李白诗中那所谓“对影成三人”的意境。
如果说独舞的舞段唤起了我置身博物馆的相同体验,那么《俑2》中三人舞的设计就更加地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三人舞蹈时的舞台就像一个“复活了”的博物馆,静静地,它就在那里。之所以称其为“复活了”的博物馆,更多地是来自于光、影、多媒体跨界结合下,所营造出的一种“烛照感”与“陈列感”,提到博物馆里的文物,我们都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细细回想,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个个出土文物被整整齐齐地陈列在馆中,他们分别被罩在一个全透明的方形玻璃壳中,玻璃罩的上面会有一盏幽暗昏黄的射灯准确地照映在文物身上,这种视觉效果就像一根蜡烛燃烧放射出的光源于昏暗中照射着你的眼睛一样,是聚焦,也是定格。
三位舞者身着素黄的袖袍,身体与脚下的方形垫子一起被包裹在服装之中,在每束顶光的映射下,真的就好似那方形玻璃罩中的“舞俑”文物,这样的“烛照感”与“陈列感”,就是我在《俑2》中感受最深的地方。舞者在剧场中“复活”的不仅仅是古代的“舞俑”文物,更营造了一个“复活了的博物馆”,观众就这样置身其中,实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跨越。而这样的跨越,正是田湉借助多媒体的跨界所带来的。此刻,不再历史是历史,你我是你我,我们与舞俑“同呼吸”,在方寸舞台上实现了“天涯共此时”的美好。
三、我们与“俑”在当下的相遇
在限制中实现对身体的“重构”我们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的确留给了我们后辈极其珍贵的文化财富,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属于时间所记录的,却并不真正属于我们,只有我们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自己与历史发生关系,产生某些有趣味的化学反应时,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才会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才会拥有我们当下这辈人的时代烙印。
正如编导田湉在谈及《俑2》的创作理念时,所说到的那样:“舞蹈是转瞬即逝的。古代舞蹈的“真相”已然逝去或大部分失去,我们只能通过博物馆里的舞俑形态或敦煌壁画上的舞俑形态,来对古代舞蹈进行思考。所以,《俑》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个从“俑”到“人”,塑造汉代舞俑“活”形象的创作;也是将“过去的”与“现在的”相连接,让古代舞蹈的“真相”与现代相重逢的一部作品。”因此,我们与“俑”在当下相遇,在《俑2》中尝试完成一场与历史的游玩。
这样的相遇与游玩,不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冒险之旅,其可谓处处有限制,每每有束缚,《俑2》就是田湉在限制中实现了对身体的“重构”。对于《俑2》这一作品的创作,其最大的限制便是历史与身体间的限制。《俑2》的创作原型来源于真实的舞俑文物,舞俑是静止的,舞蹈却是相对流动的,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实现彼此舞姿造型间的连接就是编导所面临的一层限制。其次,不同于芭蕾大开大合、抬腿旋胯的身体使用,舞俑相对沉稳、古朴内敛的身体造型也是舞蹈编创中的另一限制。
那么如何突破这样的限制,在《俑2》中构建起新的身体呢?在我看来,便是田湉对历史及身体做出的一种“重构”。“‘重建’和‘复现’的古典舞,都需要对过去‘原本’进行恢复;其区别在于: 对过去‘原本’遗留至今的依托程度不同。比如一件古瓷器被打破了,我们可以用胶把碎片“黏”起来以使这件瓷器“还原”,我们几乎拥有所有的“原本”,所以恢复程度就高,这就是“复现”。然而,西安的大雁塔被毁掉了,只剩下了图纸,那么我们按遗留下来的图纸重新建构大雁塔,让它大致贴近“图纸”的模样,这其中就必须通过想象来“复建”或“重建”使其“还原”,原因是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在了。”①这样的“重构”是一种“新解释”,她将舞俑、汉画像中的舞姿借助史料整合研究后得出的一种艺术直觉力,实现了彼此间的连接,即舞的动律,她以一种动词的作用串联“来”和“去”的中间环节。如果说舞姿造型是《俑2》创作的风格所在,那么动势连接则是专属于《俑2》的舞蹈韵律, 田湉借助博物馆里的“舞俑”形象并将其激活,不仅让观众感知到了历史的生命力,更建构起一个立足当下、包孕过去、又奔向未来的空间场。
尽管《俑2》在当下还尚未构成一种经典的作用与意义,“但是它的出现,对于推动古典舞创作走向无疑提供了一种新颖并或可参照的积极可能。”②或许就像晚唐诗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所言那样:“乘之欲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四、结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被时间积淀与记录,而舞蹈专业的发展也离不开一批又一批在历史长河中踏实前行的“引路人”,只有将过去与现在搭建起一道沟通、连接的有效桥梁,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才会拥有我们当下这辈人的时代烙印。适时探究,永不停步,作品《俑2》的出现或许就是一种继承与发展之间、探索与创新之间的积极尝试,一颦一簇,一舞一动间,汉唐文化绝妙之美立现眼前。
注释:
①田湉.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构形:“重建”与“复现,2018.
②黄磊,田湉.历史意识下民族身体的剧场构建——舞作《俑》创作笔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