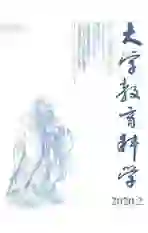大学评教“共谋”行为及其治理路径
2020-04-06蒋贵友郭丽君
蒋贵友 郭丽君
摘要: 随着高校教学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不断强化,基层教学单位与教师在执行上级组织的评教政策时共同谋划,以应对各项教学检查与突发状况,这种共谋行为并不鲜见。大学评教共谋行为根植于复杂的组织制度环境,它的出现与重复再生是高校制度环境与评教实施之间的不兼容所导致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校集权决策、教学惩治机制强化以及组织制度理性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然而,这一非正式行为在周期性生发过程中逐渐合法化与制度化,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教学评价的各个环节。为此,高校应从外部规范的管理制度与内部平衡的发展机制两个层面来共同构建大学评教运行的有序局面。
关键词:教学评价;共谋现象;制度分析;教学发展;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717(2020)02-0105-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校教学评价活动中,基层学院不仅作为教务管理部门与一线教师之间的纽带,还扮演着教师教学活动的监督者与管理者角色。除了评教组织外,高校科层化的内部教学组织均被视作理性的单元,高校通过组织间的有效互动确保教学秩序的稳定。但是,现代学校作为开放系统中的一个动态组织难免受到政策制度、文化观念以及经济政治的影响,这便导致教学活动中出现了诸多与政策不一致的灵活做法[1]。然而,这类变通行为早已成为教学评价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即,基层教学单位常与教师共同谋划应对更上一级组织的政策规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措施联合应付评价过程的各项检查[2]。因此,这便导致评教实践活动严重偏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高校教学评价在提供学生、同行以及督导评教之意见并改进教学质量的同时,也为不同评教组织与主体之间的共谋互动构筑了组织基础与制度环境。具体而言,教师之间的联合变通主要发生在同行评教中,表现为互评高分[3];在学生评教中,教师评学与学生评教的共谋催生了彼此的分数膨胀[4];而教师与基层教学组织间的非正式互动却存在于任何评教场景中,主要表现为对教学丑闻和教学事故的相互遮掩与消息封锁[5]。但对教学事故的遮掩、包庇抑或化解,均与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正式规定相违背。与正式评教相比,这类行为都是通过非正式手段与方式予以落实的,具有隐蔽性与非常规性特征。周雪光早已观察到基层政府间存在的非正式行为,并用“共谋”一词来概括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变通现象[6]。对此,本文亦将教学评价过程中出现的、与制度期待不一致的非正式行为称之为大学评教的共谋行为。
教师、学生与基层教学组织间的共谋是高校不愿意看到甚至是厉行禁止的,但这类行为仍然反复发生。这意味着,教师与组织间的共谋已经牢牢建筑在高校内部的制度基础与组织环境中,并逐渐演变为常态化的非正式行为。在实际过程中,区分度较低的同行评教、走向分数高位的学生评教以及基层教学组织虚报评教等情况均已被教务处与各教学单位所默认与接受。由于高校内部长期存在教学活动的利益协调问题,这一共谋行为逐渐在组织环境中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随着评教共谋行为屡试不爽,它慢慢反复发生、稳定存在,并不断催生出评教制度内的“共享常识”(Common Knowledge)牢牢融入教师与组织的观念体系与行为逻辑中。因此,本文主要着眼于大学评教过程中与正式规则相悖的非正式行为,试图剖析这一行为的具体表现以及发生动因,探寻该现象为何合法地存在于大学场域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路径。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采取质性研究的方法,对20位高校教师与8位学生进行访谈。受访的高校教师中既有从事教学的教授与青年教师,也有参与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价的教务管理者。此外,研究还抽取了受访教师所在高校的学生样本,旨在对教师为主的访谈进行补充。由于单一方法收集资料有限,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叙述的方法策略。受访教师的叙述涉及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属于本体论叙述,主要涉及教学评价制度运行与教师教学过程等内容;第二个层次属于分析层面的叙述,主要将教师个人的叙述放置于高校制度环境与组织变迁中予以考察,这有助于理解不同教师与基层院系的评教互动情况。
除了叙述与访谈外,本文还通过课堂观察、制度文本分析与访谈资料进行三角互證,进一步核准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在资料搜集中,本研究通过三种策略以确保分析资料符合研究所指向的问题。首先,研究进行了历时较长且反复多轮的访谈与观察,这不仅强化了教师的评教经验,还促进了双方对于评教共谋内涵的理解。其次,为了获取访谈资料的最大饱和信息,研究选取不同地区、院校层次以及教龄职称的教师进行深度访谈,直到多名教师的访谈资料没有呈现新的信息特征时才结束访谈工作。最后,本研究不断进行反思与比较,从受访者的回答出发进一步反思访谈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以及失误,确保资料处理过程客观有效。总之,本文围绕问题展开调查,将访谈资料进行处理并转化为概念工具与分析框架,力争回答大学评教共谋行为发生的深层原因。
三、大学评教共谋行为的组织制度分析
“共谋行为”研究早先出现在经济学领域,意指几个大公司通过非正式手段瓜分市场,谋求垄断地位的经济行为[7]。在评教过程中的共谋行为主要是指高校教师与不同评教主体相互联合,采取各种对策应对更上级部门的教学评价或教学检查以达成个人或组织目标。基于组织制度的分析,这种非正式的评教共谋主要是由于高校组织环境与评教制度实施间的不兼容及其矛盾所导致的。
(一)制度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的矛盾
高校教学评价制度具有统一的制度效力与规制权威。教务处作为评教活动的组织者与实施者,通过多主体评教对各教学单位以及教师教学进行标准化考核。但由于实施统一的评教制度成本过大,教务处可能会将部分评教权限委托给基层教学组织,让学院自主开展内部教学质量评价与监控工作。于是,在评教任务的发包过程中,权力分配、内部控制与经济刺激成为组织内部有效治理与稳定互动的主要措施[8]。除了赋予评教自主权外,高校还通过设置校院两级教务管理的垂直化组织以及将评教实施效果与教学单位的目标考核挂钩,以便通过内部控制与利益刺激维系教学评价制度效力与实施效果的统一性。但是,评教制度的统一性也给予了基层学院更大的执行空间。由于校、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基层院系拥有对评教形式与数据采集等内容的决定权与解释权。对于教务处而言,囿于有限的制度激励效应与不完善的制度设计,他们只能将基层数据作为正式的教学质量评估结果予以采纳。
评教制度执行灵活性存在多种形式。一是制度运行本身存在灵活空间。在行政发包过程中,评教权限被交付给基层学院的同时,也拓宽了学院灵活处理的制度空间。二是基层学院运用不同手段“拼凑应对”以完成评教任务。在制度性的教学检查中,基层院系存在诸多成果替换、信息造假的拼凑行为,这是教学管理与运行中的效率机制所决定的。三是即使评教制度是合理的,但是一旦嵌入到多元制度背景中,不管组织还是个人都可能会围绕利益这个核心点灵活操作。由于教务处有限度的督查范围与多层次的评教范围之间的矛盾对立,导致了评教徇私舞弊以及结果虚报等现象层出不穷。随着基层组织灵活性被不断增大,教师与基层学院间的共谋行为将被赋予更多的合法性基础,也即制度统一性与执行灵活性之间的矛盾成就了评教共谋的组织基础与制度环境。
(二)教学惩治强度与组织目标替代的冲突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大学评教中“评”的工具理性不断被强化,而“教”的价值理性被逐渐遮蔽、异化甚至是集体性失语。二者力量此消彼长的现象导致了评教的激励与惩治失当[9]。通常而言,教学评价结果被用作奖优罚劣的依据,而这一制度性奖惩机制仅覆盖少数教师群体,使得大多数教师绝缘于评教激励。与此相反,高校为了维系教学质量的最后底线,通常建立了与激励强度截然不同的惩治强度。一旦上级组织发现教师教学事故,基层组织与教师个人在考核中将会面临一票否决。然而,这一惩治机制实际上很少在教学事故预防和发生时发挥作用,常常还适得其反。究其缘由,应在于教学事故的惩治目标与基层教学单位的组织目标相冲突。正是由于制度执行过程中矛盾与冲突的存在,不仅助推了作为惩治对象的组织与教师等利益相关者相互联合,为二者间共谋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前提性条件,而且还进一步导致了上级组织的惩治目标被基层教学组织的其他目标所替代。
在教学事故或者评教结果产生后,基层学院的组织目标通常不是启动审查以及启动惩治程序,而是通过说服、作假以及胁迫等方式应付或者阻止相关人员将信息上报。具体而言,高校对基层教学单位以及教师有较强的惩治力度,其结果表现为扣除目标管理分、一票否决以及取消评优等。这一严厉的教学考核机制,迫使基层教学组织与教师发生非正式与隐蔽的共谋行为,以便替换掉上级组织的惩治目标而使其免于处罚。这一目标替代现象在评教活动中层出不穷且随着教学惩治力度越大,组织内部的替代目标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更进一步地催生教师与基层教学组织间的共谋行为。
(三)组织制度理性化与基层关系人情化的悖论
组织与制度是现代社会理性原则下的产物。高校通过评教内容条目化、管理层级化与保障体系化等方式,不仅帮助教师在学生评教、同行评教或督导评教中获取不同立场的意见与反馈,还使教学活动在评教制度约束与规训下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根据组织实施与制度设计的理性原则,正式的评教行为应该取代非正式的共谋行为。但是在实际评教中,教师与教学组织、教学组织与管理组织间的对话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通过非正式的特殊关系予以维持并且逐渐强化。这是因为科层化的行政部门与扁平化的学术机构相互交错为行政人员与基层教师之间的对话、交往乃至建立社会关系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同时并存创造了条件。对于教师或者基层组织而言,即使评教活动是一项常规化的组织任务,但也需要防范伴随着评教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出于对风险的管控,教师与基层教学组织的非正式互动程度被逐渐强化,并演变为人情化了的基层关系。
评教过程中的共谋行为建立在非正式关系基础上,而这种关系牢牢嵌入基层关系人情化的社会网络中。这就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与共谋行为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转化的效应递增机制。一方面,评教任务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非正式行为需求滋生了人情化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牢固的基层关系为评教任务过程中的共谋行为赋予了更多的确定性因素。从更深层次来看,正是由于制度悖论空间的存在,共谋行为才会由制度化的管理机制所生产并凭借社会关系反复出现[10]。因此,无论组织制度如何理性,教师或基层学院可能会通过经营社会关系网络来共同抵御评教政策执行所帶来的不确定性,最终达成组织或个人利益的共赢。
四、大学评教过程中的多元共谋行为
大学评教的共谋行为不是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随机化产物,它在周期性生发过程中具备了合法性基础的同时,还以多种形式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因此,高校组织与教师的行为逻辑会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转换。这意味着,不同共谋利益群体在评教主体、标准与环境的变化下,随时发生解体或者扩容。即使教学评价是定时发生与偶然性排查的常规活动,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无处不存在着更广义的多元共谋行为。
(一)信息控制下的包庇行为
相较于教学评价制度,科研评价制度会产生更大的激励与声誉效应,诱发高校教师主动地参与学术活动。谈及教学与科研关系时,多数受访教师表示难以保障充足的教学投入,而且还存在调课、迟到或压缩课时等情况。为了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本,教师将教学时间逐渐让渡于学术活动,并通过非正式手段为教学“减负”。一旦发生教师无故调课或迟到导致学生不满的情况时,基层院系常常会对该类事故进行调解与控制,旨在预防学生及教师将组织内部的问题转变为组织外部的危机。当教学事故发生后,学院会为教师利益进行隐性辩护,表面上努力消解学生的不公情绪并想方设法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是对相关事故进行包庇与控制,防止信息的逐级扩散。因此,学院或教师作为被考核检查的一方总会蛰伏在现实场景与虚拟空间中,或通过控制学生与教师群体中的关键性人物,以完成对教学环节的信息控制。
如果信息控制难以发挥作用,那么基层包庇与作假行为便会应运而生。教务处与学院教务办公室处于一种上下级关系,学院教务秘书理所应当极力配合甚至服从上级教务部门的工作要求。但在现实中,即便教务处控制与监督着评教的各个环节,却因为评教信息的不对称性与模糊性,基层教学组织总是能够策略性地化解教学检查与考核过程中的随机性危机,且拥有对问题解释信息的加工、美化以及策略性回应的优势。这就意味着,无论评教过程中发现何种问题,基层教学组织总是占据信息优势与主动权,并通过包庇、作弊策略影响上级管理部门的检查结果甚至是扭转问题的评判。
(二)共享常识下的身份认同
越上层的行政部门,其教学质量检查频率越低,但所对应的奖惩力度却越大。尽管高校行政与教学呈现为管理与被管理的二元对立关系,但作为被管理者的教师与作为考核方的行政人员,他们共处于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与扁平化的学术组织相互交叉的基层院系中,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亲密但又对立的张力中。通常而言,高校行政与教学人员之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利益分配上,然而不同的身份归属更是加剧了关系间的紧张。基层学院为了缓和行政与教学人员的冲突与对立,常通过设置制度化的组织活动使行政与学术群体走向融合。这就可能改变了学术共同体与科层组织之间的物理距离,使二者共享一套经验常识与文化规则,并逐步加深彼此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还体现在组织身份的双重属性上,一旦充当考核教师教学的基层教务部门或行政人员面临更高的评教组织时,他们的考核角色随即转变为被考核方。因此,各级评教组织便同时兼具“考核”与“被考核”的双重身份。
这种双重角色为组织中的个人或群体共享一套经验、规则与文化并为上升到集体化的组织认同提供了身份基础。自上而下的组织评教使下级教学单位、管理组织与教师间结成一种暂时性的契约关系,即共同策略性地降低与化解上级组织教学考核的风险。正是组织间的身份默契,原先互为对立与疏离的考核方与被考核方会迅速建立起基于经验与常识的身份认同。而这种局内与局外的身份互换,代表着正式且理性的高校科层权力关系迈向了一种不稳定与非正式的合作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组织制度的统一性与有效性,为评教活动的共谋行为提供了观念认同与文化共享基础。
(三)熟人关系下的制度软约束
基层组织间通过一套认知与情感的共享机制完成身份认同并做出符合利益的共谋行为。这一共谋过程并非完全由身份认同机制所主导,还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熟人关系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以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而人们凭借关系的亲疏远近赋予彼此的权利与义务[11]。高校同样作为熟人社会,这一组织特征使教师被置于立体化的社会网络节点中,拥有了多重维度的人際关系[12]。尽管教学评价是基于组织理性与效率原则的制度安排,但是教师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会生成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以抵御组织制度的强制规范。面对评教制度的理性规约,基于利益需求的高校教师群体会形成非正式化的自然系统,并围绕利益与人情关系而发生群体性共谋行为。基于此,教学评价的考核规则与监督程序逐渐被仪式化与空心化,并由教师群体中所默认的非正式运作手段所取代。
高校熟人社会中同样充斥着人情与面子,此背后勾连出的不同权力源泉成为评教共谋的基本运作方式[13]。一是通过互惠机制达成观念与行动上的默契。评教活动的封闭系统削弱了评教过程与结果的权威性、独立性与公正性。譬如,学生与同行教师会依据与受评教师之间的关系远近而决定教师教学效果的优劣。由于均衡互惠的人情规则,互评高分成为了教师间的资源互换,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具有了不可让渡性且要求接受者必须完成对等的义务与责任。因此,普遍的“教学优秀”成为不同教师群体间的共同选择。二是通过关系网络抵御评教过程中的不确定风险。当教师与评教主体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时,他们在既有的互惠交换中建立起更为长期与稳定的关系网络,并逐渐演化为隐性且合法的利益共生体。特别是极强的惩治机制使教师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这也推动教师与组织内部彼此建立起合作型社会网络,以弱化非人性化的评教规章制度。
四、大学评教共谋行为的治理路径
大学评教共谋行为根植于复杂的组织制度环境,它的出现与重复再生是高校制度环境与评教实施之间的不兼容与矛盾所导致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校集权决策、教学惩治力度强化以及组织制度理性化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为此,高校应从外部规范的管理制度与内部平衡的发展机制两个层面来共同构建大学评教运行的有序局面。
(一)构建评教协同机制,提升评教组织化水平
由于评教制度实施范围较大、参与主体较多以及评价反馈链条较长等因素,导致高校将部分的评教实施权与监督权委托给基层学院。这种权力上的让渡形成了“委托-代理”组织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导致偏离评教制度的灵活执行现象出现。面对评教共谋现象时,高校并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予以惩治,而是秉持不发生教学事故的底线原则进行处理。这一妥协与模糊的态度间接加剧了评教共谋行为的反复发生,最终造成了大学治理的困境。简言之,评教决策与实施的不兼容程度和高校评教决策的集权程度成正比,而评教共谋行为正是高校实施统一制度所应付出的代价。对此,高校理应在评教制度设计与决策过程中将基层学院纳入其中,以便赋予其更大的决策权与参与权,并促使传统的科层化评教组织向扁平化的协商组织转型。但是,高校扁平化的评教组织结构不是松散的联结体,而是结构性的评教协同网络。通过构建评教过程中的协同机制,高校不仅可以有效落实评教组织与主体的权责,还可以引入第三方评教监督机构以便进一步厘清评教决策、实施与监督三者间的职责边界,更大程度地激发与释放评教组织与制度的效能。为了解决评教制度决策与实施相分离的问题,高校有必要通过构建评教过程中的协同治理体系以解决层级分割式评教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失败。其实,构建评教协同机制并不是为了去组织化,而是为了有效评教的再组织化。因此,高校构建评教协调机制,能够通过协商与共治等方式使不同治理主体组成结构化的评教制度体系。
(二)转变评教制度取向,推动教师教学发展
教学评价作为一种教学规范制度,既需要满足作为评价工具的管理效率,又需要维系扎根在教学实践中符合教学价值的合法性基础。但如果基于行政制度上的教学评价逐渐转变为以管理效率作为核心取向,并过度介入到教学活动中进行细密地管控的话,那么,身处管理环境中的基层学院与教师群体为了应对来自上级教学行政部门的管理与问责,便会在评教过程中达成共谋以消解随机评教的不确定风险。当然,教学评价的管理规范功能有其存在价值,但是这种功能被放大到整个教学评价环节便会演化为应付评教的另一种管理困境。针对这一情况,高校有必要在管理规范与教学价值的两种教学评价制度取向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高校应加强内部评教监督与奖惩力度。评教制度的执行灵活性以及组织目标替代的常态化意味着评教过程中的共谋行为的失败代价很小,而教学评价的奖惩机制比较有限。高校除了强化第三方评教组织的监督力度外,还需要设置不同层次与范围的评教激励与惩治机制,以此突破评教共谋行为所形成的利益圈围。另一方面,高校应转变评教制度的管理主义取向。大学评教共谋现象足以说明,持续性的激励或惩治只会为教学管理带来更加僵化与失控的局面。为此,立足于管理规范的基础上,高校还应凸显教学评价制度的发展性功能[14]。这就意味着,教学评价既需要在分等的评教结果中继续进行分类指导,还要求尊重教学差异与呵护教学个性。因此,高校唯有实施管理与培养联动的评教运行机制,才能将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共置于教学质量的连续统一体中,最终实现有机融合,并改变教师与组织之间的对立或利益共生关系,从而消除评教共谋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三)培育评教制度环境,促进教学共识达成
即使正式制度改变了,但非正式约束并没有随之消失,且后者还会与新的正式制度之间产生一种持续的张力,这是由于它们在诸多方面都无法兼容所导致的[15]。同样,高校教学评价虽然转变了制度取向,但是旧有的文化惯习、地方性知识与社会规约仍在教学评价过程中透过非正式约束发挥作用,会使新生的评教制度逐渐仪式化、空心化。那么,除了变更教学评价的正式规则外,高校仍需要重塑适于发展性评教的制度环境,而这背后离不开学术共同体的支持与参与。从知识生产的学术观分析,高校教学评价不仅是知识应用的实践场所,也是不同主体通过评议、诊断与协商方式不断生产新知识的制度土壤。因此,高校应该积极培育以合作与共享为核心的评教制度环境,推动教学层面的学术共同体建设,以此淡化高校熟人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影响效力。再者,高校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会进一步促进教学共识的达成。教学共识是不同主体对于教学的一种共享理解,旨在规范与约束教学组织管理活动与教师教学行动。可以说,学术共同体所达成的教学共识不仅强调不同主体在评教制度决策与实施时所应遵循的默契,而且还通过观念系统影响组织集体的行为逻辑,并以此维护教学秩序。那么,学术共同体的培育与教学共识的达成便会反向营造利于教学发展的评教制度环境,进而有效解决大学评教的共谋问题。
参考文献
[1] 严玉萍.大学共同治理的新局面:基于组织文化和制度领导的视角——以北欧五所大学为例[J].大学教育科学,2018(04):78-83+90.
[2] 刘佳.第四代评价理论视阈下高校教学评价制度的反思与重建[J].教育发展研究,2015(17):56-61.
[3] 郭丽君,蒋贵友.高校教学同行评议的制度化困境研究——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03):100-104.
[4] 哈巍,赵颖.教学相“涨”:高校学生成绩和评教分数双重膨胀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9(01):84-105+243-244.
[5] 孙鳌.分数膨胀的博弈分析[J].现代大学教育,2016 (05):23-27.
[6]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8(06):1-21+243.
[7] 周雪光.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96.
[8]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J].社会,2014(06):1-38.
[9] 郭丽君.走向为教学的评价:地方高校教学评价制度探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06):68-73.
[10] John W.Meyer,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 (02):340-363.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12] 胡娟.熟人社会、科层制与大学治理[J].高等教育研究,2019(02):10-17.
[13]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2-164.
[14] 张男星.以OBE理念推进高校专业教育质量提升[J].大学教育科学,2019(02):11-13+122.
[15] [美]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25.
The Collusion Behavior of University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ath
JIANG Gui-you GUO Li-jun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tendency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rdinary teaching departments and teachers plan together when they implement the evaluation policies organized by their superior authorities, so as to cope with the endless collusion in various teaching inspections and emergencies. The collusion behavior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rooted in the complex organiz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 Its emergence and repeated regeneration are the result of th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Significantly, it is also the unexpected result of the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eaching punishment mechanism,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for teaching evaluation. However, this informal behavior is gradually legaliz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 the process of periodic development, and exists in various aspect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in different for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llusion in evaluating teach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construct an orderly situa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wo aspects, the external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balanc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Key words: teaching evaluation; collusion behavior;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eaching development; governance path
(责任编辑 陈剑光)
收稿日期:2019-11-1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一般课题“大学教师发展视野下的高校教学评价制度研究”(BIA20170209)。
作者简介:蒋贵友(1993-),男,湖南洪江人,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海,200062;郭丽君,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