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
2020-04-06杨超
杨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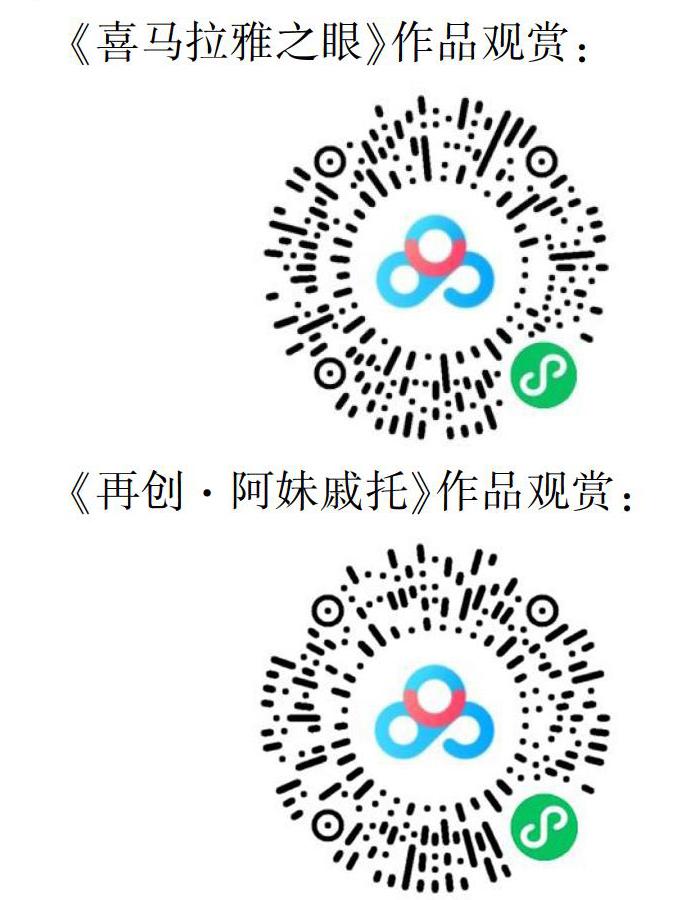


[摘要]近年来街舞作为一种流行文化的现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街舞艺术,已经使亚文化街舞逐渐转向多元化发展,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我封闭的“亚文化社群的舞蹈”环境中。本文主要针对街舞在全球化视野下、多元语境中产生的由意识形态支配的街舞作品现象,通过审美价值观、选材与立意、舞蹈语汇以及调度与构图这四个方面来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进行详细的阐述,并通过具体的作品品鉴与分析来对上述四方面内容进行案例解释,创新性的实现了对街舞进行中国民族化的首次作品实践与理论分析研究,从而为街舞进行中国民族化实践进行一定的可行性参考和实践性创新。
[关键词]街舞;中国民族化;实践;创新
街舞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作为一种城市舞蹈诞生在美国纽约最北端的布朗克斯贫民窟,最早是作为美国黑人城市的一种贫民舞蹈而流行,随后在八十年代则因嘻哈音乐的改变而逐渐形成了old school和new school两种风格的街舞形式[1]。街舞强烈而轻快的节奏、棱角分明而迅捷的肢体语言、极度彰显自我个性的舞蹈表现,使其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青少年的追捧与热爱,逐渐出现在各大赛事以及商业流行的舞蹈MTV中。街舞以一种美国为主导的当代舞蹈体系,目前正以全球化的势态蔓延开来。
但是随着文化全球化与人口迁徙,大众文化的观念也随着其地域变迁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西方流行舞蹈随着“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多元文化”中的“一元”[2]。但是街舞这一文化领域中的艺术形态其从以海洋文明为主的欧美世界传播到以大陆文明为主的中国社会时,西方街舞在文化观念、美学特征、语言符号等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多角度“碰撞”是必然[3],这一碰撞使得西方街舞也应当适应中国的国情来不断调整街舞的姿态和表现内涵,通过中国特有文化特色来为传统欧美街舞注入新的文化血液,而不是一味地模仿甚至抄袭欧美街舞。
近几年对于街舞中国化、民族化的创作与研究也逐渐兴起,如《自觉与自信——浅谈中国街舞民族题材创作》《街舞运动传承中华文化与创新当代艺术融合发展研究》《西方流行舞蹈的“中国化”生态模式》以及《从Tai Ji探析街舞与中国元素的融合》等文章均从不同的角度对于如何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街舞进行了分析研究。他们的共通点均是从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的角度谈到中国街舞应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理念,提出承领、复制西方流行舞蹈的动作、服饰符号,融入戏曲毯子功、武术动作元素,从舞蹈语汇及艺术形态方面进行“中国化”创新,但并未深入探究如何“以他山之石挪为己用”,未从审美价值观、舞蹈语汇特性及艺术形态均深入、具体地剖析东方与西方、民族与流行两种不同语境中的舞蹈特性及其如何融合的问题。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从审美价值观、选材与立意、舞蹈语汇以及调度与构图这四个方面来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进行詳细的阐述,并且通过具体的作品品鉴与解析来对上述四方面内容进行案例剖析,使读者能够更为形象化地了解审美价值观、选材与立意、舞蹈语汇以及调度与构图这四方面内容在街舞中国民族化的具体运用与实践。本文实现了对街舞进行中国民族化的首次研究,并且创新性地实现了将街舞的作品实践与理论分析进行案例融合的首次探讨。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为西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思路与实践借鉴,从而助力于中国街舞的更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民族舞蹈和文化的进一步传承。
一、街舞的民族化审美价值观创新
审美价值观的形成与建立直接影响人们对舞蹈与美的鉴赏和判断,因此,要进行街舞的中国民族化,首先要在审美价值观方面进行定位,即西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康德认为,鉴赏是评判美的能力,而鉴赏能力的形成则与我们的文化语境息息相关。文化随着人类的产生与发展不断变化,表现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东西方截然不同的地域条件、生产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形成了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和文化符号,即文化语境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审美标准和审美价值观。具体来说,街舞盛行的欧美地区的文化由环地中海文明延伸、发展而来,形成海洋文明,因此导致了西方的文化属性中具有冒险、自由、追求创新的精神,强调个体主义;而中国由于地域条件的原因则主要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使得中国文化重农抑商,不突出个人权利和自由,而是讲和谐、讲协作、讲紧密的团队血缘纽带。农耕文明之中,儒、释、道三大教派的相继出现,以中庸之道、缘起性空、天人合一的理念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美的鉴赏。
当前的街舞主要以讲述欧美故事为主,街舞的“一元”表现形式异常普遍,并常常伴以一种快餐式的酷炫形式,这样的快餐文化以及欧美舞蹈形式极大地挤压了我们的传统民族艺术。并且,在当前的街舞比赛舞台上,几乎没有有关中国民族的作品,所有的中国参赛队伍均以欧美街舞的发展为风向标,对欧美街舞顶礼膜拜,导致其比赛作品一味地模仿欧美街舞作品,这样的模仿和发展滞后使得中国舞者在世界街舞舞台上屡屡遭受失败[4]。但是反观同样的亚洲国家日本近几年在国际街舞大赛上的佳绩,这与其在街舞中融合日本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那么,如果中国舞者也能将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象征融合进街舞中,用适合中国舞者的语言去表达中国民族化的街舞作品,这不仅有可能提高中国舞者在国际街舞大赛中的成绩,还能通过更广阔的舞台来进行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中国语境下的街舞发展,势必要凝炼着中国民族符号以及中国的民族化审美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街舞,中国的街舞才有可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站在世界街舞的舞台上。
中国作为一个五千年历史的多元民族国家,无论从精致的叙事资源还是独特的形式资源都对街舞的民族化实践与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丰富的宝藏。具体来说,在叙事资源方面,神秘的西藏王朝《古格王朝》、传说神话《格萨尔王》;彝族的民间传说《火把节的传说》、民间文学《阿诗玛》;中国西部古老民族羌族的神话故事《木姐珠和斗安珠》、民间传说《羊皮鼓》等一系列的民间文学及民间故事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无限的资源;在形式资源方面,戏曲中的青衣水袖、川剧中的变脸、云南彝族的阿妹戚拖舞蹈、羌族中的羊皮鼓舞蹈以及苗族的反排木鼓舞等,这些流淌着中国民族血液的艺术形式不仅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与符号,最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形式保存了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族精神,是有待我们用当代语境去开发的一块宝地。
在实际的街舞比赛中,街舞与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也得到了实践。2017年,笔者参与创作的《喜马拉雅之眼》在美国荣获世界街舞大赛“World Of Dance最佳主题奖”的殊荣;2018年,笔者将贵州晴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阿妹戚托》进行街舞再创,荣获世界街舞大赛“World Of Dance季军”,中国舞蹈家协会“首届全国街舞创作作品展演优秀作品”等荣誉。上述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向世界舞台证明了中国街舞的巨大潜力。鲁迅先生早在《且介亭杂文》中就说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5],要想中国街舞能够立足于国际舞台,我们更应当站在前人的思想高度下,明确以流行的方式传承民族文化,用当代语境创作中国作品,用街舞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创建具有中国精神内核的街舞作品,实现西方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审美价值观的创新,是构成“街舞民族化实践与创新”的核心,也是其艺术行为之一。
二、街舞的民族化选材与立意创新
街舞作为当下的流行语码,不仅是要紧跟时代的脉搏,更要在时代的潮流中树立民族形象,这样的艺术作品才具有生命力。民族化选材与立意的选择以及民族文化内涵形象的凝练、融入,是构成“街舞民族化实践与创新”艺术行为之二。街舞的中国化实践从作品的选材到立意,都需要与民族化的传统理念相融合,既要保留街舞节奏紧密、棱角分明的舞蹈属性,又要具备中国审美的情感表达。
一方面,从街舞的民族化选材来看,为了实践街舞民族化,我们应当在中国民族文化中进行选择与提炼。例如,笔者根据藏传佛教中的智慧眼进行创作,选择了朝圣者形象作为贯穿于第一部街舞中国化实践作品《喜马拉雅之眼》的主线。在该作品创作之前,主创团队深入藏区与当地的老艺人学习与交流,从学习最传统的肢体语言到了解这些传统语言的相关知识;从收集大量的相关材料,到了解当地的民族传说及民族文学,在梳理、提炼、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创作所需要的相关舞蹈语汇。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藏传佛教信仰者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便是朝圣。他们历经数年、不畏艰险,在恶劣的环境下依然朝行夕止地向着目的出发,虔诚并执着,这在电影《冈仁波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而笔者则选取了朝圣者这一经典的中国藏民族形象来进行街舞再创,这一独特的选材使得《喜马拉雅之眼》增添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内涵,其街舞舞蹈的寓意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与升华。
另一方面,从街舞的民族化立意来看,街舞的民族化文化内涵形象实际是这一民族综合内容的具体体现,是将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凝练成一种象征文化系统,形成一种集体人格,而这样一种人格通过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符号,即民族艺术符号[5]。朱良志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中说:“中国人以生命概括天地的本性,天地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生命,都具有生命形態,而且具有活力。生命是一种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一种创造的品质。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就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体、为最高真实的精神。”[6]显然,具有生命哲学的中国艺术从未离开过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因此,融入具有生命感的民族文化内涵形象是作为街舞中国民族化实践最重要的一步。具体来看,笔者在作品《喜马拉雅之眼》中独具匠心地设定了一个贯穿整部作品朝圣者角色,她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她虔诚而笃定地磕着长头,小小的身板在朝圣的途中逐渐老去,在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时,她依然手握转经轮步履蹒跚地向着朝圣目的地走去,眼光笃定而坚毅。群舞演员从双手合十到虔诚朝拜,一个个从生活中提炼的肢体动作成为奠定民族文化内涵形象的基石,这一形象的树立,使这部作品不仅有了人物的温度及血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将藏民族的选材形象融入到作品当中。
又如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贵州晴隆县的原生态舞蹈“阿妹戚托”,汉语意为“姑娘出嫁舞”,俗称“跳脚舞”,是彝族姑娘出嫁前夕举行的传统群体性舞蹈,阿妹戚托以足传情,顿地为节,氛围热烈,表达了对新娘的美好祝福,被誉为“东方踢踏舞”[7]。在500多年的历史文化基因的限定之下,彝族的阿妹戚托不仅是彝族婚俗的一种表演形式,更沉淀了一种彝族新娘灵动、秀丽,娉婷婀娜的集体形象。这是一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女人形象,也是一种燃尽一生化不成半颗舍利,但她们甘愿用此一生为家铺平荆棘的女人形象,一种质朴无华,在平凡中谱写伟大的女人形象。笔者将此形象融入到作品《再创·阿妹戚托》中,创造出两个鲜明的彝族女人形象:一个是出嫁前夕的彝族姑娘,她灵动秀丽、娉婷婀娜,既展现出了嫁前的憧憬,又具有对出嫁后的担心和不舍;另一个形象则是为待嫁女孩做婚鞋的彝族母亲,她们质朴无华,燃尽一生为家付出,平凡而又伟大。这一个个生命个体汇聚成典型的彝族女人集体形象,而笔者则通过艺术形式将这一形象融入到街舞中,使其更加具有生命感和民族文化内涵。
三、街舞的民族化语汇创新
舞蹈语汇是构成舞蹈动作组合的语言材料,它具有传情达意以及支撑舞蹈构图、烘托舞蹈氛围的作用。“人体动律学”创始人鲁道夫·拉班说:“单一动作,只像语言的辞和字,不给人一定的印象,或者一种适合流畅的概念,概念流畅得表现在句子里。动作的序列是演说的句子,从静的世界浮露消息的真正负荷者[8]。即:舞蹈是需要具有传情达意的动作语汇组合而成,以此来传递编导的理念。不同的舞蹈种类,有不同的舞蹈语汇,因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体系,当我们将西方的街舞和东方的民族民间舞进行融合、创新时,实际是在将两种不同语境下诞生的舞蹈语言和该舞种形成的审美体系,进行打破、解构和重组,既要符合西方街舞的审美还要保留东方民族舞的审美特性。而从中国民族舞蹈的语汇特性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舞蹈语汇,可以说有多少个民族就有多少种民族民间舞的语汇特性。下面本文将对与本文实际作品案例相关的藏族舞、彝族舞以及街舞语汇特性进行总结。
(一)藏族舞的语汇特性
藏族舞形式多样,特色鲜明,较常见的藏族舞蹈有弦子、锅庄、踢踏等。关于藏族舞蹈的特性在民间歌谣中也有记载,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9]
从以上歌谣我们可以看出,藏族舞蹈要求男子的上身动作挺拔彪悍,女子含蓄典雅,腰部灵活摇摆,膝盖松弛颤动,双脚灵巧多变、节奏鲜明。
(二)彝族阿妹戚拖的语汇特性
彝族的阿妹戚拖舞蹈主要载体是人體下肢,运用膝关节、髋关节与踝关节的运动变化,形成踢、悠、踏、跨等动作,舞蹈动作整齐、干净利落、节奏欢快,被人们称为东方“踢踏舞”。
(三)街舞的语汇特性
街舞中的old school多以大幅度的动作、力量、速度和炫酷的技巧为舞蹈特性,例如breaking(霹雳舞)中的freeze(定格造型)、powermove(技巧型的力量动作)、popping(机械舞)中的pop(震动)和locking(锁舞)中的wrist twirl(绕腕)。而new school则更注重身体的协调性以及肢体的律动性,以身体上下左右起伏的摆动为特色(up&down),开发肢体的小关节协调,没有规定动作,舞者可以即兴发挥自我表达,更注重舞蹈与音乐的贴合度[11],例如流行天王Micheal Jackson的《Remember the time》。
在进行《喜马拉雅之眼》以及《再创·阿妹戚托》的作品创作中,不仅要包含民族文化内涵形象的塑造,而且在舞动的过程中是需要一个个具体的动作去呈现。这些动作风格不仅需要符合人物形象的塑造,融入民族舞蹈的特性,重点还得符合街舞的审美。当代美国心理学阿恩海姆提出的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每一个现象都是一个完形,即“格式塔”,而任何一个完形都是一个内部张力结构,也就是一种“力的样式”[10]。玛丽·魏格曼说:“力的因素,在舞蹈里比时间因素更重要——变动的动力是舞蹈生命的搏动”[11]。综上所述,“力”是舞蹈启动的按钮,能体现舞者的情绪,因此本文以“力”为出发点,研究两种不同舞蹈中“力”的异同,由此寻找创作动机。
街舞中关于“力”的几种表现:着力反弹的弹力、肌肉动作瞬间爆发的爆发力、瞬间停顿的控制力、小关节快速收放的寸劲儿。在中国民族舞蹈中,不同的民族舞蹈有不同的发力方式,例如,藏族舞在弦子中力的表现为缓而均匀的发力,踢踏舞则是小而快速的发力,锅庄舞的甩袖是以肩带力,袖子舞通过大臂快速的挥动,将袖甩向空中的甩劲儿;彝族阿妹戚托的踏步是利用脚与地面之间着力反弹的弹力,转脚尖则是脚踝轻快灵活的脆劲儿。通过对于上述“力”在不同舞种中的分析,笔者在在《喜马拉雅之眼》的创作中从朝圣者的形象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五体投地”“双手合十”等动作形象,而后再结合街舞、藏族舞中“力”的相近表现,对于小而快速的发力、肌肉瞬间爆发的爆发力,则运用手腕的转动、翻转,形成不同形态双手合十的动作造型;在空间造型方面,笔者根据低、中、高的三个纬度对于朝拜动作进行解构和重组;在道具经幡的使用方面,笔者利用托举、跑动的造型与动态,呈现被风吹起而飘动的经幡。通过解构朝圣者的经典藏文化形象,笔者将中国民族内容与西方街舞相融合,编创出一套新颖、有别于街舞又区别于藏族舞的新舞蹈语汇,它既包含了街舞的审美特性,同时又融合了藏族舞的民族特性。
而在作品《再创·阿妹戚托》中,笔者依然从它本有的动作提取进行改编和再创,保留本有的踢、悠、踏、跨的动作特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将街舞中着力反弹、小关节的寸劲儿和阿妹戚托中转脚尖的灵活脆劲儿的“力”进行融合,将脚踝的开关以及脚尖、脚跟的变化融入到插秧的动作形态中,并在这变化中不断重复插秧的造型,不仅保留了插秧的原本动作,更丰富了视觉变化;在踢板壁及鸭喝水的动作元素上,语汇加入了上肢的协调配合,利用脚与地面着力反弹的同时,将重心与上肢进行配合,呈现更多变的动作形态。这一贵州民族形象与西方街舞的融合也同样使得这一作品实现了中国民族化的实践与创新。
2.舞动节奏的变化
瓦尔特·索雷尔为《美国百科全书》写的“舞蹈”条目说:“舞蹈是人体配合某一节奏连续进行的、有一定空间范围的运动。”[12]凯克林·麦斯杰伊为《美国新知识百科全书》写的“舞蹈”条目说:“舞蹈是身体的一种有节奏的运动”[12]。可见,舞蹈与节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声音的可视化在街舞的审美特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非常注重肢体动作与节奏的契合度以及肢体情绪与音乐情绪的贴合度。这一点早在我国《书·益稷》有记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13]就是拍打着石刀、石斧之类的劳动工具为舞蹈者伴奏,在非洲的舞蹈中,表演者周围的群众常常运用拍打身体或者叫喊的方式为舞蹈者伴奏[11]。因此,笔者在设计动作时不仅改变了民族舞蹈的动律、形态,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其舞蹈的节奏。例如,《阿妹戚托》的舞蹈动作基本是平均2/4、4/4节拍,而笔者将这一平均节拍打破,根据音乐节奏快、慢、强、弱及旋律的抑、扬进行变化,因此动作呈现更贴合音乐表现,像是用身体创作了一首歌曲。笔者通过舞动节奏的变化来打破了原有的框架,从肢体的“力”到节奏的“破”,重新创造出不同的舞动规律,融合中国民族舞蹈的特性进行街舞语汇的再创,通过肢体语言塑造人物形象,创造出符合舞蹈形象的舞蹈语码,是构成“街舞中国化实践”的艺术行为之三,由此实现了街舞的中国民族化语汇创新。
四、街舞的民族化调度与构图创新
调度与构图是舞蹈艺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观点,强调纯形式的审美性质,认为“意味与形式存则俱存,亡则俱亡。”[14]在进行街舞的民族化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根据中国传统舞蹈作品进行分析、梳理,看到作品中经常运用“圆”“线”的调度与构图形成千变万化的画面,一会由中心散开成圆形,一会从圆形流动成S形,一会又是双龙吐珠式的穿插等,整个画面丰富多彩,让人目不暇接,并且每一个调度、构图与舞蹈语汇表达相得益彰,构成具有中国意味的审美形式。再反观国外街舞的作品,我们常看到国外街舞更讲究冲击力与分裂式的调度与构图,因此他们常常运用三角、方块、矩形的几何构图,进行块状切分与层次切割,构成了具有欧美意味的审美形式[12]。
(一)圆
中国文化中对于“圆”赋予了独特的理解及情怀,圆融、圆满、圆通、圆润、圆善的特点,反映出中国和谐、秩序的审美特性。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太极图,是中国古人对圆形、对称、阴阳认识的结晶,象征自然界两种物质势力的对立、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这样的文化基因及哲学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古典艺术,因此“周而复始”、对立、统一,成为了中国古典艺术结构的特性与特点。在舞蹈艺术中,中国古典舞中以“圆”的动势与动律贯穿始终,如“平圆”“立圆”“8字圆”以及“风火轮”中肩部与手臂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圆,都是“圆”在舞蹈中的具体体现。在民族舞蹈中,“圈舞”舞蹈文化在各民族中普遍发生、传承,每当有節庆日,或欢迎尊贵客人时,各民族总会出现围圈而舞、踏歌且舞的“圈舞”现象,从舞蹈构成形式上有“联环型圈舞”“缺口型圈舞”“虚线型圈舞”和“多环型圈舞”,如云南盈江诗蜜瓦底傈僳族“联环型圈舞”,他们通过前手与前面舞者的后手或衣饰相握或相接,形成一个结构完成的圆形;羌族的“萨朗”和蒙古的“安代”他们有部分舞者并不相互通过手或物件相连接,围绕着一个圆心进行绕圆,以“虚线型”方式构成圈舞;纳西族的“热美蹉”则是一种以“缺口型”连接构成圈舞,其首、尾两位舞者并不相连,在环形结构上保留一个“缺口”。综上所述,可以总结出“圆”的调度与构图具有中国意味的形式,不仅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更反映了“中华之美”的理念。
在作品《喜马拉雅之眼》中,笔者将“圆”作为象征人们祈求神灵保佑,寄托美好愿望的寓意。具体而言,笔者将“圆”的调度与构图运用在经幡拉出的瞬间,将圆形呈放射状往外扩散,在舞动的过程中经幡呈时针般转动起来;在“圆”的构图上进行朝拜、双手合十的动作变化,用“虚线型”的方式构成圈舞,为了突出中心的信仰之光,笔者还采用了“缺口型圈舞”的方式舞动;这些调度与构图的运用不仅是起到舞蹈丰富画面的作用,更是考虑到“圆”的寓意与意味。而作品《再创·阿妹戚托》则主要采用了“缺口型圈舞”的构图方式,在舞蹈高潮部分,在姑娘们快速踢、悠、踏脚的过程中逐渐变化形成“缺口型圈舞”,形成圆心围绕,表达对新娘的美好祝福。
(二)线
德国舞蹈大师玛丽·魏格曼说:“空间是舞蹈家真正活动的王国,舞蹈的空间是一个流动的空间”。[15]中国的书法艺术从甲骨文演变,历经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等,书法一直以“线”的形式在时代的空间里流动、变化,散发着艺术魅力。而整体而言,中国书法是以“线”组合文字的艺术形式,主要通过字体的结构章法、线条的流畅与钝点进行组合造型,表现主体的审美情操,而舞蹈亦是如此,通过肢体线条、动态动势、舞姿造型来表现主体的情感意蕴。书法家的笔在纸上疾厉、徐缓都是受到主观情感的驱使,舞蹈动作的行云流水、抑扬顿挫也都受到舞者的情感而推动而,书法作品能够展示书写者的学识、涵养以及折射出书写者的个性,舞蹈作品同样能够展示编者的涵养及其审美个性。所以,书法中通常有“字如其人”的说法,舞蹈中也有“舞如其人”的说法。与西方芭蕾相异趣,中国舞蹈强调的不是动态造型——展示定型舞姿,而是人体运动的过程,即舞蹈在空间中的流动本身——线的运动、线的韵律。张衡《观舞赋》云“连翩终绎,乍续乍绝”;彦真卿《赠裴将军》写“剑舞若游点,随风萦且回。”[16]这些描述都展现了中国舞蹈“线”的特性,这些属于中国特色的“线”在流动的过程中体现“有意味的形式”。
在作品《喜马拉雅之眼》《再创·阿妹戚托》中,笔者将“线”这一构图的中国民族艺术融入其中,不仅有折叠式的两排斜线变纵线,也有流线型的曲线变横线,同时还有行云流水的层次变化。“线”的融入,使得原本街舞中切割式的层次对比变得圆润饱满了,流动的画面也使得原本块状的变化更加灵巧与丰富了。在《喜马拉雅之眼》的画面中,既有象征山路崎岖的曲线,也有象征朝圣之路的斜线,同时还有象征不同人生之路的纵线。这些“线”的运用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处理,更是编者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形式都是编者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运用。
“圆”与“线”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民族符号,它独特的形式成为了中国舞蹈具有代表性的美学范式,将其合理地运用到街舞作品中是构成“街舞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的艺术行为之四。
五、结语
街舞从亚文化转向主流文化时期,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舞蹈形态,舞蹈类型由原本泾渭分明的各类舞种向融合转变,舞蹈种类之间边界模糊。舞蹈形式由原来的竞技性斗舞发展出了表演型齐舞,舞蹈作品也从原来崇尚欧美的风格逐渐多元化地发展,注重舞蹈构图以及舞蹈语言的创新。这促使我们思考和展望中国街舞的更多可能性。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街舞如果想要据有一席之地,应当通过其个性化的民族特色来与传统的西方街舞形成不同,中国街舞应当充分利用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积攒的文化积淀和民族特色来进行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
在本文的研究中,笔者通过街舞的民族化审美价值观创新、民族化选材与立意创新、民族化语汇创新以及民族化调度与构图创新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来对传统西方街舞进行实践与创新,并通过笔者主创的《喜马拉雅之眼》和《再创·阿妹戚托》两部作品来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充分的案例论证和实践创新,将藏族舞蹈和贵州彝族舞蹈的民族文化内涵和立意融入到现有的传统街舞中来,这不仅丰富了街舞的内涵与厚度,更传承了中国传统民族舞蹈和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用当今的舞蹈语言讲述中国老祖宗留下的故事,街舞的中国民族化实践与创新既是一种艺术自觉,也是一种民族自觉。
附:
《喜马拉雅之眼》作品观赏:
《再创·阿妹戚托》作品观赏:
参考文献:
[1]熊玲玲. 街舞:共同体视角下亚裔美国青年人的身份构建[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
[2]刘颖,郭超,孙平.街舞文化全球化及中国的姿态[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21):241-242.
[3]黄河,吴玉华,肖随龙.中国街舞发展回眸与展望[J].体育文化导刊,2016(03):38-41.
[4]赵艳.西方流行舞蹈的“中国化”生态模式[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12(03):56-60.
[5]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37.
[6]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7]杨军.彝族舞蹈“阿妹戚托”传承问题研究——以贵州省晴隆县三宝彝族乡为个案分析[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5).
[8]吕艺生.舞蹈美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376.
[9]强巴曲杰.藏族舞蹈审美特征略探[J].中国藏学,2002(4).
[10]曹琳.阿恩海的姆“张力”理论在艺术作品中的形式解读[J].读天下,2016(9).
[11]李宣霖.“力”在舞蹈中的运用及审美[J].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8.
[12]朱立人.西方芭蕾史纲:舞蹈卷[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13]林同华.中华美学大词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4]谯梁.从真实到装饰——谈形式与内容的关系[J].艺术品鉴,2018(12).
[15]毛毳.论空间在舞蹈中的呈现方式及其特性[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8(2).
[16]袁禾.中国舞蹈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