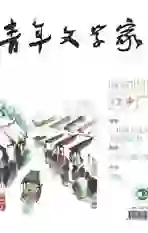“致用”文学传统下的汉魏六朝小说
2020-04-01王小丹
摘 要:在中国人传统的文学观念中,一直存在“致用”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也作实用主义,功用主义。“致用”是付诸实用之意,探究其源流,这种思想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致用”的文学传统也影响到了汉魏六朝小说,这也是汉魏六朝小说算不上是有意识的艺术创造,仍处于雏形阶段的原因之一。本文首先分析中国“致用”文学传统的源流,其次是在这种“致用”传统下的汉魏六朝小说,主要包括政治、宗教、教化方面的创作目的,以及小说内容“真实不诬”、语言风格“趋于史书”的文本体现。
关键词:“致用”;史学传统;“资于政道”;真实不诬
作者简介:王小丹(1996-),女,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標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2
一、中国“致用”文学传统源流
“致用”要求文学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赋予文学以实用功能,因此文学从出现开始,就承载着重大的社会历史使命。它作为古代文学“实用主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源远流长,自成系统。
(一)早期的“致用”理论和实用美学思想
文学“致用论”源远流长,自先秦开始,历代诸多文论家都有相关的论述。作为发端的道家、墨家、法家、儒家都提出过“致用”相关的理论。
首先是道家学派,道家主张“天籁”,认为不加修饰的自然之音就是最完美的,只有去除华而不实的身外之物,人才会更完美;儒家学派辩证地看待艺术的实用性,但也指出艺术会使人堕落,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墨家学派对坚决抵制艺术,认为艺术没有任何实用性;法家学派主张功用主义的文学观,也认为艺术应该有实际功用,韩非子认为只有糟糕的事物才需要依靠修饰来阐释。
伴随着先秦诸家的致用思想,以实用为美的观念也由此产生,在《国语》中武举认为“无害即是美”,让“美”带着功利性的色彩。孔子也提出“以善为美”的思想,孔子将谦虚这种美好品德比作土地,以土为美,充满了功用的意识。这种以实用为美的观念也影响到文学,开创了“致用主义”文学传统。
(二)“致用”文学传统在汉魏六朝的表现
功用主义思想一直流传到汉魏六朝,在汉代达到一个顶峰。罗根泽先生评价两汉是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而《诗经》之所以能一直流传,就在于它的实用功能。
汉代王充秉持文学的“功用主义”原则,十分反感作品中的“虚妄”,他提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1]”文章对社会有用的,越多越好;对社会无用的,只有一章也是多余。到了思想比较活跃的南北朝时期,功用主义思想传统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文学作品中的虚拟成分依旧被反对。刘勰也不认同屈原作品中的浪漫色彩,他提出“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原则,认为文学应该注重真实的内容,而不是只关注华丽的辞藻。
在“致用”文学传统的影响下,汉魏六朝小说被赋予了不容浪漫性、虚拟性和娱乐性的“实用”的使命。但也因为其中的虚构猎奇而被视为“小道”,这持续到晚清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政治之关系》,才使小说的地位受到重视。但梁启超论述的小说参与政治的作用依然是假借传统的实用思想,所以小说还是带着“实用主义”的枷锁。直到今天,关于小说的娱乐性和实用性也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二、创作目的:汉魏六朝小说“致用性”
在中国一直流传下来的致用文学传统下,汉魏六朝小说也明显带有功用主义。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宗教和教化三个方面。
(一)政治:“资于政道”
受史传文学传统的影响,小说从出现开始就被赋予“资于政道”的职责,胡应麟认为小说“有补于世,无害于时”,小说应该讲究实录,有记录史实的功能,只有实录才能为史书提供不同的视角,起到补遗史书的作用。
汉魏六朝小说家也具有自觉服务于政治的意识,他们强调自己有补史之责,把自己的创作看作对历史的补充。东汉郭宪认为自己创作《洞冥记》的初衷是为了补遗史书的空白,书中载录的内容都是史书所未收录的,可以填补史书的缺失和不足。就史书的编撰者来说,也把小说当作“信史”。在晋代的时候,甚至形成了“小说入史”的潮流。《杂说上·史记》中:“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书,省功易阅者”[2],皇家官方在修《晋史》的时候,其中的题材内容也有很多取自于小说,由此可见史学家对小说的实录性的肯定,也肯定了小说“资于政道”的功能。
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观是信史的实录观,小说家和史书编纂者都认为小说具有“资于政道”的使命。小说家采取实录的方法记录历史与社会,所以汉魏六朝的所谓“小说”,实际上是小说家将流传于民间里巷的小家之言编撰而成的“小说书”[3],这些书旨在客观呈现事件的真实面貌,以“资于政道”。
(二)宗教:“自神其教”
汉魏六朝小说除了在政治上“资于政道”之外,还有很多在宗教上是为了自神其教。小说成为宣传宗教的载体,被用来教化民众。教徒是写作小说的重要群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其书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4]。
汉魏六朝时期神仙思想盛行,方士参与小说创作。方士创作小说的目的主要有两种:迎合统治者和获得群众基础。汉代小说中开始出现方士运用神仙方术的情节,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中更多地谈及到方术及神仙鬼怪思想。两汉时期的小说作者多为方士,虞初是汉朝的方士,大概作了九百多篇小说,受小说作者的影响,汉代很多小说内容都涉及到神仙方术。到魏晋时期,由于社会盛行玄言之风,方士创作小说的风气并没有停息,干宝的《搜神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在书中收录了很多神仙鬼怪的事迹,并以此来证明“神道之不诬”。
汉魏六朝除道教之外,越来越多佛教弟子也加入小说写作的行列,比如信佛教的刘义庆;佛家弟子萧子良、陆杲等人,他们也将小说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自神其教”的特定目的。
(三)明道:“教以化之”
“教化”是汉魏六朝小说“致用”的又一基本内容。“教化”将小说作为对民众进行道德感化的一种方式。小说家在作品中寄寓道德伦理思想,由“教”而“化”,从而对民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比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作者是通过韩凭夫妇为了爱情的反抗来宣扬不慕富贵,不惧强暴的美德,鼓励普通劳动人民也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汉魏六朝小说大部分都寄寓道德思想,使读者能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中能够被感化,能自觉恪守道德。这一直影响到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小说戏剧理论,也将文学的道德伦理教育功能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元戏剧家高明借《琵琶记》中人物的来表达“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5]戏剧小说中也寄寓了浓厚的道德伦理思想。
三、“致用”的文本表现
在功用主义的创作目的的统领下,“致用”性也体现文本之中,主要是小说内容上的“真实不诬”和语言风格上的趋近史书。
(一)小说内容:“真实不诬”
我国有着深远的史学传统,至少从西周开始,整个中原文化便是一种史官文化,史学几乎垄断了整个文化,史学著作几乎成了这个时期唯一的著作[6]。史学传统及其强调“实事实录”的精神影响到了汉魏六朝的小说作者,使他们在创作小说时不论是志人还是志怪,都当做曾经发生过的真人实事来记述。
这主要体现在小说家认为自己的创作内容“真实不诬”,所以他们会在小说中特意标明故事的来源是真实可考的。干宝在《搜神记》中表示本书是对“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的记录[7]。除了小说家之外,时人也普遍将小说作为纪实之作,并将记事是否真实作为评价一部小说的标准。
小说追求“真实”虽然有助于在史学渊源深远的文学传统里争得一席之地,吸引更多的读者,但这对小说的消极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它束缚了艺术想象及小说体裁的充分发展,使其长期以来不能摆脱对史学的依附,导致其发展曲折。
(二)语言风格:趋近史书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过程中,汉魏六朝小说以正史的叙事语言风格为主,力求简洁,并遵循史传的“某时某地某人发生了某事”的叙事方式。
小说从出现开始,就依托史书,但古代小说长期处于末流的地位,为了摆脱这种不被重视的地位,小说自觉地依傍正史这种主流文化。因此汉魏六朝小说不仅参照史书纪实的原则,在语言风格上也是趋近史书。汉魏六朝小说的很多篇章都追求语言的精炼,向史书的语言风格靠拢。比如葛洪的《神仙传》中对墨子的记载,用简洁的语言描写了墨子阻止楚国攻宋的事件,用“徒行诣楚,足乃坏,裂赏以裹之,七日七夜到楚”[8]短短十八个字表述墨子一路的艰辛过程,这体现出语言的精炼简短;之后墨子与公输班争论也只用三十余字来介绍。
受“致用”传统的影响,汉魏六朝的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与史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小说也带着强烈的现实功用的意味。
四、小结
中国“致用”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这影响到了汉魏六朝小说,使汉魏六朝小说带有功用主义的色彩。小说写作的目的就不是纯粹为了愉悦和欣赏,而是带有政治、宗教和教化的目的,在这种创作目的的统领下,小说在内容上力求真实,在形式上,语言风格接近于史书。这种“致用”观念为小说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使汉魏六朝小说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小说”。
注释:
[1](东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第466页.
[2](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采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56-457页.
[3]何亮.论“史识”对汉魏六朝小说叙述的干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05):145-150.
[4]鲁迅著:《鲁迅全集》卷九《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83 页.
[5](元)高明著;李芳民改编.《琵琶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61页.
[6]王枝忠著.《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第11页.
[7](晋)干宝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2页.
[8](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421页.
参考文献:
[1]王枝忠著.《汉魏六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2](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3]鲁迅著:《鲁迅全集》卷九《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4](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东汉)王充著;陈蒲清点校.《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
[6](元)高明著;李芳民改编.《琵琶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7](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何亮.
[8论“史识”对汉魏六朝小说叙述的干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05):14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