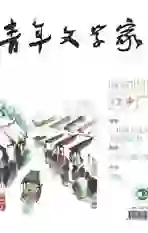子君人物形象分析
2020-04-01郭婕
摘 要:《伤逝》中的子君是被启蒙者、“出走的娜拉”、涓生之妻,除此之外,鲁迅笔下的子君形象显出格外的空洞性。子君形象是涓生构造出来的,反映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语处境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戕害。子君也可视为鲁迅的心理投射,子君和涓生是鲁迅心灵的两個侧面。鲁迅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以女性形象自喻,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实现了性别借代。
关键词:鲁迅;女性主义;性别借代
作者简介:郭婕(1996-),女,汉族,河南人,西安工业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5-0-03
《伤逝》是鲁迅写的唯一一篇有关婚恋主题的小说,在它收录进《彷徨》小说集前,未在任何刊物上公开发表过。有人相信这是鲁迅心灵的独特抒写和歌哭,是独属于鲁迅的,所以不足为外人道。《伤逝》以一对年轻人美好的爱情开篇,最后却以“一伤一逝”结局。学术界比较多认为《伤逝》表现的是鲁迅对启蒙的反思,可与《药》相联系,而本文从子君的人物形象为切入点,以女性主义理论视角探究鲁迅的心境。
一、子君女性形象及其空洞性
子君首先是被启蒙者,她和涓生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涓生对子君讲西方思想和文化,“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在涓生和子君的爱情中、在涓生对子君的启蒙中,子君变成了新人。当她离开涓生的破屋时,她目不斜视,不惧周围人的眼光,并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与子君,既是爱人关系,又是启蒙与被启蒙者的关系,如同老师和学生,这就导致了两人关系的不平等,这也为之后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子君是“出走的娜拉”。为了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子君勇敢地离开了封建家庭,和涓生同居。1918年,《新青年》刊登了剧作《玩偶之家》,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为摆脱痛苦的婚姻家庭出走,成了当时许多青年男女效仿的榜样。娜拉式出走一时成为风潮,鲁迅却冷静的分析出娜拉走后的出路:“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是为什么鲁迅安排子君被涓生抛弃的原因。在《伤逝》中,鲁迅安排子君离家和涓生在一起后,苦于生计,被涓生抛弃,再次回到封建家庭。
子君和涓生在一起后,成为了涓生的妻子。可悲的是,受到启蒙的子君,勇敢叛别封建家庭的子君,她“新生”的落脚点竟然是成为一个人的妻子。这既让人怀疑涓生究竟是怎么启蒙子君的,他究竟是启蒙,还是利用自己在思想和地位上的优势欺骗了子君。其实可以想见,如果子君受到启蒙后,成为了一名革命者,加入了当时的革命大潮,为家国救亡而行动,那即使在动乱的年代壮烈牺牲,是不是比起小说的结局少了几分空虚?而在小说中,她不明不白地死去了,死因模糊、意义模糊,她究竟是为谁而牺牲?
抚卷静思,《伤逝》中的子君形象竟是那么空洞,大多数时候她都是安静的、害羞的、体贴的,作了妻子,她是勤勉的。她从未为自己发过声,她的所有的话,为数不多的几句话,都是在涓生的诱导下说的,从出走到嫁人再到归来,这中间势必经过很大的心理转折,可我们在文本中一无所得。
二、男性构造与女性失语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手记”,我们知道了涓生是小说名义上的作者,整篇文本以涓生的视角叙述的。鲁迅采用第一人称,将涓生的心理暴露无遗。而子君这个人物形象其实是涓生构造出来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子君的形象那么的空洞,因为这个形象是服膺于男性想象的,是被造出来的,故而没有自身的生长力和生命力。
“她目不斜视地骄傲地走了,没有看见;我骄傲地回来。”身在传统社会,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子君,面对未来她是不可能做到完全充满信心、没有丝毫胆怯的。只是因为涓生需要一个坚定勇敢的伴侣,所以子君不应该看见搽雪花膏的小东西的脸。“然而我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没有知道她怎样说或是没有说。” “她却是什么都记得:我的言辞,竟至于读熟了的一般,能够滔滔背诵,”涓生不记得子君的话,却强调子君记得他的话。在涓生的无意识里,觉得子君的话不重要,她只要服膺自己、顺从自己就好了,而既然重视、顺服自己,当然会将自己的话记得牢牢的。“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我和子君说起这,她也领会地点点头。”子君是涓生创造出来的,她不需要有自由的意志,她不需要做出评价和提出自己的见解,她只要静默地“点点头”就好。“但我的心却跳跃着。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涓生勇敢时子君就勇敢,涓生怯弱时子君就怯弱,不必奇怪,子君就是涓生的心理映照,纵使原本的子君不是这样的,但在文本里涓生一定会把子君想象成这样。毕竟本质上十分怯懦的涓生,根本没有勇气直面一个坚强子君的可能存在。正因子君是涓生的心理投射,当我们分析子君的形象时,涓生的形象也会慢慢勾勒出来。
“子君,——不在近旁。她的勇气都失掉了,只为着阿随悲愤,为着做饭出神;然而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丈夫的失业、家庭的重负怎会不使子君憔悴瘦削,但是自私、怯懦的涓生在自己的想象中大概是看不到的。这种“美化”子君,是在为下文抛弃子君找借口,虽然境况已经如此凄惨,子君却没受到波及,那么即便涓生抛下她,她大概也不会有事。这是涓生狡黠地为自己的自私做心理建设,使之合理化。涓生的自私,涓生的想象创造了子君的最有力证据是在得知了子君的死的时候。“真的?”我终于不自觉地问。“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谁知道呢。总之是死了就是了。”像子君这样在当时敢于反叛出走的女性,回归而身死,是多么重大的新闻,可以引为谈资,人们关于她的死应该能说出好几种死法来才合乎人性,流言当是甚嚣尘上的。而涓生竟然不知道,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视而不见”,在涓生的记忆里将其美化为了友人不知道子君是怎么死的。不知道同村人的详细境况,从常理上就说不通。而涓生的话就更耐人寻味了,本来涓生的话的本义应是追问子君的死法,但他说出口竟然是“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但是”十分突兀,为什么要强行转折,联系下一句就能够明了,涓生是在引导对方说不知子君的死因。胆小、没有担当的涓生承担不起他是子君死去的首要原因,就在自己的记忆中,将子君的死刻意“美化”、淡化了。
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涓生创造出了子君,正如男权社会创造了女性,女性没有自主意识,而成为符合男性想象和理想的产物。鲁迅以涓生的视角凝视子君、涓生的话语描述子君,通过子君形象的空洞性反映出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戕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有两条路,要么冒充男性角色进入社会秩序(如革命文学中抹杀女性角色的性别特色的一面),要么成为某人妻,不然在这被规定好的两条路外,“女性便只能是零、混沌、无名、无意义、无称谓、无身份,莫名所生所死之义”。子君的死,就是这种男权社会对女性意义的残酷抹杀的反映,不知死因、不知死的意义、没有了解的必要,再沦为一种可悲的粉饰。
因为传统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性,所以女性长期以来处于失语的可悲境遇。在中国封建社会,女性长期是男性的附庸,制约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社会规训,女性不能受教育、女性不能抛头露面、女性不能从政从商甚至不能从事农工,男权社会的重重围困使女性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声音。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一部文明史几等于男性的历史、男性的传记史。在涓生的手记里,子君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始终处于失语的地位,她的行为、心态,都是通过涓生转述告诉我们的。鲁迅选择以第一人称、以涓生视角写作《伤逝》,既是为了更全面深刻地披露涓生的自私猥琐,也是为了以这种特定的手法表现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处境。
不能发声的子君如同“阁楼上的疯女人”——《简·爱》中罗切斯特的前妻伯莎·美森,她的疯狂浪荡都是由他人描述的,没人知道究竟这是她的真面目、还是被构造出来的。当罗切斯特和简爱约会的时候,她始终被关在阁楼上,而她的最终结局是被大火烧死,不发一言地、始终静默地被烧死了。她像子君一样死得无声无息、无人问津,而连《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堪称一句壮烈。而子君(和伯莎)的悲剧就在于没有涓生以夫的身份的认同、呼应,甚至涓生放弃了子君,两人的感情便不能成为经过秩序滤化和认可的夫妻之情,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无法像刘兰芝那样(焦仲卿之死使刘兰芝的死有了殉节、殉情的高义)引起人们道德上的同情和美感。
三、集体无意识下的性别借代
“以女性形象、女性身份自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个悠久传统。甚至可以说,从《离骚》一直沿袭到《红楼梦》。”在《离骚》中,屈原很多次使用女性作为抒情主人公,以香草美人意象表现他的爱国忧思,香草指代他高洁的品格,美人指代他自身。唐代张籍的《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表面上写一位妇人对丈夫的忠贞,其实是作者以妇人自况,传递对朝廷的忠心、不为高官厚禄所诱的决心。甚至有批评家认为,《红楼梦》中贾宝玉与黛玉、宝钗的关系也可以如此理解,黛玉和宝钗分别是贾宝玉的本我和超我的心理投射。
我们知道,子君的形象来自于涓生的心理投射,那么子君与小说的作者鲁迅有关系吗?鲁迅小说有两大主题,分别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主题。涓生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知识分子,而鲁迅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知识分子主题的小说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孤独者》写成于1925年10月17日,《伤逝》写成于1925年10月21日,间隔只有四天 ,两篇都是万言篇,不可能短时间一蹴而就,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孤独者》和《伤逝》是相近的构思时间里完成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后来都收录在《彷徨》里。
《孤独者》和《在酒楼上》写于五四落潮期,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作者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而“感到寂寞”“荒凉”,甚至迷茫感伤(虽然鲁迅是一个斗士,在经过短期的颓唐,他便能继续坚定自我、不惮于前驱)。鲁迅是在辛亥革命之时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青年,相对于《新青年》的一帮同人,他是一个早早清醒、早早碰壁、对现实悲观消极的老青年了。五四的落潮在他的意料之中,可他仍不免为现实的残酷而痛苦,《彷徨》中的小说都反映了这种心境。
三篇小说的第一个共同点在于它们以“梦醒者”为主人公,他们相应启蒙的潮流,勇敢追求个人独立与自由,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推动国家的进步,却无可奈何地在现实中碰壁。其次,三篇小说都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小说的结局都是悲剧的。还有,《孤独者》和《在酒楼上》都是复调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和“我”是鲁迅心灵的两个侧面,通过两个人物之间的交流表现出鲁迅的内心矛盾,《在酒楼上》也是这样(吕纬甫和“我”)。而《伤逝》也有复调小说的特色,子君和涓生、魏连殳和“我”、吕纬甫和“我”的人物设置,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子君是涓生的心理投射,也可视为鲁迅的心理投射,鲁迅有借子君自比的想法和意味。子君是“出走的娜拉”,子君被涓生抛弃就是在现实中碰壁,子君同青年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期的遭遇何其酷肖,充满激情走出家门,斗志昂扬反抗封建权威,却要遭受现实泼下的冷水。在这一点上,鲁迅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以女性形象自喻,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实现了性别借代。
鲁迅为何要如此呢?中国古代文人中又为何形成以女性自喻的传统?在父权社会中,君臣、父子、男女同构,这是当时固守的封建伦理秩序。在君面前,臣永远是臣;在父面前,子永远是子。作为臣子的众多男性其地位属性都是属阴的,这是其性别意义上的阉割情节,以女性自比是很相宜的,“女性形象装填了他们‘阴属的情感载体”。“被阉割不仅意味着一种性心理焦虑,而且意味着对自身主体职能的焦虑。”鲁迅以子君自比,正暴露了经历再一次打击的痛苦焦虑,而鲁迅的急于掩饰则导致了子君形象的空洞。
涓生启蒙了子君,子君本可以成为涓生的同路人。但涓生抛弃了子君,重回了会所求得生存。涓生对子君说要找寻“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可是自己却重回了旧路(从“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可以推出),可见其虚伪残忍,但涓生以其虚伪自私在革命的浩劫中生存下来。鲁迅心灵的两个侧面分别投射到了涓生和子君身上,涓生代表了鲁迅对成为在革命落潮中出卖同袍之人的恐惧,子君代表了鲁迅对在革命落潮后被抛下的恐惧。鲁迅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呼应了小说集《彷徨之名》,也反映了在五四落潮后独自坚守阵地的焦虑恐惧。
结语:
子君形象的空洞性,既反映出涓生形象的自私虚伪,也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语处境。男权社会创造了女性,女性没有自主意识,而成为符合男性想象和理想的产物。男权社会利用其权力、地位上的优势,抹杀了女性的真实所指,创造了女性的虚妄能指,并使其为男权社会服务。鲁迅特意用第一人称、以涓生的视角展开叙事,就是为了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不幸遭遇和被动处境,对以子君为代表的弱势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子君这个人物形象的设置,还存在鲁迅自比的意味,涓生和子君是鲁迅自我的不同侧面,涓生代表了鲁迅对成为在革命落潮中出卖同袍之人的恐惧,子君代表了鲁迅对在革命落潮后被抛下的恐惧。子君形象的空洞性里,也有对这种焦虑心态的掩饰。对《伤逝》的女性主义解读,相信会给鲁迅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路和视角,更清晰全面地了解鲁迅的心境。
参考文献:
[1]鲁迅. 彷徨[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09.
[2]鲁迅著.鲁迅全集 第1卷 热风 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 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安文军. 病、爱、生计及其他——《孤独者》与《伤逝》的并置阅读[A].《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下)[C].中国现代文学馆,2009:16.
[5]鲁迅著;鲁迅博物馆编校. 彷徨[M].郑州:海燕出版社,201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