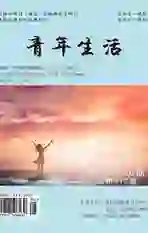五凉时期河西佛教特征简析
2020-03-28吉强
吉强
摘要:佛教于汉代进入中国,五凉时期河西佛教发展壮大,然而并未玄化,其迥异于江左佛教。涅槃学在中原和江左兴起后,河西亦缺失义学的发展,其地以重视行业修行与阴阳之术为主,究其根本在于其地所处位置及其与当地儒学传统之交互影响。
关键词:五凉;河西佛教;玄学化
一、凉州佛教发展简述及其特征
汉武帝西击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设置河西五郡,凉州始划归中原王朝版籍之内。凉土西傍西域,东接关陇,是海运未开之前中原地区与中亚交流之重要通道,张骞通使前已有民间交流,只是未形成规模,汉朝控制河西后,其中转作用更趋明显。其后经由河西至西域的文化交流日渐频仍,佛教亦是自此逐渐东传,进入中原腹地。
五凉,是十六国时期于河西地区先后建立的五个以凉为号的地方政权,分别是汉族张氏之前凉(公元301-376年),氐族吕氏之后凉(公元386-401年),匈奴沮渠氏之北凉(公元397-439年),鲜卑秃发氏之南凉(公元397-414年),汉族李氏之西凉(公元400-421年)。五凉政权多在十六国时期,其时中原战乱,而凉州因远离中土,较为安定。俗谚有言“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即反映了当日之情境。五凉政权世奉释教,广开佛寺,同时又推重儒学,讲授经史,皆不偏废,为河西文化之发展助力颇多。其时先后有天竺、月支、罽宾、康居等国僧人西来弘教,驻锡姑臧、敦煌等处,亦有中土和凉州僧人西行求法,携带梵经东归翻译。在这些僧人的努力之下,凉州佛法之盛,一时誉于中原。
凉州佛典翻译,以中天竺僧人昙无谶为最显,其于北凉沮渠蒙逊时代入姑臧,而其翻译佛典之多,次于罗什之后。其最重要的贡献是译出《大般涅槃经》。涅槃与般若皆是大乘空宗之重要学派,然而般若释空,涅槃讲有,尤其在佛性这一概念上,涅槃所阐述之“一阐提悉有佛性”以法身常住与人皆有佛性对空宗之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是佛教理论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
北魏太延中,拓跋焘平凉,将凉州之众徙于平城,此后凉州佛事渐衰,甚至于不再有高僧出现。在短暂的发展时间内,凉州佛教融合中原与西域文化风格,拥有别具一格的特色,颇殊于中原汉地与江左佛教之发展。
五凉时期短促,未能使凉州成为长久的佛教义学重地,而罗什弟子道生驻锡江左,倡佛性皆有之说,后又得观《涅槃经》,遂于江左广宣涅槃学。《涅槃经》之研究,尔后全移于罗什派学者之手,但因《涅槃经》之率先译自凉州,姑臧亦因之成为涅槃义学之发源地,昙无谶诸弟子于此传道授学,亦颇有可观。
佛教虽然于汉代即传入中国,然其真正繁盛却是在两晋南北朝之际。十六国东晋时期,佛教之南北发展呈现出迥异趋势,五凉之地佛教与长安佛教同江左佛教之差异明显,此种情况颇值得注意。
汉代佛教发展,与中土旧有之谶纬阴阳,五行方术有交融处,或有依附之嫌,此一时代为后人所称之佛教方术化时代,而魏晋时期,玄学盛起,佛教义学与玄学互相交流,彼此影响,儒学玄学化和佛教玄学化并相发展,此一时代则被称作佛教玄学化时代,其于东晋一朝更为显见。
佛教思想之所以在晋代盛行,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利用玄学哲学来解释宣扬般若空学,般若之空,与玄学所谓“贵无”结合,因而大为风行,视其与汉时之寂寂无闻相去悬殊,而此亦为中土佛教发展之一大变。佛教由汉之方术枝属,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静无为之玄致,亦是由于汉魏之际清谈之风繁盛所致。
五凉佛教却与之迥异。凉土佛教较少玄谈。学问高僧重义学讲授但又侧重译经,而民间信仰之众重视佛事供奉,行业修行。如北朝建塔开窟之事业多起于凉州,北凉尤其更盛。且凉土佛教不失阴阳方术之征,此为其虽处两晋之际,却大异于中原佛教与江左佛教之处。抑且不论其所处之地,民族混居,信众之杂,亦为不同。
二、凉州佛教特征差异原因分析
玄学兴起由于儒学之发展演进,其與时代状况多有影响。汉末道家思想发展,儒道兼综融合,汉末清议演变成清谈而兴起,综合影响产生玄学,至何晏王弼以老庄之道诠释儒家经典,则玄学渐盛,故而在与佛教般若学教义有相似之处的情况下互相引发而导致中原地区及江左佛教的玄学化。凉州之地,汉末即有世家大族西迁,而魏晋动荡,流民更盛,其地儒学则多承继汉儒家法,有汉代经学遗风,于清谈涉及较少。故而凉土佛教并未受此风气影响。
后汉末迄至魏晋之世,中原战乱动荡,兵燹流及,百姓四散。世家大族或南迁江左,或经关陇入蜀,而仍有一部分随流民播迁河西。来到河西的儒学世家,基本保留了汉魏旧学,以家学为依托,传授学问,延续了汉儒经学与魏晋才性之学,对于其后隋唐制度之形成有巨大渊源关系。
《魏书》记载程骏就学刘昞,谈及老庄“抱一之言,与性本之旨”,其与儒家学问之要旨实际相通,虽可目做玄学谈问,但亦不属于清谈之类,有别于《世说新语》阮修之与王衍所谈“将无同”,实是汉儒学问在魏晋兼采道家思想的一种自然演进。凉州虽亦不乏老庄之学,却仍守汉儒家法,因此凉土佛教在与汉族世家互相沟通的过程中并未受玄学清谈之影响。沮渠蒙逊等少数民族君主,虽倾心汉化,却实不得玄谈之风。
凉州儒士不受清谈之影响,除保有汉儒旧学外,更是因为清谈于个人进退升迁无太大关系。五凉时期,各割据政权君主皆按汉代旧法,推举文学贤良之士充任官次,并未以清谈为据。西晋却不然,清谈攸关仕进,与东晋时期清谈落于纸上之玄谈不同。清谈由于在河西无太多施展空间,其在河西儒学与佛教之发展中并无太大影响。
五凉时期河西佛教不脱离方术之征,传道诸僧颇有神异,比之于东晋江左与姚秦时期以译经及义学讲授之佛学发展,多有不同之处。《晋书》载“刘弘携左道客居天梯山,然灯悬镜”,天梯山是游览胜地,北凉于此开凿石窟,可见当时方术之士亦盘于凉土,至于普通信众,只在乎寻求超解,却不一定在乎形式,故而其地阴阳道术与佛教有所结合亦是可能。
总而言之,五凉时期,河西地区的佛教地位是重要的。其与中原尤其是与江左佛教特征迥异,与其所处地域与交通要道的影响,及迁入的世家大族的交流,和统治者的扶持推动都有诸多关系,因而最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许杭生:《魏晋玄学史》,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