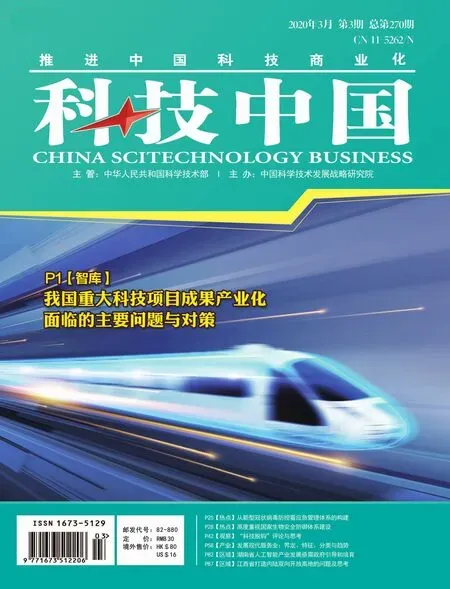“科技脱钩”评论与思考
2020-03-24苏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文/苏楠(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特朗普执政后,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开始撰文警示美国有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倾向。2019年在中美经贸紧张态势未有缓和的同时,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调查华裔科学家等举动,进一步增加了各界对中美存在“科技脱钩”风险的担忧。本研究从“科技脱钩”的动因、可能性以及应对举措三方面,对国内外媒体和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提出我们对“科技脱钩”的认识与应对建议。
一、“科技脱钩”是美国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称霸世界的重要手段
各方对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动因方面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科技优势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根基,中美科技差距的缩小让美国感到担忧和不安,因此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封杀华为的会议上说:“封杀华为会使贸易谈判变得更复杂,但美国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中国在靠其科技力量‘称霸世界’,如果我们现在不这么做,以后就没有机会做”。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认为,“科技脱钩”问题的核心涉及到了两国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竞争的关键就是谁的技术和标准将会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认为,“科技脱钩”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要遏制其他国家的科技赶超。长期以来,美国凭借科技优势占据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顶端,掌握了高科技产品和全球价值链定价权,攫取了高附加值,同时掌控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方向,深知科技发展对于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只有保持科技和产业上的领先优势,才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并称霸世界。二战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纺织品、彩电、钢铁、汽车和半导体等对美出口猛增,引发了美日贸易摩擦,80年代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在汽车、电脑、半导体等领域在美国市场挑战美国企业,更在技术上直逼美国。在日本学者牧野昇.志村幸雄撰写的《美日科技争霸战》一书中提到,美日贸易摩擦到80年代有逐渐转向尖端科技摩擦的趋势,美国采取措施加强对日本科技情报流出的限制,如美国政府为限制复合材料、陶瓷等尖端科技情报流向日本,强制加入美国复合材料学会的会员必须为美国公民,尽管这一规定是针对所有外国人,但一般认为是以限制日本籍研究人员为主要目的;限制政府资助项目取得专利授予国外企业;以往日本外务省可以向美国国防部和NASA申请获取两家机构委托研究的所有论文,但1983年以后,多数申请在探寻阶段即遭到拒绝,1985年前后申请已经变得不可能;日本有力银行向美国著名银行交涉,拟以共同投资的方式设立风险投资公司,结果以“与尖端技术情报外流有关,势将遭到政府管制”为由遭到拒绝。
二、完全“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重点领域遏制不可避免
在“科技脱钩”的可能性方面,少部分观点认为“科技脱钩”可能性较大,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表示,中美脱钩已不再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国不太考虑成本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怎么发泄对中国的怨气。大部分观点认为完全“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科技竞争将日趋激烈。具体观点如下。
一是大部分学者从科技与经济关系、产业链关联角度出发,认为“科技脱钩”不可能实现。如《日本经济新闻》2019年7月31日刊文指出,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技术和经济就无法脱钩。
二是从科技本身及其发展特性看,“科技脱钩”不具备基础。在2019年7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欧洲研究委员会主席布吉尼翁接受采访时认为,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做到只依赖自己就能进行学术研究,对知识共享持开放的态度是在未来获得成功的基础,同时,知识就是知识,不存在所谓中国的知识、美国的知识,无论哪个国家想划定知识边界,都将是徒劳的。

三是完全“科技脱钩”不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2019年6月27日的《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美国必须在技术方面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但不应该以脱钩的方式阻碍中国技术进步,割裂的技术世界将破坏美国产业和创新生态,甚至可能使美国失去技术竞争力,也会导致美国在发展最快的行业无法融入全球供应链,美国作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地位也难以为继。“科技脱钩”不符合美国企业长期利益,尤其不符合短期经济利益,任正非在一次访谈中说:“向华为供货的上游芯片企业,想尽一切办法向华为供货,虽然不能排除在长期的合作中结下的友谊,也可能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看的财务报表,更多的利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刘遵义认为,苏联建立独立和封闭的服从于保家卫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使自己失去了与外部充分竞争和交流的机会,长期增长的动力也会丧失,美国如果重蹈覆辙也将遭受巨大损失。
四是中美科技竞争将长期持续。尽管完全“科技脱钩”可能性较低,但中美之间激烈的科技竞争难以避免。很多观点认为中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让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而科技是两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旅美学者、目前任职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的董洁林认为,中美科技脱钩不是一时风潮(wave),而是一个“大逆转”(reverse),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相比贸易摩擦,“科技脱钩”给中国的冲击更深远更严峻。
我们认同上述观点,同时认为,美国一直在不断试验和权衡“科技脱钩”对美国的利弊,在不断动态博弈中找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一方面,为了减少美国企业经济损失,2019年5月商务部宣布的对华为禁令推迟90天施行,8月又宣布将再次延长对华为的暂缓令,允许华为从美国公司购买产品;另一方面,又在对国家安全和产业标准有重要影响的领域进一步限制合作,9月19日国际网络安全组织事件响应和安全小组论坛(FIRST)宣布,由于美国政府禁令,该组织将与华为断开联系,暂停并取消其会员资格。
我们认为,由于美国在寻求利益平衡,中美之间完全“科技脱钩”不切实际,但美国对重点领域的遏制不可避免。从美国在人员交流限制、针对华裔科学家的调查、收紧投资准入、加强技术管制等方面动作看,美国最为敏感的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领域,这也是颠覆性创新最有可能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美国希望在这些领域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在一些前沿和颠覆性领域,尽管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产业化方面仍未取得大规模市场突破,如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生物技术等,而且发展速度不及预期,陷入“科技高原”。我国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本土市场创新经验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资源优势等使得我国有快速紧随创新的能力,美国担心即便其在基础前沿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但在产业化方面居于垄断地位、制定产业标准和掌控价值链高端的时间窗口可能缩小,甚至在产业化方面会被中国反超。因此,美国寄希望于通过切断中美之间在人员、学术和产业等方面的交流,延缓中国接触前沿科技和开展前沿创新的步伐,为美国在新兴领域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留下足够的时间,为美国企业形成技术和产品的代际领先优势和攫取更多的垄断利润创造条件。从历史上看,美日贸易战背后的科技摩擦并没有升级为“科技脱钩”,而且有观点认为,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美国再次成为信息技术和产业的领导者之后,美日贸易和技术争端才有所缓和。因此,美国对中国的科技遏制,并不是全面“科技脱钩”,不是形成两个割裂的技术体系,而是为了牢牢把握未来技术制高点和价值链主导权。
三、形成开放合作新理念,加强前沿领域技术和制度创新
对中美两国如何解决当今困局,各界并没有统一的观点,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指出,“科技脱钩”涉及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核心,没有解决问题的现成剧本。在中国如何应对中美“科技脱钩”方面,少部分人认为可以借贸易战或断供为契机,发展独立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绝大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并加强全球科技合作,具体包括:一是更开放地开展科技交流,更兼容地参考跨国技术标准,建立能够“钩”住其它国家的技术体系;二是不论技术战如何演变,中国都应建立好具有自身优势特点的技术体系,全球各国之间形成各具优势的跨国技术网络;三是科技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经济存在紧密联系,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两国经济存在联系,科技必然伴随其中,因此要进一步深度融入和嵌入全球产业链,在更好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的同时,通过保持经济交错互融,以增加“经济脱钩”成本,降低“科技脱钩”风险;四是以多元化合作降低中美“科技脱钩”的负面影响,包括拓展和加强同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以色列等科技强国的合作与交流,扶持科技较弱的国家,针对这些国家需求和发展水平提供定制化技术,与当地建立良性合作关系;五是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引入全球创新者和创新资本,既通过加速内部竞争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也增加国外技术和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附度;六是加强中美民间科技交流,加强与美国地方州政府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如在2019年5月底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举行的第五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上,多位州或地方负责人表示愿意继续推进美中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合作交流;七是加强在中美或全球共同关切领域的创新合作,如气候环境和医疗健康等,维系畅通的国际交流合作渠道。
我们认为,中国在整体上作为科技发展后来者,必须更加开放、兼容并蓄才能更好融入全球创新体系,才能更好地谋发展和谋复兴。首先,在观念上,不应过度强调技术的自主可控,中国科技发展不是、也不可能通吃所有领域核心技术,而是要在全球创新合作和产业分工中,打造符合自身优势的全球产业链体系,而不是封闭的全产业链体系。第二,更加注重在全球创新合作中的输出。过去在中美科技和经济合作中,中国主要扮演输入者的角色,未来需要在平等合作的前提下,更多进行善意的输出,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解决方案,共同解决相关经济和社会问题。第三,针对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前沿和颠覆性领域,必须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尤其是加大合作创新力度,力争在相关领域全球创新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在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新兴领域,如新能源汽车等,注重多技术路线培育,防止下一代技术出现落后,如加强固态电池研发和产业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处于发展初期的产业,加强市场驱动的技术创新,实现专有芯片突破;在可能重新定义产业和改变产业规则的前沿探索领域,如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为开辟新赛道提前布局和谋划。同时,要注重制度创新,包括科技伦理、数据收集和使用规制、平台型创新组织治理等,一方面引导和规范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探索通过特色或特殊制度吸引国外优势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加速国内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