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名巷(节选)
2020-03-23主持人林云霞
○主持人 林云霞
没错,是“记意”,不是“记忆”,这不是拼音输入法造成的别字。我的意思是,这两者的内涵有区别:记忆是现场在不同时间维度的客观再现,记意是记忆经过主观情感筛选后的局部性的后续呈现。记忆务实,记意高蹈。刚好诗歌也是高蹈的,于是记意和诗意常常融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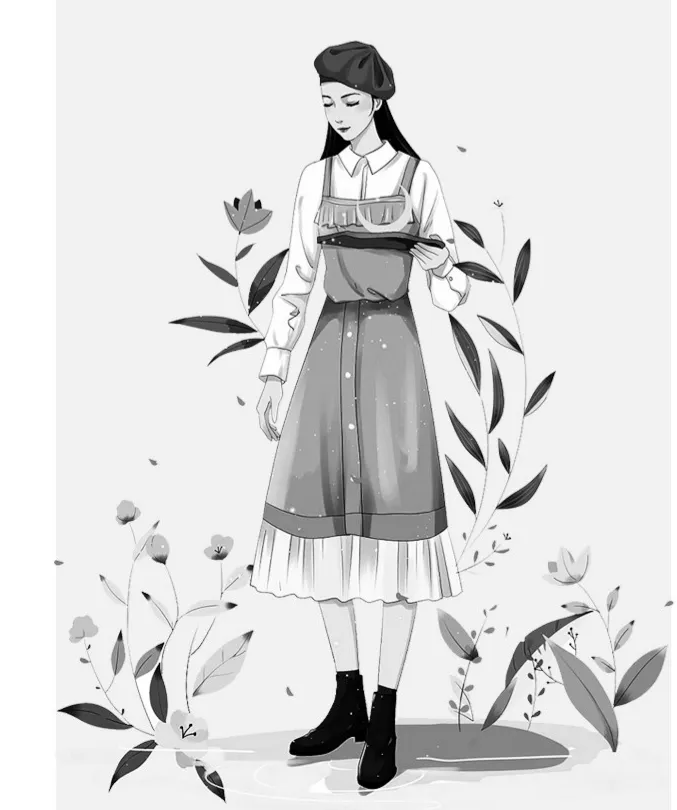
1941年前后,日本飞机经常入侵赣州,城里没有防空武器,日机也就敢于低空轰炸扫射;开初我们一听见那汽笛狂鸣、钟声急促的警报,就往菜地边的竹林跑,错以为那里隐蔽、安全。有一天,几架日本飞机低低地冲下来,低得机翼上的血红圆团都看得见,巨大的轰鸣声和机枪密集的扫射声很是吓人。我们吓得趴在地上,只听得竹子被机枪子弹打得哗啦啦地折断下来,我二姐维仁以为是子弹泼来,忙脱下她的蓝布上衣遮在我头上,以为可以帮我挡住子弹……多少年后,我想起二姐,就会感动地记起她对我这弟弟的关怀。
从那以后,跑警报成了我们紧张、恐惧的生活。早上匆忙吃点儿东西,母亲就带着我们出南门,跟着人群往河边树林里躲,中午在外边吃点儿冷饭,天黑时才敢回去;这样天天跑,实在太累了,而且城里中小学都停课了,读不成书,母亲就把我送往已疏散到离城约15华里的桃源洞的省立赣县小学去读五年级。农村的校舍是用篾墙、竹瓦做成的,吃的是南瓜、糙米饭,很苦,却较安全,但远远望见日本飞机扑向城里,接着是炸弹爆炸声、机枪扫射声,我就会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我那杨名巷的家怎样了,爸爸妈妈姐姐弟妹们平安吗?
周六回来,见杨名巷如旧,爸妈都好,我才放心了,与邻居们平安相见,彼此又多了几分亲切,前些日子吵过嘴、打过架的小伙伴也会重新和好。
1944年冬,日本侵略军溯赣江而上,赣州一片恐慌,人们多在雇车雇船远逃;我们家人口多,又因为父亲已经失业,经济困难,无力远走,只好先叫我这15岁的小孩搭乘父亲朋友的便车,把两箱衣物、字画送往他在于都的朋友家寄存。

于都离赣州几十公里,当时搭乘烧木炭的汽车,车程两三个小时。我把东西送到,第二天往回走时,买不起车票,两头见黑地步行了一整天,两脚都走起了水疱。一路上只见逃难的人、车辆络绎不绝,我还以为赣州已经沦陷了呢!问那些逃难的人,他们也不清楚,只是含糊地说:“快了,快了!”我为父母弟妹担忧,走得更快了,在天黑时才接近城边,城门口已经堆满了沙包,像要随时封闭城门进行巷战似的。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城内,拼命往家里跑;杨名巷内本来就没有路灯,这月黑风高的冬天夜晚,那几户人家有的逃难去了,有的出于恐惧不敢点灯,小巷显得极为阴森。我又一路疾跑,才进大门,就听见徐家老二的媳妇在哀哀哭泣,她喂养的那几十头猪怎么办?带不走,也卖不掉……
我进到屋里,只见父亲一个人枯坐在昏暗油灯下。见我回来了,父亲才如释重负地连声说:“好,好,你回来了!”我去了于都后,父亲仍在四处寻找车船,一位同情父亲在职时不贪污不敲诈的药材商人,愿意在他雇的木船上免费给我们家一席之地,就由母亲领着姐姐弟妹们先去赣州下游的夏府,父亲则留下等待我。
母亲他们走得匆忙,连碗筷都来不及洗,抱了几床被褥和一包衣衫就上船了。
又过了一天,日军已越过遂川,逼近赣州,城里已经跑得没有多少人了,我们才在那北风凛冽的早晨挤上了一条下行船,赶往夏府与母亲他们会合。又是搭乘别人的船,大小家具和父亲珍藏多年的书籍、瓷器、古董都不能带。我们是含着泪走出杨名巷的。
解读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战争只能和“残酷”“绝望”“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它和“诗意”是对立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诗意发生在多年以后。彭荆风回到赣州,重温曾经生活的地方,见到曾经熟识的人的后人,想起过往岁月,记忆发生了化学反应,诗意奔涌出来,化作了滔滔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