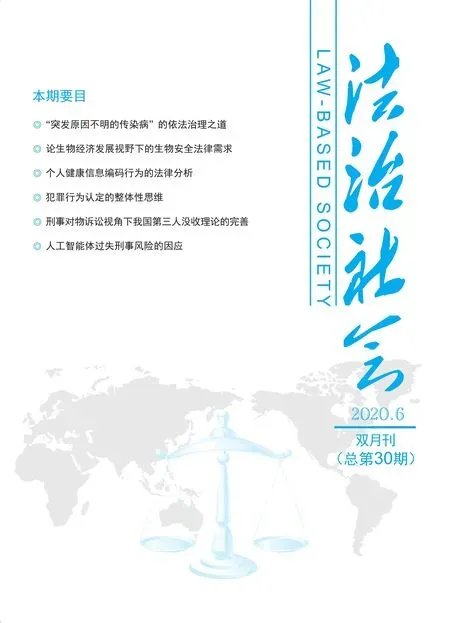论生物经济发展视野下的生物安全法律需求
2020-03-22刘长秋
刘长秋
内容提要: 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是生物经济时代下生物安全问题所显现出的三个明显特征。 法律之所以被适用于生物安全问题, 其原因在于法律具有特定的功能, 能够满足应对和解决生物安全问题的需要。 由于生物经济发展客观上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的负面效应并尤其是生物安全问题, 人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立法应对需求会相对更加强烈。 生物安全法作为国家为应对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之挑战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必须要承担起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使命: 其一是防范生物安全问题, 其二是保障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
生物技术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飞速发展, 其在相关行业领域的应用, 对增进人类福祉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 产业化发展无疑是所有技术深入发展以最大化增进其对社会惠益的客观规律。 生物技术也在此列。 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促生了生物技术产业, 而生物技术产业则是增长最快的现代经济部门之一。①See Debra M. Strauss,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Importing Caution into the U. S. Food Supply,Food and Drug Law Journal, 2006, p.167.我国生物技术产业也在快速发展之中, 而国家迄今已制定了包括 《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 生物产业发展规划》 等在内的多个政策性文件, 明确提出要将 “生物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目标, 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保障生物产业发展的针对性措施。 现在,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正在以其巨大的影响改变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而科学家们也普遍认为, 生物产业(亦即生物技术产业) 是二十一世纪的支柱产业,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经济的世纪。②董良: 《21 世纪是生物经济的世纪》, 载 《中国经济导报》 2005 年11 月15 日第C02 版。言而简之, 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力量, 而生物技术产业化发展所带来的生物经济形态的出现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辨证地看, 生物技术进步尤其是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巨大推动是不言而喻的, 但另一方面, 生物技术的进步也带来并增加了很多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便在其中。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当代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生物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而生物经济则是 “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 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③邓心安: 《生物经济时代与新型农业体系》, 载 《中国科技论坛》 2002 年第2 期。其发展有赖于生物技术的进步, 并同时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切问题, 其中自然也包括生物安全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 透过生物经济发展的视角来探讨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对于明确生物安全法在应对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定位, 科学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以保障生物技术乃至生物经济的健康发展来说, 无疑将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本文拟从分析生物安全问题之特点入手, 就此浅加研究!
一、 生物安全问题的特点
法律需求是法律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 其含义是指经济社会发展所引生的、 人们对于立法及以之为基础的执法、 司法等法律活动的需求。 在一般论著中, 法律需求侧重于指立法方面的需求, 即经济社会发展所引生的人们对用以调整特定社会关系和解决相应社会问题的相关立法之需求。 从法理上来说, 生物安全法是否会出现、 会以何种形式出现, 以及将具有什么样的立法理念与内容, 都取决于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而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则受生物安全问题特点的直接影响。 易言之,生物安全问题所显现出来的特点会生成相应的特定法律需求, 并会引发相应的法律供给。 而作为一种非传统型的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一) 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圈向来存在但伴随生物技术的突破式发展才越来越凸显出来的一类现代性问题, 所影响的往往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 而是不特定的人群, 尤其是在生物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 由于生物经济的发展, 生物技术的影响将会超越实验室层面而进入经济流通环节, 而 “这种传播是没有国界的, 在市场上更没有界限”,④Christian BYK: 《遗传基因: 魔鬼工程? 或是对欧盟政策的怀疑?》, 韩小鹰译,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要——2007 年 “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第154 页。这必然会使得生物技术的影响对象从以往仅限于实验室操作人员转而向生物技术产品所及的所有范围内的任何对象 (这一对象既可能是人也可能会是其他生物) 扩展。 在这种情况下, 一旦生物技术被人滥用, 将会直接危及某个种群甚至是全人类的安危, 造成大规模性损害、 杀伤甚至毁灭。 以该技术被滥用来生产生物武器为例,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现在 “彻底毁灭的危险变小了, 但大规模杀伤的危险更大了”, 因为生物技术被滥用来生产生物武器的可能性已经使人们 “主要令人担心的不是拥有成千上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对手, 而是那些拥有少数杀伤性武器的敌人”。 在该学者看来, 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生物武器来杀伤大量平民,因为生物武器比较容易制造、 运输和走私, 很难被发现, 并且杀伤性极强, 典型的就如炭疽热病毒的传播。⑤Richard K. Betts, The New Threat of Mass Destruction, Foreign Affairs, 77 (1), 1998.不仅如此, 对于生物武器而言, “病原体难以检测到, 传染病开始流行的症状可能要过几天才会显现出来, 故袭击可能被误认为是自然爆发”,⑥姜涛: 《生物安全风险的刑法规制》, 载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20 年第4 期。其造成的危害极大。 由此不难看出, 受生物安全问题影响的主体范围是非常广泛且往往难以确定的。 这决定了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必将是一种极为强烈且普遍的、 具有明显公益性的法律需求。 在生物经济时代, 生物安全问题影响群体的广泛性会因为生物技术的产业化发展而进一步彰显, 国家对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无疑会更加迫切。
(二) 影响范围的跨国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尽管有个别国家意图逆该潮流而行, 采取了很多反经济全球化的举措, 但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显然不可逆转。 当代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其相互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越来越频繁。 与此同时, 经济技术发展的风险也开始跨越各国与各地区的范围而逐步向全球扩散,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技术发展所必然会引生的一种风险, 也遵循着同样的轨迹。 特别是在各国生物产业发展的推动下, 生物产业发展客观上所必然要求的生物技术人才、 资本以及产品的跨国流动使得生物安全问题越发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 其影响范围不断扩散, “在一时无法控制的情况下, 它所影响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 而可能是某个区域内所有邻近的国家或地区, 这将对全球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更为负面的影响。”⑦张谨: 《生物安全及我们的对策》, 载 《社会科学》 2004 年第9 期。“……目前生物技术及其成果的流通与转移越来越普遍, 生物技术风险的跨地区性、 跨国界性也越来越严峻。 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本国生物技术发展落后, 而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技术及其成果, 缺乏必要的生物技术风险防范措施。”⑧张建伟: 《论中国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的构建》, 载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年第4 期。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的药害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注脚。 近年来, 生物制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这一技术的经济效益倍增, 也使得医药生物技术产业获得了飞速发展, 并成为未来生物经济的先导。⑨参见杨胜利: 《工业生物技术与生物经济》, 载 《中国基础科学》 2009 年第5 期。然而, 另一方面, 对医药生物技术经济效益的过分追求, 也使得很多药品生产商急于冒进, 开始忽视药品的安全, 甚至受短期高额利润的引诱而放纵瑕疵药品的生产, 很多危害甚大的药害事件无不是因此而生, 如著名的 “沙利窦迈事故” (Thalidomide Disaster)、 “万洛事件” “拜斯停事件” “长春长生疫苗事件” 等等。 由于药品是针对所有具有同类病症的患者所设计的一种特殊消费品, 其销售往往是面向全球的, 而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仅面向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因此, 一旦制药技术在安全方面出现了问题, 则作为这一技术之最终产品的药品所产生的危害也必然波及全球, 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必须认真加以对待并须要合作采取应对策略的全球性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使得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绝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之内, 而必然会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法律需求。
(三) 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生物安全问题是现代环境问题乃至生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环境问题与生命问题都具有不可逆性, 即作为环境污染与生态损害对象的生态环境, 其一旦被污染或破坏, 将是无法完全恢复的,而作为人们最高法益的生命健康, 其一旦受损, 也将难以复原如初。 作为一种以生物为介质和以生物技术为最重要载体的新型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问题也具有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即其一旦发生,就将是不可逆转的, 造成的损害也无法弥补。 当代生物安全最大的问题在于生物技术安全问题。 因为生物技术发展已经进入了以改变物种原有遗传特性为特征的现代生物技术阶段, “这种具有中度干预特征的现代生物技术将有可能引发转基因生物的蔓延以及遗传资源丧失等风险。”⑩秦天宝: 《〈生物安全法〉 的立法定位及其展开》, 载 《社会科学辑刊》 2020 年第3 期。转基因食品技术就是很好的例子。 转基因食品技术产生的转基因作物是能够自行转移和繁殖的生命活体, 一旦发现释放的转基因作物有害, 便几乎再也无法收回, 反而会随着其种群的扩大而造成更严重的危害。①杨庆文: 《转基因水稻的生物安全性问题及其对策》, 载 《植物遗传资源学报》 2003 年第3 期。而要消除转基因作物所造成的后果几乎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 发生在2003 年的“非典” 以及当前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已经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生物安全问题的不可逆性。 换言之, 在生物安全问题面前, 人类是没有后悔药的。 生物安全问题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危害性及其在生物经济时代所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的趋势, 决定了人类在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方面是极为迫切的。
总体而言, 生物安全问题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人类社会对更有可能会引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技术之发展必然会提出较以往技术发展更高的要求。 具体而言: 一方面, 人们希望生物技术的发展能够极大地增进人类自身的福利, 这是生物技术发展的最终价值目标; 另一方面, 对于生物技术这种高风险的、 容易引发生物安全问题的技术, 人们希望其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确保自身的安全, 避免或至少是减少因为该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 以保障人类自身的生命健康与生态和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 这使得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 上述要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对于生物技术进步所提出的客观需求, 必然会借助立法的方式得到表达。
二、 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法律经济学理论认为, 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 不仅是社会现象的产物, 而且也是经济现象的产物。②黄文平: 《论法律行为的经济基础》, 载 《经济评论》 2000 年第6 期。立足于经济学的视野, 立法是由作为公民代言人的国家应社会之需要而经由立法部门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社会需求决定着法律供给。 “从理论上讲, 法律的需求决定法律供给, 当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法律这种社会调整手段产生需要并积极谋求法律秩序对其利益的维护时, 就必然要求法律供给发生。”③冯玉军: 《法律供给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载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6 期。而生物安全方面的法律需求亦由此而发生。 “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④张辉: 《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论》, 载 《现代法学》 2008 年第6 期。当代生物技术发展在极大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 也引生并加剧了生物安全的风险, 对人类社会乃至整个生物界都带来了挑战。 在这种背景下, 客观上必然会产生社会对于生物技术发展方面的安全需求, 而由于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具有的特殊功能, 使得这种安全需求最终上升为一种通过法律来加以表达和实现的规范性需求。
(一) 法律的功能视野下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
功能一词的一个基本含义, 是指能力和作用。 当我们把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基本手段时, 就会很自然地涉及到它的功能问题。 所谓法的功能实际上就是法律在调整现实社会关系时所实际发挥的能力与可能会产生的积极社会作用。 从法的功能的一般学说来看, 任何法都有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之分,⑤沈宗灵主编: 《法学基础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第42 页。前者是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所具有的调控功能、 指引功能、 评价功能、 预测功能、 强制功能及教育功能, 后者则指法律作为一类社会行为规范所具有的管理及服务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法律在维护人类社会秩序稳定和消除社会混乱方面一直都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任何社会, 无论大小、 强弱都为其自己制定了据以发展的原则框架。何为可为, 何为不可为; 哪些活动是被允许的, 哪些活动是被禁止的, 都被一定社会的意识进行了明确区分。 社会的进步正是在于它拥有一套能够组合一定的群体去追求被普遍接受之目标的规则体系, 而法律则是约束团体成员固守被认可价值与标准的重要因素。 通过设定权利与义务, 法律既能够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引导, 又能够对那些违法行为进行惩罚。⑥参见[英] 马尔科姆·N·肖: 《国际法学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 页。尽管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诸如政策、 伦理道德等在内的各类不同社会规范的共同支撑, 但 “法律则在当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因为它使社会选择公共化, 并且使它在现实中得以实施。”⑦Christian BYK: 《遗传基因: 魔鬼工程? 或是对欧盟政策的怀疑?》, 韩小鹰译,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要———2007 年“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
从法理上来说, 法律需求理论的支点在于法律具有特定的功能; 换言之, 人类社会之所以会产生对法律的需求, 其原因就在于法律承担了某些特定功能, 从而使其自身具有了其他社会行为规范所没有的特点与优势, 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国家和社会, 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在调整公共事务方面的作用。”⑧葛洪义主编: 《法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第83 页。而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基点显然也在于生物安全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特定功能。 具体来说, 生物技术发展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诸种负面效应尤其是直接关涉人类生存状况的生物安全问题, 客观上需要法律尤其是生物安全法这类以确保生物安全为自身特殊使命的专门法通过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来予以防范和抑制。 这是法治之法作为当今时代下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所内含之义。 “法治之法作为一种价值理性, 所蕴含的对人的生存状态、 自由、 权利、 尊严和价值的关怀和尊重, 就构成对科学技术的非理性、 非人道利益的抑制, 对因过度强调技术理性而导致的人的技术化、 客体化和社会生活的技术化的矫正。”⑨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第491 页。生物技术尤其是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日益广泛应用, 必然会且事实上已经对于良好的法律制度产生强烈的依赖性。 这是因为, 在法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国内社会主旋律的宏观背景下, 要限制和克服生物技术尤其是生物经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现代生物技术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 正确应对生物安全问题, 就必须要重视法律尤其是作为生物安全风险的最后一道 “防护网” 的生物安全法所应当发挥的作用, 从制度上重视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与防范。 而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一类重大安全问题客观上所具有的影响群体的广泛性、 影响范围的跨国性以及危害后果的不可逆性, 决定了只有且必须通过法律这一法治社会中之最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才能够使其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才能将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内。 基于此, 为了防范和降低生物安全事件, 在生物技术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法律显然有必要设置某些 “禁区” 与 “红线”, 以此来防范生物技术的滥用, 减少和控制生物安全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降低其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使生物技术发展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被控制在人类社会可以承受的水平之内。
(二) 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特殊性分析
生物安全立法的降生主要应因于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的现实需要——尽管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应对和防范所有生物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立法需求是人类社会为应对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而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实立法需求, 是确保生物安全最为理性和有效的手段。 在生物经济时代,由于生物经济发展客观上会无限放大生物技术的负面效应并尤其是生物安全问题, 从而给人类社会的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人们对于生物安全问题的立法应对需求会相对更加强烈, 对立法的要求也会更高。 生物安全立法作为国家为应对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之挑战而向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 其目标就在于保障生物安全, 它一经产生就必须要承担起以下两个方面的基本使命: 其一是防范生物安全问题; 其二是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亦即 “生物技术安全立法一方面要考虑到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不能过于苛刻, 另一方面要针对其潜在的风险, 加强安全管理。”⑩参见前引⑧, 张建伟文。
1. 防范生物安全问题
生物安全法, 顾名思义, 就是用以维护和确保生物安全的法律, 因此, 其核心使命应在于防范生物灾难, 确保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法必须要对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或可能会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作出提前预判, 并通过设置相应法律制度及时予以回应, 以避免生物安全问题真正发生而给人类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灾害, 或者尽量减少生物安全问题发生后所带来的损害。 生物技术作为一种现代高新技术, 在其应用中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一旦引导不利或规范不好, 将极有可能会给整个人类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甚至灾难。 不仅如此, 生物技术的进步在改善人们的生命健康,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引生了诸如人类遗传资源的窃取与买卖、 克隆人、 代孕以及转基因食品泛滥等在内的众多伦理问题, 对人类传统生命伦理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与冲击, 使人类传统生命伦理面临垮塌的巨大风险。 除此之外, 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并没有改变人们对现代生物技术安全性的担忧。 有关生物技术 (如转基因食品技术、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等) 的安全和潜在的危害虽然还无法得到有力的科学论据的论证, 但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公众对它一直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事实上, 释放到环境中的每一种遗传工程生物都会对生态系统构成潜在的威胁。 而生物经济的出现不但没有消除这些威胁, 反而进一步放大了生物技术的潜在危害, 因为这一新经济形态的出现意味着很多原本处于实验操作状态的、 其危害仅及于实验操作人员的生物技术开始借助产业的形式大规模的走向市场, 其危及的范围开始无限放大。 生物技术发展所潜藏的这种巨大风险性注定了以防范生物安全问题为主旨的生物安全法必然会成为生物技术的规范法, 亦即 “生物技术的应用必须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要借助法律的强制力。”①李恒: 《试论生物技术对传统法律体系的挑战》, 载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 年第1 期。“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来坚决抵制严格防范生命科技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②曹丽荣: 《现代生命科学技术呼唤着法律》, 载倪正茂、 刘长秋主编: 《生命法学论要——2007 年 “生命科技发展与法制建设”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第68 页。由于生物安全问题所具有的跨国性, 使得各国在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注意相关国际措施尤其是国际法作用的发挥。
2. 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
生物技术恰似一柄双刃剑, 在创造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 其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③秦天宝: 《论实验室生物安全法律规制之完善》, 载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20 年第3 期。为此, 需要立法谨慎对待。 就保障生物技术健康发展来说, 生物安全法对生物安全问题的应对必须以不对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带来妨害作为准线。 即 “对生命科技活动的法律规制不应当在事实上妨害该类技术的进步”,④刘长秋: 《论生命科技刑事责任的功能与我国刑法之完善》, 载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10 年第2 期。这是因为, “法的规则和药物对人体的药理作用一样, 具有双刃剑的性质。”⑤[日] 植木哲: 《医疗法律学》, 冷罗生等译, 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第296 页。作为专门规范生物技术发展以抑制和减少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安全法, 一旦其规则设置不当, 将直接会压制和打击人们从事生物科技活动的积极性, 影响生物技术的进步。 而生物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不仅是生物安全这类负面问题, 更有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具体而言: (1) 生物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与各种疾病与灾难做斗争的能力, 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公共卫生福利。 “科学的进步使得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治愈或不可改变的疾病之治愈成为可能, 并使得可能治愈的疾病之范围不断扩展。 然而, 由于新的治疗手段越来越依赖于有关分子和遗传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以致他们不仅带来了减轻或治愈那些威胁人们生命、 致使其身体和精神虚弱或痛苦的疾病的可能性, 也使得 (至少在理论上) 明显提高人们的身体或精神状态或带来纯社会性的或美学上的利益成为可能。”⑥Deryck Beyleveld, Roger Brownsward, Human Dignity in Bioethics and Bio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19.(2) 生物技术发展促进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生物技术产业既是高科技产业, 也是高效益产业, 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 例如, 一个基因可能形成并带动多个产业, 一个基因药物可能治疗几千种基因病症, 一个重组蛋白质可能创造几百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财富。 目前, 就世界范围内来看, 生物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其产业化的浪潮已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3) 与传统技术相比, 生物技术发展使人们能够开发出更加适合人们需要的生物品种。 以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应用为例, 农业转基因技术带来了农业生产能力的革命, 转基因操作允许科学家们在植物和动物中加入新的特性并在物种中植入DNA, 如将某种细菌或动物的性状转入植物之中, 从而使得转基因农作物具有较传统农作物更强的适应性, 不仅可以增加单产, 且增强了抗旱、 耐碱、 抗病虫害的能力, 增加了农作物的营养; 而一些原本具备高营养但产量偏低或不易培育的农作物品种现在经过改良后也已不仅可以大规模生产, 且由于在农产品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生物的特性而增加人们所需要的养分。 而动物产品经过应用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 其品质也得到了根本改良, 抗病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产量亦大幅度增加。 一些原本不具备饲养价值的动物经过改良也已能够大规模饲养。 总体来看, 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不仅在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且极大地改善了贫困地区人民的健康状况, 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为国际社会消灭贫穷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 推动生物技术进步以发展生物经济无疑应当成为当代法律的一项基本使命, 而这一使命使得生物安全法又必然会承担起生物技术健康发展之保障法的角色。 作为生物技术健康发展的保障法, 生物安全法不是也不应当成为以限制生物技术进步为目标的法律, 而更应当成为协调生物科技发展正面影响与负面效果, 以实现生物科技发展效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法律。 这显然应当成为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内含之义。
三、 结语: 兼对 《生物安全法》 的简要评价
“技术发展改变了人类生存形式, 也就是社会结构, 并影响所有生活领域和法律领域。”⑦[德]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 丁小春、 吴越译,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第21 页。而“社会所有领域的快速的结构变迁产生了许多新的、 需要法律调整的利益冲突。”⑧参见前引⑦, 伯恩·魏德士书, 第21 页。站在法律经济学的角度上, 法律是适应利益调节之需要而产生的, 法律的变化和发展根源于利益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且归根到底根源于人们利益要求的变化和发展。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抽象的利益并不构成法律。构成法律的是要求, 即真正施加的社会力量。”⑨[美] M·弗里德曼: 《法律制度》, 李琼英、 林欣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第359 页。“法律是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强制力量的规则的总体”,⑩王铁崖主编: 《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 第6 页。其产生和发展来自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尤其是现实的利益需要。 生物安全法作为现代法律的一个特殊而极为重要分支, 显然也遵循此律。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所潜藏的各种风险以及这类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福利, 决定了人们对待这类技术既不能简单对待、 一禁了之, 也不能不管不顾、 放任自流。 生物安全法不仅要成为生物安全问题的防范法, 令其自身履行防范生物技术风险、 防范和避免生物安全灾难的基本使命, 也要成为生物技术进步的保障法, 承担起促进生物技术理性应用和最大限度发挥生物技术进步惠益的重要职责。 这显然对生物安全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生物技术进步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并同时抑制其风险、 减少和避免生物灾难, 生物安全立法必须努力寻找保护生物技术进步与管制生物科技活动之间的 “黄金分割点”,帮助人类平衡好生物技术发展 “机遇” 与 “安全” 之间的关系, 以便在帮助人们或缺生物技术发展惠益的同时, 最大可能地处理好生物技术发展所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
2018 年底发生的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以及迄今仍在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充分看到了生物安全问题的危害性和严峻性, 也再次将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凸显出来, 将广受关注的生物安全立法一次次推向前台。 在此背景下, 我国自2019 年启动了生物安全立法的步伐, 并在2020 年4 月下旬全文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草案二次审议稿)》。 在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的基础上, 2020 年10 月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以下简称 《生物安全法》)。 就其内容来看, 该法紧承我国 《国家安全法》 精神,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将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对生物安全工作的领导, 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制,将生物安全保障纳入了法治轨道之内。 在此基点之上, 《生物安全法》 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 对包括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 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和动植物疫情等可能引生的生物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和严密防范, 不仅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以及包括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 生物安全风险调查评估制度、 生物安全信息共享制度、 生物安全信息发布制度、 生物安全名录和清单制度、 生物安全标准制度、 生物安全审查制度以及统一领导、 协同联动、 有序高效的生物安全应急制度和生物安全事件调查溯源制度等在内的生物安全防范应对制度, 运用制度理性构筑起了强大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机制, 还特别设置了严厉的法律责任制度, 极大地提高了生物安全违法成本, 将风险防范、 以防为先的理念注入到我国生物安全工作之中。 另一方面, 《生物安全法》 并没有因噎废食, 基于生物技术自身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之考量而禁止生物技术发展, 相反, 其为生物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充足的立法空间。 为此, 《生物安全法》 明确规定, “国家鼓励生物科技创新, 加强生物安全基础设施和生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生物产业发展, 以创新驱动提升生物科技水平, 增强生物安全保障能力。”①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五条。“国家采取措施支持生物安全科技研究, 加强生物安全风险防御与管控技术研究, 整合优势力量和资源, 建立多学科、 多部门协同创新的联合攻关机制, 推动生物安全核心关键技术和重大防御产品的成果产出与转化应用, 提高生物安全的科技保障能力。”②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六十七条。“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加强生物基础科学研究人才和生物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 推动生物基础科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③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由此来看, 《生物安全法》 坚持了发展生物技术与抑制生物技术风险且通过发展生物技术来提升国家生物安全保障能力的思路。 通过建立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机制, 严密防范生物安全问题的发生, 以期避免或至少是减少生物安全灾难的出现, 降低其危害; 而通过鼓励生物科技创新, 加强生物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支持生物科技产业发展, 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确保生物技术发展产生的惠益, 另一方面则以此提升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换言之, 《生物安全法》 将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之根本性解决寄希望在了生物技术自身的进步上, 即通过生物技术本身进步必然带来的人类应对能力的提升来解决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 而这显然合乎我国生物安全立法之现实需求, 也是生物经济时代生物安全法所理应肩负的一项基本使命。
当然, 目前来看, 《生物安全法》 在内容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 其有关生物安全的制度安排更多地是以现行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或规章为基础的, 内容上似乎是对现行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融汇与杂糅, 而对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制度涉及的生物安全领域则规定不多。 例如,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上, 国务院2004 年制定了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但迄今并未制定 《转基因食品研发实验室安全管理条例》 等其它生物实验室方面的法规或规章, 为此,《生物安全法》 只是关注并强调了现行立法已经关注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可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而对于其他也可能会产生生物安全问题的生物实验室, 如转基因食品研发实验室、 种子实验室等,则关注有限, 只是设置了 “企业对涉及病原微生物操作的生产车间的生物安全管理, 依照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规定和其他生物安全管理规范进行。 涉及生物毒素、 植物有害生物及其他生物因子操作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管理, 参照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规定执行”④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五十二条。这样一条兜底性条款。 再如, 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必然会带来各种伦理问题, 而伦理审查制度则是国际上公认且通行的、 解决这些问题并更好地应对和防范生物安全问题的一种最重要制度, 为此, 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专门建立了伦理审查制度, 并专门制定了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 但迄今并未制定非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规则, 而 《生物安全法》 尽管也关注到了生物安全工作中的伦理问题, 且强调相关活动要 “符合伦理原则”, 但显然更多地只是将视角限制在了生物医学领域, 要求“从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 应当通过伦理审查”,⑤参见 《生物安全法》 第四十条。而对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规章尚未涉及的非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 (如转基因食品研发领域的伦理审查) 则没有任何要求。 这不仅会极大地限制伦理审查在应对和防范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使得 《生物安全法》 的法网出现疏漏, 也表明了该法制度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对于生物安全问题预判能力的欠缺。 这些作为即将于2021 年4月15 日起生效的 《生物安全法》 尚存在的显见不足, 显然是其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方面。 但很显然, 作为我国生物安全领域一部综合性、 基础性、 系统性、 统领性的立法, 《生物安全法》 在防范我国生物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无疑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