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路去邮局
2020-03-19彼得·洛弗西
〔英国〕彼得·洛弗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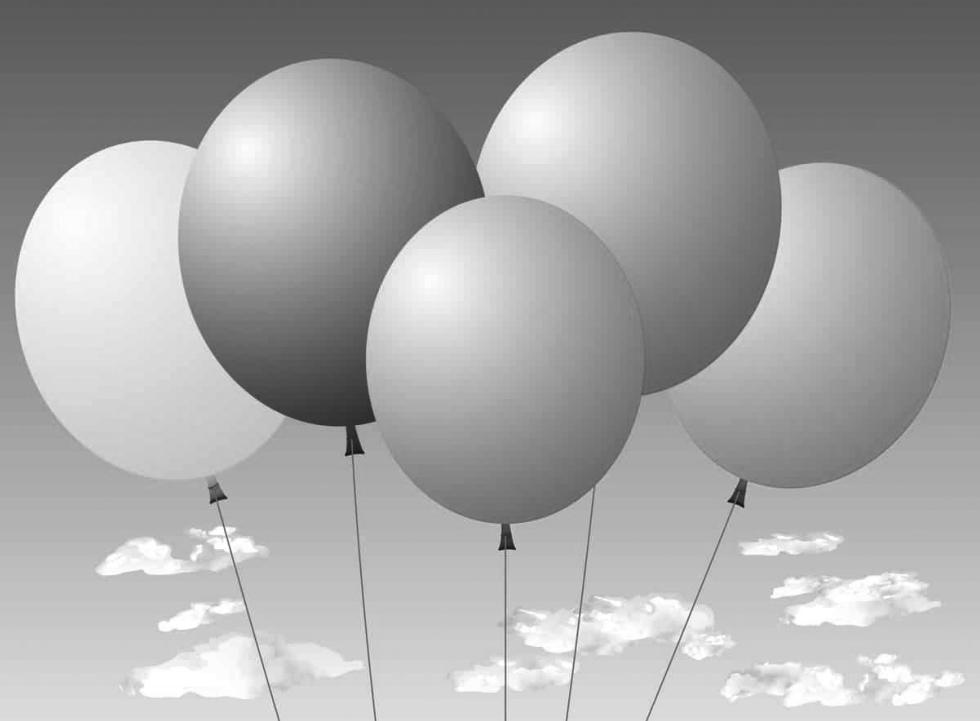
我最喜欢采访内森。他讲的故事太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相信他。他身子前倾,一双温柔的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一副积极自信的样子,让人信服。他这一副做派完全不会让你觉得他与暴力有任何联系。“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老是问我這起谋杀案,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当时只是去一趟邮局,没多远,可能就十分钟的路程,沿着史蒂文街走,然后走到梅尔罗斯大道。”
“就去了一趟邮局?”
“听着,医生。我刚跟你说过。”
“当时你带信了吗?”
“不记得了。”
“我这么问,”我说,“是因为人们通常只有想寄一些东西时才会去邮局。”
他笑了。“说得好,我喜欢。”记忆短暂丧失是内森所患病的症状之一。内森并未意识到,如果有人收到了寄出的信,他的说法会更可信。
随后我觉得他又开始编故事了。他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伸在我俩之间,仿佛魔术师在变硬币似的。“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我点点头。
“我当时,”他说,“走在大街上。”
“史蒂文街?”
“是的。”
“走在右边还是左边?”
“这有区别吗?”
据摩根探长说,案发地是史蒂文街29号,在路的左边大约三分之一处。“就是问问。”
“好吧,我不用过马路,不是吗?”内森说,“所以我在左侧,当我到梅尔罗斯大道时——”
“等等,”我说,“我们还没说完史蒂文街呢。”
“我已经说完了,”他说,“我正要和你说在梅尔罗斯大道发生了什么。”
“你在史蒂文街有留意到什么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留意呢?”
“有人告诉我那里出事了。”
“你又提这事了,是不是?我一直和你说,我对这起谋杀案一无所知。”
“那继续讲吧。”
“你绝对猜不到我在梅尔罗斯大道看到了什么。”
他的话没错。你总是难以预料他在去邮局的路上发生了什么。“跟我讲讲吧,内森。”
“三头大象。”
“在梅尔罗斯大道?”梅尔罗斯大道是郊区的一条小街。“它们在那儿干吗?”
他咧嘴一笑。“它们甩着长鼻子,扇着大耳朵。”
“我是说,它们在梅尔罗斯大道干什么?”
他吊着我的胃口并为此感到骄傲。“你觉得呢?”
“我猜不出来。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它们正排队走着。”
“什么,它们自己排队走?”
他看着我,仿佛我才该接受心理治疗。“很显然,有个饲养员和它们一起。”
“那些大象受过训练?”
他为我的无知叹了口气。“梅尔罗斯大道可不是非洲荒野。一些小型的巡回演出马戏团正在公园里表演,它们是马戏团队伍的一部分。”
“内森,如果这是一个马戏团队伍,它们会沿着商业街走,这样所有逛街的人就都可以看到。”
“你说得对。”
“那么大象跑到梅尔罗斯大道做什么?”
“防止塌陷。”
我等他说得详细些。
“你知道建筑工人把电视的电缆铺设在商业街的什么地方吧?他们没有把那块路面填好,正中间出现了一道裂缝。他们不希望情况变得更糟,所以让大象改道前往梅尔罗斯大道附近,这样队伍会轻快很多——军乐队、小丑和无鞍骑手,他们可以去商业街。”
这个故事和内森的很多故事一样有逻辑。上次去邮局的路上,他看到约翰尼·德普正在某人的前花园修剪女贞树的树篱,德普扮演一名职业园丁。内森问他们在干吗,有个人开玩笑说他们正在排练一个场景,和一部讲英国郊区生活的电影有关。他还建议我到那儿,试试当个临时演员,我只能说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
“你看,梅尔罗斯大道是条分流街道,商业街禁止重型车辆和大象通行。”
讲到改道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史蒂文街的双重谋杀案中扯远了。“内森,我很想知道那天下午你回家的时候为什么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衣服。”
这引起了他的一阵偷笑。“那就说来话长了。”
“想来也是,我得听听,说吧。”
他摊开双手,好像在一大群人前演讲。“有三头大象。”
“你已经和我说过了。”
“啊,我刚才是吊你的胃口。我刚看到大象时,我不知道它们在梅尔罗斯大道做什么。我想问问饲养员来着。我不怕和陌生人说话。一般来说,人们不反感接近他们的人,但饲养员在照看动物,我就没打扰他。我听到乐队的声音从商业街传来,我猜这些大象和乐队有关,然后我就去了梅尔罗斯大道的尽头。”
“邮箱在那儿。”
“邮箱跟这有什么关系?”
“你一开始要去邮局。”
“现在你打断了我的思路。你知道我的记忆不如正常人的。”
“结果现在你朝着乐队声音的方向走去。”
他笑了笑。“我抬头一看,空中有很多气球,五颜六色的,都在往上飘,里面充了某种气体。”
“氦气。”
“谢谢。气球一定是宣传马戏团用的。我走到梅尔罗斯大道尽头时,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拿着一个气球,有字——我指的是气球上有字,不是孩子们身上。我看不清上面写了什么,但我猜一定和马戏团有关。”
“很有可能。”在我的工作中,耐心不仅是种美德,更是种必须具备的品质。
“你可以这么想。”内森说道,举起食指以示强调。“但奇怪的是,我快到梅尔罗斯大道尽头时,我又抬了头,看还能不能看到气球。我无意中注意到有个黄色的气球挂在了一棵柳树的枝杈间。你也许知道那棵树,它没长在街上,而是从一户人家的花园里伸了出来。我想让气球飞走,但够不着,不过我爬上墙就可以轻易地拿到它。我就是这么做的。当我够到它并把它拿下来后,我看到侧面的文字与马戏团无关,而是写着‘祝苏茜生日快乐。”
我的内心惴惴不安。我知道这些故事会如何发展。有一次内森在去邮局的路上捡了一枚胸针,就带到了警察局。然后警察要求他戴上米老鼠面具,和其他嫌疑人一起接受目击者指认,还让他说:“把抽屉里的钱全都交给我,否则我就打爆你的头。”这之后又促成了一段全然不同的故事。“你对它做了什么吗?”
“对什么?”
“对那个生日气球。”
“我必须对它做些什么,因为它在我手里。我想它可能属于那户人家的,所以我敲了敲门。他们说不是,但几天前他们注意到有一些黄色的气球绑在史蒂文街一栋房子的门柱上。”
“史蒂文街吗?”我兴奋起来,“门牌号是多少?”
“不记得了。这些人——住在梅尔罗斯大道、家里种着柳树的人——有点吃惊,因为他们觉得那栋房子是一对老夫妇的。老人过生日一般不会用气球的,对吧?”
“所以你去史蒂文街的那栋房子问了问。”我说道,给他的故事推波助澜了一把。
“对,他们在家,说非常感激我想得那么周到。他们所有气球的绳子都松了,几乎都被吹跑了,所以只剩下这一个。我想着要祝老太太生日快乐,就问她是不是苏茜。可她不是,她的名字和苏茜一点儿也不沾边。我想是叫阿加莎或奥古斯塔,也可能是安东尼娅。”
“没关系,内森。继续讲吧。”
“他们请我进门去见苏茜,说她刚过完七岁生日。你信吗?它是只狗,是我见过的最小的狗之一,耳朵很大,眼睛圆鼓鼓的。”
“吉娃娃。”
“不,是苏茜。它绝对叫苏茜。令人惊讶的是,这只小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面有小靠垫、能吱吱作响的玩具,还有一台小电视,正在放电影《灵犬莱西》。但它一看到我就叫了起来,然后跑出房间,径直从我身边跑过,没什么能跑得比它更快。房子的后门开着,它跑了出去。老人有点惊慌失措,说一般只有在她牵着绳的情况下才会带苏茜去花园,因为狗狗太小了,他们怕它从篱笆的间隙里跑出去。我想我得为吓跑苏茜的事儿负责,所以赶忙跟着跑进花园,想盯住它。我看着苏茜冲过草坪,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幸的是,我没注意到有一个金鱼池塘横在我面前。我一脚踩了进去,滑了一跤,脸朝下栽进水里。”
“你总是碰上事儿,内森。”
他把这话当作夸赞,咧嘴一笑。“好在苏茜跑了回来看看发生了什么,老太太一把抱起它。我整个人都湿透了,身上沾满了泥和浮萍。他们说我可不能就这样走在大街上。于是老先生给我找了一套西装,他说他穿不上了,我可以留着。”
“好吧,”我说,趁机打断他的话,“你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現在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了。”
他又耸了耸肩,似乎忘记了谈话是从哪里开始的。
这正是暂停视频录像休息一会儿的好时机。
摩根探长在我办公室的电脑屏幕上看了这次谈话,时不时发出不满的声音。看完视频后,他问道:“你相信他说的话吗?这家伙满脑子幻想,真应该当个作家。”
“他的有些话倒是和事实相符,”我说道,“上周末这里的确有一个马戏团,而且我敢肯定商业街上的电缆铺设工程在完工后确实造成了一些问题。”
“我在意的是住在史蒂文街29号的老夫妇被杀了,而在案发时间前后内森应该在去邮局的路上。”
“这话你昨天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我说,“我今天问了他,他矢口否认,表示毫不知情。”
“他在撒谎。他的话漏洞百出。你注意到他回避了他是否拿了信的问题吗?”
“去趟邮局只是托词。”
“什么意思?”
“意思是他只是出门转转。他需要自己的空间。他不是真要去邮局。”
“我可不这么理解。这明明是他掩盖双重谋杀的借口。”
“这仅仅只是一个假设,不是吗?”
“他承认他走在史蒂文街的左侧。”
“嗯,是的。在他去商业街的路上。”
“你似乎站在他那一边啊。”
“我只是试着坚持真相。作为精神治疗师,坚持真相对我的工作很重要。”我忍住没有和他说警察也应该坚持探究真相。
“你桌上的那些是他的案例记录吗?”摩根问道。
“是的。”
“有暴力记录吗?”
“你听到他的话了,他是个软心肠的人。”
“我看是疯子吧。凶手似乎是一时冲动,毫无作案动机。这对和蔼的老夫妇可从来没招惹过谁。像这样的案件,我们会排查所有的可能,不过我敢用名誉打赌,这一定是一个疯子干的。”
“我可不会那么叫他,探长。”
“随你怎么说他,你懂我的意思。一个理智的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人的。他们的房子里有贵重古董,还有两百多英镑现金,可凶手什么也没拿。”
“在你看来,盗窃杀人是不是更合理?”
“这样我就知道他的动机了,不是吗?”
“那案发现场呢?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吗?”
“那里真是一团糟,法医正在进行全面鉴定。最好是凶手刚好沾了一些和老夫妇DNA相匹配的血,毕竟他免不了会沾上一点儿。如果找到内森那天下午穿的衣服,我们就能下结论了。但他似乎把证据都销毁了。他可不像他装得那样傻。”
“他借的那套衣服呢?”
“和垃圾一块给扔了。他说衣服不合身,对他没什么用,而且老人也不要了。”
“这倒是说得通。”
“当然。我们假设凶手在房子里作案后脱光衣服,冲了个澡,然后把自己的衣服塞进塑料袋里,从老人的衣柜里拿出一套衣服。很可能还给自己选了一双干净的鞋子。”
“我可不是法医专家,但如果他真那么做了,那肯定会在房子里留下一些DNA吧?”
“希望如此,那样的话我们就能抓他了,我希望能告诉你他被逮捕的消息。”
“另一个嫌疑人呢?”
摩根吃了一惊,沉默了一会儿,交叉起双臂,瞪着我,好像我在故意激怒他似的。
“以防万一,”我说,“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我和一个叫乔恩的人谈了话,看看谈话视频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我认识乔恩是因为给他做过很长时间的心理治疗。他像往常一样,驼着背坐着,双手紧握,眼睛直直地看向地面,显得十分消极压抑。
“乔恩,”我假装不经意地问道,“你在史蒂文街尽头的公寓里住多久了?”
他叹了口气。“三年,或许更久。”
“对,应该有这么久了。我治疗你都两年多了。你还是一个人住吗?”
他点点头。
“那你做得很好,又购物又做饭的。在这个现代社会能生存下来的人都很不容易。不过我估计你应该有点业余时间,空下来的时候你最喜欢做些什么呢?”
“不知道。”
“看电视?”
“不太喜欢。”
“你没有电脑?”
他摇摇头。
“除了购物和来这儿,你还会出门吗?”
“会吧。”
“去散步?”
他皱起眉头,仿佛在努力听远处传来的声音。
“可以呼吸点新鲜空气,锻炼一下身体,”我说,“你住在一个不错的地方。春夏季时公园里开满了花。我想,你应该经常出去的吧。”
“你说是就是吧。”
“那么我猜你一定见过你的一些邻居,住在史蒂文街上的那些人,他们在屋外洗车、做园艺或者遛狗。你跟住在29号的那对老夫妇说过话吗?”
他坐在椅子上,开始前后摇晃。“可能说过。”
“他们有一只宠物狗,是吉娃娃。据我所知,他们非常宠爱它。”
“我不喜欢他们。”乔恩回答道,还在摇晃着椅子。
“为什么呢?他们做了什么吗?”
“不知道。”
“我想你知道原因。也许他们会让你想起曾经认识的一些人。”
他默不作声,但愈加不安地晃动着。突然,他抬起下巴,露出了脸,脸上满是惊恐。
“上次谈话,我们谈到了你的童年,你的养父母会把你锁在楼梯下的橱柜里,这对老夫妇会不会让你想起他们呢?”
他呻吟了一声。
“他们也有一只小狗,不是吗?”
他蒙上眼睛说道:“不要讲了。”
“好吧,”我说,“我们谈点别的吧。”
“你会因为给我看这些记录而被赶出工会的,”摩根说,“你不是得为病人保密吗?”
“首先,我不属于任何工会,”我说,“其次,我是在努力保护各方的最大利益。”
“你觉得他会再次作案,对吧?”
“你指的是谁?”我问。
“第二个嫌犯,乔恩。他似乎很讨厌老人,而且他显得非常抑郁。”
“他平常就这样。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凶手。在你对内森下结论之前,我希望你能先看看这段访谈视频。”
“可以肯定的是,内森不抑郁。”
“对,他的性格比乔恩开朗。你注意到他们的肢体语言了吗?内森坐着时身体前倾,会有眼神交流,而乔恩在一直往下看,很少能看到他的脸。”
“乔恩被养父母锁在柜子里的事是真的吗?”
“哦,是的,我敢肯定。我相信喬恩告诉我的一切。他说得不多,但你可以相信他。内森我就不确定了,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而且渴望跟人交流。他一直努力把自己的经历变得有趣。”
“你指的是掉进池塘那段?你相信他说的吗?”
“不是不可能。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换了衣服。”
“我之前敢肯定他是在胡说八道,可现在你给我看了另一个嫌犯的视频,我就没那么确定了。我想亲自审问乔恩。”
“那是不可能的。”我说。
他脸都气红了。“现在要我收手太晚了!这是我的工作,没人能阻止我。”
“探长,在你对我发火之前,我想把第二次谈话的其中一部分再放一遍。我会把声音关掉,我想让你仔细看看乔恩,他向后摇晃的那一刻,灯光照在了他的脸上。”
我倒带后重播,快进到我想要的那一段,就是当我提到那对老夫妇时,乔恩开始摇晃,神情紧张的那一段。“就这里。”我点了暂停。
乔恩的脸没对上焦,但还是能认出他来。
“我的上帝,”摩根叫道,“他们是同一个人。他是内森。”
我让他好好消化一下这个发现。
“我说的对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可能让你难以接受。内森和乔恩是同一个人的两个不同身份。这种病叫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以前称为多重人格障碍,但现在我们对此的理解更透彻了。这些所谓的人格是组成同一个人的碎片,而不是独立的身份。乔恩是主要人格,悲观又抑郁。内森是第二自我,外向、开朗、富有创造力。”
“我听说过,”摩根说,“就像被不同的人附身一样。我看过一部与此有关的电影。”
“没错。这为好莱坞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如果真得上这种病就不好玩了。这种精神失常真实又可怕。一个患者可以呈现多种人格状态,每种都有自己的形象和身份,这些身份仿佛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消解他们,最终将他们融合为单个个体。乔恩和内森会变成乔纳森。”
“干净利落。”
“可能听起来利落,但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对我来说干净利落,”他说,“我不确定他俩谁是凶手,但现在我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我已经找到他了,管他说他自己是谁。”
“我可不指望这能奏效。”我说。
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治疗这种病需要在所有人格之间寻找连接点。当你带着双重谋杀案来找我的时候,我可以预料到这会对乔恩造成极大的困扰。很大一部分内疚感是他自己施加给自己的。但你的调查带来的困扰可能是有益的,这可以让他回想起病症的创伤根源,我认为就是他在养父母那里受到的虐待,他们碰巧也养了一只狗,而他们对狗的宠爱远胜于他。”
“真可怜,”摩根说,“但我得公事公办,有两个人被他谋杀了。”
“所以你是告诉我,乔恩认为他可能杀害了这两个老人,但事实上他没有。”
“得了吧。”他说。
“请听我说。内森的故事是真的。他真的去捡了气球,追了小狗,又掉进了池塘。对他——这个更积极的人格——来说,这就是一次能作为话题的有趣的经历。但对乔恩来说,他也经历了这一切,但这让他不安,让他想起抚养又虐待他的养父母。他的感觉全然不同,甚至想杀人。”
“等等,”摩根说,“你是想告诉我这起谋杀案从来没发生过?”
“发生过,不过是在乔恩的脑海里。对他来说这一切都很真实,好像他真的亲手杀了那对老夫妇一样。但我向你保证,这对老夫妇安然无恙。午饭时间我去了趟史蒂文街,还和他们聊了会,他们证实了内森的话。”
“我不明白。我觉得你也疯了。”
“但更重要的是你得知道,”我告诉他,“还存在着第三个身份。他充满良知,报复心和控制欲都很强,随时准备谴责别人。他确信谋杀案发生了,因此必须进行调查。认识到这一点是走向人格融合的第一步。帮我个忙,再看一眼屏幕上乔恩的脸。”
他不耐烦地叹了口气,瞥了一眼屏幕。
“现在看看这个,探长。”
我递给他一面镜子。
(张修竹: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级英语系,邮编:21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