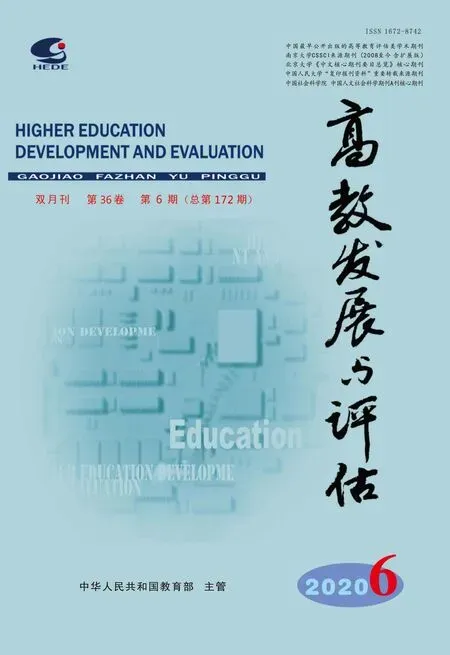通过关注历史来诠释近现代课程的发展
——伊恩·韦斯特伯里(Ian Westbury)教授访谈录
2020-03-16埃米尔鲁兹加王海莹
埃米尔·鲁兹加,著;王海莹,译
(1.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课程与教学系,厄巴纳,美国 618920;2.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天津 300191)
2017年夏天,我很荣幸地访谈了荣休教授伊恩·韦斯特伯里。我以一种小规模的口述历史的半结构访谈来谈论课程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希望能激发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学术交流[1]。一般来说,学者个人经历记录是当代和未来教育学者可能会受益的重要历史记录,我希望现在这篇访谈建立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作为课程领域的教授,韦斯特伯里学术卓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B部在2003年授予他终身成就奖。从1975年到2009年,韦斯特伯里先后担任《课程研究期刊》(该领域重要出版物)的助理及之后的主编职务。由于他长期在《课程研究期刊》任职,这使得韦斯特伯里具有得天独厚的视角讨论该领域问题。本文是此次访谈的内容。
一、历史考察:课程领域的危机
M.埃米尔·鲁兹加 (R):
一些研究课程的学者最近谈到了该领域的危机[2]。您认为课程领域危机的本质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课程领域的危机?
伊恩·韦斯特伯里(W):
我认为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美国课程领域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课程肩负着美国中等学校由精英预科学校向大众终端中学转变,并在初级学校开展进步主义运动的任务(终端即:大多数学生中学后不再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 )。20世纪5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结束后,高中不再仅仅是一所服务于大众的终端学校,而是成为一所服务于民众的大学预科学校。课程方向开始变化,从为“生活”做准备转向为大学做准备。
传统课程虽然濒临死亡,却又在自我更新。到20世纪70年代末,激进的“进步”社会文化运动、女权主义、种族的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等革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将课程理论视为文化研究的运动,最初由马德琳·格鲁梅特、比尔·皮纳尔、汤姆·波普克维茨和亨利·吉鲁等人领导。
这些运动被学生们所追捧。旧式课程、寻求理解学校和学校理念的概念实证研究兴起。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福柯文化研究是适宜的,但更应该基于社会和文化。基金资助者对作为教师教育这部分议题并不太感兴趣,转移了课程领域的注意力,使其不再关注学校面临的“现代”问题,例如,美国学校教育的结果不公平、“城市”问题、技术、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评估和制度问责,而这些问题在不同时期都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之一是使教师教育和课程研究分开,许多介于二者之间、研究课程的学者转向到教师教育研究,从事学校改进的实践工作。
R:这场危机与1969年施瓦布定义的危机有何关系?它们一样吗?
W:这也是施瓦布50年前所说的危机。我参加了1967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议题是“课程和课程理论的未来发展如何?”施瓦布等人出席会议,发表了关于课程理论化的看法:传统的课程教科书与现实无任何关联。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课程”教授方法是一种“一般方法”,即向学校工作人员讲授不符合主题的方法框架。
课程研究中的“研究”是什么?是应用教育心理学吗?课程理论是什么?泰勒理论是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来教授的,后来我曾与泰勒一起参加一个为期一个月的研讨会。这使我意识到,用这种方式教授毫无意义,他没有试图“启发”我们:力量来自于听众。泰勒有时会以奇闻轶事的方式回答问题或评论,有时会用格言,抑或用他所谈及问题的“规则”来表述。泰勒理论是一组笔记,在提醒学生是在课堂上。
对我而言,课程理论主要通过与历史理论的类比来思考学科及领域。我们曾思考过如狄尔泰(Dilthey)生命同情中的“理解”,迈克尔·斯克里文或威廉·德雷有关的《历史解释》的著作,显而易见,这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我认为,对于包括阿尔诺·贝拉克(Arno Bellack)和埃利奥特·艾斯纳( Elliott Eisner)在内的许多人来说,理论意味着一个平台或一种思想体系,如进步主义等。对其他人而言,理论意味是超越了仅仅“做”的层面,是基于研究的观点,要是思考“为什么”就好了,就像赫伯·克利巴( Herb Kliebard)的《美国课程的争斗》(ThestrugglefortheAmericanCurriculum)或者伊沃·古德森(Ivor Goodson)的《学校科目和课程变化》(SchoolSubjectsandCurriculumChange)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对其他人来说,课程理论是直接理解课程和教学现象的课程研究。如《课堂语言》(TheLanguageoftheClassroom)一书或比尔·里德(Bill Reid)和德克尔·沃克(Decker Walker)共同编辑的《课程变化中的案例研究》一书所示。会议上各家众说纷纭。会议结束时,施瓦布告诉我,他已经“解决了”会议的问题,这是形成他理论体系的基础。
R:为了更好地概念化这些问题,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的历史可能会有所帮助,您怎么看待这个领域的形成时期?
W:菲利普·杰克逊(Philip Jackson)曾谈论过三种将“课程”教学概念化的方法,这些方法从地点或机构的角度来考量的话是理想的类型。“师范学院”的特点是开展大型讲座班,讲座的任务是交流时代的伟大思想,涉及历史、社会经济和哲学等领域。时代的问题在诺曼底爵位伯爵的《学校敢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DaretheSchoolsBuildaNewSocialOrder)一书中得以体现。这是源于大萧条时期的契约,是对苏维埃抱有浪漫主义兴趣的臆想。“芝加哥”之外的这些学校,倾向于接受教育新秩序,那是甜蜜和轻松的。很多地方的授课者是退休人员,他们是皮纳尔(Pinar)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保持着“旧”思想对学校的理解,他们是从学校走出来,在学校曾担任过校长和教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课程会议是师范院校大规模思考“新理论”的契机或“新平台”。
随着概念主义重构者披上杰克逊的理论外衣,这个领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采取了师范学院的诸多风格。在概念重构主义者的例子中,华盛顿会议的“理论”任务被赋予了文化研究,几个早期倡导者最终进入了文化研究。芝加哥学派就是皮纳尔所称的“概念性经验主义者”,是由年轻学者,诸如我,斯坦福大学的戴克·沃克(Decker Walker)等人所接受,我们要么参与评估,要么进行教师教育研究等。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若要对学校产生影响,必须了解学校是如何运作的。
但是那时,皮纳尔已经把我们从他的课程观中删除了,他把课程视为文化研究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社会科学,而概念经验主义者则试图为学校教育提供一个研究基础。但核心问题是,我们这些概念经验主义者无法确保有一个清晰的未来,因为我们身处芝加哥大学,而芝加哥大学却关闭了它的教育系。
二、施瓦布作为一名课程学者对课程的深入思考
R:您谈到您准备以施瓦布的“实践教育”为研究基础的计划,您能给我们谈谈施瓦布的个人及学术研究吗?
W: 施瓦布是一位优秀的本科生教师。他能理解学生并能唤起他们的强烈忠诚和承诺。20世纪40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学院做教师,该学院在11至13年级的学生中进行了一项实验,以重新审视美国的教育结构。在那个时候,施瓦布作为自然科学学科方面的主席领导了生物学的变革,他被泰勒发现,泰勒当时是教育系主任。施瓦布以教育哲学教授和自然科学教授的身份入职教育学院教育系。大约20年后,他在《学院课程与学生抗议》(CollegeCurriculumandStudentProtest1969b)一书中更新了他对学院和本科教育的看法。
施瓦布对教育的思考来自于他在大学的教学经历,包括“实践”的概念。事实上,课程中“实践”的概念是《学院课程与学生抗议》的一部分。施瓦布所阐述的“实践”,定义了大学课程的形成和讲授,他做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也秉持同样的理念。在华盛顿会议结束后,他以第一篇“实践”论文对会议的讨论作出回应。他第一篇“实践”论文是在他完成《学院课程与学生抗议》之后立即撰写的。读者试图描绘出他的实际关注点以及如何在课程中发挥作用,施瓦布被广泛引用的的实践论文需要结合《学院课程与学生抗议》一书的背景,论文中的背景在此书中有更全面阐述。
R:从个人到专业,我认为施瓦布对课程领域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W: 我不认为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它与教师教育不同的是,它已经从课程研究中消失了!当大肆宣扬变革和抗议的时候,实践论文出现了。施瓦布认为,像课程这样的事情必须深入到学校实践。施瓦布的实践观念与激进派形成观点的对立。“实用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把它看作是提倡一种普通的、感性的、传统主义的学校改进方法,而这种方法缺少了施瓦布“实践”的复杂性。
我相信激进派不承认施瓦布对英美课程领域的影响。继续谈论施瓦布的人通常都是芝加哥学派,他们与施瓦布有过直接的接触,比如已故斯坦福大学的艾略特·艾斯纳( Elliot Eisner)和李·舒尔曼(Lee Shulman)等。我认为,随着芝加哥大学教育系的关闭,实践教育研究并未得以进一步研究和在实践中应用。
R: 那么,您如何解释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遗产,特别是它的概念解读?如果一个跨入课程领域的学生问您为什么他/她应该读施瓦布?您会如何说服年轻的学者或学生去读施瓦布?
W: 因为他在教育各方面的观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这个领域的研究目的不是改善实践,那是什么呢?在大学,课程研究领域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改善实践?”接下来是另一个问题:“用以完善课程的学术工作的本质和形式是什么?”“什么是课程研究?”“我们如何将课程研究设想为一个可以教授的(维持或改变)行为的领域?”作为研究机构,学校教育是关注的重点。教育改革需要围绕着学校教育,而不是教育的理念。施瓦布是唯一能让您看到这种观点的人。
我发现了杜威的一篇精彩文章,文章指出,在19世纪末期,学校中不同领域的两种人达成了共识,即:第一,理论研究者,他们宣扬教育的甜蜜和光明,并垄断了教育意识形态;第二,学校管理者,控制学校的预算和资源,并垄断学校的实际运作[3]。杜威讨论学校应通过变革制度来实现教育理想,改革者设法通过改变教师而非管理者的教育理念来改善学校教育,管理者依然按照陈旧观念给教师分级班,每班40多名学生,在数排桌子和一本教科书的教室里授课。不可避免的是,管理者对学校的控制抑制了教师对甜蜜和光明的任何渴望。概念重构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研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杜威在这篇精彩的文章中分析了学校改革问题。六七十年后,施瓦布试图解决这个百年未解之难题,但他并没有像杜威那样清楚地把学校看作一个机构。我认为泰勒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关心学校制度的改变。学校的变革不能简单地改变老师的想法,学校变革是个制度变迁的整体过程。
R:许多学者, 如您1994年、里德1999年、纳尔(Null)2011年的书中,都认同施瓦布的理念,并对现在大家熟知的审议方法作出了贡献[4-8]。比如,老师或行政管理人员让您说服她/他为什么要慎重地设计课程,如何说服教育实践者?换言之,施瓦布与您提出的审议的传统对课程领域的潜在贡献是什么?
W:应该说,里德创建了“审议课程理论”。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一个标签来聚焦组织作为概要课程理论章节的一部分。
您的问题涉及到对学校和“实践者”可塑性的看法。我曾在一所学校做过两年的研究项目评估员,通过比较我们和他们教给“职前”学生的概念,我学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他们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提供服务:社会工作者的干预权来自于他们提供服务的机构,例如咨询、缓刑、酒精康复、收养等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也是提供服务的机构,教师的角色是从制度上衍生出来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类服务提供机构是否具备与“购买”课程不同的开发课程的常规能力,这种开发出来的课程是大型文化社区中可用的一种小型课程。我相信很少有学校有人手和预算来进行服务创新,而不是提供服务。例如,每一所学校都需要清楚要教多少种语言以及哪种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还是汉语、法语、德语和日语?这涉及到社区的教育愿景、管理者,因为他们控制预算、人员配备和社区关系,还涉及教师教育、教师认证、教师招聘与教师稳定等人事政策。
创新与提供服务之间存在着重要区别。问题是谁有能力创新课程?我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一个国家科学基金会项目正在开发一门工程课程“人类创造世界”(The Man-made World ,TMMW)。尽管国家科学基金会投入大量资金推广这门课程,但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这里,我不能说服任何人对此感兴趣。 我们与学校项目负责人之一,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工程系主任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见了工程学院院长以及几位工程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教师中,没有人能够胜任“人类创造的世界”项目课程,因为他们的经验与“人类创造的世界”暑期工作坊的老师们相差甚远。在工程学院,所有被提到可能对幼儿保育和教育项目感兴趣的人都被归为“教师”类型,也就是说,他们作为研究人员是“失败”的。“成功”的工程师们没有时间学习幼儿保育和教育,也没有时间和学校教师们一起工作。
正是这样的经历,我才意识到制度创新问题,也是杜威在2001年在《教育局势》(TheEducationalSituation)中所持的观点。我甚至不能提高教师们对培养幼儿创新的兴趣,也没有办法让创新项目进入学校。
三、德国教学论与课程
R:您发表了很多关于德国教学论的文章。您能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对德国传统教学感兴趣的吗?德国传统教学为什么值得关注?
W:对德国教学论的研究纯属偶然。我和沃尔特多尔(WaltDoyle)分享了一篇关于数学教育的论文。后来,沃尔特问我,作为一个曾在瑞典和德国生活过的人,如何看待德国传统教学( Didaktik),这也是我文章的缘起。我说我不知道,但我的同事,德国人斯特凡·霍普曼(Stefan Hopmann)那时在德国基尔大学工作,非常热衷于将传统德国教学论传播给完全不清楚德国教学论的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学者。因此,在挪威、瑞士和德国同事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教学论的研讨会,并开始计划一本关于德国教学论书籍的翻译工作。
虽然作为修辞学发展的教学论有其自身传统,但它与麦克奎安(McKeon)和施瓦布一样,产生于亚里士多德和解释学传统。在美国,我们谈论反思性教学,但没有人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反思性教学。德国教学论为反思性教学提供了框架,同时也为1987年舒尔曼提出的教学内容知识提供了框架——请记住,舒尔曼是施瓦布的学生和追随者[7]。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教学论(Didaktik)是反思性教学和审议惯例模式。德国教学论并没有被译为“课程”,我认为,美国的课程传统本质上是关于建立学校和学校体系的教学,而德国传统教学论是指在国家规定框架内个体的教学。
四、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对课程意味着什么
R:说到德国这一传统,我们把讨论引向更广泛深入的层面。我认为该领域的两个主要问题是:教给学生什么?如何教呢?此外,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新鲜,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只需要看看西方的“七门自由艺术”(这七门是中世纪文法、逻辑、修辞学、算术、几何、天文及音乐),就知道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很久。因此,“七艺”经过发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通识教育[8]。请您谈谈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以实践为导向的当代世界中需要把一切做好?
W:我记得几年前有一部名为《文明》关于艺术史的电视剧,由英国国家美术馆前馆长肯尼思·克拉克( Kenneth Clark)出品。该剧记录了美术历史,即雕塑、建筑、园林等。然而,在后来的一个节目中,克拉克在飞往纽约的画面上说我们现在是20世纪,纽约以其庞大的地下地面工程以及城市景观成为“文明”的标志。但是,此处的文明及后续节目都是关于美术、古典和“高级”通俗文学。它是贵族、上流社会和神职人员的文明,通常存在于农村,重点是乡村富人社区和教区。克拉克的新文明指的城市的成功企业家、工程师和建筑师,而不是画家和牧师所取得的成就。
我认为克拉克的观点是您提出问题的核心。博雅教育一直持续到20世纪,它是一个关于如何培养人们(男人们)的教育,把人们(男人们)培养成为乡村绅士、乡村牧师、陆军、海军军官、律师以及医生。在文化和技能方面,博雅教育在为培养绅士、士兵和或乡村牧师做准备,是关于培养“既善于讲话又有学问的人”的教育。它是一种对文明艺术的世界性认识,是参与“文明”社会的能力。
博雅教育课程起源于美国,当时大学里挤满了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孩子、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孩子、欧洲移民的子女以及富裕的非移民家庭的子女。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就把学习作为走出贫民区和工人阶级的一种手段,但“他们”不像“我们”,他们需要知道在社会中如何才能不那么“柔弱”,那就需要更广泛地参与到文化中来。学院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在宿舍、剧院、食堂等地方形成的。他们的大学生活不是宅在屋里,所以这些建筑的效用是有限的。那么,文化可以传授吗?他们应该知道什么?通识教育根源在于这些工人阶级及移民孩子需要受到文学、艺术、古典人文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熏陶。
基于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大学开始了一场通识教育运动,最初明确的任务是让学生了解西方文明和文化、美国文化、宪法、选举制度以及职业纪律等。在这一时期,“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成了同义词,但内涵却不一样。它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偶尔会在芝加哥保持涵义一致,因为麦基翁来自哥伦比亚教育通识课程运动,但他真正深入思考的是博雅教育。因此,芝加哥大学的麦基翁、施瓦布等致力于设计一个“现代”的博雅教育课程,该课程围绕着文化适应和现代历史而构建,形成“心灵的力量”,也就是掌握三重元素的技能:语法、逻辑和修辞。芝加哥大学教师期待学生回到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或其他任何地方时,成为法官、立法者、州长以及教授。这些希望建立在教育所赋予他们的品格、推理能力以及同样重要的信心基础上,这三者是有机结合的。换言之,博雅教育和通识教育是不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任务,由于大学和学院的结构,通识教育在美国很重要。在大学或学院出现之前,没有“第六种形式”或体育馆来承担通识教育任务。
R:我认为,对博雅教育的批评者与其支持者一样多。您如何来回答一个博雅教育的批评者,他声称博雅教育只代表精英资产阶级?
W:博雅教育与资产阶级无关,而与农村士绅和“有学问”的职业有关,这些职业是指法律、医学、高级基督教神职等。C.阿诺德·安德森(C.Arnold Anderson),社会学家和比较学家,是芝加哥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阿诺德曾在肯塔基州和南方工作过,他曾说过,“南方高等教育体系完全失败的最明显证据是种族隔离。”我提出疑问:“为什么?”,他告诉我,因为高等教育的核心功能是地方精英的社会化。地方精英们必须学习世界价值观和掌握实现这种价值观的技能,即赢得选举。种族隔离完全被世界主义文化所拒绝,在南方,他们却维持种族隔离。这就是高等教育失败的绝对证据。他拿自己的研究草图:饮用水中的氟化物对于牙齿是至关重要的,这当然是强制性药物,因为精英们决定你最好使用氟化物。从科学上讲,氟化物可以减少儿童的蛀牙,而且无害。他对全民投票中有关将氟化物纳入当地供水的得失进行一次分析,在氟化物被否决的地方,当地精英选举失败了。这些地方精英是学校的管理者、校长、律师和医生等。大学生需要具备融入开明世界规则的技能。社会化是博雅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不是欧洲资产阶级的特权。
五、评估与课程
R:在我们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想知道您对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MS)等评估在课程领域如此流行的看法。
W:我不确定他们在课程领域是否流行。然而,在美国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学习结果存在巨大的不公平,国家教育进步评估等项目所进行的大规模评估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关注,第一,国际大规模评估,如(PISA)或国际数学与科学趋势研究项目是否有价值?第二,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大规模国际评估的结果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结果?如果说评估不好,那么课程无需在意研究的结果及大家的看法。关键是政府如何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如何利用这些成果为学校创建新的管理目标。这关系到人,关系到人的个性。但是,政府运用这些研究结果与人们运用这些结果所产生的问题是不同的,因为人们普遍关注有关不平等或种族不公正的问题。换言之,脱离评估,就不能理解课程的完整性。
我们甚至可以将“美国问题”复制到其他国家。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果您观察分布图,所有国家或多或少在四分位数都有相同的结果分布。问题出现在最低的四分位值上,国际教育成就评估协会第二次国际数学研究发布的结果显示:美国、新西兰和比利时似乎没有为学生取得的成就设置底线,其他国家似乎为学生取得成就设定了底线。
国际大规模评估的一个很遗憾的结果是: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学校里的人们疯狂地想提高学生的成绩,而排名后四分之一的学校一点也不在乎。于是,整个政策的重点都着重改进,例如数学、科学和STEM教育,但是,只有开设这些课程且排在前四分之一的学校在努力改进。奇怪的是,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思考大规模评估的过程和结果。如果教师、课程学家、心理测量学家、政策制定者都不能对评估过程与结果深入研究,那么如何有希望去说服政客们去思考评估呢?如果婴儿死亡率很高,需要知道如何分配资源。我们拒绝研究哪些学校的成绩是糟糕的。因此,我们以完全错误的方式来分配政府资源,或者更谨慎地以非最佳方式来分配政府资源。
R:最后,我希望您对课程领域的未来进行预测。未来该领域会发生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发生什么?
W:我不知道。我有个亚洲朋友想辞去课程教授的职位,但是在美国,他却在课程领域找不到职位。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这个领域框架不同,虽然“工作”并不少,但是这个领域工作正再次转移到学科、政策分析、心理学甚至教师教育,因为大家依然正在从这个领域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