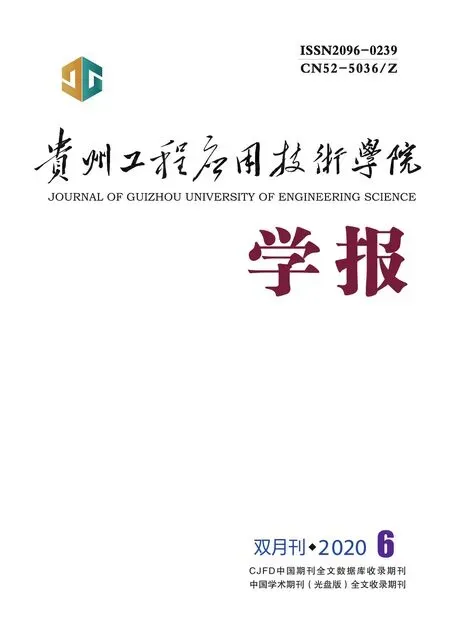谢文洊《程山十则》切己思想探析
2020-03-15黎雅真
黎雅真
(肇庆学院文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一、前言
谢文洊(1616─1682),明清之际理学教育家,字秋水,号约斋,江西省南丰县人,时人称其“程山先生”。谢文洊出生于南丰县大井里,其家族为书香世家,故自幼好礼重仪,承传家学,孝亲敬长、敦睦兄弟,孜孜勤奋向学,毕生聚徒授学,专志于著书立说。谢文洊生平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阶段是谢文洊求学期,其由务举业而入禅,由入禅而习儒,习儒则又由崇奉阳明转而师承程朱,途中颇多曲折,但其能不断地自我完善,使治学日精月进。后阶段则是谢文洊治学的兴盛期,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和著书立说,奠定著名的“程山谢子之学”。
正当明末清初之际,学者开始对理学思想有所反省,为导正明末以来阳明后学所造成的虚浮学风,进而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使得学风为之趋实,理学思想在此风气影响下,亦有重实践、趋实行之风,以理学的理论及修养方法修身,推广教化、讲习讨论,并将儒家的文化推展,强调古圣先贤的理想,实践于治国安民。谢文洊身处在动荡的时代,正是经世致用学风再度兴起的时期,其在面对当时的窘态,依然主张中兴理学,以挽救世道人心。可惜的是当今学界对谢文洊的研究向来不热络,固本文以其《程山十则》之切己思想为主轴,探讨谢文洊躬行实践的观点,进而开展出其教育理念与风格,达到继往开来之目的,期盼能抛砖引玉,促使学术先进、同好,关注谢文洊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价值。
二、《程山十則》切己思想内容
(一)辨喻以定志
谢文洊在为子孙立家教时,认为志学者应当品格端正,志向高远。因此其《程山十则》开宗明义第一条即为“辩喻以定志”:
人贵立志,志一则气从。然未有器识鄙陋,而能特然以圣贤为志者,故先须辨别所喻。如见解意趣只在富贵功名,或辞章技艺,或乡党自好,则其志之所向,不过成就富贵功名而止,辞章技艺而止,乡党自好而止,如此而欲求入圣贤之门墙,登其堂奥,岂可得乎![1]754
谢文洊认为“定志”为学者之首要原则,人贵立志,志一则气从,惟有确定立志的方向,才可一鼓作气达成目标。关于“定志”必须明辩所喻,若意趣只在富贵功名、辞章技艺、乡党喜好,把志向建立在这些肤浅的事物上,将如何走进圣贤的门墙呢?所以辨别所喻,清楚自己期望的方向、了解自己理想的抱负,方可达成圣贤之志。接着文洊谈到欲学需先读《西铭》:
故愚欲学者先于西铭一篇,细研实体,捐去私吝,识得天地万物一体之意,寸心耿耿,有独契而难以语人者,则志之所之,决不肯自安于狭隘,其光明俊伟之胸怀,轩昂振迅之气概,虽欲自异于圣贤之徒,而不可得矣。[1]754
谢文洊认为《西铭》明喻甚是,“定志”必须弃除自私吝啬,认识天地万物实为一体。而立定志向,心胸不可安于狭隘,必须开广光明,才可如同圣贤之恢弘气概。关于“立志”文洊在《日录》中亦指出: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252
指出学者须要以“明经立品为本”,如此立志则不自弃,也就是说无论身为师长抑或学生,都要做个于国、于民、于社会、于传统文化都有裨益的志士。文洊在《果育斋教条》第一条中,也有谈到关于士人如何“立志”的要点:
今之学者岂不曰:“我独读书志在科名,与彼力作较子毋者,岂可同日而语。”殊不知认此士字不真,则科名到手,温饱是计囊槖,既充满欲自恣,不过农工商贾之才且黥者耳,吾不解其所谓士者何在也?王子垫问孟子曰:“士何事?”对曰:“尚志”。夫惟尚志乃知自重,学者宜时时勿忘此意,不尔则自暴自弃而已。[2]127-128
说明今之学者若把读书立志摆在科名,即是对士字认识不真的行为,此和农工商贾之才就毫无差别。正如孟子认为,所谓“士”重在“尚志”,“尚志”讲求“自重”,所以学者当以切己自重,时时提醒自己实践不可自暴自弃。
(二)实践以立基
谢文洊重视“切己”来奠定治学基础,认为只有躬行实践的教育环节,才得以巩固学业基础,所以《程山十则》第二条即为“实践以立基”。文洊在“实践以立基”中内文提到:
日用下手,不过当下一步,放过不得,躐等不得。为学而舍却当下,决无有入手处也。如在家则孝父母,友兄弟,抚妻子,畜婢仆;在外则料理世事,应酬人情;在馆则亲厚师友,教授生徒,以至一切动静语默,见在所值,皆属当下一步。愚所编幼学先言一书,便是教人当下着力样子。[1]755
日常生活不过是注重“当下”的艺术,任何一小步骤皆不得放过遗漏,譬如为学若舍去当下,即无处可下手。在家须孝顺父母、爱护妻子、畜养婢仆;在外应处理世事合理、待人接物合宜;在学馆则敦睦师友、教授学徒,关键在因地制宜活在当下,在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事情。文洊主张教育人才要及早,应从幼年开始,其在《初学先言》中即教人“当下一步”的实践作法:
不论成人小子,皆从此一一践履过去,方得成章,方可上达。如造大厦,不先坚固基址,则梁栋轮奂将无所施。故凡见地远大、志愿高迈者,须急求实践,以立基址,庶不堕罔念之狂。[1]755
谢文洊认为无论是成人或小孩,行事皆该践履笃行立定基础,方得成章、即可上达;如同建造大厦,不稳固地基,则梁栋无所依靠,所以凡事见地远大、志向高迈的人,躬行实践是奠定深厚基址的开始。
(三)奋厉以去习
谢文洊认为学者常有俗情、惰习、浮气、骄心四者通病,而为学只要有其中一样习染,即与道相阻隔,惟有俗情消,惰习除,浮气收,骄心抑,方可谓之好学。文洊在《程山十则》第三条“奋厉以去习”中提到:
为学之蠹,莫大于气质习染,惟自幼得严明父师为之绝其萌芽,正其机势,庶几坦行无阻。傥质已僻,习已深,虽将义理看得灿然,如一物在眼前,只须拾取,必且扞格沮御,若有一人阴掣其肘而不得自遂者。于此稍一因仍,则日甚一日,久而相忘,照人则明,照己则昏,胜人甚勇,胜己甚怯,岂不可叹![1]755
学者为学的阻碍,莫大于沾染恶习,恶习一日一日增长,久而不知其害,对照人明显、反照自己则昏沌;胜人则逞匹夫之勇、胜己则显胆小退怯,惟有自幼父母师长断绝其恶习,才不至于往后积习根深蒂固,无法改进修正。其最后亦探讨去习的工夫:
若夫具真见、立真志之豪杰,定然奋不顾身,用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力,如先儒所谓持志如心痛,防过如猫等鼠者,日渐月劘,必期扫涤至尽而后已,决不肯自欺自怙,苟且偷懦,以了此生也。至于人各一偏,不能列举,平心细察,必自了然。[1]755
谢文洊认为身为豪杰之士,必定奋不顾身持志去习,加倍努力勤奋向学,不可稍有怠惰自欺欺人,以免学业误入歧途。因此文洊在授学的过程中,总是告诫弟子务必切己去除陋习,将不良有害的恶习渐渐驱除殆尽,才不至于枉费此生的努力。
(四)坚苦以砺操
谢文洊的治学态度向来坚毅严谨,故其对门下弟子也是要求甚严,强调无论师长、学生均要艰苦磨砺意志,刻苦固守节操。如《程山十则》第四条“坚苦以砺操”内文所言:
人生素位,逆多顺少,而逆境之操尤难。三代以下,儒者之不得志,身处逆境,皆视为本分事。知为本分,则安心宁耐,固守不移,一切援上陵下、怨天尤人之意,俱归消融。[1]755-756
说明人生在世逆境多顺境少,学者在治学时若处于逆境,尤其容易怠惰放弃,因此视逆境为助力,以解决困境为本分,耐心固守信念,不怨天尤人,才是正确之道。文洊再指出:
其生平行己,防范则如处女,坚贞则如金石,光明则杲日之丽中天,洁清则秋月之映止水,如此胸次,有何顺逆可分。吾辈生多贫贱,而拂乱时有,于最难过处,当勉思古人以自砺,驯至于安贫乐道,斯可不愧儒者矣。[1]756
说明生平行己,处事防范、坚贞;态度光明如日中天、如月止水,能保有如此广阔的胸臆,为人行事则顺逆可分、富贵贫贱不改其志,并以古人劝勉自励,安贫乐道即便身处逆境,亦当奉行不改初衷潜心于学。
(五)绎理以养心
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11],通过减少不良的欲望,可以达到涵养心灵的作用,发展自己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就好比是在给自己的心浇水、施肥,保持内心的健全发展。谢文洊对于“养心”也有其一番见解,《程山十则》第五条“绎理以养心”内文提到:
人心不得所养,则天理无所滋益,而私欲日渐生长,久之,本心蔽昧将有必不可为、必不肯为之事,忽隐忍为之者,此学者所当大惧。[3]151
人心的习惯是多年养成的,虽不能一下子戒除所有毛病,但只要日积月累的切己改进,则可逐渐将多年养成的恶习消除,因此人心本身必须有所培养,若人心不得所养,则天理无所依归、私欲渐渐成长,久之本心逐渐被私欲蒙蔽,此为学者所戒慎恐惧不得轻忽。其接着谈到阅读先儒书籍对“绎理养心”实有帮助:
故先儒语录,当时加思绎,其析理之精,发明五经、四书之旨各有独得,而古人用功得力处,其甘苦滋味又最能引人着胜地,能时取而涵泳之,则浸灌日深,机趣日熟,从理自顺从欲自逆矣![1]756
谢文洊认为养心能培养健全的心灵,需要充分的时间、耐性长远着眼细心体验,并非一蹴而就,不可一曝十寒,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其强调阅读先儒语录,得以思绎其理则,判断其精义;藉由四书、五经之记载要旨,实有所取养其心智,尤其阐发古人用功成就处,最能引人入胜奉为表率。
(六)读史以致用
唐太宗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由此说明历史上有许多警世的教训,如同一面镜子,我们可由过去的演进历程中省思,而史书具有相当的教育功能,藉由阅读史书不但可以通晓历史遗留下来的经验,并能以此作为借镜致用。谢文洊在《程山十则》第六条中发表其对于“读史以致用”之看法:
二帝、三王修已而天下治,然兵农礼乐各有致用之方。详内略外,非圣贤之学也,故中庸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又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可见治天下亦非徒一修己可了。[1]756
古代二帝三王由修己进而治平天下,无论士兵农民各有其礼乐致用的方式,圣贤之学如同中庸所言:“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儒家传统理想中对学者的最高要求,读书不仅要提升自我心灵修养,更要对国家社会有所作为,所以致用之方不应只是向内修己,也要向外治国平天下。文洊亦深入探讨“读史”的功用:
经世之术,济变之方,莫备于史。读史者须别其是非,究其利弊,通其时势,坐可言,起可行,方谓有用之学。经曰:“安而后能虑。”注云:“虑处事精详。”不到能虑,终算不得得止也。[1]756
谢文洊认为阅读史书,探究历代古圣先贤之得失及朝代演变之兴衰,汲取他人生命经验与智慧,以读史达才为用,不但能熟悉经世的御术,还可以运用济变的方法,如此一来方能通晓时势,进而运用权变处事致用于世。
(七)勤讲以精义
谢文洊所谓“勤讲”,既是独立授学的聚徒“讲学”,也包含志同道合学者之间的讨论“会讲”①,主张通过“勤讲”深化学识水平。其在《程山十则》第七条“勤讲以精义”中提到:
为学固在自己,然孤而无辅,终难课进。昔圣人以学之不讲为己忧,不耻下问为可谥,盖以天地闲义理无穷,闻见有限,是非得失,所争在毫厘闲,而私意一蔽,遂有莫能自别者。此非藉朋友问辨之力,将何由得当![1]756
说明为学须靠自己不断努力精进,孤僻而故步自封,终将停滞不前无法进步。古之圣人遇到难题常不耻下问,原因在于天地之间的义理无穷无尽,但个人的闻见常会因观念固守而有限制,所有的是非得失,皆在抉择者的一念之间。文洊表示为了避免被私意所蒙蔽,学友之间的问辨会讲显得格外重要:
故诸友无论朔望讲会之期,即平时相对,偶尔过从,意中口中,无非为此事放舍不下,必互相质证,彼此剖析,然后快心。若相见之时,止以寒温套语及泛常闲事了之,亲厚者又不过家庭俗务,一再筹划而止,则志气悠忽,工夫粗疎,欲与之研究理路于几蔽之介,判决事机于疑似之闲,不可得矣![1]756-757
谢文洊认为只有勤于会讲,做到“互相质证,彼此剖析”,才能明乎理,精于义,并藉由学者间的问辨会讲,达到“敬业乐群,朝夕讲贯”,借着师生彼此教学相长,学者互相探讨切磋,学业才会有所进步。
谢文洊生平治学对书院教育给予相当的重视,认为“书院”是志学者聚会之所,德业相成之地,其称道书院即如古人所设的庠序学校,尤其是书院定期举办的会讲,能使人未知者知,未能者能;滞疑者得达,脆靡者更坚。正因如此谢文洊在教育生涯中一直对其所开辟的程山学舍教学竭尽心力,同时对书院会讲也倾注相当大的热情。
(八)简事以专功
谢文洊在《程山十则》第八条中,举出“简事以专功”,强调治学应当克尽本分,完成份内该做的事,才能专功精研学业。其内文说道:
职分内事,当一一尽之,使无遗阙,此即是学。但务外喜事,得已不已,则最为妨功,且令精神疲倦,心气粗浮,不惟于圣贤精微之言渐不相入,即辞令容止之闲,亦易流于尘俗。[1]757
谢文洊认为治学必须克尽本分,完成自己分内该尽的责任,太多繁杂琐碎的外务,不但会妨碍学业,导致精神疲倦,甚至心浮气躁,日渐与圣贤观念相背离,最后流于尘俗而不自知。内文列举孔子、朱子之言论印证:
论语曰:“居敬而行简。”程子曰:“居敬则所行自简。”人不能简者,皆繇利念,名念及好气之习不能自克,是以无事辄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变难事,一事生多事,羁绊层迭,迄岁不了,反将分内学业荒疎废置。迁延既久,恐一段初志俱汩没矣。惟敬以居心,则克己有力,内地既清,外事自简。[1]757
表示为人虽然修身严谨行事严密,不过待人接物却非常简明客气,意旨人不能简者,容易功名利禄熏心,无法克制恶习,导致无事则有事、小事成大事、易事变难事、一事生多事,如此层层羁绊,拖延过久还会造成初衷消沉、志气衰落,影响分内学业的发展,所以惟敬以居心,内事居敬,外事自简,才得以专功学业、迈向坦途。
(九)自反以平谤
孟子有言:“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2]28,此说明当有人对我有所批评,经过反省,知道是自己的言行不正直,的确有值得检讨改进的地方,纵然对方是一个着粗布粗衣的平民,我能不害怕恐惧吗?但经过自我反省,只要合乎义理,无愧于良心,纵然面临千军万马、数万群众,我也一样毫无畏惧会昂首直前!谢文洊“自反”的意义,就是能大彻大悟,判别义与不义,能辨是非、别利害、识顺逆、明生死的道理。这里所谓辨、别、识、明四者,即是彻底“自反”的切己工夫。文洊在《程山十则》中第九条“自反以平谤”内文谈道:
君子自修,惟务独知,不必人言是问。然谤议之来,正可自考。其中吾失者,吾之师也,急求改过以谢之;其不中吾失者,或不中吾此一事,亦当深思精察,平日必有致谤之繇,万一在己无歉,亦可以防于未然,作他山之石,而为委土之师。若但知尤人,不思自反,则不惟学问无长进处,而人益谤之,若张的而招射者矣。[1]757
谢文洊和孟子的看法雷同,认为君子自修,虽不必人言是问,但若遇到责难谤议,必须向内自我反省,知道自己的言行的确有该检讨改进的地方,将立即改正并感谢其忠告,经过自我反省行事无愧于良心,则须深思精察平日有否得罪他人而招致谤议,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人的指正意见能够帮助自己改正错误,如同导师纠正缺点提供借鉴。相对来说为人若不自我慎思反省,则学问即无法增长进步,接踵而来的谤议将永不停歇不可细数。
(十)相规以有成
谢文洊主张在求学态度上要互相规谏,做到“相规以有成”,以增广见闻,增进学识,也就是使受教育者做到谦逊诚恳,能虚心接受他人的忠言,且热于慷慨给予他人指教。其在《程山十则》中最后一条“相规以有成”内文言道:
人有能虚受不能忠告者,有能忠告不能虚受者,均非也。虚受者,虚己从人,不文过,不好胜,听而能受,受而能改,固为难矣。然见友有过,缄默隐忍,坐视成败,此非关切之诚有未至,则善柔之气不能自强也。[1]757-758
说明人有分“仅虚受不能忠告者”、“仅忠告不能虚受者”两类,不过此两种人皆不尽完美。所谓虚受者,不文过饰非、强辩好胜,能虚心接纳他人的建议,并予以自我改正;然而看见朋友有过失,却保持缄默隐忍,放任朋友的过错,不予理会坐视不管,此善柔之气终不能自强。文洊亦表示:
忠告者,刚直不回,恳款陈言,如不容己,夫岂易及?但过在己躬,友言见及,则拂然色沮,或争辨自怙,此岂友实无识,其言悉不足采欤?或亦好胜刚愎,抑遏不下,而吝于自反耳。故忠告者贵虚受,虚受者贵忠告,二者循环不已,相与有成,则同堂中如五味调适而共烹,八音和谐而合奏,于以享宾降神,敬无不将,而诚无不格矣。[1]758
说明忠告者的性情刚直,遇见朋友犯错往往恳切相劝,不吝惜苦口建言;只是当朋友见其处事不妥,尝试给予建议时,常因好胜刚愎压抑不下面子,而面红耳赤争辩不休,不知应该自我反省。文洊表示为学必须从善如流,积极虚心讷谏,不文过饰非;相对而言他人有过亦当坦诚相告,不为友人避讳、不吝啬指教,达到“忠告者贵虚受,虚受者贵忠告”,二者相规有成循环不已,使彼此皆能在学业上扬长避短共同进步。
由“相规以有成”可知,文洊已明确阐明交友对一个人的品德及其学术之影响与重要性,主张在学习中广交师友,而且要交天下非常之士,并非结党营私,所以慎选益友、远离损友自然成为学者不可或缺的课题。
三、结语
明末清初宋明理学的辉煌时期渐渐衰微,身为理学教育家的谢文洊,对于功利救世一直抱持着保留的态度,认为“经世”必须先由内在成德匡正心智开始,方可达到昌明的大同世界,其极力倡导切己力行,期望由教育讲学进而改造社会,强调实践个人道德的重要,主张在人伦生活中体现学问,我们从《程山十则》之思想内容,足以明显地看出来,从立定志向了解自己开始,注重躬行实践奠定治学基础,提出去恶习、砺节操、养本心的修养功夫,由读史、会讲鉴往知来,从不空谈抽象理论,透过个人反省,接纳他人谏言,不断地自我完善,其治学态度不仅只是对理学的发扬,亦是对儒学的传承,更是对清代切己实践的教育发展有着不可抹灭的功劳。
注释:
①魏禧《与谢约斋》:“愚谓会讲日当分三事:一讲学,今所已行是也;一论古,将史鉴中大事或可疑者,举相质问,设身古人之地,辨其得失之故;一议今,或己身有难处事,举以质人,求其是而行之,或见闻他人难处事,为之代求其是。于三者外,更交相规过……讲学则是非之理明,论古则得失之故辨,议今则当事不眩,规过则后事可惩。”收于《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页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