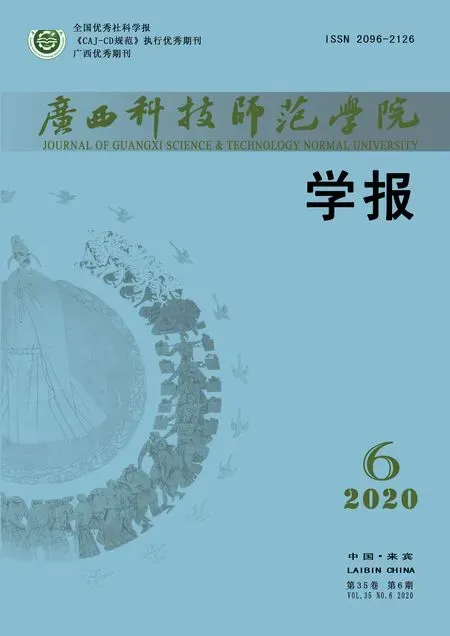烟雨湖湘与漏屋空床
——略说电影《半条棉被》的空间叙写
2020-03-14刘伟生赵思卓
刘伟生,赵思卓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株洲 412007)
潇湘电影集团出品的电影《半条棉被》,讲述的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红军借宿故事,重点表现红军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当前,对《半条棉被》的各类报道与影评大多停留在主题的宣讲,间或论及人物的塑造手法,罕见有涉及空间与意象方面的阐释。就艺术成就而言,电影《半条棉被》最出色的还是棉被意象的使用与相关空间的叙写。电影以影像为语言,它的能指本身是可感的客体,“影片能指的图像特点甚至可以赋予空间某种优先于时间的形式”[1]。《半条棉被》用具体物件作叙事线索,以红军长征为历史背景,将故事置放于湖湘烟雨与空床漏屋间,充分利用了电影的空间特性,富有湖湘地域特色。探究电影空间特质及其叙写策略,不失为理解《半条棉被》主题、人物、情节的切当方式。
一、晦明未定的湖湘烟雨
《半条棉被》给人的直观感受最突出的是山多、水多、雨多、雾多,整体色调趋于蓝色灰冷。电影一开场就是村民们为躲避官兵而冒雨从纤细的田间小路跑进幽隐山林的镜头。满屏都是纷纷扬扬的雨、迷迷茫茫的雾、兜兜转转的山、曲曲折折的路。这重重浓雾与霏霏淫雨笼罩着丛林、竹山、石岗,浸透着木桥、溪流、民居,淋漓成沼泽、泥潭、雨巷、漏屋。在这烟雨世界里活动的人有惊慌的民众、犹疑的屋主、自律而勇猛的战士等。伴随着风声雨声的有枪炮的轰隆声、房屋的倒塌声、人马的嘶叫声;掺和在泥桨与溪流里的有汗水、泪水与血水。这迷茫的天地与淋漓的世界既是宏大背景的拟喻,也是细切生活的写照;既切合地域景观的实际,也匹配长征电影的主题。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漫漫长征。10 月底,中央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从赣南安远、信丰间通过,11 月初,在汝城县通过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各部驻扎秀水、文明、沙洲、韩田等地,稍事休整。电影《半条棉被》中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家的故事就发生在1934 年10月至11月间湘南汝城县的沙洲村。长征不光要爬山涉水,还要躲避天上敌机的狂轰滥炸,突破地上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无数的艰难险阻,是人民军队的低谷期,真可谓“风雨潇潇”“风雨如晦”。
钱基博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2]张谓《长沙土风碑铭》称湖南“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3]。湘南汝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周边崇山峻岭,中杂丘冈盆地,境内河流树形辐射,分属湘江、珠江、赣江水系,有“鸡鸣三省,水注三江”之称。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年降水日平均达180多天,更具重山迭岭、卑湿瘴疠的地域特色。电影中烟雨湖湘的形象实有湘南气候地理的依据。
长征既是一部气势磅礴的历史史诗,也是特殊人物在特有环境中衍生出的特别故事,艺术家们在呈现这些故事时会用到这些自然意象。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就反复用到风雨烟雾的意象:“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住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电影《半条棉被》的立意,在于展示斗争形势的严峻,展示生存环境的危苦,展示红军与百姓血肉相连、鱼水情深,屡遭磨难才成就辉煌的卓绝历程。电影选取湘南飞天山、仙人村等故事发生地的自然景观,利用阴雨连绵的自然气候,再运用各种道具与电影镜头元素,制作出风雨如晦、遍地泥泞、迷雾重重的艰辛景况与迷茫影像。
毛泽东的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著称,其《七律·长征》诗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为了展示必胜的信心,电影《半条棉被》也在结尾处使用了云开雾散的镜头。从风雨如晦到雨过天晴,既象征着革命的背景,也预示着革命的未来。
二、冷暖自知的漏屋空床
电影《半条棉被》最重要的具象空间是村民徐解秀的居所。这居所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屋漏床空,电影最主要的情节也都发生在这漏屋空床里。漏屋、空床,是自古以来苦难家庭共有的景象。汉乐府《东门行》云:“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底层民众铤而走险,只因无衣无食。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写出了穷困者的艰苦辛酸:“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徐解秀家的贫穷状况其实是底层百姓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
家徒四壁的居所正是三位红军女战士与徐解秀一家鱼水情深故事的发生地。一个大雨滂沱的深秋之夜,三位红军女战士挤在一处屋檐下避雨,村民们都到山里躲“过兵”去了,徐解秀因为小孩生病,将自己反锁在家里。当她从门缝中仔细观察,看到屋外女红军虽然饥寒交迫,却纪律严明时,忍不住从门缝里将钥匙递给她们。这个情节用了剧中人物村民徐解秀的视角,门锁的打开其实也象征心结的打开。徐解秀通过自己的观察初步了解与接纳了这三位女红军。进得屋来,换成了女红军们的视角,除了家徒四壁外,她们一眼看到的是躺在床上的小孩与小孩身上的蓑衣,董秀云赶紧解下背包里的被子,给小孩盖上。接下来是更多的互动:徐解秀生火帮女战士烘衣服,拿出珍贵的盐巴给受伤的廖小湘消毒,取来地瓜给她们充饥。女战士们则拿出师长牺牲前都舍不得用的金鸡纳霜为徐解秀的小孩治病,甚至还爬上屋顶帮徐解秀家“捡漏”。这一切都伴随着视角的变换与心灵的沟通。除了以徐解秀的视角看红军与以女红军的视角看徐解秀家,女红军之间、徐解秀夫妻之间也有视角的切换与默默的交流;女红军自己不用好药而将其用在徐解秀小孩身上,是通过关切而理解的眼神进行交流的。徐解秀夫妇之间传递的则是对红军的信任与感激,并暗示可以让村民放心地回家。随着视角的切换,故事也在节段性地发展。村民们回家了,徐解秀与三位女红军也聊起了更多的家常。最后董秀云决定将被子送给徐解秀御寒,徐坚决不要,董执意将被子剪成两半,并许诺:等革命成功后,再送一条完整的新棉被。
居所是家的空间存在方式,鱼水情深的心灵交流就适合发生在家里。“因为家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家目睹了我们所受的羞辱和面临的困境,也看到了我们想展现给外人的形象。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家依然是我们的庇护所,因此我们在家里感到很安全,我们对家的感情最强烈。”[4]在村民徐解秀家里,徐解秀对红军由恐惧与躲避,到观察与认同,再到赞赏与感激,这是一个交互与渐进的过程。俗话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老百姓心中自有衡量标准,他们能感受到红军与既往兵匪的不同。由认同到付诸投桃报李般的行动是一个情感不断深化的过程,由个体到全体的信任则是这种鱼水深情逐渐普及的过程,正可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乎衣食的半条棉被也自然让人想起“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在这空床漏屋里,三位女红军的介入让村民徐解秀不仅心理有变化,思想也在不断进步。从“大人”的称呼、“求神问祖”的言谈到主动解放双脚便是进步的表现。
三、家国同在的洞房花烛
棉被是新婚的家当之一。董秀云的这床棉被很自然地引出她关于洞房花烛的记忆。电影中的洞房花烛并没有出现盖头红烛的景象,仅仅只是一纸休书和一床棉被。董秀云是韩玉山家的童养媳。韩玉山从军在外,多处负伤,不想耽误董秀云,在地方首领的见证下写了休书。他休书中写到:“因妻董氏进家门才十岁,年龄尚小,我多年没回家,不能照顾其左右,不能耽误董氏人生。天天在外打仗,不能侍奉双亲,家中琐事不能顾及,无奈特写休书一封,将董氏送回。日后听由娘家任意发落,男方老少均不干涉,为防生变,立字为据。”这其实是一个革命军人的牺牲与担当。但董秀云却说:“你能当红军,我也能。”她又把休书退回给韩玉山。然后,董秀云交待新婚鸳鸯棉被的来历:“这是我添的棉花,你娘绣的被面,这床被子就是一辈子,就是家。”此情此景就如《古诗十九首·客从远方来》所言:“文采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这就是董秀云的洞房记忆。由此家到彼家的洞房记忆既交待了棉被的由来,也起底了其红军的出身。“记忆非它,实际就只是对于一个其自体不是现实存在的形象的反复思念。”[5]“记忆所由产生的特定的物理环境,对人类的记忆具有广泛的影响。这影响几乎在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所表现。”[6]可见,记忆具有选择性与空间性。也许董秀云和韩玉山的新婚就是这么简单,但储存在记忆中的事件并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原生事件。
电影叙述的对象是经过精心加工过的故事而非原生事件。按法国人高概的说法:“只有现在是被经历的。过去与将来是视界,是从现在出发的视界。人们是根据现在来建立过去和投射将来的。一切都归于现在。历史之难写,正在于它与我们的现在有关,与我们现在看问题的方式以及投射将来的方式有关。只有一个时间,那就是现在。”[7]现在的主旋律电影也善于将宏大叙事与个人记相结合,取材于具体小故事的《半条棉被》便是用女性的进步与女性间的融洽来表达鱼水情深、家国同在的主题。董秀云由童养媳成为红军战士,她怀着孩子,并追寻丈夫韩玉山的足迹,开始漫漫长征。她在长征路上成长为担架排排长,一面抢救伤员,一面帮助百姓,关键的时候还要挺身而出带头执行阻击敌人的任务。廖小湘目睹师长被炸得粉碎,仍强忍悲痛修好电台,最后为保护电台而壮烈牺牲。胆小的王秋兰在最后关头勇毅地扬起红布以引开敌人。柔弱的女性们都走上了战场,并在火与血的历练中成长与牺牲。这更足以表现革命的艰辛与意义。
“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8]女性与家宅的关联最为密切,当女性与家宅都担负着安家定国、兼济天下的重任时,这说明电影中家宅空间的构建既是革命起点的标志,也是革命目标的喻示。当身负重伤的董秀云见到丈夫时,她只说了一句:“我们有孩子了”。这便是家的力量。
四、结语
空间不仅“确立了此地和他处,具有存在属性,通过空间能够表现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存在关系”[9],也参与叙事。空间叙事“以空间秩序为主导,以空间逻辑统辖作品,以空间或空间性作为叙事的重心。叙事通过空间形态、空间位置、空间顺序、空间关系、空间描写、空间的意义等得以组织,表达和完成”[10]。电影《半条棉被》是通过贯穿于烟雨湖湘、漏屋空床与洞房花烛等空间的棉被意象来叙述故事。棉被意象及其所赖以存在的空间与关联的人物也因此具有叙事功能。《半条棉被》故事由亲历者讲述,《经济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加以挖掘整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杨尚昆、聂荣臻等老红军传布,习近平更将其作为共产党爱护老百姓的典型故事予以讲解。根据这样真实的故事拍成的电影更具有诗史意义、传承意义与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