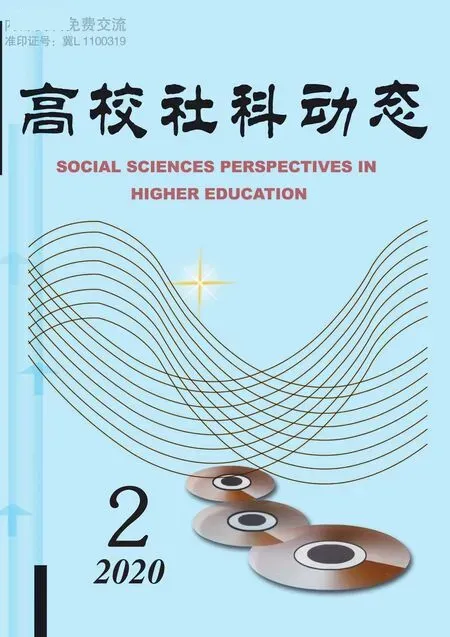近30年黄飞鸿电影研究综述
2020-03-14黄浩
黄 浩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00)
自上世纪40年代第一部黄飞鸿电影诞生至今,以黄飞鸿为主人公的电影已经多达百余部,创造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就有香港学者对黄飞鸿电影进行了零星的研究,研究成果多见诸于报端,或者被收录在香港各大电影节的论文集里。这个时期的黄飞鸿电影研究虽然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总的来说缺乏理论深度。90年代,黄飞鸿电影重新风靡全港,无论在影坛抑或学界都引起不小的轰动,香港学者开始对黄飞鸿电影进行系统的研究。1994年,吴昊撰写的《黄飞鸿之英雄三变》是90年代香港学者较早研究黄飞鸿电影的学术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视角独特、见解精辟,对后续研究产生较大影响[1]。接着,罗卡、列孚、卓伯棠、李焯桃等香港学者也纷纷投入到黄飞鸿电影的研究行列中。这些研究者多数是职业影评家或者电影从业者,他们的研究焦点往往集中于对人物角色的解读、电影拍摄的技巧以及作品风格等方面。进入21世纪,香港学界研究黄飞鸿电影的热情逐渐冷却,内地逐渐成为黄飞鸿电影的研究重镇。自2000年到2019年底,内地各大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关于黄飞鸿电影的单篇研究论文有近60篇,虽然不乏观点陈旧、滥竽充数的庸作,但也有一些目光灼灼、言之有理的力作。在知网上搜索可知,以黄飞鸿电影为研究专题的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5篇,涉及黄飞鸿电影话题的硕博论文难以统计。另外,有研究专著三部,还有一些学者的著作中辟有专门章节研究黄飞鸿电影。受到外国结构主义理论影响,内地学者除了致力于黄飞鸿形象研究外,更多把目光聚焦到黄飞鸿电影的叙事模式及其隐含的文化意蕴上,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近几年,姚朝文、林伟良等学者纷纷撰文论述黄飞鸿电影对当下岭南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对黄飞鸿电影文化价值的发掘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香港及内地学者对黄飞鸿电影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对如此繁杂庞大又鱼目混珠的研究文献,系统而细致的梳理、归纳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及文化价值三个方面入手,对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数十篇研究文献进行初步的梳理,为近三十年的黄飞鸿电影研究史画一个粗略的轮廓。
一、千面英雄:黄飞鸿形象的多重解读
黄飞鸿电影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影主创者们塑造了一个契合大众审美期待的黄飞鸿形象。黄飞鸿电影在香港绵延50年之久,可以分为50-60年代、70年代及90年代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黄飞鸿都呈现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他们可以是乡野武夫、捣蛋小子,也可以是侠骨仁心的一代宗师,这些不同的形象满足了不同年代观众的心理需求。正如学者袁道武所说:“电影作为一种文艺样式,某种角度说当然是社会存在的一个镜子,在这个文艺形式的‘镜像’中,电影肯定是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理想的一种反映。”[2]电影是反映社会的一面三棱镜,黄飞鸿银幕形象的演变折射出了香港社会心理的变迁。香港学者吴昊在《黄飞鸿之英雄三变》中最先关注到了黄飞鸿形象的“变”,他认为黄飞鸿形象之所以脱离历史真实而不断变化,主要是因为“电影偏爱传说”,而传说的演变则与社会心理息息相关[1]85。进而指出50-60年代的古典主义英雄十分适合当时香港社会的守旧民智;70年代的喜剧英雄形象充满了当时香港社会投机取巧的资本主义精神;而90年代的戏谑英雄则是席卷全球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银幕上的反映。吴昊这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处处隐藏着独到的见解与精辟的论断,他对不同阶段黄飞鸿形象的概括及原因的分析对后来的黄飞鸿电影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内地学者薛园媛在其硕士毕业论文《英雄的建构与消解:黄飞鸿电影流变》中继承了吴昊的观点,指出黄飞鸿形象的演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但她对黄飞鸿形象演变原因的分析较前人有所突破,认为50-60年代黄飞鸿的传统英雄形象是当时饱受天灾人祸的香港流民对“救世主”的呼唤与幻想;70年代的“功夫小子”反映香港经济的腾飞及本土意识的确立;而90年代的“夹缝英雄”与被嘲弄的“黄师傅”形象则体现了香港民众面对回归时迷茫、矛盾及焦虑的复杂情绪[3]。薛园媛以“他者”的视角对香港不同时代的社会心理做了全面、客观的剖析,避开了香港学者在分析黄飞鸿形象演变时的视角盲区,对黄飞鸿形象的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李新良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像代偿——透过〈黄飞鸿〉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变迁》中同样对黄飞鸿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近50年的黄飞鸿电影史中,黄飞鸿形象主要经历了从“侠”到“英雄”的演变。在他看来,“侠”与“英雄”是两个不可混淆的概念,“侠”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离、对“真我”的自由释放,而“英雄”则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迎合、对“真我”的压抑,黄飞鸿从“以武犯禁”的民间侠客演变成“心怀家国”的民族英雄实际反映了回归前夕的香港民众对“国家”的呼唤与认同[4]。李新良对“侠”与“英雄”的独到见解对黄飞鸿形象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忽略了港人文化心态变迁的复杂性,片面夸大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导致文章的论证较为单薄。自2000年到2019年的20年间,内地各大刊物上涉及黄飞鸿形象演变的论文多达十余篇,如袁道武《从“黄师父”到“阿飞小子” ——“ 黄飞鸿”系列电影中侠的精神流变史》(《西部广播电视》2016年第13期)、赵卫防《香港电影中的武侠历史人物黄飞鸿》(《艺术评论》2009年第4期)等,但除了上面详细讨论的几篇颇具特点外,其它的只是在论述方式上各有不同,鲜有独特的见解。
尽管银幕上黄飞鸿的形象一直在变,但“侠义精神”始终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侠”已经成为黄飞鸿形象的一个重要标签。陈默认为“侠”至少具有以下特征:在行为上,“侠”仗义疏财、除强扶弱;在品格上,“侠”信守诺言、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在理论上,“替天行道”是侠文化的精神支柱。他还指出:“侠”的概念具有时代性,近代的“侠”更多是指“反帝反封建”或“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英雄,成为“为国为民”“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侠之大者”。总之,“‘侠’成了永恒的精神象征,体现着民族文化及时代精神的某种本质”[5]44。他对徐克版黄飞鸿的“侠义精神”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徐克版黄飞鸿的成功,主要是因为该系列电影把黄飞鸿这一人物摆在中西方的政治、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摆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中考察,改变了旧作黄飞鸿的正与邪、即侠义与罪恶的冲突主题,实现了黄飞鸿形象从“传统侠客”到“侠之大者”的升华,从而使“新”的《黄飞鸿》电影及黄飞鸿这个人物有了新的审美意义[5]411。陈默对“侠”的精辟论断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研究,内地学者李新良在《集体无意识的影像代偿——透过〈黄飞鸿〉系列片看香港人的文化心态变迁》(《齐鲁艺苑》2009年第5期)中对“侠”与“英雄”不同内涵的辨析、任占涛在《狮舞与侠者的文化况味》(《焦作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中对武侠精神文化的阐发,其实都建立在陈默“传统侠客”“侠之大者”等观点上。孙彦冰在《剑啸江湖侠客梦》中对黄飞鸿的“侠义精神”则有新的见解,他把黄飞鸿称为“现代侠客”,与“传统侠客”相比,“现代侠客”有三个重要的特点:“行侠的初衷与身份的相悖”、“行侠过程中的自我反思与纠结”以及“‘行侠——离去’的圆形回归模式”[6]。在对第三个特点的论述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黄飞鸿行侠的结果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到后来仍避免不了“离去”的命运,而这种“离去”并非“传统侠客”的“飘逸离去”,而是充满宿命色彩的“被迫离去”。以黄飞鸿为代表的“现代侠客”演绎的实际上是一场命运悲剧。孙彦冰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使得黄飞鸿这个“现代侠客”形象具有了更加宽广的审美空间。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理想人格,黄飞鸿形象一直是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像诠注,学者们在讨论黄飞鸿的“侠义精神”时也往往离不开儒文化的思想框架。香港学者罗卡在《黄飞鸿家族:精神的繁衍》中指出黄飞鸿隐忍谦让、以德服人的品格体现了儒家智、仁、忠、勇等传统美德,因而可以称他为“儒侠”[1]5。国内学者郝莉洁深化了这一观点,她在《“黄飞鸿”电影儒家理论道德观》中指出,黄飞鸿形象不仅保留了儒家伦理道德观中的优良传统,还对儒家文化中禁锢人性的糟粕进行了反思,从而搭建起“中西方道德文化交流的桥梁”[7]。而崔腾在《徐克: 儒家思想的影像诠注——以〈黄飞鸿〉系列电影为中心》中更是直接把黄飞鸿称为“儒家思想的化身”[8]。儒家思想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重视人的社会责任感,提倡“达则兼济天下”,黄飞鸿作为“侠之大者”自然要负起“保家卫国”的历史重任,徐克版黄飞鸿电影塑造的正是一个心怀家国的“民族英雄”形象。因此,学者们对徐克版黄飞鸿的讨论也往往与“家国意识”“民族情怀”“身份认同”等宏大主题相关联。何启洲在《系列动作电影英雄形象创造研究——以“徐克版黄飞鸿”与“007”系列电影为例》中指出,徐克版黄飞鸿既有“体现中国人精气神的中国武术”,又有“凸显的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仁义与正直’的儒家精神”,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实现了“对香港社会‘国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一种召唤。”并进一步认为黄飞鸿英雄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国复兴路上的英雄期待”[9]。而盖琪在《从黄飞鸿到冷锋:中国当代影视英雄形象核心话语的嬗变》中则认为黄飞鸿这个身处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的风口浪尖上的民族英雄形象体现的是一种“弱国反思”[10]。这两者虽然意见不一,但都能自圆其说,都从某种程度上丰富了黄飞鸿形象的文化意蕴。王旭文、刘旸等学者更是另辟蹊径,他们分别从“他者”想象、黄飞鸿对手群体的演变等角度入手,间接地讨论黄飞鸿形象体现的民族主义精神,为类似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另外,孙昊明的《华语功夫武侠电影中“英雄”形象的文化身份书写》(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崔原赫的《试论香港电影中的英雄主义叙事风格》(2015年吉林艺术学院硕士论文)等文章都从“民族”“国家”的高度对黄飞鸿的英雄形象进行解读,可惜大多言谈泛泛,未见有出类拔萃之作。
二、类型淘宝:黄飞鸿电影的叙事模式
黄飞鸿电影多达百余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电影叙事系统。这个叙事系统是个性与共性的综合体,其“个性”自然不难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导演创作的黄飞鸿电影有不同的风格,每一部黄飞鸿电影中的人物、事件、背景等细节也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套在时间上跨越五十多年、数量上达到一百多部的超长人物系列电影,不同创作者在对前人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累积不少“文法”,这些“文法”在创作者与接受者的互动中逐渐演变成一套约定俗成的叙事规则,这也使得百余部黄飞鸿电影在叙事模式上有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共性”,成为特征显著的“类型电影”。约翰森·桑德斯指出:“类型电影是遵循某种叙事传统、惯例或模式,所制作出来的一部又一部具有某些共同特色而被归类在某种电影类型之下的电影片。”[11]可见,叙事模式的单一化与固定化是类型电影的主要特点。基于这一特点,强调内部结构统一性的结构主义理论自然成了学者们研究类型电影的理想工具。外国学者威廉·莱特就尝试利用斯特劳斯的神话叙事理论与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理论来分析西部类型电影,写了《六把枪与社会:西部片结构研究》,这部作品虽然毁誉参半,但是它的启发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国内学者陈默在其著作《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同样利用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理论对建国以来的武侠电影作了系统的类型分析,对后来武侠电影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有了前人的经验积累,研究者们便纷纷借用结构主义理论对黄飞鸿电影的叙事模式进行系统的梳理。国内学者姚朝文首先做出了尝试,他在其著作《黄飞鸿叙事的民俗诗学研究》中辟出近乎三分之一的篇幅对黄飞鸿电影叙事的文化母题进行分类研究。他注意到了黄飞鸿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基本情节单元,认为这些情节单元的不断重构形成了关于黄飞鸿叙事的一系列文化母题,对这些文化母题进行分类研究不但能管窥百余部黄飞鸿电影的全貌,还可以深化我们对黄飞鸿电影中所呈现的民间文化形态的把握[12]90。同时,他还注意到了黄飞鸿电影叙事的特殊性,指出由于庞大的黄飞鸿功夫叙事活动中涉及的许多反复呈现的最小情节单元不是单一或独立地加以表现,而常常呈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节单元之间的交叉或复合。因此,他创造性地把研究重心放在两个以上情节之间的复合效应,并将黄飞鸿系列叙事划分为“比武结缘:英雄+才女”、“擂台决胜:除暴+灭洋”等六组文化复合母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对每组母题的内容、表现形式进行详细描述的同时,还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从而克服了结构主义研究法机械、单调、无视文本审美价值的通病。但是也有美中不足之处,研究者在对某些母题进行分析时几乎完全脱离故事文本,如在对“武林门派:悬壶济世+以武止戈”的分析中就难觅具体的故事情节,全然是没有根底的长篇大论,这种脱离故事情节的母题分析颇有舍本逐末之嫌。香港学者刘大木在其论文《类型淘宝——黄飞鸿电影》中也对黄飞鸿电影的叙事模式作了一番探讨。作为一个专业的电影编剧,他曾参与多部武侠电影的制作,对该类电影的叙事套路烂熟于心,他指出“中国与功夫电影的结构与神话的结构接近,有颇稳定的模式,甚至公式化,所以用结构主义和民间故事形态学来研究武侠和功夫文类,虽然有点过时,但也不失为一个适合的方向。”[13]为了证实这个观点,他借用斯特劳斯的神话叙事概念与普洛普的功能概念对黄飞鸿电影的故事序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概括分析。他首先对《黄飞鸿天后庙进香》《黄飞鸿义贯彩虹桥》及《黄飞鸿大闹佛山》三部电影进行形态分析,在此基础上,理出了“公众地方结怨→错摸→邂逅美女→情同意合→英雄救美→教训徒儿→误会→仇恨益深→再斗奸人→邀高手相助→汇点贼巢→结局”等三条情节序列,通过对三条序列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了黄飞鸿电影主要的叙事功能结构:“公众地方结怨、教训徒儿、错摸/调包/易服、危机加深”。刘大木对黄飞鸿电影的分析深入到了每一个叙事构件,揭露了该类电影情节结构的组装规律,用简洁的故事序列实现了对百余部电影的系统概括,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一次成功尝试。但不能忽略的是,结构主义理论有其双面性,如果用力过猛,其负面作用往往会被无限放大,刘大木很大程度上就犯了这个毛病:当他在对黄飞鸿电影进行外科手术般精细的切割时,隐藏在电影肌理中的审美意蕴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此外,各大期刊杂志上涉及到黄飞鸿电影叙事分析的研究文献至少还有5篇以上,但大多都是平庸之作,有些研究者甚至还没有弄清楚结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就仓促动笔,最后得出的成果自然是一塌糊涂,让人难以卒读。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论证详实、观点鲜明的出彩之作。如甘圆圆在论文《〈黄飞鸿〉系列电影的模式化与单一化》中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使用就显得十分老练,而且在方法上较前人也有所突破。她首先利用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的平衡公式法对影片主要的叙事脉络进行初步的梳理,接着用普洛普的角色结构理论分析电影中四种固定的角色模式,最后再用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法分析人物类型、场景环境和表演这三者之间的关系[14]。甘圆圆由表及里、由浅到深地对黄飞鸿电影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得出的成果颇具说服力,而且她对“平衡公式法”“角色结构理论”“二元对立法”的应用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在理论的拓展上也可以说有一定的贡献。袁道武的硕士论文《徐克“黄飞鸿”电影中现代性事物的符号学研究》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使用更是别开生面。他将黄飞鸿电影中所出现的“现代性事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结构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符号的归类,结合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结构主义、普洛普的形式主义叙事方法,探究电影中现代性事物的叙事功能及其意义生成的途径[15]。他从“现代性事物”入手对黄飞鸿电影的故事肌理进行“毛细血管式”的探究,从某种程度上修补了结构主义分析流于空洞和宽泛的弊病,是一次十分有价值的尝试。但是,他似乎更侧重于讨论“现代性事物”的象征意义与审美价值,而无意对其叙事功能作过多的关注,因此,这篇文章对研究黄飞鸿电影叙事模式所产生的启发意义也相对有限。
三、价值重估:黄飞鸿电影的文化价值
上世纪香港地区生产的百余部黄飞鸿电影为后人留下了一座珍贵的文化宝库,无论哪个年代的学者都能从中读到反映时代脉搏的内容,得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启示。近十年来,随着“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软实力”等关键词成为国内文化研究的主流,对黄飞鸿电影文化价值的关注也逐渐成长为学界研究的新领域。
与其他电影相比较,黄飞鸿系列电影有一个极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电影中带有浓郁的岭南民俗风情。著名武侠片导演张彻评价黄飞鸿电影“富有广东街坊风味”;香港电影研究者钟宝贤更是直接把黄飞鸿电影称为“港粤色彩南方电影的代表”[16]。黄飞鸿电影对岭南文化的记录、传承与传播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何海巍在《香港电影与岭南地域文化传播研究》中讨论了以黄飞鸿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对岭南文化的传承价值,认为香港电影通过对岭南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提升自身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推动岭南文化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17]。王琴在《岭南文化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传播》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对黄飞鸿电影中出现的西关大屋、粤曲、功夫茶、醒狮等岭南民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指出这些岭南民俗元素不但保留了特定年代的文化记忆,也有力地促进了岭南文化的传播[18]。何海巍、王琴对黄飞鸿电影与岭南文化互动关系的关注颇具启发性,但由于这两篇文章研究的整体对象是“香港电影”,黄飞鸿电影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所以他们对黄飞鸿电影与岭南文化关系的讨论只是点到为止。真正对这个话题给予高度重视的是姚朝文教授,他在《黄飞鸿叙事的民俗诗学研究》中充分认识到了黄飞鸿电影中岭南民俗元素的重要价值。他认为,在黄飞鸿电影里呈现出来的岭南民俗尽管是经过人为加工后的“影视民俗”,但它保留了当时的民间工艺制作过程,或者记录了民间叙事的一些程式、母题,展现了某些生活民俗是怎样演化成电影里的“仿民俗”的转换关键环节。观众通过或真实或想象的方式,借用这些影视画面里的民俗,创造出似曾相识的风物、情景,可以强化生活真实感,建立和保护人类生活与艺术的多样性,增强社会族群的认同感、凝聚力和文化创造活动的承续性[12]259。姚朝文借用“影视民俗”的相关理论对黄飞鸿电影中“人工民俗”的文化价值作了充分的发掘,无论对黄飞鸿电影的研究、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还是“影视民俗学”学科理论的建设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005年到2019年的十五年间,姚朝文教授先后出版了与黄飞鸿电影研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著作五部,学术论文近二十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不仅讨论了黄飞鸿电影之于传统文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也注意到了它对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黄飞鸿电影蕴含的品牌价值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为佛山乃至全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在2009年发表的《黄飞鸿影视民俗研究的定位与策略》中对黄飞鸿电影所蕴含的品牌价值作了奠基性的论述,指出包括电影在内的黄飞鸿民俗叙事活动是“一个持续百年于今尤烈的文化产业资源宝库!”[19]这一篇带有纲领性质的文章,为他后续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在2010年发表的《黄飞鸿功夫电影海外传播路线及文化影响力分析》一文中,他对国内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贫弱的文化原创力之间的巨大反差提出了批评,进一步强调了发挥以黄飞鸿为代表的中国功夫电影品牌价值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认为中华武功文化“应该上升为地区乃至于国家级的文化产业整体战略,扩大中国在世界文化艺术市场的份额,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来之不易的地位。”[20]在2013年发表的《创建“岭南功夫影视城”的构想》中,他更是直接为实现黄飞鸿电影的品牌价值出谋划策,在论证创建“岭南功夫影视城”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国际权威的世界功夫影视文化产业论坛”等“三大建议”及“引进国际级战略投资者”等“三大对策”[21]。无论姚朝文教授的构想最后是否能付诸行动,在国内文化产业停滞不前的今天,他对黄飞鸿电影品牌价值的挖掘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点外,学者们对黄飞鸿电影文化价值的考察还涉及到其他多个方面。如韩春萌的《论历史名人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彰显》(《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讨论了黄飞鸿形象在当下发挥的文化价值,并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和文化传承有机结合”等方面对历史名人文化价值的发掘提出了可行的建议;谢明川的《黄飞鸿与醒狮及其21世纪的动态展望》(《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关注了黄飞鸿电影对当下醒狮活动的推动作用,认为“武舞结合”的黄飞鸿电影不仅提高了“南派醒狮”的影响力,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而林伟良的《黄飞鸿武医结合的需求背景与当代发展》(《搏击》2012年第4期)则探讨了黄飞鸿电影对传承与发展黄飞鸿武医之术的积极意义……此外,起码还有十余篇论文涉及黄飞鸿电影的文化价值,但是所提出的观点都没有太多的现实意义,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四、结语
黄飞鸿电影研究是一个十分丰富的话题,近三十年来,学界对它的研究主要从其人物形象、叙事模式及文化价值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成果多达数十篇,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虽然这些研究成果良莠不齐,多有跟风抄袭之作,但也足以说明黄飞鸿电影研究在大众文化和影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黄飞鸿电影的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低潮,但内地学者对其的研究热情却在与日俱增,上世纪港产的百余部黄飞鸿电影成为供后人吸取营养的艺术宝库,学者们总能从中回味到新的内容,得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启示。2019年,中央正式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成为时代发展的热点话题。大湾区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大湾区文化认同的形成中,电影担负着重要的文化责任。文化记忆是身份认同与国族认同的基石,扎根于岭南传统文化的黄飞鸿电影向来深受粤港澳三地民众的喜爱,成为他们表达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如何从港产的百余部黄飞鸿电影中吸取成功的经验,为当下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出谋献策,这应该会成为黄飞鸿电影研究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