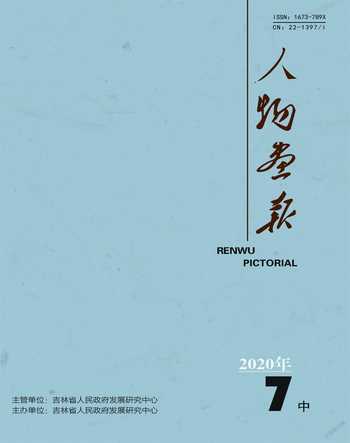论有意味的形式
2020-03-14赵武颖 吕宇星
赵武颖 吕宇星
摘 要:谈论艺术的本质问题,不可避免要谈到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章从艺术的本质研究出发,探讨“有意味的形式”的内涵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论;有意味;形式
关于艺术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观点,一件艺术作品的形成,离不开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容对形式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内容可以解释为作品的主题或思想,没有内容的形式反映在作品上是空洞的;而形式则服务于内容,是内容的载体和表达方式。对于艺术创作来说,艺术形式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有创意的形式会使创作内容更出彩。内容随着主体的不同,艺术家对事物认知的不同以及时代的变化等因素也更加变化多端,形式也会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一幅好的作品要想拥有一个好的内容与形式,就需要融入创作者的创造力与思想情感,这样的艺术作品才拥有灵魂,艺术形式才能更加灵动。正所谓“气韵生动”,艺术作品正是因为有了有灵魂的气韵风格,才拥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克莱夫·贝尔认为美是“有意味的形式”,他提出“唤起我们神秘情感的一切审美对象中普遍的而又是他们特有的性质”这一性质即“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在此指的是艺术作品的线条、色彩、构成形式等所构成的纯粹的形式,那么“有意味的形式”就单纯等于“有内容的形式吗”?并不尽然。孩童的画作也是有内容的形式,孩童用自己童稚的笔法画出自己所认知的世界,想表达的事物,这也是“有内容的形式”,来源于孩童对客观世界的模仿,但并不等同于“有意味的形式”。而我们在此谈论的“意味”则指的是不同于日常审美的模仿表达,“‘意味’是纯粹的审美情感,‘意’多指抽象的观念或哲理”,是一个完全形式化的抽象意义,一定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模仿与再现,它完全来源于创作者主观的审美情感,贝尔提出的美学观念,把“意味”的定义与作品的一般情感表达的审美情趣割裂对立开来。认为有“意味”的美是不带有一丝功利性的、完全超凡脱俗的。例如原研哉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强调“空”和“白”,很少有华丽的形式,仅用几根线条、几个色块便让人们感受到作品中流露的禅意和美感,激起人们在作品中感受到的特殊情趣,这是一种超脱从自然事物中感受到的美和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享受之外的精神共鸣。
将形式论放到作品创作中来谈,“没有形式的创作,或者说形式不好,其作品也就不存在内在价值,更不可能具备相应的内涵与精神,从而产生不到思想上的共鸣。”丹纳认为艺术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艺术品从属的第一主体就是它的创作者,自古以来,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有其鲜明的特点,米芾的烟雾缭绕的“米氏云山”、徐渭泼辣洒脱的大刀阔斧、黄荃的“凡所操笔,皆迫与真”,徐熙的“以墨为格,杂彩副之”等都在充分说明这一点,这些风格上的差异并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个性差距,还在于艺术家所处的环境、时代审美等因素,所有的关键词都落到一点——“我”。
“艺术创作是一个自我发现、此在关照和界限突破的过程。换句话说,艺术家要尝试着学会认识自己,注重艺术创作中内心的真实感受,同时,又要不受技法、材料、门类、理念等因素的束缚,进行自由的创作。”艺术创作中模仿现实、注视历史是必不可少的部分,但是艺术的主题是人,是作者,正是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多重情绪的复杂体,人的头脑不仅可以储存知识,复制现实,最重要的是拥有创造力,这也是人区别动物,可以改造世界、站立于世上的根本原因。
一般人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看不到艺术家的自我,看到的是艺术家描绘的内容,自我角色游离在画面之外。但是经过推敲就会发现,好的艺术家正是在看似没有自我的形式中,通过作品折射出自我情感的升华和自我认识的笃定。中国绘画艺术在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作者笔下有不同呈现,在西方美术史上也有同样表现,文艺复兴时期高举“自由解放人文”的旗帜,在这一大背景下艺术家们一反中世纪的黑暗压抑,开始回归希腊罗马文明,这一时期达芬奇理性科学的完美交融、米开朗琪罗激荡宏伟的英雄气质……这些反映都来源于特定时代,扎根于作者本身,尤其到了印象主义时期,艺术家们更强调个性的自我表达,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的出现也正表达了艺术家们思想个性的外化。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在艺术表达中,就是艺术家在界定的环境内尽全力达到最高点的“我思”,所以创作了艺术作品中的“我在”。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的精神、经历、思想、美感、个性的总的集合,反映在具体的物质实物表达,而艺术创作如何永葆青春,紧跟时代,要求的除了扎根在“我”,还要求不断的“超我”,艺术是有限定的,限定的时代,限定的个人审美,而一个好的艺术家要做到的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不断学习未知,不断突破自己的知识与审美的边界。“艺术”的反义词是“平庸”,“平庸”来源于创作思想的溃泛,来源于创作模式的固化,失去了无限创作的可能性,作品就不再有生命与动人的审美情感。
作品中没有“我”,但站在作品前的我,把汲取到的生活百像,把心中的现实写照以自己创作的自由形式付诸到作品之中,作品于是成了“我”。
参考文献:
[1]克莱夫·贝尔:《艺术论》
[2]常熳:《“有意味的形式”与中国古典“意象”的比较研究》,載《大众文艺》,550025
[3]文斯:《探析绘画的“形式美”与“有意味的形式”》
[4]魏建明:《艺术创作漫谈》,载《艺术新视界》,2019.12
作者简介:赵武颖(1996.7),女,汉族,籍贯:河北邯郸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艺术设计,研究方向:平面设计;
吕宇星(1996.9),女,汉族,籍贯:山西吕梁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艺术设计,研究方向:平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