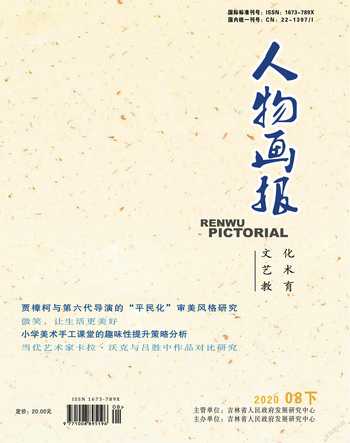滴不尽相思血泪,开不完春柳春花
2020-03-14浦卓
茅盾与张爱玲刻画的女性主要生活在都市之中,她们的爱情是战乱都市里的爱情,茅盾笔下的女性富有活力,奔放,叛逆且自我,具有超前的爱情观。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则如凌霄花,终其一生都在攀附着男人,在苦海中沉沦。而许地山,沈从文描摹的女性大多不生活在都市之中,许地山笔下的女性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但她们能够以一种坚韧而平静的态度来反抗着,沉默却坚定地追求着自主的爱情。而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则较为幸运,她们生活在边陲,甚少受到封建礼俗的压抑,她们的爱情完全发乎于天然,成为诠释生命状态的一个重要方面。
茅盾是由“五四”孕育的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作家,他广泛地吸收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同时又兼备古典主义的熏陶。因此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典型的代表东方文化的女性,例如《幻灭》中的章静,性格单纯,温婉怯懦,多愁善感,轻信他人,在理想与幻灭之中沉浮。茅盾将传统的理想化的爱情婚恋观放置于复杂的乱世中考量,也即是考量传统的、恬静和谐的女性品质与风云变幻的革命浪潮将会发生怎样的碰撞。而第二类女性形象则是富有西方特色的“新人”,她们从外表到内在,从气质到观念,都反抗着封建传统女性婚恋观。我认为她们的爱情观下有三点性格内核作为支撑,一是叛逆,二是自我意识,三是主动。以《动摇》中的孙舞阳为例,她周旋于多名男子的暧昧关系中,却提出“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有时我也不免——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且不评论这样的观念是否合乎道德,这种敢于反抗封建传统对于女性束缚的叛逆精神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这种叛逆之中,又包含着强烈的自我意识,肯定了女性性欲的合理性。主动性是深层次的性格内核,作家常常将这两类女子放在一起进行描写,正体现了匠心之独运。如将章静与慧对比描写,将孙舞阳与陆梅丽进行对比。章静与陆梅丽虽有着古典女性的懦弱被动,却受到了一定的新思想的影响,有着追求自由爱情的美好愿望,但却缺乏行动力,甘心处于被动地位。在追求理想时,她们同样不敢主动,而是等待着适应社会。可以说,茅盾的女性刻画其实是服务于革命精神的探索的,新派的女性充满活力,叛逆不羁,作者对她们加以肯定的态度。作者在书写着胸中对于革命精神的一团火,也在发出自己的疑问,旧派女性该何去何从,新派女性是否能够在革命事业中大放异彩呢?
与茅盾以革命,以政治为导向来书写女性不同的是,不问政事的张爱玲笔下悲情的女子。张爱玲的出身以及坎坷遭遇决定了她难以写出茅盾笔下那样奔放独立的女子。葛薇龙一旦走进那幢花园洋房,便开始走向不可逆的悲剧。在葛的身上,体现了一个普通女子在物欲主义下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的深渊。葛薇龙,没有浓厚的家庭背景,在各方势力的压迫下,物质和精神世界同样的匮乏,人生体验的空白导致她们急于抓住什么来寄托自己的生命,女性自身力量的薄弱更加剧了情欲的支配地位。同样是张扬情欲,孙舞阳是因為勇敢,而葛薇龙是因为怯懦。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孙舞阳,张素素,章秋柳这样的女性,她们叛逆,主动的底气出自何处?在时代的滚滚车轮下,她们最终的结局是否会和葛薇龙如出一辙呢?
与茅盾,张爱玲笔下或波澜壮阔,或苍凉哀愁的笔调不同。沈从文和许地山的文学世界,或是原始的边陲小镇,民风淳朴,风光秀丽,富有神话色彩。或充满了禅意,有一种永恒而奇幻的宗教色彩,流露出一种超然的智慧。这样的氛围也催生出他们笔下独特而迷人的女性形象。许地山笔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坚韧的毅力,反抗封建思想束缚的勇气,以及面对命运无常的超然。《命命鸟》中的敏明,不顾父母对她爱情的阻挠,受到梦境的点化以后,以平静祥和地走入水中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理想。《枯杨生花》中的老妇人云姑,多年以后见到年轻时的恋人,回忆起年轻时的甜蜜却心酸的往事,两人决定重修旧好,作者肯定了云姑即使年老却勇于寻回爱情,反抗封建婚姻爱情制度的难能可贵。她们在面对封建礼教的压迫时,没有表现出极端激烈的反抗,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承受之,甚至对于迫害她们的人包括她们的丈夫,都能以一种平和,谅解的视角来看待。但是另一方面,她们仍然可以坚守住自己,没有像章静,或是曹七巧,葛薇龙那样迷失在乱世的洪流中甚至扭曲了自我。当爱情缺失的时候,“云姑们”,“尚洁们”能够安守自我,当爱情降临时,她们又敢于接受。这恰恰体现了许地山充满佛教思想的蜘蛛哲学在爱情观上的演绎。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则比上述的都更加幸运。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三三每天“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日子”。她们是沈从文对于原始纯粹,古朴自然,没有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浸染的美的象征。她们无需反抗封建礼教,无需抵御都市的物欲横流。她们的爱情是纯粹的,是发乎于天性的,不用像白流苏一般精打细算,时刻进行利益的博弈。她们对待爱情是坦荡的,媚金没有等到豹子,毅然决然自杀。自由的爱情被全体族民歌颂,纪念。她们对待爱情是坚贞的,翠翠日复一日地等待着傩送,“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翠翠等待着傩送,不是心急如焚地等待,不是等待戈多式的等待,这样一种爱情的等待,即使泛着忧愁,也是混合着绿水青山,鸟唱虫鸣的秀丽优美的忧愁。沈从文笔下的爱情,正体现了他营造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并以这种方式去批判现代都市文明对人的异化和扭曲。
由上观之,作家的人生遭遇不同,思想认识不同,其笔下的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也就不同。作家常常将自己对于人生的思考以及疑问投射到其创作的女性身上,无论是都市女性,还是边陲乡野女性,当中多元化的爱情观都可以成为研究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学取向的标尺。甚至对于当今时代的爱情观塑造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浦卓(2000.03-)女,江西省南昌人,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昌东镇紫阳大道99号江西师范大学,小学教育(语文方向)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