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与汉魏经籍阐释方法
2020-03-12袁晶
袁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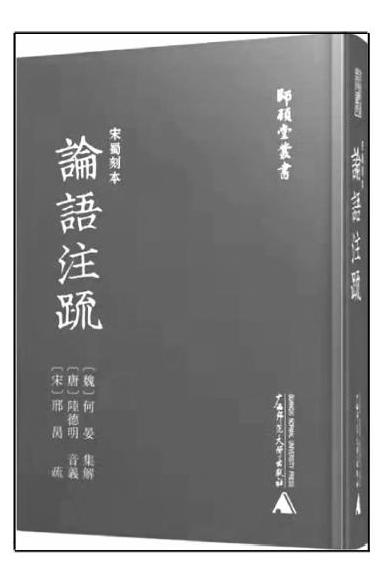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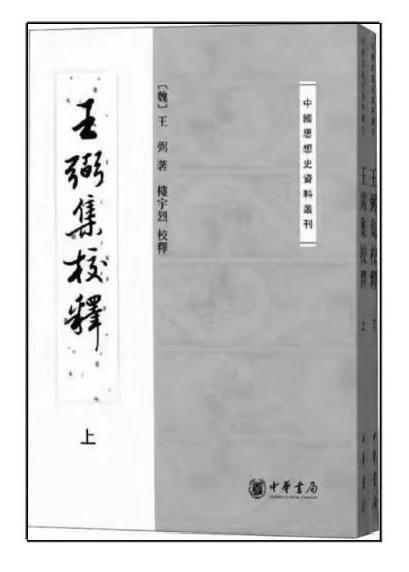
据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载,王肃于曹魏初注《论语》,其注本在曹魏被立于学官,王(肃)说与郑(玄)说异,前者开魏晋之风,后者承汉代传统。魏晋时《论语》学可称得上是显学,记载在案的《论语》学著作有84部之多。[1]而彼时之《论语》学与《易》《老》《庄》有较大关联,此种关联既体现在注解内容上,也体现在阐释方法上。经过魏初名理学的发展以及何晏、王弼等人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汉代经学的改易,“言意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新方法,主要包括辨名析理的逻辑分析法,“意会,,“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方法。魏晋经籍阐释方法与汉代较为明显的差别即是运用了“寄言出意”“得意忘言”之法。而此种思维方法又与魏初何晏、王弼等人对“本末”“有无”的讨论密切相关。
一、汉魏《论语》注解内容之差别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有:“魏礼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论语集解》由何晏总领而集,且如其《论语序》中所言:“前世传受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2]所谓“前世传受师说,虽有异同”盖指西汉时论语有古、鲁、齐三本,鲁人所学为《鲁论》,齐人所学为《齐论》,从孔壁出的为《古论》。后张禹将三者合而为一,去《齐论》中《问王》《知道》两篇,从《鲁论》二十篇而有《张侯论》。后马融、荀爽、郑玄、王肃、王弼、荀顗、何晏等人皆大体为三家合派,注解逐渐由较为古朴的随文释义向义理化转变。梁有《古文论语》十卷,为郑玄所注,而王肃、虞翻、谯周等人之注本皆已亡佚,至正始有《论语集解》为何晏所集。
从何晏的《论语序》中可以看出,虽是集诸家之说,但在材料的选择上是有所损益的,即所谓“集诸家之善”,“善”涉及选择的标准问题,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个人化特色;再者对前人注解也并非完全按照原样辑录,而是有所改易。改易可被视为创造的过程,承载了改易者的思想旨趣与目的,故而一般来讲,历代学者基本都将《论语集解》视为何晏思想的反映。[3]后南北朝随儒、佛讲经,说经之风而义疏亦盛,有皇侃《论语义疏》“引其它通儒注释三十三家……集汉学、玄学、佛学于一体”。[4]
《隋书·经籍志》载“《论语》十卷,郑玄注。梁有《古文论语》十卷,郑玄注;又王肃、虞翻、谯周等注《论语》各十卷,亡。《论语》九卷,郑玄注,晋散骑常侍虞喜赞”[5]。朱尊彝《经义考》中有郑玄《论语注》《古文论语注》和《论语释义》三本,单承彬《论语源流考述》认为前二者为同一注本。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言“郑注《论语》,以其篇章言,则为《鲁论》,以其字句言,实同孔本”。何晏《论语集解》中亦辑郑玄注,但因其集解过程中有所取舍及改易,故恐与郑注原貌有别。隋时何注与郑注并行,唐时独尊郑注,南宋时郑注基本亡佚。本文所引郑注皆本于王素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的《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郑玄注经不同于前人者在于其兼采今文、古文,如其注《易》用费氏古文,又以六爻与十二辰相配合说《易》。对此,皮锡瑞总结曰:“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采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宏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于是……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6]143其注能盛于一时,主要在于去除了汉代注经之繁杂,而兼采今、古文之优点。郑玄注《论语》多采朴实训释之文献考据法,考释字词音、义,交代春秋史实与《论语》中出现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对名物、典制等相关知识进行解释,在很多地方也不乏今文经学之神学特质。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但这些理解一般皆无过度阐释,多只附随文意而发。如其释“夫子之道,中(忠)恕而已意(矣)”(《里仁》)一句,日:“告仁(人)以善道,曰中(忠)。己所不欲,物(勿)施于仁(人),日恕乎(也)。”[7]35虽是阐释性理解,但皆在《论语》基本思想的框架内进行阐发,与文字贴合紧密。
据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记载,何晏于正始六年(245)主编完成《论语集解》。何注流行于魏晋时代及南北朝时的江左。南北朝时“北学”仍尚郑注。汤用彤认为经学的南北之分同时也是学术守旧和趋新两种趋势之分。守旧一派的思想承袭汉人的宇宙论,以阴阳五行间架为本;趋新一派则从老、庄以无为本的思想出发,在宇宙、人生和学理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到晋末之际,南北新旧之学的分别已十分明显,“因此南朝北朝的名称,不仅是属于历史上政治的区划,也成为思想上的分野了。”[8]北学以郑玄为宗,延续汉代章句之学,上承汉学;南学以何晏、王弼、孔安国、杜预为尚,注重会通其意,多玄虚臆解之谈。
王弼撰《論语释疑》,所著时间不可考。《隋书·经籍志》载三卷,《唐书·艺文志》载两卷,《经典释文序录》载三卷,已亡佚,后《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9]何晏注与王弼释疑在宗旨上是相同的,《三国志·魏书·钟会传》引何劭的《王弼传》:“于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10]二人注经皆以“以无为本”为纲,“得意忘言”为法,略于具体之物象、言论而探寻普遍之义理与言外之意。如《为政》篇:“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汉儒所注皆随文释义,孔安国、马融皆说明此段大意在于“文质礼变”,郑玄先解释了制度变迁之迹是否可知,后又言“所损益可知者,据时篇目皆在可校数也。”[7]14而何晏则解为“物类相召,世数相生,其变有常,故可预知”[2]24,此种解释从较为具体的制度变迁之事,普遍化至事物在时间序列中的因袭变化之理,可谓略于文字字面之意而求言外之旨。又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一则,唐写本《论语》郑注为“孔子疾世,故发此言,子路以为信。从行,故曰好口,无所取材之。为前既言,虽中悔之,故绝之以此口。”[7]42而何晏的《论语集解》中引郑注与此不同:郑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者,无所取于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戏之耳。”[2]57以整体注解特色推测,何本所引疑并非郑注,故“不解微言”之说恐是何晏所解。
又如“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矣。”,(《公冶长》)郑玄注日:“文章渭(谓)艺之义里(理)也。性,谓仁(人)受血气以生,贤愚吉凶。天道,谓七政变动之占。”此处是以汉易象数的思路来解读性与天道,将其与吉凶祸福、占卜相术结合起来。汉儒注经多用《易》义,但大都是汉易路数,尚灾异、吉凶之论断,而何晏注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2]61何晏此为引《周易》《老子》释《论语》,其以元亨日新之道为天道,元为始,亨为通。《周易》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坤卦卦辞为“元亨,利扎马之贞”,此谓天地配合而开创万物,使其亨通。《易传·系辞》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此“天道”为《周易》化生万物之道,同时也是《老子》之道,以无为本,隐而无名,故深微而不可得而闻。天道之不可言说一语虽出自《论语》,但此处所谓之“天道”乃综合儒、道之天道。何晏之注虽引《易》作为诠释依据,但和郑玄相比,已基本放弃了占筮、灾异之说,转而探求形而上之义理。汉代《论语》注的神学化逐渐向魏晋的《老》《庄》《易》化转变。此种转变所依赖的方法便是突破言、象,而主“得意忘言”。
二、“言意之辨”与汉魏经籍阐释方法
汉代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文经学与政治结合紧密,尚以阴阳五行、灾异之说解经,如董仲舒治《春秋》,以公羊学灾异之变,推至阴阳五行,探象纬以明人事,此种“假经设谊,依托象类”的注经方式容易出现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现象;又有谶纬神学的介人,使得解经趋于神秘化。《汉书·李寻传赞》“或不免乎‘億则屡中”,颜师古注曰:“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时有中者耳,非必道术皆通明也。”[11]儒学神学化倾向于将社会人生的一切现象皆纳人神学化的逻辑框架中加以解释,而失却了文本本来的意义。但其从根本上是为了论证天、人与社会政治之关系,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建构为目的的阐释行为。古文经学则多随文释义,注重训话,较为朴实;严守师法、家法,师法溯其源,家法衍其流。师法、家法之严苛导致习经与注经者需以祖述继承前学为主,不能随意发挥。虽然期间也有松动者,但此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极不可取的。严格的师法、家法也导致了士人解经、注经之繁杂与刻板,以文字及先学之言为重,在意义的阐释上很难有发挥的空间。汉魏之际,注重大义与训话的古文经学在荆州被合法立于官学,官方经学由日趋繁复和妖妄的今文经学变为古文经学,学风为之一变,如《刘镇南碑》所言:“深憨末学,远本离质,乃令诸儒,改定五经章句,删划浮辞,芟除繁重。赞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机者多。”[12]至晋代,所立博士无一为汉十四博士所传,今文师法基本不传。
汉代章句之学主随文释义,朴实说经,魏晋说经则尚会通其义而不拘泥文字的“寄言出意”之法,要言不烦,自抒己意,经典之言与作者之志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注者想借以呈现的思想旨趣。故而其注疏虽皆采前人注解而集之,但多有径庭取舍,而附以己意。皮锡瑞对此种解经方式持批评态度,认为其“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6]159此说是立足于经学传承的连续性来讲的,然而魏晋时社会学术思潮产生了变化,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对魏晋士人调和老庄思想,以及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世说新语·文学》载:“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13]王弼讲“以无为本”来源于老子之学,道之本体为无,无乃无形无象,无形无象故而不可名言,所以道隐且无名。名言为有,是末。但在以无为本之外,王弼还强调“崇本举末”,即作为本之无与作为末之有皆不可轻慢,也就是说名言虽非道之本体,但也是极为重要的,再具体点说即是,圣人之名言与老庄之体无皆不可偏废。他援用老庄思想来注解儒经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想要调和儒道。汉人说经也讲“微言大义”,不乏至约至精之论,但其笃守师说,重视经典言說本身的价值;而魏晋玄学之士所尚之约言只是借经书与注经之言来表达义理,言只是作为通向玄理的路径存在,最终目的在于“寄言出意”,故而二者并非只是注经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根本旨趣之差异。
曹魏荀粲言“六籍圣人之糠秕”,他是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为依据,否定了六籍,认为其乃圣人之糠秕。他对经籍表意能力局限性的强调在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之后本体论基础上言意关系的讨论和寄言出意的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何晏《论语集解》“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2]61,王弼《论语释疑》有“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中道,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淳淳者哉?”[14]何、王二人所言“天”与“天道”并非五行术数之天,而是作为宇宙本体之天,其轻言的思路与荀粲一脉相承却有所深化。王弼指出了立言垂教和寄旨传辞的弊端,而修本废言是天道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荀粲否定的是圣人之典籍,而非圣人之思想,而何晏、王弼并未否定言本身,而是将其视为达到意的工具。荀粲的观点虽具有开创性,但彻底否定六经对当时思想发展来讲并无实质意义,何晏、王弼等人以“得意忘言”为解经之基本方法来融合儒经与老庄,以传统资源为基础,催生出新的阐释方法和阐释结果,将时代需求带人了对历史文本的阐释之中,发掘了经典内部新的可能性。
儒家典籍在汉代由于为中央集权意识形态确立合法性的需要而被董仲舒等人尊为圣典。约埃尔·魏因斯海默在《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到经典与圣典的区别。经典是单数的,特点在于“一分为众”,也就是说其具有众多的可能性,且经典并不存在排他性,依靠其特殊的品质、品格和价值获得认可,且这些品质、品格和价值与个人或特定群体的直接目的无关。而圣典是复数的,特点在于“众合为一”,所谓的“一”指目的和宗旨上的一致性,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圣典性并不强调其内在的品质和特征,而主要指发生在其身上的事件之结果,此一事件是指圣典化的过程,“圣典的要求或是制度化的、传统的,或是历史的”。[15]故而作为圣典的儒经在意义、价值、阐释标准和目的上都是相对固定的,虽汉代之经学也吸收了黄老形名、法家等思想,但其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成型的思想体系具有一定的排他性。自汉末大一统意识形态崩塌以来,圣典的地位和作用皆不复存焉,故而儒家典籍作为经典的价值便有所实现,最显著的体现便是魏晋玄学家的注解。儒家经典作为存在于阐释语境中的历史流传物,伴随着人的阐释活动而不断涌现出新的意义。魏晋六朝时调和文字和精神、身体和灵魂之间意义差异的时代需求,也使“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解经方法具有了合理性。
三、“得意忘言”思维方法与“以无为本”“崇本举末”
“言意之辨”中“寄言出意”作为玄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之一,在经籍阐释方面被用于解决解经过程中玄理与章句之间的冲突,实现会通儒道的目的;而在理论上与本末有无之辨密切相关。故而魏晋经学虽源出于汉代,但有很大不同。“得意忘言”的解经方法融合了《易》《老》《庄》之言意观,又以“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为基础。王弼的《周易略例》中对此有明确论述。王弼亦用此著《论语释疑》,该书已亡佚,其卷数与篇目远少于十卷本《论语》,故而大致是取文意较难疏通者释之,所用之法皆为“寄言出意”。后南朝梁皇侃作《论语义疏》也沿用此法,《梁书》《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经籍志》等皆有著录。皇侃注重对经文文意和注文文意的疏解,与王、何等人一样,不拘泥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话等内容,善以《老》《庄》之旨解《论语》意。这也与当时佛学讲经的风尚与方法有关。
汉末魏初名学与道学复兴,综合名实与道家“以无为本”相结合,逐渐向无名无形发展;具体的识鉴人伦逐渐延伸到本末有无的抽象讨论。《晋书·王衍传》中提道:“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名即是不可言,故五千言说道只是“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即是勉强说之,而道的本体则在言说之外。何晏、王弼皆延续了老子的思路,持“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观点。本体论上的有无之分在评论人事上即表现为外在形迹与内在神理之分,在言意关系上即表现为言象与无名无象之分,在自然与名教关系上则表现为本体玄旨自然而然之状态与因名设教之分。其基本思路是: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无者无名无象,是道的本体,道以无形、无名成万物之始。而“玄学家之贵无者,莫不用得意忘言之义以成其说”。[16]意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其最高层次为超言绝象的“道之体”,即是本;而言所呈现的是有形之迹象,是在得意之后应该舍弃的东西,故而为末。
值得注意的是,何晏、王弼虽皆“以无为本”,但并未否定有,而是强调要“崇本举末”。天下万物以无为本,但有无相依,是特殊与普遍的关系。老子之“道”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可言可思之一般道理,即可道之“道”,亦即朱熹所谓“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第二个层面是老子专指之“常道”(帛书《老子》中为“恒道”),即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永恒存在之道,亦即《老子》所言“天之道”。“天之道”包含却不只有一般道理的内容,不可俱以智知,亦不可俱以言明。“名”是事物的称谓,是具体事物抽象化的结果,亦是言说的基础。“常道”本于无,无者无象,名以定形,无象故而无名,无名故不可言,即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但一般之“道”是可以言说和思考的。“以无为本”主张无言,但并不意味着否定有和言说,只是在不同的意义层次上语言的效果也不同。“可道之道”与“可名之名”相对,“常道”(“恒道”)与“常名”(恒名)相对,“道”与“名”皆是特殊与一般的结合体,从这个方面来说,二者可谓异名而同实。“老子把‘道与‘名作为同一事物之两个方面提出讨论,指出了名与实,个别与一般的区分;同时他以‘恒道‘恒名与‘可道‘可名,即‘无名与‘有名阐明事物实体与现象的辩证关系”[17]。虽然常道是不可表达的,但又必须尝试论之,所以老子的表达策略是不正面论述“常道”是什么,而是侧面描述“常道”像什么,或者描述“常道”不是什么。老子对“道”的表达一直是依靠认知中介来实现的。描述对象都是可以靠感官及理智去理解和把握的形象和行为,如用谨慎、警惕、严肃、淳朴、豁达和浑厚等状态来形容“善为士者”之玄通。故而,无论老子承认與否,他“尝试论之”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实体与现象并举、一般与特殊结合、有无相生的内涵,何晏、王弼的本体论和言意观将此种内涵挖掘出来,并在阐发和继承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了新的方法论价值。如何晏在其多篇文章中皆试图通过讨论名实关系、有无关系来调和儒道思想;王弼在“以无为本”“崇本举末”的基础上结合老、庄与《易传》之言意观,提出了以言明象、得象忘言,以象存意、得意忘象的思维方法。
[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玄学思维方式与六朝文论话语生成机制研究”(项目号:18SKGH085)研究成果。]
注释
[1]朱汉民.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M].天津社会科学,2010:3.
[2]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495一520.
[4]甘祥满.玄学背景下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从《论语集解》到《论语义疏》[J].中国哲学史,2007:1.
[5]隋书·经籍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7:935.
[6]皮锡瑞.经学历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6.
[7]王素.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8]汤用彤.魏晋思想的发展[G].魏晋玄学论稿及其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6.
[9]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404·
[10]三国志·魏书·钟会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6:795,796.
[1]]汉书·李寻传赞[M].北京:中华书局,2007:3195.
[12]刘镇南碑[G].全三国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55.
[13]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235.
[14]王弼注.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论语释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0:633,634.
[15]约埃尔·魏因斯海默著.哲学诠释学与文学理论[M].郑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9.
[16]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26,27.
[17]高明撰.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222.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