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论“表演”
2020-03-12李盛
李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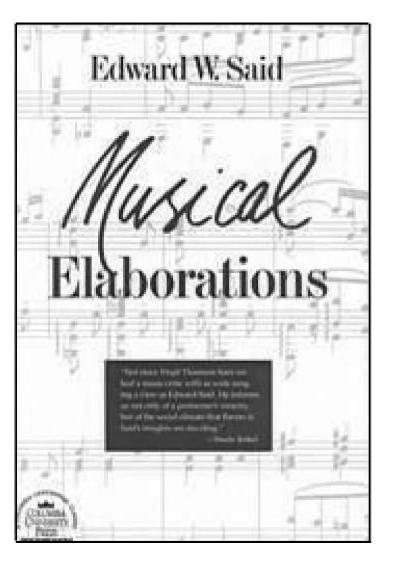


Said,Edward W.Musical Elabora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
《音乐阐发》(Musical Elabora-tion)是萨义德(Edward W.Said)首部音乐理论著作,它为我们经由音乐重新认识萨义德的丰富性提供了典范,也对经典萨义德研究排除其音乐批评,将它简化为“东方学”等封闭概念的企图做了有力回击。从第一章“表演作为极端场合”,到第二章“论音乐的越界元素”,再到第三章“旋律、孤独和确认”,音乐表演贯穿始终,与作曲家的创作相比,演奏者的表演显然更受重视,这是因为音乐表演既是萨义德的阐发对象,又是演奏者对原作的阐发行动,它同时容纳演奏者与阐发者“两种意图”,最能体现萨义德现世性的音乐观。在音乐因专业化日益走向封闭的当下,通过表演对原作的激活,萨义德使音乐不断朝具体的时间、境况与社会敞开,表演也成为他重新打开音乐最有力的武器。
一、“极端”的场合:音乐走向专业化的发展进程
《音乐阐发》第一章“表演作为极端场合”(Performance as an Ex-treme Occasion)开篇,萨义德引用波利尔(Richard Poirier)的经典文章《表演自我》开始了对表演的讨论:
表演是一种渴望行使权力的行为。它之所以令人好奇,是因为它最初是如此强烈地自我询唤,甚至自恋,到后来却渴求获得公共性、爱和历史的维度。这种隐秘行为的积累最终构成一种形式,它假定与现实本身相符,以控制被暴露于它的心灵。写作、绘画或舞蹈等方面的表演由成千上万这种微小动作组成,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通过单纯的计算完成。我的意思是,这些运动有一种内在的道德中立,它们只被设计成互相服务,而不为其他目的;它们是无辜的,因为它们对自己最终可能要负责的东西,即最后被称为“作品”的东西,仅有一个模糊的笼统概念。[1]1-2
引文从两个层次界定了表演,其一为表演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双重性;其二是表演以自身为目的。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它解释了萨义德视表演为场合的原因,即当代音乐表演的“个人一社会”双重背景,于他而言,表演的实现“取决于虽不可见却真实存在,使表演成为现实的机构和权力:表演者的训练和天赋;像音乐会协会、经理人、售票单位等文化机构;诸多社会文化环节的汇合;观众的意愿和口味共同促成一个特定的音乐事件。”[1]17此处,表演明显带有布迪厄(PierreBourdieu)“场域”色彩,各种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问题和观念在其中交锋,但在将表演上升为理论性的场域前,萨义德更愿意在具体时空中谈论它,他分析的不是抽象的社会异常,而是“音乐会仪式自身的社会异常”[1]17。
具体到当代音乐表演赖以存在的场合,即讲求严格仪式性的现代音乐厅,萨义德用定语“极端”加以限定,认为眼下的表演场合并非令人安逸地欣赏音乐之所,更像一个“战场”,充斥演奏者对观众的征服与观众对演奏者的审视和判断。随着演出场合由前现代室内沙龙转向现代音乐厅,演奏者与观众的亲密关系不复存在:演奏者的“卡里斯玛”身份使他卓然于观众之上,然而处于被动地位的观众时刻在对演奏者施以监督,稍有不慎,演奏者的“卡里斯玛”身份连同他的表演都将归于失败。表演由此成了不带中介、没有妥协余地的极端场合。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现代音乐厅因其仪式性,使观众处于被动地位,因而变成资产阶级自我拒绝(self-denial)的庆典。音乐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分离成了后工业化资本主义病态发展的重要症候。”[2]表演场合的极端表面上指由现代音乐厅严格的仪式性造成的演奏者与观众的紧张关系,背后则是音乐与现世的分离。
在萨义德看来,从固定宗教使用范式中分离出来是当代音乐表演得以诞生的基础,诺曼(Jessye Nor-man)、波里尼(Maurizio Pollini)、梅纽因(Yehudi Menuhin)等伟大的歌唱家、钢琴家和小提琴家之所以会涌现,与音乐抄本(transcription)的出现密切相关,只有“抄本成为一种艺术呈现和(对原作的)侵人以及随之而来的先在音乐文本被相对降格之际,他们才被孕育”。[1]4抄本或更宽泛意义上的改写的出现,改变了表演,使其日益呈现个人化倾向,进而颠覆了原有的演绎观:从作曲家中心论转向演奏家中心论。但悖论的是,音乐抄本与改写等赋予音乐自主性的行为,却被伊凡·休伊特(Ivan Hewett)视作音乐与其社会功能分离,进而被对象化的元凶。在近代某个时候,认为音乐可以脱离社会功能并随意移植的观念开始萌芽。音乐形式的可适应性(如改编曲、变奏和加花装饰)正是音乐具备可移植性概念后的必然结果。当音乐成为社会性的可移植品,其性质随之改变。[3]最终,以音乐自主性和演奏者个性为核心的音乐现代性运动,使音乐陷入危机,表演场合也从“演绎传统剧目、管弦乐、管风琴乐曲和歌剧”的室内沙龙转向“新的、高度专业化的环境”[1]6,即现代音乐厅。
按照阿达利(Jacques Attali)的劃分,表演的不同场合对应音乐反线性的不同区域或网路(见表1)。
音乐会作为再现社会的中心,仍在重复社会中运作,“但是其景观愈来愈存在于音乐厅本身,在于听众与作品和演奏者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在于它与听众之间的沟通共融:今天,音乐会的听众判断的比享受的多;音乐已成为一个人显露自己素养的借口,而非一种生活方式。”[4]音乐会景观由音乐表演转向音乐厅本身,暗示了两种音乐厅的存在。其一是作为再现社会核心表演场合的音乐厅,彼时,表演处于绝对中心,不论意图表现情感还是传递意识形态,表演者总带着巨大热忱使观众相信,意在维持与观众的共融状态,音乐厅成了表演者与观众亲密关系的象征。其二是由再现社会迈向重复社会的过程中,音乐厅本身成为音乐会的景观,渐趋符号化,尤其是古典音乐成了炫耀手段和文化资本,此时,观众聆听古典乐多是为了批判而非享受,表演者与观众的关系变得紧张,音乐厅最终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历程,变成一种极端场合。
随着重复社会的出现,“借由大量生产震耳欲聋、折中的音乐来达到沉寂,使所有其他人类的噪音消音。”[4]23“音乐网路不再是社交的形式,不再是观众见面和沟通的机会,而是一种大规模制造大量个人音乐的工具,这个新的音乐网路预告了资本主义体制中所有社会关系被重复大量生产的新阶段。”[4]42当噪音被消音,音乐由欣赏而背景化、环境化,表演的公共性让位于私人性,这使阿达利能够想象一种超越交换性的音乐网路,即作曲。“在该网路中,音乐是为了音乐家自己的愉悦而弹奏的,是自我沟通,除了自娱外别无他用;根本上是不属于沟通的范畴,是自我超越,是一种孤独的·自我本位的非商业行为。”[4]42作曲重新赋予“噪音”发声机会,使音乐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为反对商业交换,自我本位的作曲完全拒绝与观众沟通,即便令“噪音”重新发声,也难被听众听见。
因忽视了表演兼具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双重特质,阿达利的“作曲”囿于私人性的圈禁,不仅无法克服当代表演场合的极端性,甚至加深了音乐的现代性危机。然而,它又并非毫无理论意义,尤其是它的创造本质,“作曲网路在本质上是制造秩序的,因为在没有任何优先性符码的情况下,音乐为观赏者创造了秩序”[4]43,赋予它超越自身的潜能。作曲在没有任何优先性符码的情况下创造秩序的能力暗合于萨义德笔下表演本质的第二个层次,表演始终以自身为目的。借助其创造锋芒,萨义德希冀不断颠覆观众对表演、对舞台的定见,甚至“把它带到极限,迫使人注意到它本身,注意到表演的人为性(the artificiality of per-formance)”。[5]由此,萨义德道出“极端”的第二个方面,它属于表演自身,而他要做的,正是以极端的表演疗治极端的场合,使表演超越作曲,成为介人现世的行动。
二、“极端”的表演:表演作为目的及其情境本质
回到波利尔的表演论述,萨义德认为,波利尔意在将社会各种思潮对文学的态度从文学表演的过程中分离出来,因为那些态度往往服务于正统、体制和标准,而文学表演因其“混乱且令人不安的冲动”本质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因此,表演不仅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更是“一种必须穿透段落(passages,意为原作)的行动,尽管这些段落阻碍着行动并赋予行动以形式。就在潜在的破坏性冲动爆发的时刻,表演开始发挥作用并从材料中产生它最重要的不可简化、清晰、因而美丽的本性”。[1]2虽然波利尔的论述对象是济慈(John Keats)、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等现代作家,但在萨义德看来,钢琴演奏家、小提琴演奏家、歌唱家等人的表演因其“本质上的再创造性和阐释性的搬演”[1]2分享了表演颠覆原作的破坏性冲动,它们理应被纳人波利尔意义上的“表演”中,鉴于音乐作为与观众隔绝甚深之“最专业美学”的特殊地位,音乐表演甚至占据了颠覆性更强的突出位置。
为萨义德看重的,正在于音乐表演本质上颠覆原作的破坏性冲动,然而当遭遇音乐创作和音乐欣赏,“表演作为创作与欣赏的中介”这一陈词滥调钝化了它的颠覆锋芒。众多作曲家、演奏家、批评家一面强调表演者的个性以坚决捍卫表演的独立地位,一面将其视为创作与欣赏的中介,一种附属性的位置。这显然不符合表演在萨义德心中的定位,在他看来,表演就是目的,即便由自我询唤乃至自恋转而渴求获得公共性、爱和历史等维度,表演想从外界获得的也只是关于自身的评价。借用上文波利尔的话来说,“尽管这些段落(原作)阻碍着行动(表演)并赋予行动以形式”,但原作只是用以被穿透之物而非表演传递给观众的目的。
到后现代思想家那里,“表演作为目的”被发挥到极致,比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剽窃”(pastiche)和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概念,它们彻底拆解了本体(原作):通过“转喻方式运作”的表演以及作为“中性模仿实践”的剽窃,所谓“规范的东西”最终成为由“一种重复、一种仪式”表演出来的话语。虽然萨义德未将创作降格至如此地步,但以表演为目的而相对忽视原作确是他音乐阐发的真实状况。与原作相比,表演具有更强烈的情境性,一定的表演总存在于一定的场合之中,即便是私人聆听,不同场合也会带来不同体验,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表演更不待言。
在《萨义德与阿多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音乐家》一文中,特里盖尔(Peter Tregear)以“表演的政治”和“表演作为政治”为名,专章讨论了萨义德笔下的表演。他的“政治”视角不言而喻,表演不只具有政治性,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他认为:“随着萨义德越来越直接地介人巴勒斯坦问题,越来越普遍地讨论知识分子面对政治议题的责任,对表演的反思就变得更有意义。”[2]212但他也承认:“虽然总想从中脱离,表演同样被视为一种文化艺术风格,一种拥有相当批评潜质的行动。”[2]213可见,不论具有政治还是作为政治,“政治”只是表演的一个面向,萨义德强调表演与音乐的越界性,为的是打破当代音乐作为“最专业美学”的封闭状态,但从未将其简化为同样封闭的“政治”。
虽然特里盖尔一直以“业余性”“越界性”等术语强调表演的情境特征,但他的批评实践最终以“政治”之名遮蔽了表演。相较而言,H.阿兰姆·威瑟(H.Aram Veeser)的做法更切近萨义德,他就后者关于舞台的看法(On Stage)做的整理和再闡发,虽然阐发对象并非实际的音乐表演,也没有精致理论,但他通过举例和类比(如萨义德在讲座后与提问者、在访谈中与主持人的对答场面)呈现了不同情境中的表演,以践行的方式[6]道出萨义德表演论述的精髓。
萨义德强调要“先处理次要问题,然后再处理主要问题”,这被威瑟认为是世俗批评的关键,即抓住“运动元素”,“引起人们关注表演的人为性,那种模拟的英雄式语调。这意味着,即使处于危险境地,(表演)也在反对体制。”[6]122正因为表演不仅作为自身,也为了自身而存在,这使它很难被对象化,始终处于过程之中,表演的独立个性和生成特质不断将原作从过去拉回现在,使音乐在“强烈地自我询唤,甚至自恋”之上获致“爱和历史的维度”。因此,像阿达利那般遁人自我本位的“作曲”以打破当下音乐作为“最专业美学”的封闭以及与大众的隔绝状态,注定无法成功。唯有以私人性为起点,探讨“音乐在创造社会空间中所扮演的角色”[5]130,极端方能开端,表演创造秩序的本质才得实现。
三、托斯卡尼尼与古尔德以“极端”作为“开端”的现世启示
在阿多诺看来,文化工业及其后果——大众的“听觉退化”(theregression of hearing),共同促成表演作为极端场合的结局。虽然这种极端性或他偏爱的否定性重新肯定了艺术的自主性,但就像姚斯(HansJauss)批评的,它的“力量和无法替代的价值是以牺牲全部交流功能为代价的”。[7]因此,被阿多诺当作结局的表演,面对自身与观众的分离,除了自怜和自恋,不再具有介入现世的行动能力。萨义德则相反,表演的极端性恰成为他音乐阐发新的开端,就像特里盖尔所说:“承认音乐表演的批评潜质被证明是萨义德相比阿多诺最具生产性的区别。……萨义德不否认当代音乐表演的极端性。然而,作为音乐这一‘最专业美学和‘文化表达之社会形式的聚合点,萨义德仍声称表演文化应当获得批评家更为正面的评价和积极的参与。”[2]210
明确了表演作为目的并指明其情境本质后,萨义德以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与古尔德(GlennGould)为对象,分析了以极端作为开端的实现路径。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两位音乐家的作品似乎就某個意义而言也是有关表演……他们可说是执着于表演的观念,把它带到极限,迫使人注意到它本身,注意到表演的人为性”。[5]132具体而言,此两种路径,其一为托斯卡尼尼坚守舞台,以对音乐的绝对控制姿态,将表演者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其二为古尔德在坚持主体性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文化工业的音乐生产,将舞台表演扩展至唱片灌录、演讲、访谈,最终使表演从舞台走向现世。
相比古尔德重新定义表演的开创之举,托斯卡尼尼过渡性更强,甚至略显保守,但其价值恰在于对舞台的保守态度,他让我们窥见舞台表演可被推至何等极端的地步,他那极致的主体性,一种深具美学意味的极端性,颠覆了我们对舞台表演的想象。关于托斯卡尼尼的极端表演,同时代的著名指挥家富特文格勒(Wihelm Furtwangler)评论道: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生硬、简单,速度太快且少变化,过分仰赖全奏和咏叹调,不仅背叛了忠于原作的声明,更破坏了海顿(Franz Haydn)刚柔结合的风格精髓、忽视了德彪西(Achille-Claude Debussy)敏感的音调语言、分解了贝多芬(LudwigBeethoven)音乐极其宽广的范围。换言之,托斯卡尼尼严格军事化的演奏精神对当代音乐危害甚大。但正如富特文格勒的《1924-1954年札记》英文版编者米歇尔·泰纳(Michel Tanne)认为的,这篇评论一定程度上是他“出于面对托斯卡尼尼在柏林的成功演出而产生的个人妒忌和自尊心受损”。[8]同样是关于《命运交响曲》,萨义德透过托斯卡尼尼呈现的“逻辑的绝对严密性”,看到了“不能被化约的独特、古怪、与日常生活相反的过程,甚至是叙事,一种显而易见的审美选择而非寻常人的艰辛劳动”。[1]19
如果抛开个人好恶因素,不论对社会历史现实,还是音乐自身演进,托斯卡尼尼的极端表演都有其价值。关于前者,阿多诺认为“托斯卡尼尼是末期资本主义的一种失调,他精通主控,象征一个没有灵魂的领袖那种威权主义式的、机械式的完美”。[9]紧随其脚步,霍洛维兹(Joseph Horowitz)对当代美国社会的“托斯卡尼尼崇拜”深怀反感,认为托斯卡尼尼的影响造成了演奏规范的标准化,助长了美国社会将文化简化为僵死杰作的不良倾向。萨义德反对将美国文化不对劲的发展完全归因于托斯卡尼尼,认为托斯卡尼尼比霍洛维兹承认的更令人尊敬,因为托斯卡尼尼“剥夺了家乡、个人、家庭、传统或民族风格的任何痕迹”[1]20和“音乐演奏里虚假的传统主义和邋遢的滥情”[9]59,展现了“与表演场合完全相反的品质”[1]20,这种近乎形式主义的表演不仅对音乐演进遗泽久远,更迫使人注意极端本身,即表演的人为性,从而在文化工业的填密运作中撕开小口,使人在舞台表演中窥见权力的生产与争夺。
随着讨论的推进,关于本文的关切:极端的表演如何破除当代音乐表演场合的极端性,如何将音乐拉回现世,使其再次具备现世的行动能力。笔者的回应逐渐变得清晰:首先,表演兼具私人性和公共性的双重性使其天然具有现世特质;其次,表演的极端性,即托斯卡尼尼那类表演者近乎形式主义的演出姿态,颠覆了观众的舞台想象,促使观众思索内在于表演的权力运作。然而,极端作为开端的最后一步是直接介人现世,就此而言,古尔德无疑更典型。
萨义德的第一篇乐评就是讨论古尔德(《古尔德对位法慧见》),自此,古尔德成了被他不断重返的开端性人物。其中,萨义德最精妙的评价出自《音乐阐发》:身处正常的社会文化环境,古尔德“持续不断的人为性”描绘了坚执于反常的一生,这种反常如此强烈,以至使他呈现了不只是“不自然”(unnatu-ral)而是“反自然”(antinatural)的面目[1]22。这里,“自然”首先指观众对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建立的钢琴演奏共识,古尔德不承认此共识,他将当代钢琴演奏曲目的核心,以肖邦(F.F.Chopin)等人为代表的浪漫派作曲家剔除出去,转而倾心于前古典的巴赫(Johann Bach)与20世纪的“新音乐家”勋伯格(Ar-nold Schonberg)等人。此外,他还擅长制造别人从未想过的奇怪组合,这并非出于刻意求新、求怪,而是对浪漫派作曲家“自我炫耀的戏剧姿态”乃至当代钢琴演奏共识的根本嘲弄。
古尔德的嘲弄姿态,演奏时的奇怪装束,独特的蜷缩姿势(见下图),边弹边哼哼以及与指挥争抢指挥权的不良记录,使他成了观众眼中的怪人。在萨义德看来,他的“怪”与托斯卡尼尼指挥的“生硬”一致,都将表演推至极端,但古尔德的进步之处在于摆脱舞台束缚,直接介人现世。萨义德在《音乐阐发》中将话题由托斯卡尼尼转向古尔德时,刻意提到当代音乐表演与生产分离的现状,“一个世纪前,作曲家同时作为作者和表演者占据舞台中心,但现在只剩表演者”。[1]21这一颇堪玩味的过渡暗示古尔德试图将作曲家与表演者合二为一的雄心,并以拥抱技术的进步姿态反向考古,逼问场合的极端性本身。因此,他的“反自然”,反的不仅是钢琴演奏共识,更是对表演乃至音乐范式的倒转。
1964年,古尔德告别传统音乐会舞台,一头扎进录音室,他的转向被巴扎纳(Kevin Bazzana)解释为对儿童时光的复归,其音乐美学也深受弥漫于20世纪30年代“虔诚之多伦多”的清教主义思潮影响,但从客观效果来看,这一转向毫不保守,相反呈现了对待音乐与技术关系一往无前的激进性。在与老一辈钢琴家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的对谈中,他强调“技术的存在不会伤害、妨碍人类……有助于加速这种接触,使之更为直接和迅捷,并让人们远离诸如竞争、自我中心等对社会有害的事物”。[11]就表演自身而言,技术同样对他施加了巨大的有益影响,录音的可重复性赋予他“事后思索、编辑的机会,它给他一种力量”[11]231,这不仅化解了音乐瞬时性带来的表演场合的极端性,更使他得以重构甚至创造新作,从而将表演的创造本质推至极端,就像古尔德所言,“我不认为(表演与创作)这两者之间有真正的区别”[11]231。透过录音,他将表演者与作曲家合二为一,使音乐重归前现代时期,彼时,表演者与作曲者尚未分离,音乐亦与现世紧密结合而未被对象化。
通过将技术引入音乐,古尔德以进步姿态使音乐表演重返类似前现代室内沙龙与观众共融的亲密场合,这一构想在他舞台表演时期即显露端倪,“顾尔德的独奏会曲目常常是一整落当初设计为私人小型聚會的场合来演奏的”。[10]229 1964年后,邀请三两好友进入录音室,欣赏他的表演/创作,成了古尔德后舞台时期的常态。当然,这并不意味他将情境性的表演简化为私人聆听,古尔德表演的情境性从空间场合化人唱片、广播、电视节目,它们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本身就是公共性的体现。换言之,古尔德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挑战听觉退化的悲剧结局,也未止步重建室内沙龙这一和谐场合,而是谋求成为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或萨义德所谓“机械复制时代之子、机械复制时代的伙伴”,[12]在艺术变得不可能的时代发现艺术的可能,在阿达利的重复网路中制造无法重复的艺术之美。
在《音乐阐发》中,萨义德总结道,“托斯卡尼尼与古尔德首先接受,进而阐发当代古典乐的社会文化逻辑,并且至少带着自我意识和精神采取行动。”[1]34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与古尔德的唱片,不仅从某一侧面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同时融注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从而具备只属于前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光韵”(aura),这种丰富性成为真正的表演者介人现世以极端表演疗治极端场合的实践成果,也为我们思索当代音乐表演专业化封闭的突围路径提供了启示。
注释
[1]Said,Edward W.Musical Elabora-tion[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1:1-2.
[2]Tregear,Peter.Edward Said andTheodor Adorno:The musician as public in-tellectual[A].in Curthoys,Ned&Gangu-1y,Debj ani.Edward Said:The Legacy of aPublic Intellectual[M].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2007:210.
[3][美]伊凡·休伊特.修补裂痕:音乐的现代性危机及后现代状况[M].孙红杰译,杨燕迪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14.
[4][法]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M].宋素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1.
[5][美]萨义德.批评、文化与表演[A].单德兴译.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6:132.
[6]引文一:1992年4月29日,华盛顿,萨义德在一场关于“民族主义”演讲的提问环节与提问者的对答。
提问者(带着轻微口音,可能是以色列人):听了你的演讲,我希望你关于(巴以)对话形式能有更平衡的观点。像一些相对较小的(细节),比如你关于乔·帕普的演讲,你没有提到在接下来的一周他确实短暂的任职并邀请了——
萨义德:不,他没有。很抱歉打断你,但我能纠正你吗?
提问者:当然可以,它只是一个次要问题。
萨义德:它确实是个小问题,但我想说,我们为何不先处理次要问题,然后再处理主要问题呢?乔确实说日后将邀请他们,但前提是同时上演一部以色列歌剧。这就是他做的一切。他们被迫在另一家剧院演出。我去参加了,我在那里,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对情况了如指掌。
引文二:在《国家“新闻与讨论”电视节目》中,当被主持人介绍为“是一名以色列裔以色列政府政策分析专家和任教于美国华盛顿一所大学的教授”,萨义德与阿莫斯·波尔穆特做了如下对谈。
萨义德:嗯,我想说,不像波尔穆特先生,我事实上更感兴趣于——
波尔穆特:小说。
萨义德:对,我的意思是——
波尔穆特:你是一名英国文学教授,你喜爱小说。
萨义德:对,是这样。我不太清楚你是什么专业的教授,但肯定不是历史。
……
波尔穆特:我让你说,我让你说,你也得让我说。
萨义德:哦,你为什么要让我说?
See Veeser,H.Aram,Edward SaidThe Charisma of Criticism[M].New Yorkand London:Routledge,2010:122-124.
[7][德]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M].迈克尔·肖,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26.
[8][美]阿杜安.富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M].申元译.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32.
[9][美]萨义德.万人迷大师(评《了解托斯卡尼尼》)[A].彭淮栋译.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随笔[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57-58.
[10]1963年3月,古尔德于哥伦比亚唱片位于纽约第三十街的录音室,拍摄于录音期间。[加]凯文·巴扎那.惊艳顾尔德——品味钢琴巨擘的生命与艺术[M].刘家蓁译.台北:商周出版,2008.
[1]]杨燕迪编著.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235.
[12][美]萨义德.古尔德对位法慧见[A].彭淮栋译.音乐的极境:萨义德音乐随笔[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12.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