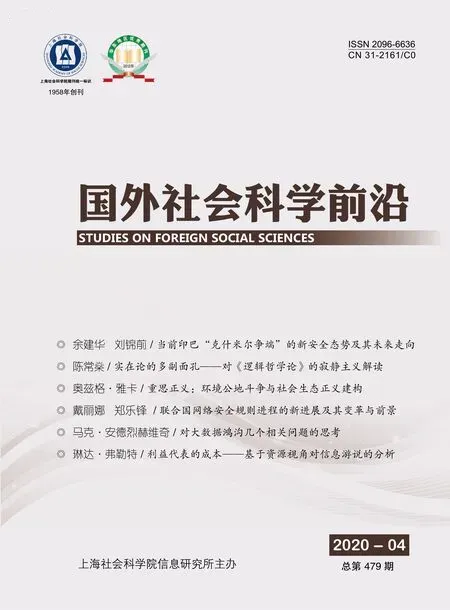重思正义:环境公地斗争与社会生态正义建构 *
2020-03-12奥兹格雅卡
奥兹格·雅卡
内容提要 | 本文基于土耳其当地社区与河流水力发电厂斗争理论的经验式研究,探讨了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本文将这一特殊案例视为更广泛的环境公地运动的代表,采用行动理论的视角,将民间环境运动中产生的新兴正义主张转化为正义理论的概念性词汇;并以南希·弗雷泽的三维正义模型为出发点,探讨了扩展正义边界的可能性。维护社会与生态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需要从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本体论角度重新思考“社会性”与“社会正义”。因此,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扩展了正义的范围,将人类和非人类生态的关系性存在视为一个正义问题。
一、引言:作为永久性建构的正义
《逆流而上》1《逆流而上》由乌穆特·科卡戈斯(Umut Kocagoz)、奥兹莱姆·伊西尔(Ozlem Isil)、艾兹格·阿克约尔(Ezgi Akyol)集体撰写,并于2011 年推出,网址为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mj_JPuJxik。是近十年来记载土耳其当地社区反对水力发电厂斗争的许多纪录片之一。其中,来自卡斯塔莫努(Kastamonu)洛克谷(Loc Valley)的一名年轻妇女大声抗议一个私人承包商,他在没有等待法院判决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当地的河床上建水电站。尽管该项目受到法律起诉,但私人承包商受到军队的保护,而作为公民,这名女性的权利却被忽视,她对此感到愤慨。“为什么会遭受这种不公平?”她哭泣道,“难道为了保护河流,我们都应该死在这里吗?”正义理论会对来自黑海村庄的年轻土耳其妇女的正义诉求做出何种解释?我们如何将她的主张转化为正义理论的概念性词汇?本文将土耳其的反对水电站运动定位为“寻求正义”运动,旨在根据反对水电站的斗争中隐含的正义概念,拓展现有正义理论/模型的边界。论文采用行动理论的视角和迈克尔·布拉沃(Michael Burawoy)的扩展案例研究方法,论证了经验案例研究有助于阐述更广泛的正义问题。
正义论是政治哲学中一个成熟的领域。不过,该领域的主要讨论以道德框架为主导,正如公正、平等、责任、义务、道德状况等概念所反映的那样。分配范式和能力方法都共享这一框架,这一框架被雷纳·福斯特(Rainer Forst)等学者正确地批评为“前民主主义”,因为“它赋予目的论价值以优先地位,这些价值理应奠定公正或良好的社会秩序基础,而那些受到这种秩序制约的人并不像其作者所宣称的一样”。另一方面,政治哲学中的另一种思路在正义观念与具体的日常不公正经验之间建立了必不可少的联系。这一思路不是将正义视为一套既定的正式原则和程序,而是将正义视为“永久性建构”,它通过程序正义与其结构性过剩之间的界限斗争而不断得到扩展。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强调正义总是超越法律,揭示了正义尚未捕捉到的新兴维度与历史上给定的正义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张力是由那些遭遇不公正而没有被现有的正义制度所代表的人的主张所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正义理论不能被视为脱离正义斗争或仓泽富幸(Fuyuki Kurasawa)所谓的“正义社会劳动”而存在。因此,正义的概念应该完全向未来的正义敞开,即通过“社会斗争的媒介”揭示正义的新维度。
当代环境运动为此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因为他们的正义主张超越了现有正义制度的“既定语法”。“正义”概念在当代环境斗争中的核心运用——例如环境和生态正义——并非巧合。在环境运动、斗争和实践中产生了对正义的强烈需求,而这些正义诉求不易被转换成既定的正义理论词汇。
大卫·施洛斯伯格(David Schlosberg)和戈登·沃克(Gordon Walker)等学者致力于从事一般的正义理论探讨以寻找这样的转换。这些讨论主要运用了现有的正义理论来研究环境运动的正义诉求,取得了众多成果且富有启发性。相反,本文试图在另一个方向上迈出一步,根据环境斗争中产生的正义诉求,研究讨论和修正现有正义理论的可能性,尤其是为环境公地而进行的斗争。为了使这项任务取得成功,必须对确定正义制度的既有规范的界限和合理性提出质疑,因为那些运动产生的正义诉求包含了它们与非人类生命和自然的关系。因此,本文将生态学问题及时提上了正义理论的议程,并引入了正义的社会生态维度,作为对环境公地斗争的概念性回应。
将正义的边界扩展到非人类环境的尝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然/社会与人类/非人类生活的关系本体论也不是新鲜事。其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对话来阅读这两种文献,在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的关系中反思正义。
二、迈向行动理论的正义概念:为环境公地而斗争
自1971 年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发表《正义论》以来,对分配范式的批评就一直主导着关于正义的辩论,该批评强调了除分配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正义。在诸如艾里斯·马瑞恩·扬(Iris Marion Young)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人物的著作中,承认(recognition)已被视为正义的主要原则。霍耐特以格奥尔格·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和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自我主体间性概念为基础,将承认概念化为自我实现、自我尊重和自我肯定的前提。另一方面,扬直接涉及政治身份和差异,强调分配范式的局限性,她认为,分配范式仍然缺乏对作为压迫的不公正的回应。对新社会运动的批评,直指各种形式的父权制、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异性恋正统主义(heteronormativity),这当然有助于将承认作为正义的主要支柱。1事实上,扬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正义与差异政治》(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的开篇是,“左派政治相关的新的群体性社会运动(如女权主义、黑人解放运动、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的主张,对政治哲学有什么影响?这些新的社会运动隐含地吸收了哪些社会正义概念,它们如何面对或改变传统的正义概念?”这标志着她对正义的态度与对20 世纪60 年代和70 年代新社会运动的批判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本文认为,现在是对新一波社会运动提出相同问题的时候。随着身份和差异问题的日益突显,错误承认也被视为一种压迫,它对个人和社会群体造成的伤害与不当分配同样严重。
在认真对待承认的同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在她的模型中保留了再分配的方面,将承认和再分配以及阶级和身份问题结合在一起,全面地考虑了社会正义;随后,代表制也被纳入到该模型中。在后民主时代,将政治层面的跨国形式整合到正义理论中至关重要,因为在后民主时代,代议制民主日益简化为正式选举程序,不包括任何参与性内容。弗雷泽的论点——代表制是正义必不可少的维度——符合过去十年中社会运动的要求,这些运动正在挑战世界各地街头和广场上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形式。
如果新兴的正义诉求来自于与不同形式的不公正作斗争的运动,且在重新构思正义的概念中处于中心地位,正如承认和代表性的诉求一样,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转向我们这个时代的运动及其诉求,以进一步扩大正义的边界。社会学和社会运动研究的中心人物之一阿兰·图兰(Alain Touraine)认为,特定的社会运动与特定的社会类型相对应。1弗雷泽将正义的不同维度与不同的社会斗争联系在一起:再分配与劳动的斗争,承认与身份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斗争,代表与民主化的斗争。当时的新社会运动是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与其制造的不公正的产物,为了回应这些运动,以图兰为代表的学者们通过强调身份和认同来重新认识正义的意义。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体制中,其特点是市场关系扩展到以前非商业化的领域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生活的空间。今天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新形式的不公正,以及针对这些不公正形式的新运动。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社会运动,正以争取城市、公民、环境和非物质公共空间的形式,与这种扩张主义趋势作斗争。
争取公共资源的斗争标志着一个新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承认、再分配、代表以及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已经动态地、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新的围城浪潮和扩大市场关系对自然和自然资源进行殖民的过程中,当代环境运动尤其是环境公地和环境正义运动,处于斗争的核心。这些运动的共同点——也激发了气候正义运动——是将环境问题视为社会正义问题。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环境/生态学与正义之间的融合。 我们如何才能在概念层面上达成这种融合呢?弗雷泽的三维正义模型——结合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制,分别对应于社会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领域——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框架,用于解决环境正义运动所提出的正义多样性和交叉性要求。问题是:除了简单地用弗雷泽的模型来描述这些正义诉求的多种特征外,我们能否根据从当前的斗争中得出的经验性见识,发展、扩展或修正弗雷泽的模型?换句话说,这些斗争能否帮助我们,抓住一个新兴的、尚未被捕获的正义维度?我将根据我对当地社区与土耳其的水力发电厂作斗争的案例研究来探讨这些问题。
案例:土耳其当地社区与水力发电厂的斗争和弗雷泽三维正义模型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十年中,土耳其急于建造数以千计的私人河流水力发电厂,这已经导致了大规模的异质性运动,主要是以社区斗争的形式遍布全国。这股水电站建设浪潮是住房、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热潮的一部分,这些项目是正义与发展党发展战略的核心——“推土机新自由主义”。对于水力发电来说,增长和发展的论点并不新鲜,将以多种不同方式维持生命的河水看作一种单纯生产手段的观点也不新颖。时任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宣称, “我们的河流将不再白流”,并利用国家权力支持私营公司,正如《卫报》报道的那样:“在驱逐村民、征用私人土地、清理国家森林和压制正常规划方面给予了特别的权力,以实现到2023 年建成4000 个水电项目的目标。”
径流式水力发电厂不会像水坝那样淹没大片地区,而是将河水通过管道改道到发电站,然后再回到下游。然而,这意味着沿河的村庄被剥夺了数百年来一直作为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河水。随着2007—2008 年第一波水力发电厂对河流两岸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受到新项目威胁的社区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这主要是在地方一级,但有时也会建立全国性的网络,例如河流平台姐妹会。
接下来的讨论借鉴了2013—2016 年我在土耳其三个地区——地中海、黑海东部以及东部和东南部(库尔德)地区——进行的民族志学研究。1为了进行比较分析,我在每个区域选择了3~4 个案例,每个案例都涉及几个微案例。我在这三个地区进行了几次实地考察,在参与性观察的支持下,对村民和当地的活动家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对材料的分析主要集中于随后追踪和识别正义与不公正的概念。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每种情况下,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性的各个方面都根据该地区的具体特点而不同地交织在一起:气候和自然景观的具体特征、社会和空间关系的具体组织和文化特征、政治遗产、河水的物质属性,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和环境特定的联系方式。从再分配开始,我们应该认识到,关于弗雷泽“可分割商品的公平分配”的概念,可能不足以涵盖环境斗争所隐含的正义的经济层面。再分配似乎与福利国家的理念以及国家通过某些社会计划、补贴等在公民中分配财富的作用有关。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面临的问题是失去你已经拥有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作为私人财产而是作为公共物品,你无法从所创造的财富中分一杯羹。
因此,这更多的是一种剥夺,而不是分配不均。正义的经济层面是“穷人的环境保护主义”的核心,在土耳其的案例中意义重大,因为河水传统上被用于自给农业。这一维度在地中海地区更为明显,那里漫长而干旱的夏季需要灌溉农田,而河流是灌溉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斗争的主要动机是担心丧失基本生存手段;不再能种植水果和蔬菜;以及害怕被迫迁移到大城市,只能加入失业大军。
承认也正在发挥作用,因为河流不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而且还是文化遗产、地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元素,是安纳托利亚不同地区仪式、神话和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承认的主张在库尔德地区占主导地位,在那里,整个问题都处于库尔德人争取自治的大背景之下。大坝或小型水力发电厂项目被视为土耳其国家对库尔德人进行文化同化的一个要素。承认和同化问题常常是争取环境公地和环境正义的核心,在这些地方,少数群体正试图保护他们的土地、森林和水域,就像美国的美洲原住民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土著人民的斗争一样。在这些情况下,土地和水被认为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一位美索不达米亚生态运动的年轻男性活动家埃尔坎解释道:“支配我们的水意味着支配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将水理解为一种文化价值。”
这一特定的背景清楚地表明,个人主义心理学家对霍耐特的定义不能揭示反对水力发电厂斗争中隐含的错误承认/承认(mis/recognition)。2霍耐特将承认定义为对所有个人的尊严的认可和对个人自我实现的支持。相反,弗雷泽和扬的框架更有帮助,因为扬强调的是群体身份和差异,而不是个人身份。弗雷泽认为,这是一种由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造成的身份伤害。要求承认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库尔德地区,与“公开证实的障碍”密切相关,妨碍了库尔德人作为社会正式和平等成员的地位。
作为对先前“二维”正义观的补充,弗雷泽阐述了第三个维度,即代表制,主张参与政治和决策过程是提出正义主张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代表制“为争取分配和承认的斗争提供了舞台”。事实上,人们可以观察到,在地中海、库尔德和黑海东部这三个地区,错误承认/承认是其基本方面,就一切情况而言,这场斗争的主要原因是,受将水的使用权转让给私营公司这一决定影响的人们没有被纳入有关其自身环境的决策进程中。弗雷泽所说的“一般政治中的错误代表”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重要动机,所有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人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也没有得到重视。这导致了一种深刻的疏离感,正如来自阿拉基尔(Alakir)山谷卡拉考伦村的埃斯玛(一个30 多岁的女人)所说:“我们知道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而是公司的。”
如上所述,弗雷泽的三维正义模型——排除了再分配概念的局限性——有助于解读不同地区的社区所面临的不公正现象,也有助于解读他们反对水电站的斗争所隐含的正义诉求。然而,这些概念无法捕捉到一个维度,即我称之为社会生态的维度,它是反对发电厂运动和民间环保主义正义诉求的核心。因此,经济、文化和政治概念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释沿河社区的正义诉求。这些诉求的核心是河流,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维持着生命。河流是人类和非人类生态系统的生命源泉。反对水电计划的斗争不仅仅是反对经济剥夺和文化同化,也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生态存在,即人们与河流建立的内在联系。
在我对土耳其黑海地区的民族志学研究中,这一点变得尤为明显,那里是抵抗水力发电厂的发源地。在黑海东北部地区(从特拉布宗到格鲁吉亚边境),水力发电厂的开发集中在那里,沿着这些河流的村庄处在陡峭的山谷和茂密的森林中。经济和文化层面的正义概念隐含在当地运动的某些论点、话语和做法之中,但它们并不占主导地位。1我的一些受访者声称,水力发电厂会改变小气候,因此从长远来看会影响农业活动。这样的论点意味着,水力发电厂的建设会造成经济分配的不公平。黑海东北部的村民通常不将水用于直接的经济目的,因为雨水足以维持单一文化的茶和榛子农业。与在库尔德地区一样,同化和身份主题也很少被使用。相反,河流被视为并代表了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人们沿着河流建造房屋,以便欣赏河流,并将河岸作为公共空间,就像城市广场一样:妇女在田间工作后在河边休息,孩子们学习游泳、恋爱……河流作为重要的行动体(actants)2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使用的“行动者”(actants)概念是广义的,既可指人类,也可指非人类存在,将其译为“行动体”,更符合中文表达。——译者注,通过其物质特性或某些行为来塑造空间想象的、情感的景观和象征性的秩序。
三、发展社会生态正义概念
反水力发电厂运动的著名口号——“Su Hayattır”(水/河流就是生命)代表了河流在生命中的中心地位,它包含了社会再生产和文化形态,但不能归结为承认和生存。要描述这里的利害关系,我们需要超越正义理论的既定词汇,因为它忽略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我们社会存在的意义。承认理论无法解释这场特殊运动的正义诉求,因为核心问题既不是个人尊严或地位等级,也不是身份和差异。它的核心是非人类形式、生态和自然对人类社会生态存在的重要作用。
人们进行了许多尝试,将承认理论扩展到自然界和非人类世界。施洛斯伯格的工作尤其值得一提,因为他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讨论承认问题,目的是“揭示一种正义的共同语言……我们可以用来解决环境和生态正义问题”。施洛斯伯格通过承认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相似性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来扩展承认概念的讨论,确实令人鼓舞。然而,当他转向公认的承认理论并试图将其应用于非人类世界时,“作为承认的正义”的局限性就变得清晰起来。他同意弗雷泽关于承认的结构性理解,即承认概念“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制度实践而不是个人经验”,比霍耐特的框架更适用于自然和非人类的世界,因为后者的研究建立在个人心理学基础上。尽管如此,他基于对自然伤害状态错误承认的运用,未能揭示诸如土耳其黑海地区为环境公地而斗争的不公正现象。
将承认自然的理论应用于身份损害的情况,可能有助于对生态正义的思想进行道德讨论。但是,社会生态正义的行动理论概念,需要的不仅仅是承认概念的扩展。它要求在正义理论中引入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本体论,从而将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界定为正义问题。一些地理学家和环境正义学者已经采取了初步的步骤,将关系性维度引入正义。有学者对研究环境正义运动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制这三维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警告。1伊莉娜·韦利库(Irina Velicu)和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没有扩展三维模型,而是完全拒绝了它,取而代之的是对正义更叛逆地理解,这种理解受到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政治和叛逆观念的启发。玛格丽特·兹瓦特文(Margreet Zwarteween)和罗格德·波伦斯(Rutgerd Boelens)甚至宣称,水的正义问题意味着第四个领域,即社会生态正义和完整性,不过他们没有详细阐述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另一方面,另一组学者正在发展关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研究。埃里克·斯威格杜(Erik Swyngedouw)的社会性概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把自然作为社会生活新陈代谢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斯威格杜关于人类既是社会的又是自然的主张相一致,史黛西·阿莱莫(Stacey Alaimo)通过为环境正义和健康而进行的斗争,证明了人类身体的跨物质性(trans-corporeality)。由于人类的身体总是与更广泛的世界交织在一起,人类的本质最终是与环境分不开的。然而,正义和关系这两个主题并不一致,也不参与对话。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旨在通过利用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关系本体论,探讨既定正义模型的局限性来促进这种对话。
以黑海地区为例,对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关系理解体现在当地社区的叙事中。 这些叙事清楚地表明,生活在该地区河畔村庄的农村社区与河水的关系超出了经济生存和文化认同的范畴。我采访的大多数村民将保护河流的斗争视为生死攸关的问题,声称他们离开河流就无法生存。“生命”在这里指的不仅仅是生存和身份,而是指在“生命之网”中与非人类形式、实体和生态系统共存的特殊方式。与非人类世界的联系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且是亲密的、感性的、情感的、有形的。河流位于这个与非人类世界、亲密而情感的关系网的中心,但是河流维持的人类生活也是一个关注点。来自阿尔哈维市的居民问:“鱼会怎么样?”“它们会在那些管道里生存吗?”“熊、鹿以及所有从河里喝水的野生动物呢?”来自里泽市的一位老人哈桑体现了这种亲密的联系,正如他感知到的:“夺取我们的河意味着把我们带入一个活着的坟墓。没有河流,绿色就会消失,自然平衡被打破。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都不能再住在这里了。”
当地社区的某些叙事也将人类和非人类世界建构成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人类生命被非人类世界所界定,反之亦然。在反对水力发电厂运动中,水的物质特性促进了认同,“水在人体和环境之间的流动……导致对共同物质和连接的深层联系意识。”2Strang V, Fluid Consistencies: Material Relationality in Human Engagement with Water,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vol.21,2014, pp.133-150.一位50 岁的妇女对《激进日报》的记者说,“他们不明白的是:这条河是我们的命脉,夺走我们的河流基本上就是切断我们的生命线。”他们将血液循环和河流流动视为人类生命的基础。另一位中年妇女雷姆齐耶,同样认为河流具有身体的重要功能:“河流意味着人类,河流意味着灵魂,河流意味着呼吸,河流意味着我们的血液……”
河流是这些叙事的核心,因为反对水力发电厂的斗争主要是为了保护河流。 然而,河流只是黑海东部人民尤其是女性所认同的非人类环境的一部分,57 岁妇女莱拉在接受土耳其《自由报》采访时说:“植物死了,蜜蜂消失了……他们把我们的山撕裂了……每当我看着这座山时,我都感觉它在哭泣……我感到我内心的痛苦。我们与土地合而为一,夺走我们的土地意味着夺走我们的生命……在村庄中,我们就是大自然本身……”
莱拉的陈述阐明了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创造的“土地伦理”,“它扩大了社区的范围,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只要莱拉不认为自己在本体上与自然分离,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山、河流、植物、蜜蜂也会成为受苦、死亡、哭泣的对象……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和菲利普·迪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等人类学家已经表明,将自然作为与社会和文化领域相分离和外在存在的理解绝不是普遍的。他们认为,就算将自然作为一种观念,也并非是显明的。事实上,在尼汉·博佐克(Nihan Bozok)等人的采访中,这个想法对于年长的黑海东部地区的妇女来说毫无意义。这些妇女可以谈论她们与河流、海洋、雨水、树木、周围的植物和动物的关系。但是自然作为一种有别于社会和文化的本体论范畴,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河流、树木、植物和动物是他们社会和文化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莱拉与其他许多人一样,将土地和河流与她的生活和她的社会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与非人类世界的强烈亲和力表明了对人类生命依赖于水、土地和空气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所构成的统一命运的生态学理解。在这里,自我并不孤立于其生态环境之外,而是一个“在自然—文化的连续统一体中起作用的扩展的、关系型自我”。
对非人类生命的认同,以及将自我概念扩展到包括非人类生命和实体,似乎主要体现在非工业和土著社区。按照日常生活经验,即与当地环境的密切持续接触,看似会危及与非人类世界的亲密情感和感性关系,实际上使人们能够一致认同并促进对人类生态和非人类生态的相关理解。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关于自我与非人类生命的横向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是土著人宇宙观所特有的,它只是人类状况的一种表现。
众所周知,现代化进程使自然成为人类生命和社会之外的事物,成为必须从中解放出来的领域,成为要统治的荒野。同样,非人类的生命和自然仅仅被看作是为人类服务的资源。然而,这一范式仍然缺乏对非工业/农村和工业/城市空间中人类状况的分析。自我,无论是土著的、乡村的还是城市的,都是在与他人互动的世界中形成的,不仅与人类有关,也与非人类的身体和实体有关。我们的自我认识、意识和主体性是通过许多感官和情感的方式与环境接触而产生的,人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世界。这样,不仅是生物的机体,而且其个性和主观性都是涉及非人体、生物体和物体关系的集合。
二元范式也被证明越来越不足以应对当前的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挑战。换句话说,我们当前正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生命的生态嵌入性不仅仅是偏远地区/土著社区的特征。在每种时空背景下,人类生命都是以生态方式嵌入的,尽管方式不同。事实上,人类的生活、社会性和能动性与非人类生态日益纠缠在一起并依赖于它们,这一点越来越难以否认。对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以及生态和社会性的二元理解,在概念上无法与我们生态性嵌入的社会存在相适应。正如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指出的:“现实已经超越了二元范式的容量,二元范式已无法帮助我们追踪眼前正在展开、加速和放大的真实变化。”1Moore J.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Verso, 2015, p. 5.
四、社会生态正义概念化
我在这里要介绍的社会生态正义概念是基于从特定事例中得出的经验见解,但是它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支持,尤其是地方社区以及土著人民为环境公地和环境正义而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体现了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相互关系,他们将“自然”定义为不是与社区分离的东西,而是“社会世界的一部分”。他们还展示了“政治社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扩展到非人类”的方式。
由于社会生态正义建立在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的关系本体之上,因此它既不同于环境正义,即涉及环境危害和利益在人类之间的公平/不公平分配(对人类的正义),又不同于生态正义,即强调“我们与非人类世界的道德关系”(对自然的正义)。相反,它建立在人类与生态,自然与社会/文化,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相互联系之上,承认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有权在不受社会和生态破坏与退化的环境中共同生活和繁荣的权利。这种正义的概念来源于生态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并需要一种概念框架,该框架将把对人类的正义概念与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的正义相结合。
环境正义的概念在将环境问题与权力、正义和不平等联系起来,并挑战那些在社会中未能认识到环境不平等的主流环保主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文献大多将环境(environment)作为另一种反映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统治与压迫关系的情形(setting),如种族主义、贫穷和父权制。尽管在每一种社会情形中指出这些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但由于对环境危害分配正义的强调不足,便不能将正义理解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生命之网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尽管某些环境正义学者例如史黛西·阿莱莫论证了“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物质联系”,却没有讨论他们在构建环境正义之“正义”部分时所做的重要工作的概念含义。
另一方面,由尼古拉斯·洛(Nicholas Low)和布伦丹·格里森(Brendan Gleeson)提出并由布莱恩·巴克斯特(Brian Baxter)采用的生态正义,暗含着以一种本质上的争议和利益冲突来构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里,“重点是……人类实践如何因不尊重和没有尊严地对待自然世界而使其退化或毁灭。”生态正义被称为人类对待自然的公平,它被深深地隐藏在非人类物种作为正义主体的道德可考虑性的讨论中。处理复杂的伦理问题是思考正义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对自然的正义和对“自然—人”的正义。然而,如果一种严格的生态主义将动物平等主义排除在人类中心主义之外,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强调我们的生存取决于生活在其中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这一事实并不会自动谴责自然界和非人类世界的“内在价值”。恰恰相反,正如沃里克·福克斯(Warwick Fox)所强调的那样,生态意识往往源于我们对非人类世界的深刻认同,而不是出于对其内在价值的复杂伦理考虑。借助我们在世界上的关系和超个人经验,伦理也可以作为一种“存在状态”来培养,而不是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应该反对的是将非人类世界纯粹作为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即人类工具主义。与人类工具主义相反,人类中心主义可能会产生一种生态意识,尽管是通过利己主义实现的。这是一个自我利益的扩展概念,它建立在破坏生态环境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意识之上。
简言之,社会生态正义是一种超越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双重性尝试——要么是保护自然免受人类社会的侵害(自然权利),要么是保护人类免受环境的危害和剥夺(人类对环境的权利)——这与人类生命与非人类生命的本体论区分是一致的。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生态正义将正义置于社会现象与生态现象内在联系的关系本体之内。它涉及理解“自然中的人类”的权利和利益,这并非争论,而是符合非人类自然的权利和利益。正如黑海东部事件和其他许多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只要社区将自己视为周围非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关心自己的生命和关心环境可以是一回事。
这些例子证明,人类工具主义并不是人类与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方式。利益冲突可能仍然存在,但扩大自身利益的概念将大大降低冲突的程度。以拉丁美洲土著人的“Buen vivir”概念为例,它借鉴了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宇宙观,“Buen vivir”,即美好生活的概念,正是由于“自然权利”所具有的影响力从而被厄瓜多尔宪法采用,这是首先承认生态系统具有存在和繁荣之不可剥夺权利的宪法。这个概念,以及它所激发的讨论、运动和方法,都表明自然本身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是通过人与自然的联系构成的。因此,人类社区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反之亦然。自然权利不需要概念化,以反对人类在自然中的权利。
社会生态正义将人类生态和非人类生态的关系性存在界定为一个正义问题。本体论的关系理论将社会存在和生物存在都保持为“关系存在”。换句话说,“事物”不是在它们的关系之前,而是在关系之中才存在。“社会”正义必须重新思考,因为人类社会与非人类环境处于“复杂的相互依存”和“横向相互联系”中。“社会生态学”的措辞还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社会”和“社会性”的概念与非人类生态学(财产、实体、有机体、事物、行动体等)和物质性的关系,作为不仅在人类之间,而且在“非人类”世界中的“互动实践”。因为人类社会从来不是完全的人类社会,社会也从来不是纯粹的社会。
本文认为,将正义延伸到非人类世界,是“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 因此,正义的概念应该包括在人类生态学和非人类生态学的关系本体论的扩展词汇中。地方社区在为环境公地而斗争,就像在应对水力发电厂时一样,他们自己用正义的概念来确定他们的斗争。要求为自己伸张正义,与要求为河流以及非人类生命伸张正义是分不开的。从行动理论视角来看,也许有人会说,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框架是由社会底层行动者通过“寻求正义的主体”创造出来的。而且,正如阿莱莫所言,认识论的转变需要道德的转变。换句话说,维持人类生态和非人类生态之间的关系性和跨越性,有着伦理和政治上的意义。正义在探讨这些道德和政治含义时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因为在共同关系中,它“涉及道德的最低标准”。
如果破除社会/自然二元对立需要一个新的词汇,那么一定要越过现有的政治和哲学/伦理概念的既定界限。因此,这种新词汇不仅涉及发明新术语,它还涉及重新阐述诸如民主和正义之类的“旧”概念,以审视超越人类世界的关系。这些旧概念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们是由人类创造并用来分析人类世界内部关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根据关系本体论来重新考虑它们,以促进“一个共同世界的渐进构成”1拉图尔为解决集体问题而对宪法、民主和集会概念的重新阐述。参见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同样,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它表达了人类社区的要求,但它扩展了这个术语严格的人文主义边界,因为它将人类和非人类生态关系界定为一个正义问题。因此,当一个概念表明人类的物质实体和社会存在都与非人类生态密切相关时,其以人类为中心的起源就不一定是个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弗雷泽关于再分配、承认和代表的术语,则社会生态维度相当于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生态系统在一个共同的星球生态系统中以其复杂的、内在的和多维的关系共存。最近,弗雷泽采用马克思“隐蔽的生产场所”2参见《资本论》(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04 页。——译者注思想来解释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背景条件:社会再生产、地球生态和政治权力。用她自己的比喻,可以说社会生态正义是分配、承认和代表的可能性的背景条件,因为它为人类在“地球生态”中(共同)存在设定了条件,这一条件是人类与非人类生态系统、资源和物种的内在关系。共存涉及非人类生命的权利和处于自然界中人类的权利,反对生态系统、栖息地和资源的破坏、退化、污染、毒化和商品化的体制性不公正现象。
五、结 语
由于市场关系扩展到了以前非商业化的生命领域,当代新自由主义扩张型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不公正形式。对资本主义施加的各种新型剥夺形式的抵制,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环境保护主义,这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时代的后唯物的主流环境保护主义根本不同。这是一场围绕当地环境公地组织起来的全球性运动,反对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掠夺,反对强制私有化和流离失所,反对有毒废物和污染,以及最近的反对气候变化,它影响了所有这些问题。这些运动不同于先前形式的环境保护主义,它们想象自己与自然的关系,并坚持将环境和气候问题视为正义问题。
这些运动所暗含的正义观念是多维的和交叉的,因为它将分配、承认和代表的问题并列在一起,并在社会生态学框架中加以融合。面对这种从民间运动重新构造正义的尝试,社会理论不能保持沉默。如果正义是“一项永续性的建构”,“只有通过受害者在社会结构的‘多重性’内创造或执行的间隙才能使人们看到和听到”,3Balibar E., et al.(eds.), The Borders of Justice,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2.那么我们应该转向那些新兴的、被剥夺的不公正的受害者,这些不公正跨越了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态领域。这篇文章追随他们的脚步,拓展了正义的概念。正如土耳其当地对水力发电厂的抵制案例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要求建立一种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其中涉及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权利,以确保其在“错综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发展和繁荣。
社会生态正义概念承认并回应了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中心地位,至少对于地球上的人类生命来说是如此,现代主义的经验在现象学上已经遮蔽了这种关系。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提醒我们:“自然和社会指涉的不是现实的领域,而是一种相当明确的公共组织形式。”4Latour B.,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然而,自然—社会二元性的现代组织,似乎夹在了“前现代”的专断与生物技术、生态危机、混合体、半机械人等超现代化的混乱之间。事实上,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使我们对“横向”的相互联系有了敏锐的认识。在这一历史紧要关头,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生态状况对生态系统和非人类世界的依赖。
社会生态正义理念应该与超越人类/非人类和自然/社会/文化的广泛议程进行对话,通过最近的概念转向物质性、物质和新的物质主义、身体和具体化、对象和事物、混合物种和集体、生态学、生态系统和动物。因此,这项研究应该被视为对人类和非人类生态学关系本体论的跨学科研究的贡献。对非人类环境兴趣的兴起呼唤人类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采取后人文主义的方法,这将影响我们对能动性、主体性、社会性、正义和民主的理解。对政治和社会的重新思考,不仅要求考虑人类之间,也要认识到人类与非中心的正义理论。1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将社会中心主义定义为“仅仅通过参照其他社会过程来理解或解释社会过程的倾向”。这是向正义理论的一个概念性转变,这个理论涉及后人类状况和“人类世”(Anthropocene)2“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是由获得诺贝尔奖的大气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 Crutzen)于2000 年首次正式提出,他认为当今的地球已进入一个人类主导的新的地球地质时代,即人类世。——译者注。社会生态正义视生态环境为人类社会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正义的边人类之间共同生活的过程和斗争。这就需要对环境、社会关系和人类主体性进行横向地思考。
本文试图通过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正义,从而超越以社会为界扩展到非人类生命领域。本文拓展了社会生态正义的概念,这建立在社会底层行动者的物质实践和话语实践以及它们所指涉的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