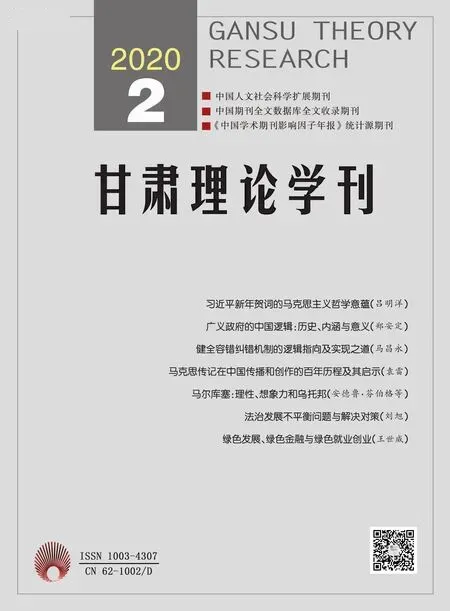马尔库塞:理性、想象力和乌托邦
2020-03-12安德鲁芬伯格包大为
安德鲁·芬伯格(著),包大为(译)
(1.西蒙·弗雷泽大学 技术哲学研究所;2.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杭州 310028)
引言:理性的概念
在美国,马尔库塞完成了两部杰出的著作,《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和《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这两部著作颇为典型地展现了马尔库塞哲学中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dystopian)的片刻。在本文开端,我将简要论述这两本著作中有助于我理解马尔库塞的基本概念,对这些概念的具体阐释则被安排在正文。
本文将马尔库塞哲学视为一种存在论的本体论,并尝试对其进行重新理解。马尔库塞的本体论的根基是一种准现象学的(quasi-phenomenological)经验的概念,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理论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想象力理论。其统一的研究主题则是《单向度的人》当中关于理性的独特理解。
理性与普遍性概念同行。概念对连贯世界中经验的无限变动进行排序。柏拉图哲学就已经揭示对理性的排序工作是不完整的。特殊(个别)缺乏定义自身的概念的完美实现。没有画在纸上的三角形才是真正的三角形,没有白色物体才是真正的白色。基于此,概念是不能化约为特殊的。概念包括先验性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够被不完整或不完满的经验主体所触及。这些内容必须归因于想象力,而不是转瞬即逝的感觉,因为只有想象力具有超越现存状态、向理念形式投射的权力。
马尔库塞认为想象力是理性的一个本质维度,因为想象力引导着主体趋向一个真实的、或许尚未实现的经验世界。马尔库塞将黑格尔意义上的真实和理念的战力理解为否定性的真理。普遍性不是单纯地与特殊划清界限,而是对特殊的“否定”(negate),苛责特殊的不完满性,向主体指示出理念。
想象力是一种心理官能,也是对现实进行创造性洞见的一个源头。马尔库塞将本质性思维归因于想象力,并将本体论嫁接到心理学。弗洛伊德的想象力理论是联接存在论和心理学的桥梁,而《爱欲与文明》则发展了这种联接关系。
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提供的关于想象力概念的内容在本体论意义上是极为重要的。笼统而言,这些内容对生命的肯定是与性欲相关的。因此,普遍性的先验性内容并不单纯是理性,而是基于生物机能的结果。但是生命并不只是一种生物学的范畴,生命的结构及其将主体导向客体的方式,在黑格尔哲学中呈现为本体论的关键。
就像生命,存在是本质的发展进程。存在的生成将存在展示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鸿沟。生命则坚持不懈地试图克服这一鸿沟,因为正是通过将环境摄取至自身,生命才得以生长。这是概念和客体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具体形式。在马尔库塞看来,生命的概念因此调解着想象力的两个层面,即生物学的特殊性层面和本体论的普遍性层面。乌托邦并没有静态地解决这一矛盾本身,而是在促使人类能力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下解决了这一矛盾的建制。
以上是对基本概念的简介。我将阐释马尔库塞在多个层面应用这些概念的方式,涉及了马尔库塞哲学的多个概念:社会的规范概念、在世界和本质的概念、性概念的重构、美学、理性、存在、替代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的技术,以及对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的解释。
生命的逻各斯
马尔库塞在著名的“解放辩证法”(Dialectic of Liberation)会议(London,July,1967)开始演讲的方式是:
“我相信所有的辩证都是解放……不仅是智识意义上的解放,而且是包括灵与肉、人类存在整体的解放……那么当下,所有的辩证是解放意味着什么?这是对压迫性的、坏的和假的系统的解放——不论这种系统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的、心灵的还是智识的系统——解放的力量从这种系统内部发展出来。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因为这个系统是坏的、假的,解放才能够凭借该系统产生矛盾的德性。我之所以有意在此使用道德和哲学的价值和术语:‘坏’、‘假’,是因为没有一个关于更好、更自由的人类存在的客观正当的目标,所有的解放都必然是无意义的——充其量只是奴役下的进展。我相信马克思同样认为,社会主义是‘应其所是’。这种应然性归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它是一种生物学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必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这种生物学的必需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需是几乎等同的,它将遵从生命的逻各斯、人类存在的本质的可能性,不仅精神地或智识地遵从,而且是有机地遵从。”[1]175-176
正如众多该时期的马尔库塞的言论,这个文本必须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乍一看,任何听众都能够理解这一论述: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由一个更好社会替代的糟糕的社会。但是在更深的层次,该论述有更多的意涵,体现在“假的系统”“客观正当”(objectively justifiable)、“应然”(ought)、“生命的逻各斯”等语词。一个“系统”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既是坏的又是“假的”?价值怎样才能被“客观地”正当?一种“应然”在什么意义上才能与“科学社会主义”“逻各斯”联系起来?
首先,客观价值的问题。马尔库塞支持的价值不包括平庸的价值:和平、爱、自由。这些价值之所以被排除,是因为这些价值是一种解放的理性,能够在斗争性冲突中证明对压迫的反抗并构建自由社会。谁会讨厌和平、爱和自由呢?理性的这个概念与这些价值有什么关系呢?批评者指出,在实践和哲学中,对这些价值的简单宣称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价值,也不知道如何在哲学中证明这些价值,我们将裹足不前。
然而,对马尔库塞的方案的这种负面评价公平吗?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早期,马尔库塞所期待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对价值的本体论的证明。马尔库塞在1966年首次关于“哲学的理性”的演讲中,传递出了对加州大学的承诺,即让哲学超脱于哲学家的Lebenswelt的问题和矛盾[2]2。Lebenswelt在字面上指的是“生活的世界”。这个词被马尔库塞早年的老师引入哲学,即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传统的创建者。生活世界是生活经验的世界,马尔库塞将其称为“未被清洗的、未被毁坏的经验”;与之相对的,则是潜伏于自然科学中受限制的经验[2]15。生活世界的经验包括的不仅仅是经验事实,它还充满了在既定经验中能够被察觉到的价值。尽管马尔库塞无法发展一种明晰的现象学的本体论,他对生活世界的引用也不是无意的,这展示了现象学的持续影响(1)马尔库塞关于现象学最明确的讨论参见Herbert Marcuse,On Science and Phenomenology,in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1965: 279-290.马尔库塞赞成并总结了《欧洲哲学的危机》,尤其胡塞尔对基于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存在论的批判,但是反对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从历史和生活世界之行动中抽象而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的主体性”并非是先验的,而是极其物质性的。。
对马尔库塞更深刻思想的解释隐含在其生命的逻各斯的概念中。马尔库塞认为,逻各斯属于一个经验世界,这个世界不仅在事实上更在价值潜能中驱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那么逻各斯又与生命有什么关系呢?古希腊的逻各斯概念指向了言语、理性和人类行为——尤其是技术行为的理性。例如,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引导真正的工匠的是一种逻各斯、一种意义或目的。医生被健康之形式(form)中的逻各斯所引导,诸如此类。逻各斯并不简单地是中立手段的一种外在(extrinsic)目的,而是对手段本身进行了内在塑造。工匠的每一种工具和手势存在于一种属于技艺之自然(nature of the craft)的目的,使用与正当目的无涉的中立手段的则是冒牌货,例如演说家和化妆师,他们受益于对道德合法性和健康锻炼之成就的模仿(simulacra)[3]。
基于对逻各斯的这种理解,先验于现存事物的正是规范性原则和一种“应然”。马尔库塞以他的双维度存在论来描述“是”与“应然”之间的关系,亦即经验事实和价值之潜能的维度。科学的-技术的理性剥夺了经验世界的大部分内容——“第二性的质”。经验主义接受了这种被剥夺之后的经验世界,并将其当作本体论的基础。理解世界的概念也同样被限制为特殊性的总和或平均。马尔库塞拒绝这种“单向度”的本体论。现象学地思考经验,会发现经验遗失在科学束缚中的大量内容,这些内容包括价值和事实的鸿沟。
第二个价值维度的先验性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应然”被理解为现成事物的一个可以达到的潜能。这种潜能的原初模型(model)是有机生长,生长的生物实现着一种被包含于其自身内的潜能。在传统文化中,生命的逻各斯潜藏于技术活动。文化所护卫的模型调节着技艺,使之成为客观的。设计的实现过程,就如同被人类介入促成的生长(growth)过程。在现代社会,潜能并非是自然的,也不是传统的,而是必然被想象力的集合所投射的。
这种投射激活了对更好世界的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发展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人类潜能的实现并不是单纯自发的,而是被一种实践提示出来的,这种实践能够被锻炼并且或多或少变得熟练。人类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实现其自身本质。这种实践内在于社会中,其影响被称为“历史”。
但是历史实践并不是某种指向固定目标的技艺,不是柏拉图所理解的那种逻各斯。那么将人类生活视为趋向于客观目标的运动有什么意义呢?什么区分了“潜能”与旧的变化,包括那种所有人都厌恶的变化?这些的确都是来自马尔库塞之本体论路径的难题。为了提供答案,我们需要理解马尔库塞所说的生活辩证法的意义。
世界和本质
在其早期著作中,马尔库塞提供了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问题的现象学的解读,此后又被大量关于黑格尔和弗洛伊德著作的兼容性阅读所补充。马克思的研究提供了尤其丰富的论述:“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4]520马克思的这一观点通常被决定论地解读,因其表达的是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因果联系。但是马尔库塞觉察到马克思试图在哲学上提出一个关于自然的更有趣的论点,亦即现象学家所说的“世界”。
人类通过在生产中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使得其本质属于世界。这种本质的归属不仅是因果和物质的,更是存在论的。它包含了人之为人、参与某种特定存在方式的意义(2)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解读在马尔库塞早年关于狄尔泰的论文中颇为明显。Herbert Marcuse,Der Problem der geschichtlichen Wirklichkeit.in Herbert Marcuse,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Frühe Aufsätz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8,PP.483-485.。人类与世界之间难分难解的联系,与现代哲学中的笛卡尔主义假设相矛盾,开启了对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提出的本体论路径的哲学反思。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价值呈现为一种存在的维度,而不仅仅是主体性的维度。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的大量讨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继承并革命化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种事物的本质都是其自身的目的(telos),都以某种未经解释的方式潜藏在其表象之后。本质所保存的东西只与外在、偶然的环境发生着联系。以生物为例,它所包含着那种潜能,是它的生长所必需追求的东西。
黑格尔拒绝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藏在表象下的内在本质的形而上学假设。黑格尔所寻求的那种解释路径在于事物两个方面的关系——事物的“表象”、事物与其环境和世界的联系。这使得事物必须与自身同化才能坚持其存在。这种表象和联系的结构必须通过张力和鸿沟产生本质,使得事物在经历突发变化时能够再生产自身,并催生出本质发展的内在源泉(3)关于马尔库塞对黑格尔著作的讨论,可参见以下著作:Herbert Marcuse,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Boston: Beacon,1963; Herbert Marcuse,Hegel's Ontolog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city,trans.Seyla.Benhabib,Cambridge,MA: MIT Press,1987; Andrew Feenberg,Heidegger &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New York: Routledge,2005.。
因此,黑格尔保存了亚里士多德的核心观点:他们都基于本质的概念,认为潜能不是一种由主体强加的外在的目的,而是归属于事物的自然/属性(nature)。但是二者又存在一定的差异:黑格尔将事物与其表象和环境联系起来,进而通过一种只是与表象和其它事物发生偶然联系的内在本质来推翻亚里士多德关于作为“物质”(substance)的事物的概念[5]98-99。
在与海德格尔决裂之前,马尔库塞以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存在”(being-in-the-world)来解读黑格尔的本质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下,世界是具有意义的整体,故而是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本质对象;世界并非与主体性无涉,而是在本质上参与了主体性。正如意义和对意义的理解的难解难分,主体和世界的客体在现象学意义上也是难以分割的。
通常被科学抽象的现实方面被世界所容纳,这些方面是意义、价值和情绪。许多哲学家认为这些方面是完全主观性的设定,但是海德格尔不这样认为。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话语中,人类的存在“透露”或“揭示”了意义、价值和情绪中的世界。这些方面并不是被事实所强加的,而是照亮了事实。通过透视(perspective)概念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这一看法。透视并没有创造已被显现的东西,而是使得现实能够被觉察。海德格尔将这个概念延伸至我们与世界的一切关系,否认了从外部解释透视的那种知识论存在——上帝视角(god-like view)的外在存在。
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着一个意义和因果性的鲜明区分,这可能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哲学发展的结果。狄尔泰和新康德主义比较了科学模型的解释和解释学(hermeneutic)的阐释。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是一次解释学的建构,而不是事实的集合,不是意义的结构。海德格尔认为,主体不应该笛卡尔主义地被把握为纯粹的意识,因而本体论地依赖于物质现实。海德格尔将世界言说为指引(reference)意义的系统,主体则在本质上介入了世界中的客体。他举了木匠作坊的例子,作坊中存在着大量内在相关的工具,这些工具不仅互相指引,而且指引着主体在劳动中实现其存在。与新康德主义不同,海德格尔认为,意义在实践中是活的、发生的(enacted),而不是单纯的思辨内容。因此,通过引入第三种存在主义的维度:活的经验中行动着的主体-客体,海德格尔转变了主体性意义和客体性事实的区分[6]175。
“在世之存在”所提示的统一性包括了宏大总体性中的主体和客体。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讨论的主体和客体并不是机体和物体。作为物质,他们的关系是因果和随机的。物质的主体和客体能够轻易地脱离对方。与之相反,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层面共存于一种本质关系,这种关系被发生的意义和理解所操持。拿起锤子的木匠,通过对主体性层面的意义的理解,使工具的、客体性层面的意义得以发生。这种关联使得主体和客体在“在世之存在”的统一便于理解。因果联系的事物分散于偶然关系之中,然而理解和意义要求彼此的共存。
马尔库塞在这种现象学的意义上解读了黑格尔的本质概念。本文将追踪马尔库塞在其黑格尔主义变革中承接自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4)作者对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关系的解读,可参见Andrew Feenberg,Heidegger and Marcuse: On Reification and Concrete Philosophy,London: Bloomsbury Press,2013.。在马尔库塞看来,黑格尔以一种笼统的本体论模型看待生命。但是一旦脱离了世界,生命无法被充分地理解。例如,人类、客体及其环境,本质上通过复杂和必然的劳动形式参与到对方之中。这并不是偶然的关系,即我们通常在物理客体中构想的关系,而是一种由相互关联的存在所提示的内在关系。
因此,生命具有一种近似于现象学的世界概念的结构。生命作为主客体、有机体与环境之统一的存在,围绕着主体而被建构出来。马尔库塞以树木为例:“正是树木自身(我们在此指涉的是其实体性)让自己穿行于环境,而不是环境扑向树木。”[5]99这个描述与海德格尔的生命概念是一致的,立足于海德格尔对雅各布(Jacob von Uexküll)对周围世界(Umwelt)和周遭(Umgebung)的著名区分的本体论转述:“有机体并不是独立于自身权利因而自我调适的东西。相反,在每一个实例中,有机体都是将特定环境调适到自身内部(self)。有机体之所以能够将环境调适至自身,只是因为其开放性……归属于其本质……”(5)参见Martin Heidegger,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Finitude,Solitude,trans.William.A.Ma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Von Uexküll认为有机体及其生态位置是本质关联的。有机体并不是笼统地适应自然环境,而是从有限的自然中选择它的环境和世界。
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哲学中,主体和客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事物,而是在环绕主客体的统一活动中的分叉(biforcations)。马尔库塞总结道:“有机的统一……首先将一个世界融入另一个世界……允许自身作为世界而发生。”[5]13本质描述了这个自我再生产的统一,当本质通过实现潜能和“呈现”所促成的变化而感知到自身,进而将自身构成客观的、意义的。
存在论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尔库塞有机会阅读和思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存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抽象变得具体。事实上,黑格尔的劳动理论已经提出了一个比海德格尔现象学论述更为具体的关于“在世之存在”的视角,而马克思又增加了新的因素:需要(need)。主客体居于需求和满足的关系之中。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是“本体的”“本质的”,“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4]242,“生命模式”(mode of life)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驱动力中介着主客体的统一。
但是,马克思又是怎样在其“世界”图景中将主客体两个层面统一起来的?人类及其需要难道不是处于对自然的偶然关系中,是一种用以满足的工具吗?劳动和原材料之间的本质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只有在存在主义的理解模型中把握需要和满足,主客体的统一才是有意义的。需要揭示了在世界之中才能满足自身。因此这是一个理解世界的特殊方式,而不是一个单纯生理学(physiological)的视角。感觉是劳动者遭遇作为客体和劳动的事物的工具,这并非只是物理的遭遇。马克思在“实践中的理论家(theoreticians)”的意义上似乎意指主体能够从对象中提取出意义。事实上,劳动的事实已经提示出了意义,因为劳动并不是瞬间与世界遭遇,而是通过满足自身的潜能遭遇世界。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向获得解放的人类揭示的世界将会是一个更为富足和美丽的世界,而不是参与到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异化的世界。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及其世界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是思辨的。需要和满足之间单纯理论的联系让他颇为不满,现实中诸多需要难以得到满足的那种哲学观点值得称道吗?需要和满足必须实践地和理论地统一。主客体的统一带来一个规范,因为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能够或多或少被实现。当这种关系被完全实现,人类将能够表达自己的潜能和本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无法实现的。异化通过扭曲人类与自然界和自身本质的关系阻碍了这种关系的实现。在一个异化的社会,人类及其所依赖的环境等方方面面都被损害(mutilated)了。
从揭示意义这一点可以看出,马克思有一种现象学。事实上,马克思需要一种现象学的区分,针对存在意义(遭遇和发生的意义)和客观存在。但是,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区分无法在现有哲学中被构想出来。在马尔库塞1932年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评论中,他非同寻常地解读了马克思的“类存在”(species being)概念,这一概念或多或少补足了这种现象学的区分。马尔库塞认为,人类之所以是类存在,是因为人类能够识别存在的“类”,进而能够构想出普遍性的概念。“作为具体的人类‘生命活动’,劳动的根源在于人类的‘类存在’;劳动的前提是人类关联客体之‘一般’层面及其内在潜能的能力。”[7]96这就是“实践理论家”的意义:普遍却也特殊、现存却也潜在,首次向感觉展开了。
在《哲学的理性》中,马尔库塞通过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类的外在概念构想出了这些观点。马尔库塞写道:“哲学所追求的真理如果是关于人类普遍的理论,那就是一个正确的理论……[这种]哲学追问指向的是人类能够完全实现其具体人类能力和愿望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客观的,因为作为(潜在的)理性动物的‘人’发现处于这样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使得一般概念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有效性(general validity)。”[2]4总而言之,人与世界形成了统一整体,其最佳架构(configuration)将通过实现人的理性本质、他(以及她)的能力,最终形成普遍性,从而与人和物质的“可能性”、潜能发生关联。
此处呈现出马尔库塞出于“客观可证性”拒绝一种“虚假系统”的最终的本体论基础。理性本身就是问题,这一问题使得真理和客观价值进入了对社会的评价。统一整体的构造,即人类遭遇自然的“系统”,或推动着、或阻碍着作为人类最高潜力的理性的传播。
理性为什么如此重要?不是因为马尔库塞接受了知识分子对纯粹思想的热爱,而是因为理性是哲学传统命名自由遭遇事物本质的名称。这种遭遇既超越了主体的本能反应,也超越了被理解为简单事实的客体的局限性。这是世界概念的最深刻含义:获得普遍概念意味着主体能够自由、全面地遭遇其世界。因此,“理性与自由完全是一回事”[2]8。
马尔库塞认为,对理性的辩护属于“真理的存在论意义”[8]51。真理不仅仅是一个认知事实,而且是道德地、存在论地介入知识的主体。如果某个系统阻碍了理性基于自身实现的发展潜力,那么该系统就可以在存在论层面被认为是坏的、“假的”。这正是发达资本主义的状况。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任意限制人类的发展,而在此很早之前,发达资本主义就已经消除了稀缺——这种稀缺曾经使得理性的全面绽放成了一小撮精英(a small elite)的专属财产(exclusive property)。因此,为了实现潜能,就必须对整体进行激进而又整体的变革。
马尔库塞的政治学直接来自其关于本质的规范性概念,规范性出现在经验的结构中。潜力的确是一种理论建构,同时也呈现出对暴力和破坏的消极反感,对团结和乌托邦梦想的积极态度。
因此,经验不仅仅是对特定事实的理解,即所谓的“第一性的质”(primary qualities)。生活世界中“原初”的日常经验并未对此做出区分。价值和事实在日常感知中融合为一体,二者并没有像在以研究为目的的科学重建的经验中那样被分割开来。因此,哲学逻各斯“是一体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2]11。
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为了把这件事说清楚,我们必须考虑晚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和黑格尔的生命概念的弗洛伊德式的重释。在《爱欲与文明》中,通过弗洛伊德称之为“永恒爱欲”(eternal Eros)及其“永恒的对手”——死亡本能(Thanatos)的关系,马尔库塞提取出了一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9]92马尔库塞的观点不仅涉及经济,更涉及文明激进变革的心理条件。正如马克思扩大政治概念以包括经济那样,马尔库塞则扩大政治概念以包括弗洛伊德开拓的精神维度。前文探讨的抽象本体由此获得了社会的、心理学的具体内容。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是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版本。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曾提示过这种综合的可能性,而马尔库塞则通过将这一综合纳入其现象学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让这种可能性走得更远。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将探究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综合的历史和哲学的背景,从而在下一部分分析马尔库塞本体论的结果。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表现出对启蒙主义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的拒斥,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替代方案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最初由小型家庭团体所组成,而这些团体的统治者则是父亲,他们为了自己的愉悦独占了女性。逐渐被剥夺了权力的兄弟们反抗和杀死了父亲,获得了曾经拒绝过他们的愉悦。但是他们深感罪疚,并内化了父亲对他们的压迫。这种内化的罪疚感成为文明生活建立的基础,以弗洛伊德所处时代那种更为压抑和神经质的人类而告终。这是弗洛伊德在文明维度对被压迫者以精神病痛和暴力形式复归的解释。
弗洛伊德理论中有一个结构性基础。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基本的驱动力,生的本能和死亡的本能,爱欲(Eros)和死亡本能(Thanatos)。爱欲渴望将社会世界的碎片创制为更大的统一体,死亡本能则力求回归无机物,因而具有破坏性。性只是爱欲的一个方面,因为爱欲本质上包含了确认-生命的一切人类冲动。文明进步带来的不断强化的压制,升华了情欲(erotic)的能量,并使之在艺术、宗教、友谊和非性之爱中得到了表达。
爱欲和死亡本能在弗洛伊德式的心灵中是相互作用的。爱欲试图掌控死亡本能,以便将其破坏性能量应用于生命。爱欲将破坏性力量引向超我(superego)和自然,这正是道德和技术的基础。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爱欲和死亡本能为掌控心灵而展开的竞争变得愈发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爱欲并非总是掌控着死亡本能。与肇始于启蒙主义的自由乐观主义相比,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末日论的,但是他对科学世界观的坚持使他错失了爱欲概念的激进内涵。
马克思的理论开始于生活在部落社会中的人类,其特点是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享。这种社会既不知道私人财产,也不知道由于资源稀缺而引发的竞争。当然,在这种贫困和联系紧密的社区中,人的个体性必然是很低的。随着农业和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到来,社会合作开始消退,人的个体性得到了发展,最终形成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的现代个体自由,以及对真正利益的认知。但是在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享受个体性的发展,这促成了一个垄断大多数人口劳动果实的统治阶级。另外,社会和技术进步成为一种可能,最终形成了现代资本主义。
工业革命产生了协作劳动的无产阶级,从而能够发展出高水平的个体性。这是第一个不仅能抵抗剥削,更能够理解剥削的工人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将是最后一个阶级社会,很快就会被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态所取代,这个新社会的基础是高水平的个体性与合作,而不是竞争。这一结果的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极大丰富。在马克思那里,历史发展的模式是辩证的:没有个体性的合作被没有合作的个体性所取代,共产主义社会将早期生命形态各自的优点融合于一个基于合作的个体性(cooperative individuality)的社会。
弗洛伊德的理论终结于迅速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马克思的理论的总结则有待于在遥远的共产主义未来,那时社会和民族的冲突将得到解决。弗洛伊德的理论建立于心理学,马克思的理论则建立于经济学,二者都反对民主资本主义制度下持续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二者如何能够和解?为什么会有人尝试着调和这两种极为不同的世界观?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同寻常的状态中找到。第二国际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支持除俄罗斯以外的动员战争。民族主义显然是一种比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更强大的力量,即使对工人来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所预测的革命并没有发生在富裕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6)参见https://digilander.libero.it/moses/gramsci05.html,accessed Sept.3,2018.葛兰西在1917年的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那一代革命者的震惊。。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他们再也不能否认现存无产阶级与他们理想的革命主体之间的巨大鸿沟。谁能对此作出解释?
马克思曾假设一定的条件使得工人阶级能够理性地理解其所处的状况,并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一假设显然源于旧的自由主义的进步叙事,只是在马克思的版本中通过引入革命性突破而略微进行了调整。但实际上,马克思所预测的工人阶级的理性的觉醒,却被针对想象的敌人的暴力狂热之非理性战胜了。很显然,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这需要一种心理学的解释。但是,弗洛伊德的解释却阻隔了未来,并且几乎让人绝望,而使弗洛伊德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相恰则需要大手术。
马克思的理性主义的无产阶级观取决于他的一个看法,即最终驱动人们的是物质需求。无产阶级的物质需求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中无法得到满足,这个事实本应激发起革命。但是,马尔库塞意识到人类生活不仅被物质需求驱动,同时也被欲望驱动,欲望的结构更为复杂,更不容易被理性主义地解释。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的理论视为起点,但是却增加了马克思的历史观。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在遭遇了顽固的现实之后,婴儿对快乐的追求随之被改变。致力于追求愉悦的力比多的能量受到抑制,自我(ego)才建构出适应现实的能力。快乐原则屈从于现实原则,这是文明可能性的条件,这带来了很多结果。生殖器的性行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身体已经被去性化(desexualized)以便更适合于生产和社会任务。对追求快乐的道德限制升华了力比多的能量,创造出了更大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成就,这就是人类心灵适应现实的意义所在。
但马尔库塞会问:现实是什么? 现实的本质是永远不变的吗?这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我必须适应的那种阶级社会的现实,与原始共产主义的部落社会的现实、基于资本主义成就的未来发达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弗洛伊德并没有领会到现实中的物质的不连续和转变。当然,弗洛伊德意识到物质的发展,但是却无法看到在某个超越点上,社会变革将会带来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关系的质变。社会发展的这些差异与不同的心灵结构有关,而不仅仅是不同程度的压制。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的历史化是马尔库塞的综合的关键。
马尔库塞同意弗洛伊德所说的文明依赖于压制,但问题是何种程度的压制?这个答案取决于物质匮乏的程度。在贫困的阶级社会中,个体必须克制欲望,因为满足需求的手段通常是匮乏的。因此,维持社会秩序(civil order)所需要采取的内在、外在的压制程度通常是很高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能够生产如此多的产品,因而绝对匮乏不再成为首要的压制理由。相反,社会组织产生的相对匮乏需要持续的压制结构,直至这一阶段被技术性地淘汰。因此,马尔库塞对他所说的操作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与弗洛伊德的现实原则加以区分。现实原则确定只有技术进步才能克服对愉悦的自然限制,而操作原则说明社会变革可能消除社会建构的束缚,操作原则将个体与先进资本主义创造的人为匮乏相适应。
根据现实原则所要求的低限度禁欲与操作原则所要求的过多欲望的区别,马尔库塞区分了必要压制和过剩压制。在不威胁文明存续的前提下,可以免除过剩压制所代表的过度。故而,革命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概念化为剩余压制和相对应的操作原则的目的。这种新的革命概念需要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心理和可能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心理进行深入探究。
想象力
核心问题与幻想或想象的本质有关。在阶级社会中,幻想与不正当的性和艺术有关。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两者都是爱欲的表达,都位居当代“现实”之外,因而被当作调整的对象。自我(ego)必须规训幻想,以便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生存条件。随着匮乏的消除,现实开启了对这些方面的容纳。
必须避免这种观念简单地限制某种关于性高潮的话语,这是许多评论家所犯的错误,他们只看到在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中的回归。事实上,马尔库塞在人格结构层面重复了马克思在其历史哲学中引入的辩证发展的模式。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并没有回到婴儿期(infancy),而是重新发现(recapitulation)早期文明阶段成年人人格中的一些积极层面。同时,马尔库塞也没有减少性的自由。他认识到除了性,文明生活还涉及很多其他内容。爱欲的胜利不会只带来性解放,而是会超越性,影响劳动、技术、创造性活动和社会关系。
《爱欲与文明》提供了四种不同的假设:
革命将身体从去性化的劳动投入中释放出来,身体的整个表面都将被色情化,成为去污名化(de-stigmatized)的性行为的任意形式,这些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则是被谴责的。
与现实的技术关系对艺术和想象力的排斥,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克服。
融入想象力的新的理性概念将伴随着带来革命的社会经济变革,这种新的理性概念将被识别为“真实的”自然之美,以及真实的人类和社会的潜能。
存在自身将得到转变,世界、“真实”,将会被呈现为色情化感知的审美对象。
下文将评论马尔库塞的革命概念的四个乌托邦后果。
性欲。婴儿的性并没有被专门化,而是涉及了整个身体,这种多形态(polymorphous)性行为与现实原则相冲突。生殖性行为对于成年人而言是可接受的欲望渠道,将身体释放给了劳动。与劳动中的身体相伴随的是生殖性行为的特权和父权制的一夫一妻制家庭(monogamous family)。这些结构是历史偶然的,有赖于心理和社会对匮乏和阶级统治等条件的适应。一旦这些条件被消除,其影响也将被克服。因此,革命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生活,也会影响个体理解和持存其身体存在的方式。
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变化只有在他所处的时代才能够被理解为双重挑战。《单向度的人》和《爱欲与文明》批判了作为消费社会附属物的性解放,并且对性变态(sexual perversion)进行了积极的重新评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一种转变,从崇尚劳动和禁欲(renunciation)的社会转向消费社会——这种社会在消费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从旧道德束缚中释放出了性欲。但是,从压制中获得的释放所关注的是个体消费和生殖性行为,远未达到一般的社会解放。这个限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利用这种变革,通过力比多的投入将个体更为紧密地与系统捆绑起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此称之为“抑制的去升华”(repressive desublimation),在巩固现存社会的条件下,部分力比多能量回归到一般的满足渠道。
《爱欲与文明》的观点更具有反传统性(iconoclastic)。在弗洛伊德看来,性变态必须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幻想或被秘密地追求。性变态展示了与人的再生产和家庭生活无关的性行为,因而与文明生活相对立。但是马尔库塞认为,随着现实原则的转变,最初的多形态性行为可以回归,幻想也将被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库塞在1955年为性虐(sadomasochism)提供了合理性的辩护,其中关键的段落如下:
性变态这个术语涵盖了本质上有着不同源头的性现象。同样的禁忌被放置到与文明、压制性文明——尤其是与一夫一妻生殖霸权(supremacy)不相容的本能的表现上……在同一种性变态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差异:在一个自由的力比多关系和党卫军(SS troops)行为中,性虐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些非人的、强迫的、暴力胁迫的(coercive)和破坏性的性变态形式,看起来与压制文化中人类的一般变态存在相关联,但是性变态具有与这些形式完全不同的本能根据,这一根据也许在与更高层次文明相恰的其它形式中能够表达自身[10]203。
今天我们很容易辨识出马尔库塞在这段论述中的观点。附着于非传统性行为的羞耻已经消退,反而当下的广告时常含蓄或并不那么含蓄地提及性虐活动,这在1955年的礼貌社会(polite company)中是难以启齿的。旧金山的精神在最近已经广泛传播,并最终合法化了几乎所有的性行为形式。但是马尔库塞的论点并不是关于公民权利或宽容,这在当时必须看起来是熟视无睹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即各种性表达的形式所暗示的存在方式,何以成为人类以及何以拥有身体。
马尔库塞在1948年对萨特《存在与虚无》的评论预示着这一结论。马尔库塞指出,在性欲中,人不再被迫承担具体化意识和具体化对象之间根本分离的角色。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鸿沟在爱抚中被克服,爱抚将身体从社会世界的工具系统中拯救出来,并将身体显示为纯粹的“肉体”(flesh)。“‘渴望的态度’(attitude désirante)从而揭示了一个世界(及其可能性),在这个世界中个体与整体是完全和谐的……”[11]150萨特的本体论在原则上排除了作为一种自由象征的性欲,而马尔库塞则认为,性欲通过革命是可以被实现的。
美学。马尔库塞指出审美的概念是模糊的,跨越了感知和艺术表达之间的界限。艺术呈现出理想形式的感性物体,取消了与其本质相矛盾的偶然特征。美学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认知能力。美学提供了“一种综合,重新组合被扭曲的人性和自然中的碎片。这种回忆(recollected)的素材是想象的领域,它已被艺术中的压抑社会所认可”[12]70。马尔库塞认为,在一个非压抑(non-repressive)的社会中,理性不再屈从于适应和生存,而是能够在现实中实现美学,这成为马尔库塞在社会主义社会重建科学和技术的计划的中心论题。
1969年,在《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中,在对新左派的思考中,马尔库塞回归了这一想法。马尔库塞认为,新左派并不仅仅是在通过激进政治观点提倡替代方案,而是在预示着与世界的另一种存在关系,主导这个世界的则是爱欲。
美学的生活世界(Lebenswelt)似乎是暴力现实的重要替代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同样将美学引入了技术基础,认为人类并不像动物那样,与自然的关系完全被需求所决定,“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163。
马尔库塞并没有期待新左派发起革命,而是将新左派视为按照“美的规律”的世界——而非按照利润的世界——的可能性的鲜活证据。
理性。马尔库塞对艺术和性自由的捍卫并没有构成对理性的拒斥,而是对新的“力比多理性”形式的投射,使之不再局限于操作原则。“爱欲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理性”[10]224。马尔库塞认为要扩大理性概念,使之不再局限于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新的理性概念将具备能够定义第二维度的想象力的方面,这个维度就是事物固有的潜能。“爱欲唤醒和解放了有机物和无机物中真实存在着的潜能——真实的,但是在非情欲的现实中被压制的潜能。”[10]165-166
如上所述,对潜能的富有想象力的理解并不是独断的,而是对以生活为模型的增长概念的回应。生活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和繁茂,在那里生命能够实现其潜能。理性通过在事实中寻找的事例和指示来建构一个潜能的观念,这在生物事例中并不是一个问题。诸如健康或成熟的标准,可以通过客观地挑选事实来支持潜能的概念,但是在历史事例中却更为复杂。什么才有资格作为民主、教育、沟通和家庭生活的潜能?再一次地,答案取决于发展的概念,但是标准又是什么呢?确认生命的观念总是太过模糊,无法解决复杂的争论。马尔库塞认为哲学和艺术可以提供指引,任何被进步标准介入的历史斗争都是前设的,但是最终历史也没有产生诸如生物学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潜能的最后一句话必须留给民主来决定。
马尔库塞对潜能的讨论借鉴(draws on)了黑格尔对本质观念的重构;另外,马尔库塞认为潜能的投射取决于想象力。因此,只要本质是理性思考的对象,理性本身就必须具备想象的能力。但是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灵感念中,想象力植根于爱欲。一个新的理性概念将在人与自然的第二维度的基础上评估社会安排和技术。融合想象力和理性的“力比多理性”将揭示一个情欲的现实,这种现实以美的形式呈现自身,并包含等待实现的潜能。这当然仍旧是一种理性形式,但却是一种不那么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理性形式。
存在。常识告诉我们现实是事实的总和,是我们在孤立现实中感知世界的事物。我们并不会把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视为它们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将其视为心灵的状态。存在独立于主观性。这种常识的存在观与科学是一致的,但是却忽略了大量的经验内容,包括弗洛伊德的爱欲和死亡本能类别的客观关联。在马尔库塞看来,这些被忽略的关联不仅是主观驱动力,更反映了存在自身的多个方面。
正如马尔库塞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本体论改造,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也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基础。马尔库塞认为存在在历史中是极为重要的(7)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绝对历史主义”的角色的分析,可以参见Andrew Feenberg,The Philosophy of Praxis,London: Verso,2017.,他将一种历史化了的生物驱动力观念引入一种如同“在世之在”的东西[13]1。这种做法是模糊和复杂的。这将基本驱动力视作现实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方面。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爱欲转化了存在。”[10]171
马尔库塞明确地将弗洛伊德引入了自己的准现象学(quasi-phenomenological)方法中,认为“似乎可以将一般的本体论意义赋予[弗洛伊德的]概念”[10]125。他认为现实的情欲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公开,它使得想象力优先于既定事实,使得大自然呈现为一个可能的领域,本质上与人类对美、和平和爱的需求相对应。参照马克思对需要的讨论,马尔库塞以扩大的理性概念赋予这些价值以形式和意义。这个新的理性概念隐含着一个规范性的层面,就主-客体关系那种满足人类需求的架构而言,这的确是有效的、“真实的”,正如马尔库塞在“解放辩证法”会议中的论文所说。
弗洛伊德也许会反对人类需求在界定现实本质时的特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然科学所界定的现实是与人性无涉的。马尔库塞对现实的本体论角色的强调似乎是将现实融化在意识中,但是这并非是马尔库塞真实的观点。马尔库塞追随胡塞尔的解释,认为自然科学的结构和概念包含了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不是现实溶解到意识中,而是意识早就存在于我们用于现实的东西了,同时存在于界定科学理解的那种世界的基本范畴和类型当中。[14]虽然被科学自然主义理解的存在似乎独立于意识,但事实上仍然以意识为前提。物理现实因而与主观性交织在一起,并没有先验于历史。马尔库塞认为:“(物理的和历史的)客体性的两个层面或维度是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客体性的历史层面永远不可能被消除以至于只剩下‘绝对的’物理层面。”[15]218
因此,将经验的各个层面视为幻觉既不符合经验的科学表达,也是不合理的。科学本身有着更深层次的基础,因而无法定义存在,而马尔库塞试图在弗洛伊德那里寻找不同的资源。马尔库塞的本体论基于弗洛伊德的原初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理论,但是却超越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被本能驱动的存在本身。婴儿起初的经验是“通过吞噬环境,综合自恋的自我(ego)与客观世界”[10]168。这种看法见之于弗洛伊德对原始心理状态的描述中,为马尔库塞提供了一个线索,看到元心理学隐含着一个有待开发的本体论。爱欲以世界之本色揭示了世界,而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与人类欲望关联的。
自恋也许包含了一个不同的现实原则的胚芽:自我的力比多贯注(libidinal cathexis)……也许变成对客观世界的新的力比多贯注的资源和储备(reservoir)——将这个世界转变为一个新的存在模式[15]169。一个新的存在的基本经验会改变人类的整体存在[15]158。存在被经验为满足感,通过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使得人的满足不再伴随着暴力,并同时成为自然的满足[15]165-166。
马尔库塞的挑战是让自恋的延伸概念和“人类的整体存在”或曰文明化的生活协调起来,必须让爱欲指向非压抑条件下的更高的文化目的,马尔库塞将此称之为“自我升华的爱欲”。马尔库塞相信自己能够通过一个简短的评论来支持这个观点,在这一评论中弗洛伊德认为,升华涉及了在附着到新客体之前对力比多能量朝向自我的原初的重新定位。无论弗洛伊德是否正确,马尔库塞的确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以便支持一个“非-压制的升华模式,这种模式来自力比多的延伸,而不是力比多的约束性偏转(constraining deflection)”[15]169-170。这一假设使马尔库塞摆脱过剩压制得以重构文明的条件,这同时解释了马尔库塞的情欲本体论的心理学条件(8)关于这一假设的重要讨论可参见Douglas Kellner,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chapter 6,pp.183-187; Edward Hyman,Eros and Freedom: The Critical Psychology of Herbert Marcuse,in Marcuse: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eds.Andrew Feenberg,Robert Pippin,Charles Webel,South Hadley: Bergin & Garvey Press,1988.。
马尔库塞的看法是完全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爱欲与文明》的内容很少涉及心理学到本体论的演进,马尔库塞在该书中只是提到由于主要的本能同时属于有机物和无机物,因而这意味着一种本体论。[10]107在我看来这个不合逻辑的推论太偶然和突兀了。马尔库塞或许在写作过程中的某个片刻决定直接忽略针对心理学不必然具有本体论含义的反对意见。马尔库塞追随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1944年也提出过相似的主张,认为感觉和激情“是对存在(自然)真正的本体论的确认”。
这种忽略有一定的来源和根据,即在社会现实中对哲学的抽象范畴的元-批判(meta-critical)的重建。这一方案开始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复兴,被法兰克福学派所延续。马尔库塞对自恋的论述提出了德国古典哲学试图在纯粹理论层面克服的“主客体的背反(antinomy)”。马尔库塞通过弗洛伊德的资源将主客体概念带回到尘世,并继续将主客体的分离视为有待解决的哲学问题。
马尔库塞将主客体的分离及其解决方案投射到弗洛伊德的驱动理论上,爱欲和死亡本能因而作为现实——而非心理的结构原则进入了世界。美,正如经验的客体所表征的那样,是情欲驱动的客观联系,发挥着哲学的主体的角色。确认生命(life-affirming)的社会世界的成就因而不再只是被规范性地证明是合理的,而是解决了哲学的根本矛盾(主客体的背反)。马尔库塞甚至认为康德原本应该想到一种在时空直观之外的关于美的直观形式。[13]32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将论述作为死亡本能之关联的技术的角色。
技 术
即使与美作为生命本能之对象相关联的死亡驱动的对象没有得到马尔库塞的描述,破坏和暴力还是显而易见获得了重视。但是技术概念所提示出来的与破坏本能相关的联系则更让人惊讶,技术是马尔库塞回应海德格尔的另一个概念。
在晚年作品中,海德格尔将现代的崭露模式(mode of revealing)描述为“技术”。海德格尔在此意指世界将自身呈现为技术资源的巨量总和。马尔库塞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大致相似,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写道:“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它就会限制(circumscribes)整个文化;它投射出一个历史总体性——一个‘世界’。”[15]154但是与海德格尔不同,马尔库塞将相当薄(rarefied)的“架构”(enframing)概念视为存在的一个历史阶段,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达,他转向弗洛伊德来解释技术暴力之主体的存在模式,对技术控制的痴迷不足以解释这个无数生命毫无意义地死于战争,由互相破坏来维持和平的这个世界。技术控制与死亡本能是不可分割的,必须被大量地投入到生命的情欲控制,以便实现人类的繁荣(9)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理论中弗洛伊德和海德格之间是一种隐秘的关系。参见Jürgen Habermas,Antworten auf Herbert Marcuse,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1968,pp.10-11.。
《论解放》完成于法国五月风暴的阴影之下。这个事件,如同新左翼,预示了自由的意识。五月风暴提出“对权力的想象”(L'imagination au pouvoir),这个口号极其接近马尔库塞的关注点。这导致当时世界上的年轻人似乎都已经成为了马尔库塞的门徒,但事实上他并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只不过是他回应发达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意图的一种巧合。马尔库塞发展了他的老观点,即一个不那么压制的文明和更多的具体性,他认为出现了一种与一个审美世界而非工具世界相关的“新感性”(new sensibility)。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看法,而是关涉了一种情感和实践结构,乃至一种存在论的政治。这种政治的一般化如果发生了,那将带来一场极其深远的革命,超出迄今为止所有的构想。
马尔库塞的核心立场是爱欲影响下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当然,这个观点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方济会修士与鸟类的谈话,而是寻求与有利于人类生活的自然潜能之间更和谐的关系。“科学和技术必须转变当前的方向和目标,必须根据新感性——生命本能的要求——而被重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谈论革命的技术和科学想象的产品,才能摆脱剥削和劳作自由地设计人类的普遍形式。”[12]69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综合最终聚焦于作为本能表达的技术设计。在临终之前,马尔库塞识别了环保运动中的爱欲权力,他将此解读为生命本能的复苏,针对的是现有技术所体现的破坏性本能。
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在经验中得到哲学的验证,而且在生态学上得到科学的验证。为主宰自然而开展的侵略斗争摧毁了“被扭曲和压制的自然之力,这种力量原本可以支持和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12]66。拯救作为人类生活世界的环境的斗争真正联合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对自然的]冒犯和压迫意味着人类对抗自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行动,伤害自然的一些客观属性——这些属性对生活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正是基于这个客观前提,人性能力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紧密相关——‘真理’不仅在数学上而且在存在论意义上都归诸自然。人的解放(emancipation)包含了在事物和自然之中承认这个真理。”[16]69
结论:乌托邦的功能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不同寻常的综合遭遇过激烈的批判,许多批判者认为马尔库塞没有忠实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原则。但是,我将在结论部分回应另一个更为基础的批判,这一批判针对的是乌托邦计划和非压制社会的虚假性(implausibility),难道这些观念至多不过是对人性过分乐观的看法吗?或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只是围绕着虚假联合借口的早熟的同质化社会吗?
诚然,马尔库塞对非压制社会的想象表现为引发这种批判的一种挑衅,他试图经受住对人类潜能的冷酷评价。马尔库塞认为他生活在一个病态的社会中,他赞同弗洛伊德的观察,“我们可能没有理由被诊断成这样:在文化冲动的影响下,一些文明,或者一些文明阶段——或许整个人类——已经变成了神经质?”[9]91发现这个诊断需要面临一些困难,解决困难只能通过两条路径:对症候的反乌托邦夸张,用于判断现状的对乌托邦式健康的描述。当然,马尔库塞的意图是说服读者,但是他似乎已经相信将读者从自鸣得意中恫吓出来也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马尔库塞的修辞策略不应该分散读者强烈和明智的观点,这些观点以及立场是对马尔库塞的支持。
马尔库塞完全了解反对自己的基本观点。为了反驳这些观点,马尔库塞需要确认个体性的可能性以及非压制社会中的矛盾。另外,他必须假设一个学习过程,使得人们能够趋向于这样一个非压制的社会。《爱欲与文明》的最后一章包含了对这些问题极有说服力的反思。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所关乎的只是度。很明显,回归婴儿愉悦的原则是与文明生活和生活本身不相容的,但是马尔库塞并没有呼吁让人们回到子宫,也没有让人们回到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婴儿状态。这些稻草人论点(straw man arguments)并没有击中马尔库塞的观点。马尔库塞明确要排除对非压制社会概念的这种解读。在此意义上,他的非压制社会与现存压制社会是连续的,确切地说应该被称为“更少压制的社会”(less repressive society)。
这种温和版本的理论被马尔库塞对全面革命性突破(revolutionary break)的频繁启用所遮掩,但是,这种突破只会导致压制程度的快速下降,而不是彻底废除。攻击(Aggression)不会消失,但是会被爱欲更好地管控起来,这在本质上将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的理论嫁接了起来。尽管对马尔库塞的这种解读使他更为趋近弗洛伊德,但是二者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马尔库塞的革命性突破变革了人格结构,从而减少了攻击和压制,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不可能的[9]90。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会带来压制的增加,以及神经质症候的扩散。
马尔库塞认识到人类个体性的这一事实,即需要一定程度的镇压。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指出,废除私有财产或许看起来是诱人的——马尔库塞也会同意这一点,但是这不会消除性选择方面的冲突[9]90、60-61。在个体及其内在冲突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性方面,马尔库塞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人们可以真正作为个体而存在,每一个人都塑造着自己的生活;人们以真正多元的需求和满足模式面对他人……快乐原则的支配地位因此会对抗敌对性(antagonisms)、痛苦和折磨——这些个体为争取满足时产生的冲突”[10]227-228。
这种让步是否与马尔库塞乐观的愿景不相容?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禁忌的存在和克服来区分人类愉悦和动物满足[17]82。黑格尔则认为人类愉悦来自早已被接受的自欲望的满足,这是一种再现(reflected),而非对自身的反映(relexive)。马尔库塞同意这些看法,并且认为针对阻碍的斗争本身就是“满足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gratification)的一个方面[10]228。他认为“力比多的道德”的可能性并非基于外在压制的内投射(introjection),即超我,而是基于追求愉悦的诉求。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观点。马尔库塞的准弗洛伊德主义(quasi-Freudian)的论证并不能让人信服,但是他所说的力比多道德却有一个常识的内核:当阻碍被克服,欲望的满足度就会更高,从而使得对象价值和主体德性得到确认,这一点在人的关系中尤为明显。相对应的挑战则是关乎本质的,是来自他者的暗示。但是这会造成失败的风险,并要求个体在即使最不那么压制的社会中也接受欲望满足的偶然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阻碍被克服的情况并不会引发暴力和对统治权的争夺。“没有冲突的社会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但是一个冲突明显存在但能够在不触及压迫和残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社会,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18]79
最后,问题仍然是“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中的个体如何理解他们的处境,这是第一代的困境,困扰着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尤其是卢梭。卢梭苦苦思索被贵族统治腐化的人民如何才能学会自由社会所要求的公民德性。马尔库塞认为,这一困境的构成所围绕的是在社会形态转型中同样造成问题的需求。“富足社会”的革命必须被新的需求激发,这种需求无法在现存压制系统中得到满足,只能在非压制社会中才有可能得到满足。
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指出教育转正(educational dictatorship)是对这种困境的早期合理回应,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答案已经过时(obsolete)了:创造人类存在的手段的知识不再局限于一小撮特权精英……理性和非理性权威、压制和过剩压制的区分,能够通过个体自身被创造和证实。”[10]225但是这个进程却被需求的操控所阻隔了,而人民则臣服于这种操控。然而,在原则上,一个涉及人民的试错(trial and error)进程可以在现存社会中达到一个本应更好与合理的替代方案。
新左翼的出现为这一充满希望的构想提供了政治内容。围绕着诸如妇女权利和环境主义等主题的第二代政治斗争确认了这一学习进程的可能性。马尔库塞认为这些政治运动代表了被唤醒的爱欲。这一版本也许看起来有些夸张,政治在根本上仍然是关乎生死的斗争。他认为这只是理性分歧的幻想阶段性地被人类破坏力的一次又一次的残忍回归所粉碎。今天西方社会的生活富足得让人震惊,但是毫无疑问,在不那么幸运的地区的观察者会嘲笑那些需要被唤醒的人们。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提出了对这一现实的理论阐释,马尔库塞则试图为弗洛伊德伸张正义,同时为创制更美好世界的斗争寻求根据。马尔库塞其实就是这场斗争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