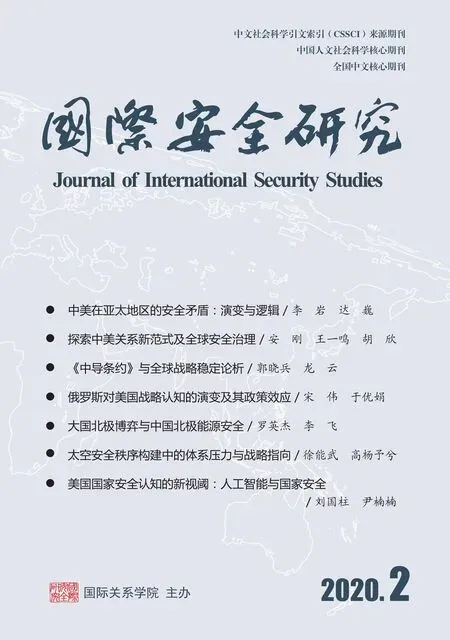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及其政策效应*
2020-03-11于优娟
宋 伟 于优娟
安全战略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及其政策效应*
宋 伟 于优娟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变过程分为友好合作、竞争凸显和激烈对抗三个阶段。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和安全政策,表现为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的强硬战略姿态以及追求超出自身相对实力的外交和安全目标。俄罗斯战略认知的演变与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之间有着相互塑造的关系,但是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利益考量。俄罗斯之所以把北约东扩、乌克兰走向、叙利亚局势等看得如此重要,不惜投入大量资源,这是与塑造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历史和心理因素是分不开的。美国采取的许多对俄政策和行为,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才被俄罗斯看作是“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从而导致了双方敌意的螺旋式上升。由于俄罗斯独特的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俄罗斯对俄美两国的利益冲突作出了激烈的回应,这些回应虽然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整体利益,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随着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逐步定型,俄美关系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所谓的“重启”。从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战略认知自身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在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从而使得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未必完全遵循理性主义的路径。
俄美关系;战略认知;外交与安全政策;强势外交
近年来,虽然俄罗斯的经济遇到较大困难,但是它的安全政策、尤其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却表现得非常强烈。从支持南奥塞梯独立、夺取克里米亚半岛,到争夺叙利亚控制权、派遣军事人员到委内瑞拉,一系列事件导致俄美关系滑落至苏联解体以来的最低水平,双方的敌意在反复拉锯式的较量中螺旋上升。俄罗斯官方对美国的战略认知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地步,未来又将如何发展?这不仅对于俄美双边关系会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对于全球政治局势的走向也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变化源于两国地缘战略利益的冲突,即美国通过北约东扩等方式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但是,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法,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俄罗斯应该保持一种相对克制的外交政策,避免与霸权国的直接对抗和在国际上的过度扩张。然而,现实主义理论不能解释的是,在上述背景下,俄罗斯为何采取越来越强势的应对措施,例如夺取克里米亚半岛、介入委内瑞拉这样的行为。有的学者已经指出,俄罗斯对外政策不符合传统的成本-收益考量原则。[1]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与它对国际局势的战略认知,尤其是对于俄美关系的战略认知,有着直接而重要的联系。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不仅取决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也与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历史记忆、民族性格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后面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不安全感和强烈的敌对认知。从科索沃战争到南奥塞梯冲突,再到乌克兰危机,普京的“大国外交”给俄罗斯带来了沉重的军事和经济成本。尽管这可以理解为普京或许更在意国内的民意支持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愿意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和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俄罗斯为何要在叙利亚、委内瑞拉等与俄罗斯安全利益无关紧要的地区和美国展开对抗。
俄罗斯对美国和俄美安全关系的战略认知并不仅仅是俄美利益冲突和两国政治关系变化的附属物;相反,战略认知自身在俄美关系的变迁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既可以从俄罗斯的相关政策文件中获得了解,也可以从俄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尤其是俄罗斯的对外行为中得到印证。俄罗斯与美国关系的变化和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之间的确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论证。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变化,受到双方互动过程的影响,这种互动过程是根源于国际政治结构和双方的国家利益计算的,但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也有其自身的发生机制,即利益冲突、社会心理、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等都会影响到俄罗斯的战略认知变化。
俄对美战略认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作为伙伴关系的战略认知初生期(1991~1998年);第二阶段是竞争关系凸显的战略认知变革期(1998~2012年);第三阶段是陷入对抗关系的战略认知恶化期(2012年至今)。尽管俄美两国在反恐、军控、核不扩散等领域继续进行一定的合作,但近三十年俄罗斯的对美战略认知是不断恶化的。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演化过程及其在俄美关系和俄罗斯对外政策之中的体现,进而分析导致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从伙伴关系到敌对关系演变的生成机制,从而说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为何在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仍然采取与霸权国美国对抗的诸多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一 战略认知初生期(1991~1998年):友好合作
1991年12月21日的《阿拉木图宣言》标志着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俄罗斯联邦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急剧动荡,而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成立的叶利钦政府走上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道路,外交上则一改冷战时期与西方国家的对立态势。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美双方致力于建设一种新的双边关系模式——战略伙伴关系。这一设想反映出双方对彼此友好的角色认知。这种角色认知不仅基于共同的国际安全利益,而且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即俄罗斯相信与西方合作、走西方式的道路将促进俄罗斯的繁荣发展和国际地位。叶利钦在1994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指出:“全球对抗已经一去不复返,要充分利用俄罗斯与美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机会。俄罗斯在欧洲方向上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建设一个和平、团结、民主的大欧洲,这一时期里程碑事件是欧安会的《布达佩斯协定》……与美国保持双方的利益平衡,是稳定国际关系的基础。俄美关系的日益稳定不仅符合两国政府的利益,还符合商业、人道主义及两国公民的利益。”[2]
这一时期,俄美战略伙伴关系是通过以下宣言逐步确立的:第一,1992年2月布什总统和叶利钦总统签署《戴维营宣言》,指出“俄罗斯和美国不再认为对方是潜在对手”。双方讨论了苏联解体的问题,同意继续削减战略核武器,开展防务贸易领域的合作,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该宣言谈到俄美希望建立“新的合作伙伴联盟”,即从有限范围的合作过渡到联盟类型的关系。[3]第二,1992年6月,俄美两国签署《俄美伙伴和友好关系宪章》,重申《戴维营宣言》的立场,缔结了若干经济协定,俄罗斯同意开放东西伯利亚的空中航道,美国同意向俄罗斯提供45亿美元经济援助等。该宪章规定,俄罗斯当局与西方国家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时,必须遵循民主、自由、保护人权和尊重少数群体权利的原则。因此,俄罗斯领导层默认美国有权作为仲裁者评估俄罗斯的改革。[4]这意味着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没有平等的联盟,而是根据俄罗斯“行为”确定是否与俄罗斯发展进一步的关系。[5]第三,1993年4月,俄美两国签署《温哥华宣言》,宣布俄罗斯与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刚就任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叶利钦总统确定俄美关系发展方向和原则的重要事件。
俄罗斯联邦建立初期,美国为维护叶利钦政权的统治地位,全力支持俄罗斯转型改革,允许俄罗斯继承苏联的政治遗产,尊重俄罗斯大国地位。这些都是促成俄罗斯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友好战略认知的重要原因。1990年1月31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尔公开表示,德国统一后,“北约地区不会向东扩张”。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艾迪生·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也表示:“一英寸也不进犯。我们理解向苏联提供担保的必要性,北约只停留在德国,北约部队的管辖权不会延伸到东部。”[6]1994年,俄罗斯和北约在解决巴尔干危机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共同谴责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对内对外政策。1992~1996年期间,俄罗斯对美国是一种友好和信赖的战略认知。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1995年声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能滑向冷战边缘,建立独联体国家防御联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并非新的军事集团。”[7]当然,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认知也基本如此。双方在削减限制进攻性武器、增强商业和文化联系等方面开展了密切的双边合作。1995年5月9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参加了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红场阅兵仪式。此外,双方各种首脑会议期间的高级别对话交流多。叶利钦参加七国集团首脑会议框架内的多次会晤,俄美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俄罗斯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大幅增加,美国一度成为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1992~1998年,美国直接向俄罗斯投资77亿美元,约占外国投资总额的1/3。[8]
美俄安全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1994年1月,北约布鲁塞尔首脑会议正式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中东欧国家以及俄罗斯建立“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6年5月31日,俄罗斯宣布正式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并签署了俄罗斯和北约的《双边军事合作计划》。1996年底,俄罗斯政界人士开始就俄罗斯与北约的相互关系进行谈判,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1997年5月,双方在巴黎签署《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础文件》,宣布俄罗斯和北约是合作伙伴而不是潜在的敌人。根据这一文件,双方建立由北约秘书长、俄罗斯代表和北约成员国代表组成的俄罗斯-北约常设联合理事会,该理事会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对涉及双方利益的问题作出决定。此后,俄在北约总部派遣常驻代表,北约在莫斯科设立了联络处。
二 战略认知变革期(1998~2012年):竞争凸显
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变革期以科索沃战争为起点。塞尔维亚在历史上是俄罗斯的传统盟国。尽管俄罗斯政府一度同美国站在一起谴责米洛舍维奇,但是北约空袭南联盟的行为,没有顾忌到俄罗斯对传统势力范围的特殊感受。这当然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冲突和立场对抗,但是也充分表明,俄罗斯的战略认知是深植于俄罗斯自己的历史记忆、大国情结等文化背景之中的。
1998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介入科索沃危机,使俄罗斯与北约关系从“相互谅解”演变成“信任危机”。这一年,南斯拉夫联盟的族群冲突升级为武装斗争。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政权实行国际制裁,支持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领导人。科索沃的独立与俄罗斯战略利益相悖。俄罗斯宣称反对科索沃分裂主义,建议评估科索沃独立的长期影响。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俄罗斯就是否赋予北约维护科索沃和平问题的第1199号和第1244号决议行使了否决权。1999年3月24日,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批准的情况下,北约开始轰炸南斯拉夫联盟的城市公共设施和军事基地。随后,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正式加入北约,完成北约第一次东扩,由此,俄罗斯毫不犹豫地冻结了其与北约的关系。这表明俄美友好战略关系的脆弱性,也说明美国和西方国家低估了俄罗斯捍卫自己大国地位的决心。虽然俄罗斯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物质手段来阻止科索沃局势的消极发展,但在俄罗斯的对美战略认知中埋下了不满和对抗的种子。
21世纪初影响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演进的重要事件还有: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北约东扩等。这些都体现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多的利益冲突。[9]在利益冲突的背后,是俄罗斯经济的逐步恢复、自信心的增强以及重新燃烧的大国情结。2000年6月,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俄罗斯将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安全、影响全球进程,形成稳定、公平和民主的世界秩序,为俄罗斯的逐步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10]2002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根据美国领导层的说法,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旨在保护欧洲免受伊朗导弹袭击,俄罗斯领导层断然拒绝这样的解释。普京在各种公开演讲中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表示不满。2003年初,俄罗斯、德国和法国强烈批评美国入侵伊拉克。普京表示,美军入侵伊拉克导致俄美关系恶化并产生严重分歧。[11]2004年3月,北约东扩延伸至波罗的海国家,突破了叶利钦定下的“红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7国正式加入北约,改变了欧洲安全版图。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回忆录中写道:“普京将北约扩张描述为一种侮辱,美国人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地位。”[12]
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今天俄美关系处于艰难时期,存在很多问题。俄罗斯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显著成就,愿与其他国家一道,应对经济放缓带来的困难,有必要建立机制来阻止国际社会某些成员错误、自私、危险的决定。在军备竞赛中,俄罗斯要有效对抗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并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设施进行无线电抑制。”[13]2007年2月,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反对在东欧部署美国军队和导弹防御系统。他指出,美国正试图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北约和欧盟努力取代联合国。普京的讲话引起了西方(主要是美国)政界关于国际局势“重回冷战”的争议。美国代表们在会议上一致认为,普京的讲话是“自冷战以来所有俄罗斯领导人最激进的表达”。[14]
尽管俄罗斯领导人提出抗议,但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两国国内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位置部署了“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发射包括“战斧”巡航导弹等多种类型的导弹,防御系统可以瞬间转变为进攻性武器。尽管这一举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但却削弱了俄罗斯对东欧国家的战略威慑力和影响力,导致俄罗斯想要恢复传统的势力范围和大国地位变得更加困难。这当然会深深刺激到俄罗斯。2007年7月14日,普京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暂停执行《欧洲常规武器力量条约》及相关国际条约的法令。观察家们认为,这一决定是欧洲大陆政治与安全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第一步。
2008年4月,美国与北约盟国在布加勒斯特联盟峰会上讨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事宜。[15]俄罗斯联邦总参谋长尤里·巴鲁耶夫斯基将军当即表示,如果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将被迫采取军事措施确保国家利益。[16]出于报复,普京打算“实质性地支持”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2008年8月,格鲁吉亚军队入侵南奥塞梯,俄罗斯与美国发生新一轮对峙。俄罗斯宣称,南奥塞梯爆发的敌对行动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野心勃勃的结果。俄罗斯持续数日轰炸格鲁吉亚军事设施,宣布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由于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国内经济实力(1999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7%,经济总量增长6倍)[17]以及南奥塞梯地区作为重要的能源运输路线,为防止北约东扩(即以南奥塞梯的独立问题牵制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进程),巩固自己在高加索的军事存在等目的,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包括直接与美国对抗的安全政策——出兵格鲁吉亚。这反映了俄罗斯自信心的增强以及对美国和北约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已经从之前的友好合作,逐步演变为竞争凸显。尽管2009 年 3 月,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Сергей Лавров)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按下象征两国关系恢复的“重启”按钮,但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重启”。[18]
俄罗斯政府在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对美国和北约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姿态,通过国防建设巩固大国地位的战略思维在俄罗斯社会中得到强化。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自1998年起俄罗斯国防军费开支逐年上涨,从1998年的567亿卢布上升到2001年的2 467亿卢布。[19]俄罗斯军费开支三年内增加3倍多。俄罗斯认识到自己的战略劣势,并试图弥补这一劣势。这与友好合作时期俄罗斯安于这一劣势的情形发生了根本变化。俄罗斯方面认为,一味退让只会牺牲根本利益,只有不断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提升国家军事能力,才能确保战略威慑能力和防止军事冲突。这一时期,俄罗斯在装备和武器现代化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例如,2009年开始研发的“萨马特”导弹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新型战略武器,在向目标移动时根本不使用弹道飞行轨迹,因此,当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根本无法防御。[20]2011年初,普京将在利比亚的西方军事行动与十字军东征进行了比较,从而引发了俄美关系的新裂缝。与此同时,普京批评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的决议(俄罗斯投弃权票,没有使用否决权)是“劣等和有缺陷”的。[21]
尽管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俄罗斯经济受到了重创,“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俄GDP下降7.8%,2010年俄经济开始回升,2010年与2011年经济增长率均为4.3%,但2012年降为3.4%,而2013年又降为1.3%。2014年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仅为0.6%。经济衰退始于2015年,一季度之后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该年GDP下降3.7%。2016年GDP下降0.2%。”[22]但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却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持续扩大,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所导致的,例如介入到叙利亚内战、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等。而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给俄罗斯经济和国家实力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所导致的西方国家对俄制裁,以至于俄罗斯经济从2015年开始陷入衰退。事实上,作为核大国和世界顶尖的军事强国,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并不真的面临迫切的威胁。要理解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强势倾向需要理解它对国际局势尤其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
三 战略认知恶化期(2012年至今):激烈对抗
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出现衰退,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形象却更加鲜明。俄罗斯力图恢复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从而卷入了各种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争端之中。这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强势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常说的“过度扩张”问题,反过来削弱了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因此,在理解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围绕着各种具体冲突所展开的对抗时,我们仍然有必要跳出这些冲突本身,认识到俄罗斯如果基于完全的现实主义或许可以有其他的选择,例如收缩战线、放低姿态。但是,在现实中,2012年以后的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轨道,在与美国和北约对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叙利亚问题上,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希望阿萨德政府倒台。北约指责俄罗斯支持叙利亚政权,没有参加阿斯塔纳和平谈判。2012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进行投票时,俄罗斯使用了否决权。2013年8月,俄罗斯向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提供临时庇护,俄美双方就叙利亚局势和俄罗斯人权问题也存在分歧,原定奥巴马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会谈也被取消。美国政府关于奥巴马取消原定2013年9月访问俄罗斯的特别声明指出:“过去一年在导弹防御、军备控制、经贸关系、全球安全问题、人权和公民社会等问题上,俄美完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23]
俄美关系再度紧张升级缘于克里米亚事件。1994年12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梅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签字国承诺,在乌克兰实现无核化,“尊重乌克兰现有领土的独立和主权”和“避免使用武力等方式威胁乌克兰”。这意味着英美应该对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负有条约责任。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的行为破坏了该备忘录。克里米亚冲突起始,美国就主动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在2014年通过了“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案”。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之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外交上孤立俄罗斯,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完全消失。2014年3月以来,美国政府暂停2009年成立的俄美总统委员会的工作,取消大量双边合作,拒绝给部分俄罗斯官员、联邦议会议员、企业家签发赴美签证。虽然面对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巨大制裁压力,但是普京政府并没有屈服。在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的演讲中,普京愤怒地表示:“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欺骗,他们在既成事实之前已经做出所有决定。随着北约向东扩张,他们在距离我们最近的边境部署军事设施,还不断告知,这一切不是针对我们。”[24]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开展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敌意互动,最终形成了双方互为对手的角色认知。这种战略认知反过来又加强了俄罗斯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强硬趋势。当然,美国的对俄政策也呈现出类似的特点。
2015年6月,美国计划在东欧部署坦克、装甲车、火箭炮和其他重型武器,美俄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2016年10月,普京下令暂停与美国就2000年达成的钚处置协议。围绕着乌克兰东部分裂运动,美国、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一直在持续,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理由是俄罗斯在背后支持这些地区的分裂势力。2015年《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美国和欧洲支持乌克兰反宪政联盟导致乌克兰社会分裂和武装冲突,有意恶化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形象。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军事活动密集化,不断扩大联盟,其军事基础设施紧逼俄罗斯边界对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18年11月25日,在刻赤海峡发生了俄乌冲突,乌克兰三艘军舰被俄罗斯扣押。特朗普随即宣布取消与普京在阿根廷G20峰会期间(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的预定会晤。美国宣布因刻赤海峡事件将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敦促欧洲盟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以示惩戒,呼吁欧盟放弃“北溪-II”石油管道项目。
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曾经与普京互相表示好感,普京原本希望借此机会改善俄美关系。但很快美国情报机构就开始指责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从而开始了漫长的“通俄门”调查。特朗普断然否认“通俄”。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在对俄政策上采取更加强硬、激进的政策。特朗普上任后宣布与俄罗斯合作打击“伊斯兰国”,但俄美领导的两个国际反恐联盟互动仅限于电话沟通。2017年4月初,特朗普让叙利亚当局对造成80人死亡的化学袭击事件负责,并下令对叙利亚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进行导弹袭击,一共发射了59枚战斧巡航导弹。俄罗斯当局称,“这次袭击是对主权国家的侵略”。[25]2018年春,前俄罗斯双面间谍在英国遭毒害事件引发英俄外交风波升级,美国等西方国家下令驱逐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美双方对等关闭两国在西雅图和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特朗普政府努力阻止其阿拉伯盟国与叙利亚和解,俄罗斯则敦促其在阿拉伯世界的伙伴恢复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
委内瑞拉政治危机激起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另一场对抗,它们相互指责对方干预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严厉批评美国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美国如果对委内瑞拉武装干预将“充满灾难性的后果”。[26]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准备与委内瑞拉的所有政治力量进行合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Sergey Ryabkov)表示,俄罗斯将支持“友好的委内瑞拉”作为其战略伙伴。里亚布科夫警告美国不要对委内瑞拉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这将导致灾难。[27]与此同时,俄罗斯向委内瑞拉派遣军事人员,高峰时超过1 000名军官和技术人员在委内瑞拉军队从事培训等工作。在美国试图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背景下,俄罗斯的这一举动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不满情绪,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下令在罗马尼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除了采取超出自身国力的大国外交政策之外,俄罗斯继续在国防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2018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03.63万亿卢布,约为1.6468万亿美元。相比之下,2018年,美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美元,也是全球第一个GDP突破20万亿美元的国家。尽管俄罗斯与美国的综合实力相差巨大,但俄罗斯仍然试图在军事上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从而投入了大量的资源,2014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为840亿美元,达到世界第三的水平,占俄罗斯联邦当年总预算的34%左右。[28]这一时期,俄罗斯装备现代武器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增加了3.7倍,超过300种新型军用设备投入使用。远程武器的载体数量增加了12倍以上,高精度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加了30多倍。[29]俄罗斯建立了联邦国家防务指挥中心,建立了远程海域的作战指挥体系。俄罗斯预备役军人数量增加了2.4倍,武装部队的人数从70万增加到90万~100万。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建立一个高精度的高超音速航空导弹综合体“匕首”,相关测试已经完成。自2017年12月1日起,该综合体开始在南部军区的机场实际部署。当然,由于经济困难,普京曾经设想的宏大的强军计划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挫折。从2016年开始,俄罗斯的国防开支出现了负增长,这也反映出俄罗斯的困难局面。2018年,俄罗斯的国防开支约为530亿~60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的1/10,排在世界第六位。
目前,俄美关系已经进入冰封期。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认知不断恶化的确是由于双方在各种国际性和地区性问题上的频繁对抗所引发的,俄罗斯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倾向于选择与美国展开强硬对抗。问题在于,这些政策虽然可以解释为两国利益冲突以及美国在某些方面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但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的行动并不涉及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即便是乌克兰危机,美国也一直避免与俄罗斯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而采取经济制裁手段。因此,导致俄美战略认知恶化的直接原因是这些对抗事件和利益冲突,但是认知恶化的程度和对政策的影响力却超出了这些冲突本身,使得俄罗斯面临一个更加不利的国际环境。俄罗斯把美国作为对手的战略认知,超出了自身的国家实力,但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国际影响力和威望,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在经济十分困难、与周边国家关系趋向紧张的背景下,反而采取了越来越强硬的对抗姿态和对抗政策。在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已经基本定型的背景下,即便普京和特朗普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也将是一个缓慢、困难的过程。只有俄美双方都做出反复的、非常多的实质性妥协,才有可能改变已经定型的战略认知。考虑到美国国内同样拥有强烈的反俄情绪,这种敌意互动的建构过程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这也意味着俄美关系在可见的将来仍然会处于一个紧张对抗的状态。
四 战略认知的塑造:利益冲突、历史记忆与大国情结
自从1998年以来,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抗态势逐步加强,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姿态都表现得十分强势,但这并不符合俄罗斯当前的相对实力地位。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国家利益的范围和目标,应该与自身的相对实力一致,不能追求超越自身能力范围的目标。但是,俄罗斯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显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这一预期。利益冲突是造成俄罗斯和美国频繁对抗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俄罗斯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强势特点,我们还是需要说清楚,俄罗斯为什么不是选择其他相对温和的途径,而是采取强硬对抗的方式,为此不惜消耗自己的国家实力,恶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直接、明白的一个发问是:俄罗斯眼中的不安全感、屈辱感和对大国地位的寻求为何如此强烈?因此,其战略认知虽然受到利益冲突和实力对比的制约,但在与美国的对抗中却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这些制约。
在分析俄美关系的演变,尤其是俄罗斯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时,除了考察俄美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之外,还需要纳入战略认知方面的因素。俄罗斯对美国战略认知的生成,除了受到两国利益冲突和政策对抗的影响,也受到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的影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由于沉迷在“冷战胜利者”的定势思维中不能自拔,忽视俄罗斯的情感需求,不能以尊重平等的方式相待,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是导致俄美关系严重恶化、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不断恶化的导火索。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当北约再次计划扩展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时,俄罗斯民众反对北约的情绪达到极点,克里米亚入俄事件在俄罗斯民众看来就觉得理所应当。在指出美国忽视了俄罗斯的感受之后,我们也需要明白俄罗斯的战略认知存在什么样的特别之处,使得其战略认知中的“非理性”方面居于主导地位,从而采取了过于强势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一)俄美战略认知中的利益冲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俄罗斯的西面是东欧平原,易攻难守,造成俄罗斯不断通过对外扩张缓解地缘劣势带来的战略压力。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欧盟不断扩大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认为这是对其国家利益的威胁。美国不仅在东欧地区,也包括蒙古国、吉尔吉斯斯坦等东亚、中亚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俄罗斯当然视其为重大“威胁”。尽管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对俄罗斯这样一个核大国和军事强国构成威胁。但是,北约东扩和东欧反导系统部署都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安全是一种心理上的感受,北约东扩自然会被俄罗斯看作是一种安全上的威胁;而且,即便美国和北约不会真的对俄罗斯发动进攻,但北约东扩势必会削弱俄罗斯在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影响力,从而影响到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地区优势。俄罗斯政府认为,美国持续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美国正在构建从东亚到中亚的对俄包围圈,防止俄再度崛起。[30]
影响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由于北约东扩会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因此俄罗斯和美国之间为此频繁较量、冲突不断升级。1995年,北约发表《北约扩大研究报告》,详述北约扩大的原则、目的和流程。研究指出,北约被理解为欧洲安全格局的重要部分,有意加入北约的国家需要经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进行改革。[31]为了化解安全担忧并保障自身安全不会受侵犯,俄罗斯希望建立一个覆盖全欧洲的安全体系,提倡把欧安会当成这种体系的支柱与核心。但在1999年3月,波、匈、捷正式加入北约,完成北约组织第一次扩大。2004年3月,北约东扩延伸至波罗的海国家,突破了叶利钦定下的“红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七国正式加入北约,实质性地改变了欧洲安全版图,这使得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2008年4月,美国与北约盟国在布加勒斯特联盟峰会上讨论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事宜。2008年8月8日,格鲁吉亚军队入侵南奥塞梯,俄罗斯出兵反击,并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为独立国家。
相比格鲁吉亚,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来说战略意义更为重要。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曾说过:“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能成为帝国。”[32]乌克兰作为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延展了俄罗斯的战略纵深。2012年3月,乌克兰与欧盟草签了《联系国协定》,并欲在2013年11月正式签署《联系国协定》以及《自由贸易(FTA)协定》。乌克兰选择加入欧盟,对于俄罗斯和普京的欧亚经济联盟计划都是重大的打击。普京政府对乌克兰过渡政府采取不承认、不接触政策,当发现实在无法让乌克兰回心转意时,就采取最大限度地削弱乌克兰的对策,从而出现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分裂运动一直持续的问题。在俄罗斯看来,克里米亚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隶属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是苏联时期建造航空母舰最主要的工厂,也是维护保养航母重要的场所。在失去克里米亚的二十多年,苏联生产的航空母舰因无法维护保养,基本处于报废状态。俄罗斯每年需要支付大笔费用租借塞瓦斯托布尔军港作为黑海舰队的海军基地。克里米亚除了战略安全的重要意义以外,还提供给俄罗斯巨大的商业利益。苏联60%的海上贸易是从黑海经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布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完成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时期,苏联也是通过黑海向埃及补给军事战略物资。因此这条贸易通道为俄罗斯外贸出口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
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希望借助叙利亚增加同北约谈判的砝码,缓和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但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经过对叙利亚的大量投入后,尽管保住了自苏联时期建立传统友谊的阿萨德政权,但是也使本已非常困难的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在与美国和北约的地缘政治对抗中,俄罗斯表现得非常强势,但是总体上处于守势。
(二)俄美战略认知中的历史记忆
对外政策的偏好根植于基本价值观念和对历史的不同解读。[33]不同的个体学习和类比历史的方式与手段不一, 但总体上他们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34]俄罗斯的战略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历史记忆的影响,历史记忆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塑造。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工业水平最发达的地区位于东欧大平原,波兰立陶宛联军、拿破仑军队、纳粹希特勒军队都是从这里入侵莫斯科,没有天然屏障的俄罗斯极度缺乏安全感,历史上无数次惨痛的教训迫使其形成“以攻为守、先发制人”的战略文化以及对于地缘政治缓冲区的高度重视。俄罗斯政治精英把过去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视为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历史基础,因而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的政治干涉就等于使俄罗斯丢失了大国地位。[35]
第二,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冲突历史多于合作历史所形成的负面效应。即便俄美两国间能够暂时合作,但这种合作不会是朋友间的,而是相互利用和相互警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和美国曾经是盟友关系,共同抗击纳粹德国。但是,二战胜利不久,两国关系就转向了冷战。冷战结束初期,虽然俄美战略认知的性质和内容不再受到严厉的军事-政治对抗逻辑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和美国对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冷战思维就是俄美战略认知中无法抛开的历史包袱。冷战初期,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承诺大多口惠而实不至,导致俄罗斯对西方世界幻想逐步破灭。
第三,休克疗法对于俄罗斯战略认知的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决策者和民众一致希望通过私有化、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革使国家走上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道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1992年,俄罗斯代总理盖达尔宣布实施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佛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创立的激进改革方案“休克疗法”,美国顾问经常来俄罗斯协助实施该计划。[36]但“休克疗法”的失败使得俄罗斯民众产生了对美国动机的怀疑。“休克疗法”通过私有化打破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按照西方国家模式构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GDP累计下降40%。从1992年到1999年的叶利钦执政期间,俄罗斯经济除1997年和1999年分别增长0.9%和5.4%外,其余6年都是负增长。[37]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对与西方国家合作的热情逐渐减弱,开始怀疑美国帮助俄罗斯的真正目的,指控美国“利用俄罗斯困境”进一步打压俄罗斯经济。[38]
第四,俄罗斯人的克里米亚情结。克里米亚承载了俄罗斯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寄托着民众对于国家再次强大的期盼。2018年,普京以83.5%的支持率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就源于普京为俄罗斯赢得尊严,捍卫国家荣耀。俄罗斯与土耳其为争夺克里米亚和黑海制海权发生过10次战争和不计其数的冲突。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军队入侵克里米亚,塞瓦斯托布尔军民抵御德军围困250天(1941年10月30日至1942年7月4日),有效拖延德军北上进入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的步伐,为苏联赢得宝贵的战略缓冲时间。塞瓦斯托布尔是苏联的英雄城市,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象征。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普京冒着与美国和西方世界决裂的风险,依然要收回克里米亚。普京在2014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在乌克兰和欧盟的谈判中,我们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没人考虑过乌克兰和俄罗斯是独联体内的邻国,没人考虑过我们历史上农业和工业的合作,没人考虑过我们共用一套基础设施,他们不仅是没考虑这些问题,甚至不愿听我们说句话。”[39]
(三)俄美战略认知中的大国情结
俄罗斯对外政策不符合传统的成本-收益原则,要理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必须了解其国家认同和安全利益都是基于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塑。[40]俄罗斯的大国情结,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俄罗斯对美国和北约战略意图的认知,也塑造了俄罗斯激进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保持着作为大国的自豪感,即便在实力相对下降以后,其民众仍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大国,这势必影响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2019年5月27日报道,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34%的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21世纪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苏联曾拥有的超级大国地位。[41]面对北约东扩等不尊重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做法,俄罗斯民族自然的感受是“受到了侮辱”,因此容易做出相对激进的反应,希望通过这些激进的措施能够挽回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克里米亚情结本质上也是俄罗斯大国情结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的执着,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普京在克里米亚危机中采取的激进行为,这一行为也导致了俄美关系的急剧恶化。
俄罗斯共有民族特性是弥撒亚意识,成为世界大国和拯救世界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内容。1453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提出“第三罗马”学说,“两个罗马先后衰落,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罗马不会出现。俄罗斯作为最后一个罗马,作为世界唯一正宗信仰的载体,应负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和责任。”[42]“第三罗马”的符号内涵就是弥撒亚主义。弥撒亚主义不能容忍共同存在,它是唯一的,按照自己的雄心来统一世界。[43]俄罗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救世使命感和自我牺牲精神,当民族遭到外敌入侵时,弥撒亚意识就会激发俄罗斯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坚韧的抗争意志;而在顺境之中,弥撒亚意识又会幻化成为大国沙文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44]
俄罗斯精英们大多认为,俄罗斯理应有崇高的世界大国地位,“横跨世界两大洲,介乎东方和西方之间,一只胳膊紧靠中国,另一只紧靠德国,我们理应在自己身上将精神天性的两大因素——想象和理智结合起来,让全球的历史统一于我们的文明之中。”[45]这种大国情结促使俄罗斯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大国荣耀。大国情结被认为是构成俄罗斯自我意识的最关键部分。[46]托马斯·安布罗西奥(Thomas Ambrosio)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寻求大国公认,是因它对世界地位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47]1995年2月,叶利钦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强调,未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连贯性的、坚定的、灵活性、实用性相结合”。俄罗斯不会和其他国家对抗,但也不允许任何国家小看俄罗斯。[48]俄罗斯试图同北约建立一种基于“相互信任”和“相互合作”基础上的伙伴关系,但是这种尝试基本上是失败的。普京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表示:“应该坦率地说,我们把独联体地区看作我们的战略势力范围。”[49]
五 结论
俄罗斯的对美战略认知经过了三个基本的阶段,从友好合作到激烈对抗,导致俄罗斯在处理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时采取越来越强势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传统势力范围,但是本质上并不利于促进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基于这样一个“非理性”的现象,俄罗斯的战略认知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能简单地将战略认知视为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附属物。俄罗斯的对美战略认知是俄美利益冲突与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和大国情结共同塑造的结果。正是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和强烈的大国情结,导致俄罗斯在国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采取了越来越强势的外交与安全政策。这些政策虽然是“非理性”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一个案例研究,本文并不试图做出理论上的发展。但是,有关俄罗斯对美战略认知的研究确实告诉我们,大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总是理性的;战略认知不仅受到国家利益的影响,而且受到历史记忆、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之所以把北约东扩、乌克兰走向、叙利亚局势等看得如此重要,不惜投入大量资源,这是与塑造俄罗斯战略认知的那些历史和心理因素分不开的。美国采取的许多对俄政策和行为,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些因素,才被俄罗斯看作是“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从而导致了双方敌意的螺旋式上升。本文并不是证伪现实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应该尊重国际结构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50]事实上,由于俄罗斯追求超越自身相对实力的目标,一定程度上已经损害了自身的实力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意味着,虽然俄罗斯的强势外交和安全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理性的。
[1] Anna L.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Vol. 47, No. 3-4, 2014, p. 288.
[2] Ельцин Б. Н,“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1994 г.,”Февларя 1994, http://www.intelros. ru/?newsid=58.
[3] Глебов Г. И., Милаева О. В.Пенза: Изд. Пенз.гос. ун-та, 2010, C. 283.
[4] Богатуров А., “Три поколения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трин России,”No. 1. Январь-апрель 2007, C. 13.
[5] Глебов Г. И., Милаева О. В.Пенза: Изд. Пенз.гос. ун-та, 2010, C. 294.
[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IA 199504567,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Flashpoints Collection, Box 3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Mikhail Gorbachev and James Baker in Moscow,” September 1990, http://historyfoundation.ru/doc05/.
[7]李静杰、郑羽:《俄罗斯与当代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87页。
[8]Иванян Э.А.,, М.: Междунар отношения , 2001, С. 605-617.
[9] Георгий Ильичев, “США выделяют $85 миллионов на развитие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России,” Июля 2005, https://iz.ru/news/303988.
[10] Документы,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0 г., ” Июля 2008, http://www.kremlin.ru/acts/news/785.
[11] Полина Химшиашвили, “Ведомости-Путин не заметил «перезагрузки»,” Марта 2013, https://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2012/12/20/putin_ne_zametil_perezagruzku.
[12] Newsru, “Тони Блэр в мемуарах рассказал, почему Путин из прозападного демократа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националиста,” Сентября 2010, https://www.newsru.com/world/07sep2010/blair_ putin.html.
[13]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2005 г.,” Апреля 2005, http://www.kremlin. 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
[14] Lenta, “Путин вызвал у главы Пентагона ностальгию по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е» ,” Февраля 2007, https://lenta.ru/news/2007/02/11/gates/.
[15] Lenta, “Саакашвили вслед за Ющенко попросился в НАТО,” Марта 2008, https://lenta.ru/ news/2008/02/15/letter.
[16]Reuters,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рмия угрожает военным 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м, если Грузия и Украина присоединяются к НАТО, ” Апреля 2008,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newsOne/idUSL1143027920080411.
[17] Global-finances,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1999-2008,” Апреля 2018, http://global- finances.ru/vvp-rossii-po-godam/.
[18] 张建、周琪:《奥巴马第二任期美俄关系论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1期,第84-105页。
[19]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https://www.sipri.org/yearbook/2002/06, p. 259.
[20] 这一武器系统在2013年被对外宣布。2018年的俄罗斯《国情咨文》宣布将在2015年前采购40枚200吨级的“萨马特”导弹。俄罗斯方面宣称一枚导弹(携带10~15颗核弹头)就可以摧毁法国或者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参见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2018г.,” Марта 2018,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21] Андрей Артемов, “Путин: Эта операция – бессовестный крестовый поход, ” Марта 2013, http://www.aif.ru/society/24194.
[22] 陆南泉:《从经济结构分析俄罗斯经济前景》,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第115页。
[23] Иван Лебедев, “Нажали паузой:об охлажд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США,” Августа 2013, https://www.kommersant.ru/doc/2253803.
[24]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Марта 2014,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25]Сергей Строкань, Евгений Федуненко, “Война и мир Сирии: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ю страны мешает раскол между двумя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ми коалициями’,”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s://www. kommersant.ru/doc/3511567.
[26]Михаил Коростиков, Екатерина Мареева, “Военные не поддержали переворот в Венесуэле. Россия встала на сторону Николаса Мадуро,” Января 2019, https://www.kommersant. ru/doc/3861715#id1700152.
[27] Александр Щетинин, “Россия вызвалась стать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между оппозицией и властями Венесуэлы,” Января 2019, https://www.rbc.ru/politics/25/01/2019/5c4b02279a7947c1a7bd0ee6? utm_source=yxnews&utm_medium=desktop.
[28]王安妮编译:《普京背后秘密的军费开支到底有多少?》,寰球政事,2015年6月4日,https:// m.jiemian.com/article/296579.html。
[29]Юрий Гаврилов, “Равнение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Июля 2017, https://rg.ru/2017/11/07/ shojgu-dolia-sovremennogo-oruzhiia-v-rossijskoj-armii-vyrosla-do-59.html.
[30]马峰:《大国博弈与乌克兰危机的演变及发展趋势》,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4期,第7页。
[31] NATO, “Study on NATO Enlargement,” September 1995, 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 official-texts-247733.htmp.
[32][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33]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34] Yaacov Y. I. Vertzberger,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ers as Practical-Intuitive Historians: Applied History and Its Shortcomings,”Vol. 30, No. 2, 1986, pp. 223-247.
[35] Anna L.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Vol. 47, No. 3-4, 2014, p. 289.
[36] НекипеловА.,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Д.С. Львова Путь в XXI век: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1, 2000.
[37] Илларионов А. , “Политика — это всегда о деньгах,” Апреля 2004, https://www.novayagazeta.ru/articles/2004/04/15/22401-andrey-illarionov-politika-eto-vsegda-o-dengah.
[38]Богатуров А., “Три поколения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трин России,” Января 2007. https://portalus.ru/modules/internationallaw/rus_readme.php?subaction=showfull&id=1229191682&archive=&start_from=&ucat=&.
[39] 普京:《2014 年俄罗斯国情咨文(全文)》,观察者网,2014年12月6日,https://www. guancha.cn/Vladimir-Putin/2014_12_06_302598.shtml。
[40] Anna L. Clunan, “Historical Aspirations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Pursuit of International Status,”Vol. 47, No. 3-4, 2014, p. 288.
[4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民调: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认为俄应重回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地位》,俄罗斯卫星通讯网,2019年5月27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905271028576101/。
[42]Забияко А. П.,. М.: Пайдейя Моск. учеб., 2002, СС. 266-267; Бердяев Н.А.M.: Наука, 1997, С. 248.
[43][俄]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王建钊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88页。
[44]Мищенко Т.К.,М.: Наука, 1999,С. 30.
[45]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248页。
[46] Mark Urnov, “Great powerness as the Key Element of Russian Self-Consciousness Under Erosion,”, Vol. 47, No. 3-4, 2014, p. 305.
[47] Thomas Ambrosio,,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5, p. VIII.
[48] Путин В. В.,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2007 г.,” Апреля 2007, http://www.kremlin.ru/ acts/bank/25522.
[49] [俄] 弗·弗·普京:《2003 年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载《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50]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邮编:100872);于优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欧洲学院讲师(北京邮编:100024)。
10.14093/j.cnki.cn10-1132/d.2020.02.004
D815.5;D801;D81
A
2095-574X(2020)02-0073-18
2019-06-09】
2019-07-18】
*非常感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论文中的错漏之处由作者负责。
【责任编辑:苏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