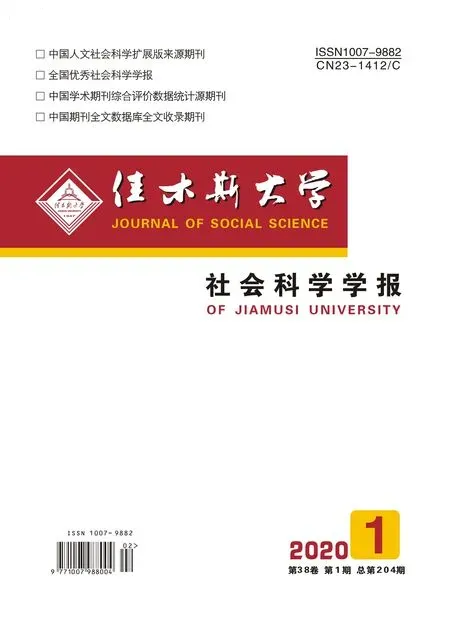朱熹悼亡诗分类研究*
2020-03-09李兵
李 兵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悼亡诗,在中国文学中特指悼念亡妻之作,这几乎是约定俗成的。[1]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愈益意识到,将悼亡诗单纯的划定为悼念亡妻之作,并不足以涵盖庞大纷繁的悼亡诗作。因此,有学者主张将悼念亡夫的作品纳入悼亡诗的范围。[2]而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的诗歌中,除了悼妻、悼夫之外,也存在大量的对亲朋好友的悼念。所以,又有学者提出,悼亡诗的范围应予以一定程度的扩大,认为“悼亡”并非单纯的悼夫、悼妻之作,也可用于悼念其他人、物。[3]显然,相较于前面两种观点,第三种观点更加符合中国悼亡文学的实际情况。因此,本文对朱熹的悼亡诗研究秉持的是第三种观点。悼亡诗的传统,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唐风·葛生》,其后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五代,悼亡诗作的数量和质量呈不断增加的态势。悼亡诗发展到宋代,除了表情达意之外,还沾染上一层理学气息。作为理学家代表的朱熹,除了主张“文从道出”之外,也注重文学的言情作用,最深刻地体现在他的悼亡诗作中。而现行的文学史在讲述悼亡诗史时,大多忽略了理学家的悼亡诗作。因此,对朱熹的悼亡诗作分类研究,并以此来探究朱熹真实的情感状态是必要且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的。
一、悼亲眷
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独自赴崇安任上,因要远离五夫里,故而将自己父亲的坟茔祭扫等事托付于灵梵院僧人。在崇安,物候的变化让朱熹想起了远在五夫里的朱松墓,自己因忙碌政事而不能亲自祭拜,而在悲伤之中写下了《十月朔旦怀先陇作》[4]251一诗,诗云:
十月气候变,独怀霜露悽。僧庐寄楸槚,馈奠失兹时。
竹柏翳阴冈,华林敞神扉。汛扫托群隶,瞻护烦名缁。
封茔谅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衔训倘在斯!
此诗是朱熹为悼念父亲所作,诗一开始即在悲凉的氛围中展开,物候的变化引起情感的变化,遥想父亲的坟茔只能寄葬在僧庐之侧,并且自己此时因公事不能前往祭拜,只能独自怀念,遥想父亲当年教育自己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朱熹之父朱松殁于绍兴十三年(1143),据其《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朱府君迁墓记》所述,其父“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4]4341,朱松与其妻祝氏育有一子一女,男即朱熹,“女嫁右迪功郎、长汀县主簿刘子翔”[4]4341。朱松去世之时,朱熹才十四岁,正如朱熹自己所说“幼未更事”[4]4341。同时因为朱松是激进的主战派,自然就遭受到了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打击和排挤,官职越来越小,最后只能奉祠闲居。而宋代的祠禄甚微,这就导致了朱熹一家居无定所。又因为朱松在福建未购置田产,他做官时,只得居于官邸,而闲居时,则多寓寄在朋友家里,故去世后只能寄葬在公家的庙田里。而据朱熹《朱松行状》所谓“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4]4341,《朱府君迁墓记》所云:“初,府君将没,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灵梵院侧”[4]4341,可知,此时只能将朱松暂时寄葬在五夫里的西塔山灵梵院侧。此后,朱熹一直居住在五夫里,来往祭扫,直到赴同安任上,才不得已将祭扫诸事托付与院内僧人。
朱松的墓从绍兴十四年(1144)到乾道六年(1170),一直在灵梵寺侧,而朱熹自同安归来后,在风俗之日也往祭扫,作有《三月三日祀事毕因脩禊事于灵梵以高阁一长望分韵赋诗得一字》[4]301,诗云:
逝川无停波,岁月一何疾。居然雨露濡,我意日萧瑟。
共惟西山足,宰树久蒙密。晤言起哀敬,时事该礼律。
肴羞既纷罗,荐馈亦芳苾。周旋极悽怆,俛仰讵终毕。
更衣适精舍,邻曲会兹日。簋黍畀煇胞,从容罄膋膟。
此诗乃是清明节时朱熹往祭父墓,事毕之后,在僧寺之内招待朋友所作,虽有游赏之娱,但对先人的怀念更多,凄怆感油然而生。
朱熹兄长早夭,故与妹妹感情深笃。妹妹嫁与刘子翔,淳熙八年(1181)二月以疾卒,葬于“崇安县西三里大夫公茔左若干步”[6]4227。父亲早逝,妹妹远嫁后相夫教子,家庭和睦,本以为一切都在逐渐好起来,但谁能料到,意外如此突然。在经历早年丧父之痛,中晚年丧妹之痛的朱熹,深感家人的重要性。因此,十月妹夫刘子翔将赴官浏阳县丞,朱熹作诗以送[4]515,诗云:
急景彫暮节,高风振空林。病夫掩关卧,长谣拥孤衾。
闻君千里行,四牡方骎骎。重此别离感,青天欲愁阴。
君行岂不劳,民瘼亦已深。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
君行宽彼氓,足以慰我心。荐书会满箧,社酒还同斟。
所念家同产,与君如瑟琴。兹焉不并驾,宰木寒萧椮。
尚喜吾诸甥,男恭女知钦。明朝复相忆,怅望楚山岑。
妹妹去世时,朱熹刚从吏役归,未能得见。故诗中不仅谆谆告诫刘子翔要体恤百姓,更要其时刻念想自己的亡妻,也要好好抚育孩子。而对亡人的追思,只能通过“尚喜吾诸甥,男恭女知钦”来表达出对自己亡妹的深切思念,“明朝复相忆,怅望楚山岑”,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悼亡与离别、伤时一齐流出,情感真挚动人。
二、悼君师
因父亲早逝之故,朱熹不得不求学于朱松的生前好友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四人。但四人之中,刘子羽并未指导过朱熹,其主要从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人。朱熹在其《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中这样说道“盖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熹饮泣受言,不敢忘。”[4]4167朱松殁后,朱熹遵父之遗愿,禀学于三君子。在求学过程中,朱熹居住于刘氏庄园内,往来问学于刘子翚等人。可以说,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对朱熹有养育之恩。因此,这几人去世以后,朱熹几乎都有诗作悼亡。
绍兴十六年(1146),刘子羽卒,朱熹作诗二首挽之[4]278,诗云:
其一
天地谁翻覆?人谋痛莫支。公扶西极柱,威动北征旗。
肉食谋何鄙,家山志忽赍。平生出师表,今日重伤悲!
其二
生死公何有?飘零我自伤。向非怜不造,那得此深藏?
心折风霜里,衣沾子侄行。哦诗当肃挽,悲哽不成章。
刘子羽,字彦修,建之崇安人,资政殿学士韐之长子也。[5]11504曾为中兴名将张浚之幕僚。绍兴初年除保文阁直学士,故称“宝学”。朱松将朱熹托付于刘氏等人,刘子羽慨然为己任,往来奔走,不遗余力,朱熹视其如父。刘子羽虽然没有担负朱熹的教育任务,但解决了朱熹家人的居住问题,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韦斋殁,文公年十四,少傅为筑室于其里,俾奉母居焉。”[6]24因此,刘子羽殁后,朱熹作诗以挽,首诗叙述刘子羽的政治功绩,次诗表达对刘子羽的恩情感谢。
后一年,刘子翚卒。刘子翚,字彦冲,号病翁,崇安人,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四十七岁,因秩满“以疾归里,筑室屏山以终”[7],学者称为屏山先生。刘子翚在病中,朱熹以童子侍疾时问刘子翚“平昔入道次第”[4]4169,刘子翚详以答之。刘子翚卒后,朱熹因忙于筹备婚事,故未能作诗以悼。到了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与刘子翔等人游瑞岩时,读到刘子羽、刘子翚兄弟在瑞岩所题诗作时,兴怀所致,因此作诗以悼,诗题云《伏读二刘公瑞岩留题感事兴怀至于陨涕追次元韵偶成二篇》[4]294,诗云:
其一
谁将健笔写崖阴,想见当年抱膝吟。
缓带轻裘成昨梦,遗风馀烈到如今。
西山爽气看犹在,北阙精诚直自深。
故垒近闻新破竹,起公无路祇伤心。
其二
投绂归来卧赤城,家山无处不经行。
寒岩解榻梦应好,绝壁题诗语太清。
陈迹一朝成寂寞,灵台千古自虚明。
传来旧业荒芜尽,惭愧秋原宿草生。
二诗朱熹自注“(其一)右怀宝学公作。近闻西兵进取关陕,其帅即公旧部曲也。(其二)右怀病翁先生作。翁领崇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二诗皆以刘氏二人的瑞岩题诗生成,其中“抱膝吟、西山、犹在、灵台、秋原”之类,巧于假借,不做细节描述,刘氏二人之高风亮节便自诗中缓缓流出。由此可见,朱熹与刘氏二人感情深笃。正如《朱子可闻诗集》所述:“先生于两公,真性命交也。”[8]205
刘勉之,字致中,生于元祐六年(1091),卒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五十九岁,因“知不与秦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学者踵至,人号曰刘白水先生”[9]1395。刘勉之卒后,朱熹只有祭文悼亡。
三师之中,二刘早死,朱熹自谓事“籍溪先生为久”[5]13462。胡宪,生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卒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七十七岁,学者称籍溪先生。刘子翚和刘子勉均早死,朱熹自谓父亲病殁以后“于三君子之门皆尝得供洒扫之役,而其事先生为最久”[4]4505,按高令印考释,朱熹从学三人当在其十五岁时,即绍兴十四年(1144)[10]48。仅从时间上来看,其事胡宪达十八年之久,确为时间最久,故胡宪去世后,朱熹较为悲痛,在隆兴元年(1163)胡宪会葬于建阳县东田里时作诗以祭[4]295,诗云:
其一
夫子生名世,穷居几岁年。圣门虽力造,美质自天全。
乐道初辞币,忧时晚奏篇。行藏今已矣,心迹故超然。
其二
澹泊忘怀久,浑沦玩意深。箪瓢无改乐,山水自知音。
册府遗编在,丘原宰树阴。门人封马鬣,寒日共沾襟。
其三
先友多沦谢,唯公尚典刑。向来深缱绻,犹足慰飘零。
乔木摧霜干,长空没晓星。伤心遽如许,孤路转竛竮。
三诗作于隆兴元年胡宪会葬时,诗中回忆了胡宪的生平和高洁的品格,并且以自己当时达到的思想深度,对胡宪做了盖棺定论,抒发自己的深切缅怀。虽然朱熹事胡宪最久,但遍观朱熹关于对胡宪的论述文字,其中讲到自己跟随胡宪学习的体会少之又少,况且,朱熹在二十四岁以后,已经转随李侗学习,其思想和胡宪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提到朱熹的思想,就不能不提到朱熹的另一位老师李侗。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生于元祐九年(1093),殁于隆兴元年(1163),世称延平先生。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可谓深远。
绍兴二十三年,朱熹执父礼见李侗,与李侗谈论禅学。李侗对朱熹过去所学之禅学进行了大力批评。朱熹在此批评之后,深刻的体悟到了佛禅思想与圣门之学的区别,于是开始调整为学方向,对佛禅思想避而远之。同安任满后,朱熹多次拜见李侗,且频繁与李侗书信问答。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思想是在李侗的影响下逐渐完整的,故而对李侗的情感更为深厚一些。
隆兴元年(1163)李侗谢世,隆兴二年会葬,朱熹深感悲痛,写下两题五首诗,表达自己对李侗的深切追思,其中一题为《挽延平李先生三首》[4]308:
其一
河洛传心后,毫釐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
本本初无二,存存自不邪。谁知经济业,零落旧烟霞。
其二
闻道无馀事,穷居不计年。箪瓢浑谩与,风月自悠然。
洒落濂溪句,从容洛社篇。平生行乐地,今日但新阡。
其三
岐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
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
另一题为《用西林旧韵二首》[4]308:
其一
一自篮舆去不回,故山空锁旧池台。
伤心触目经行处,几度亲陪杖屦来。
其二
上疏归来空皂囊,未妨随意宿僧房。
旧题岁月那堪数,惭愧平生一瓣香。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首诗即叙述李侗得二程道统之正,次诗歌咏李侗的德行,末诗表达对失去李侗的痛心。而《用西林旧韵二首》乃是回忆求学于李侗时的过程,朱熹多次拜访李侗,每次问学都是寓居在西林院,在西林院有题诗,故而印象深刻。李侗殁后,回忆往昔,情不自已。
李侗的去世,带给朱熹莫大的伤痛,但朱熹并没有忘记李侗的教诲。他继承着李侗的学问,在理学的这条道路上走的越来越远。
前述几人,均对朱熹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而朱熹的政治抱负、理学实践和治理才能得到孝宗的赏识。庆元四年(1198),党禁正严,朱熹有感于自己命将不久,作《孝宗皇帝挽歌词(有序)》[4]535,一为悼孝宗皇帝,一为自悼,诗云:
阜陵发引,诏许近臣进挽歌辞。熹恭惟盛德大业不易形容,方将攄竭鄙思,以效万一,冥搜连日,才得四语,而忽被闵劳之诏,罢遣东归,遂不敢成章以进。杜门累年,每窃私恨,戊午之春,大病濒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无路补报,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谨因旧篇,续成十有六韵,略叙本末,以见孤臣亡状,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传心妙,文明抚运昌。乾坤归独御,日月要重光。
不值亡胡岁,何由复汉疆。遽移丹极仗,便上白云乡。
九有哀同切,孤臣泪特滂。讵因逢舜日,曾得厕周行。
但忆彤墀引,频趋黼坐旁。衮华叨假宠,缟素识通丧。
似有盐梅契,还嗟贝锦伤。戴盆惊委照,增秩待行香。
手疏摅丹悃,衡程发皂囊。神心应斗转,巽令亟风扬。
未答隆儒厚,俄闻脱蹝忙。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长。
内难开新主,遄归立右厢。因山方惨澹,去国又怆惶。
疾病今如许,形骸可自量。报恩宁复日,忍死续残章。
诗序交代了作诗的原由乃是“病濒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无路补报,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谨因旧篇,续成十有六韵,略叙本末,以见孤臣亡状,死不忘君之意云”,而诗中乃记述了孝宗皇帝的功绩和治理国家的才能,以及求贤若渴的心情,讲述了自己得到孝宗皇帝的赏识而不胜感激,表现出自己忠君爱国的思想。
可以这样说,三师及李侗,是朱熹理学思想的引路人,指导朱熹认清关于“体”与“用”的关系,而孝宗皇帝,则是让朱熹践行了“用”,故而让朱熹对于“体用”关系的思考更加深化。但正如《礼记·学记》所说的那样:“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11],在朱熹的成长道路上,朋友是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朋友的交往论学,让朱熹的思想更上一层楼,因此,朱熹的诗歌中,悼友人的诗歌数量最多最广泛。
三、悼友人
朱熹悼友人的诗歌比较复杂,原因在于其思想的复杂性。朱熹早期曾沉溺于佛禅,故与禅僧有来往,就算是后来成为理学大家之后,其对佛禅的态度依然暧昧,故朱熹的诗歌中不乏有追悼禅僧的诗歌。除此之外,在朱熹的学理的过程中,与其他学派的代表相互往来论辩,如陆九渊、张栻等,虽然主张各不相同,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故而,友人去世以后,朱熹也有诗作悼亡。因此,本节要分为两个部分来展开,一为悼禅僧之诗,一为悼学友之诗。
(一)悼禅僧
朱熹与佛禅的渊源可谓深厚,自十四岁在刘子翚处得见密庵宗主道谦之后,开始出入佛禅十余年,一直到二十四岁见李侗才开始转变为学的方向,而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朱熹主要跟随道谦学禅,因此,朱熹在此一时期深为学禅。在绍兴二十年(1150),朱熹回婺源扫祖墓,归闽时特地绕道江西德兴贵溪、铅山一路,目的是为了参学问禅。在贵溪,朱熹前去礼拜晋代高僧支道林的驻锡之地——昂山兴山寺,为之题额“昂山胜概”,凭吊圣迹,题诗一首“支公肯与世相违,故结高堂在翠微。青菜漫随流水去,黄彪时逐暮云归。乔林挂月猿来啸,幽草生风鸟自飞。八万妙门能测度,个中独露祖师机。”(《访昂山支公故址》)此中朱氏以“青菜漫随流水去,黄彪时逐暮云归”道出支公所言“色空”论和惜福惜劳之德操,非有深切体验是无法有此佳句的。[12]
绍兴二十二年(1152),道谦殁,朱熹有祭文。道谦殁后多年,淳熙八年(1181),朱熹与友人同游于仙洲山昼寒亭时,回忆起往昔在仙洲山的往来问禅于道谦及生活的林林总总,故而写下《游昼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韵赋诗得竹字》[4]432一诗,诗云: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椀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宵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
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沐。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篑今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匊。
后生更亹亹,俊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这里的道人即是道谦禅师,诗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回忆了在道谦处学禅的经过,表达出对道谦的敬仰和怀念,对仙洲山的怀念之情,而后半部分交代游历之始末。但此诗中不仅仅是表达怀念之情,此时的朱熹,刚从南康任上归来。在南康,朱熹努力的践行了儒家的治平之道,更加深刻地明白了儒家关怀的本质。诗中所谓“十年落尘土,尚幸不远复”乃是对自己青少年时期学禅的深刻反思,“不远复”乃是指自己迷途知返,回归本心。而这三字是刘子翚在病重时传授朱熹的为学之道。故而此诗有悼念之意,但更多的是体现朱熹对异端杂学的反思。而这种反思,一直延续到朱熹去世。
此后,直到庆元五年(1199),朱熹又做了一首悼僧人之诗,题为《香茶供养黄檗长老悟公故人之塔并以小诗见意二首》[4]540,诗云:
其一
摆手临行一寄声,故应离合未忘情。
炷香瀹茗知何处,十二峰前海月明。
其二
一别人间万事空,他年何处却相逢。
不须更话三生石,紫翠参天十二峰。
据《朱子可闻诗集》卷五载:二氏本先生所恶,其不绝方外友者,以交情也……正破释氏真性之常在。二诗虽是怀友悼亡之作,然诗中辨识佛氏之谬乃是正事。[12]849然除此之外,亦可作一简单讨论,党禁正严,生活心酸,希望能以禅家之理超脱,寻求一种精神寄托。
(二)悼学友
朱熹的一生结交了许多朋友,且与友人书信来往讨论理学的诸多问题,故友人去世后,朱熹多作诗以悼。因此,朱熹的悼理学之友的诗歌居多,故不一一详论,只选择几个对朱熹思想有重大影响的人为代表,如范如圭、罗博文、张栻、吕祖谦等人。
绍兴二十八年戊寅(1158),朱熹与范如圭、吴耕老等人展开了一场关于“一贯忠恕”问题的论辩。在现存资料中,这是朱熹最早的一次重要的书信论辩。[13]30而这次论辩也夯实了朱熹的理学基础。故而在绍兴三十年(1160),范如圭去世时,朱熹作诗以悼[4]282,诗云:
其一
献纳陪兴运,如公众所期。忧时最深切,信道不磷缁。
落落归来赋,匆匆殄瘁诗。菟裘当日计,宰木后人悲。
其二
先友多名士,存亡几许人。惟公且彊健,于我更情亲。
出处论心晚,音书枉诲频。素车今日会,谁与共伤神。
范如圭,与朱松交好,并且与朱熹讨论过理学问题,指导过朱熹,故而首诗回忆了范如圭的高洁品行,次诗表达了对范如圭去世的痛惜和对范如圭教诲的恩情的怀念。
隆兴元年(1163),李侗殁,朱熹跟随罗博文学习,罗博文与李侗交好,常求教于李侗。朱熹在其思想转变期间的学习情况,李侗常与罗博文书信往来,相互知晓。据李方子《紫阳年谱》载李侗与罗博文书信内容,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14]267云云,可知罗博文也指导朱熹为学。而在李侗谢世以后,朱熹问学于罗博文。据朱熹《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行状》载:“及先生殁,乃获从公游……自是入蜀,相望数千里,书问岁亦一再至,所以劝励从臾者殊厚。”[4]4525故而在罗博文殁后,朱熹作诗表达对罗博文的悼念[4]356,诗云:
其一
江阁论心地,重来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
但使穷新得,终当订旧讹。话言虽永隔,吾欲问沧波。
其二
行义追前辈,孤风凛一生。子平婚嫁了,元亮去留轻。
涪万无归棹,严杨有旧盟。空令同社客,生死痛交情。
罗博文卒于乾道四年(1168),此时乃是朱熹思想形成的阶段,对许多问题还处于一种迷蒙的状态,故而朱熹在诗中发出“此道竟如何”的悲叹。所以,此诗除了表达对罗博文逝世的悲伤,还体现出朱熹思想处于形成的阶段,但此时朱熹的思想已经逐渐开始明朗,因此在诗中也能看到其乐观的一面。
罗博文去世后,朱熹并没有停止探索理学的脚步,继续在李侗和罗博文的基础上,就二程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与其他理学家展开讨论。如与汪应辰讨论杨时之学的佛老问题,与魏掞之讨论《孟子集解》,与刘珙讨论《二程先生文集》。
上述诸人,虽与朱熹讨论理学问题,然诸人学理皆早于朱熹,故朱熹是抱着一种求学的态度。然与同辈人之讨论,朱熹的辩论就异常的激烈。在相互论辩往来中,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故而这些人去世时,朱熹也最为悲痛,诸如张栻、吕祖谦等人。
张栻,生于绍兴三年(1133),比朱熹小三岁,父张浚,师从胡宏。胡宏去世以后,成长为湖湘学派的领袖,隆兴元年(1163)应诏入都下,与朱熹相识。自此开始与朱熹往来论学。朱熹虽比张栻大三岁,但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易为多”[15]56,由此可见,张栻对朱熹思想的影响颇大。朱熹与张栻主要来往讨论了“中和”问题、胡宏《知言》的问题、“仁”的问题,而在这几次论辩之中,朱熹界定厘清了许多观念名词。可以说,朱熹理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与张栻的论辩,故而张栻的去世,对朱熹的打击是巨大的。
淳熙七年(1180),张栻卒,朱熹悲不能已,作有《祭张敬夫殿撰文》《又祭张敬夫殿撰文》《祭张敬夫城南祠文》《祭南轩墓文》[6]卷八十七。后来,朱熹在欢迎闽中故人自湖南任还乡时,在诗中悼念张栻[4]351,诗云:
军府资长算,家山辍胜游。故人千里别,归骑两年秋。
吊古宁忘恨,开尊且破愁。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
曲江楼,乃是张栻所造,楼成,朱熹为之作记。此诗乃是作于张栻新逝之时,诗中“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表达了对张栻深切的怀念,由此可见,张栻与朱熹之关系,非同寻常。
除了与张栻交好,朱熹也与吕祖谦交好。吕祖谦大概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在1156年任职于同安县时,曾因公事前往吕祖谦父亲任官的福州,得以认识吕祖谦,两入开始书信往来。在12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两人的书信往返激增。朱熹在1181年接到吕祖谦最后一封信不久后,获悉挚友去世的消息。他们的友谊维持得很久,比朱熹与张栻的关系还要长八年,这或许与吕祖谦的家在金华有关。金华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又在临安前往福建的路上,所以两人相处的机会自然比较多。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尚存104封,比写给其他人的都多。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则有67封流传下来,也比给其他人的信函多一倍有余。[18]105双方在书信中除讨论学术政治问题外,也谈及许多家庭事务。而吕祖谦对朱熹的影响也甚为巨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吕祖谦不仅是朱熹的学友,也是其理学成长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吕祖谦家学甚深,学问广博,故而思想比较驳杂,但这也是其优点,能够调和不同学派和理论之间的分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则是朱熹与陆九渊在鹅湖寺会面论辩时,吕祖谦从中斡旋,调和二人之间的矛盾,没有造成朱陆二人更激烈的纷争。由此可见,吕祖谦的道学影响力之大。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在与黄銖酬唱赠诗时有感而发,作《读子厚步月诗时方闻吕伯恭讣后数日赋此》、《次子厚秋怀韵》[4]499二诗以怀吕祖谦,诗云:
其一
晚步曲池上,西风吹我裳。仰观天宇阔,爱此明月光。
念我素心人,眇焉天一方。没者永乖隔,存者为参商。
飘零百岁期,寂寞幽鬓霜。还坐三太息,高林郁苍苍。
其二
秋风何方来,为我涤残暑。庭梧亦何与,索索终夜雨。
冥思感物变,念此离索苦。浩荡信莫量,幽纷那得睹。
丁年舍我去,憔悴故其所。廓落济时心,颓然复安取。
永怀平生友,梦想见眉宇。今晨枉秀句,烂若朝霞举。
去去同采芝,高轩坐凝伫。
首诗即云“没者永乖隔,存者为参商”,是为表达生离死别之痛。吕祖谦去世时,朱熹已经五十二岁,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故而有“飘零百岁期,寂寞幽鬓霜”之语,而吕祖谦的去世,让朱熹觉得为学路上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伙伴,故而“还坐三太息”。次诗“念此离索苦”不断深化生离死别之痛,遥想还在人世之时的林林种种,与现在对比,只能“梦想见眉宇”,而今晨吟咏的佳句,一个“枉”字便使之黯然失色。
除了上述诸诗之外,朱熹还有《挽汪端明三首》(卷六)、《挽刘枢密三首》(卷六)、《哭刘岳卿》(卷十)、《挽周侍郎二首》(卷十)、《挽陈检正庸二首》(卷十)、《挽吴给事三首》(卷八)等悼亡诗。[4]
四、结语
朱熹现存的悼亡诗,悼亡对象有亲人,有朋友,有引导其从学的老师,也有与其在朝中一同为官的幕僚。不管是亲眷还是师友,朱熹在其悼亡诗中都表达出了对亡人的深切思念。同时,诗中夹叙夹议的方式,将诗歌的叙事性与抒情性高度统一在一起,并且采用独特的理学意象,将情感准确表达的同时,也间接展示出自己的思想变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