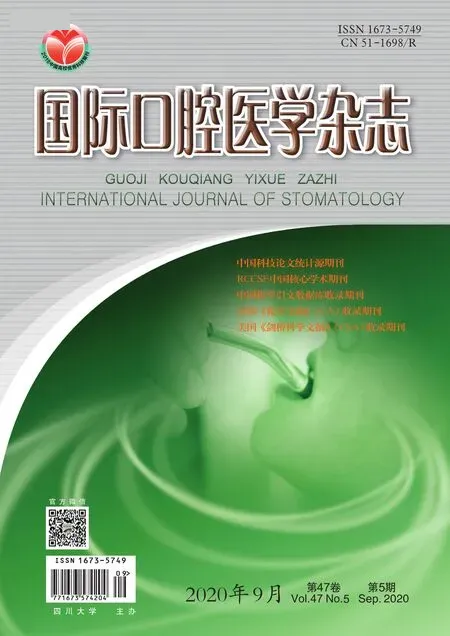龋病牙菌斑微生态研究进展
2020-03-05杨志雷刘宝盈
杨志雷 刘宝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科 郑州 450052
龋病是在以细菌为主的多种因素影响下,牙体硬组织发生慢性进行性破坏的一种疾病,人类长期的龋病防控努力依然没有减轻该疾病的全球负担[1]。在全球范围内,约有24.3亿人受到龋病不同程度的影响[2]。在中国,2015年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3]结果显示:5岁儿童乳牙患龋率为70.9%,12岁儿童恒牙患龋率为34.5%,35~44岁中年人患龋率为89.0%,65~74岁老年人患龋率为98.0%,且患龋情况呈现上升态势。
长期以来,基于传统致龋菌理论的防治手段并不能有效降低龋病的发病率,这不禁引发人们对龋病病因的再思考。近年来,口腔微生态失衡理论在龋病致病理论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菌斑学说的提出,为龋病的病因提供了新见解,进而对探索建立高效的龋病的防治策略指明了方向[4-5]。本文将对龋病牙菌斑微生态相关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龋病病因探索历程
一直以来,对龋病病因的探索从未停止。早在1890年,Miller便提出龋病是由细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而后“四联因素学说”进一步强调细菌是龋病发生的先决条件[6]。针对龋病的微生物因素,“特异性菌斑学说”和“非特异性菌斑学说”分别强调了单个致龋菌及整体微生物在龋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7-11],然而长期以来基于这两种学说的龋病防治策略并不能有效降低龋病的发病率,龋病病因有待进一步考证。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菌斑学说首次提出,将龋病病因的探索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12]。与此同时,伴随着以16S核糖体RNA(ribosomal RNA,rRNA)基因为基础的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成熟,为从菌群微生态方面探究龋病病因提供了可能,龋病微生态研究得以快速发展。2000年以来,新兴的“生态菌斑学说”越来越广泛获得认同[13],即将菌斑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其所表现出来的生物学行为。由此对细菌微生物在龋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升华到从整体菌群微生态平衡方面考量[14-15],支持龋病是一种多菌种感染性疾病,龋病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牙面菌斑生物膜的菌群微生态失衡,向产酸、耐酸的菌群倾斜所介导的。“生态菌斑学说”为龋病病因的研究及高效龋病防治策略的探索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2 龋病牙菌斑微生态
2.1 龋病牙菌斑微生态的组成
龋病牙菌斑微生态是由菌斑微生物群体、其所处环境及微生物在所处环境的功能活动组成。
研究[16-17]表明,在口腔中发现的微生物达700多种,这些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病毒、古生菌以及原生动物。由于个体生活的环境、年龄、遗传、生活方式具有差异,每个个体口腔所含微生物种类有所不同,平均每个个体含有100~200种微生物[18]。
龋病牙菌斑所处环境即菌斑所附着区的固有口腔环境,其环境特征包括温度、湿度、氧气条件、pH值、氧化还原电位、营养和代谢产物、局部解剖形态及组织结构等。除局部解剖形态及组织结构相对稳定外,其他环境特征随着个体及微生物的活动不断变化。
微生物群的功能活动即在菌斑环境下,微生物体进行的一系列转录、蛋白质合成、代谢与物种间交流等活动。菌群微生物的功能活动依赖于菌斑环境,又反作用于菌斑环境,影响其结构特征。
2.2 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的组成
菌斑微生物的组成具有个体、时间及空间特异性,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个体之间菌斑微生物具有显著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年龄、不同口腔部位及不同患病状态之间菌斑微生物同样存在显著差异[19-20]。因此,对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的阐述应建立在不同的年龄、患病状态等之上。
微生物多样性等是描述菌斑微生物组成常用的参数。所谓微生物多样性,即指在一个微生物集合群落中,众多不同类型微生物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的丰度,包含物种丰度和物种均匀度2个构件。物种丰度即群落中物种的数量,反映群落中所含物种种类的多少;物种均匀度则是指群落中物种种群量的大小,反映群落中各物种含量的相对比例及均匀程度。
为探寻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的规律,近年来“核心微生物”、“核心菌群”、“核心微生物组”等概念在众多研究[21-23]中被提及,其叫法不一,但均指在特定人群菌斑中共存的一些微生物,可能与健康或龋病存在一定的关系。而“龋病相关微生物”则是指定植在口腔中的微生物中与龋病的发生、发展有关的一些微生物,它们能够有规律地组合,并可能具备产酸、耐酸等特性[24]。
2.2.1 乳牙列期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 早期儿童龋(early childhood caries)是儿童最为常见的疾病,是该阶段乳牙龋病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发病率高、破坏性大、治疗难度高[25],受到广泛关注,对于儿童龋病的研究大部分均围绕其展开。
Ling等[26]通过焦磷酸测序技术,对60名3~6岁健康及患有早期儿童龋的儿童进行研究,在牙菌斑中共检测出属于10个菌门的200多个菌属,龋病与健康个体具有相同的8个主要菌门,即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梭杆菌门、螺旋体门和候选菌门TM7及SR1,但不同个体具有的各菌门及各菌属间的相对丰度不同;在龋病个体菌斑中,链球菌属、韦荣球菌属、放线菌属、颗粒链菌属、硫单胞菌属的相对丰度较高,与龋病的发生有关;与健康个体相比,龋病个体的物种丰度相对较低。而Teng等[27]则发现,来自共生菌的链球菌属、普雷沃氏菌属和细孔菌属在早期儿童龋患者中过度丰富,导致了龋病的发生,并且普雷沃氏菌属可以作为检测早期儿童龋的标志物,不受年龄的影响。
严重早期儿童龋(severe early childhood caries)病损更严重,相关研究[28-29]表明,相对于早期儿童龋,其菌斑微生物多样性进一步降低。在属水平上,除与早期儿童龋共有的链球菌属和放线菌属外,卟啉单胞菌属也被发现与严重早期儿童龋个体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从种水平上观察,变异链球菌、内氏放线菌、马氏棒状杆菌、口腔卟啉单胞菌、毛螺旋菌(G-3)、丙酸杆菌、月形单胞菌、福氏新月形单胞菌、消化链球菌、TM7、韦荣球菌(G-1)等在龋病个体中丰度增加,与龋病发生存在相关性。
为进一步明确在早期儿童龋发生、发展过程中菌斑微生物组成及结构的变化,研究者开始采用纵向研究进行探索。Xu等[30]对144名基线时健康的3岁儿童进行为期1年的纵向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个体的菌斑微生物物种组成未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显著变化,而龋病的发生却伴随着菌斑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降低、均匀度增加,物种间相互关系增强,联系更加紧密;与横断面研究结果一致,龋病菌斑与健康菌斑中“核心菌群”相似,即具有共同的主要菌门,但在龋病个体中链球菌属、普雷沃氏菌属等的相对丰度较高,被认为是龋相关菌种。然而有部分纵向研究[31-32]表明,随着儿童龋病的发生,虽然菌群的均匀度增加,但物种的丰度却保持相对稳定,健康与龋病个体之间物种多样性无显著差异。导致这种不一致结论出现可能的原因包括:不同研究所处地域不同、样本纳入标准不同、选择的微生物分析方法不同等。
2.2.2 替牙列期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 该时期儿童口腔具有特殊的局部环境,即混合牙列,决定了其不一样的微生物特征。Xu等[22]在40名6~8岁健康和患龋儿童的菌斑中检测到的物种属于18个菌门,较乳牙期的研究具有更丰富的物种组成;另外,发现放线菌属和链球菌属的丰度在龋病组明显高于健康组,被认为是龋病发生的相关“核心菌群”。然而另有研究[33]表明,对于替牙期儿童,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弯曲菌属、月形单胞菌属、类杆菌属、Parvimonas在龋活跃组具有更高的检出率。对该阶段的相关研究较少,仅存在少量散在报道,有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
2.2.3 年轻恒牙列期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 1项针对15~17岁青少年牙菌斑的研究[23]结果显示,在88名有龋及无龋青少年牙菌斑中共检测到401个物种,较之乳牙期和替牙期研究检测出的菌斑物种丰度进一步提高;相对于无龋组,龋病组具有更低的物种丰度。另外,该研究还发现,在未接受日常口腔治疗和预防措施的人群中,变异链球菌和表兄链球菌普遍存在,与龋病发生具有相关性,“核心微生物”的概念并不适用,因为龋病相关微生物并非是占据绝大多数的主要物种,除变异链球菌和表兄链球菌外,乳酸杆菌、放线菌、双歧杆菌等产酸菌均能参与龋病的发生,不同个体可具有不同产酸、耐酸菌的组合。
为探究不同龋坏程度菌斑微生物间组成的差异,Aas等[11]对年轻恒牙列期的完整釉质表面、龋白斑、浅牙本质龋及深牙本质龋的菌斑进行微生物测序,共发现属于8个菌门的197个菌属,其中变异链球菌、韦荣球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丙酸杆菌、放线菌属及奇异菌属在龋病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其他一些研究[34-35]结论相似;在不同龋损程度中,早期龋损的组成更为复杂,并拥有较高的放线菌水平,晚期龋损中乳酸杆菌水平更高;此外,在10%的龋病个体中并未发现变异链球菌,这说明变异链球菌并非导致龋病的唯一菌种,具有产酸、耐酸功能的微生物均有可能参与龋病的发生,不同龋病个体可具有不同龋相关微生物组成。
2.2.4 成年人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 He等[36]采集了37名有龋及无龋成年人牙菌斑,应用16S rRNA测序技术进行分析,龋病患者的微生物群落具有更高的均匀性和个体间变异,但其生态网络却相对简单,韦荣球菌属、放线菌属、颗粒链菌属、纤毛菌属、硫单胞菌属以及普雷沃氏菌属在龋病组具有更高的丰度,与龋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Xiao等[37]对健康和患有较低程度龋病(龋失补牙数DMFT≤4)、中等程度龋病(4<DMFT<8)及严重龋病(DMFT≥8)的成年人牙菌斑进行研究,共453个菌种被检测到,反映出物种丰度较年轻恒牙列期进一步提高;发现龋病个体微生物多样性较健康者低,且随着龋病严重程度的增加微生物多样性逐渐降低,这与其他研究[38-39]结果相一致,一些菌属(如奇异菌属、短小杆菌属、乳酸杆菌、优杆菌属、苍白杆菌属、假单胞菌属、根瘤菌属、拟杆菌属、石胡荽属、拟普雷沃氏菌属、弯曲菌属、巨型球菌属、支原体)在龋病个体中明显增多,被认为是龋病相关菌;还发现变异链球菌在深层牙本质龋中含量较釉质龋和龋白斑高,与其他相似研究[11]结果共同说明,同一个体在不同龋坏程度下可具有不同的微生物组成。另有研究[40-42]表明,对于不同程度的龋齿,含微生物种类最多的是开放性牙本质龋,其次是隐匿性牙本质龋,最少的是釉质龋。这些结果共同说明不同个体、不同程度龋齿含有不同微生物组成,不同菌群的组成能造成共同的结果,即龋病的发生。
2.2.5 老年人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 Jiang等[43]对老年人健康及龋病牙菌斑进行研究,发现在46位个体菌斑中共检测到305种微生物,其中疣微菌属、丛毛单胞菌属和巨型球菌属在龋病个体中丰度较高,被认为与老年人龋病的发生有关。
根面龋是老年人龋病主要的表现形式,因龋病发生部位特殊,其菌斑微生物的组成也具有特殊性。Preza等[44]在21例老年人根面龋中发现了8个菌门的245个菌种,其中变异链球菌、乳酸杆菌、放线菌、奇异菌、奥尔森菌、假细菌、丙酸杆菌和月形单胞菌均与老年人根面龋的发生有关;测序分析表明,不同个体之间微生物的组成具有显著差异,不同个体可以具有不同的龋病相关微生物组成,且龋病组的微生物多样性明显低于健康组。然而Chen等[45]利用454焦磷酸测序对42个健康及根面龋牙菌斑进行研究,发现老年根面龋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在生物量、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多样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基于菌群组成结构的β-多样性在两组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且根面龋组具有更高的变异性。
总体而言,龋病牙菌斑具有丰富的微生物组成,菌斑微生物多样性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多[38];龋病的发生伴随着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物种均匀度增加[23,28-29,36,38-39,44,46-49];龋坏程度越高,微生物多样性就越低[11,37-39]。不同个体及同一个体不同程度的龋坏可具有不同的龋病相关微生物组成和微生物多样性,除变异链球菌外,许多新发现菌种均被证明与龋病发生存在相关性,而变异链球菌并不是龋病发生必不可少的菌种,有些龋病个体并不含有变异链球菌,部分个体即使含有相对丰度也较低,仅达菌群总量的0.7%~1.6%[40-41]。健康与龋病菌群的主要区别在于:龋病发生过程中选择产酸与耐酸菌,而不是包括核心微生物组在内的主要微生物群[50]。龋病发生过程选择的产酸与耐酸菌是正常共生菌的一部分,即使在健康状况下其相对丰度非常低,但龋病的发生伴随着其相对丰度增高及酸敏感菌相对丰度的降低甚至消失[51]。微生物领域中很多物种均具有产酸、耐酸的能力,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口腔中检测到的可能的产酸、耐酸菌包括变异链球菌、表兄链球菌、乳酸杆菌、放线菌、双歧杆菌、奇异菌、丙酸杆菌和月形单胞菌等,其中只有变异链球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的产酸与耐酸能力得到明确验证,被认为是龋病最相关的产酸、耐酸菌[52],大量龋病相关的产酸、耐酸菌有待进一步开发。
以上这些对龋病相关微生物的研究证明了龋齿菌斑生物膜具有复杂的微生物组成,新的龋病相关微生物不断被发现,说明龋病相关微生物不仅限于变异链球菌、放线菌及乳酸杆菌等传统致龋菌,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菌斑学说的认识。然而截至目前,相关研究的人群主要集中在学龄期儿童、青少年以及成年人,部分年龄段存在欠缺,如替牙期儿童,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展。另外,各研究结果之间具有较高的异质性,一方面这可能取决于口腔微生态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研究在地域、人群、样本量、取样部位、取样方法、微生物分析方法、统计学分析等方面各有不同。
2.3 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的功能活动
微生物群落是一种功能单位,不同的微生物群落可以发挥相同的功能,同一种微生物在不同的环境或微生物群落中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17,53],因此对菌斑微生态的研究只讨论微生物的组成结构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探讨其功能活动特点,才能对菌斑微生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如前所述,不同龋病个体可以具有不同的龋病牙菌斑微生物组成,但均导致了共同的结果(即龋病)的发生,说明在龋病牙菌斑中进行着相似的功能活动。随着宏基因组学、宏转录组学、宏蛋白质组学及宏代谢组学的研究与应用,对龋病牙菌斑微生态中微生物的功能活动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正常情况下,菌斑微生态内各微生物间相互协调,保持动态平衡。菌斑内含有相关微生物如变异链球菌等,能够代谢碳水化合物,产生有机酸和细胞外多糖。乳酸是这些有机酸中酸性最强者,同时细胞外多糖能将有机酸限制在菌斑生物膜内,使菌斑内维持较低的pH水平[36,54]。与此同时,pH下降引起唾液链球菌等代谢菌斑内的精氨酸和尿素产生氨和二氧化碳;血链球菌等通过代谢产生过氧化氢;韦荣球菌等将乳酸代谢成较弱的酸;相关微生物将硝酸盐还原为亚硝酸盐,当pH低于5时,亚硝酸盐能够分解为一氧化氮,这些负反馈调节机制均能缓冲碳水化合物代谢产生的酸,维持菌斑内pH的稳定[17,19,55-57]。当大量频繁摄入碳水化合物或唾液的流速减低时,大量有机酸生成,超过了菌斑的缓冲能力,则导致pH持续降低,当pH低于5.5时,牙齿脱矿超过再矿化,龋齿形成[58-59]。
生态网络分析显示,龋病牙菌斑的生态网较健康菌斑简单,但其物种均匀度较健康组高;微生物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负性链接减少,表明物种间拮抗作用减低[30,36],这与Murray等[60]发现的龋病相关微生物间协同作用增强的结论相一致。
宏基因组研究[36]发现,有机酸合成相关基因(如编码1-磷酸果糖激酶和乳酸脱氢酶的基因)在龋齿菌斑中具有更高的丰度;而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基因在龋齿菌斑中的丰度较健康者低,该基因表达产物有利于氨基酸代谢产氨(如精氨酸代谢等)。研究[61]显示,龋病个体中编码单糖及双糖的基因组转录本是菌斑生物膜转录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在龋病牙菌斑中抗菌活性相关基因(编码细菌素等)、degS、degQ、胞质周应激反应相关基因(编码荚膜和细胞外多糖等)以及应激反应相关基因(编码杆菌肽等)的表达较健康组明显增加[62]。这些基因相对丰度的改变,表明龋病牙菌斑具有更强的代谢碳水化合物产酸能力及较弱的酸缓冲能力。
宏蛋白质组研究显示,当碳水化合物摄入后,糖酵解途径中的葡萄糖6-磷酸、果糖6-磷酸、果糖1,6-二磷酸、二羟基丙酮磷酸、丙酮酸盐以及戊糖磷酸通路中的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核酮糖5-磷酸、七磷酸脂糖7-磷酸、乙酰辅酶a均增加[63],表明糖代谢能力增加。然而特异性脲酶和精氨酸脱亚氨酶在龋齿菌斑中表达量较健康组低[55],说明龋病牙菌斑中碱性物质产生能力下降,酸缓冲能力降低。另外,在牙本质龋菌斑中检测到高表达的胶原酶和其他蛋白酶(如丝氨酸蛋白酶、糖蛋白蛋白酶、羧基末端蛋白酶和金属蛋白酶),可能在牙本质蛋白的降解中发挥重要作用[40]。
在宏代谢组方面,相对于健康组,龋病牙菌斑中存在较多的磷酸转移酶糖摄取系统,包括葡萄糖、半乳糖、乳糖、麦芽糖、葡萄糖苷、纤维二糖和N-乙酰半乳糖胺的摄取系统,另外与龋病发生呈正相关的还有大量双组分组氨酸激酶-反应调节系统的增加[64],这些代谢途径的增强均说明微生物代谢碳水化合物产酸能力增强。另外,与龋病伴发的还有抗生素耐药性系统和锌、锰、镍、钴等金属转运系统的增强[65-66],前者说明龋病牙菌斑具有更高的抗生素耐药性,而后者可能与菌斑破坏牙体组织有关。
综上可以看出,龋病牙菌斑生物膜不仅具有复杂的微生物组成,同时更进行着多样的功能活动。相关宏组学的研究展现了一个动态的菌斑世界,不仅说明了龋病牙菌斑内“都有谁”,还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整体上随着龋病的发生,菌斑微生物间协同作用增强,微生物代谢碳水化合物产酸的活动增加、产酸能力提高,同时微生物的抗生素耐药性也进一步上升;然而其代谢氨基酸等产碱的活动却在减弱,酸缓冲能力下降。但目前对龋病牙菌斑微生物功能活动的研究多数局限在糖及氨基酸的代谢上,更多龋病相关功能活动及研究有待进一步开发。
2.4 龋病牙菌斑的环境条件及其对菌斑微生物的影响
菌斑环境是菌斑微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微生物的功能活动均是在对应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口腔的温度约为37 ℃,pH值平均约为6.7,加之口腔潮湿的环境及唾液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来源,为菌斑微生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条件,然而这些环境特征可受各种因素影响而发生改变,从而对菌斑微生物产生影响[67-68]。
研究[58-59]表明,大量及频繁摄入碳水化合物引起酸产生增多,菌斑酸性环境持续时间增长,从而引起正常微生物群失调。Bradshaw等[69]通过体外研究表明,当菌斑pH值下降到5.5~4.5时,可能会使潜在的变异链球菌、乳酸杆菌等致龋物种富集,但此时奈瑟菌、核梭菌等与健康相关的物种相对不受影响;当pH进一步降低(pH<4.5)时,不仅可以增强龋病相关物种的竞争力,而且可以抑制非龋病相关物种的生长和代谢。Kianoush等[42]在研究牙本质龋不同龋坏深度菌斑pH与微生物的关系时发现,随着菌斑pH降低,菌斑微生物的多样性也在逐渐降低,其中拟杆菌门、梭杆菌门、变形菌门的优势逐渐减弱,放线菌门保持相对稳定,而厚壁菌门的优势却在不断上升,当pH将降至4.5时,厚壁菌门所占比例可达78%。程兴群等(第十三次全国老年口腔医学学术年会,武汉,2018)研究发现,在pH=6的酸性环境中,血链球菌、副血链球菌的H2O2合成不受影响,而戈登链球菌、齿链球菌等口腔链球菌能够利用丙酮酸节点的可塑性,调节H2O2合成,提高乳酸的产生,增强耐酸能力。
牙齿、舌、黏膜等不同口腔部位的菌斑生物膜具有不同的微生物组成[20,43,70],说明局部解剖形态及组织结构等均能对微生物产生影响。口腔内可因牙体缺损、充填修复等改变局部解剖形态,研究[71]显示修复材料表面的粗糙度与牙菌斑微生物的组成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中血液链球菌黏附量与修复体表面粗糙度呈正相关,一方面修复体表面越粗糙,可供微生物黏附的面积就越大;另一方面,修复体表面的沟纹成为微生物的避难所,使其免被清除。其次,修复体表面粗糙度增加,其表面的组成和极性发生改变,更有利于蛋白质的结合和细菌的黏附。
氧化还原电位是表征微生物生长状态的物理化学参数之一,在口腔中有很大的变化,这种波动有利于不同细菌群的生长[68],其中氧化还原活性气体(O2、H2和H2S)的pH值和浓度的变化被认为是控制微生物生长的主要因素[72]。
龋病牙菌斑环境的研究有利于对菌斑微生态更加全面的认识,以上研究结果共同说明菌斑环境对菌斑微生物的组成、结构及功能活动均有一定的影响,其中菌斑环境的酸性条件对菌斑微生物的影响尤为显著。然而目前龋病牙菌斑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微生物组成和功能上,很少涉及菌斑环境或仅为简单的概述,因此菌斑环境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待进行系统的研究。
3 小结与展望
复杂的微生物组成、多样的微生物功能活动及多变的菌斑环境共同构成了龋病牙菌斑微生态,宏基因相关组学的研究开启了对这个微生态系统的初步了解。目前相关研究尚存在部分研究人群(特别是替牙期儿童)欠缺、菌群功能活动探索局限、菌斑环境研究缺乏等问题,这既是现有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菌斑微生物、环境及微生物的功能活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未来对龋病牙菌斑微生态的研究应建立在三者之上。相信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和相关研究的开展,对龋病牙菌斑微生态将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高效的龋病防治措施也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