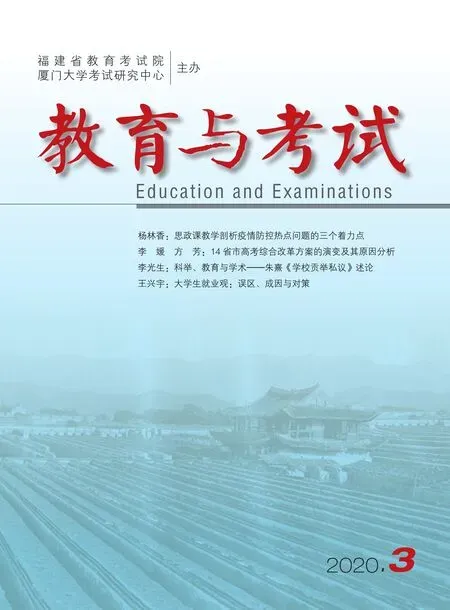述评左宗棠的科举观及实践
2020-03-04莫惠清
莫惠清
科举自创建以来,就成为官方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古代士子若要进入官僚政治体系,大多要经历科举,因此科举成为多数读书人走向仕途的必经之路。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度仍是清政府取士任官的根本制度。[1]在“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左宗棠亦欲通过科举这一“正途”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其仕途坎坷,三次会试均榜上无名,无疑是科举之路的失意者。正值晚清时期,科举制弊病百出,八股取士严重脱离实际,已难以选拔出适世之才。在此背景下,左宗棠推崇经世致用的理念,主张“轻科名,重实学”,认为读书并非“为科名计”,而在于“明理做人”;并指出科举实行的八股取士,严重阻碍了人才的发展,造成“人才日益庸下”的局面,但又深知科举对于国家选拔人才、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科举观既是科举认识行为的出发点,也是科举评价活动的归宿,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2]左宗棠的科举观体现在其实施的一系列有关科举、教育的实践上,他致力于实现陕甘分闱,建立甘肃贡院,凝聚知识分子的向心力,维系社会稳定;建立福州船政局,提倡开“艺科”,派遣留学生,培养和选拔实用人才,其中一些实践活动或成为晚清科举变革的先声。
一、左宗棠的科举经历:科举之路的失意者
要探究左宗棠的科举观,就要了解其科举经历。嘉庆十六年(1812年),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的“耕读世家”,其曾祖父是县学生员,祖父是国子监生,父亲是县学廪生,[3]1其先辈均为官学学生,是科举的储备人才。左宗棠的家庭同辈也都纷纷“入官学、赴科考”,在左宗棠八岁时,其长兄左宗棫入县学,次兄左宗植“科试高等,补廪膳生”。[3]4左宗植后来与左宗棠同年参加乡试,并中第一名举人。在此家庭背景下,左宗棠自幼便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文,以便日后应举。道光六年(1827年),15岁的左宗棠应童试,次年五月应府试,并获得第二名,后因家庭变故,左宗棠没有继续参加院试,故未取得参加乡试的“秀才”资格。道光十二年(1833年)左宗棠通过捐资成为监生,参加当年的乡试,其文章被同考官斥为“遗卷”,便不向主考官“荐阅”,本不能中举,适逢道光帝诞辰,特命搜阅“遗卷”,时任主考官的徐法绩,从五千份所遗的考卷中选取了六份,左宗棠居于首位。乡试发榜时,左宗棠中举人第十八名,其兄左宗植中第一名解元,兄弟双双中举,可谓佳话。而后左宗棠便与其兄左宗植一同赴京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不幸落第而归。由于科举竞争激烈,一次考上进士的人毕竟少数,左宗棠并未放弃科考,1835年再次赴京应试,因查明湖南多录取了一名,本在榜上最后一名的左宗棠被划去,他又一次与进士无缘,仅被取为“誊录”。左宗棠最后一次参加科考是在道光十七年(1838年),又以落第告终,[3]6-16左宗棠三次会试不中,最终没能取得进士科名,仅为举人出身。
左宗棠体会过“金榜题名”的喜悦,也尝过“名落孙山”的苦楚,他的科举经历是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科举生涯的真实写照,左宗棠也难摆脱“读书为应试”的科举效应。左宗棠一波三折的科举经历、崎岖不平的科举道路无疑对其科举观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左宗棠科举观的内容
(一)以“淡泊科名,讲求实学”为核心的科举观
左宗棠“轻科名、重实学”的思想是其科举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左宗棠认识读书与科名、科举与人才关系的思想渊源,更对其后来的科举实践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其形成与当时社会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及左宗棠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
经世致用是既与儒家传统相联系,又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思想。[4]300早在明末清初时,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儒家学者便大力提倡“通经致用”,掀起了实学之风。乾隆嘉庆年间,社会兴起了“考证、训诂”的考据之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也渐消沉。自乾隆中后期,清朝统治由盛转衰,道光年间,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统治危机,这使得不少有识之士重拾经世致用的理论,如魏源、龚自珍等,他们著书立说,以扬实学,再次掀起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热潮。左宗棠在此学术文化背景下,开始了自己的求学生涯。道光六年(1827年),15岁的左宗棠中府试第二名,但由于其双亲相继离世,他未能参加院试,科举之旅暂告一段落。此后,左宗棠居忧勉学,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经世致用之学中。期间,左宗棠阅读了魏源和贺长龄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深受启发,并在书上做了大量的批注,乃至“丹黄殆遍”。[3]7此外,他还读了顾炎武的《方舆纪要》以及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经世致用的学术著作,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与举业无关的“无用之书”,他却能潜心钻研,视若珍宝,实属难得。这体现出左宗棠不片面追求科名,而能够着眼于现实,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此可称得上是人潮涌动的科举路上的一股清流。道光十二年(1833年),左宗棠在经历第一次会试不第之后,虽有失意,但不以科场落第介怀,而是针砭时弊,关心时务,他在给乡试主考官的信中写道:“比者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恩,与吾夫子平生期许之殷。”[3]11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再次落榜的左宗棠决心不再参加科考,不沉迷于追求功名,而是归家研究农学,留意农事,遍览农书,探讨农耕生产,撰写了《广区田图说》,以宣扬区田法的实际效用。可见,左宗棠力求学以致用,将自己所学付诸实际,始终践行学用结合的治学理念。他在《与沈吉田书》中言:“仆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3]16这表达了其对于科名仕途的淡泊心态。
在家庭教育中,左宗棠并不将考取功名作为对儿子的期望,对传统观念中的登科及第乃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不以为然,“吾所望于儿孙者,耕田识字,无忝门风,不欲其俊达多能,亦不望其能文章取科第。”[5]16希望子孙能坚守“耕读家风”,在他看来,“科名得失无足重轻,弟向不以此介怀,惟儿辈立志读书,束身庠序,则观光逐队亦本分所宜,未便止之。”[5]7“科名亦有定数,”[5]16以一种“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态度看待科举,淡然处之。
左宗棠“淡泊科名,讲求实学”的思想,在当时专习举业的学风下是难能可贵的。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左宗棠积累了丰富的实学理论和经验,打下了深厚的地理学、农学、水利、军事等实学基础,这对其后来镇压太平军、进行洋务运动、收复国土、治理边疆等政治活动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左宗棠“轻科举,重实学”的科举观在其人生中的积极意义。
(二)科举与读书的关系:读书非为科名计
在科举与读书的关系上,左宗棠认为读书不是以科举为目的,读书的真正目的在于学会做人,做有用之人,即“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5]16
左宗棠对读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首先,在读书目的上,左宗棠认为要学以致用,非为科名计。他反对读书人沉迷举业,追名逐利,而忘却读书的根本在于“务实”。他在给其次子孝宽的信中称:“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5]71左宗棠将“致用”视为读书之根本,提倡读书明理,讲求实际。左宗棠奉命在外作战途中,得知其儿子孝威即将参加乡试,在家书中语重心长地讲道:“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致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5]16其次,在读书内容上,左宗棠主张多读圣贤之书、有用之书,而不是只专注八股应试之学,他熟读儒家经典且研读了大量的实用著作。左宗棠幼年时,其父左观澜开馆授徒,他随同学习,5岁就能诵读《论语》《孟子》,还喜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少年时期,左宗棠在应科举的同时,还悉心研读经世致用的著作。左宗棠17岁时便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若读到适用于当下、能够付诸实践的内容,便“另编存录之”。[3]7但他认为,科举的考试内容也需要多加练习,“读书不为科名,然八股、试贴、小楷亦初学必由之道,岂有读书人家子弟八股、试贴、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为佳子弟者?”[5]29在他看来,这是读书人应掌握的基本内容,并非只为应试而学。再次,在读书的方法上,左宗棠推崇“耕读家风”,务实为本。他以自己为例子教育子女恪守此读书之道,在给其长子孝威的信中写道“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5]16
正是因为这样的读书观,左宗棠仅将科举看作读书人的晋身之阶,而非读书的真正目的,他以为士人不必耗尽心血执着于此,而是要将“读书明理”“耕读务实”作为读书的志向和准则。但左宗棠对于科举还是抱理解态度的,他认为“读书非为科名计”的同时,还指出“然非科名不能自养,则其为科名而读书,亦人情也。”[5]7这是因为科举作为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将读书与做官捆绑在一起,左宗棠亦是科举的过来人,能够理解士子希望通过科举跻身官场,改变命运的想法,此乃人之常情也。左宗棠的儿子亦走过科举一途,他之所以支持儿子参加科考,并非让其追求富贵名利,而是以此激励其向上好学,“前因尔等不知好学,故尝以科名劝尔”[5]16“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5]66
左宗棠真知灼见的观点实则揭示了科举绑架读书人价值观的社会现状。他倡导读书人应抛开科举功名的利诱,志在“明理”“做人”,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左宗棠不陷入追名逐利的科举泥淖中,而能保持对读书纯粹的初心,这样的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三)科举与人才选拔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大清帝国日渐衰落,八股取士却达顶峰,士人思想禁锢,脱离实际,盲目追求科名而不问实事。科考内容不合时宜,科举考试所选拔的人才无裨国用,科举取士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有识之士纷纷质疑科举制。龚自珍认为八股取士令“天下之子弟,心术坏而义理锢”。[6]魏源亦对科举考试的内容提出批评:“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呜呼!天下果真无才哉?”[7]冯桂芬亦指出八股取士其“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8]可见,八股取士在当时被许多人诟病,无益于国家选拔有用之才。
左宗棠也认识到八股取士的弊端,即不利于造就经世致用的人才。他指出:“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5]17他反对读书人盲目追求功名的行为,质疑道:“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5]16这是因为科举的内容陈旧空洞,多为经义、八股文等形式化的空疏之学,不合时宜,而科举作为士人读书的引路灯和指挥棒,令多数士子醉心于研究应举之学,造成人才“日渐庸下”的局面。
左宗棠也不以科举功名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士人穷其一生,经历院试、乡试、会试,由生员、秀才、举人、进士到翰林,故世人普遍认为官入翰林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耀,进士优于举人,举人强于秀才,秀才胜过生员。左宗棠却摒弃这种传统的科举人才观,他“重科榜而轻甲榜,有以进士、翰林来谒者,往往为所揶揄”,而对会试落第归来的举人,却“仍以函招致署,宾主相得如初”。[9]
但左宗棠亦肯定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制度的合理性。首先,他对于“举业累人”这一说法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若科举士子能够研读圣贤之学,科举亦能选拔出有用的儒学人才。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左宗棠致信好友贺仲肃,写道“举业累人之说,此自为世俗科举之学沈滞于语言文字者尔。若夫心圣贤之学,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此则举其本而遂赅其末,自明以来儒先之达者由此其选,乌有所谓累邪?”[10]57其次,左宗棠认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在治学研究上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同治二年(1864年),他在与孝威的信中提及“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5]49
由此看来,左宗棠较为客观地看待科举制与人才选拔的关系,既不满科举考试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指出八股取士有碍于士子养成“经世致用”之才能,又并非一味指责科举贻误人才,他认为科举人才的学习能力是值得肯定的,科举亦能选拔出有用之才。
三、左宗棠的科举实践
(一)主张改革科考内容:设置“艺学”一科
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政府多次对外战争以失败告终之后,他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于是便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军事技术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艺学堂”,其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军事理论,培养洋务运动所需的新式人才。但“科举才是读书正途”的守旧思想已扎根在人们心中,加之清朝在划分官绅出身等级时,将艺局学生出身者列为第七等,排在进士、举人、贡生、扁生、监生、生员之后,[11]多数士子不愿放弃科举而就读于艺学堂,可见在科举之下创办新式学堂的艰难。为吸引学子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左宗棠在《艺局章程》中制订了一系列奖惩条例,如提高学堂毕业生的待遇,但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新式学堂出身之人的鄙夷态度。于是,1884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科”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以储人才”。[12]改革科举受到了顽固派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主张“止开艺科”,以“预防微渐”。[4]218针对反对者的谬论,左宗棠写下《艺学说帖》,提出中国要抵御外侮“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13]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的“艺学”应该为国人所知、所学。同时,左宗棠还奏表了如何将艺学纳入科举考试中的可行之法,指出:“惟登进之初,必先由学臣考取,录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后分发各海口效用差委,补署职官乃凭考核。……至于取中额数,以应考各数为断,大约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自强之策,因无有急于此者。”[4]218-219
显然,左宗棠认识到改革科举、培养新式人才对于振兴国家的重要性,其充分利用科举选拔人才的优势,试图将艺学纳入科举考试的一科,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和选拔新式人才,更有助于改变科举传统,打破长期以来儒家经典占据科场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讲,左宗棠设“艺考”这一主张开创了后来“改科举、废八股”的思想先河。此外,左宗棠还积极将西方先进知识引入课堂,福州船政局的课程体系中不仅有先进的造船技术和理论,还包括了外语、天文、数学、地理等近代科学知识。不仅如此,左宗棠还多次派遣留学生赴欧洲的英、德、法等国家学习,培养了一批为中国近代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进人才。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是左宗棠为弥补科举制难以选拔实用人才而采取的补救办法,成为除科举育人取才的重要途径,对推广新式学堂、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
(二)推动陕甘分闱,维系社会稳定
陕甘分闱在中国科举史上的意义举足轻重,这一历史壮举是由左宗棠极力促成的。陕甘分闱不仅是一个区域科举政策调整的问题,更是左宗棠西北兴学的主要措施之一,目的在于“转移风化,同我太平”。[14]原因在于在科举功名的巨大利诱下,士人一心向学,这使社会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且科考内容多为儒家经典,在以考促学的影响下,儒学所倡导的“忠君”思想深植于读书人心中。因此科举制起到了凝聚广大知识分子,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科举制也就成为统治阶级笼络人才、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早在乾隆时期,陕甘分闱就曾两次被朝臣提议,但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清朝授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深知甘肃重要的政治地理位置。在西北战乱之时,左宗棠除了应对战事,还主张“文教治边”,他认为“关陇要事,读书为急。”[10]84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正式提出陕甘分闱事宜,上奏朝廷道:“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更五六千里不等。”[15]故士子赴一次乡试要经历数月之久,路途艰辛,花费颇多,这对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而言无疑是沉重的负担,消磨了他们的科考热情,进而造成甘肃的应试人数不断减少,以至于大大少于陕西。次年,礼部下发文书,要求左宗棠欲实现乡试分闱,就先要确定陕甘两省的中额分配。于是,左宗棠又致力于增加甘肃乡试中举名额。由于陕西的考生多于甘肃,若分闱后将两省的总中举名额各分一半,对陕西而言是不公平的,为此,左宗棠提议“赏准甘肃增额九名,合计科分额二十一名,广额十名,则甘省可得四十名。”[16]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批准了陕甘分闱,并以当年的恩科乡试作为第一次分闱录取举人的开始。但对于“广额”的提议,清廷予以否决,左宗棠认为,捐输广额可以“作育士气”,因此他仍不放弃争取广额,于是在甘肃首次乡试的第二年,再次奏请增广额。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左宗棠此奏获批,此后,甘肃乡试的中额定为40名。至此,左宗棠主张的陕甘分闱终告完成。陕甘分闱有利于选拔人才,这是恢复战后甘肃治理颇有远见的策略。
在奏请陕甘分闱的同时,左宗棠还积极筹备建立甘肃贡院。甘肃的第一次乡试便在新建的甘肃贡院举行,由左宗棠亲自监考。据统计,当年参加此次乡试的举子近3000人,比分闱前明显增加。这充分证明了陕甘分闱不失为一次正确的历史选择,为甘肃士子参加科考提供便利,使更多的有识之士通过科举跻身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舞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对推动西北文教事业的发展、维系甘肃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深远、积极的作用。
综上,左宗棠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动荡社会下,饱经举业不济的挫折,并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促成了其对科举的深刻认识。左宗棠辩证、理性地认识科名与实学、科举与读书、科举与人才选拔之间的关系,这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开创意义的。“由于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7],左宗棠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官员,既批评科举时弊,也认识到科举对于选拔人才、维护统治的作用,因此他进行的一系列的科举实践,无疑是对百病缠身的取才制度的合理治疗,亦是晚清改革科举热潮中的有机组成。左宗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科举取士的优越性,但他未能摆脱封建主义的藩篱,仍将科举视为笼络人才、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没有提出废除科举的主张,其科举观亦具有封建主义的局限性。总体而言,左宗棠的科举观及实践在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下,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