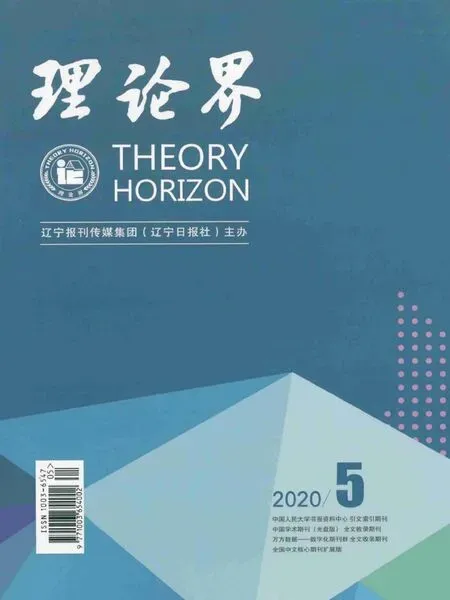爱的动机与爱的基础之反思
——基于弗洛姆《爱的艺术》的理论
2020-03-04吴必健
吴必健
一、爱的动机之反思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的孤独问题,而且它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爱既可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独立自由,又可以把人联结起来,从而摆脱孤独。爱有成熟和非成熟的形式之分。非成熟的爱是病态之爱,只有成熟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成熟的爱是一种给予的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主动性,用弗洛姆的话来描述这种主动性就是:“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得 取。”〔1〕(Love is primarily giving,not receiving.)
对此观点,需要注意“主要”二字,英文原文是primarily 一词。在国内的译版里,有两种译法,除了“主要”这译法外,李健鸣先生的译版为“首先”。〔2〕Primarily 一词既有“主要”的含义,也有“首先”的含义。但不管是“主要”还是“首先”,弗洛姆所强调的都是给予。但与此同时,也暗示了爱并不全部是给予,它也需要得取。要不然无需primarily 一词加以说明。换句话说,爱存在动机。如果爱是为了解决人类生存中的孤独问题,那么给予是不是会基于这个需要,或者说朝着这个目的行动呢?弗洛姆只说出人不能忍受孤独而活着,但他并未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似乎人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动物,不能忍受孤独是不言自明的。
事实上,人不能忍受孤独可以从人的正常生长过程中得到启示。每一个人存在的第一个家都是妈妈的子宫。在这个家里,人不需要给予就能得取,整个生命得到全方位的照顾。食物、温暖、安全感的无条件满足形成了人的最初体验,这种体验即使在人出生后还会持续好长一段时间。弗洛姆自己指出:“大多数八岁半到十岁的儿童的主要问题仍然是被爱,无条件的被人爱。”〔3〕这种体验往往没有给予,只有得取。它在人的生长最初阶段出现,使人对这种体验不但适应而且扎根,形成一种依恋。
随着人的成长,自我意识、理性、想象力的增强,人开始在依恋中向往独立自由。这需要一个健全的人格才能实现。如果说只知道要被爱,不懂得去爱,这是幼稚的,没有异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去爱就无需被爱,去给予就无需得取,更不意味着得取被爱不重要。事实上,被爱作为人之初的体验,是一个人后来要解决生存的孤独问题最普遍最根本的动机。人需要在自由的孤独中重新找回被爱的体验。哈佛大学瓦利恩特(George E.Vaillant)教授在《精神的进化》一书中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这种被爱在人心中的位置,想象一块石头投进池塘的情景,“最靠近核心的那一波涟漪代表的是孩童对母亲炽烈的、率性的情感依恋”。〔4〕爱之所以能作为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好解答,不仅仅因为爱能使人与人联合并保持独立自由,更重要的是爱能产生被爱,让人重新找回被爱的体验,满足被爱的需要。爱如果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不仅可以通过给予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得取来展现。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如果你的爱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对你的爱,如果你作为爱者用自己的生命表现没有使自己成为被爱者,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而这种爱就是不幸。”〔5〕不重视爱的得取是不切实际的,而且这将违背弗洛姆自己所倡导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弗洛姆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要尊重人性,满足人性的客观需求,从而使人的人格能够健全发展。被爱作为人之初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实是一种必需。C.S.路易斯在《四种爱》一书中把被爱称为需求之爱,他认为被爱不应该受贬,被爱的需求不是自私,而是人性的体现。“我们的整个存有就其本性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需要。”〔6〕任何人在生命之初都是非常脆弱的,极其需要无条件的照顾方可存活。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说,“人是所有动物中最无能的”,〔7〕并非一生下来就会走路说话,既不能像鸟天生能飞,也不像鱼天生能游,而且从出生到可以独立生活,比任何动物的时间都要长,都要复杂,都要麻烦。
既然如此,就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爱的动机。那就是婴儿的爱者,无条件地利他,给予爱,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或者应该先问,这种爱有没有动机。婴儿的爱者最常见的是其母亲。弗洛姆认为,母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母爱是否因此也无动机呢?莱布尼茨把爱定义为——“爱是倾向于从所爱对象的圆满、善或幸福中得到快乐。”〔8〕在莱布尼茨看来,那种只着眼于他人的快乐而不顾自己的快乐的爱是不存在的。“他人的快乐正是造成或毋宁说构成我们的快乐的,因为如果它不是以某种方式返回我们身上,我们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要脱离好处本身是不可能的。”〔9〕现在,以此细究母爱的无条件,似乎存有两个前提。第一,孩子在母亲的体内形成,本跟她是一体,爱孩子在某种意义上等于爱她自己。即使孩子出生后肉体与她分离,孩子作为她的产品,爱孩子就是珍爱自己的产品,希望自己的产品好,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等于爱她自己。第二,母爱是期待报答的。弗洛姆说:“母爱是福气,是安宁;它无需去获取,它也无需被报答。”〔10〕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需被报答是阶段性的,在孩子的早期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孩子长大以后可以实现。母亲作为一个人,她对孩子付出爱也需要孩子的爱,使自己成为被爱。因为一个母亲也有她本身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要不然她对孩子的爱将是一种不幸,既不能使孩子感恩,也无法使自己快乐。母爱所期待的报答可以说是滞后的,但并不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有句老话说:“积谷防肌,生子防老。”这种思想虽然略显功利,但却道出母爱的动机是存在的。最开始的无条件付出爱,或多或少是希望自己将来有一天可以得到照顾,实现被爱。
爱说到底,的确如弗洛姆所言,主要出于一个事实,就是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如果人与人无需建立任何关系也可以满足生存的需要,爱根本不重要。但是事实表明人一出生就需要有依靠、需要提供无条件的被爱才能活下来。为了生存和发展,人注定要与他人建立各种关系。被爱从广义上说,就是人在所处的社会中被接纳被认可被照顾。瓦利恩特教授指出:“人类依靠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存活,包括无条件的依恋、宽容、感恩和满含深情的眼神交流。”〔11〕那么在这种生存情境下,渴望被爱是很自然的需求。正因为存在这种需求,去爱去给予才有了意义。
弗洛姆认为,一个人是否在爱上乐于给予与他的性格密切相关。生产性性格的人会乐于在爱上给予,其动力在弗洛姆看来,是生命力和潜能的展现。“正是在给予的行为中,我体验到我的力量、我的财富、我的能力。这种提高生命力和潜能的体验使我充满了欢乐。”〔12〕但是这种爱如果不能换来被爱,是很难持久的。因为具有生产性性格的人也需要被爱,他也要解决生存问题。在解决生存问题上,没有人的需要是例外。一味地强调给予,不重视得取,是不符合人性的客观需求的。托马斯·阿奎那在谈论爱的问题中就指出:“每个人都以选择之爱来爱自己,从选择中他希望得到有益于自己的东西。”〔13〕(each loves self with the love of choice,in so far as from choice he wishes for something which will benefit himself.)
此外,不应该把被爱的理解简单化。被爱其实是存在三种不同情况的。第一种是,被爱没有被被爱者体验到。珍妮·西格尔(Jeanne Segal)在《感受爱》一书中就指出,被爱与感觉被爱不是一回事,有人关心自己和感觉到有人关心自己不是一回事。〔14〕假如爱一个人却没有令这个人感受到被爱,这种爱就等于没有爱。第二种是,被爱者体验到被爱,但不接受。虽然生产性性格有助于在爱上给予,但这并不意味着被给予者没有主动权和选择权。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爱者的爱不是被爱者所需时,被爱者可以选择不接受。爱的复杂性就在于此。爱并不是只要给予方做好就行的,它还需要接纳方配合。一味给予却没有被接受的爱,并不是成功的爱。第三种是,被爱者既体验到被爱,也接受爱者的爱。只有这种被爱才能使爱者的爱具有意义和价值。接受爱者的爱是对爱者的认可,这是爱者反过来成为被爱者的开始。
爱从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得取被爱既是一个人最早期的体验,也是一个人在生存与发展中最基本的需求。被爱的需求使爱具有意义,成为爱最广泛的动机。
二、爱的基础之反思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最基本的爱是博爱,它是所有形式之爱的基础。”〔15〕(The most fundamental kind of love,which underlies all types of love,is brotherly love.)博爱对弗洛姆来说,是对全人类的爱,没有排他性,是一种平等的爱。爱的问题不在于对象,因为爱是人的一种潜能,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这种态度的取向决定了一个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联系性,而决非只是和一个爱的对象相联系。”〔16〕
另一方面,在弗洛姆看来,爱作为对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要处理的是人生存本身的问题,而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爱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前提是爱人类,如果对人本身不感兴趣,没有感情,就不可能爱任何人。“爱所包含的基本意义与使被爱者体现出人类本质特性直接相关。因此,爱一个人就意味着爱人类。”〔17〕弗洛姆并不认为爱人类是因为对某个特殊人物的爱而产生的抽象概念,相反,爱人类是对某个特殊人物的爱之前提。但是弗洛姆又承认:“尽管一般来说,对人类的爱是在爱具体的个人时获得的。”〔18〕
如果博爱是爱某个人的前提,又必须通过爱某个人来实现,这将存在一个问题。任何一个人虽然都会具有人类的本质特征,但这并不表示每个个体的个性微不足道。爱某一个人推不出凡是人都爱,就像喜欢吃香蕉的人不一定就喜欢吃其他水果,尽管香蕉是水果。如果说博爱作为基本是因为人类本身就值得爱所以才会去爱某个人,这又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预设,人类本身就值得爱意味着作为人类的每个个体,其性质和表现都会是一样的,排斥了其他可能性。事实上,博爱作为对全人类的爱,无排他性,是爱的最高表现形式,这种爱必须消除个人偏见,而且不为个人利益所左右,才能做到。博爱是人类对彼此融合的一种美好愿望,但是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身上并不容易。凯瑟琳·奥德怀尔(Kathleen O’Dwyer) 在《我们可以学会如何爱吗?——弗洛姆〈爱的艺术〉探析》一文中指出:“所有人都值得爱,但我们爱的意愿和能力仅限于那些我们在个人层面上选择去了解和珍惜的人。”〔19〕(All persons are worthy of love but that our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love is limited to those whom we choose to know and cherish on a personal level.) 欧 文· 辛 格 (Irving Singer)更是在《爱情哲学》一书中质疑人与人融合的可能性,他指出:“我们,作为人类,在我们努力去爱别人的时候,不是像小溪流一样存在,而是作为不同的个体而存在。在人格上,我们没有融合,我们也不能融合。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在融合,你最终会成为你的亲密关系的现实中弄虚作假的一方。”〔20〕他还说:“渴望融合(很多人发现这是一种非常迷人的感觉)的一个后果就是,男人和女人在这个或者那个方面扭曲了自己。仅此一条就足以让我们怀疑,爱能否成为实际的融合。”〔21〕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这种特点带来的问题是不同,有不同就难免出现分歧,有分歧就难免会引发冲突,有冲突就难免会引起怨恨,有怨恨就会破坏爱,人与人之所以很多时候难以融合相爱,问题就在于此。
博爱如果是所有形式之爱的基础,那么性爱就是博爱发展出来的产物。博爱是没有排他性的,但性爱则是具有排他性的。弗洛姆认为,性爱只是在完全将自己和另一个人融合的意义上才是排他的,爱人类的本质没有变。问题是,性爱所排斥的就是第三方的人,如果爱人类是基础,又怎么会排斥呢?博爱是对全人类的爱,性爱是对某个人的爱,从爱人类发展到爱个人,反映了爱的范畴是从大到小发展的,这与博爱的精神背道而驰。就连弗洛姆自己也承认:“因为我们又都互有差别,因此,性爱要求某种特殊的、高度个性化的因素,这些因素只存在于一些人之间,而并非存在于所有人中间。”〔22〕这无意中说明,博爱作为各种形式之爱的基础,缺乏说服力。
如果博爱不是所有形式之爱的基础,那么什么才是所有形式之爱的基础呢?答案是:自爱。费尔巴哈认为爱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自爱,“存在,就意味着爱自己。”〔23〕自爱是一个人保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的存在以身体为载体,不管愿不愿意,都要把它照顾好才能生存下去。一个人如果不自爱,不是自残就是自灭。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爱就是一种必需。陈新汉教授在《自我评价论》一书中指出:“有我就必然有自爱,没有自爱也就没有人的生命本身。自爱由此就成为人生存的本体论根据。”〔24〕不自爱的人不可能好好地活,也不可能有能力爱别人,因为爱的主体本身都没有爱,就像一盏灯本身就没有亮,不可能照亮周围。因此,自爱又是能够爱别人的前提和基础。
伏尔泰说:“正是对我们自己的爱,助长了对他人的爱;正是由于我们互相的需要,我们对人类才有贡献;互相需要乃是一切商业的基础,乃是人与人之间的永恒的联系。”〔25〕这句话按照弗洛姆的理论可以理解为,因为人需要排解孤独感,人若爱自己,就要通过爱他人实现与他人融合,从而解决孤独问题。如果想被人爱,首先就要自爱。扬子曾有言:“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26〕罗伯特·霍尔登(Robert Holden)在《爱的能力》一书中指出:“自爱能让你更好地爱人及被爱,因为它们是同一种爱。我怎么爱自己与我怎么爱别人实则是同一个问题。”〔27〕这见解与弗洛姆的自爱观如出一辙,弗洛姆就认为爱己与爱人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在爱他人的身上会发现一种爱自己的态度。”〔28〕在弗洛姆看来,爱就根植于自身的能力中。
以自爱为爱的基础来解释各种形式的爱,会发现比博爱更加合理。不管爱是排他性的还是非排他性的,都需要以自爱为基础,没有自爱,任何形式的爱都无法体现。人必须爱自己,才有可能为其他形式的爱提供能量和动力。如果爱要通过主体给予体现出来,给予者自身就必须先有爱。爱人先学会爱己,只有懂得爱自己才能懂得爱别人。这道理孔子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9〕如果所有的爱是一列火车,自爱便是火车头。
对于自爱,弗洛姆已经澄清它不等于自私。作为爱的基础,还必须进一步说明,自爱也不同于自恋。自恋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弗洛伊德看来,自恋是力比多转向自身的结果。“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转向了自我,并因此产生了可以称之为自恋的态度。”〔30〕自恋所表现出来的是人对自身的迷恋,是一种自我满足。自恋的人兴趣点只在于自己,对非己的外部世界缺乏真正的兴趣。自爱并不如此。自爱的宗旨是生存与发展,是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之实现的内在要求。一个人只有爱自己,才会为自己创造价值,为自己实现幸福。此外,人有理性,也同样为自爱服务。斯宾诺莎就说:“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在于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寻求自己的利益。”〔31〕理性使人明白,个人的价值和幸福离不开所处社会的资源,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一个人如果爱自己,最好以爱对待所处的社会和他人,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成为被爱,从而更好地实现爱自己。
三、为爱找到根本的动力和正确的起点
必须说,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阐述的思想理论,都是积极且富有启发性的,尽管有些地方具有乌托邦之嫌。弗洛姆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一生所关注和想解决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弗洛姆之所以要写一本书专门对爱进行阐释,一方面就因为发现爱可以积极地解决人类生存的问题,使人走向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另一方面则因为人们对爱存有误解。《爱的艺术》开篇就指出爱是一门需要学习和实践的艺术,是人的潜能一种主动发挥,而不是被爱问题、对象问题或者坠入爱河的体验。在这种论调下,会提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得取”的观点就不足为奇。弗洛姆把爱看成是人的一种能力,可谓是对爱的本质一种深刻洞察。这种能力潜在于每个正常人的人格里。但这种能力并不是既成的,它需要学习和实践,并且要通过给予才能体现出来,否则就意味着不能爱。不能爱是一种能力缺失,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性格倾向问题。
根据弗洛姆的理论,人的性格倾向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非生产性性格的人由于缺乏生产性,很难轻易做到主动给予或者乐于给予。而生产性性格的人则会通过给予来展现自身的力量,并因此体验给予这种能力的快乐,赋予生命的意义。对弗洛姆来说,生产性性格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应该有的特征。弗洛姆指出:“人格的‘生产性取向’是一种基本态度,是人类在一切领域中的体验之关系的模式。”〔32〕只要一个人能在人格上得到正常发展,他就会形成生产性性格,有了生产性性格,他就会具有爱的能力,有了爱的能力,就会通过给予体现出来。
由此可知,弗洛姆所谓“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得取”之观点是爱在生产性性格上的表现。然而非生产性性格倾向的人同样存在,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们早已被以市场交易为主导的社会价值观所侵蚀,大部分的人都因此形成市场倾向的性格。正如弗洛姆自己指出爱在现代社会衰变就因为“现代人与他自己、与他的同类、与他的本质异化了。他被转变成一种商品;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他对自己生命力的体验变成一种必须带来最大回报的投资。”〔33〕在这样的社会里,提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得取”将很难被人们广泛接受并付诸实践。当爱成为一种交易时,不仅不利于个人幸福,也不利于建构一个健全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洛姆提出“爱主要是给予而不是得取”是对现代人的价值观进行积极引导的一种尝试。如果每个人都能意识到爱要从自身出发,培养性格的生产性,主动发挥爱的潜能,积极给予,那么人的许多问题都能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也因此变得美好。但问题就是,积极主动给予爱的动力何在?一种思想观念要被主动践行最好提供践行的动力。如果要让每个人都自愿践行,这种动力就应该是一种人性的客观需求。如果积极主动给予爱只是生产性性格的人的表现,那么对非生产性性格的人来说,像市场倾向性格的人,“没有得取的给予对他而言就是被欺骗”。〔34〕这样一来,非生产性性格的人也找不到要改造成生产性性格的理由和动力。结果最可能便是性格上缺乏生产性的人依然还是缺乏生产性,甚至因为异化问题的影响变本加厉。
现在,通过阐明得取被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为积极主动给予爱找到根本的动力。被爱需求根植于每个人的生存问题中,是每个人作为人存在能够正常生长不可或缺的需求,因此,从被爱需求出发爱才有持久强烈的动力。也许有人认为,以得取被爱为目的去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倘若没有得取被爱,去爱便失去动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不通过爱去实现被爱,也会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因为被爱的需求,再次强调,是要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因此,不管得取被爱是成功还是失败,并不会动摇被爱的需求。去爱的过程中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去爱是想得取被爱是不可取的。只有给予不求得取的爱也许存在,但是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说,绝对不是爱的常态。就算是上帝,也没有伟大到在爱上只给予而不求得取,圣经中的第一诫命,就是要人全心全意爱上帝。〔35〕(And thou shalt love the Lord thy God with all thy heart,and with all thy soul,and with all thy mind, and with all thy strength: this is first commandment.)爱要真正做到积极主动给予,就必须从被爱的需求里找到根本的动力。而实现被爱的最好方式就是去爱。因为去爱能促成相爱,相爱便能被爱。爱也只有在互相作用的关系中才会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从弗洛姆对爱的阐释中可以知道,爱不是外在于人的东西,它来自人的内在潜能。既然如此,爱就是由内往外发展的,因此要培养爱的能力,必须从学会自爱开始。在被爱需求的驱动下,自爱是爱的正确起点。自爱的人比不自爱的人更容易得取被爱。原因很明显,自爱的人会为自己积极生产爱,会主动践行得取被爱的最好方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自爱促进了在爱上的积极主动给予。
不管是谁,在爱的问题上,挫折与失败往往是难免的。有时问题也许出于爱者,有时也许在于爱的对象,有时也许两者都有问题。弗洛姆自己也承认,要成就爱并非易事。他在《爱的艺术》的序言里指出:“爱并不是一种任何人都能轻易纵享的感情,而不管人的成熟程度。”〔36〕换句话说,要成就爱,人要成熟。
学会自爱可以帮助人走向成熟。有些人在爱情上遭遇挫折和失败,会有自暴自弃甚至自杀的倾向。这都是不自爱或者说自爱程度过低的表现,同时暗示的是人格的不成熟。爱情上的挫折和失败固然让人难过,但是一个人如果学会自爱,决不会因此放弃自我,而是会努力克服困难。人就是凭着自爱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走向成熟的。
此外,爱以自爱为起点,既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也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做到的事情。这就保证了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向成熟并成就爱。也只有这样,爱作为人类生存问题的解答,才具有人道主义和现实实践的双重意义。■